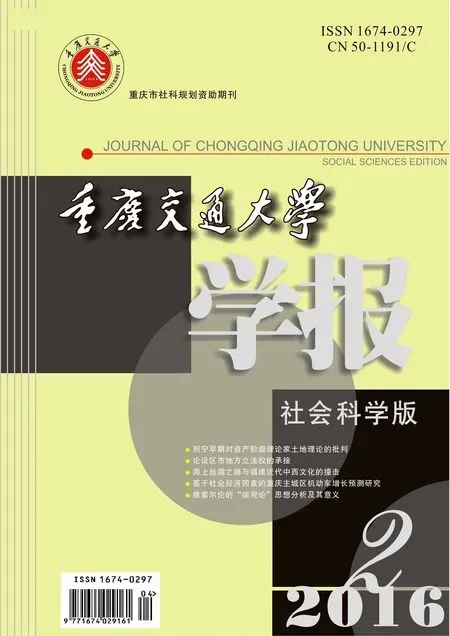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
金秋蓉(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州350007)
·历史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
金秋蓉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州350007)
摘 要: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盛行,留给福建的是开放的视野、海洋的精神、兼包并容的心态以及遍布世界的福建华工,这些因子成为福建文化嬗变的重要力量。当历史推进到某一特殊时刻,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福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任,自觉成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点。船政学堂是民族自救的一面旗帜,其培养出来的人才直接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铸就了福建近代中西文化的历史性撞击。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中西文化; 福建; 撞击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得天独厚的海域港口优势,既有宋元时期的世界名港泉州港,也有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长乐港以及明代后期重要贸易港口漳州月港。这些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处的地位,使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并对福建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迸发出嬗变的力量,让福建成为近代中外交流的撞击点,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继张骞出使西域(前139年—前119年)促成了陆上丝绸之路,汉武帝开辟了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经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到南印度的海上航线(前140年—前87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1]。
福建天然优良港口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海上贸易活动中表现一直很活跃。唐代泉州曾是中国南方四大贸易港之一,与交州、广州、扬州齐名。宋元时期,泉州港进入繁荣期,以泉州作为起点的海外贸易航线由东南亚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西岸[2]14。元朝政府鼓励发展海外贸易,让利于民,在泉州设市舶都转运司,极大促进了泉州的对外贸易活动。当时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多达40多个,以泉州为起点和终点的贸易航线有6条,泉州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1292年)中对当时Zaitun(即泉州港)商人云集、货物满仓的盛况有过仔细描述[3]。一直到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Ibn Batuta)还盛赞泉州为世界最大的港口[4]。泉州港的鼎盛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实行海禁,但郑和七次下西洋实际上把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一个高潮,把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红海乃至非州东海岸。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从福建长乐港出发,且在福建逗留的时间较长。福建对郑和下西洋的贡献颇多,郑和船队也很好地带动了福建的对外贸易交流,福州和泉州成为福建对外交流的窗口和前哨。
1567年,明朝政府准许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人海外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贸易船只在月港云集的盛况是这样的:“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2]16西班牙于1571年占领非律宾马尼拉之后,开辟了南海—马尼拉—南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漳州月港与菲律宾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572—1644年间,共有1086艘中国货船驶抵马尼拉,从月港运来的主要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这些货物从马尼拉运往阿卡普尔科,形成了以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转站、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福建—菲律宾—墨西哥海上丝绸之路[5]2。据记载,中国丝绸等商品约占18世纪末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可以说,明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较以往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福建一直都是重要的存在。这种以海上交通和交往为主的贸易活动,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直接影响了地域文化的形成。
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福建地域文化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福建经济贸易的发展,让泉州、福州、漳州的城市得以发展,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文化的传播,其对福建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海洋精神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
福建倚山临海,拥有宽广的海岸线,很早就会利用海上交通和海上资源发展经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更是大力开辟闽越海道,促进福建对外交通,使泉州港从原来广州、扬州大港的中转港口一跃成为直接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深入,福建的福州、漳州的月港逐渐成长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漫长的海岸线和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让福建人与海洋的对话来得直接而深刻,“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精神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
何为海洋精神?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读。在王东维先生看来,海洋精神是与特定时代相联系的海洋群体的思维方式、思想状态、内在品质以及价值追求的统一体。尤雪等认为,“海洋精神是海洋群体在涉海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并为海洋群体所认同的海洋认知、观念、思想、意识和心态,包含开放外向、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冒险和拼搏精神。”[6]笔者认为海洋精神是海洋群体在涉海活动中所形成的与海洋特性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和价值追求,开放与包容、冒险与拼搏是其精髓所在。
中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海洋国土面积达到300万平方公里,但一直定位为陆地国家,国人的思维范式受农耕文化影响极大,表现为踏实有余、创新冒险不足。对海洋仅停留在“兴渔盐之利和通舟楫之便”的初浅认知上,缺乏探索的热情;当倭寇等因素作为海洋的危险因子出现时,则简单地采取了海禁、闭关自守的政策,来逃避海洋文化的冲击,为明清国运的衰退埋下了祸根。
福建人则不然,福建人对海洋的态度是积极进取的。“靠海吃海”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海洋对他们意味着机遇、商机和财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与延伸,闽人身上的海洋文化特性越发明显。闽人“恬波涛,轻远游”,以泉州为起点和终点,福建人开通了“泉州—占城、泉州—三佛齐,泉州—印度及波斯湾,泉州—亚丁湾及东非,泉州—菲律宾古国麻逸、三屿等地,泉州—高丽、日本”等6条航线[5]140。闽人“利商舶”,茶叶、陶瓷、丝绸是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最主要商品。福建不仅大力推广种植茶叶,德化陶瓷与江西景德镇陶瓷齐名,宗元时期泉州出产的丝绸质量不逊京杭。闽人轻生死,郑和七次下西洋被誉为世界航海史的一次壮举,每次都在福建放洋,许多福建卫所的官兵随行,其中不少人后来就留在了南洋,与当地居民一起种植、经商,共同开发、建设南洋。
福建人这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精神让泉州港从原先的中转港成长为世界名港,而“开放与包容、冒险与拼搏”并存的海洋文化也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显性特征。
(二)多元文化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隐性特征
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与拓展,带给福建“市井十洲人”的繁荣盛况。闽人身上的海洋文化特性使其能更好地包容、吸收多样化的外来文化和舶来文化,并与福建本土文化相融相生。多元文化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隐性特征。
1.宗教文化多元化
福建本土文化以儒学为主,朱熹理学更是影响深远。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来泉州的穆斯林商贾与日俱增,伊斯兰教在泉州得到广泛传播。元朝时,泉州有清真寺院6~7所,因侨居泉州的穆斯林信徒(蕃客)较多,民间流传有“回半城”“半蒲街”的说法。明清天主教传入福建,与儒学为主的本土文化产生了碰撞。历史上有名的福建与中西礼仪之争爆发于福建,出现了“天儒相印”“天儒相斥”两派论点,福建是主战场。这场争论虽然最后以天主教被禁告终,期间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双向文化交流对福建影响很深。
2.移民文化的反哺
福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延伸和贸易港的繁荣,闽人敢于冒险、勇于开拓拼搏的海洋文化特性得到充分的显示。闽人如薄公英的种子纷纷在世界各地落地开花,成为旅居世界各地的侨民。据资料记载,福建的侨民自明代中叶开放海禁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福建华侨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自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海岸,北起缅甸,南到印度尼西亚群岛,都有福建侨民的足迹。这些侨民带去了中国的文化与技术,为当地经济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侨民从当地获取的财富与当地的文化交织在一起,又反哺福建地域文化,影响福建人的生活形态,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另外,贸易港给福建带来了众多的番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日本、阿拉伯人等),他们中不少人长期旅居福建,给福建人带去了迥然不同于本地文化的异域文化。
3.西学东渐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活动的途径,还是文化传播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给福建带来了西方传教士,他们在福建传播宗教的同时,积极输出西方文化和技术,成为福建西学东渐的主力军。1867年,传教士艾儒略撰写《西方答问》一书,以问答的形式介绍西方文化中的方方面面,上至天文、历法、地理、政治、经济,下至饮食、婚配、医药、风土人情等问题,满足了中国人对西方充满好奇的愿望,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欧洲的一个窗口。
多元化的宗教、移民文化的反哺以及西学东渐,这三种文化交织成福建地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它不同于海洋文明的鲜明与张扬,而是潜移默化为福建地域文化的底色。
三、福建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撞击点
清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凋零期:从1655年“无许片帆入海”的海禁,到1684年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开海禁,到1716年的南洋禁海令,再到1727年仅留广州一地通商,历经海禁、解禁并最终走向闭关锁国。
(一)海上丝绸之路赋予福建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自觉
闭关锁国是清朝这个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农业经济国家对海洋文明及其风险做出的防御性选择。这种选择并没能阻止西方列强侵略的脚步,反而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的距离。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逼迫清政府签下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对垒的结果才让国人幡然醒悟。痛定思痛,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谋求救国富民之策。
在这历史的特殊节点,福建成为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点: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诞生了船政学堂,培养出了大批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方面的仁人志士,全面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福建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缘于海上丝绸之路对福建地域文化长期浸淫之下的历史自觉选择。
(二)海上丝绸之路赋予福建中西文化碰撞的现实条件
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如前文分析,海洋文化和多元化是福建的地域文化特征,海洋文化的开放、自由与包容使福建人能客观地看待海洋文明;多元文化的背景让福建人更早接触到西方文化,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奠定了文化基础。如国学大师辜鸿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福建三杰”之一,其曾祖父是定居南洋的侨民,少年时代随养父到欧州读书,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全英式教育的中国人。这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成长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也让他有能力担负起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辜鸿铭一生以向西方彰明国粹、弘扬中华民族道德伦理为己任,行之终身,并为西方社会所推崇,把他看成是“中国文化之代表”。辜鸿铭的出现是福建海洋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明清福建华侨大量移居东南亚后产生的“文化效应”带来的深远影响。
1.睁眼看世界的清醒
福建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汇、撞击点,涌现了林则徐、徐继畲、丁拱辰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他们冷静、睿智,能客观看待海洋文明与国家目前的积弊,既不盲目崇洋,也不自卑自弃,而是积极学习西方长技,谋求富强之道。
林则徐即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认为只有正视现实,睁开眼睛了解西方,才能知其长而师之,以此寻找“制夷之策”和“富强之道”。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组织人才编篡《四洲志》,详尽地介绍了3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打破“天朝尽善尽美”的陈旧观念,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军事科学技术,提出建设一支有近代化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新式海军的主张。
徐继畲,福建布政史,因工作关系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西方史地知识,其编写的《瀛环志略》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概况的必读书目,帮助中国人较为准确地了解西方世界。
丁拱辰,福建晋江人,出洋经商多年,先后到过菲律宾、伊朗、阿拉伯等国家。回国后正赶上鸦片战争爆发,他便将多年研究积累的西洋武器资料整理成册,出版了《演炮图说》一书。该书详列西方各国炮式,吸取前代军器著作之精华,参照西洋先进武器之学说,中西结合,发展创造,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正确完整论述西洋武器和铸造洋式大炮的人。
在探索西方世界的问题上,林则徐等人的远见和胆识具有超越时代的清醒,开创了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先例,影响了一批开明志士积极著书立说、探索西方世界,从而一扫明末清初“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民学,两家遂成隔阂”的沉闷局面,一时间研究西学蔚然成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汪毛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等都是受此风气影响而问世的。
2.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担当
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在福建,很大程度上缘于福建船政学堂及其培养的人才。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办者左宗棠当年深得林则徐器重,亲授其治国良策。后来左宗棠创办船政学堂,选址在福建马尾,也算是历史的因缘际会。船政学堂创办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科技层面回应、对抗西方海上文明。从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富国富民”的洋务改革运动:办学堂、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的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他们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率先迈出了中国在造船、铁路、飞机、矿业、电灯、电信等行业的探索步伐,全面引领了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
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的摇篮。首任大臣沈葆桢修舰船、兴海防,培养海军人才,组建海军舰队,是中国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真正进入近代化技术操作层面的人,其海防思想及其平定台湾等海防实践在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史学家誉为“中国海军之父”。培养海军人才是船政学堂创办的初衷之一,从1866—1907年,福建船政学堂在这40多年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职业海军军官,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以及海军留学欧洲的先河。海军名将萨镇冰、叶祖珪、陈绍宽、黄钟瑛、程壁光等人都在中国海军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船政学堂因此被李鸿章称为海军的开山鼻祖,后人亦认为船政学堂“是中国防海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设校之基”[7]。
船政学堂成立、发展于新旧时代激烈碰撞的特殊历史时期,船政学堂的留学生制度让一批优秀毕业生得以到欧州留学深造,从而接触到西方文明。全新的西方文化为这些学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强烈冲击着他们的思想和灵魂。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担当让他们勇敢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严复、陈季同、王寿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詹天佑、王助、高鲁等人成为近代科技的垦荒者……福建成为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点。
综上所述,近代中西文化在福建交汇、碰撞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王爱虎.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和文献研究看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价值和意义[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1):1-14.
[2] 李金明.福建应发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J].福建理论学习,2014(6).
[3] 马可波罗游记[M].陈开俊,等译.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192.
[4] 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J].新东方,2015(1):10-15.
[5] 林金水.福建对外交流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6] 尤雪,王文雅,刘军立,等.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与海洋精神的互动关系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4-87.
[7] 金秋蓉.观澜船政文化[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63.
(责任编辑:张 璠)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Impact of Fujian i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JIN Qiurong
(Fujian Chuanzheng Communications College,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Fujian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the opening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popular,which makes Fujian a field of open vision,the spirit of the sea,and package and the mentality of capacity and Fujian Chinese workers all over the world.These factors become the important force of the change in Fujian culture.When history advances to a special moment,in the face of grave national disaster,Fujian bravely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task of history,consciously becomes the impact poin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of modern China.And the ship administration school is the national self-help banner.Its cultivated talents directly lea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It can be said that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improves the historic impact of Fujian i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maritime silk road;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Fujian;impact
中图分类号:G127.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6)02-0018-05
* 收稿日期:2015-12-03
作者简介:金秋蓉(1972—),女,福建闽侯人,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写作教学和船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