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女人
□离原
双面女人
□离原
正月里的一天,我们在朋友家喝酒,陈默的手机响了。我刚喂了一下,就传出一个女人声:你是不是总给他打啊?告诉你,郑国有老婆孩子,以后不许再给他打了。我忙说,不是我打的,是吴学用陈默手机打的。陈默上卫生间了……不等我说完,对方挂机了。
什么人哪!我说。大家正在酒兴上,都哈哈大笑。我很窝火,有种屈辱感,我真要找情人,也得找个比陈默优秀的。就是闭着眼睛,也找不到郑国头上呀。
我希望一辈子都不要见到这个女人。我说。
郑国在通达街开“一元利书店”,兼营卖书和租书。陈默和吴学总去。有时是晚饭后,有时吃完午饭就走了。后来回家越来越晚。我这才知道,他们是在那儿玩麻将。是吴学不小心说漏了。陈默知道我憎恶那玩意儿,要么说去送货,要么编别的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让你没法质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又知道玩的是十元二十元的小麻将,总不会赔房子赔地吧?总不能三根肠子空了两根半他还去玩吧?我懒得再跟他计较,只好安静下来。
一天晚饭后,我跟他去散步。白天越来越长了,六点钟,太阳还没落山。我们漫不经心地在街上走,不知不觉来到通达街。我突然意识到他想去哪儿了。果然,他用手指了指,撇下我,径直迈上台阶。台阶很高,我犹豫一下,还是尾随进去。
一阵欢笑涌过来。墙角临窗台的位置四个人在玩麻将。除了那女的,其他人我都认识。
去去去,让陈默玩。郑国对那女人说。
那天不让你再给郑国打电话的人就是她。吴学对我说。
又一阵大笑。刘洋离开麻将桌,红着脸走到我跟前:不好意思,这事儿他们都笑话我好几次了。
我笑了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环顾起四周来。屋子有三十多平方米,被书塞得满满的。三个书架依墙而立,中央摆着两个长桌拼成的书台。门口架子摆的是出租的书。
多好啊,什么时候都有书看。我说。
也不怎么看,有时候胡乱翻翻。她说。搬来一只塑料方凳,让我坐。
我想站一会儿,晚饭吃得太饱了。我说。
我也是。她说。然后用手揉了揉肚子。刘洋是个大轮廓的人。个子比我高些。头发烫成时兴的样子,随便耷落在肩上。穿着粉色的套头针织衫,衣服有些瘦,使腰部凸显出几道赘肉。下面穿着黑色的百褶裙,肉色的打底裤,黑色的鹿皮矮靴。
你们俩去公园吧。陈默说。一边哗啦啦地码着麻将牌。
我们俩每天都去公园绕圈儿,今天没去呢。陈默对他们说。
去吧,交流交流。郑国说。
尽管不愿意,我还是觉得这是最好的主意。
我们走得很慢。刘洋告诉我她从前开过发廊。在街上卖袜子、手套。被城管撵得到处跑。有一个女儿。在第三中学,初二了。我问哪个班。原来跟我儿子是同学。真是太好了。
我们在公园的甬道上走。空气暖烘烘的。偶尔一只刚苏醒的苍蝇从眼前飞过。杏花已经打骨朵。杨树垂挂着毛茸茸的虫子似的絮,用不了几天,它们就会变成嫩黄的叶子。路灯亮了起来。我们一会儿经过树林,一会儿经过湖泊。总之,我们的轨迹是圆的。
我讲生意上的一些事情,轻描淡写。主要听她说。当我们走第二圈时,她给我讲她的恋爱史。一个夏天的午后,就在这个公园,郑国握本《文友》出现在她的视野。俩人像这样围绕着湖水慢慢地走。他一米七左右。腰板挺直,肩膀宽厚,穿着白色的条格子上衣,从后面看,俨然是个帅哥。就是脸黑了点,眼睛小了点。以后,他们在柳树林坐下来。他给她翻书里面他写的一篇小说。那书现在还留着,和一个什么获奖证书放在一块儿,因为担心被虫子磕,每年都拿出来,吹吹风,晒晒太阳。但还是黄了,透着一股子霉味儿。那是他目前为止唯一发表的作品。每次都向女儿显摆:看,这是你老爸年轻时的大作。
一天晚上,他们去爬他家后面的山。那是秋天,庄稼都成熟了,空气里有股湿乎乎、香喷喷的味道。他们手拉手,穿过玉米地进了苹果园,七扭八歪地到了山脚下,找到那条上山的路线。他们轻松地抵达山顶。等他们坐下,俯瞰被皎洁的月光照得朦朦胧胧的万木及遥远处渺小的楼居,她感到一丝恐惧。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一种神秘感取代。郑国盘腿打坐,吹起箫。她一动不动地听着。起初,蛐蛐还叫,后来,它们也不叫了,仿佛也被那奇妙声吸引。在山顶,听一个男人月下吹箫,说起来就觉得浪漫。总之,那一切,都让她心醉神迷。
美好总是那么短暂。她说,看着天空。我有点累了,咱们坐一会儿吧。
行啊。我说。
前面正好有几块大石头,我们在那儿坐下来。
你认识舒雅吗?她说。
认识,她也写诗。
我也认识。她立刻用戒备的目光扫我一下,说,是在我结婚的那天晚上认识的。外人都走了,我们快要睡觉的时候,她去了,和一个挺高挺帅的男人。
哦。我说。看着她,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在屋子转了一圈,说祝郑国新婚幸福就走了。郑国跟我讲过,他追过她。刘洋看着湖水说。
我知道什么呢?那个叫舒雅的女人,其实,我与她,有过一面之交。仅此而已。
没有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也没有比你更适合我的男人。这是她曾经对陈默说的话。而她当时正跟陈默的一个哥儿们热恋呢。
她就那样,我说。她就是用那样的方式参加别人的婚礼。许多人的婚礼。
我当时很难受,她的影子一直留在我们家的屋子里了。刘洋说。
这个可怜的人,我一下能理解她了。
她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看,就是会打扮。刘洋仍带着醋意说。
她又离婚了。我说。捡起一小块石子扔进湖里。
真的?刘洋显出激动的样子。我看着她,心想,她是高兴呢还是惶恐呢?
谁先提出来的?
我也不清楚。
石头过于凉了,毕竟还没到能席地而坐的时候。从有健身器材那边的广场传来舞曲声,有人在学跳舞,我们起身,朝那儿走去。来,一边说着什么。口袋都鼓鼓的。刘洋迈着大步,脸上洋溢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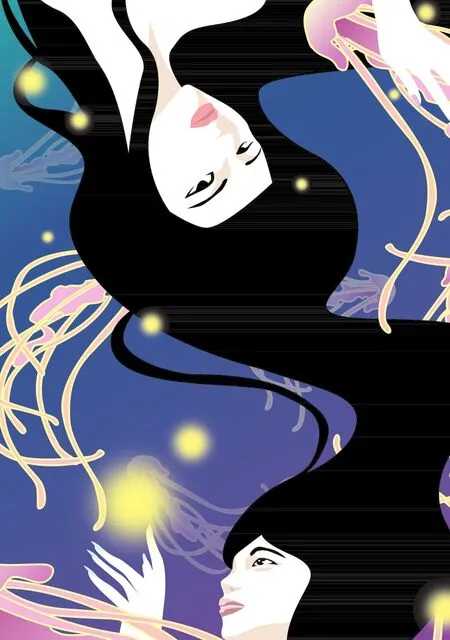
真好呀,真希望天天这样。刘洋的脸红扑扑的。一看到我们就这么说。
那天中午,两家子一起吃的饭。野菜饺子。酱汁野菜。野菜丸子。一桌纯绿色食品。反正我们能知道的做法,都做了。他们的女儿也来了,跟我儿子一起。吃完饭,两个孩子又一起去上学。
刘洋明显瘦了。六斤哪。她两手在腿上比划,在臀部比划,又在肚子上比划。如果在肉铺里买猪肉,得这么一大块呢。她两手做出环形,严肃地看着我。我乐得不行。
现在,她走路上了瘾,麻将也少玩了。
一天没走路,我觉得大腿都长锈了,你早点过来啊。她在电话里说。你儿子一去上晚自习,你就过来。
真那样,我碗筷都没洗就去找她了。远远看见书店门口有一帮人,好像在瞧什么热闹。出什么事了?我说。陈默没回答。他当然也不知道。他快走几步。我踏上第一个台阶时,他已经进屋了。从那里传出吵嚷声。房东老太太出现在门口。郑国扶着她,一边说,对,大姨你说得对,一点都没错。
隔壁就是房东家。她住在一楼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是她的小商店,卖烟酒糖茶之类,挂着“便民超市”的牌子。楼上住的是她儿子一家。老太太八十多了,头脑依旧清晰,仅仅腿脚有些不灵活。郑国一直扶她到门口,看着她推门进去,才折回来。
刘洋坐在那个被他们当做麻将桌的饭桌跟前,眼睛红红的,呆呆地瞪着窗外。
怎么啦?陈默说。摆出管闲事的样子。他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人。
不想租给我们啦。郑国说。叹一口长气。
房租到期啦?
没有。
是不是有人撬行?
不是。
那因为什么?
郑国走到门口,怕像被人听到似的,往外面瞧了瞧。那些看热闹的都走了。门口只有过路的人。
陈默在两个书架的交界处坐下来,那儿正好放着一把塑料椅子,跟刘洋我们俩成斜角。郑国从别处拖过一把椅子。两人面对面坐着。
说吧。陈默说。好像老师审问两个打架的小学生。
刘洋吸了吸鼻子,脸扭曲着往那边看一眼,又马上转过来。
嫌我们总吵架。郑国说。
又吵架了,因为什么呀?
问她吧。
怎么啦?嫂子?我说,摇着刘洋的一只胳膊。
她眯缝着眼睛,根本不理我。好像我们多此一举。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是两口子,永远是最亲密的人。得罪谁都不合适。外面多好啊,炎热正在消散,微凉的晚风拂动着珠帘,发出呼啦啦的声响。
要不,咱俩去公园吧?我试探着小声说。
她无动于衷。
郑国已经说起来,声音不大。有些话被我听到。原来妻子偷了丈夫的钱。他们家的钱从前由刘洋管。不知什么原因,改由郑国管了。有时,他不在店里,卖书的钱她也不上交。要也不给。她呢,买什么都跟他要钱。衣服了,青菜了,就是买个馒头也得回来取钱。她见钱就往自己身上装。竟然还偷上了,那两万块钱是准备进货的。
你恶人先告状啊,我的天。刘洋一听到对她不利的话立刻喊叫起来。
她跟我离心离德了。郑国咬着牙说,用了很大的劲儿。
是你跟我离心离德了。她说,站起来。我都不愿意跟外人说,既然这样,咱们就掰
这之后,我就常跟陈默去“一元利书店”了。
一般都是晚饭之后去。如果玩麻将的人够,刘洋我们俩就去公园转圈。人不够,她就得玩一会儿,等别的人来。我正好可以看看书。
郑国也许觉得过意不去,总给我沏一杯加方糖的咖啡。浓浓的一大杯。我找到喜欢的书,就在一个不易被打扰的角落坐下,读一会儿,再端起咖啡喝几口。咖啡是他弟弟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共两罐,一罐送了人。这罐呢,很快被我喝去一大截。
喝吧,反正也没人喝。刘洋说。以后都是她给我沏的。
如果早认识你,那罐就不送人了。她嘻嘻哈哈地说,一边甩着两只手。
他们玩他们的。我干我的。那些日子,我的鼻子周围始终萦绕着淡淡的苦香味儿。
我们两家还挖了一次野菜。
为这事,我准备了好几天。去早市买打包带编织的筐子。满市场只有一份,是个老太太卖的。我去三次才碰上。又在建材商店买两个小铁铲。我和刘洋商定在周三午前去。等陈默送货回来,我就给她打电话。
那天早晨,陈默去锻炼,打电话说在外面吃早饭了。之后,再也没回来。我一直以为他送货忙得没时间回家呢。十一点,我给他打电话。
喂,豆油没有了,你回来时买一桶。我说。
不行啊,我在碧水云天水库呢。他说。
啊?你跑得可真够远的。都跟谁?我说。一下火冒三丈。
跟爬山那帮人。他说。
我在屋子里乱转,憋着一肚子气。他一声不响去邻县了,我还傻兮兮地在家等。算今天,他三天没在家吃午饭了。一定出事了。吃午饭时,我喝了一杯半白酒,50度的,本地小作坊酿制。等儿子上学走,我哭起来。然后,锁上门,身体有些摇晃地朝通达街走去。
远远地,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从街对面开过来。使劲摁着喇叭。
你去哪儿?陈默说。从车窗探出脑袋。
你管得着吗?我说。继续往前走。
他从车里出来,挡在我面前。
回家。
你去玩吧,我再也不管了,晚上不回来都行。我大声吵嚷。有人停下来,看着我们。我才不在乎呢。
以后我不去了,就在家陪你。
谁信呢?我再也不信了。
走,回家。他用手拉我。
我一下就推开了。自己差点摔倒。
不用掖着藏着的,你痛快说,我给你腾地方。我带着哭腔说。
看你这出儿,怎么像刘洋呢?
我怎么像她了?我眼泪涌了出来。
他拦腰将我抱起,塞进车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们男人就这样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欺负我们女人。我晚上见到刘洋时说。她非常同意。我没把陈默说我像她的话告诉她。他已经向我保证,以后不说谎了,去什么地方都跟我请假。
第二天,我们老早动身,直奔十公里之外的郊区。郑国也关了店门。所有人都戴着遮阳帽。陈默把我们拉到一个叫马场村的尽头。那儿有一望无际的田地,刚播完种子。除了土,田垅干干净净,只有蚂蚁、蝴蝶、蜜蜂和苍蝇。我们在田埂上找到苣荬菜、婆婆丁、苦麻子、灰灰菜。一片片的。在一个仍蒙着塑料布的大棚跟前,采了许多扫帚苗。
起初四人还在一起,走着走着,就拆帮了。
陈默给郑国打电话:你们俩在哪儿谈情说爱呢?别耽误孩子们中午吃饭。
过好长一会儿,他俩从地势较凹处走出扯掰扯,郑国,你太没良心啦……
她坐在那儿,哭起来。
桌上有一卷卫生纸。我撕一块儿,递给她。她胡乱地在脸上抹着,一边擤鼻涕,让自己镇定下来。
这些年,他一直骗我,一直骗。我再不把养老保险交上,什么都没了……
你胡说八道。郑国说。他已经被她的气焰完全慑服了。
行了,你们俩。陈默不耐烦地说。
刘洋还在絮叨。
别说了,嫂子。一会儿房东又该过来了。我说。
这招挺管用。她真的安静下来。也许哭累了,她呆坐着,目光无精打采地落在某一处。
最后,陈默答应先借他们两万块钱周转。他说,保险早晚都得交,这事别再跟嫂子闹了。还有,我比你们小,不该说,可那也得说,和气生财,人家房东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郑国说他知道。
这事过去没几天,陈默的一个外地朋友来我家吃饭,喊郑国和吴学来作陪。我问郑国,他来这儿,刘洋是否知道。他说知道。吃饭时,他的手机响了。没接。之后,又响过两次,都没接。
午饭很快结束。那位朋友要去开什么会,郑国跟他一起走的。陈默和吴学坐在桌前喝茶。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辰,刚喝完酒,加上炎热,我头昏脑胀,只想快点将厨房收拾完,美美地睡一觉。
这时候,我听到了刘洋的说话声。
郑国呢?
走了,刚走的。陈默说。
我怎么没碰上?
你没碰上?
没有。
你怎么没碰上呢?陈默拉着长音说。我听出,他这时还没有急眼。接下来,就变了。
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刘洋用手拍着我家的桌子说,而且,拍了好几下。
我赶忙从厨房里出来,走到她跟前。
他不接你电话,管我屁事。陈默跳了起来。脸比刚才还红。我还从未见过他跟朋友的妻子发火。
郑国说你知道他来这儿。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
你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来这儿找呢?陈默说。
她叉着腰,气势汹汹的样子,猛然间像遭遇了重创,转身走出去。
我在后面,不知道说什么好,半天才听见自己说:嫂子,你不待会儿了?她那时已经走在一片热辣辣的阳光里。
真有病,把郑国拴在裤腰带上得了。陈默说。
吴学仍坐在那儿。我都没记得他发过声,也许咳嗽过吧。这时,他却说话了:你们说,郑国一没钱,二没权,长得也不帅,刘洋怎么就不放心呢?
都怨郑国,神秘兮兮的。我说。接电话不就没事了?
不是接不接电话的事,陈默仍带着气说。接了,她立刻就会关上店门,跑这儿来。郑国太了解他媳妇了。
嗯,肯定是这样。吴学说。
为证明其正确性,他讲起一件事。他请几个同行吃饭,也请了郑国。好让这几个老师跟他认识,也去他那儿买辅导材料。刘洋就不停地打电话,后来竟然跑到饭店来了。有个女老师,幸亏提前走了。要不,谁知道她会整出什么事?
给她丈夫一点空间,不行?陈默说。好像刘洋还在跟前听着似的。
怎么全怨刘洋呢?她之所以这样,直接原因就是郑国。我说。觉得应该替刘洋说句公道话。
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一说你们女人你就不爱听,你忘记她春天给你打电话的事啦?吴学故意说。
我才不是女权主义者呢,只是同情她。
我讲了她结婚当晚的事。一个女人给另一个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还有另外一件,有人买走一本书。郑国一下从外面的台阶跳起来,两脚交叉站在刘洋跟前。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啦?刘洋只顾跟我说话。过一会儿,她把那二十五元交给他。他立刻走了。原来这样啊。我心里一惊。他在外面坐着,耳朵却听着屋里,多累呀!
陈默,咱俩可是亲两口子,不能像他俩那样。我一边揉着头说。真累,我得睡一觉。
我也睡觉去了。陈默说。
你们两口子都去睡觉,我在这儿干什么?吴学假装不高兴地说。站了起来,伸着懒腰:我回家找我媳妇去了。
我们三天没去通达街。第四天,想去那儿看一看。
郑国蹲在书架跟前查库存。
我问刘洋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四点多钟就走了。也不接他的电话。
还没吃饭吧?陈默说。掏出一支烟递给他。
郑国说,可不。
正好,我晚上没喝酒,咱俩喝点。陈默说着走了出去。
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四处张望。天阴沉得厉害,一块乌云在头顶快速地变换着图案。远处的山和建筑灰蒙蒙的,雨似乎已经在那儿下了起来。
陈默从房东的超市拎了几瓶啤酒,又从隔壁的熟食店买了花生米、鸡翅和羊蹄。这时,刘洋出现了。用手揉着胸口。我问怎么啦,她说胸口痛。吃了许多中药,不管用。
吃饭啦,嫂子。陈默殷勤地说,声音极好听。如果他做错了什么,这就算道歉了呢。
胸口痛,吃不下。她说。
怎么回事?郑国,快带嫂子去医院看看吧?他说。
看了,医生也查不出什么毛病。郑国眨巴着眼睛,不以为然地说。
疼也得吃饭哪。他随后拉长调子说。
不吃。她说。你少惹我,比什么都强。
眼看又要吵架,我拽她出去散心。怕下雨,我们决定围绕着楼转一圈就行了。这样我们走上101国道。到处是汽车和汽车的尖叫声。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走完那段路,拐上左边人行道。转过一个弯儿,到了大西街。原来,这一条条街道,就是由楼给硬生生隔成的。
越来越没劲了,刘洋叹着气说。
我以为她指的是这样散步呢。
我想去南方。她说。
干什么去?
打工。当保姆每月还挣好几千呢。
我一直在琢磨她的话,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们很快回到书店。刚进门,雨就噼里啪啦下起来,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泥土味儿。两个男人还在喝。刘洋找了一把雨伞,出去了。
去哪儿?我说。
她好像没听到。
可能去厕所了。郑国说。
她胆子真大。我站在门口,往外面看。
雨又急又大,裹挟着可怕的风声,天更黑了。街上很快汇起一股股浑浊的河流,向着街道两侧的排水渠或凹洼处流去。上面漂着塑料袋、树枝、菜叶子。不远处,隐约听见风把门吹开,把什么东西重重地吹翻。
刘洋离开有一会儿了。公厕就在斜对着那座楼的后面。经过一个垃圾堆,再走一小段坑洼不平的土路,才能到。遇到这样的天,那段土路早已变成水路了。而且,没有电灯。厕所里面也没有。这样的坏天气,她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你是不是该给嫂子打个电话呀。我对郑国说。
没事。他说。
你看看外面的天。
郑国瞧了瞧,给她打电话。半天才打通:去哪儿啦?他说。一边从鼻孔里发出吭吭声。就像得了鼻炎似的。
我和陈默都看着他。
他关上手机,皱着眉说,去她姐家了。
刘洋的弟弟快结婚了。她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打算随五千块份子钱。她也想这么给。她就这么一个弟弟,自己在北京打拼得不错,有房有车,有自己的广告公司,父母也都接过去了。三十五岁,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北京女孩。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郑国说,
可她们都这么给呀。刘洋说。
人家都有钱。
人家有钱是人家老公能挣,你还好意思说呀?我都不好意思。
你咋也不能让我借钱给你弟弟随礼吧?
借点儿咋地?她说。一副不妥协的样子。再说,我弟弟也不在乎我这点钱,他最后得背着别人偷偷给拿回来,你还不了解他吗?说不定比咱们给的还多。
是那么回事吗?
咋不是那么回事?
反正不行。
他背过身去,开始整理书架上的书,位置颠倒的,给摆正。几本书,上面好像落了灰尘,他抽出来,拿着往另一只手上拍打,声音很大。他一本本地抽出来,一本本地拍打。她觉得他是故意的。一个老主顾来换书,那是一个十七八的学生,总看魔幻之类的书。他留下钱,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
她的心口痛又犯了。
行,依你,一千就一千。她最后说。
他没有回头,继续整理另一个书架。仿佛那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姐和我妹都是全家去,咱们也得全家去。她说。
我不去,你自己代表就行了。他挺轻松地说。好像他们说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去呢,不方便,说不定还要添什么乱。
她原来只担心他不让女儿去,没想到他也不去。他怎能这样对待她呢?她们家对他可不错。她每次回家,弟弟都要给他这个姐夫带吃的喝的,还有抽的烟。有时,给她买衣服也捎上姐夫一份儿。母亲呢,一见到她,总说,二闺女,缺啥跟妈说。
他怎能不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呢?那可是刘家最重要的事,也是有史以来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事。想一想,就知道场面会有多气派。男的、女的,都成双成对、喜气洋洋,她呢?她的肺都要气炸了。在这节骨眼上,郑国不出现,不是明目张胆和她作对吗?他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呢。
她离开书店,往家走。穿过一条叫长脖店的胡同。土路,既细又长。两旁的房子大多是等待拆迁的平房,零星几栋小二楼,破旧不堪。她从那儿走过,闻到空气里有炒菜的味道。是做晚饭的时间了。今天,她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反正女儿去奶奶家吃。走出胡同,横跨一条大街,拐上另一条胡同。走了一段上坡路,来到铁轨跟前。再往上走不远,就能看到她家的楼了。她改变了往常的路线,沿着铁轨往东走去。踩着一根根枕木,时快时慢。她忽然想到了女儿,她还没上大学呢。然后想到母亲。她还要为她们活呢。弟弟快结婚了,唉,她真蠢,多不吉利!
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天一广场跳舞呢。她对我说。
我给你打三遍了。我说。
听不着,音乐声太大了。她说。从铁路下来,我就想明白了,我还要潇洒地活呢。他爱去不去。
我是在半路遇上她的。她听到我的电话,就从天一广场往回走。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协商的?我说。
你说咋跟他协商吧?
也许,他怕耽误生意。去一天,回来一天,加上那天的婚礼,四天都不够,会不会影响信誉?我说。
那又怎样?
如果你俩都去,孩子怎么办?
也去呀。
你不怕她耽误学习?
她可就这么一个舅舅。她说。扭过头,朝我翻动着白眼珠子,嘴里发出嘶嘶声,气鼓鼓朝前疾走。
我追上她,用手拉她的胳膊。她一下躲开了。
真有意思,我们是朋友,你怎么不向着我说话,处处向着他呢?什么意思?她用一种恼怒得近乎绝望的声调说。
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这么说。我赶忙解释。别瞎想,回家我告诉陈默,劝劝郑国。
我又挎过她的胳膊。这次,她没躲,脸依旧绷着,眼睛看着别处。
过些日子,我就去南方。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为自己说的那几句话懊恼了很久。
那段时间,我们一有机会就劝郑国。
他终于同意去了。但是,他和女儿得比刘洋晚走一天。
刘洋走的那天下雨。其实,雨前两天就开始下了。
午后五点,陈默的手机响了,我立刻想到郑国。果然是。他让我们过去吃饭。他无法掩饰他的兴奋,嗓门很大。
行,好好喝点。陈默说。
是不是你也希望我离开你几天?等他关上手机我说。
那可不行。陈默一本正经地说。
还在下雨。陈默开车接上吴学,我们很快到了一元利书店。桌上摆满了酒菜,比刘洋在家时还丰富。多是买现成的凉菜。两盘热菜,是从饭店端来的,用保鲜膜盖着。他们俩直接坐到桌前,吴学还凑近那冒着缕缕热气的盘子前闻了闻,要不是隔着一层,他的鼻子保准粘上肉汁儿。
我饿了。吴学说。刚才还不饿呢。顺手抓起几粒油炸花生米塞进嘴。
郑国还在打电话。过一会儿,他说,天气不好,他们不来了。
每个人都倒了酒,开始不客气地吃喝。他们提议为郑国短暂的自由干杯。我不喝。他们笑起来,说那就为雨天干杯。背着我,几个人还是为郑国干了杯,好像很羡慕他。
何必认真呢。我似乎又听到陈默说。我总能不定时地听到这话。即使有时,他没说,甚至都没看我。
估计雨天不会有客人,郑国让我把门关上,因为我坐在最外面。
我走到门口,一个撑着伞的女人也来到门口。等她进来,收起雨伞,我心里发出一声惊呼,但我还是忍住了,试探着说,舒雅,是你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搂抱我,夸张地说:天哪,你开的店吗?
我说不是。
听到说话声,喝酒的几个人都朝这边张望,郑国已经直起身。舒雅?他说。舒雅,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陈默也从那边站起来,哈哈大笑,声音整条街都能听到。
她把滴着水珠的伞戳在门后,朝这几个男人快步走去,一边说,怎么是你们哪?我刚才在街上走,还在想,从前的朋友都去哪儿了呢?
他们握手。
陈默说,这是吴学。
两人握完手。
吴学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她端详着他,摇了摇头。她曾经是小城的名人呢。
是我媳妇认识你。吴学说,张甜甜。招待所的。
对不起,我真想不起来。她说。
没关系,见面肯定能认识。吴学说。
郑国这时请她坐下,跟大家一起喝。我从别处搬来凳子。
舒雅说,我吃过了。你们接着吃吧。
我给她找来干净的碗筷、酒杯。当着她的面,用温水消毒,之后,又反复冲洗。来吧,大家正好聊聊。她说她不喝酒。在家时,偶尔喝点儿葡萄酒。
郑国要出去买。舒雅不让。说,买也白买,反正我不喝。
于是,大家就那样坐着跟她聊。她不肯坐,站在我背后。我只好侧转身,瞧着她。她回来有些时候了,看她的妈咪。她是那样说的。儿子十二了,个子很高,这点不随他的父亲。房子很大呢。她回来,就剩保姆一人了。聊天是一问一答式的。我跟她不太熟。他们与她多年不见,也变得拘谨了。简单地了解彼此之后,相逢时的热情很快消失。她还那样站着,仿佛讲师面对着一群如饥似渴的学生。我觉得她倒很享受呢。
我在这儿影响你们,我得走了。她最后说。
她走到门口,举起右手,轻声细语地说,拜拜!我的朋友们。出了门,一步一步走下台阶,消失在夜雨中。那神态,仿佛还是十八岁。十多年过去,她发福了。
这以后,话题几乎围着她。吴学觉得她适合做演员,而不是别的。他给我们讲她失恋的事,是从他媳妇日记里偷看的。她总去招待所打电话。那时市长都没手机呢。一天,她又来了。打完电话,告诉张甜甜,她要结婚了。跟她的兵哥哥。其实,前一天,张甜甜还看到她的兵哥哥了呢,那个脸庞白白的高个子男人,在街上走,穿着结婚礼服,挽着新娘子的胳膊。咦,那不是舒雅的男朋友吗?她可真会说谎。
她自杀了一回,为这事。也许还是演戏。她吃完安眠药,在院子里,焚烧日记和诗。邻居看到烟,跑了过来,送她去医院洗胃。
她的故事,他们都能说出一堆来。她曾经迷倒一大片男人呢。陈默有所保留,我知道。
那天,我们一直喝到孩子们下晚辅导。雨还在下,比白天还猛了些。陈默拉着我们一起去学校。我儿子最先跑出来。郑国和他的女儿几乎是最后出来的。我们一直把他父女俩送到家门口。
路上,我说,可真巧啊,幸亏刘洋没在家。
还是出事了。
午后两点多钟,他们从火车站出来,打车,先送女儿去学校,然后是“一元利书店”,最后刘洋在家门口下了车。本来,她很快乐,还沉浸在回娘家的喜悦里。只是感觉有点疲惫,因为坐车的时间长了些。她想睡一会儿。就是从那时起,她的心情重新变得恶劣起来。她看见一条女内裤。不是她的。也不是女儿的。它明目张胆地躺在床上,像一张挑战书。她用手指勾起来,试图看得更仔细些。它是粉色的,有松紧带的地方全镶着花边。她骂了起来,都是跟性有关的话,很难听。
郑国当然矢口否认了。
她让他解释。他想了半天,说那有可能是对门的。他离家之前,把晾在楼道里、她洗的衣服都收进屋。别的都叠好,放进衣橱。这条内裤,反正她回来得穿,就扔在那儿了。她确实叮嘱过衣服的事。总下雨,她出门时,它们还没有干。
她希望这是真的。她也见过对门往这儿晾衣服。过道太窄了,要不,她也可以在她家那边拉一根绳子。那女的刚搬来不久,二十多岁,不怎么爱说话。男的一上班走,她也走了,抱着一个六七月大的男孩儿。
刘洋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敲门。没有回应。她一直留心听着。也许,他们回来了,她没听到。晚饭的时间,她又去敲那门,气嘟嘟的,用整个手掌拍。睡觉之前,她又去敲了一会儿。楼上的一个人走下来,以为出了什么事。
在那条裤衩没得到鉴定之前,就当是对门的。她跟郑国说。
当什么当,本来就是嘛。郑国说。
知道你还收进来,你傻呀?
以为是你的嘛。
我的?我的什么样你不认识?
他们背对着背睡了一宿。
直到翌日午后,对门的一家人才回来。那女人开门时很不高兴,看到裤衩,脸立刻红了,嘴巴张开着。不是我的呀,我的内衣可不往外边晾。似乎受到了羞辱,气愤地关了门。
以后的事,你就能猜到了。
那女的为什么不承认呢?可能真不是她的。也可能是,但被陌生人拿去,还是一个男的,放一段时间又送回来,心里不舒服,干脆不承认。这是极有可能的。可她不知道她的邻居为此炸开了锅。
会不会郑国真的做了什么节外生枝的事?
不可能。现在的人多现实啊。
他可以做出荒唐的事呀。比如,故意买条女人的裤衩,给刘洋看。生活既枯燥又压抑,他要制造些许神秘,好让在乎他的人醋海翻腾。我总觉得郑国就是那样的人。
他还嫌麻烦不够多吗?陈默说。
舒雅来的事,没人提。人人都知道,那是巧合。
你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你们书店喝酒,然后,去接你姑娘,我们一直看着他们进楼的。我跟刘洋说。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拉着脸,手在脖子上来回摸着,仿佛那儿很痒。说,我算看透了,什么朋友不朋友的呀,没用。
你咋这么说?我说。
她低着头,仿佛在合计该不该说。
我认识一个人,她想了一会儿说。她和她的朋友可好了。好得像一个人,可是,她却把人家的男朋友给抢了。原来呀,最好的朋友竟是敌人。
你什么意思?我不相信似的笑着说。你不是怀疑我吧?
没什么意思,就是打个比方。她扭脸看着别处,脸绷得像个铁饼。
打比方?我警惕起来。说,你有所指,我听得出来,你是指我吧?
什么都有可能。她说。
你这个人可真是的,我气得发抖。说,你真有病,去找个心理医生吧。
从那儿之后,我不再去“一元利书店”了。起初,陈默还去。慢慢地,也不去了。
不久,刘洋和一个男人在山上约会,被郑国捉住,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责任编辑 孙俊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