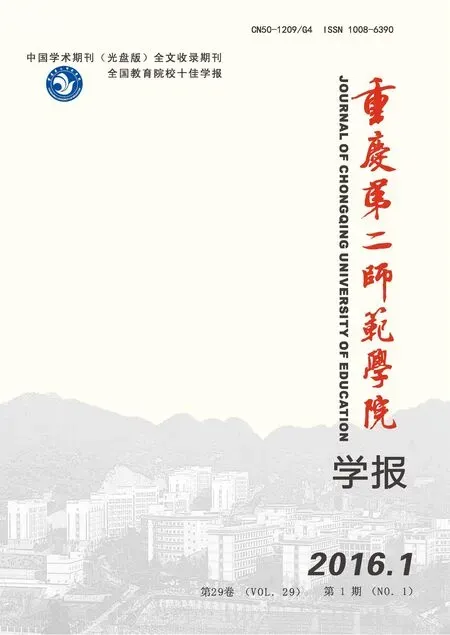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指导为文的构思法则
邓彩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论《文心雕龙》指导为文的构思法则
邓彩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文心雕龙》被称为“写作大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中对写作的构思、布局与言辞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经典的论述,影响绵延至今。本文从“命意谋篇”、“文心创造”、“率志委和”三个维度入手,论述了《文心雕龙》指导为文的构思法则。
关键词:《文心雕龙》;命意谋篇;文心创造;率志委和;构思法则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称誉《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鲁迅将《文心雕龙》提升到世界文论的高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并称:“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1]《文心雕龙》对文学本质的诠释与剖析,影响深远,“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隐括千古,包举宏纤,向为历代学人所重”[2],“而其中有些篇章和部分,却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诗文的起源,诗文作者的个性与风格……并且足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2]7特别是其关于写作的理论,更是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张少康指出,“文术论占据了《文心雕龙》全书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3],詹锳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张之象称其为“辞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驷”,这些都表明《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文章写作的古代文论巨著。刘勰不仅对文作了理论设定,还对文术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拟从文章构思的“命意谋篇”、“文心创造”与“率志委和”三个主要方面来论述《文心雕龙》指导为文的构思法则。
一、“物我对峙”之命意谋篇
“情以物兴……物以情睹”(《文心雕龙·诠赋》)①,“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虽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作为主体而首先发起的思想活动,但它的出发点却是“物”,并非是独立的形而上的内心活动,都有因由。感情随着自然景物或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文辞亦由情感的波动而生发。刘勰用《诗经》作比,“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文心雕龙·物色》)陆机所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4]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刘勰注意到情志的抒发、刻画在于“物”与“心”的“对峙与交融”。在描摹景物的气势、状貌,连缀比附景物的声色时,既能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委婉曲尽,又能应和听从内心的感触而斟酌定夺。作家创作的构思活动并非仅仅因“物”为基点而随物肆意游离,而是还需要一个作为主体的“我”的情感约束,“物”触发“我”,“我”驾驭“物”。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心物交融说”,突出了创作活动的审美主客关系。“随物宛转”与“与心徘徊”是不容分割的相反相成,它们是矛盾的统一体。王元化认为:“二语互文足义。气、貌、采、声四事,指的是自然的气象和形貌。写、图、属、附四字,则指作家的摹写与表现。”[5]94“‘随物宛转’是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为主,而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服从于客体。”“‘与心徘徊’却是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换言之,亦即以作为主体的作家思想活动为主,而用主体去锻炼,去改造,去征服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5]95关于写作实践构思之初的主体、客体,《人间词话》也有相应的论述。王国维提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6]这里的“境界”包括“物境”、“情境”、“意境”三种。尽管二者不可简单类比,但只要进一步探讨创作方法的理想和写实问题,就会归结到审美主客关系上来。“意境说”更加突出了“情”与“景”或者说“心”与“物”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也表明远在1500年前的刘勰对写作的深入钻研。“境界”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有所对应,但并非仅仅是“物”对应“物境”,“情”对应“情境”,它们之间是有交叉融会的,“情境”中不能不包含“物”,“物境”中不能没有“情”。“境界说”从物我关系上相互可通,所谓情境交融,物我双会。“有我之境”相当于“与心徘徊”、“物以情睹”,所以物境都染上了“我”的主观色彩。“无我之境”相当于“随物宛转”,所以分不清哪个是主观的“我”,哪个是客观的“物”。“心物交融说”与“境界说”都从各自角度阐明:自然外境对于作者具有独立性,它会以自有的状态、发展规律去约束、指引作家,从而消除作家的主观随意性,避免违反客观真实。“心物交融说”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补充、相反相成;“境界说”突出“有我”、“无我”,有“造境”、“写境”之分。作家不能因此屈从于物而不表现个性,而要“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从而达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的至境。
在这样一个心物对峙交融的互动过程中,创作主体由“物”、“心”而生发出创作的“意”。刘熙载《艺概》有言:“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7]苏轼也曾说过:“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龙·神思》),然后再“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文心雕龙·情采》),将胸中的感应传达于思想从而形诸笔端。作者在创作过程的构思环节,首先要明确所要表达的主旨,然后再根据主旨的条理来安排结构或做语言的调适,这样文章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这里命意的“意”是“情志”与“骨髓”的前身,是一篇文章最重要、最中心的主题。如果“意”没有确定,仅注意到文章的材料、结构、辞藻,都是本末倒置的。“意”具有统摄作用,构思是先决的。要思考如何突出作者旨意与主题的安排,要以凸显作者主题、意旨为中心,这又涉及“附会”之“杂而不越”的问题。王元化在《文心雕龙讲疏》中解释为:“所谓附会就是指作文的谋篇命意,布局结构之法。”[5]236在决定事料和章句的取舍时要做到“绳墨之外,美材既斫”(《文心雕龙·附会》)。“杂而不越”指的是关于如何处理艺术结构问题的一个概括。写作开始时“万途竞萌”,在写作过程中则要做到“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如同《总术》中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与《诠赋》中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揉而有本”,是同样的道理。艺术作品各部分必须适应一定的主旨、目的而配合一致。“四牡异力,而六辔如琴;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做文章的方法,取舍、长短的调理都要“统一步伐”。“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可见“附会”在写作中的重要意义。
刘勰概括的附会的规律作为在写作实践中命意谋篇必须遵循的法则,主要是从“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等方面来阐释的。“情志”与“事义”构成文章的思想内容,是灵魂和主干,统摄文章各部分、各细节。“辞采”与“宫商”构成文章的表现形式,从属于居于统帅地位的思想内容。
二、“杼轴献功”之文心创造
萧子显曾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8]构思与想象活动是文章写作的第一步,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刘勰在对“神思”进行定义时,主要突出了其为融合虚实、彼此不受时空限制的这么一种联想与想象活动,要以“并资博练”、“博而能一”为基础。“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舒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刘勰强调要奠定写作基础必须要在身心修养、根本功夫上进行突破。人在进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精神活动时需要一个安宁、恬适的环境,这样才能将作者“静朗如镜”或“风起云涌”的内心世界完美地展现出来。当然光有环境与心境是不够的,学识涵养与思辨能力都很重要,而且要能在研究、总结人生阅历中求得参透,从而得出某种适合自己的经验以运用到构思活动中,并吐纳出相应的语言文辞。
“若情数诡杂,体变纤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刘勰解释因文章体制与格调的变化而出现拙劣的文辞却包含精巧的义理,平庸的事料却折射新颖的含义这一事例时,用布与麻的关系来比附。学界对“杼轴献功”的理解仍然众说纷纭。黄侃先生认为:“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词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9]黄侃先生把刘勰原本是谈构思的“神思”理解为“修饰润色”,这一误解形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误导,如刘永济先生认为:“修改之功,为文家所不免, 亦文家之所难。舍人拙辞二语,陈义至确。盖孕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巧义于拙辞者,辞修而后巧义始出;萌新意于庸事者,察精而后新意始明。”[10]由此可见,刘永济先生对于黄侃将“杼轴献功”的内涵概括为修辞的说法是赞同的,并且将修饰又加深一步,认为是修改。周振甫先生与刘永济先生一脉相承,认为是修改的意思:“麻布同麻虽然都是麻,质地没有改变。但把麻织成麻布,就显出光彩,显得可贵了。这里显出修改的功效。”[11]詹锳先生则提出了新的看法:“‘杼轴献功’不仅是文字的锻炼,而且是形象酝酿变换的过程。”[12]但詹先生还是没有超越“修改”这个大范围。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发前人之所未发,不认同黄侃等人将“杼轴献功”的内涵概括为修辞的说法。王元化通过对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的剖析,认为“庸事萌新意,拙辞孕巧义”是想象活动在起作用。“‘布’是由‘麻’纺织而成的,两者质地相若,纤维组织不变,从这方面来看,‘布’并不贵于‘麻’,但经过纺织加工以后,就变成‘焕然乃珍’的成品了。没有‘麻’就纺不出‘布’,没有现实素材,就失去了想象活动的依据。就这一点来说,想象与现实的关系,正犹如‘布之于麻’的关系一样。”[5]123相比之前的龙学家,王元化对此的看法可谓是独树一帜的。然而对此进行怎样的理解才是真正恰当且最大限度符合刘勰本意的呢?左东岭站在文体意识与创作经验的高度,深刻地指出不管是“修饰”说或“想象”说,都是有失偏颇的。“刘勰当然是重视想象的,但却并非构思的全部”,“也就是说想象是在‘神思方运’的构思初始阶段的特征,所以接着才会说‘是以意受于思,言授于意。’也就是说构思存在着思绪万端与语言组织的两个阶段,其间的区别乃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王元化先生将第二阶段的语言组织混同于第一阶段的艺术想象,显然是不符合刘勰本意的。”左东岭进一步指出:“本段的意思是在强调作家构思的重要,他的作用就像将原料的‘麻’变成了漂亮的‘布’,尽管并没有添加什么,却使‘麻’产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便是作家‘文心’的巨大创造。然而,刘勰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很自然地动用了自己骈体文的创作经验。因为对仗与用典是骈体文构思中最具分量的环节……这里是说,如果不重视构思,那么即使有了‘巧义’也有可能被‘拙辞’所伤害,即使有了‘新意’也可能被‘庸事’所拖累,从而写不出漂亮的文章”。笔者赞成左东岭先生的看法,“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弄清每一时代与作家的创作情况,取得丰富的写作经验, 然后再辨析针对这些经验所提出的文学问题与理论范畴,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诠释那些文学理论经典。”[13]由“布”到“麻”的这个过程是刘勰想强调的经历文心的巨大创造所呈现的状态,并非是修饰或者单纯意义的想象。
三、“虚静养气”之“率志委和”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文心雕龙》明确指出写作构思时的“关键”与“枢机”问题。关于“志气”的理解,学界也有不同看法。“王元化在郭晋稀的‘精气和意志’,赵仲邑的‘意志力量’,陆侃如、牟世金的‘情志和气质’基础上提出‘志气’泛指情志与气质。”[14]笔者认为“志气”可理解为人在构思时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是在“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长期积累下,结合形诸笔端时的情绪、激情等形成的。刘勰注意到文思通达、滞塞与否就取决于这种“精神状态”的统摄(《文心雕龙·神思》)。在写作实践中,文思并非总是如“泉涌”般一气呵成的顺畅,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与波折。“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陆机从艺术想象的视角出发,首先发现了文思有顺畅、滞塞的情况,但却没有提出怎样去解决这一问题。“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15]作者的思想感情是文章的孕育点,如果没有了思想感情的鼓动与牵发,就会出现“关键”堵塞,精神隐遁起来,而不能展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构思活动了。可见,恰当的思想感情对文章写作的重要性。“神与物游”是“志气统其关键”的先决条件,只有“神”与“物”相互之间达到了高度的融合,思想感情才能由此产生,写作构思才能得以进行。
当写作构思展开时,“思”、“意”、“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微妙,它们衔接紧密相得益彰的时候则文思畅达,它们不能相互合作而疏远背离的时候则文思滞塞。“养心秉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刘勰认为,基于这种情况,要培养良好的心智并掌握写作的方法是不必要苦思冥想的;美好文思的酝酿只要遵循构思的准则后也无须过度操劳。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的。《文赋》中的“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勰在《养气》篇中说“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这也就是同样的道理,其论述了在为文运思中如何使文思顺畅,并认为学会“养气”是关键,“养气”可使得文思畅通、灵感迸发,可以扫除构思过程中的阻碍与滞塞。“率志委和”是指在写作构思的过程中,顺应作者的心情,从容不迫、恬静自然的一种精神状态。如果在神志不清明,心态不平和的状态下过分地钻研思虑,则会精神疲倦而气力衰弱。“优柔适会”指的是从容不迫地顺着情思后悠然宽舒、轻松畅漾地适应情会和时机。关于“养气”,涉及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临文时的一种精神状态,如同《神思》中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舒瀹五脏,澡雪精神”,“养心秉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也就是与“率志委和”、“优柔适会”相对应。《养气》篇最后概括的“水停以鉴,火静而朗”就是“虚静”的一种表现。水波不兴才能观照事物,火焰纯青才能格外明朗。要“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才能达到“率志委和”、“优柔适会”的境地。其次,长期的才、学、识等各方面的修养是“养气”所必需的,也就是之前所说的“积学”、“储宝”、“研阅”、“驯致”等过程。写作构思不管是快速或者迟缓,不管是容易或者困难,都要在广博的学识与卓越的才能的基础上进行。
《系辞上》云:“精气万物,游魄力变。”“气”这个概念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早已出现,且非常重要。《文心雕龙》中多次出现“文”源于“气”的说法,如《原道》篇将“人文”与天地未分时混沌的元气联系起来。刘勰关于“气”的认识是在王充自然元气论和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论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被刘勰称为“巨文”的《论衡》之纪妖篇有言:“刻为文,言为辞。辞之与文,一实也。民刻文,气发言。民之与气,一性也。”[16]这里直指文是由气所产生出来的,把人刻写文字与气发出言辞相提并论,同构了气与人的性质。《养气》篇中也可清楚地看到对王充的提及。《论衡·气寿》中说:“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16]29王充认为,人的生死与他所持有的气的强弱有莫大关系,气是生命力的表现。黄侃认为“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字不同。”[9]247笔者认为,刘勰继承了王充“气”之于“人”的同构性,其《养气篇》所言的“气”指的是“血气”、“精气”,是一种内在精神气质,也可以说是“志气”、“才气”。《文心雕龙·体性》篇言:“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可见刘勰的“气”是包含多重成分的复杂的“气”。居于体内可言“血气”、“志气”,形之于外可成“才气”、“文气”、“辞气”,要涵养的不仅是生理方面的血精之气,更重要的是形成于体内而由内散发出来的施注于文章中的个人独特的精神、文风气质。刘勰“文气”的才行方面更多的是受曹丕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17]《文心雕龙》体性篇将“血气”、“志气”、“文气”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气”通过确定的“言辞”表现出来。这就是刘勰主张“养气”的原因了。
注释:
①本文所引刘勰原文,均出自王志彬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之《文心雕龙》。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卷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0.
[2]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
[3]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0.
[4]张怀瑾.文赋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20.
[5]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6]王国维.人间词话[M].施议对,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2.
[7]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7.
[8]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7.
[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3.
[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93.
[11]周振甫.周振甫讲文心雕龙[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2.
[1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06.
[13]左东岭.文体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J].文学遗产,2014(2):43-49.
[14]周春来.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创作论辨要[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15]张怀瑾.文赋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46.
[16]王充.论衡校释[M].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929.
[1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93-1100.
[责任编辑于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1-0076-04
作者简介:邓彩霞(1991- ),女,四川广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