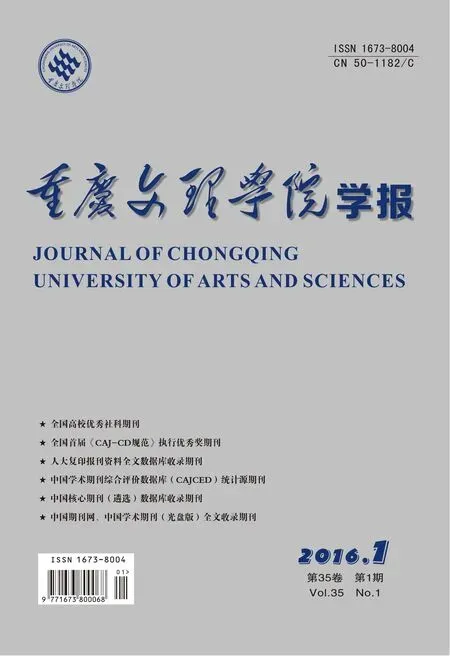夏敬观词学贡献论略
兰石洪(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夏敬观词学贡献论略
兰石洪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摘要】夏敬观是晚近词坛著名的词学活动家,其词学活动及词学著述对晚近词坛影响甚大。夏氏词学理论及时总结了他和当时同仁词创作的经验,又是晚近词坛继承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应用小学方法研究词学整理词籍开创词学研究新格局的重要创获。夏氏词论不仅深化了清代以来对词格律韵调的研究,而且深化了对唐五代北宋词的研究,还总结和深化了历代关于“词”“学”关系命题的思考和探讨,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夏敬观;词学理论;词学贡献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号盥人、吷庵,江西新建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至宣统元年(1909)三月,任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监督。民国八年(1919)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民国十三年(1924)弃官,移居上海,以书画著述终老。夏敬观的学问涉及经史、音韵、训诂、诗词、书画等多个领域,一生著述近40种。
夏敬观被龙榆生在《晚近词风之转变》中推为“晚近词坛之领袖作家”之一[1]419,其词学活动及词学著述对晚近词坛影响甚大。夏敬观早年师从著名经学家皮锡瑞,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同乡前辈著名词人文廷式学词,1909年3月,夏敬观入江苏巡抚陈启泰幕,在苏州与朱祖谋、郑文焯等前辈词人唱和论词。1929年以后,夏敬观词学活动主要是组织词社、协办词学刊物等社会活动以及进行词籍整理与研究。夏氏的词学活动既贯连了晚近词坛著名词人的创作活动,又贯连了著名词学家的学术活动。
其词学著述则有《词调溯源》(1931)《词调索引》(1942),《词律拾遗补》(1941,)《戈顺卿〈词林正韵〉纠正》(1943),《二晏词选注》(1931),《忍古楼词话》(1933 ),《汇辑宋人词话》(1942),《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1942),《五代词话》《吷庵词评》(1985葛渭君辑录,载《词学》第五辑)等10种。前四种是关于词声调韵律的著作;第五种为普及性读本;第六种记载与夏氏交往过的词人资料,对我们了解晚近词坛颇具文献价值;第七种为宋人词话资料的辑录与汇编;第八种是对况周颐《蕙风词话》的评论;第九、十种为夏氏对唐五代宋词的评点与批评。夏敬观的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后三种著述及相关的词籍序跋中。夏氏的词学理论及时总结了他和当时同仁词创作的经验,又是晚近词坛继承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应用小学方法研究词学整理词籍开创词学研究新格局的重要创获,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深化了清代以来对词格律韵调的研究
夏氏在清代万树、戈载等人词律词韵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层,将词的格律韵调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其《词律拾遗补》在清代万树《词律》、杜文澜《词律补遗》、徐立本《词律拾遗》三书之外,又根据相关宋词资料补出一百五十余调,二百余体。其《戈顺卿〈词林正韵〉纠正》纠正了堪称宋代以来词韵整理和研究最为善本的《词林正韵》的某些错误。戈载的《词林正韵》是词家必备之书,被词林奉为枕中鸿宝,晚晴词论家如况周颐、朱祖谋、蒋兆兰等人均极为推崇,汪辟疆《词籍举要》评云:“戈载之书,区部析韵,条理秩然,道咸以降,几定一尊”[2]876。夏敬观重新对唐宋词用韵进行排比归纳,他在《戈顺卿〈词林正韵〉纠正》纠正了戈韵所归纳的词韵与唐五代宋词实际用韵殊未尽合之处的错误,他指出戈韵将“以灰贿太(半)队废”入第三部韵并不符合唐五代宋词的用韵实际。如他又指出唐五代宋人词韵也存在本部词韵之外个别通叶的例外情况:“唐五代宋人词韵,确有若干例外,如戈韵第六部真轸震,与第十一部庚梗映,诗韵绝不相通,第十三部侵寝沁,第十四部覃感勘,皆闭口韵也,诗韵绝不相通,然唐五代宋词,用第六部真轸震与第十一部庚梗映通叶,或用第六部韵与第十一部韵者,多掺叶第十三部侵寝沁韵。”他的看法比戈载更通达,也更符合实际。《词调溯源》则是词学史上从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词调起源的重要创获。一方面,夏敬观认为词调溯源“若作根本上的研究,须先问词体是为何种音乐造就成的,他所配的音乐,始于何代”,而隋代是燕乐兴起并取代清乐的关键时期,他说:“自郑译演‘龟兹乐’成功以后,隋代所留存的清乐,也都改用了郑译的方法。至唐代虽分清乐燕乐二部,清乐名存实亡,所用的实只燕乐,即郑译所演‘龟兹乐’,非别有汉魏以来遗声也。”夏氏认为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泛龙舟》,即是《隋书·音乐志》所载的“新声”之一,是与后来词体形式虽异而所配音乐却相同(均为燕乐)的歌词。这就从学理上区分了词调产生与词体产生的不同概念与不同时间。另一方面,夏氏正确区分了“腔调”与“律调”的不同义界。在夏氏看来,“腔调”是伴随音乐产生的一种唱腔的体制,跟音乐关系密切;而“律调”则是追步创“腔调”之人词作而形成的一种格律规范,如四声平仄押韵亦步亦趋前人之作遂形成一种新的格律。他说:
古之乐府,无所谓“腔调”,他的“腔调”,在乐工的乐谱中,我们无从得见。从乐府变新体诗,“腔调”有点显露的意思。从新体诗变律体诗,“腔调”成功了数种,即七言律、五言律、七言绝、五言绝、六言诗之类。从律体诗变为词体,于是词体的“腔调”渐渐成功。而各词有各词的“腔调”,名之曰“词牌名”。古乐府谓之“题”,在一题中,无一定的体裁。词谓之“牌名”,在一“牌名”中,虽也有数体的,而词家照何体句调长短,即谓之何体。剏“腔调”的人,初未必这样呆做。而追步的人,则不敢丝毫变动了。于是论词的人,便又误认“腔调”即是“律调”。
可见新体诗及词就是配乐演唱中形成的一种“腔调”,一个词牌名实际上是一种“腔调”,一种词牌名下往往有数体,说明“腔调”只是一种音乐体制,配词有较大的自由度,并非像后来填词那样有严格的格律体制规范。他又认为“腔调”也不仅仅是四声的关系,更多的是词与音乐配合的和谐问题。在厘清词调与音乐关系的基础上,夏敬观据隋郑译所创七音八十四调(实际二十八调)①以及南宋乐谱等考订了各种词调的源流演变,在词调研究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深化了对唐五代北宋词的研究
夏敬观的词学理论还深化了对唐五代北宋词的研究。自南宋格律词派奉姜夔为宗主以来至清前中期,北宋词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明确提出宗法南宋并奉姜夔词为极诣的主张:“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中略)填词最雅无过石帚”[3]9。他又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说:“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可见朱彝尊、汪森等人宗奉南宋词实际上只是将词学引入专师姜夔、张炎词的偏狭途径。浙派中期代表词论家厉鹗在标举姜、张的同时,又把周邦彦加入师法行列:“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张今涪红螺词序》)[4]753-754他又说:“南宗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吴尺凫玲珑帘词序》)[4]754厉氏援引南宗画胜过北宗画的画论入词论,以南宗画比拟周邦彦、姜夔等人之词,以北宗画比拟南宋辛、刘豪放词派之词,他对周、姜为代表的格律词派的推崇和对以辛、刘为代表的豪放词派的贬抑溢于言表,可见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派词人师法范围稍有扩展。常州词派理论家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5]1634的词论突破了浙派词人专师姜夔、张炎的偏狭途径,将师法对象扩大到北宋周邦彦、南宋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等人。后常州词派代表词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的取法对象基本不出此范围,基本上没有走出南宋词的牢笼。夏敬观则在《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五代词话》等著述中深化了王、况等人提出阐释的“重、拙、大”词学命题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点,认为历代词真正具有“重、拙、大”美学特征的应首推唐五代及北宋词(包括辛弃疾、吴文英的部分词作),提出了与王、况等人不同的从五代、北宋词入手的观点,深化了对唐五代北宋词的研究。
一方面,夏氏指出况周颐“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以及王鹏运“宋人拙处不可及,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之论(况氏所引)的失察之处。他说:
北宋词较南宋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于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张皋文、周止庵辈尊体之说出,词体乃大。其所自作,仍不能如其所说者,则先从南宋词入手之故也。(《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
这里夏氏认为南宋词纤巧多于朴拙,较北宋词少朴拙之气。况氏论“重拙大”时忽视了“大”的意义,导致评衡南宋及清初词时出现以“轻巧”为“重拙”的不当之处,清初即如大家陈维崧、朱彝尊之词的语言及内容多涉“轻巧者”,很难够得上“拙不可及”的评价。张惠言、周济等人倡言推尊词体但创作实践“仍不能如其所说者”的原因亦在于“先从南宋词入手之故也”,不能摆脱南宋词纤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夏氏提出了应从北宋词入手的主张。他说:“取法北宋名家,然后能为姜张;取法姜张,则必不能为姜张之词矣。止庵谓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乃倒果为因之说,无是理也。”(同上)
另一方面,夏氏以“重、拙、大”标准剖析唐五代北宋词,在词评中提出了很多精辟深刻的见解。关于唐词,夏氏族认为唐词源于诗变具有浑厚的特点,《花间词》承唐词余绪,亦不像后来南宋词那样过露痕迹而显得纤薄,他说:“唐词初由诗变,所以浑厚。故学词者,必先知诗,乃能造诣上乘。飞卿深美闳约,神理超越,张皋文、周止葊知其无迹象之中字字连系,得其章法脉络。持此法寻《花间》诸词之绪,庶不浮泛笼统,而亦悟南宋词之过露针缕痕迹为薄也。”(《吷庵词论辑补》)他认为温庭筠词的命意遣词夺胎于六朝乐府,句中绝少使用虚字,唐词到温庭筠才始告大成:“飞卿词实从六朝乐府出,不仅命意,遣辞亦然。句中绝少使用虚字,转折处皆用实字挺接,故不见钩勒之迹。唐时词体,至飞卿始告大成。”关于五代词,夏氏将五代词分为“稍流丽”的南唐词和“务为严重”的蜀派词,蜀派词比南唐词更具有唐词古拙雄浑的特点:“《花间》乃蜀派,南唐与之稍异。南唐二主词稍流丽,蜀派则务为严重。及宋,二晏、欧阳,皆宗南唐。其宗蜀派者,惟张子野一人。”(《跋〈花间〉、〈尊前〉二集》)“飞卿词实开蜀与江南二派,蜀派得其以拙胜者为多。”(《五代词话》)关于宋词,夏氏也提出了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如提出张先词具有唐五代词“凝重古拙”的特点:“子野词凝重古拙,有唐五代之遗音。慢词亦多用小令作法,后来涩体,炼词炼句,师其法度,方能近古。”(《吷庵词论辑补》)又如关于周邦彦词对柳永词继承和创变的论述极为透辟:“耆卿写景无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真效之,故学清真词者,不可不读柳词。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同上)对于常州词派理论家所推崇的稼轩、梦窗词,夏氏也指出了稼轩词“率”和梦窗词“琢”的弊病:“梦窗学清真者,清真乃真能不琢,梦窗固有琢之太过者。稼轩学东坡者,东坡乃真能不率,稼轩则不无稍率者。”(《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夏氏论词时以“不见钩勒之迹”“凝重古拙”“不事雕琢”等为高,而以“轻巧小”“琢”“率”等弊为戒,可见夏氏论词才称得上真正贯穿了“重、拙、大”的论词标准,而非像王鹏运、况周颐等人持此标准论词的不彻底和扞格之处。
三、总结和深化了历代关于“词”“学”关系命题的思考和探讨
历代以来,关于“词”“学”的关系争论不已,夏敬观的词学理论总结和深化了历代关于“词”“学”关系命题的思考和探讨。宋代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学际天人”的欧阳修、苏轼等人之词存在丧失词本位的毛病而为“句读不葺之诗”,南宋辛弃疾驱使经史子集典故入词也受到后人的诟病。清代学术昌盛,对于文学与学术相互关系的争论和探讨更加热烈,“词”“学”关系之命题在清代后期引起了理论家的关注。常州词派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提出“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5]1630的观点,强调词中寄托表现性情、学问、境地的统一。谭献在选辑《箧中词》时提出词分词人之词、才人之词、学人之词的观点:“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派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中略)阮亭、葆馚(按:指王士禛、钱芳标)一流,为才人之词。宛邻、止庵(按:指张琦、周济)一派,为学人之词。惟三家(按:指前文所提纳兰成德、项鸿祚、蒋春霖三家)是词人之词。”(谭献《复堂词话》)[5]4013这里谭氏他最推许以纳兰成德、项鸿祚、蒋春霖为代表的词人之词,并将蒋春霖比之于“倚声家老度”,对张琦、周济一派的学人之词则微露贬意,对王士禛、钱芳标之流的才人之词更加鄙视。晚清民初资学入词成为词坛共识,如张尔田《词莂序》回顾自己跟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从游资学入词的创作道路时说:“及壮,获与半塘、大鹤、彊村三君游。三君者,于学无不窥,而益用以资为词,故所诣沈思嫥进而奇无穷”[6]739。到底如何处理“词”与“学”的关系,夏氏提出较为允当中肯的意见。一方面他在推举“词、学相济相因”的“学人之词”时,强调学人之词的词本位特征。他在《遯庵乐府续集序》中说:“予尝谓词人易致,学人难致,学人兼词人尤难致。有词人之词,有学人之词。君乡先辈沈寐叟(曾植),学人也。《曼陀罗寱词》,学人之词也。(中略)词于文体为末。而思致则可极无上。学者虽淹贯群籍,或不能为,盖记丑无所施于用,强之则伤其格。若于学无所窥者,但求诸古昔人之词,又浅薄无足道,弥卑其体,其上焉者,止于词人之词而已。君学人也,亦词人也,二者相济相因而不相扞格,词境之至极者也”[7]。夏氏这里将词分作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并认为学人之词的境界要高于词人之词。因为词人之词只是“求诸古昔人之词”,若取法乎中,则仅得其下,若取法乎上,亦是止于“词人之词”而已,难于进一步提升词境。而像张尔田、沈曾植这样博通群籍、学问精深的学者,他们并非有意在词中炫耀学问,而是不忘词人本色,词、学相因相济而弥见精彩,远高于词人之词专于词中求词的境界,这也是民初学人之词于唐宋清词苑囿之外别开埠头卓立词史的重要贡献。夏氏在《遯庵乐府序》评张尔田词时更加突出抒情为词之本质特征的观点:“君自遘世蹇屯,益励士节,勤撰述。其寓思于词也,时一倾吐肝肺芳馨,微吟斗室间,叩于窈冥,诉于真宰,心癯而文茂,旨隐而义正,岂余子所能几及也”[8]201。夏氏认为张氏于世运偃蹇中仍然敦励品节,问学不辍,勤于著述,并不时借词婉转发摅心中郁结之忧思,辞采丰茂,微言大义,故张氏寄情窈冥、直诉真宰之词远远超出时流之上,这也可见出夏敬观评词视抒情为词之本体特征的主张。
另一方面,夏氏在强调学力对成就大词人重要作用的同时,又反对在词中搬弄学问。他说:“作词功力,能渐至于名家,既要天分,亦要学力。有天分而无学力,终不能大成也。(中略)诗词文章,虽前贤名作如林,仍有无穷境界,待后人开发。书卷酝酿,得之于前人者也。性灵流露,则得之于目前之境地,得之于平昔之学养。”(《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可见在夏氏看来,学力有助于成就大词人,学养有助于后人开掘词家新境界。但是他对好搬弄学问、滥征典故的资学为词行为深恶痛绝,直以为此是词中之贼,他说:“多读书,始能医俗,非胸中书卷多,皆可使用于词中也。词中最忌多用典故。陈其年、朱彝尊可谓读书多矣,其词中好使用史事及小典故,搬弄家私,最为疵病,亦是词之贼也。不特俗为词之贼耳。”(同上)可见夏氏之论为“词”“学”聚讼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释:
①夏敬观在《词调溯源·郑译演“龟兹乐”的真相》中说:“郑译见苏祇婆所传有‘七音’,不得不于五音之外,增以‘变宫’‘变徵’。又因五旦之名,旦作七调,而演为‘七音’‘八十四调’。实则琵琶只有四弦,“徵”弦不备,每弦七调,共二十八调。唐宋所行用者,只有此数。”可见郑译“八十四调”实则只有二十八调。
参考文献:
[1]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汪辟疆.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朱彝尊,汪森.词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厉鹗.樊榭山房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郭绍虞.中国近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夏敬观.忍古楼文(不分卷):第五册[M].上海图书馆藏稿本,1935.
[8]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黄贤忠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ontribution of Xia Jingguan’s Ci-theory
LAN Shi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Xia Jingguan is a famous Ci poetry theory activist, and his Ci poetry theory activities and his Ci poetry theory work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ecent Ci-poems circles. His Ci poetry-theory summarized his and his colleagues writings experience in time, which is an important Ci-theory achievements, and his research finished create new pattern, because his theory is carri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Wang Pengyun, Zhu Zumou and other’s“Xiao-xue”methodology into studying Ci-theory and collating Ci books. His theory not only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Ci-poem metrical rhythm from Qing Dynasty, but als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northern song Ci, also summarizes and deepens the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proposition about“Ci-poem”and“learning”, therefor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theory.
Key words:Xia Jingguan; Ci poetry theory; Ci poetry contribution
作者简介:兰石洪(1973—),男,湖南岳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项目号:13&ZD118)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8-12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6)01-00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