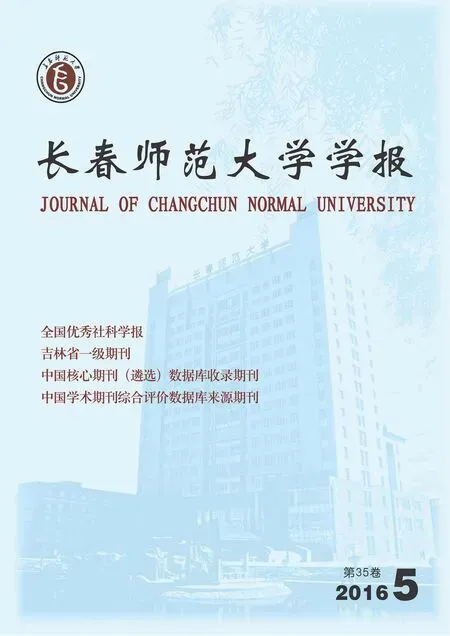论清末小说《东欧女豪杰》女权人物形象的本土化
李羿璇,刘 钊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论清末小说《东欧女豪杰》女权人物形象的本土化
李羿璇,刘钊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要]清末小说《东欧女豪杰》讲述了俄国虚无党领袖苏菲亚参加革命的人生经历。作为维新派女权思想在中国的文学阐释,苏菲亚的形象被明显地本土化了。它通过中国女性华明卿形象与苏菲亚的比照,提出了倡导女学与女性参加革命的主张,希望当时的中国女性效仿俄国女英雄苏菲亚,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革命赴汤蹈火,成为建构“新中国”的有生力量。
[关键词]苏菲亚;女权;救国;本土化
19世纪末,在国势日衰的环境下,维新派启蒙家们在建立“新中国”的理想诉求中认识到“女国民”在强国保种中的重要性,于是积极倡导和推行戒缠足、兴女学、办女报等一系列启蒙女界的活动,并将西方的女权学说介绍到国内,梁启超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02年2月,梁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11月又创办《新小说》杂志,体现了他欲以“新小说”启发“新民”的政治意图。在此之前,梁启超发表了《论女学》等文章,表达自己对于女学的充分认识。由于“合于新理想的中国女性典范极度缺乏”[1],《新小说》创办不久,便刊发了传记小说《东欧女豪杰》,将外国女杰形象输入中国,足见他对塑造女权人物形象进而启蒙女界的重视。然而,在20世纪初期女权被引进并得到大力推广的形势下,来自西方的“女豪杰”形象却被改造、挪用为本国现实政治的需要,呈现了本土化的特质。
一、《东欧女豪杰》与梁启超的《新小说》实践
《东欧女豪杰》共五个章节,未完成。作者署名“岭南羽衣女士”。关于作者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阿英认为小说是张竹君创作的,依据是张竹君以“岭南羽衣女士”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报刊文章,“岭南”暗指她的家乡广东番禺。根据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记载,作者是罗普。罗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在日本与梁启超一同创办《新小说》,岭南为他的家乡[2]。马君武则认为是梁启超所作。《马君武集·前言》中云:“梁托名‘羽衣女士’,在《新小说》上连续刊出长文《东欧女豪杰》。君武羡其文而慕其人。梁等竞故意恿君武与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函会晤,留学生界一时传为笑谈”[3]。晚清作者身份难以确定是众所周知,原因是当时众多作者频繁变换体用的笔名。性别问题也使作者身份扑朔迷离,很多署名某某女士的作者实际上是男性;有些男性作者甚至直接选用一个十分典型的女性笔名,来掩蔽自己的男性身份。冯自由和马君武当时都身处日本,了解旅居、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所以他们的说法比较可靠。二人一同创办《新小说》,必然共谋“新民”大计。《东欧女豪杰》很可能是在梁启超主导下罗、梁二人共同创作的作品。
《新小说》于1903年开始连载。之所以发表这篇小说,梁启超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他曾在《俄人之自由思想》一文中提出建议:“今日为中国谋,莫善于鉴俄”[4],表达了他从俄罗斯革命中借鉴经验的意图。小说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菲亚·彼罗夫斯卡娅形象改编,讲述沙皇俄国黑暗统治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极端的贫穷,体现了封建制度的不公平待遇,即贵族一生下来就住高楼、吃大餐、坐马车、穿燕尾服、把土地都占尽;贫民却要给贵族们当牛做马,替他们赚钱,自己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使当时俄国的知识女性们觉悟起来,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组织民众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索菲亚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闻名,被誉为女英雄。为了祛除中国读者的陌生感,小说将索菲亚译为苏菲亚,并对人物与故事进行了“中国化”的调整:中国女学生华明卿作为苏菲亚的中国对应者而存在,由她来讲述苏菲亚的故事。华明卿在整个故事中虽没有参与到她的俄国女同伴们的革命活动中,但作为一个观察者、见证人、叙述人,她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成为中国女性宣传和实践西方女权的代表人物。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英雄形象,如裴莪弥、葛妤巧、晏德烈、苏鲁业、赫子连等,对主人公、民党领袖苏菲亚则作了更为细致的描写。
二、俄国女权人物形象苏菲亚
苏菲亚是一位俄国贵族女公子,为彼得大帝所出支裔,父亲是当时的莫斯科府尹。苏菲亚天生聪慧,闻一知十,过目不忘,成绩优异。她暗自熟读了遮尾舍忌威及笃罗尧甫等人所著的禁书,坚定了救国救民的信念,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期望献身于自己的理想。1871年遇到大侠济格士奇,共同创立“革命团”,基础稳定后,开始深入各地演说,鼓动民众推翻沙俄的专制统治。
苏菲亚的父亲性情顽固、守旧异常,他得知女儿与革命者来往后,对苏菲亚进行严格的管束,甚至屡次叫苏菲亚中途废学。与父亲对女性的狭隘约束截然相反的是,苏菲亚打破传统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创造自己的多重身份。苏菲亚通过两次换装,达到了转换身份的目的。在决定去乌拉尔山区演讲时,她“尽把簪饰除去,又换了一套不新不旧的衣服,打扮着正和那贫家女子一样”,“菲亚改了贫家女子的装扮,自觉有趣,不免摄影了一副小照,分送各处相知的朋友”[5]415,表明她对换装十分满意。还有一次,苏菲亚要穿过家乡圣彼得堡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区时,卸下了贫家女子的全套装扮,改扮成一个修女,“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斜纹绒的摇曳长衣,头上戴着一顶遮天蔽日的圆阔平冠,脸上盖着一面乌染线纱织成的密网,网上又压着绿色玻璃造成的眼镜”[5]424。换装之后的苏菲亚非常享受不同的角色,不是揽镜自照就是拍照留念。苏菲亚的换装行为是自主的,这与她的贵族身份形成对比。从贵族到普通民众,苏菲亚并没有在意其间的阶级差异,而是乐在其中。她换装后的小照被华明卿评价为“越扮得质朴,越显得名贵”。苏菲亚以不同的身份深入草根阶层进行演说、鼓动革命,获得了民众的认可。
小说详写了苏菲亚在乌拉山大茅厂的演说。她从工人们的生存实际着想,劝阻了工人们罢工示威的冲动行为。她力图让民众懂得,罢工示威不但达不到威胁贵族的目的,还会让自己的生活处于更恶劣的状况之中。她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压制民众生活的根本,号召大家合力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我们平民的耳目口鼻,和他们贵族没有两个样儿,正是一般的从天地生出来,大家都是完完全全一个人。是的,既然同是大地间一个人,就应该大家同享那大地造来养人的土地,这才是自然的大道理呀。如今他们贵族却是用着人间的野蛮的势力,把那自然的大道理都压倒了。我们既已看得这个事情不平了,为什么还要忍着气容着他呢?”[5]422她向民众宣传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民众提出要将失去的土地财产等抢回来时,苏菲亚又给予了否定,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激烈。因此,苏菲亚是主张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的,这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
苏菲亚在一次去工厂演讲的途中被捕,一些追随革命团的人纷纷设法解救她。但是,苏菲亚从民众利益角度考虑,拒绝了劫狱获救的机会,原因是:“第一件,为着我一个人,烧了民房,反叫许多人受苦,我心里却是不安。第二件,万一事弄不成,害了子连各位的性命,即不然,亦必失了职业。第三,他警察署既经知道一切,当有防备,恐怕万无弄得来的道理。”[5]467-468苏菲亚身在狱中,仍把民众安危放在第一位,不愿牺牲他人,获得自身的自由,不仅表现出了仁爱之心,还深明大义、勇于牺牲。虽然小说未完,但是苏菲亚这个反抗专制强权、具有“天赋人权”思想和启蒙意识的女权人物形象已经跃然纸上。1903年,金天翮发表了中国的女权宣言《女界钟》,鼓励女子参加革命、追求自由,做“女国民”。苏菲亚形象无疑成为女权思想引进中国之时的文学性阐释,促发了女权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三、与苏菲亚相对应的本土女性形象
作品对照地描写了华明卿与苏菲亚的出生和成长过程。苏菲亚出生时,“白鹤舞庭、幽香满室”,隐喻身世不凡。苏菲亚也确实聪慧过人,两岁可识字,五岁能吟诗,八岁即过目不忘,师友无不敬重她。而华明卿的出生更为奇特,她的母亲终身未婚,受孕时已年逾古稀,而且只是做了一个梦,梦中“看了一部什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什么倚剑美人的图画看了一会,那画中美人募地一扑,扑到他身上便不见了。谁知梦醒起来,身体发病,腹中渐动。过了十个月零十五日,忽然生下一个孩子。那老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一定是个怪物,连忙用一件破衣包了,背着人抱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放下就走”[5]399。这些描写是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惯用手法,但凡有不同凡响之人诞生,其母分娩或受孕时就有异常现象发生。华明卿被母亲遗弃,由路过的美国妇人收养长大,这与中国女性康爱德的真实经历很相似。梁启超在1898年《清议报》上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中,记叙了康爱德被收养的经历和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事实,可谓作者塑造华明卿形象的基础。梁启超书写康爱德的成长历程超出了个体意义,考虑了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并且强调了中国女性在西方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必要性,认为女性接受西式教育后才能变成自立的成功之人,此为中国女性的典范。小说还强调了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和影响。作者多次写到华明卿被精心抚养长大,养母对其“抚如珍宝,珍若拱璧”。明卿长大后,养母即把她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小说并没有交代其养母的身份背景,在华明卿赴美后她便离开人世。小说树立的这位受外国教育、独立自主的中国新女性形象,是康爱德的文学再现,与当时梁启超的《记江西康女士》彼此呼应,使作品具有了中国化色彩。
作品在苏菲亚和华明卿的教育经历上也有对应的描写。养母去世后,华明卿不得不面临中途废学的命运。在苏菲亚面对求学困难时,其父亲口中说出的恰是中国规训女子的“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用中国读者熟悉的性别标准表达俄国父亲对女儿的规劝,使苏菲亚与华明卿面临同样的中国传统道德考验,也使读者更容易亲近这一来自异域的人物形象。当时中国的妇女教育问题是公众关注和有争论的话题,妇女在求学过程中面临种种困难。以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女学问题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是十分有效的叙述。除此之外,女学还为后文作了铺垫:其一,现代教育为反抗父母权威提供了知识结构上的保障;其二,接受教育成为个人独立的基础,使女性成为行动自主的人。这正是构建新女性的必要条件。
在日内瓦生活和学习哲学的期间,华明卿结交了很多观念激进的俄国留学生,苏菲亚的故事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苏菲亚与华明卿都是天生聪慧、喜读自由之书的女性,虽然二人在小说中并没有实质的交集,却有着共同的志向。裴莪弥曾向华明卿阐明过苏菲亚所办“革命团”的宗旨:“我们欲鼓舞天下的最多数的与那最少数的相争,专望求得平等自由之乐。”华明卿听此言后,亦有深深的感慨:“莪弥妹(姊)方才所说俄国民党的宗旨,诚开金石,义薄云天,人人有不普度众生誓不成佛之意。彼之同志,我在此得见的,已艳羡其济济多才,料他本国,更不知有多少人物。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姊妹,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又不但女子为然,那号称男子的,也是卑湿重迟,文弱不振,甘做外人的奴隶。忍受异族的凭陵,视国耻如鸿毛,弃人权若敝履,屈首民贼,摇尾势家,重受压抑而不辞,不知自由为何物。尚使若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能不愧死么?”[5]406她对于国情之危和人民的麻木,感到伤感与不甘。
小说借助俄国女英雄苏菲亚的形象,不仅表现了维新派思想,也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揭示。苏菲亚被捕入狱后,狱卒对其进行了非人的折磨。而后有人暗中给了狱卒好处,苏菲亚待遇立即不同。这虽然是对俄国监狱的描写,实则为晚清小说中的常见场景。此外,许多全力营救苏菲亚的人,无论是旧相识晏德烈,还是不相识的葛妤巧及赫子连,都表现出中国传统的侠义美德。赫子连试图劫狱营救苏菲亚,苏菲亚虽然婉拒,却不得不赞叹:“这位子连那么义侠,真真令人敬服”[5]467。由此可见,苏菲亚这个俄国女英雄形象附加了很多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学题材,承载了更多中国本土化元素。同时,苏菲亚形象开启了近代翻译文学“为我所用”的著译创作风尚。
四、结语
《东欧女豪杰》成功塑造了苏菲亚这一女英雄的崇高形象。梁启超希望中国女性能以苏菲亚为楷模,以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己任,反抗专制统治,为革命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阿英先生评价《东欧女豪杰》:“虽以无政府人物作骨干,而主要目的,却在宣传推翻中国的专制政体”[6]。这一点,金天翮在《女界钟》中也提到过:“法兰西之革命,有以少数女子,投身其中者,夫彼为君权之革命而来,非为女权之革命而起也。俄罗斯之革命也,有以多数女子,投身其中者,夫彼亦为君权之革命而出,非为女权之革命而奋也”。[7]因而,苏菲亚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打击了男权主义传统的“大丈夫”“英雄”论,甚至在当时有男子提出“娶妻当娶苏菲亚”[8]121,并有女子唱和“献身应作苏菲亚”[8]108,有效地鼓励了广大妇女走向解放。《东欧女豪杰》发表后,国内出现了众多女子救国题材的小说,可见当时人们救国之心十分迫切。由此,女权人物形象成为清末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群像,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别指向。
[参考文献]
[1]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28.
[2]于必昌.《东欧女豪杰》作者考[J].文学评论,1981(3):144.
[3]莫世祥.马君武集[M].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41.
[4]梁启超.俄人之自由思想[J].清议报,1901-11-1(1).
[5]董文成,李勤学.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十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6]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106.
[7]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75.
[8]夏晓红.晚清文人妇女观[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收稿日期]2016-01-19
[作者简介]李羿璇(1987- ),女,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刘钊(1965- ),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性别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5-01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