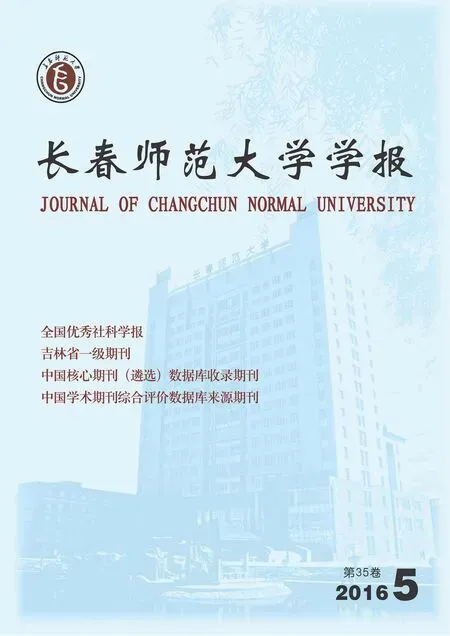非典型侦探小说家约瑟芬·铁伊的写作风格探析
丁 婧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非典型侦探小说家约瑟芬·铁伊的写作风格探析
丁婧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摘要]英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孕育了众多赫赫有名的侦探小说家,约瑟芬·铁伊就是其中一员。但这位一生只有八部侦探小说作品的女作家和同时期多数作家有着迥然相异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特色。本文试图从“抛弃读者参与”、“人物代替案件作为主体”、“尝试更多的故事结构”等方面入手,探讨铁伊这种抛弃真相、专注人性的写作风格。
[关键词]写作风格;约瑟芬·铁伊;真相;人性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类型小说,正式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时间要追溯到1841年。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写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在此之后,侦探小说在英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是由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和他笔下伟大的侦探福尔摩斯引领的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近50年的繁荣过程中孕育出许多赫赫有名的侦探小说家,约瑟芬·铁伊就是众多名家中的一员。这位一生只有八部侦探小说作品的女作家,却能保持有三部作品长期跻于百部最伟大侦探推理小说排行榜之列,并且和同时期的多数作家有着迥然相异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特色。
铁伊一生共创作了八部侦探小说作品,分别是《排队的人》《一先令蜡烛》《萍小姐的主意》《法兰柴思事件》《博来·法拉先生》《一张俊美的脸》《时间的女儿》和《歌唱的沙》。虽然她的创作数量非常少,但每一本侦探小说都体现了和当时其他侦探作家不尽相同的写作特色和叙事风格。在铁伊的小说里,读者会体会到非常不同的阅读体验,甚至可能在阅读过程中暂时忘记这是一本侦探小说。她有意无意地摒弃了侦探小说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核心——探案解谜,而将更多笔墨付诸人物角色的塑造,关注人心本身的复杂变化。也就是说,铁伊借侦探小说之名,表达的却是关注人性本身的主题,这是那个年代其他侦探小说家少有涉猎的主题。虽然就现在的侦探小说发展来看,社会派的一些新小说家更深入地将人性关注作为一种主题构思故事,但在人性展现方面并没有体现出铁伊这样抛弃真相、专注人性的写作思路。这也是有评论家认为铁伊的八部作品从文笔风格来说超越了类型小说的局限,走向了纯文学道路的原因。作为作品极少的非典型侦探小说家,铁伊打破了读者对侦探小说的一般认识,她的侦探小说也成为古往今来众多小说作品中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
一、独特风格之抛弃读者参与
褚盟在《谋杀的魅影》中指出,侦探小说的核心是解谜和侦探形象。[1]如何解谜以及侦探形象是否能够在读者心中建立,是侦探小说能否打动读者的重要因素。常规的侦探小说的叙事脉络是:侦探或者案情相关人出场——发现案情——现场侦查和侦探首次案情归纳——可能出现新的线索或者新的案情——迷雾阶段和更多的侦查——出现曙光以及挑战读者——侦探陈词,案情告破。但在铁伊的小说里寻找这样的阶段结构非常困难,读者必须跟随主要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内心活动才能慢慢接近案情的延展和后续。铁伊推动案情发展的方式是依靠人物自然的言行活动。比如在《歌唱的沙》里,作者先是介绍了一位非常有特点的列车员,为之后的故事埋下了一点伏笔,然后让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格兰特探长无意中看到列车员的举动继而发现尸体。接着继续描述列车旅行,虽然中途发现报纸上的诗歌回想到死者,但是仅一笔带过。直到人物坐在汽车里幽闭恐惧症发作,想要阅读报纸减轻症状之时才又引回案情。之后又是生活描绘,再次不经意回到案情。书几乎过半才真正进入侦查,迅速破案。这种完全体现人物日常活动的叙事方式在任何其他的侦探小说里都无法被复制。正如本书导读所说的那样,约瑟芬·铁伊不是一位规规矩矩的侦探小说家,她彻底地放弃了让读者参与的根本目的。
比如铁伊的第一部作品《排队的人》,作者在第一章里是如何引出案情的呢?她首先站在全能视角之上,利用自己剧作家的经验写出了让人赞叹的伦敦剧院门口的全景图。排队买票的人当中有人死去,胸口插着匕首的情节很妥当地插入在全景图的后半部分。警察赶来,排查死者前后的相关人士。“吉米搀扶着他泣不成声的妻子搭计程车离去。另外五个人则镇定地散坐门房为他们保留的位子上。晚场演出的《你难道不知道?》刚好拉开序幕”。这样的开场仿佛一部社会风俗小说的开头。然后作者让普通的格兰特探长成为追踪凶手的主力,但这位侦探并没有助手。这位探长既无法施展福尔摩斯那样的推断术,也无法像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那样用谈话诱敌,意味着读者能从探长嘴里挖出的信息寥寥无几。他甚至有点像其他侦探小说里所嘲讽的苏格兰场的警察一样平淡无奇。唯一不同的是铁伊不断地放大着这位普通探长的内心世界,几乎每时每刻都描绘着他丰富的内心活动,全面地呈现着他对任何人、任何事物的看法。于是读者彻底沦为了看客,只能默默地关注着探长忙于自己推演案情:“格兰特觉得这说法很合理。他想起死者纤细敏感的双手……这点和当初死者属于某帮派的假设不符,但他不能因此就轻忽这条线索。”或者是在漫长的破案过程中等待着答案:“格兰特对于鉴赏马可是一窍不通——所以他的眼睛一直在搜寻旁边那群看起来像是在谈公事的人。有个自称为‘石头’的摩伦史坦,看起来一副拥有全世界的样子。格兰特在猜他到底是用什么诡计混进马场四处招摇撞骗,3月那场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的盛会该不至于跟他扯上边”[2]。读者如同戏院里的观众,依靠舞台上演员的台词或者灯光的明暗理解某个段落场景,而绝不可能自己提前预测故事的进展。即使看到格兰特探长找错了方向,读者也只能继续对着这个似乎没有异能的探长吹胡子瞪眼睛,想要努力猜一下真凶是谁,但线索怎么也拼凑不起来,因为作者没有给出什么可供总结的线索,也没有刻意的暗示,甚至下一章节还会出现前面并未出现过的人物。这说明铁伊并不希望读者参与,只是将自己对人和事的观察记录在案罢了。读者最终也会意识到探案过程只属于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因此,只有最为耐心的读者才有可能在铁伊构筑的探案全程中获知真相。
二、独特风格之人物替代案件作为主体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认为,常见的小说人物有两种:一种是扁形人物,一种是圆形人物。扁形人物是“作者围绕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3],这个人物的言行不会超出这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扁形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殆尽”,并且“能让读者一眼认出来”[3]。扁形人物受到很多侦探小说家的欢迎,因为读者将更容易集中在案情本身的发展上。
铁伊的八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有着相对模糊的形象特征,他们更像是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一些陌生人,你可能因为他们的外貌或者言行有所注意,却无法说出那是一位什么样的陌生人。因为他们不像扁形人物那样特点十分明显,比如成功的商业人士、疲惫不堪的工人、多年不上班的家庭主妇或者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对于这些陌生人,你或许大致了解他/她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位置,却无法告诉人群为什么你认为他/她是成功的商业人士或者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因为你感觉他/她和你一样,拥有复杂的内心和善变的情绪,背后的人生也许很长很长。
在《萍小姐的主意》中,萍小姐这样总结她对几位主要学生的印象:“由双腿来辨认不同的人,与经由脸孔来辨认的效果相当。瞧瞧,眼前一双双固执的、轻浮的、清爽的、迟钝的、怀疑的腿——只要换一面,再瞄一下脚踝,她就可以喊出:戴克丝,或是茵恩斯、鲁丝、宝儿,来与这些腿配对。”[4]作为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萍小姐似乎对看人待物颇有心得,小说中几乎每章节都有她对这些学生的评价和猜想。然而学校发生了案情,萍小姐开始思考和分析,并最终失败地理解案情本身,因为她并没有在内心里指认出正确的凶手。读者可以在第五章找到些许她可能犯错的伏笔:“没错,露西心想。精神放松,健康状况良好,她铁定喜欢制造噪音。接着,几乎是立即反应,露西又想,也许她喜欢的不是制造噪音,而是在一群人中手握权力的感觉。不会的,她驱开这个想法。纳什的人生很顺,一辈子只要张口伸手,就能得其所愿。她不会需要任何与满足有关的替代品,她的生活毫无欠缺。她只是纯粹地喜欢响亮的铃声罢了。”再对照一下她在真相发现之后的内心独白:“……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便如她所愿。如果不是,她便采取行动,让事事都能顺心。露西想起来,在宝儿四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打败成人世界所有意志结合起来对抗她的力量……她无法认同挫折存在的可能性。”这两段文字说明了几个事实:首先,真凶本人的言行展现确实能够支撑宝儿作为凶手的可能性,这包括她最后捡起自己鞋子上的饰物却误以为就是掉在了萍小姐的房间一样,宝儿也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任何需要反省的地方,因为她只是在排除“挫折存在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萍小姐的心理如何变化,从而对她有更丰富的认识,比如她其实预见到了凶手潜在的性格缺陷,可是基于她之前对凶手的印象,如“金色秀发的天使”“活泼可爱”等错误地归纳为“她只是纯粹地喜欢响亮的铃声罢了”[4]。萍小姐与人为善的评价方式以及容易受到外表蒙骗的心理是读者在生活中也会体验到的故事。这就增加了小说本身对于真实世界的映照性,从而使得案情本身从朴素的推理侦破中伸向人性的沼泽。
正如福斯特所强调的那样,圆形人物“宛如人世间的一个真人一般”,他们在小说里随着小说的情节经历命运的浮沉,然而读者很难判断这样的生活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所以也就无法断定这部小说是更偏向于喜剧或者悲剧。读者唯一清楚的是故事读完了,然而思考似乎没有停止。福斯特最后总结道:“圆形人物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预料—我在这里说的生活,是指充塞在小说篇幅里的生活……”铁伊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是简单地沦为一场凶案的主谋或者被害者,不管是《排队的人》里杀人的母亲,还是《法兰柴思事件》里看似天真无邪的贝蒂·肯恩,或者《一张俊美的脸》里美国来的摄影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铁伊小说中案件只是辅佐人物展现自身的引子,而铁伊将通过案情的发展来向读者很细致地表明这位人物如何一步一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三、独特风格之尝试更多的故事结构
在《时间的女儿》的序言部分,著名侦探小说家罗勃·巴纳德这样说道:“小说家与读者之间这坚强的联结乃是基于信任——信任某人是一流的说故事家,而且不会将内容公式化。铁伊,在她最好的几本书里,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各种不同的故事。”[5]
铁伊的八部作品虽然都体现了笔者前述的两种特征,即拒绝读者参与,并且放弃以解谜为主转而以人为本,但是每一部作品的架构都不尽相同。
八部作品中,一开始就明确交代案情和侦探介入侦查的只有两部——《排队的人》和《一先令蜡烛》。《博来·法拉先生》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任何侦探侦破的情节,一切只依靠主人公自身的观察和多个人物视角对故事完成全镜观察,这种写法很有维多利亚时代纯文学作品的风骨。类似的作品还有《一张俊美的脸》,各种人物穿插其中,人物间的情感纠葛和内心矛盾赤裸裸地被摊开来,读者到最后几乎忘记了这原本应该是一部解谜的作品。《法兰柴思事件》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观察后的报告文学,详细地描述一场人为造成的假案件,从而提醒读者对偏见、舆论等一些人性问题要理性地思考。最有趣的作品莫过于《时间的女儿》,病床上的格兰特探长寂寞无聊,开始研究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为一位在历史上遭受不公正评价的历史人物翻案,全程似乎在模仿安乐椅式的侦探,但是对人物本身的内心呈现决定这不是刻板的模仿,而是一种超越。
唐诺在他为铁伊《歌唱的沙》所作的导读中说道:“在我们已经看到的七部铁伊小说中,其中有两部完全不存在死亡谋杀……有一部死了人,但却是出自于全然的意外……有一部确实有着杀人之念,但所动的手脚不是非置人于死地不可的模糊动机……换句话说,规规矩矩符合“谋杀/破案格式的铁伊小说,原则上只有两部。”[6]铁伊为了不向无聊的“谁是凶手”式的侦探小说妥协,尽可能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路线。她本人其实是一位历史戏剧家,所以写起传统的侦探小说来或许或觉得处处受限。试想一下,她是否能认同范达因提出的侦探小说二十规条呢?这对于铁伊来说,恐怕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四、结语
约瑟芬·铁伊不是一位典型的侦探小说家,她不仅与同时代的侦探小说家们相比显得特立独行,就算和现在兴旺发达的日式推理小说家们放在一起,也彰显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这种不同是铁伊对侦探小说实验性的尝试所确立的本质。即使她只有八部作品,这些作品也将永远是世界侦探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禇盟.谋杀的魅影[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8-35.
[2]约约瑟芬·铁伊著,黄妉俐译.排队的人[M]∥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7-74.
[3]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哈尔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75-177.
[4]约瑟芬·铁伊著,金波译.萍小姐的主意[M]∥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50-205.
[5]约瑟芬·铁伊著,徐秋华译.时间的女儿[M]∥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10.
[6]约瑟芬·铁伊著,吴丽娟译.歌唱的沙[M]∥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6.
[收稿日期]2015-11-21
[作者简介]丁婧(1983- ),女,讲师,硕士,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5-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