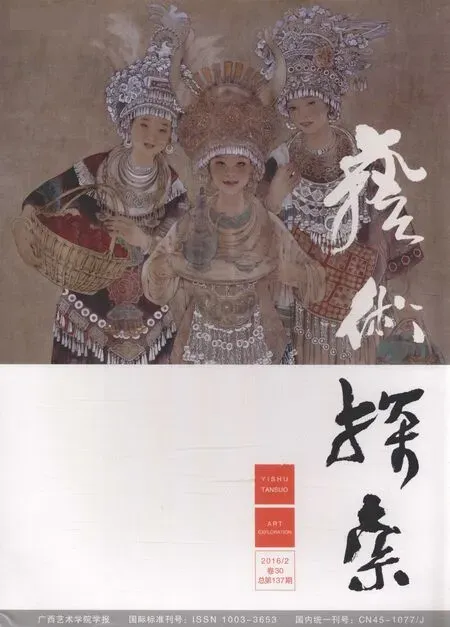从汉简《士相见之礼》到汉碑《曹全碑》——论“写本”隶书和“碑本”隶书
赵凯昕
(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从汉简《士相见之礼》到汉碑《曹全碑》——论“写本”隶书和“碑本”隶书
赵凯昕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444)
当对隶体书风的流变脉络进行探讨时,存世碑刻遗存的书迹能给予我们很多思考与启示。但实际上由于碑碣本身具有的社会功能性,使其在从书丹到成碑的过程中,揉进了人为的、面向群体审美的修饬因素。将汉简《士相见之礼》与汉碑《曹全碑》进行比对,可于“写本”隶书与“碑本”隶书在应用场合和功能审美的侧重层面上将“书写”剥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进行观察。
隶书;写本;碑本;书写
在描述隶体书风和书体沿革时,存世碑石遗存上的古代书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参照资源。清季以前对隶乃至篆、真各体的观察和取法,主要以流传有序的碑石书丹拓本为主,并校以载体实物。
此是研究隶书的传统形式,亦是主流。
清季以后直至20世纪初,简牍帛等地下文物问世。其上负载的手书墨迹,包含了篆、隶、章、草、真等纷杂多样的文字形态。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多样混呈的文字形态,与书法史传统上所梳理的文字递演形态相比,呈现的主要是文字应用和书写的自然属性。侧重材质和书写状态的考据,并不是古代书史研究的传统。但带着古远气息的文字写本的突现,不仅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梳理字体演进脉络的活标本,并且以一种鲜活且冷静的姿态,激活了书史和书道研究的新触角,使得过往对“书写”状态本身的关注,有了一个深入的空间和拓展的维度。
武威《仪礼》(甲、乙、丙三本共九篇)是20世纪新出土简牍帛遗存中,文字内容和体式都比较完整的“经本”类简册。本文选取这九篇中的《士相见之礼》册,与碑拓本《曹全碑》比对观察。在书体风格相近的基础上,可以观察书体在日常写本以及侧重“纪念碑”式社会功能性用途中的不同表现。
一、写本:汉简《士相见之礼》
武威简本《仪礼》成书于西汉宣、成帝之间,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7年。《士相见之礼》是甲本其中一篇。
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武威地区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了一大批竹木简,是当时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之一。墓中共清理发掘出《仪礼》(甲、乙、丙三本)469简,并日忌小木简共480余简。其中三本九篇共存27 400余字,较之《熹平石经》七经残存八千数百字多了将近两万字。[1]29
甲本木简和丙本竹简同长,约为55.5~56cm,约汉尺二尺四寸(以23.3cm作为汉尺一尺,则汉尺二尺四寸为55.92cm)。甲本木简分为平均的三段,每段容字20字,全简为60字左右。乙本木简容字最多,一般在100~110字之间,也有一简容字125字,几乎是甲本的一倍。除正文外,在一篇之末有记全篇字数的一行尾题,曰“凡若千字”。在篇首第一和第二简相当于第二编之下,分别写有篇题和篇次如“士相见之礼”“第三”。[1]32-33
根据整理和校对的结果,这批竹木简是古代《仪礼》的一部分。现仅存七个篇名:“士相见”第三,计16简;“服传”第八,计55简;“特牲餽食”第十,计49简;“少牢餽食”第十一,计45简;“有司彻”第十二,计73简;“燕礼”第十三,计39简;“大射”第十四,计101简。其中,仅有“士相见”一篇保存完整,其余六篇均有损失。[2]
研究认为,武威简本抄写成册的时代在西汉宣帝以后。简册“在入葬以前,不为了殉葬而钞写的,乃是墓主人平日诵习所用,因为简册上有过削改和读书的记号”。又考据墓主“生存于西汉成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时,而其人或者属于所谓文学弟子,或者是文学弟子之师。西汉所谓文学乃指经学”。[1]31那么武威简本《仪礼》的书写时间,则大概在西汉宣、成帝之间,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7年。
以上是汉简《士相见之礼》的一些简单信息。另,其作为一份手抄本,还有下面几个特点。
其一,为古经书典籍本。
《士相见之礼》册一篇共16简,属于墓中出土的甲、乙、丙三本九篇《仪礼》中的一篇。《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主要记载周代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其中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是构成古代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今文学。“现在传流的‘今本’,如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乃郑玄注而贾公彦疏的。贾疏本之杂糅今文古文的郑玄注本,而唐开成石经本亦略同于郑注本和贾疏本。”[1]30据出土时武威简本的师法和家法,研究者对其篇目性质进行校勘后,认为其在内容版本和古今文的使用方面稍别于传流的“今本”,它既保存了较早版本的内容,同时也保留了古文的成分。
包含《士相见之礼》在内的《仪礼》,记录的是两汉通行的行为范式,是其时士大夫自修和研习的重要参本。作为两汉知识分子时时诵习的手本,在版本选录和传抄的过程中,对写手的水平和文化背景必有一定要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可见相比其他地区出土的屯戍文书和日用杂简,在文字的书写和使用上,经书典籍类简册的墨迹更具有严谨性和稳定性。
其二,文义畅达,体式完整。
简本《仪礼》的七个篇目共九篇中,以《士相见之礼》保存最完整,其余六篇均有损失。“它是保存最完好的,大多数的木色墨迹如新;它虽稍有残缺,但每一篇的首尾俱全,因此保存了原书的篇题、尾题、页数和它们原来的次第。”[1]30《士相见之礼》独立成篇,文义畅达,体式完整。持用简牍写本与今本相校,我们往往更容易捕捉到书写的一些规律性和自然状态。
其三,是早期的、书写意味重的隶字。
汉简《士相见之礼》成书于西汉末宣帝时①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推定:“武威礼这个‘本子’,出现于西汉中期的昭、宣时代,即后、戴、庆生存活动的时代。而武威简本是根据这个‘本子’而钞写的,它的时代应在宣帝以后。”见《考古》1960年第8期,第31页。,是两汉士大夫常用的诵习本子。如前所言,此类流通的经书典籍,对书手的文化水平和书写技巧有一定要求,对版本和文字使用亦有一定的严谨性。那么,以《士相见之礼》为代表所反映的是两汉时普通知识分子的文字使用状态。即便不能以写手的水平确定两汉士大夫阶层的书写能力和书法水平,但起码可以由这些简册所体现的书体风格和书写状态,推定其时社会文化阶层对日常书写和风格方面的审美要求和通用范式。今世出土秦汉简牍帛墨迹,主要以经书典籍和屯戍文书两者为大宗,并有少量的医技、占卜、名剌等日用杂简。存钞经书典籍时多以较正式规范的隶书与八分书书成,屯戍文书在基层应急使用,往往为求时效退而以轻快便利之草隶或章草书成,其余少量的医技占卜杂简,有的配以说明绘图,书体在规范之上又多有装饰的要求。
大量急就而成的屯戍文书墨迹体现的是随性的天趣和书写的畅意,但以此推考两汉士大夫阶层的书法状态和审美标准未免稍显荒率且不合理。若论最接近知识分子文化阶层日常书写状态和书法审美的,本文认为应是此类经书典籍上的写本墨迹。
书法的审美自觉,或说“书字”何时从“书写之技”萌化成“书法”,这是一个无法清楚厘定的复合过程和轨迹。“书写”这种行为本身带有心理隐秘性,并有创作动机的复杂向导,成为我们观察书法自觉萌生的目障,“以绘画为基因,以文字为媒质,构成了书法的自我维持能力,从而超越随机的、动态的个体发生范围,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社会发生模式,取得了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个过程的完成,大约在汉末桓、灵之际,正是字体演变停止,书体从广义转向狭义的分水岭”。[3]今日反观这个过程,历史向我们提供了碑版刻石书迹和简牍帛墨迹既相别又相系的两种状态。相比传统书法史研究的方式和对象,写本的墨迹遗存对于我们而言又将会是另外一种启示。
二、碑本:汉碑《郃阳令曹全碑》
汉碑《郃阳令曹全碑》(简称《曹全碑》)成碑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与西汉末简册《士相见之礼》成册时间,相差约200年。
碑高约253cm,宽约123cm。无额。碑阳刻字20行,满行45字。碑阴刻字5列。明万历(1573~1619年)初年,出土于郃阳县。因埋于渭水沙碛未经风雨剥蚀,所以字划完好。其后于1957年移存于西安碑林。
《曹全碑》碑面记载了曹全略历及其官在任时平定乡里的功绩。曹全,号景完,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举孝廉,除郎中。因地方骚乱,转任郃阳(今陕西合阳)令,收拾流散,纠集残余,使乡里安定。时民感曹全功高,其部下属官王敞等为之刻石记功。①碑文内容的归纳参考陈玉池《汉〈曹全碑〉译注》,《中国艺术报》2004年12月3日,第T00版。
首先,《曹全碑》具有“纪念碑”式的功能和意义。
碑之所以立,为纪功表绩。东汉桓灵时,“官举孝廉”的官僚选拔系统主要通过考察品行德能来甄选人才。下层民意的反馈以及官僚梯队的联结形成,主要还是依靠功德歌颂和民意沸扬的途径来实现。由此,碑石以本身具有的载体特性及其社会化的设施功能优势,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层统治阶层考察社会民生的一个重要渠道。从这一功能层面来说,碑、石尤其是立于庙宇高堂、府阙门庭的方碑,俨然成为了具有“窗口”意义的书文载体。无论是假意的奉谀还是真心的感德还愿,无论是碑文还是碑体,都具有社会化的“纪念碑”意义。
那么,因这一重特殊的意义,两汉碑刻上的书文有别于书面文檄的特有面貌。
其次,关于“汉碑四品”。
从流传下来的碑碣拓本,并结合明清书史中对碑的散见描述,可知东汉碑刻上体现的成熟隶书体,是书体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环扣。东汉永寿年间成碑的《礼器碑》、建宁年间的《史晨碑》、中平年间的《张迁碑》,并同是中平年间的《曹全碑》,被书史推崇为“汉碑四品”。若“瘦劲如铁”“清超遒劲”(清王澍《虚舟题跋》)有《礼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部伍整齐,凛不可犯”(清万经《分隶偶存》)有《史晨碑》;“端正雅练”(清杨守敬《平碑记》)、典雅而又有古意的有《张迁碑》;《曹全碑》则代表柔美一路,秀雅灵动。
钱泳《书学》谓:“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所谓“四品”,自然是沿着书家文人习惯性的审美趣味,将存世的诸多汉碑分类归宗了。这四碑,则代表了这诸多风格中的刚柔两派,各具面貌和情态。
《曹全碑》是明代出土最晚的一通汉碑,拓损相对其他三碑少,且字形平整优美,笔法流畅灵活,在风格上,与汉简《士相见之礼》最为接近。
三、“碑本”与“写本”的思考
一般而言,碑帖并论。“碑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含材质属性、书写方式的叙述,同时也包括了气质、审美和风格流派的综合体现。“碑学”与“帖学”相并相较,基本构成了整个明清书史的框架。非“碑”即“帖”,成为了明清书法实践活动和审美的标向。广义的“碑”和“帖”,除了在书风和章法上有媸妍拙媚的表相对立,最本质亦最重要的是“不法”与“法”的矩度问题。掀去书法宗分的外壳,其内在不过是明季知识分子的一份自省,一种对自身身份的追溯和反思。
这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
这里提“碑本”与“写本”,只从狭义的载体概念层面,观察同一种书体——隶书在不同应用场合体现的状态。而实际上这种状态的区别,在书体风格的体现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例如仅从文字学的角度上看,汉简《士相见之礼》与汉碑《曹全碑》书字基本属于今文字。经学没落并今文学初立的两汉时代,同时已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蜕变。简本《仪礼》三本九篇共存27 400余字,都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所谓今文。②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称:“这二万七千多字,都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所谓今文。它在文字结构和说文解字并非全同,用它可以对照汉代其它器物上的隶书。说文一书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古文字,他并不代表汉代真正通用的文字。只有在武威汉简上,我们看到西汉经师所认可的今文,也可以看出书手们力趋简易的写法,说明了解除了繁复的弯曲的篆体以外,书写者对于简易文字的要求。”见《考古》1960年第8期,第33页。编者按:引文中“二万七千”“说文解字”“其它”“他并不代表”,原文如此。《曹全碑》所载亦是发展成熟的隶书,两者所反映的汉代官行隶体使用状态基本相近,只个别存在使用习惯的差异。
西汉末期,简牍隶书逐渐脱离古隶的形式,演变发展为成熟的汉隶。这时期的隶书以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简书为代表。这批简书为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所书,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注》及历书、占卜等古籍。
东汉简牍隶书艺术已达到顶峰时期,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简书《仪礼》,是前后比较完整的简册。全册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其书结字中敛略呈斜势,用笔顿挫富于变化。[4]
从书风和用笔看。行笔的提按顿挫、笔锋的突露和收放以及“切”“折”“翻”等反映书写速度和节奏的细节,在写本隶书中保留更多——关于用笔的可读信息更多。碑本的隶书经过书丹到上碑、碑刻到拓本,其中从“写”到“刻”会损失大量书写的动作和细节。可以认为,碑本隶书包含了更多人为修饬的因素,保留了时代的普遍审美眼光,加之岁月的洗礼和剥蚀,碑本隶书给予观者的更多是沉雄、古拙、雅练、遒劲的直觉触动和启示。
那么,关于写本隶书与碑本隶书的思考,落在“书写”本身,具有以下的意义。
首先,写本与碑本本身存在阅读方式和功能的区别。我们平常所说书法的章法也牵涉到字行布局与阅读方式的关系。前文提及作为一部两汉今文学的儒家经典,汉简《士相见之礼》是其时士大夫研习和自修的通行版本。此类经籍写本的章法,配合了书者跽坐并悬腕、枕腕交替使用的书写方式,与日常书籍阅读、文章写作的习惯相符。又,写本本身面对的首先是个人,而碑本面对的则是公众。那么,写本隶书满足的基本是士大夫阶层少数人亦即精英个体的审美,而侧重“纪念碑”功能的碑本隶书满足的是社会公众亦即社会性群体的审美。
其次,这些差别导致的审美要求,带来“书写”的隐秘性和社会性改变。所谓“书写”,是一个复合的模式,具有太多的心理因素和行为因素,无法简单地去描述其行为的动机、起灭过程和轨迹。尤其在面对所谓的“书法作品”或“非书法作品”的日常文字书面运用时,将“书写”从中剥离并定量描述其状态,似乎不可能,也不纯粹。机械的手部动作,何时、如何、为何从“描述”转化成带创作意味的“表现”,包含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偶发动机。在书法实践中,“书写”不能看作单纯的描述动作,而同时也是表现的动作。那么,隶书在不同审美要求的状态下,“碑本”为符合群体公众和社会风尚的口味,将“书写”及其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和不统一因素,修饬统一;而“写本”,则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书写”过程的偶然意趣,以及软笔书写工具与硬质载体之间相抗相合的火花。
总而言之,碑本隶书美在于“统一”后的范式美,产生更大的社会化审美功效;写本隶书美在于“统一”后的随性美,体现更多“书写”本身的变化和随性的意趣。
小结
通过对碑本隶书和写本隶书的观察,依然无法清楚厘定“书法创作”的关键——“书写”的动机变化与心理轨迹。但是我们能够从同一种书体处于不同的使用场合和在不同审美要求下的状态和表达的差异,捕捉“书写”这种行为在隐秘性和社会性之间切换的异态和变化痕迹。尤其在写本——简牍帛书墨迹中,能够看到“书写”在“书法”初生阶段中更自然和更原始的状态和面貌。
比起体现强烈的创作欲望和饱含情绪表达的书作而言,“书写”的本体在这里就可能显得相对纯粹了。
[1]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J].考古,1960(8).
[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J].考古,1960(5):11-12.
[3]卢辅圣.书法生态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13-14.
[4]王靖宪.汉代的简牍书法[J].中国艺术,1997(1):64.
(责任编辑、校对:李晨辉)
From Inscribed Bamboo Slip Rituals of Scholars from Han Dynasty to The Stele of Cao Quan:a Probe into Written and Stele Official Scripts
ZHAO Kaixin
Existing steles are inspiring in terms of the vicissitudes of officialscripts.However,owing to th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steles,adjustment had been made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written script to steles.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ritten official scripts by comparing Bamboo Slip Rituals of Scholars from Han Dynasty and The Stele of Cao Quan,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and aesthetics.
Official Script;Written Scripts;Scripts on Stele;Writing
J120.9
A
1003-3653(2016)02-0037-04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2.006
2015-10-26
赵凯昕(1979~),女,广东广州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绘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