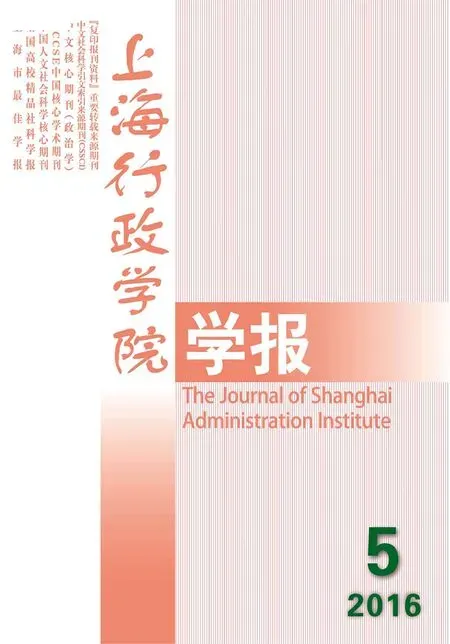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刘学浩 刘训练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000)
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刘学浩刘训练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000)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并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和研究。他的代表作《君主论》在中国有多种版本。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时代主题,也启发和影响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但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遭遇到的更多是拒斥和批判。本文描述了马基雅维利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并分析他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国家理性论
一、小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统中国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均出现严重危机,对外不足以应对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对内不能回应和容纳社会经济变迁产生的新的政治诉求。显然,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路径与思想资源已经无法支撑上述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而在欧风美雨的催生下,近代中国人开始参照、借鉴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经验与理论。然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政制复杂多样,政治思想主题与理论范式几经转换,构成了一种与“一以贯之型”中华政治文明在制度形态、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方面截然不同的“多元演变型”政治文明传统。面对一个如此异质并且内部多样的政治文明传统,中国人做出了怎样的摄取与转化,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便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议题。
本文旨在考察马基雅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的著作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时间下限设定在1949年),特别是考察他的国家主义思想是如何被近代中国人认识、理解、吸收和转化的。①选取这样一个主题乃是基于如下考虑:虽然数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围绕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诠释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但他却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他生活的时代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由盛而衰的转棙点,马基雅维利深厚的古典学修养、强烈的时代意识、敏锐的政治分析能力、卓越的写作技巧和犀利的文风使他在西方思想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积极谋求意大利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他对现代政治的深刻洞见,都使他的著作和思想与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产生明显的关联。
的确,自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在20世纪初出现在中文知识界起,中国人对马基雅维利及其主要思想绝对是不陌生的。不仅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君主论》在近代中国有多个版本面世,他的名字与简介还出现在多种出版物中,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甚至文学艺术等学科的教科书中,还是在专业学术杂志和大众报刊上都有他的踪迹。不过,近代中国人对马基雅维利的认识又是肤浅和刻板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也刚刚起步,马基雅维利的复杂性并未得到充分展现,作为初识西方思想的中国人自然也不可能发现和理解其中的奥秘;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思想中浅白和广为人知的部分也恰好与近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时代主题足够契合。
二、马基雅维利在清末的最初传入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马基雅维利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次出现可能是在严复所译的《法意》中。在第6卷第5章孟德斯鸠评论马基雅维利处,严复加注称马基雅维利(严复译为“墨迦伏勒”)为“大政治思想家,佛罗连思人。尝论其国治制,又著《帝王要术》一书,为此学巨子”。②由于严复未附注人名原文,而且在“按语”中也未加评论,读者未必会对这位“巨子”给予足够的注意。虽然这不是马基雅维利唯一一次出现在严复笔下,严复晚年对马基雅维利还有三次提及,但因为受到这些文字本身性质的限制,③一般读者应该不会通过这些文字了解马基雅维利。
稍晚于严复,梁启超在他的名篇《开明专制论》中也介绍过马基雅维利。按照梁启超的解读,古今中外的很多思想家都成了开明专制论的支持者,中国开明专制论的代表是法家思想,而在西方,“于近世史中,为政法学先登之骁将者,麦加比里也,而彼实绝对的主张开明专制之人也。其言曰:‘为君者,唯使国家陷于危亡,斯谓之恶。苟有可使国家安富尊荣者,无论造何种恶业,不得以恶论。’又曰:‘当国家危急时,何者为正义,何者为邪恶,何者为慈悲,何者为残忍,何者为名誉,何者为耻辱,举国人民刍狗之、牺牲之,以为救助国家生命、维持国家独立之用,不为过也。’”④在附注中梁启超还依次介绍了马氏的著作(《君主论》《论丛》[即《李维史论》])、历史的方法、性恶论以及思想产生的背景(意大利分裂的状况)等。梁启超在这里虽然对马基雅维利颇有赞赏,但他对马基雅维利的了解应该非常有限,并无深入研究。《开明专制论》里对马基雅维利的介绍包括那两句引文,属于典型的教科书式写法,应该是转引自日文的二手资料。⑤而当梁启超在1923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再次提到马基雅维利的时候,他竟然把马基雅维利的名字都搞错了。⑥此外梁启超也并未有其它谈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虽然梁启超本人和他掀起的论战乃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但人们恐怕很难会在其中留意到马基雅维利。
1908年,在日本创刊出版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河南》杂志接连刊发了两篇文章,都提及马基雅维利。一篇是“令飞”(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⑦另一篇为“旒其”(许寿裳)的《兴国精神之史曜》⑧。两位作者同梁启超一样,看似旁征博引、中西贯通,但也只是蜻蜓点水,无非是展现了初具世界眼光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气象而已。1910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1912年曾再版)中,还用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一概念⑨,不过由于他以英文写作,中国读者应当非常有限。
相比于下面即将谈到的民国时期,在清末,提及马基雅维利的多是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他们本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限于种种原因,其他中国人应该很难通过他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进入民国之后,由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出版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马基雅维利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而他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形象便是那最广为人知的标签 “马基雅维利主义”。
三、马基雅维利主义
1912年3月至5月间,上海《民立报》连载了马一浮翻译的法国人博洛尔(Louis Proal)著作《政治罪恶论》,这是一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西方政治中的影响的著作。本书第一章章名即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一浮译作“权谋篇第一”)。作者认为在西方政治史上,政治家们都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无论君主政治、民主政治,其身为政府者,往往弃道取容,杀人以自固,如出一辙”。⑩而近世的革命政府也难逃这一窠臼,“革命之政治家,自米拉波至于拿破仑,皆躬行麦卡费里主义者也”。⑪《民立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以说近代中国人对马基雅维利的第一印象便是为谋求政治权力无视道德仁义之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1927年马基雅维利逝世四百周年之际,《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短文《马吉亚佛利四百年纪念与今日欧洲的政治实际》,延续了这一思路,认定“今日各国帝国主义政治的实际,确在实现马吉亚佛利的政治学”。⑫作者把《君主论》(作者译为《王者》)与《李维史论》(作者译为《衡论》)统一起来,称马基雅维利两部著作“一方面要伸尊严的王者之权,或巩固的民主中央之实力;一方面要用狡狯的手腕,获得外交的胜利”。⑬不过,作者对世界形势颇为乐观,认为如今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相互依赖超过了政治因素,构成了和平的根基,马氏学说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显然,作者误读了马基雅维利也错判了世界的形势。
《君主论》最早的两个中译本的书名分别叫做“霸术”和“横霸政治论”,同样是出于类似的考虑。⑭《霸术》的译者伍光建在“序言”中尚以爱国主义稍为马基雅维利一辩。⑮而《横霸政治论》的译者曾纪蔚则在“译者序”中认为,在过往政治思想史上 “赤裸裸的描写人类的本性——势利,专横,阴谋——的,首推功利主义派麦克维利的‘横霸政治’了。……他用事例观察的方法,得着不少的结论。这种结论就是今日帝国主义的原理,也就是今日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蓝本”。⑯译者甚至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影响到近日帝国主义的伸张凌迫,比十八世纪卢骚民约论的影响于法国革命、孟德斯鸠三权论影响于美国宪法确有同日而论的价值”。⑰因此,译者认为中国作为受压迫民族理应了解西方列强的理论基础,但是,在了解西方帝国主义的根源后中国又当如何,译者并没有给出自己的意见。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有两面的。在作为被压迫者的近代中国人看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视公义、侵害中国利益当然是一方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马基雅维利主义还有“国家理性论”的一面⑱,即“为了实现某种公共的目的或者崇高的目的而不得不采取某些恶劣的手段,但目的(依据更高的道德或‘超道德’)可以是这些做法得到辩护、正当化(justify),或者至少得到原谅”。⑲而马基雅维利的这一面也被某些中国人所注意并试图加以运用。
四、国家理性论
民国时代,已经有学者明确使用了“国家理性论”这一概念指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王赣愚在1935年即指出,马基雅维利“唯一任务在树一种政治行为之论据,今人援用新名词,称之为 ‘国家利害说’(Raison d'état)。……政治之于道德,犹道德之于自然科学,各划鸿沟,格格不相入;道德仅为私人行为之准则,而公共行为则当以政治目的为依归。马氏对伦理与宗教持同样之态度,故意置之不问而不直接加以反抗,其意以为政治之为物本无道德与不道德之可言,世之所谓‘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者,乃名辞上之矛盾耳”。⑳
其实,较早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得到国家理性论启发的是严复。在1916年9月10日写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严复感慨若熊纯如能读“墨迦维黎”(即马基雅维利,译法与《法意》中不同)与“脱雷什奇”(Treitschke,今译特赖奇克)的著作便能理解,“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皆在其次”。㉑严复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乱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袁世凯,“项城不过因势而挻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㉒而令严复感到遗憾的是,袁世凯“表现出了马基雅维利式统治的所有令人讨厌的方面,而不具有任何真正的达到马基雅维利式目标的能力”。㉓20世纪30年代,中共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张申府在《续所思》中也曾流露过类似的思想。他自称“前些年我喜言,‘抱定目的不择手段’。这自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而为今日墨索里尼先师的马奇维里所持的‘目的证成手段’同科”。㉔他和严复一样期待中国出现一位 “大政治家”,“大政治家必既能认清了目的,更能认清了现下那些可能的手段可以达到那个目的,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而切实以行之”。㉕
最明确地提出要以马基雅维利为师的则是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1933年陈其刚在《复兴月刊》上发表《马克维尼与中国复兴》,称当时的中国就如同中世纪的意大利,“要复兴中国就必须要步着马克维尼的后尘努力前进”。㉖1935年“翼民”在大连的《新文化》月刊上发表《马凯维尼与中国革命》一文,亦称“在这危机四伏的危险中,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正是我们的榜样,马凯维尼,正是我们革命的导师”。㉗陈其刚赞赏马基雅维利“不顾什么道德不道德,宗教不宗教的,在他看来,只要为了国家的福利,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大目的”。㉘因而,他主张对中国人来说,“在根本上,自然的原则就是生存竞争,优则胜,劣则败,我们要用空想的伦理的观念,来制止自然的发展,岂非自寻苦恼?于事丝毫无补,徒见其心劳日绌而已。我们不要生存则已,要生存就要准备实力来竞争,为整个的国家,为全体的福利,而奋斗,而牺牲,这,对于人类文化是一个最好的推动机,对于世界前途是一个最光明的探照灯”。㉙“翼民”则疾呼:“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要实行统一,为实行统一,我们要实行独裁政治;为完成革命,我们要培养武力,注重权术。同时对反革命分子,毫不客气的加紧彻底拘惩或屠杀,以杜贻祸而免蹈近年来优容反革命分子的覆彻底。更重要的我们要把政治道德自私人道德中分出,万不能因为要避免自己恶名,置国家于不顾。要这样革命才能完成,国家才能统一,民族才有出路!”㉚此种狂热的呼吁不啻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宣言,只是这种宣言毕竟太过惊世骇俗,而且它本身正好展现了马基雅维利式国家理性论的危险之处,注定无法获得广泛的响应。
实际上,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理性论其实并不陌生,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所秉持的就是国家理性论。只不过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的理论多来自德国,“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德意志国家主义的接受史”。㉛奉行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繁复精微的哲学体系的道德压力显然小于公然拥抱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朱执信承认马基雅维利“其说以为国家之有危机,人惟当取必要之手段,以救助国家生命、维持国家独立。……以国家存在必要为第一义,一切道德宗教皆只认为国家所用手段而已”。但他立刻指出马氏之论“不过当代政局之反映,以其奉职二十余年之经验,使成为非宗教、非道德之政治家。论史以罗马为宗,从而不止主张国家主义,实并行主张帝国主义”,并以马氏之“国家主义”未能唤起意大利人为由责其实效不强。㉜“战国策派”的领军人物雷海宗在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欧洲通史》课程提纲中曾对马基雅维利有较为详尽的评述,但也未曾发挥马氏学说以为己用。战国策派中也仅有何永佶在他的《论国力政治》中正面赞赏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㉝王赣愚虽对马基雅维利多有肯定,㉞但他也明确对马氏学说表示警惕:“就其精神而言,马氏不愧为近世民族主义的先导。称他为爱国者,爱其祖国意大利者,自无可疑义的。在评者看来,他的学说确是目前我国的兴奋剂,而绝对不是今后我国的万病药。”㉟
五、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学术研究
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政论性论说,民国时期也有不少针对马基雅维利的专业学术研究。㊱1916年严鹤龄的《东西政治思想之变迁》可能是近代中国人最早论述政治思想通史的专题论文。作者在文中将马基雅维利与亚里士多德作对比,凸显其方法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至十四世纪,人厌空谈复归实际,希腊罗马之典籍趋之若鹜,政治之学乃复燦然。当是之时,有政治大家马基樊里与焉。马氏踵希腊亚利斯大德之后,以实地研究为根据。所不同者,亚氏综观各国政象之全体,分门别类,然后志其异同求其会通,而明千载不易之理。马氏不然,不志异同不求会通,就事论事,以求解决之方。……故亚氏者,政治学家也,马氏者,政术家也(马氏生于意大利福洛莲次城)。……马氏学说,时事使然,而亦代表欧洲文学复兴时代之政治也”。㊲这种论述方式是比较典型的,同时期的各类教科书上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介绍多遵循此路径:介绍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及著作,指出其方法是历史的和唯实的并常与亚里士多德相联系,论其观点(不计道德、以国家为重及主张阴谋诡诈之术等等)则必归因于时势并指其为政策、政术而非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思想了解的加深,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水平也在提高,出现了专论马基雅维利的论文。㊳此时期马基雅维利研究较为杰出者应属浦薛凤,他引用了《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三本著作,条分缕析地介绍了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权术、党争、军事、宗教等方面的观点,论述全面且注释较为规范,其中尤其以马基雅维利论人性和党争最为新颖,之前和同时代的学者在谈论马基雅维利时是鲜有论及的。㊴不过,浦薛凤终究是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通史的写作,并非是对马基雅维利的专门研究。同一时期内他专文研究过洛克、伯克、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英国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并未对马基雅维利有太多的注意。
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最为突出的当属吴恩裕。吴恩裕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教于拉斯基,并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为主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即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1944年至1948年间他共写过4篇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文章:1944年的《马开维里论人性、政治、道德及法律》(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9号)、1946年的《马开维里的时代著作及其方法》(载 《读书通讯》第108期)、1946年的《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书评(载《观察》第3卷第22期)和1948年的《马开维里的政治“理论”及其意义》(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为1944年论文的扩充)。另外,在1948年出版的《唯物史观精义》中他还比较过马克思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论。可以说吴恩裕是相当看重马基雅维利的。
吴恩裕的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关于道德的看法。前人往往着眼于论述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而吴恩裕则指出马基雅维利是将道德视为一种工具或“社会的力量”,即承认“道德的手段,往往使实行者受害;而用不道德的手段,却往往使实行者得到利益。因此,在他看来,不是抽象的‘应不应该讲道德’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不应该采取道德手段的问题”。㊵吴恩裕的研究与前人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立场。他突出马基雅维利所持的“自私自利”的人性论,认为此论在推导私有财产与国家关系方面有重要意义。吴恩裕认为,“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类必然有自私的习性”㊶,而这自私的习性又促使人获取更多的财产,并要求国家保护这些财产,马基雅维利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才奉劝君主勿夺人民财产,因而“马开维里实在奠定了近代政治理论的主要题材”。㊷但他们都不能“认清这经济意义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阶级特质”,于是只能由“马克思补足了他们的缺憾”。㊸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在吴恩裕这里达到了最高峰,也终结于此。
总的来看,在民国时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基雅维利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多种版本的《君主论》得以面世便体现了这一点。除了前文提到的两个中译本和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节译之外,尚有中国文化学会出版的全译本《君》和编译本一种㊹。此外,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由钱端升节选、加注以及导读的英文本《霸术》,收在“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中。㊺《李维史论》常被译作《论丛》《书后》,虽然没有中译本,但多为论者引用。《佛罗伦萨史》和《战争的技艺》则鲜有论者提及。㊻倒是马基雅维利的讽刺小说《魔鬼娶亲记》(Belfagor arcidiavolo)曾被胡适注意到,但也只是作为一则笑谈。㊼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君主论》的第三个中译本,由张左企与陈汝衡合译的《君》。出版《君》的机构是“中国文化学会”,这是中国准法西斯组织“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之一。㊽“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别称“蓝衣社”)组织体系庞大,拥有多种文化机关,其基层组织“复兴社”在各地的成员还参与创办了多种刊物,其中包括一种《国际译报》杂志。1934年《国际译报》的第3、4期合刊为意大利专号,文章多涉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君》的译者张左企与陈汝衡也均有译文和论文在该杂志发表。从中国文化学会将《君》列为“世界名著丛书第一种”翻译出版和组织《国际译报》的意大利专号可见当时力行社系统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瞩目,当然这也是力行社的组织性质使然。只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借助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来整饬腐化的国民党,但他仍坚持儒家思想为中国根本,最终没有公开奉行法西斯主义。力行社也因此始终是一个秘密组织,而没有公然成为中国的“党卫军”。“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也是宣称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兼收他国文化,1933年的 《中国文化学会缘起》㊾可反映其旨趣。因此,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邓文仪在为《君》所做的序言中才会既承认马基雅维利“尚权术以成霸道,西方之所称而吾华之所轻也”,㊿认为阅读此书可帮助国人了解西方政治,但又要指出西方虽以霸术而强却未必值得仿效,中国还是应当回归孔子的仁政王道。
六、结语:近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马基雅维利
总体来看,在1905-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基雅维利的名字、著作和思想并不陌生。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君主论》有多种版本面世,无论是在公共舆论的平台还是在学术研究的园地,马基雅维利都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思索中国的建国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当然,这种启发是有限的,关注到马基雅维利的论者大都对其学说和主张保留了一些疑虑和排斥。因此,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从情理上讲,马基雅维利与西方古典伦理思想的决裂、他的爱国主义及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本应该对近现代中国人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然而,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马基雅维利与古典传统到底是何种关系也仍未完全澄清,而他对基督教传统的彻底背离只有在现代早期欧洲的语境之下才显得骇世惊俗,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下,马基雅维利这一最具现代性的面相是很难激起多大回响的。在第二个方面,马基雅维利为救治当时意大利局势所开的药方,无论是《君主论》中的“权谋论”,还是《李维史论》中的“共和论”,对于处于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不可能引起太大共鸣:“权谋论”在基督教传统与复兴古典文化的人文主义风潮中当然显得意义非凡,但比之于久远的法家权术传统却卑之无甚高论;“共和论”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只有对西方古典政治史有透彻的理解之后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刻意蕴,对于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君主制/共和制”问题的中国人来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兴趣。
在近现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思潮中,只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能够与马基雅维利产生一些联系。马基雅维利当然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但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他充其量只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以及墨索里尼的一位遥远先驱而已。并且如朱执信所言,马基雅维利的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中的 “帝国主义”成分(当然包括马基雅维利本人狼藉的声誉)及不够系统的理论均不足以成为中国国家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更不幸的是,对于受压迫民族的国家主义者而言,撇清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过多地征引这位“邪恶导师”显然无益于他们的事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逐渐成为“反动”的代名词,马基雅维利也就彻底退出了公共舆论。在学术领域,吴恩裕固然强调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史地位,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下,他不过是“人类最壮美的日出”之前诸多闪亮的星光之一,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必然会被忽略而无法得到恰当的探讨。当然,张申府所期待的“抱定目的不择手段”的“大政治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终究不乏其人,“目的证成手段”的逻辑实际上也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以此观之,至少某个面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虽然未必直接来自马基雅维利本人)从未退出过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话语。
无论如何,从西方政治思想传入中国的一般情况来看,当时最时髦、影响最大的思想与流派往往率先被译介到中国,并引发国人的关注和辩论;而且,这种传播不止于智识上的兴趣,更因应于时局与政治需要。马基雅维利的例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马基雅维利被尊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但对急于“仿泰西之良法”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思想和主张却显得过于古旧和乏味,甚至让人反感:在早期,马基雅维利显然不如穆勒(密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兴民权、开民智”方面来得解渴;到后来,更不如马克思(主义)、拉斯基甚或墨索里尼等人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方面来得更有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及其著作与思想只能是“耳熟而不能详”了。
注释:
①此前,国内学术界除了李长林教授在他的《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载郑大华、邹小站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中对该主题略有涉及之外,尚未见任何介绍和研究。
②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第150页。
③ 一处仅为一句批语,参见严复:《李斯 〈论督责书〉批语》,载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5-1196页;一处为一篇英文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Yen Fuh,"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i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16(4),p.20),中译文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页。另一处是在写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详见下文)。
④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新民丛报》(第11册),1906 年1月25日,第18页,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版,第9906页。两句引文应分别出自《君主论》第15章末及《李维史论》第3卷第41章。
⑤当时的日本虽然已有《君主论》的日译本(1886年,集成社),但《李维史论》的日译本则是1906年(博文馆)才出版的,所以,梁启超纵然能够读到《君主论》,也很难读到《李维史论》。
⑥“米奇维里(Michiavlli,1492生1527死),意大利人。著有《君主政治论》一书,欧洲人以为近世初期一名著也,其书言内治外交皆须用权术,十八九世纪之政治家多视为枕中鸿秘”(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34页)。有趣的是,1930年梁启超的学生杨鸿烈在其《中国法律发达史》中部分论述与梁启超的论述颇为相近,杨将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拼做Michiavelli,仍旧是错的(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87页,此版影印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顺便一提,1906年革命派阵营中与梁启超论战的朱执信在文章中也提到过马基雅维利,将他作为“君权不当限制之说”的代表人物,只是他搞错了年代,有“十七八世纪中霍布士、马奇斐利亚辈”之语(参见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民报》1906年第五号,第46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第666页)。
⑦令飞:《摩罗诗力说》,载《河南》1908年第3号。
⑧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河南》1908年第7号。
⑨辜鸿铭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可能导致 “马基雅维利主义”。参加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辜鸿铭接下来反复提到这个概念,参见第335、337、338、340、341页。
⑩ 布乐德鲁易:《政治罪恶论》,马一浮译,《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第279页。
⑪ 布乐德鲁易:《政治罪恶论》,马一浮译,《中国文化》2015年第1期,第279页。
⑫ 文宙:《马吉亚佛利四百年纪念与今日欧洲的政治实际》,《东方杂志》1927年第13号,第78页。
⑬ 文宙:《马吉亚佛利四百年纪念与今日欧洲的政治实际》,《东方杂志》1927年第13号,第77页。
⑭ 《君主论》还有一种节译本,书名译为“制霸论”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一节译包含在《马基维尼与制霸论》(王明甫:《马基维尼与制霸论》,《政治季刊》1933年第2期)一文中。该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和观点,下篇则节译了《君主论》的第15章、第16-19章、第21章,所据底本情况由文后参考文献推测应为一个英文版的政治哲学读本(Francis William Coker ed.,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Toronto:The Macmillan Company,1914,但此选读并未收入第15章。王文参考文献中另列有英文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却未注明具体版本)。
⑮ “以意大利城市邱墟,人民涂炭,异族横行,不复能制,非治标无以救国,无以统一。观此书之本章,其悲愤爱国,情见乎辞,不啻一字一泪,岂可以其惨酷而少之哉。”(伍光建:《序言》,载马加维理:《霸术》,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页。)《霸术》是《君主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为节译本,此书正文仅64页,所据底本不详,译者分别以“分界不清晰”和“与今日时势不合”为由未译出第1章和第10章(马加维理:《霸术》,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24页)。
⑯ 曾纪蔚:《译者序》,载麦克维利,《横霸政治论》,曾纪蔚译,光华大学政治学社1930年版,第1页。从译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可以猜测,译者的《君主论》底本应该是1913年的一个英译本(Machiavelli,The Prince,N.H.Thomson tra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13),参见曾纪蔚:《清代之监察制度论》,兴宁书店1931年版,第8页。
⑰ 曾纪蔚:《译者序》,麦克维利:《横霸政治论》,曾纪蔚译,光华大学政治学社1930年版,第2页。
⑱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参见刘训练:《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学海》2013年第3期。
⑲刘训练:《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是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第91页。
⑳王赣愚:《马克维尼与近世政治思想》,《民族杂志》1935年第4期,第698页。
㉑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八),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6页。
㉒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八),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5页。
㉓参见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㉔张申府:《续所思》,张申府:《所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8页。张申府的《所思》出版于1931年,《续所思》则是在1933-1934年间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这时的张申府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书,暂离政治活动(此前的1920-1925年间他参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还曾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而此后的1935年他又同他人一起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㉕张申府:《续所思》,张申府:《所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9页。
㉖陈其刚:《马克维尼与中国复兴》,《复兴月刊》1933年第1期,第4页。
㉗翼民:《马凯维尼与中国革命》,《新文化》1935年第1期,第41页。
㉘陈其刚:《马克维尼与中国复兴》,《复兴月刊》1933年第1期,第9页。
㉙陈其刚:《马克维尼与中国复兴》,《复兴月刊》1933年第1期,第15页。
㉚翼民:《马凯维尼与中国革命》,《新文化》1935年第1期,第44页。
㉛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页。
㉜朱执信:《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建设》1919年第2号,第22-23页。
㉝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代表了西方源远流长的 “国力政治(Power Politics)”,只有“力”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尽管你怎样谈仁义道德,尽管你谈得天花乱坠,说得花团锦簇,统一一个国家还是需要军队,兵器,和武力。这个武力在数个政治权力之下则相消,在一元化的政治重心下则可完整对外”。何永佶:《论国力政治》,载《战国策》1940年第13期,第5-6页。何永佶进一步解释道:“马奇维里主义是用以对外的,而不是用以对内的,对内愈应用它而对外愈不能用它,因为内部愈马奇维里式,则团体的力量自己相消愈甚,对外的力量愈见为微弱。”何永佶:《论国力政治》,载《战国策》,1940年第13期,第7页。而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正是因为缺乏“力的文化”“战的意识”。
㉞如他认为人们常常只见战争的凶险,却忽视“对外战争之有刺激民族意识的功效……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克维尼(Machiavelli),早已看到战争是治疗弱国的良剂,其所以推崇穷兵黩武的雄主,无非欲靠他做统一的中心;其所以鼓励拓地扬威的伟业,亦所以启发当时人民爱国的情绪。依马氏看来,战争是一国生气的特征,也是一国强盛的途径”。王赣愚:《抗战与统一》,载《东方杂志》1938年第4号,第19-20页。
㉟ 王赣愚:《政治与伦理》,《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2期,第488页。
㊱ 这里所谓的专业学术研究指的是发表在学术刊物,立论平实论证相对严谨的论文。
㊲ 严鹤龄:《东西政治思想之变迁》,《政治学报年刊》1916年第1期,第167页。
㊳ 如前文提到的王明甫的《马基维尼与制霸论》、周克传:《马克维尼之政治哲学的分析》,《政治期刊》1935年第4期、吕梦蕉:《欧洲中世纪之国家观》,《政治期刊》1935第4期 (《政治期刊》与前文提到的《政治季刊》为同一份刊物,1931年复旦大学政治学会创办《政治学报》年刊,1933年更名为《政治季刊》,1934年又更名为《政治期刊》,参见:《上海社会科学志》第五编第 三 章 第 一 节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 node74288/node74297/node74447/node74451/userobject1ai90510.html。)、傅遂之:《马克维里政治思想之研究》,《国本》1937年第1卷第10期。
㊴ 浦薛凤:《自柏拉图至孟德斯鸠——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之渊源》(二续),《民族》1933年第1卷第11期。
㊵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观察社1948年版,第27页。
㊶ 吴恩裕:《〈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书评》,《观察》1946年第22期,第19页。
㊷ 吴恩裕:《马开维里的政治“理论”及其意义》,《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8年版,第14页。
㊸ 吴恩裕:《马开维里的政治“理论”及其意义》,《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48年版,第3页。
㊹ 此编译本为柯柏年所译《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第7章的马基雅弗利《霸术》。此章将《君主论》摘编为四部分:一、以才能得国;二、不以才能得国;三、如何保有其国;四、机谋。奇怪的是,在已有三个《君主论》中译本的情况下,编译者却称“就译者所知,尚未有中译本”(哈麦顿爵士编:《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精要》,柯柏年译,南强书局1936年版,第93页)。
㊺ 马基亚弗利:《霸术》(原版节选本),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该书采自里奇的英译本:Machiavelli,The Prince,Luigi Ricci trans.,London:Grant Richards,1903。
㊻ 李金髮在 《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论》一书中称意大利人“好行大志及超乎因果的大欲,有时使我们觉到一种奇形的真理”并引《佛罗伦萨史》序言中的一段佐证之(李金髮:《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7页)。
㊼ 胡适自1942年起开始收集各国有关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并根据自己的收藏戏言存在着某种定律:“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意大利倒有很多的怕老婆故事。到了1943年夏天,我收到玛吉亚维利(Machiavelli)写的一个意大利最有名的怕老婆故事,我就预料到意大利是会跳出轴心国的,果然,不到四个月,意大利真的跳出来了”(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83页)。
㊽参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八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页。
㊾部分内容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八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㊿邓文仪:《〈君〉序》,载马嘉佛利:《君》,张左企、陈汝衡译,南昌: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版,第1页。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Machiavelli's Thoughts on modern China
Liu Xuehao/Liu Xunlian
As an important thinker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s,Machiavelli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Then more and more Chinese intellectuals got knowledge of him and studied his thoughts.His famous The Prince was published in many versions in modern China.To some extent,Machiavelli's thoughts were fit for the state-building of modern China,and inspired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But there were more criticism and rejection than compliment.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transmit of Machiavelli's thoughts and offers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thoughts'impact on modern China.
Machiavelli;The Prince;Reason of State
B546
A
1009-3176(2016)05-019-(8)
(责任编辑 陶柏康)
2016-5-25
刘学浩 男(1988-)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训练 男(1977-)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