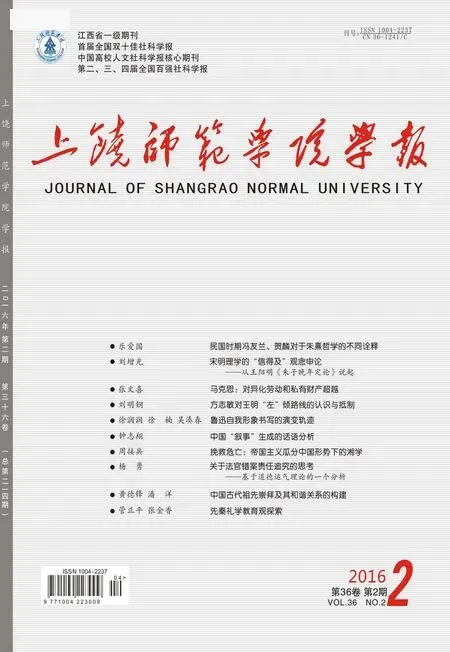民国时期冯友兰、贺麟对于朱熹哲学的不同诠释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民国时期冯友兰、贺麟对于朱熹哲学的不同诠释
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民国时期,冯友兰和贺麟都对朱熹哲学作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各自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冯友兰认为朱熹不能言“心即理”,而贺麟认为朱熹讲“心与理为一”;2.冯友兰认为朱熹的太极无动静,而贺麟认为朱熹的太极有动静;3.冯友兰认为朱熹的“格物”是道德修养方法,而贺麟认为是哲学的直觉方法;4.冯友兰认为朱陆异同在于本体论上朱熹讲“性即理”、陆九渊讲“心即理”,而贺麟认为朱陆异同在直觉方法的“向外透视”与“向内反省”之别,但最终殊途而同归。对民国时期以来朱熹哲学研究做出学术史的阐述,讨论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走向,无疑有益于当今的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冯友兰;贺麟;朱熹
民国时期,冯友兰对于朱熹哲学的阐释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的“朱子”章为代表。贺麟则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后来又发表《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宋儒的思想方法》等,对朱熹哲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尤其在朱熹关于心与理的关系、太极之动静、格物说以及朱陆异同等问题上,较为明显。对民国时期以来朱熹哲学研究做出学术史的阐述,讨论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走向,无疑有益于当今的学术研究。
一、对朱熹的心与理关系的不同阐释
朱熹《大学章句》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1]7但是又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当然,朱熹又特别强调“心”与“性”的不同,并且又讲“性即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于朱熹哲学的阐释,强调“心”与“性”的不同以及“性即理”,其中引述朱熹所言“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指出:“盖心能有具体的活动,理则不能如此也。”[2]915这是以朱熹的“心”与“性”的差异性以及“性即理”为基础,推出“心”与“理”的不同。冯友兰还根据朱熹反对释氏“以心为性”而强调“心”与“性”的不同、“心”与“理”的不同,指出:“心亦是实际的有,亦系‘形而下’者。若理则只潜存,故为‘形而上’者。”[2]927明确认为,“心”与“理”的不同,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不同。
正是通过辨析朱熹的“心”与“性”的不同,冯友兰根据朱熹所言“性即理”,推出“心”与“理”的不同,并由此而指出:“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2]939冯友兰是将朱熹的“心”看作“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因而“心非理”,此心为“形而下”;“心中之理,即所谓性”,性即理,而属于“形而上”,所以,“心”不仅与“性”不同,而且与“理”不同,于是,只能讲“性即理”,而不能讲“心即理”,“性即理”与“心即理”是对立的。为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还将程颐、朱熹言“性即理”,界定为“理学”,将陆九渊、王阳明言“心即理”,界定为“心学”。
对于王阳明说朱熹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指出:“朱子以为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太极即众理之全体;故吾人之心,亦‘具众理而应万事’。故即物穷理,亦即穷吾心中之理,穷吾性中之理耳。故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实未尽确当。”[2]955可见,冯友兰并不完全赞同王阳明所谓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但是,他又说:“惟依朱子之系统,则理若不与气合,则即无心,心虽无而理自常存。虽事实上无无气之理,然逻辑上实可有无心之理也。若就此点谓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固亦未尝不可。”[2]955对于王阳明所谓朱熹“析心与理而为二”,冯友兰虽然认为“未尽确当”,但还是认为“固亦未尝不可”,实际上又认同了王阳明的说法。
但是,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不同,黄子通于1927年发表的《朱熹的哲学》认为,在朱熹那里,“心是天地之心,心是万物之理”,并且还说:“朱熹所讲的‘心’,程明道所讲的‘仁’、‘性’,周敦颐所说的‘诚’,皆是异名而同实。朱子自己也说《定性书》中的‘性’字,‘是个心字意思’。……朱子的意思,就是宇宙的本体即在我心之中。我心以外,并没有超心的本体。”[3]显然,这是把朱熹作为宇宙本体的“理”与“心”看作同一的。贺麟于1930年发表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把朱熹的太极诠释为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唯心论中的“绝对理念”,并对二者的差异做出深入分析。该文指出:“朱子有时认心与理一,有时又析心与理为二。有时理似在心之外,如‘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等语的说法。有时理又似在心之内,如‘心统性情,(性即理,情属气)及‘所觉者心之理也’等处。”[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强调“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2]927,其中所谓“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很可能就是针对黄子通、贺麟而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后,有些学者就其中对于朱熹哲学的阐释提出不同观点。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认为朱熹“特别尊重‘心’和‘理’的合一”,因而专题阐述了朱熹的“心即理说”[5]287,并且还说:“晦庵是站在心的立场上去说明理。”[5]288“晦庵认心和理是同一的东西。”[5]297贺麟则仍然坚持此前发表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所提出的观点,说:“所谓心与理一之全,亦即理气合一之全(但心既与理为一,则心即理,理即心,心已非普通形下之气,理已非抽象静止之理矣)。”[6]与冯友兰“心非理”不同,贺麟强调朱熹的“心与理一”,而且明确认为,朱熹讲“心与理一”,即:“心即理,理即心”。
朱熹讲“心”与“性”的不同,并且又讲“性即理”,从逻辑讲,是可以推出“心与理而为二”,“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事实是,朱熹在讲“心”与“性”不同的同时,又讲二者的统一。他说:“心、性、理,拈着一个,则都贯穿,惟观其所指处轻重如何。”[7]89所以,“心”与“性”二者,“不可无分别,亦不可太说开成两个”[7]89。因此,他还明确说:“大抵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7]89就“心”与“理”的关系而言,朱熹很少把二者对立起来,反而是多讲“心具众理”“心与理一”。尤其是,朱熹还明确讲“心即理”。他说:“圣人之心,浑然一理。”[1]72“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8]又说:“仁者心便是理。”“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9]朱熹门人继续发挥这种“心即理”观念:“千言万语,只是欲学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穷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穷究,则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10]朱熹对此予以了肯定。虽然朱熹“心即理”通常是特指,讲的是圣人之心、仁者之心、知之至之心,即是理,并非就所有人而言,但无论如何,不是“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由此可见,朱熹讲“心”与“性”的不同,讲“性即理”,只是在理论上作出界定,并不是要把“心”与“性”、“心”与“理”分别开来,而是要在理论界定中,表达“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的关系,因而,“心”与“理”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关系。
二、对朱熹的太极动静的不同阐释
朱熹于宋乾道九年癸巳(1173)写成的《太极图解》认为,“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11]2。并且注《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曰:“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自然之理。)动静者,所乘之机也。(理搭于气而行。)太极,形而上之道也;(理不可见。)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气有可循。)”[11]5同年,朱熹《答杨子直》也说:“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此则庶几近之。……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12]显而易见,朱熹把周敦颐的“太极”解读为“理”,把“太极”动静看作“理搭于气而行”;并且还认为,太极有动静是指“太极”有动静之理,并非指“太极便是动静”。
但是,宋绍熙二年辛亥(1191),朱熹回应郑可学所言“太极理也,理如何动静?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南轩云太极不能无动静,未达其意”[13]2686之说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且以目前论之,仁便是动,义便是静,此又何关于气乎?”[13]2687由于朱熹在不同时段有诸多差异性的说法,以致引发太极或理本身到底是否动静的争议。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对太极动静作了讨论。他认为,在朱熹那里,“太极永久是有”,“太极亦无动静”[2]900-901。他还针对朱熹所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以及朱熹所赞同的“动静是气也”,指出:“‘动静是气也’,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故气得本此理以有动静之实例。……至于形而上之动静之理,则无动无静,所谓‘不可以动静言’也。”[2]901-902冯友兰认为,朱熹对于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采取了否定态度,属于“不通之论”。他还认为,太极有动与静之理,气有动静,而太极或理本身无所谓动静,他明确指出:“盖在朱子系统中,吾人只能言,太极有动之理,故气动而为阳气。太极有静之理,故气静而为阴气”;“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气因此理而有实际的动静。气之动者,即流行而为阳气;气之静者,即凝聚而为阴气。”[2]907这种观点,在冯友兰晚年所编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仍然可以看到痕迹:“太极是不动的,但其中有动之理,……也有静之理。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并不静。”[14]
张岱年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赞同冯友兰的观点,认为在朱熹那里:“太极中含动静之理,便能生阴生阳,而生出天地万物”;“太极即所以动静之理,便有动静而生阴阳。既生阴阳,太极即在阴阳之中;生出万物,太极即在万物之中。”[15]83
与冯友兰以为朱熹的太极无动无静的观点不同,贺麟于1938年在与张荫麟讨论周敦颐的太极与朱熹的太极的关系时,对朱熹的太极动静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张荫麟《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反对朱熹“以太极为理”,指出:“若以理释《图说》中之太极,则势须言理有动静。濂溪不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可也。朱子言太极为理,谓其动静不可也。”又说:“有动静之理,而动静之理本身无所谓动静也。……谓有动静之理,故气有动静,可也;谓理有动静之态,故气有动静,不可也。”认为朱熹的“理”本身无所谓动静,不能用以解说周敦颐的有动静的太极。[16]对此,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回应说:“你似以为周子之太极既是气,则谓气有动静,生阴生阳,本自圆通。今朱子释太极为理,谓理有动静,则滞碍而不能自圆,是朱子愈解愈坏,陷入困难。但须知,安知周朱太极或理有动静之说,不是有似亚理斯多德‘不动之推动者’之动静乎?亚氏之神,就其为Unmoved言,静也,就其为Mover言,动也。今谓朱子不可以动静言理或太极,则亚氏又何能以动静言神或纯范型乎?”[6]贺麟认为,解决周敦颐、朱熹的太极动静问题,关键在于对“动静”的理解。贺麟又说:“盖理之动静与气或物之动静不同(周子《通书》亦说明此点)。物之动静,在时空中,是Mechanical的,动不自止,静不自动。理或太极之动静是Teleological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其实乃显与隐,实现与不实现之意。如‘大道之行’或‘道之不行’,非谓道能走路,在时空中动静,乃指道之显与隐,实现与不实现耳。”[6]显然,贺麟认为,在朱熹那里,太极是有动静的,只是太极之“动静”并不是指在时空中的动静。
当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观点影响很大。直到1964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六章“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仍然持冯友兰关于朱熹的“理”无动无静的观点,其中说道:“太极本身无动静,……但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却都是太极作用的结果。”“太极本身无动静,但因为包含动静之理,因此气有动静。”[17]同年出版的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也说:“朱子以为太极具有动静之理,而不具动静之实。……因为太极具有动静之理,所以气得依据此理以显现动静之实。气动者为阳,静者为阴。阴阳为形而下者,动静之实(即实际的动静)也是属于形而下的。”[18]
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对于朱熹格致说,民国时期,蔡元培与胡适分别从工夫论和科学方法的角度进行了诠释,尤其胡适的诠释对学术界影响很大,并且还进一步衍生出从认识论角度对朱熹格致说的诠释。[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将朱熹格致说作为“道德及修养之方”来阐述,认为在朱熹那里,“工夫分两方面,即程伊川所谓用敬与致知”[2]919,从工夫论的角度阐释朱熹的格致说。冯友兰还说:“就朱子之哲学系统整个观之,则此格物之修养方法,自与其全系统相协和。盖朱子以天下事物,皆有其理;而吾心中之性,即天下事物之理之全体。穷天下事物之理,即穷吾性中之理也。今日穷一性中之理,明日穷一性中之理。多穷一理,即使吾气中之性多明一点。穷之既多,则有豁然顿悟之一时。至此时则见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至此境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用此修养方法,果否能达到此目的,乃另一问题。不过就朱子之哲学系统言,朱子固可持此说也。”[2]919-920可见,冯友兰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仅限于道德修养方法加以阐释。他还明确肯定:“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2]920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反对胡适从科学角度对于朱熹格致说的解读,而是强调从道德修养之方的角度予以解读;不过,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朱熹格致说的质疑,认为朱熹以“穷天下事物之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格物论,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是把朱熹《大学》补传中的“即物而穷其理”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1936年,贺麟发表《宋儒的思想方法》,也反对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将朱熹的“格物”诠释为科学方法,指出:“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消极方面指出宋儒的思想方法不是科学方法,积极方面指出宋儒,不论朱陆两派,其思想方法均依我们所了解的直觉法。换言之,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皆不是科学方法,而乃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性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20]将朱熹的“格物”诠释为哲学的“直觉法”,贺麟还认为:“直觉既是一种经验,复是一种方法。所谓直觉是一种经验,广义言之,生活的态度,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所谓直觉是一种方法,意思是谓直觉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工具或技术。”[20]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阐述不同的直觉方法,贺麟还讨论了朱熹“格物”的直觉方法与陆九渊的异同。
因此,贺麟不仅反对胡适对朱熹“格物”的诠释,而且也不赞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谓“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2]920。他说:“若芝生先生此处之意,系指朱子所谓格物不是科学方法,则实为了解朱学上一种进步,亦我之所赞同。因为谓朱子的格物非科学方法,自是确论。但谓朱子的格物全非科学精神,亦未免有诬朱子,盖以朱子之虚心穷理,无书不读,无物不格的爱智精神,实为科学的精神也。但他又肯定朱子的格物只是修养的方法而非求知识的方法,则我却又不敢苟同。”[20]为此,贺麟还说:“依我的说法,朱子的格物既非探求自然知识的科学方法(如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等),亦非与主静主敬同其作用的修养方法,而乃是寻求哲学或性理学知识的直觉方法,亦称体验或体认的方法。直觉方法乃是寻求哲学知识的主要方法,虽非科学方法,但并不违反科学违反理智,且有时科学家亦偶尔一用直觉方法,而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偶尔亦可发现自然的科学知识。”[20]贺麟认为朱熹的“格物”是一种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能够运用的直觉方法,而不只是单纯的道德修养方法。当然,贺麟又说:“直觉方法虽与涵养用敬有别,不是纯修养的方法,但因直觉既是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事物理会事物的格物方法,故并不是与情志、人格或修养毫不相干。”[20]
张岱年于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也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直觉。他说:“朱子所讲‘即物而穷其理’,含有直觉的体会,而‘一旦豁然贯通’更是一种直觉。然朱子亦甚注重分析,他很在‘剖析烦乱’上用力。朱子治学的最高目标,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是一种直觉的境界;而同时又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为理想,他实很致力于分析与综合。中国哲学家中,思想条理最清楚者,乃是朱子。……要之,朱子的哲学方法是直觉与理智参用,虽甚注重直觉,而亦注重理智的辨析。”[15]546
四、对朱陆异同的不同阐释
民国时期,但凡朱子学研究者,都非常重视朱陆关系问题,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就认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以学说角思理之,朱陆两派之舞台而已”[21]192。在对朱陆异同作出分析时,他指出:“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陆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21]137-138还说:“朱陆两派,虽有尊德性、道问学之差别,而其所研究之对象,则皆为动机论。”[21]138应当说,蔡元培以为朱陆两派“有尊德性、道问学之差别”,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持这一观点者,不在少数。谢无量也对朱陆异同作了评论,承认朱陆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上存在差异,说:“朱子尝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缺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者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此可为二家异同之定评。”[22]71至于朱陆在理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谢无量时而说“朱学在‘即物穷理’,陆学言‘心即理’”,“此其所以卒异也”[22]72,又认为,陆九渊“心即理”与朱熹讲“理在心中”,“亦无以异矣”[23]。
1931年,吕思勉在《理学纲要》中进一步把朱陆异同归结为朱熹讲“性即理”、陆九渊讲“心即理”,指出:“朱陆之异,象山谓‘心即理’,朱子谓‘性即理’而已。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而所谓心者,则已不能离乎气质之累,而不免杂有人欲之私。惟其谓‘心即理’也,故万事皆具于吾心;吾心之外,更无所谓理;理之外,更无所谓事。一切工夫,只在一心之上。二家同异,后来虽枝叶繁多,而溯厥根源,则惟此一语而已。”[24]
对此,冯友兰也有相同的看法。1932年,冯友兰发表《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其中第一节“朱子与象山、慈湖之不同”[25],后来编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而有“朱陆异同”一节,反对所谓朱熹以道问学为主,陆九渊以尊德性为主,认为朱陆的异同在于朱熹言“性即理”、陆九渊言“心即理”;指出:“一般人之论朱陆异同者,多谓朱子偏重道问学,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说法,在当时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学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此为一般道学家共同之目的。故谓象山不十分注重道问学可;谓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2]938而且,冯友兰进一步明确指出:“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并反对朱子所说心性之区别。”[2]939显然,在冯友兰看来,朱陆之重要的差异在于朱熹讲性与心之区别,陆九渊反对朱熹所说心性之区别。
冯友兰还进一步认为,朱陆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有之”。他说:“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发展。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二派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王阳明序《象山全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此心学之一名,实可表示出象山一派之所以与朱子不同也。”[2]938-939由此可见,冯友兰讲朱陆差异在于朱熹言“性即理”为理学,陆九渊言“心即理”为心学,明显是接受了王阳明的看法。
贺麟的《宋儒的思想方法》不同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本体论上将朱陆对立起来,并且较多地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把朱陆的思想方法都看作直觉的方法,进而分析朱熹直觉法与陆王直觉法的异同,指出:“同一直觉方法可以向外观认,亦可以向内省察。……一方面是向内反省,一方面是向外透视。认识自己的本心或本性,则有资于反省式的直觉,认识外界的物理或物性,则有资于透视式的直觉。朱子与陆象山的直觉方法,恰好每人代表一面。”[20]认为朱陆的思想方法是同一直觉方法的“向外透视”与“向内反省”的两个方面。贺麟还说:“陆象山的直觉法注重向内反省以回复自己的本心,发现自己的真我。朱子的直觉法则注重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但根据宋儒所公认的‘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一原则,则用理智的同情向外穷究钻研,正所以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样,向内反省,回复本心,亦正所以了解物理。其结果亦归于达到心与理一,个人与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则两者可谓殊途同归。”[20]在贺麟看来,朱熹直觉法与陆王直觉法虽然有“向外透视”与“向内反省”之别,但最终都是要达到“心与理一”,因而殊途而同归。
因此,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认为,冯友兰强调朱熹言“性即理”为理学、陆王言“心即理”为“心学”二者相互对立,这是“对陆、王学说太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恐亦不甚平允。且与近来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26]23。同时,贺麟还批评冯友兰过于“讲程、朱而排斥陆、王”,以为“讲程、朱而不能发展至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重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且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因而会被人批评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26]36。
应当说,民国时期,冯友兰、贺麟对朱熹哲学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于后来贺麟主要转向西方哲学的研究,他有关朱熹哲学的观点,并未被当今学术界所熟悉。但至少有一点,他于1930年发表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实际上是后来进行朱熹与黑格尔比较研究的先河,而且,他强调朱熹的“心与理一”,以及对于朱熹的太极之动静的讨论,仍然是今天朱熹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黄子通.朱熹的哲学[J].燕京学报,1927(2).
[4]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7期),1930-11-03.
[5]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上海:世界书局,1935.
[6]贺麟.与张荫麟先生辩太极说之转变[J].新动向,1938,1(4):129.
[7]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五[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89.
[8]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一百二十[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913.
[9]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卷三十七[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985.
[10]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十八[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408.
[11]周敦颐.周廉溪集(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71.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1.
[15]宇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6]张荫麟.宋儒太极说之转变[J].新动向,1938,1(2).
[1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45.
[18]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3:65.
[19]乐爱国.民国时期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解读[J].学海,2014(5):201-205.
[20]贺麟.宋儒的思想方法[J].东方杂志,1936,33(2).
[2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22]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M].上海:中华书局,1916.
[23]谢无量.朱子学派[M].上海:中华书局,1916:119.
[24]吕思勉.理学纲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17.
[25]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J].清华学报,1932,8(1).
[26]贺麟.当代中国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
[责任编辑 许婴]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ZHU Xi’s Philosophy from FENG You-lan and HE Li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Ai-guo
(School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FENG You-lan and HE Lin both closely studied ZHU Xi’s philosophy,but they had quite different opinions.The difference are mainly in four aspects:1,FENG thought ZHU Xi couldn’t say that“heart is Li”while HE believed ZHU Xi stressed the“union of heart and Li”;2,FENG thought ZHU Xi’s Taiji was motionless,while HE believed it was dynamic;3,FENG thought ZHU’s investigating things was a moral-cultivating method while HE believed that it was an intuitive method of philosophy;4,FENG though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Jiu-yuan was that ZHU insisted“nature is Li”while LU insisted“heart is Li”,while HE believ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was the difference of“outward perspective”and“inward reflection”in terms of intuitive method,but these two achieved the same end.The elaboration of the reviews of ZHU Xi’s philosoph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he tendency will be of value to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es.
the peiriod,the Republic of China;FENG You-lan;HE Lin;ZHU Xi
B261
A
1004-2237(2016)02-0001-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01
2016-03-2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07)
乐爱国(1955-),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宋明理学、朱子学。E-mail:leaiguo@xmu.edu.cn
——贺麟人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