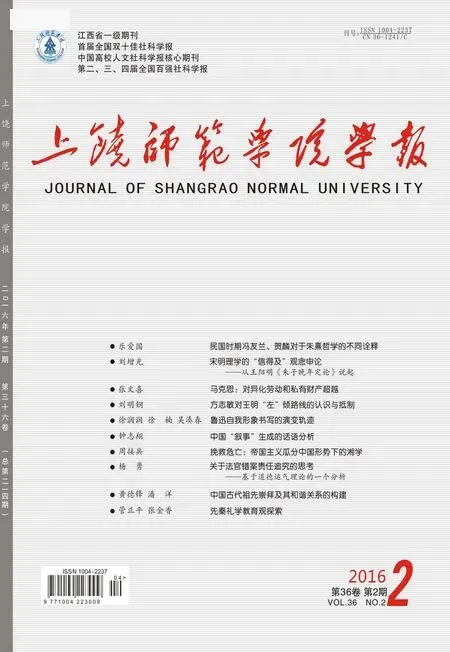方志敏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认识与抵制
刘明钢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方志敏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认识与抵制
刘明钢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方志敏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中央路线存在错误,并且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由于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左”倾错误也是有所抵制。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左”倾错误的抵制,也是难能可贵的。
方志敏;王明“左”倾路线;认识;抵制
方志敏(1899—1935),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于是,作为赣东北苏区主要负责人的方志敏对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如何认识的,是执行还是抵制了错误路线,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方志敏曾经指出“国际路线”是正确的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向各红色区域派遣中央代表推行其路线。4月,万永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召开特委扩大会,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并改组特委。7月,中央认为苏区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不力,派曾洪易来赣东北。曾洪易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对苏区的各项工作指手划脚、全盘否定,再次改组特委,由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组成主席团,把方志敏排斥在党的核心领导之外,剥夺了方志敏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9月1日,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正式成立赣东北省委,曾洪易完全控制了大会的领导权。他用极左的口号吓唬和迷惑人,开展“反对右倾”“反对调和”的斗争。大会通过了由曾洪易授意并亲自修改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大会还改选了省委,由万永诚担任省委书记,对省委其他成员也再次作了调整,曾洪易实际上完全控制了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曾给中国共产党有益的帮助,但其指导也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王明等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号施令瞎指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王明等人总是把“国际路线”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执行“国际路线”。确实,王明“左”倾路线就是“国际路线”。
方志敏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中央路线存在错误。他是1935年1月底被捕的,在南昌狱中写的第一篇文稿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
在该文中,方志敏充分肯定党的路线,写道:“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的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拿立三同志的路线与共产国际来信所提示的路线对照着,愈加清楚地看出立三路线是错误的,是有害的,是半托洛斯基主义的,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照这条路线做去,会将中国革命重复引导失败,实际上因执行立三路线,已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1]71
对于曾洪易主导的赣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方志敏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写道:“中央又派了中央代表前来,召集党代表会议,将赣东北几年来的工作,来了一个总的检阅。主要的有下列二点:(一)揭发了赣东北工作中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其恶果;(二)揭发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并决定肃清富农路线的实际工作,如按照阶级路线,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苏维埃的改造运动;农民群众阶级成分的重新确定;群众团体组织成分的审查和洗刷;以及党员成分的审查和洗刷等。党及群众工作方法亦须转变和改善。这次大会提高党员政治学习的热情,提高全党的理论政治水平,提高国际和中央在党员和群众中的威信。”[1]71-72
方志敏的这种认识在中共党内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第一,“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第二,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第三,王明等人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王明“左”倾中央,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党内的许多人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
任弼时曾任湘赣省委书记,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对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也没有认识。1944年10月26日,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它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2]350他还指出,湘赣旧省委和以自己为书记的新省委都执行了“左”的路线。
由于中共领导层是这种认识,因此,遵义会议只能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而没有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不仅如此,会议决议还指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3]4。对此,毛泽东这样解释:“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4]
总之,方志敏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他的认识在党内具有普遍性。
二、方志敏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是,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却写道:“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在赣东北确是根深蒂固,从来就没有受到最严格的打击和揭发,坐让着顺利环境白白地过去,至今想来极为可惜!一九三三年十月间,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将我们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尽情地详细地揭露出来,给了右倾保守主义第一次的痛击。那时,我代理了赣东北党的省委书记,我是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尽我力所能及地领导党内同志们向保守主义攻击,无情地检阅和批评我们工作中保守主义的错误。”[1]72-73
方志敏的认识与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截然不同,不但没有反“左”,反而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1.反右倾已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自从20年代俄共党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后,共产国际给各国党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反倾向斗争的中心。在中共党内,王明等虽然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却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在党内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已成为一种思维的定势。
方志敏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状况。比如,曾洪易到赣东北后,大力推行“左”倾路线,但方志敏仍然认为,曾洪易右倾保守。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他写道:宏义(即曾洪易)同志到赣东北后,对于右的富农路线、“左”的立三路线以及其他政治上错误的观点,都给了正确地纠正,但对于保守主义不但未有揭发,而且不自觉地多方掩护自己的与党内一般同志的保守主义的观点,使他在党内成为对外发展的阻碍[1]108。
2.当时苏区确实存在右的倾向。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更加残酷的进攻,红军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在反“围剿”初期,曾采取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但是,就在“左”倾军事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党内也存在着一些右的倾向。譬如部分人对于能否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持有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亦有人存在着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右倾心理。
这种右的倾向在赣东北苏区也是存在的。方志敏指出:从1931到1933年的三年中,“赣东北苏区的环境是相当地顺利,极有利于大发展。然而这三年中,不但没有发展,且缩小了一部分。红军的胜利,也极不够。究其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存在着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对于白区工作,没有予以极大的注意,没有遣派得力干部,没有严厉揭发白区工作的右倾错误与加紧指导和督促。红军则尽在苏区作战,没有大胆到白区去进行极大的战争(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是冲破保守主义而在白区进行较大战争,就得了很大的胜利),自然损失了不少伟大胜利的机会。而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多是晚出早归,不能在白区进行多时间的游击战。当时苏区周围的白区,是异常空虚,群众是异常地要求革命,而我们的目光只看到苏区以内,极端缺乏向外积极发展的精神,较之一九二八——二九年的进取精神,都有逊色。”[1]107-108
从局部看,赣东北苏区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右倾错误,方志敏提出反右倾也是符合实际的。
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决议也未提出反“左”倾的问题,而是强调:“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3]17。
方志敏把右倾保守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强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一点与遵义会议决议的提法是一致的。
三、方志敏执行过“左”倾路线
方志敏是遵守纪律的模范,特别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中,他反复强调,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如有哪些同志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那简直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而是冒牌党员”[1]105。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根据地领导人的方志敏理所当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比如,在军事上执行单纯的防御路线。
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术。在这种情况下,李德、博古放弃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变成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对于“左”倾中央的作战方针,方志敏是赞成的,他写道:“我们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就是集中主力于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建筑堡垒工事,在自己堡垒工事面前,实行短促的突击,以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1]87
这种以堡垒对堡垒的死打硬拼,红军伤亡惨重,方志敏写道:“红十军为保卫基本苏区,在五次战役中,打了几十次激烈的血战,其中以横峰莲荷之战,上饶坑口之战,和横峰管山之战,打得最为猛勇!……在这三战中,我军伤亡近八百人,如此,可见红十军的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敌人的伤亡总在千数百人。”[1]88
由于战略方针的错误,赣东北苏区没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方志敏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的原因:1.敌人有飞机大炮的重兵器。2.没有建立谍报工作。3.过于机械地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的战略。4.战术上有许多缺点[1]92。
但方志敏没有认识到,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才是导致反“围剿”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加紧反对富农的“左”的方针,方志敏也是积极执行的。他指出:在群众中,则开展了反富农的阶级斗争,更加坚定和发扬基本群众革命斗争的决心和热情,苏区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四、方志敏对王明“左”倾错误有所抵制
综上所述,方志敏当时尚没有认识到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但由于他能够从实际出发,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左”倾错误也是有所抵制。比如,曾洪易提出“明确阶级路线,反对富农路线”的口号,修改土地法,大举清查阶级和重新分配土地。方志敏竭力进行抵制,及时制止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曾洪易取消敌占区的“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企图断绝苏区与白区群众的往来,方志敏却始终重视白区工作,派出许多忠实积极的同志到白区去建立革命工作基础。
在军事方面,赣东北苏区虽然也进行堡垒战,但方志敏也十分注意保存实力,尽量避免死打硬拼。他主张:赤色堡垒,我们都是派很少数的枪固守的,有的赤堡只有三支枪,主力红军是拿来做突击部队[1]88;并且主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1]87,他还率领红十军第二次进入闽北,取得很大的胜利。
在肃反问题上,方志敏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最为突出。
1932年3月间,曾洪易在赣东北苏区大搞肃反,把大批持不同意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AB团”“第三党”和“改组派”;他们采用“逼、供、信”等手段,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很多领导骨干被错杀,给赣东北苏区造成了惨重的灾难。
由于肃反是中央的工作部署,方志敏也曾非常积极地投入运动之中,然而,肃反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他感到不对劲:“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1]76
吴先民系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赣东北省委委员、红十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由于对曾洪易的错误有所议论,被诬蔑为“改组派”,被抓后,吴先民不肯屈服,曾洪易大搞“逼、供、信”,把吴先民工作笔记本上记着赤色警卫师和苏区区委书记、苏维埃主席的名单,硬说是“改组派”名单。方志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找曾洪易据理力争,说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决不可能是“改组派”,所谓反革命名单,实属红军和苏区的骨干力量。曾洪易则给方志敏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大帽子,强令方志敏写检讨,并给予党内处分。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写道:“当时,我说不出这些理由来,只是感觉得不对。”“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1]77
在狱中遗墨中,方志敏着笔最多的是他的反思。历史的教训,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方志敏决定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与《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就是“血的教训”的总结。在这两篇文稿中,方志敏对肃反提出尖锐的批评:“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1]78
方志敏明确指出肃反工作发生了扩大化错误:“我坚决地向同志们说,在这几年的肃反运动中,特别在一九三二年,我们确实是错处分了一部分人,错捉了一部分人。”[1]111方志敏还写道,肃反的领导者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派的混入活动,到处疑神疑鬼!”[1]77
为什么犯扩大化的错误?方志敏认为,主要是肃反的领导者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1]77方志敏指出:“赣东北有没有隐藏反革命分子呢?无疑义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反革命的组织呢?无疑义地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庞大。这是因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力量和威信与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要寒反革命派之胆,而阻止和阻碍其发展(如弋阳反革命之组织只发展了三人),没有党、团或苏维埃中下级干部,会轻易加入反革命组织的。”[1]111他还写道:“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和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群众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的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极显明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将肃反工作扩大化。”[1]77
方志敏还认为,“肃反工作的简单化”也是造成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而且只凭口控捉人,这往往会乱探乱捉,牵连无辜!”[1]77
方志敏还认为,主持肃反工作的负责人个人素质差。指出,曾洪易等“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尽说肃反要慎重,还说你对肃反不坚决”[1]77。
肃反扩大化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就党内情况而言,方志敏的批评切中要害。
方志敏总结肃反的沉痛教训与严重后果,写道:“肃反的错误,会造成群众间的恐慌与干部的消极和不安。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损失了工作干部,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无形损失,也是不小的。”[1]111-112他强调:“错放一个反革命分子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一样的。”[1]112
这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需要格外珍惜,牢牢记取。
五、方志敏抵制“左”倾错误难能可贵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5]。
评价方志敏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那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历史条件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并且对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全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苛求方志敏在当时就认识到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并与之做不懈的斗争。
任弼时非常重视总结与研究历史。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他特别强调研究历史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的。”接着,任弼时分析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需要在这方面作自我批评。”第二种情况:“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他利用党的错误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是品质不好的人。这种人不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些什么毛病,造成什么罪恶。”第三种情况:“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样错误路线。”[2]350-351
笔者认为,方志敏就属于第三种情况。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仅仅“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了肃反运动,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遵义会议与瓦窑堡会议是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重要会议,但没有涉及肃反扩大化的问题。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对于肃反扩大化问题尚无深刻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方志敏写于1935年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与《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无疑是总结苏区肃反运动的滥觞之作;方志敏明确指出肃反犯了扩大化错误,分析发生扩大化的原因与危害,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
诚然,方志敏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但他对肃反错误的认识与批判,无疑代表了当时党的最高水平。
[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方志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任弼时.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M]//遵义会议纪念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1943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M]//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历史的丰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384.
[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责任编辑 许婴]
FANG Zhi-min’s Realization of and Resistance against WANG-ming’s“Left”Line
LJUMing-g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56,China)
In the beginning,FANG Zhi-min didn’t realize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lin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ook the“left”line.But later,he proceeded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Thus,he resisted the wrong“left”line in reality.His resistance against the“left”mistakes is commendable during aperiod dominated by a wrong line.
FANG Zhi-min;WANG-ming’s“left”line;realization;resistance
D231
A
1004-2237(2016)02-0041-05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07
2015-12-29
刘明钢(1949-),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教授,从事中共党史与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E-mail:lmg4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