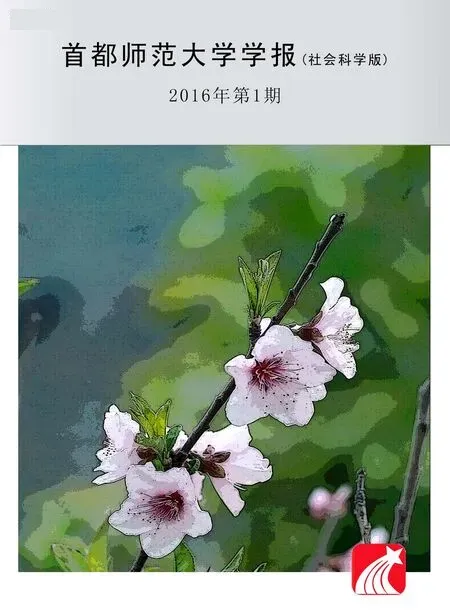《从军日记》与民国“大文学”写作
李 怡
一
《从军日记》是谢冰莹的成名之作。原系6篇,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14日至 6月22日连载于汉口《中央日报》,题为“行军日记”;1929年3月,增写《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写在后面》、《给KL》及《编印者的话》与林语堂的《冰莹从军日记序》,以《从军日记》为题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首印1500册,很快销售一空。①谢冰莹后来回忆说:“刚出来不到一个月,一万本早已卖光”(《关于〈从军日记〉》,《谢冰莹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当是误记,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揣测出当时此书的畅销状况。半年后,春潮书局再版,增加了《再版的几句话》、《出发前给三哥的信》、《给女同学》和《革命化的恋爱》四篇文章,印刷 2000册。两年后(1931年9月),此书改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内文小标题《行军日记》、《行军日记三节》分别改为《从军日记》与《从军日记三节》,撤下《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增加《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至此,《从军日记》的形态固定下来。到1942年10月,该书一共印行了14版。即便不算上林语堂的英译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和汪德耀的法译本(法国罗瓦罗Valois 书局),《从军日记》已经肯定是民国时代女作家文集中印刷次数最多的作品。
然而,作者谢冰莹本人却似乎对这一作品不尽满意。《从军日记》是在孙伏园、林语堂的鼓励下交付春潮书局的,出版前,谢冰莹自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①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9年初版,第9页。,没有出版单行本的价值。到1931年光明书局版面世时,作者又特意增加了相当真诚的“自我批判”:“总括说来,在文字里究竟理智的话少,情感方面的话多,一看就知道作者写时一定是满腔火热的热情而未曾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某件事体,分析它描写它”②谢冰莹:《“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从军日记》,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35页。,“没有系统,这几篇短东西我们如果留心点去看,马上可发现这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零碎的断片,日记太少而杂文太多,这在我觉得是侮辱了《从军日记》四个字……因为没有系统,没有一贯的精神,所以有些读者也许记不清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③谢冰莹:《“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从军日记》,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132页。。数十年后,作者依然觉得,这些作品“论文字,写的太幼稚,一点也谈不到结构、修辞和技巧,它只能算是北伐时代的报告文学”④谢冰莹:《关于〈从军日记〉》,《谢冰莹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述理智少,情感多,杂文笔法多,没有系统性,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换句话说,这是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以“美术”、“审美”为旗帜的所谓的“纯文学”理想。“纯”是相对于“杂”而言,所以“杂文”常常不受纯文学倡导者“待见”,按照“纯文学”的标准,“杂文太多”当然也就“不成文学”了。和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一样,谢冰莹显然深怀对“纯文学”写作的期待,所以销售市场的火爆与社会声誉的高涨都还不能令她满意,“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这并非矫情的自谦。作为“推手”的林语堂也清醒地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冰莹从军日记序》中进一步概括了“不成文学”的具体表现:“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⑤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9年初版,第9、10页。林语堂在这里所述的都是“纯文学”常见的审美追求。
但是更值得追问的则在于,作为新文学“审美”理想的深刻的理解者,作为立志于中国新文学海外传播的推动人,林语堂在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成文学”的特点之后,却依然如此推重《从军日记》,并将它作为自己“对外文学传播”事业的重要起点,他看中的是什么呢?请看林语堂的这段描述:
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气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⑥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9年初版,第10页。
这里描绘出来的是一种对“异样”人生的好奇与关怀。也就是说,除了“审美”,“文学”本身所记载的人生与社会景象对读者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实,自古至今,无论中外,“文学”的含义本身就是相当丰富的,并不因为近代以后“纯文学”理想的兴起就完全“审美”起来。中国固有的“文学”包含“文章”与“学术”两大范围,单就“文章”来说,也相当庞杂,远非语言文辞之“美”所能够囊括;“‘literature’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泛指‘文献’和‘著述’,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⑦马睿:《文学理论的兴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识档案》,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18世纪以后的西方的literature 开始向狭义的审美转移,近现代的中国作家也纷纷在“美术”、“纯文学”的概念中接通了这一“文学”新思维,但是,近现代的中国却从来不是一个足以令人自由审美的国度,更大的社会人生的变化时时刻刻都刺激着人们的精神,影响着人们的讲述和表达。所以,一方面是“审美”与“纯文学”的美丽的旗帜迎风招展,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另一方面则是深刻变化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依然吸引着我们的关注和介入,因为,解读和回答这些现实问题也是我们日常生存的一部分。谢冰莹《从军日记》在审美上的不足并不能掩饰它在另外对一些问题的揭示,而这些问题恰恰击中了当时人们——从普通读者到专业学人的敏感的神经。
二
在《从军日记》中,足以引发人们关切的元素至少有三:
一是战争。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而言,战争自然就是“非常态”的,而“非常态”的存在总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在西方,战地记者完成了这一类生存景观的书写,中国媒体的战地记者却相当缺乏,虽然今天的报刊史常常提及《申报》记者对日军侵台、中法战争的报道,提及武汉《大汉报》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但从总体上看,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战地报道都是十分不足的。作为中国现代战争的开始,在北伐这样的战争中,战地报道自然也不发达,关于战争的故事只好交给像谢冰莹这样的一个已入伍的文学习作者了。一手将谢冰莹推上文坛的《中央副刊》编辑孙伏园是现代报刊史上难得的策划大家,早在北平主编《京报》副刊之时,孙伏园就策划过著名的 “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征文活动,通过紧紧抓住时代脉动,制造热点话题,扩大了副刊的影响,完善了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为《京报》一举成为《晨报》强劲的竞争对手立下汗马功劳。担任武汉《中央副刊》编辑伊始,孙伏园又以丰富的媒体经验提出自己的主张:“就是对于眼前(包括时间的与地域的)发生的事情,用学术的眼光,有趣味的文笔,记载与批评。”①孙伏园:《中央副刊的使命》,《中央副刊》,1927年3月22日。北伐是1920年代中后期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孙伏园敏锐地将这一话题及时捕捉到了自己的副刊中,除了谢冰莹的“日记”,《中央副刊》还发表过田倬之《随军杂记》系列(1927年5月10日、16日、17日、28日)、徐正明的《熏风吹渡信阳州》(1927年5月28日、30日、31日)、符号的《我所记得的》(1927年6月10日)、黄克鼎《沙场日记的一页》(1927年6月25日)等,记载北伐和西征的情况。自然这些记载都不如谢冰莹的“日记”丰富而有吸引力。
二是女性。柔弱的女子如何与酷烈的战争发生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刺激性的话题,极大地煽动了人们的兴趣。对此,作者本人也十分明了:“因为是中国自从有历史以来,第一次有女兵,所以我们的生活,特别感觉新鲜、有趣。”②谢冰莹:《关于〈从军日记〉》,《谢冰莹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编者孙伏园更是刻意渲染:“这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留下的一点痕迹,所以有保存的必要。”③谢冰莹:《女兵十年》,红蓝出版社,1946年版。读过日记,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也在向副刊编者询问到冰莹的真实性别。在包括如沈雁冰这样的文坛名家的文章中,人们读出“我们的冰莹”几乎成为当时青年心仪女性的代名词。④玄珠:《云少爷与草帽》,《中央副刊》,1927年7月29日。《从军日记》不仅让人们为战争中的女子担忧,一如林语堂在序言中那样满怀深情和满怀怜惜的想象,而且作者笔之所至,还涉及到变革时代女性生活的若干领域,比如妇女协会的活动与遭遇,乡村传统习俗的变革,以及一个时代新女性面对战争、死亡、性别歧视的种种昂奋与焦虑。
三是革命。作为“国民革命”的北伐参加者,谢冰莹一开始就将自己置身于浓郁“革命”氛围之中。她的《从军日记》开篇即是“革命”的豪情:
我真高兴,无论跑到什么地方,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
汇入革命队伍,书写革命的激情可以说是《从军日记》的创作动力:“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把我所见所闻的事实,忠实地写出来,寄给伏园先生让他知道,前方的士气,和民众的革命热情,是怎样地如火如荼。”⑤谢冰莹:《关于〈从军日记〉》,《谢冰莹散文》,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这样的激情既符合北伐时代广大读者的需求,契合了“革命大本营”武汉的语境,更属于孙伏园和《中央副刊》苦心探求的“革命文学”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谢冰莹与民国历史的“合力”,让她的著作成为了“革命文学”别具一格的样本。出版者及时地捕捉了其中的“革命”意义并加以凸显。《从军日记》初版前有“编印者的话”:“革命文学的理论,曾经有时鼓乐喧闹,有时零零落落传到我们耳边来;革命文学催召的符咒,我们也常时听到。然而革命文学到底是怎般的风味,却始终叫人感到隔着一层障翁似的,不能体会得分明。文学如果是以情感为神髓的,而革命文学又是革命者情感的宣露,那这一部《从军日记》的内涵庶几当的住革命文学的称号。”①《编印者的话》,《从军日记》,上海春潮出版社,1929年初版,第2页。该书的插页广告也这样渲染:“这是革命怒潮澎湃的时候激荡出来的儿朵灿烂的浪花,是一个革命疆场上的女兵在戎马仓皇中关不住的儿声欢畅。这是真纯的革命热情的结晶。如果‘革命文学’这个名词可以成立,我们认为这就是最可贵的革命文学的作品。”那个时代的读者和评论者也都是从“革命”的角度辨析“日记”的价值。林语堂说:“这大概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硬冲前去’的同志对于这种战地的写实文字,特别注意而欢迎。”衣萍认为,作为出色的革命文学文本《从军日记》可以永远留传下去的。②衣萍:《论冰莹和她的〈 从军日记 〉 》,《春潮》,1929年第1卷第7期。李白英甚至将它视作“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文献”的“压卷”之作。③李白英:《借着春潮给〈从军日记〉著者》,《春潮》,1929年第1卷第7期。
所谓“革命文学”在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倡导;二是1920年代后期的普罗文学创作;三是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第一方面的研究侧重于发掘外来理论(日本、苏俄)之于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资源价值,第二方面的文学实践往往充满罗曼蒂克的想象,如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进入19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其实是现实“革命”挫折之后的精神反叛的形式,它更多地体现出来对阶级斗争概念的运用。与这三方面的“革命文学”比较,倒是谢冰莹《从军日记》所述的国民革命可能为我们提供记录“革命”更为明显的现实内容,而武汉《中央副刊》所展开的关于“革命文学”的种种讨论也成为这一重大文学思潮的独特的构成,虽然今天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淡化这一阶段的“革命文学”主张及创作。④关于武汉国民革命时期对"革命文学"的讨论以及后来学术史的淡化情况,可以参见张武军:《国民革命与革命交学、左翼交学的历史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
关于《从军日记》之于“革命文学”的独特意义,林语堂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我想革命文学只有两种意义。一是不要头颅与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顽固,腐败,无耻,虚伪,卑鄙反抗的文学,一是实地穿丘八之服,着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粮,手掌炸弹,向反革命残垒抛掷,夜间于猪尿牛粪的空气中,睡不成寐,爬起来写述征途的感想。不要头颅的文学既非妙龄女子所应尝试,而保守头颅的‘革命文学’也未免无聊。至于实地描写革命生活的文字,唯有再叫冰莹去着上武装去过革命健儿生活。”⑤林语堂:《冰莹从军日记·序》,《从军日记》,春潮书局,1929年初版,第12页。林语堂所描述的第一种“不要头颅”的反抗的文学侧重在一种决绝的“革命”气质,它可能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和可歌可泣的精神,但也可能与现实的人生若即若离,结合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实践,从充满个人想象的革命加恋爱模式到对苏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的硬性移植,我们其实不难见到这一类“气质大过本质”的文学创作,连革命文学队伍内部也在呼吁警惕“小布尔乔亚”式的脱离实际的情调。而如谢冰莹一般真正融入革命斗争,努力写出这一过程的真切体验虽然可能流于简陋,但却自有可贵的质朴与真诚。
三
总之,战争、女性与革命,这原本都属于现实的人生而非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对于执着于语言艺术建构的“纯文学”的梦想来说,它们实在是“不成文学”的;然而,对于刚刚脱离传统“帝国”,步入现代“民国”的中国人来说,它们恰恰属于现实人生最重要的关注对象——现代中国反复卷入内外战争的梦魇,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革命则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普通人的命运,可以说,它们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的人生乃至生命,内化成为我们日常喜怒哀乐的一部分,生发成为我们感知世界、读解人情、辨认未来的基础。较之于欧美文学,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差异:从中世纪后期的人性释放到文艺复兴的宗教与生活世俗化,再到启蒙运动的理性确立、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制度完善,但凡属于国家、民族、社会生态的重大问题都已经逐步解决或纳入到了制度化解决的轨道,文学的“现代关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文学本身”——当“文学周边”的因素可以不再成为国家公民普遍的必然的关心对象,我们的兴味完全有理由专注在语言艺术形态之中,文学有理由“自我”起来,“纯粹”起来;中国的“现代”则完全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帝国”传统挥之不去,“民国”尚属梦想,大量的安身立命的事业都在“文学之外”,包括战争、女性与革命,它们首先就不是一个“文学”的问题,单纯的语言艺术的探寻常常都不能不是我们日常人生的奢侈品。当然,现代中国的作家与欧美作家一样都立足于一个被称作“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并且在一系列的文学观念上,前者也无从拒绝来自后者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现代中国作家一方面承受了现代欧美文学的“文学”概念——对于纯文学心向往之,但另一方面却也一再表述着对“文学之外”的人生主题的强烈兴趣,现代中国文学归根结底都属于“为人生”的文学。这种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传达人生遭遇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追求也不能被视作是对文学的背叛,因为它们本身依然具有文学的基本特点——对人类情感和情绪提取和淬炼,对语言表述形态的种种摸索,只不过后者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目的。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在西方文学的古典时代和中国文学的古典时代,原本就有过如此“不纯”的文学理念,中西文学的传统差不多都有过对“杂文学”或曰“大文学”的历史追求。我们所要指出的就是,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纯文学”的运动史另外一面,其实都暗含着同样深厚的“大文学”的底蕴,对“大文学”的需要就是人们对人生现实的根本关怀,就是对文学承载生存问题的执著的诉求,即便充满“纯文学”理想的作家也实在无法拒绝这样的基本诉求。可以说,“大文学”写作方式是民国时代的显著特征,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人民共和国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尤其“日记”,按照中国传统的“日记”观念,本身就属于后来输入的文学诸文体概念所不能容纳的“杂文学—大文学”的文体范畴。朱光潜先生的考证认为,“日记”在中国脱胎于古老的编年体史书。①朱光潜:《日记——小品文略谈之一》,《朱光潜全集》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也就是说,它的首要功能就是记载社会与人生“事态”的,直、真、诚原本属于中国史家的几大追求,所谓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史记》传统,而这恰恰就是谢冰莹的自我写作期许:“‘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②谢冰莹:《平凡的半生》,《谢冰莹文集》中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就是这样,虽然新的文学知识让作家自认为“不成文学”,也一度对发表与出版的信心不足,最终还有苛刻的自我批判,但是将战争、女性与革命纳入视野的表达却那么深刻地激动过她,“我不是为了批评而写这些东西的,只是赤裸裸地说出我当时所要说出的话,在欢乐时这样,在愁苦时也这样。我不会空叫些革命的口号,也不会说些不曾经过的肉麻的话来。” 这些“实在”的、以自我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的写作也那么自然地激动过民国文坛的一干编者、读者和评论者,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事实。而且,有趣的事实还在于,谢冰莹一方面自我批判,一方面却又继续着这种集中展示个人生存体验,融自传、日记与社会世象于一炉的写作方式,《从军日记》之后,又有《女兵自传》、《新从军日记》(《抗战日记》)从“日记”到“自传”,受邀写作、在期刊连载最后结集出版的方式都完全相同,前有孙伏园、林语堂和夏康农的提携,后有陶亢德、林语堂与赵家璧的鼓励。这说明,作者虽然有过种种的自我不满,但这种写实掺杂情感的叙述已然成熟,既为通过作家文字来了解、认知社会情形的读者所喜闻乐见,也方便了作家对时代社会的记叙与个人观感的实录,无论是社会的描写还是自我的感怀,都诉诸于真切质朴的描绘,而与种种艺术的“炫技”无关,或者说语言艺术方面的刻意推敲、经营并不是这些“日记”与“自传”的目标。这就是一种源于历史实录的文体传统,属于我们所谓的“杂文学-大文学”的追求。一方面,进入“民国”,置身于更多“公共事务”的中国读者需要透过作家的文字来关心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作家也在顺应这一需求中训练和发展了自己。“大文学”的写作方式就这样成型了,成为了民国文学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提出谢冰莹《从军日记》的“大文学”写作现象,并不是寻机拔高它的文学价值,更不是说超越“纯文学”写作的“大文学”现象应当是衡量现代文学价值的至高标准,而是借此提醒:“大文学”写作是民国时期作家写作难以避免的特点,它在读者接受中的广泛影响更是我们真正走入民国文学的基础,只有最充分地意识到这一“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的起点状态,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摸清民国文学的历史形态,并最终恰如其分地把握它在各个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