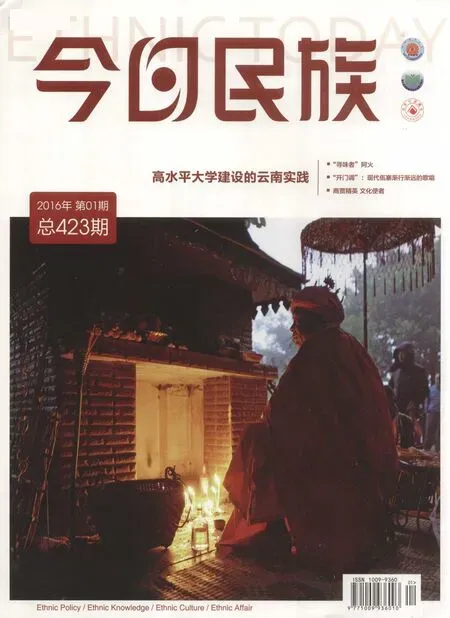“开门调”现代佤寨渐行渐远的歌唱
文·图 / 赵颖
“开门调”现代佤寨渐行渐远的歌唱
文·图 / 赵颖

与陈岩惹老人一家合影
即兴演唱,并不是张口就来——那样的话不过是表演——而是经过思考的言说。
村支书在前往陈岩惹家的路上特意嘱咐我:“你们去不要说你们知道他是村里的名歌手,只说想来听他唱歌,要不然他不露给你们听。”
陈岩惹是帕良村有名的歌手,他的歌技,家喻户晓。他最拿手的是佤族青年结婚迎亲时所唱的“开门调”。听村里的人说他去年凭借这门技艺还帮着本村的佤族小伙去山里佤寨娶了一个媳妇回来。
“开门调”是佤族古老的歌唱形式,现在还流行。佤族男青年到了娶亲的那天要请上本村最会唱歌的人去女方家,通常这个时候女方家人会把家门紧闭,将迎亲的队伍拦在门外并与对方对歌。双方在歌里相互抬杠、打趣、商榷婚后诸事,直到男方的歌手唱“赢”了女方的娘家人,方可将门打开,迎娶新娘。所以娶亲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方歌手的歌唱技艺。而我将要去拜访的陈岩惹就是这样一位歌手。
作为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去到帕良村之前,像很多前辈一样,我也做了一点案头工作。帕良村属于沧源县,是佤族聚居地。我是带着开门调的音乐属于什么调式,它的句法、唱词、节奏是什么样的,它所流行的地区在哪,演唱是否有固定时间,歌唱者的身份怎样,歌唱中是否有信仰崇拜的观念等等问题而来。
因为带着“理论”问题而来,对于眼前的佤寨、汽车穿过的成片的竹林与油菜花,坝子里的云海,起初没有特别在意。但等听了音乐,调查结束离开佤寨以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佤寨里的歌与这竹林、云海和土地的关系。
与“开门调”相遇
来到陈岩惹家里,他正在院子里拿着农具做农活,年龄看上去六七十岁。村支书用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便放下手中的农活,请我们到屋子里去坐。自当地政府将帕良村从山里搬迁到离沧源县城较近的坝子里后,每户的房子都改建成水泥结构的两层砖房,客厅里彩电、DVD等家电一应俱全。
寒暄过后,陈岩惹的妻子搬出了一竹制的桌子(类似茶具)。村支书说:“有客人来了,他们拿出茶和烟来招待你们,还要念一念经。这风俗世世代代都不会丟。”随后,陈岩惹的妻子将一根裹起来的烟叶点燃,村支书将它拿在手上,连同竹制桌子一起举起来,口中念念有词。陈岩惹夫妇取下帽子,起身蹲在村支书脚下,我们一行人也按他们的样子蹲了下来。女主人端起桌子顺着沙发给大家发起烟来,我不抽烟,但是村支书说,不抽烟也要拿,这是礼貌。
随后村支书与陈岩惹进行了一番短暂的交谈,老人很配合我们的采访。在唱歌之前他拿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唱了一首“劝婚调”,随后他又与老伴对唱了一首“开门调”。“开门调”的演唱方式与旋律都与佤族其他类型的民歌有很大的不同,他唱的“劝婚调”应属于“开门调”的范畴,而“开门调”并不是一首歌,而是发生在亲属与乡民之间的,以佤族姻亲制度为纽带的一系列歌唱行为。这时我对“开门调”的认识进了一步。

在陈岩惹老人的家里访谈
土地里生长的“歌”
1.用竹子做比喻
村支书给我们翻译陈岩惹的歌词。他解释说,这些歌词无法用汉语完全翻译,因为这些歌词里有很多比喻。
翻译的困难,不难理解,因为一个是佤语与汉语表达习惯上有很大差异,另一个是比喻很难翻译,直译之后不能准确理解它的原义,而且比喻只用在歌唱中,它本身就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想要解释清楚,需要先搞清楚歌词中所涉及到的文化意象。
村支书给我翻译了劝婚调,大概意思是:“一棵竹子不成林,一个人也不成家,一个人在家里,家也不成家。找了媳妇,一个人就有了家,一棵竹子才能成为竹林。”
用竹子来打比方,并不难理解,因为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竹子,竹子是佤族人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不过,竹子的比喻,或许还有更深的意义。我联想到我在沧源经常看到的一个佤族符号——两条直线相交成的一个“叉”。这“叉”可以是房梁上交叉的木头,也可以是过去佤王座椅背后的图案。当地知识分子说,“叉”象征着团结,又说“叉”是一个叫“司岗”的图腾。我觉得这里茂密的凤尾竹交错成林,应该也有不少“叉”的构成,也就是说竹子还有抽象的含义,这含义让它很适合比喻结婚成家。

佤族村寨 李学明 摄
2.乐中的“生灵”
陈岩惹老人唱开门调的时候,我把旋律记了下来:

这段谱看似简单,但记录起来十分困难,某种程度上,比听懂他们的唱词还要困难。开门调特殊的歌唱方式是记录旋律的主要障碍。特殊的歌唱方式在民族音乐中并不少见,最典型的是蒙古族的“呼麦”,歌者用喉音与嗓音同时发出了两种在不同音高上的声音。
“开门调”的发声方式同样是特别的。当陈岩惹准备开始演唱之前,他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若有所思,眉头微皱,从喉咙与鼻腔中间挤出了第一个音,他开唱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开始唱歌了。因为歌唱的声音是从胸腔经过被挤得非常紧张的嗓子中“哼”出来的。
这种“哼”一方面是因为咬紧大牙而吐字不清;另一方面是由于口腔不打开,歌者要达到某个音高时,必须夹紧嗓子。这种“哼”的效果与西方音乐声乐练习中的“哼鸣”类似,但是发声点位置靠前,是在喉咙处。这种歌唱的声响效果与人平时说话的音色完全不同。所以,我记写旋律的时候很难去抓住旋律的具体音高,而在每句歌唱的结尾处又总是终止得非常果断,好像词还没唱完但歌手已经急于闭上了嘴巴。
这让我联想到了佤族人所崇拜的“牛”的叫声,如果说这是模仿,是有意为之,那也应该是合理的假设。一方面,学术界对云南的少数民族音乐有一个共识,就是很多歌唱方式都跟他们的生活相关,所以要么模仿牛,要么模仿羊。云南民族音乐学者吴学源说,丽江纳西族的唱腔很多都学的是羊叫。我们不妨大胆假设,沧源佤族开门调的唱腔多半是从牛那里得到灵感。
当然,另一方面,牛在佤族社会中意义非凡。佤族社会很多重大的仪式场合,都需要牛,挂牛头,剽牛等习俗,我们并不陌生。尽管对牛在佤族社会的文化意义,还众说纷纭,但牛的重要,不容置疑。
现代社会中远去的“歌”
“开门调”歌唱过程中,陈岩惹和他的妻子唱得非常投入,歌曲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激情释放,而其二人的投入体现在歌唱过程中的思考,他们在思考要唱什么,要在歌里表达什么,他们若有所思的状态让我对即兴演唱的认识深了一步。
即兴演唱,并不是张口就来——那样的话不过是表演——而是经过思考的言说。歌唱是要表达某种想法,这点类似说话。但和说话不同的是,歌唱的内容和形式,常常是某个社会语境的产物,离开一个社会(社区),歌唱就失去应有的价值,或者价值发生转移。
歌唱在社区中的功能很多,这是民族音乐学的大课题,我这里不去展开。但当听到陈岩惹和他的妻子即兴演唱开门调的时候,我想到当日常生活的言语不能表达,或者不被允许表达时,歌唱就是一种替代方式。所以正如音乐学者梅里亚姆说的,在歌曲中,个人或群体显然可以表达他们在其他场合不能诉诸言语的真正感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保留在歌唱里的“言语”,因为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与日常生活的言语相比,变化更慢,因此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遗物。

待客的“茶具”
那开门调是怎样一种历史(社会)的产物呢?无论是仪式(婚俗的一部分)还是歌唱,都至少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及其风俗的改变,开门调正在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土壤,已经越来越像一种文化“遗产”了。
据了解,沧源佤族互相通婚的寨子,有的已经不会唱开门调。因为一方不会唱,另一方也自然无法完成唱开门调的迎亲习俗。按照现在的情况看,开门调这种佤族古老的歌唱和相关仪式会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在郁郁葱葱的竹林深处。
在我要离开陈岩惹家的时候,有一幕颇有意味。陈岩惹老人的孙子和孙女追着要看我拍摄的视频,他们对视频中爷爷唱的歌十分好奇。我无法分辨这种好奇是因为开门调远离生活而变得很新鲜,还是摄像机对他们来说还很新鲜。陈岩惹老人对视频中的自己,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推辞了我所给的些许报酬,但希望我能将本次采访所录制的视频刻成碟子寄给他,他说要为他的孙子孙女们留着,告诉他们,爷爷曾是这村里最有名的歌手。
(责任编辑 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