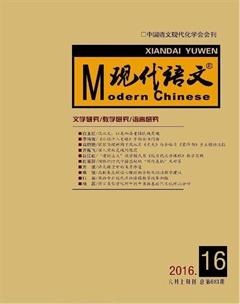论《欢喜冤家》的贞节观书写新倾向
璩龙林
摘 要:成书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短篇小说集《欢喜冤家》,在贞节观书写方面,虽有儒家思想传统所带来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了与其不一样的新倾向,着力描写了女子的性体验和性快乐。在此基础上,还对守节与否作了变通理解,从而带有晚明思潮的特色和自身独有的思想观念,体现了男性中心文化机制下的女性话语色彩。
关键词:《欢喜冤家》 贞节观 新倾向
《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艳镜》《欢喜奇观》《三续今古奇观》等,作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1],全书共计二十四回,每回演一故事,基本上都与男女风月有关,从书名亦可窥其大概。西湖渔隐在序中称:“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2](序第1页)、“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2](序第2页)可见他之所以偏好写男欢女爱故事正是出于这一观念。作为晚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马克梦认为“冤家”是“形容男女恋人因纵情过度而终于反受其害的情形。在晚明小说中,激情超出了所能容纳的限度”[3](P104)。是故作者用“冤家”作为小说题目,足以体现出小说文本中的“激情”色彩,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世情与色情的结合。
一、女子的性体验和性快乐
明代通俗小说特别是描写世情男女欢爱都小说,虽然也经常涉及到性,但在性的描写中多注重男子的感受,写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性体验比较普遍。在一个男权至上的时代,女性的性感受和性体验是缺席的,她们在性爱体验当中的位置基本上是处于辅助和从属的地位,是配合男子的快感而存在的,就算有一些性欲比较强烈的主动寻欢者,如《金瓶梅》中的几位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也只是写她们的动作,写她们在性爱时的呼叫,那只是配合西门庆的淫欲而发出的浪语,她们自己的性体验却从未明晰地表达出来。潘金莲在与西门庆的第一次偷情时,有一句写偷欢交合快感的“真个偷情滋味美!”,但那也是作者在诗词中的评价,而不是出于金莲口中。总之,女性的快感附着在男子的体验之上,而自身的体验因极少得到表达而呈现失语状态。
《欢喜冤家》的特色之处,正在于对这一方面缺失的弥补。《欢喜冤家》经常书写偷情女子的性体验,不像其他小说中多写男性的快感,或只就性交场面作描写,而缺少女性的体验和快乐,如第九回叙刘二娘被丈夫小山叫去以色相行骗,骗取张二官的钱财,后来她假戏真做,真的和张二官好上了,二人偷欢时:
二娘呼的一声道:“我死也。”二官道:“又是我见你丢了,故不动着。若是弄到如今,真正死矣。”二娘道:“怪不得妇人要养汉。若只守一个丈夫,那里晓得这般美趣。”[4](P395)
第一回中的花二娘与英俊知趣的任三官偷情甚美,“从做亲已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任三官放出千般手段,她全身心陶醉,感叹“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3](P5)。第三回中的李月仙更是一个典型,年轻貌美的孀妇李月仙,嫁给王文甫,“夫妻二人十分欢喜,如鱼得水,似漆投胶。每日里调笑诙谐,每夜里鸾颠凤倒”[4](P116)。可是丈夫外出经商后,她又难耐寂寞,经不起小叔章必英的英俊风流,与之偷情,再度良宵,月仙“今番禁不住了,叫出许多肉麻的名目”“那月仙丢了又丢,十分爱慕。从此就是夫妻一般,行则相陪,坐则交股”[2](P50),以至于后来丈夫回来半年后再度外出经商,月仙先是“暗暗欢喜”,以为又可以与必英私会,假意道:“你既要去,我也难留。只是撇我独自在家,好生寂寞。”后来听说文甫此次要带二官同去锻炼,“心如冷水一淋”。为救丈夫出狱,月仙卖身给人做妻,想到丈夫尚在监牢之内,开始还扭捏羞涩,而后“月仙见新郎之物与必英的差不多儿,十分中意。此时把那苦字丢开一边,且尽今宵之乐”[4](P154)。弄得他魂飞天外,捧着脸咋着舌头,把柳腰乱摆。又叫道:“死也从来未有今朝这般快活。”[4](P155)二官道:“此时你还想前夫么?”月仙道:“此时无暇,待明日慢慢细想。”[2](P163)“过了两个月日,每夜盘桓,真个爱得如鱼得水,如胶投漆。”[2](P52)但她良心未泯,想到自己享受快乐,丈夫却在狱中受苦。可是一旦二官假装要将她送给丈夫,月仙却不舍得,一把搂住他“快活死我也”[2](P56)。
在这些描写中,作者“总是以非常细腻的笔触,不厌其烦地描写女性在偷情时感受到的强烈的生理刺激和心灵震撼,突出她们性爱的欢乐、如梦初醒般的惊喜以及因此焕发出的生命活力”[5]。这些描写透露出贞操并非女性婚恋生活的目的,更非婚姻的全部,相反,生命的幸福、性爱的快乐和享受,比贞操更为重要,幸福原则才是人生的第一准则。像李月仙偷情时的真实心理:“再无别人知道,落得快活,管甚么名节。”[2](P50)似乎有点无耻,却又真实自然,显然,在她心目中,“名节”只有当别人知道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快活”才是第一原则。这种认识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以及传统贞操观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欢喜冤家》甚至会描写“贞妇”在遭劫后与匪人的两性生活场面。一般而言,古代小说对此情境的处理多写她们在威逼之下被迫与贼人强盗生活,但她们本身是极不情愿的,而且一般也不会写到她们的性生活场面,即使偶有,她们也是痛苦伤心,而绝对不会表现出快乐的一面。不过揆诸常理,这并不是非常真实的人性书写,因为强盗匪人也是人,也有多种类型,也有雅俗之分,其行止也分三六九等。但《欢喜冤家》却往往写这些落难女子的直接感受,快乐毫不掩饰,但又并非忘了前夫,体现了俗世人性的真实。如第五回的元娘遭爱慕她的蒋青设计劫走之后,本欲贞烈自杀,虑及腹中有孕,不得已而强从强盗,但在后者表现出真情与她交合时,她也暂时将原夫抛诸脑后,将快乐体验真实表达。如果我们将元娘与《西游记》里的唐僧之母殷温娇做一对比,就更能发现《欢喜冤家》如此叙事的意义,以及其思想的独特和不凡。
当然,书中有些性描写难免过度,且无甚交代过渡,便直奔主题,有色情化倾向,全书因此充斥一些色情淫秽小说中常见的词语。不过,就总体而言,《欢喜冤家》与多数明清色情小说还是不同的,书中的这些性爱的描写,尤其是女子的性体验的欢悦表达,在考察明代通俗小说贞节观和人性的演进层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守节的变通
守节与否应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变通,持一种灵活的、实用主义的贞操观。第一回中,花二娘得知自己和任三官私通之事败露,李二白已和丈夫设计谋害自己和三官。为了救人且自救,花二娘将计就计,主动和李二白发生性关系,借前来捉奸的丈夫之手将李二白杀掉。花二娘和李二白的性关系,无论对其丈夫还是情夫都可谓不贞,但作者却不以为然,反而大为欣赏,在总评中称赞她“出奇制胜,智者不及”。第三回中,李月仙的丈夫王文甫被其情夫章必英构陷入狱,企图谋夫夺妻。为救亲夫,李月仙被迫改嫁章必英。对此,作者借小说中人物李禁之口说:“今日之嫁,是谓救夫之命,非失节之比。”“周全丈夫生死,可与节义齐名。岂比失节者乎!”[2](P62)以上两篇所表露的观点,都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贞操观针锋相对,暗含了“失节事小,人命事大”的严肃命题,体现了作者对个体感性生命的高度重视,这与传统“贞操观”显然是悖逆的。第五回的袁元娘被蒋青强抢为妻,本想投水自尽,“只因身怀六甲,恐绝刘氏宗枝,昏昏沉沉,只是痛哭”[2](P94),后又以绝食相抗但禁不住蒋青甜言蜜语哄骗,加上“到了蒋家见比刘家千倍之富,况蒋青又知趣,倒也妥帖了”[2](P98)。后丈夫来寻,元娘本应跟丈夫回去,又为财物暂留蒋家。蒋青死后,元娘占有了全部家产、夫妻团圆。显然,在渔隐主人看来,当贞操与宗嗣、名节与实利不能两全的时候,弃贞节之虚名,图宗嗣、金钱之实利,实为明智,不可谓失节。第九回的王小山企图以妻子方二姑的美貌为钓饵,谋骗张二官的合伙资金。方二姑假戏真做,与二官频频私会,并将店中财物夤夜偷与二官,助其另开铺面,气死了丈夫。不久,二姑就明公正气地嫁给二官,做了长久夫妻。对方二姑所为,作者虽未旗帜鲜明地予以赞扬,但仍以含蓄的理解和首肯委婉地表明了“夫妇之间若没有恩爱,即没有贞操可说”[6](P640)的思想。
当然,毋庸讳言,《欢喜冤家》的贞操观就其本质来说,仍未超出男性中心话语范畴,作者对于妇女贞操问题的表现和思考,依然是男性中心文化机制下的一种有限观照;对于女性的角色还是停留在男性附属品和私有物的定位上。正如第十回许玄对秋鸿所说的,“若得小姐嫁我时,你是家常饭了,不时要用的”[2](P178),把女人看作男人随时可用且可随意处置的器物。因此,它对于女性失节行为的宽容和谅解以及对于失节标准的种种变通,都是建立在男性利益的基础上,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保障男性利益的最大化。女性失节与否以及要不要守节,都要看与男性的利益和需要是否一致,以及利益的孰大孰小了。但它毕竟还是表现出了与许多传统贞操观念相悖逆的东西,有些认识还具有近代人文色彩和某种超越意识、反叛意识。
注释:
[1]萧相恺:《〈欢喜冤家〉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
[2]周有德等点校,[明]西湖渔隐:《欢喜冤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按:简称点校本。
[3][美]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古本小说集成》本《欢喜冤家》,影印明崇祯山水邻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按:简称影印本。
[5]李淑兰:《<欢喜冤家>贞操观的现代解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6]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第四卷),《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