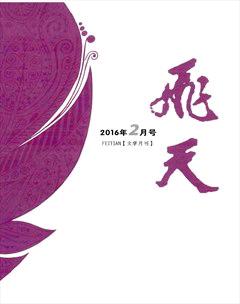零虚构

周瑄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人丁》《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多湾》,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在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多篇小说被转载和收入各类年度选本、进入年度小说排行榜。现居西安。
一
原以为大半夜的,街上一定是人迹全无,只有我们一家出没,哪知道还是车来车往,行人走动。城市继续喧嚣,只是压低了声音,灯光接替阳光,孜孜不倦地照射。女儿或许以为这是一场梦,她怀着无辜的心情,没有声息地坐在后面。我甚至不敢回头看,害怕见不到人,只有一堆糖稀顺着座位往下流淌。
夜里一点半,丈夫推醒我,问女儿还烧不烧。我起身摸她身上,天哪,还是烫手!两小时前,抱着侥幸心理叫她吃了药睡下,想着明早起来就会好的。
看来扛不到天亮了,赶快上医院吧。丈夫下楼开车,我叫女儿起床,换衣,收拾东西,拿上医保卡、水杯、毛巾等,下楼坐上车。去哪个医院呢?我说,去最近的呗。
夜市上灯光明亮,男男女女在开心吃喝、大声说话,桌上空啤酒瓶林立,脚底下一片狼藉,他们就像坐在废墟之上。
因为修地铁,医院所在十字路口堵成了迷宫,竟然不知道该从哪个通道拐进。路口车辆还是一辆紧跟一辆,难道每个车上都有一个发烧病人?有什么要紧事让他们凌晨两点还不睡觉,开着车在大街上跑呢?
右拐后,见医院大门关闭,门口堆放着建筑材料,根本不能接近。大门改了,改在哪里了呢?无处问人,也不能开着车乱找,于是决定到它后面那家医院吧,虽然小些、破些,但总是三乙医院,治个发烧还是没有问题的。从大医院旁边的巷子右拐,过一个小十字路口,向前走了几十米,一辆大型垃圾车停在路中央,环卫工人围着在忙碌,一派火热场面,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们的车跟得太近,垃圾车上有飘飘洒洒的东西散落。小街太窄,路两边又停满了车,根本没有调头的位置,只好一路倒回。后面又有车跟上来,灯光哗的照射,于是停下,打开门告诉后面,走不成了,向后转吧。看来,半夜开车一点也不比白天省心。
倒回刚才那个小十字,向东去,走到一条大路上,再从另一条小路折回,来到那家替补医院。
半夜看病的好处是,没人跟你争,也不用排队。所有房门和窗口都静静地等你来,医护人员即使打着哈欠,趴着睡觉,因你的打扰而满脸谴责,但总算是坚守在岗位上。
其实当医生也不难,刷刷刷单子一开,化验血、化验尿、拍胸片,最后得出结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好像她刚才用手电照到红肿溃烂的嗓子、量体温39度6、拿听诊器听前心后心,还不足以判断似的,必得把诊断权交给机器,再花了这一百多元,才能进行下一步程序。去吧,先交钱,再抽血。
丈夫去交费,我陪女儿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待。从门外进来几人,中间一男,周边簇拥着几个女的。男主角头上用白纱布层层包裹,脸上和短袖上,就像是红颜料桶扣下来一般,鲜血迸裂,图案鲜活而生动,真实记录着不久之前的一场殴打场面。几个女人像对待真正的英雄一样叫他坐下快坐下。英雄用毫不在乎的表情,不,甚至有点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风采,步履轻捷,走过来坐在我们身边,掏出一支烟点燃,仰起脸,轻松地吐个烟圈,好像他是来医院休闲的。那几个女人蛾子般在几个窗口扑来扑去,忙着挂号、问询。我和女儿紧张地对视一下,不敢就此发表什么意见,当然也不敢表现出受惊吓的样子乍身逃开,尽管我们非常想这样做。伤了英雄的自尊,可不是好玩的。幸亏丈夫交费结束,叫我们去那边抽血,我们努力做出平淡的姿态走开。
大门外又进来三个女孩子,两边的小心地搀扶,中间的那位手捂着肚子,弯腰艰难地走,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
所有检查做完,结果很快出来了,我们拿着去往急诊大夫那里。
医生说先打两天吊针。丈夫问打柴胡行不行,也就是只肌肉注射?我们小时候发烧,打针柴胡就好了,因为孩子明天早上还要补课,不想请假。医生说,从前那针已经不能退现在的烧了,必须吊瓶。让她躺着打,针扎上后就可以睡觉。
躺着打针的房间里有三张床(对面是坐着打吊针的房间,两排沙发相对),分别靠着三面墙。女儿躺在门口那张床上。护士扎上针后交代,一共两瓶,得打三四个小时,因为有一瓶会有些疼,不能快。我们关了房间灯,为的是让女儿睡觉。我和丈夫躺在另一张床上,他在里,我在外,随时可以起来。其实也睡不着,蚊子嗡嗡叫,一会儿胳膊上、腿上全是疙瘩。
门被推开。“来病人了,你们起来起来,注意点影响!”护士引进来那三个女孩子。赶快起身,打开灯,那个肚子疼的女孩子躺在最里那张空床上,扎上了针,她向床的里边靠,外面好再躺一人。那两个女孩子互相谦让,叫对方躺到床上去。她们彼此用极小极小的声音说话。其中一个穿牛仔短裤的女孩子,皮肤晒得挺黑,身材细溜,双腿修长得令人惊讶,似乎不是人的真腿,好像她因为伙伴犯了病,走得急,拉了橱窗模特的腿就走。长腿女孩告诉另一个说,你上床睡吧,我今天夜班,早上回宿舍再睡。于是另一个被请上了床,大大的身子横卧在床的这头,姿态不甚文雅,但憨态可掬,睡得香甜。那长腿女孩俯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姿态美好,短裤很短,长腿暴露很多,却非性感的诱惑,而是黝黑而贞洁的懵懂,仿佛她在给画家摆出造型。一种友爱温馨的气息被她们呼出,在那个床畔环绕。可能是哪家超市里的打工女孩,远离父母家人,相互陪伴关爱,这个特殊的夜晚,两个女伴的踊跃前来显得尤为重要。
走廊上又有喧闹惊慌的脚步声、呼喊声。又来病人了。隐约听到医生问,吃了什么?有人回答,海鲜。
蚊子继续叫,屋子里非常闷热。其实房间里有个空调,可是连着两晚我们都没发现,或者它的老态让我们没有奢望它能正常工作。我们只是做出想睡觉的样子,但其实除了两个病人外,都没有睡踏实。丈夫被咬得气恼,说他到走廊的长椅上去睡。我拿着折迭几层的单子去给他铺到铁椅子上,看到另一间抢救室里灯光大亮,两张床上,一张躺了个学龄前儿童,另一张躺了个女人,可能是母子俩,都已经挂上了吊针,旁边还有一个青年男人,一个中年妇人,或许也是母子俩。医生护士在旁边站着观察,孩子脸色苍白,紧闭双眼,刚才的那一阵忙碌使得小家伙止住了抽搐,这会儿累得睡着了。
那个英雄,与陪他的女人中的一个坐在另一排椅子上,他还在抽烟。他们到医院来时,已经包扎好了伤口。是在别的医院包的,还是在这家医院包好后又出去办什么事,再回来的?他们不打针,也不离开,也看不出困累,只坐在这里商谈什么事情。
回到房间,摸摸女儿额头,沁出汗来,头发都湿了,看来是药物起了作用。见那个长腿女孩脚也上到椅子上,双臂环抱,把自己收成一把折叠伞。只有足够苗条和年轻的人,才能这样收折身体。我慈母心作祟,碰了碰她,叫她到我这边的床上睡,她推辞一下,猫儿一样上到床的里边。我说,你放心睡吧,我是睡不着了,看着两个人的吊瓶。她腼腆地一笑,黑黑的皮肤像巧克力一样融于暗处,露出白牙,楚楚动人,像一条长长的美人鱼,侧身躺在床的里边,很快发出均匀的起伏。
三点多了,走廊里安静下来,英雄和他的女陪护们已经离去。就像是白天的午后,到了三点,一切都累了,时间步入谷底,进入一种天不管地不收的迷茫状态,离奇的故事也该进入尾声,诸多矛盾不再爆发,问题与病痛,撑过三点也就能等到天亮,想必不会再有人来看急诊。熬夜的人也该睡去,早起的人还未醒来,这可能是夏夜里最平安宁静的时刻。医生护士也清楚这一点,她们的房门掩了起来,用床单盖住身体,若不是我来叫换药,她们会靠在椅子上睡着的。只有蚊子不知疲倦地嗡嗡叫,不停息地咬人,它们难道是夜猫子,白天睡觉晚上叮人?或者也轮班休息,二十四小时工作?我的胳膊腿上、脸上布满了疙瘩,不停地挠,万不得已,被子盖到小腿上。女儿因为烧着,身体发冷,盖上被子,露在外面的脸,汗水形成保护层,蚊子不得下口,她睡得还算踏实。
进入伏天,天天气温35度以上,学校坚持补课。海可枯石可烂,补课的心不能变,哪怕天塌何惧地陷,千令万申突击检查学生举报统统没用,反正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补课的决心。补也就罢了,简直是丧心病狂,早上七点十分到校,中午十一点半放学,下午一点半上课,一点二十就得进到教室。每天中午,将准高三学生从短暂的午睡中叫醒,迷迷瞪瞪,扑到大太阳下,疾走二十分钟到校。女儿每次出门,把从前的再见换成了:讨厌你。开始我不明白她为何每天要带着厚厚的校服外套。她说,教室里,男生把空调温度开得非常低,穿着外套都冷。白天已经占满了全部时间补课,晚上不留作业了行吗?不行,坚决不!每晚作业写到十一点,算是便宜你的,早上六点多,照常起床上学去。室内外温差大,学习强度大,身体不出问题才怪。就这,她还要心心念念,打了吊针,明早继续去上学。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系统,莫不是被一个外星人恶魔控制住了?不把祖国花朵们的身心损坏,不把他们全部洗脑变成精致的白痴,誓不罢休。
早上六点,两瓶针打完,女儿像个水人,全身无力,眼睛睁不开。终于决定,请半天假。天塌不下来,先回家大睡一觉再说。
二
医生说,今晚打针最好在十点之后,不要与凌晨那次间隔太接近,于是决定,等女儿写完作业,十一点多再去医院。
我们带了驱蚊剂、电蚊拍、床单。俨然是一支灭蚊小分队,二次来到医院。
丈夫去交费取药的时候,我先在病房里一通喷洒,一直到走廊外面,厕所门口。
女儿要换个手扎针,躺在了直对门口那张床上,左手放在外面。今天是先打慢的那一瓶,一个多小时,才下落一半。我订了手机闹铃,却也睡不踏实,闷热难耐,怎么躺都难受。蚊子前赴后继而来,驱蚊剂、电蚊拍基本失效,扎上针后我们就好好睡的打算泡了汤。
两点时分,忽听得门外闹闹哄哄,有人大声呼喊,急诊,医生!好像是很多人涌进走廊,听到有人喊,吐血,止不住,半个小时了!有医生在忙乱奔走,问,喝了多少?有女人答,没多少。问,喝的白酒还是洋酒?答,葡萄酒。
看来城市并未入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演进。夏天的夜,找尽各种理由,变出多个花样,迟迟不肯结束。
夜晚有着无限可能,急诊科,是那种将我们从正常生活中劫持出来的机构,天大的事也先放下,解决被突然打乱的身体秩序,它的前奏常常伴随着暴力和意外,对身体机器的野蛮操作,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冒犯,付出无知的代价,只好赶来紧急弥补与缝合。走廊上明亮的灯光,标志着急诊室是永不休息的地方,医生护士严阵以待,随时收容版本迭出的身体故障,再稀奇的事对他们都是稀松平常,也难怪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不认为你是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的人,而是各式各样出了问题的机器,他们要寻找、要对付的相同性症候群,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诊治。
人们的来回走动、奔跑,使走廊上凝滞的空气流动起来,弥漫着红酒的香甜气息,好像是挺高级的酒。听到有人大声呕吐的声音,联想到吐出的是鲜血,恐怖感罩住了我,睡意全消。一个女人的哭声传来,每呕吐一下,她就放声哭一回,好像那位喋血者与她之间通了电,使二人有了相同的频律。我走出去,斜对面抢救室门口,几个人,看样子都喝多了,飘飘浮浮站在那里,一个身体修长的女人,脸儿绯红,是酒精的作用,失声地哭,翻腾自己的小包包,向外掏钱。“你那里还有多少?你呢?”她问身边的人,让哥儿几个把钱都拿出来,快去交费,几个人都在翻口袋。一个男的在哄劝她,先是站她对面,摊开双手,让她别哭别哭。抢救室里又一阵呕吐声,那女子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一个小时前,她还是个风姿绰约的美人、恋人,一场酒局的女主角,沉醉在美酒与爱情里,此刻变成一个惊吓无措的孩子。对面的男子也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该怎样更好地安慰她,除了拥抱,人类好像也没有发明出更管用的办法。他试试探探,终于大胆地将比他高出一截的女人抱在怀里,颠三倒四地说,何姐,何姐,听我说,你听我说……舌头打绊子,或者大脑跟不上,他却啥也说不出来。几个人凑了一些钱,那位拥抱者抓在手里,向交费处跑去。
很多故事并没有随着白天的结束而中止,而是借着夜晚的神秘顽强地上演,不屈不挠地在等待、在煎熬、在交涉。深夜在这里变得叵测多姿起来。
女儿出了很多汗,头发贴到脸上,我洗了毛巾给她擦拭。看到刚才去交费的那个青年拿着单子跑回来,收不住脚步,跑过了,像动画片里的汤姆或者杰瑞,脚步踉跄地退回,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四下看看,拍拍脑门,恍然大悟的样子,进到医生的门里。
第一瓶药水总算滴完,我去叫护士换药,进到值班室,空无一人,发现这里跟抢救室是相连的,人都在那里面,对付那位喋血青年。我走进去,见床上躺着一个男子,上身裸着,贴了好多管子,皮肤蜡黄,肚皮那里陷下去一个坑,周边围着今夜值班的所有医生护士。我向前走去,想看到一点鲜血,满足好奇心,可他已经被清洗干净,见不到任何证据,只像一张皮似的躺在床上,打着吊瓶,昏睡过去。护士听到我的脚步声,转过身,问,药完了吗?见我往床上看那青年,用身体挡住我,不知是爱护他还是爱护我,用哄孩子般的口气说,不看不看,喝多了,走,看娃去。端了药来到我们房间。
这一瓶快,大概一个小时就能结束。一楼走廊又恢复暂时的平静。时间进入黎明前的黑暗与安宁。
医院急诊科,是一个预设的前提,每晚都要有几个人光临,医生护士不愁没事干。外面的夜市,路上的交通,不和的家庭,破裂的感情,花样百出的经济纠纷,不断为他们输送各式各样的惊险。我一直在想,医生的心里到底是希望越忙越好,还是巴不得失业?
外面渐起争吵声,好像是那喝醉的人,做梦一样想起来什么,责怪医生抢救不及时,让他的朋友多吐了几口血,多遭了一会儿罪,让他们的何姐承受了惊吓。医生说:“你还要我们怎么样?人一抬进来,就动手处理了,用药得等你的交费单子,没有单子药开不出来。”喝醉的人语无论次:“咋说呢,你们这就叫不负责任,不为患者着想,人都大口大口吐血,哇哇的,吐了半盆子,你们一点不着急……”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好在人已经控制住,现在静静睡着,他的谴责也就像是撒娇般的絮叨,只是在证明他已经恢复了说话能力。
灯被打开,注射室进来一位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人,好像是一对母子。母亲躺下,护士给扎上了针,儿子坐在床边守着。母亲抱歉地说:“要不是坚持不住了,我不会半夜给你打电话的,打扰你们。”儿子模样的人说:“没事没事。”我看她的针正常滴着,建议把房间灯关了,这样病人可以睡得好一些。母子俩欣然同意。只有走廊上透进来的一点微光隐隐探视,病房又恢复到宁静与安详。母亲往里面躺,拍着身边,用很期待的语气让儿子躺在她外面。来回让了几次,儿子坚持不躺。他一定是个已婚的人,从法律到身心,属于了另一个女人,再与母亲躺在一起让他有羞耻感,他宁可在床前身体笔挺地坐着。母亲絮絮叨叨地小声说着她的病情,可能是血压高,引起了难受。她讲述的口气是那么平静幸福,没有一点疼痛或受难的感觉,好像因为病情的发作,才得以与儿子共度半个夜晚,她是多么珍惜这美好时光,很惬意地半侧着身子躺在那里,面对儿子,一会儿问他热不热,一会儿又问喝不喝水,好像需要照顾的是儿子。
我收拾东西,叫护士来拔针,叫醒丈夫,赶快开车回家。快四点了,女儿回家还能接着睡两个小时,再起床去上学。昨天早上已经退烧,今天打的,只是巩固一下。拜拜了,注射室,再见了,花样迭出的急诊科。
三
中午女儿放学回家,说又烧了。一量体温,39度4,我着了慌。按说打了两天针,不应该再烧了呀!她说男生把空调温度开得太低,她穿着校服外套都冷。
“我不想再请假了,可是全身难受,走路都没劲,怎么办呀?”她站在床前,呜呜哭着,是个痛苦抉择的人。现代教育把学生训练得如此忘我,请个假就是重大损失、严重事件,让她有痛心疾首的感觉。
“那必须请假,下午好好睡半天再说。”
“可我的课本还在桌子上没有收呢!”
“睡到下午五点多起床,或许就好了,赶六点放学的时候去学校收拾课本。来,吃了药,好好睡一觉。”
下午四点多,摸她脑门,依然烫手。我立生恐惧,会不会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什么急病、怪病?突然我的想像力空前的丰富,就像她放学没有按时回家一样,车祸、绑架、拐骗等节目在脑子里快速上演,甚至想起我编过的一本书《失独家庭调查》。天哪,这样烧下去,会不会化到床上成一摊水呢?将我唯一的女儿人间蒸发!再量体温,39度6,她缩在毯子里哭了起来:“妈妈我会不会死呀?”
“死倒不会,不过这样烧下去,有可能变成弱智、白痴,明年高考,什么中大、南大、厦大,想都不要想了,弄个蓝翔技校、桃李春烹饪学校凑合上得了。我给你爸爸打电话,咱还是去打吊针吧。”
丈夫把车开到楼下。我又收拾昨晚那一套东西。来到医院,在门口他把我们放下,调头回去到女儿学校整理书包。
刚过六点,急诊室换了个年轻的男大夫。给他看了前面所有那些材料,再量体温,还在39度6。大夫怀疑是支原体感染,让再抽血化验,不过结果明天下午才能出来。他说昨天的药里没有退烧的,这可能是导致温度又上去的原因,今天要加上。
医生护士全都换班了。一个护士准备好药之后,让我们先去吃饭,否则药会刺激胃。我俩在附近饭馆吃了饭,回到医院门口,见丈夫背着书包在等我们。
病房门口的床上躺了一个男人,盖着被子打吊针,一定也是发烧。
女儿躺在最里面一张床上,扎上了针。不知怎么一抬头,发现墙上竟然有空调,床头柜上有遥控器,拿起来打开,竟然能制冷,只是噪音有点大,总比热着强。
我让丈夫出去吃饭。
又进来一对母女,女儿二十多岁,躺下打针,母亲坐在床的另一头,两人亲热地说笑,好像姐妹一样,谈的也都是家长里短、明星逸事,看不出女儿有什么病。
门口床上男人的电话响了,他接听,一口广东腔,说的什么进货、入库之类,再后他电话不断,不是打出就是接听,很繁忙的样子。他在一个电话里告诉对方,下午正在工作,感到不适,全身发冷,没有力气,自己来医院看病的。一个为事业奔波的小老板,蒙在被子里,还在密切与外面那个世界保持联系。又一个电话打来,是个女人,流水账般说了许多,他不表态,冷静地说,明天我打给你,现在身体不舒服。对方问,怎么你病了吗?在哪里?他不回答,只说,明天上午我打给你。又问,小孩子怎么样,还好吧?对方说挺好的,在玩。他挂了电话,掀开被子起身上洗手间,自己举着吊瓶出去。是个三四十岁的男人,脸形狭窄得让人吃惊。
一会儿他回来,电话又响,一个女子的声音。他说,你在这个路口下车,自己问吧。
丈夫吃饭回来。我让他照看着女儿,我出去履行每天傍晚的一小时散步。走过金店门口,看到电子屏显示,黄金每克248元。网上有消息说,炒黄金的中国大妈赔惨了。我在大商场看到服装大降价,一楼摆了一片衣裙摊点,好多挺漂亮的丝绸裙子三五百元,我蠢蠢欲动,可是没带钱。我为了找一个钉鞋的,走了几条小街,要给凉鞋鞋绊重新换两片粘贴。之前那个经过磨损,已经粘不牢,走路总掉。找到一个很简陋的小店,那钉鞋老人坐在那里,与一个女人吃西瓜,每一个来钉鞋的人,要先接受他目光的嘲讽与严厉审查。他带着很不屑的表情,扔了西瓜皮,用极快的方式,也不拆之前那片旧的,就将新的铰了一块,往上面一砸,两分钟完事,鞋子扔回来,问我要五块钱。我吃了一惊,于是想起来这里是市内治安最差的地方,常有恶性事件见诸新闻,起因都是为两三元钱的纠纷。他的女人用一种非常豪放的姿势仰面摊在躺椅上,好像她不是女人一样,用一种预设的挑衅目光看我。放下五块钱,我赶快走了。
回到病房,第一眼见到直对门口床上的那对母女变成了父女,妈妈回家做饭去了。一个小时前,我出门的时候,当妈的让女儿给爸爸打电话,问他在哪里。爸爸跟妈妈坐的姿势一样,整个人在床上,靠在另一头,亲昵地跟女儿说着话,用的音量是这间房里的三分之一,自觉地在他们该有的界限内,谈的话题也基本属于公共,适合别人听到。门口广东人的床上,笼罩着一个年轻女子,身体歪在床的上方,用手臂将病人环绕起来,大有随时要将他揽入怀中的感觉。
我摸了摸女儿的额头,开始冒汗,温度有些下来了。丈夫靠在床头看手机,我坐在床头椅子上看书。年轻女子开口说话,声音大得刺耳,以至于她一开腔,大家都沉默下来。她不明白这沉默是对她的谴责,反而更加得意地说着,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房间的对话应该使用三分之一音量,或者小于三分之一。他二人完全是三分之三,甚至大于三分之三,那女子不但嗓门大,还夸张地装饰她的嗓音,将每个词每个音节都勾上花边,学习电视主持人的发音方式,像过度包装、华而不实的商品。不知道内心里对自己有何种期许的女子,需要这样矫饰的声音。我心里烦得要命,真想结结实实瞪她几眼,可出于对她的蔑视,始终没有看她的脸,一直不知她长什么样,可我相信,肯定不怎么样,好看的女子不会这么变态地在声音上大做文章。我克制地扫视一眼她的腿和脚,皮肤很黑,不是前晚那长腿女子,为了生活在太阳下奔波晒黑,而是生来就黑的那种,不甚洁净、皮肤糟污的那种。脚上穿一双后跟和底子特别高的廉价凉鞋,穿这种鞋的女子,其实是在向世界宣布:我压根不知教养为何物。他们边玩手机边说话。女子说:“哎呀手机又快不行了,慢死了,打不开。”广东男子说:“换个新的。”“唉,对于我这种一年换几个手机的人来说,也不能买什么好手机。”她用一种明显虚假的声音,为自己使用廉价手机开脱。
我想那男人接下来会说,我给你买一个吧。是个男人,这会儿都应该这样说呀!屋子里安静下来,似乎都等着广东男人说这句话,年轻女子也在期待,我仿佛听到她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三个瓶子的滴答声突然调整为一个步调,都等待一个结果。不想,广东男人说:“叫你男朋友给你买呀!”
啊?那你们二位啥关系呢?这还搂抱着呢。屋子里的人都快要面面相觑了,我感到丈夫用后脑勺在问我,什么情况?
女子说:“哼,他才舍不得给我买呢。”她在鼓励广东男,似乎逼着他说,那我给你买吧。对面床上那一对父女各自眨巴着眼睛,看着墙,不说话。广东男也不说话,三个瓶子滴答、滴答,不置可否。七个人一起捱过短暂的沉默,广东男说起别的事,这个话题就此过去。于是我心里给这女子定位:贱人。
贱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屈不挠,继续装饰她的声音,嗓门大得完全不适合夜晚,更不适合病房。我知道所有这样说话的女子过的都是与声音不同的生活,因为寒酸,所以华丽,越寒酸越华丽,除了声音她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无止尽地夸张、修饰,反正没有成本,也不需承担什么后果,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音节的边缘、末梢都极尽雕琢,不是她自己在说话,而是她期待成为的那个人在表演,就像在气球上跳舞一样轻浮无着落,极尽奢侈,也极尽让人厌恶。
她一开口我就心烦,深深被打扰、被惹恼。那对父女也不再说话,心情都不太好了的样子。我放下书到走廊上去。一会儿那女子出来,到护士办公室拿温度表,我得以从身后打量她,身材基本属于傻大黑粗那种,偏偏穿着紧身衣裙,走路夸张地扭动。
她回到病房,用着宫廷剧里学来的姿态给广东男将温度计夹上,幻想自己成为受宠的人,然后又那么用胳膊环绕着他,生怕他被另外那些妃子抢走似的。病房里气氛变得很难受,对每个人都是折磨,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大家也都没心情说话,分贝让给他们,那二位贱人,立即继承大家转让的资产,开心处,无所顾忌地大笑,音量扩大到三分之五、三分之六。过一会儿,女子又亲手将温度计取出来,用夸张的动作举起来看,期待这一姿态在广东男眼里楚楚动人,用一种惊喜的语气说,哇,37度5,不烧了耶!好像她在参加电视节目,猜猜看,有个白痴问题是:请问他打了两瓶吊针后,体温降到了多少度?而她一下子猜中啦,好能干耶!她夸张地一拧身,迈着时装模特的步伐出门,还温度计去了。大家稍微喘了一口气,乞求广东男的吊针快点打完。
她又迈着很铺张的步子回来,款款坐在床边,脚的位置只离我坐的椅子半步远,用一种放肆的姿态,脚尖面对我。我们五人都不再说话,好像她夺去了我们的权利,让我们变作哑巴。那四人在看手机,我拿着一本书,却读不进去。我们的沉默是某种退让,使他二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放大了音量。轻浮的双关语,不打粮食的废话,无谓的调笑。我看了看广东男的吊针,快了,就快完了。终于的终于,广东男抬手按头顶上的铃,很快护士进来,给他拔了针。谢天谢地!女的照顾男的起身,帮他提起包包,更加开心地说着废话,挎着胳膊出门去了。屋子里的人都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女儿第二瓶针剩下一半的时候,我遵医嘱去要来温度计。想到这有可能是那对贱人拿过的用过的,我在水管下冲了又冲,直到凉透。
37度6。汇报后,医生说,嗯,好了,退烧了。我问,明天还要打吗?他说,如果不烧,就不用打了。
第二天傍晚,我去散步,顺便取化验单,女儿要我一拿到单子就发短信告诉她结果。“我可担心了,要是真感染了,可怎么办呀?”她说。
“真感染就继续打针呗,那么我这个小说就有可能写成中篇啦。小小注射室,多么精彩,指不定咱还遇到什么奇葩呢。”
夏夜的热风中,我一路走向医院。马路上汽车疾驶,或者堵在那里,发出压抑的吼声。路上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觉得他们都是急诊室的潜在客人,一不留神,就会去光顾那里。
医院大门口,有一排隔离汽车的圆石墩,光溜溜的,圆润可爱。每个上面坐着一个乘凉的人。有两个年轻人,各拿一瓶啤酒,相对而坐,边喝边挥动手臂,激烈地讨论着什么。坐在这里,是准备随时喝醉了或谈崩了打架,瓶子碎裂,身体开出红花,去急诊室更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