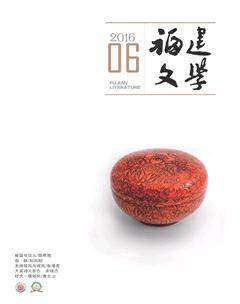梅州客家老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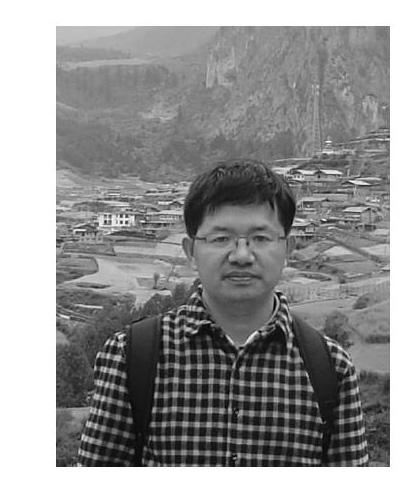
黄发有,1969年生于福建上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文学史料与文学制度研究。出版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文学传媒与文学传播研究》《文学与媒体》《媒体制造》《想象的代价》《边缘的活力》《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等专著。
时空边缘的惊叹
联芳楼位于梅县白宫镇新联村,从白宫镇路口进去还有不近的路,它偏居一隅,却将古今中外的建筑元素融会贯通,如耸立在静谧田野上的一个突兀的惊叹号,它在客家建筑中是一个异数与特例。我曾在小书《客家漫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燕窝外部凹凸不平,一些树枝和草秆参差交错,但是,燕窝内部却极其光滑整洁,其圆润程度是任何一个泥瓦匠的手艺所无法比拟的。这种轻外重内的生存观念与客家人极为契合,客家人身上奔涌着的流浪血缘使他们不太计较外部环境的舒适与否,而是着重于内部的调适。……在我看来,客家土楼不管是圆楼、方楼、八卦楼还是五凤楼,其建筑特征都颇似燕窝。客家土楼的外部追求坚固与实用,内部却修饰得较为舒适。那些用生土夯筑起来的外墙,显得寒酸和粗糙,而庭院却是那么空寂而洁净,木质的栏杆上还雕龙绘凤。”联芳楼不仅在结构上玲珑剔透,浑然天成,而且修饰得雍容华贵,端庄典雅,称得上美奂绝伦。
联芳楼的外观巧夺天工。中央及左右两个门厅都在四根直径近一米粗的白色罗马柱烘托下,挺拔地向上升腾,显示出宫殿一样的高雅气派。门厅上方飘出漂亮的半圆形柱廊,闪耀着空中楼阁一样的梦幻色彩。阳台的顶端承载着用雕花的石材精制而成的拱形穹顶,就像一顶顶飞来的冠冕。中央钟楼上浮凸出烫金的五角星和“联芳楼”三个大字,字的下方是双狮滚球浮雕。而左右钟楼顶部雕刻着两个鬈发高鼻的天使,背上长着一双翅膀,他们托着一颗巨大的五角星,一头威武的雄师盘踞在五角星的上方,双眸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夺目的光辉。原来,它的眼睛镶嵌有蓝宝石和黑宝石,碧眼黑眸,轮转着岁月的倒影与流光。中央二楼柱廊两根廊柱的顶端,伸出四个经过变形处理的瑞兽头像,形状似龙似鹿,又有麒麟或牛的特征,嘴里含着长长的链环,眼眸中的蓝宝石熠熠生辉。中央柱廊两侧护栏的栏板外面,以简约的风格雕刻着传统写意山水画,工艺精巧。中央门厅的门楣上以浮雕形式讲述着郭子仪拜寿的历史典故,其间还点缀着花草鱼虫图案。左右门厅的门楣正面如天女散花般落满四时佳果,色彩缤纷,隐隐地弥散出果香的清芬。门楣两侧浮游着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似乎随时都要破墙而出。
房屋正面的窗户上装饰有孔雀开屏和雄鹰展翅浮雕。中央门厅两侧的窗户上栖息着一对孔雀,下方镶嵌着两幅壁画,在小桥流水人家的背景中,有妇人打着伞袅娜地行走,有若干部自行车穿行其间,展现出一派具有现代气息的田园风光。房屋左侧和右侧的窗楣上,守望着两只展翅的雄鹰,下方同样镶嵌着两幅壁画,只见农人赶着耕牛在犁地,渔人满载着收获走向迎接他的家人,海滨耸立着尖顶的教堂,与挺秀的宝塔遥相呼应,海面上穿梭着精致的小船,还有冒着浓烟的豪华轮船呼啸而过。匪夷所思的是,居然还有穿山而过的火车奔驰向前。自行车、轮船、火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在本分的农人的眼中,有着怪力乱神似的魔力,而联芳楼的主人居然把它们作为纳吉求祥的装饰,这样的冲击就像把圆形的围墙冲开了一个缺口,给守旧的村民幽暗而封闭的内心世界带来了一缕让人惊恐而好奇的光线,为这个偏远的村庄打开了一扇窥探外部世界的天窗。
联芳楼是由钢筋水泥构筑而成的三堂六幢的二层楼房,在内部结构上借鉴了中原府邸式建筑和三堂两横客家围龙屋的布局,共有“十厅九井三堂四廊”。联芳楼长近百米,宽四五十米,总占地面积约三千六百多平方米,敞厅和天井将98间房间分隔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区别于传统客家围屋用走廊贯通房间的方式,既有重门叠户的空间感,又有别有洞天的隐秘性。内部装饰采用传统工艺和装饰手法,中堂、上堂之间设明代风格的金漆木雕屏风,桌椅为红木雕花的清代样式。富贵(牡丹)花开、鸾凤和鸣等团花图案点缀着屏风、立柱和房梁,而二楼地板上以凤凰、麒麟为主题的浮雕,在黄昏模糊的光线中似乎正缓缓地向上腾跃,翩跹起舞。门盆栽的花木点缀其间,红绿掩映,弥散出来的鲜活气息与室内浓郁的古典氛围相映成趣。上的铜锁刻有精美的花纹,连下水管道也是铜制的。楼上的数十个房间采用西式布置,还建造有蹲坑式的卫生间。穿行在曲径通幽的走廊上,偶尔会看到藏在角落里的风车、打谷机等农具,让人萌生出时空交汇的错觉,恍惚中不知是置身于西式别墅还是田园农舍。
白宫镇因宋代元丰年间当地建有一座白色庙宇“明山宫”,附近百姓称其为“白宫”,故得名。这是一个富足的小镇,也是著名的侨乡,居民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侨眷。联芳楼的建造者丘星祥、丘麟祥五兄弟就是印尼华侨,他们在印尼经营大米加工和销售,业务遍布东南亚,是远近闻名的一代米王。白宫华侨多有断家不断屋的习俗,即使身在海外,也要在老家留下根基,接续祖宗的地脉。联芳楼从1928年开始规划,对法国文化心怀仰慕的丘氏兄弟延聘一中一法两位设计师,构想梦幻家园的蓝图。1931年正式动工建设,耗时三年,耗资二十四万光洋,耗材多由国外进口,雕刻、镶嵌、油漆等细活由国外和潮汕的工匠精心打磨而成,匠心独运。联芳楼中西合璧,它是客家山居文明与外来文明交融互渗的象征,旅外华侨犹如南来的季风,为这片深居内陆的客家乡村吹来海洋的风韵,在与山地云层的撞击中化为雨露,无声地滋润这片自闭和板结的土地,驱使客家乡亲走出画地为牢的千年定势。
联芳楼是兄弟情谊的见证与结晶,其楼名包含“五叶联芳华”之蕴涵,楼顶上镶嵌的烫金五角星正是丘氏五兄弟同心协力的形象概括。由于客家聚居地多为偏僻而贫穷的山区,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不少兄弟联袂建造房屋,但合族聚居也常常导致种种摩擦与冲突,兄弟阋墙也是常事,所以富裕者大多喜欢自立门户建造新居,留守大规模的客家土楼或围龙屋的多为贫困的弟兄。发人深省的是,到海外创业的客家人在饱受了立足之艰和异乡之苦后,倒是十分团结。梅县有一首反映客家人过番生活的山歌这样唱道:
好花难有百日鲜,番片患病真可怜。
自己手中无钱使,无只亲人在身边。
正是举目无亲、寸步难行的刻骨体验,使身在异乡的客家人格外珍惜亲情与友情,自觉地组成以宗亲为核心的创业团队。外部危机常常能强化客家人的凝聚力,激活其反抗潜能,客家侨区的居民多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而过度封闭的内部繁衍只会弱化其创造力,甚至滋生种种内部矛盾和宗族冲突,那些缺少流动性的客家山地的村民,他们的生活就有点坐井观天的味道,胸襟比较狭隘,锱铢必较。正如一则客家谚语所说:“行前三步脚,另有一片天。”
来联芳楼之前,听朋友说,他们在这里只碰到一个叫“梦梅”的守楼老太,非常和善地任他们自由出入。当时,我脑子里忽然蹦出几个字眼——“一个人的楼台”,感觉人和楼都笼罩着一种寂寥与迟暮氛围。来到联芳楼,一只看家狗异常威严地朝我们狂吠,一会儿走出一位秀丽的小姑娘,为我们开门,狗顿时收敛了那副凶相,摇着尾巴躲到一边去了。在一楼左边的饭厅内,我们看到墙上贴满了当地小学颁发的奖状,才知道小姑娘名叫丘瑜婷。她的父母在广州、东莞等地做生意。她和她的姐姐坐在卧室里看电视,让我们随意观看。黄遵宪的《眼前》诗中有句:“添巢燕子双雏黑,插帽花枝半面红。”我想,这小姐妹就像旧巢里的雏燕一样,等翅翼丰满后,也会追风远游,但有一种情感就像长长的脐带一样,使她们与“胞衣迹”——这座华丽的围楼和周围的村庄紧紧相连。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儿女而言,屋家也正是精神的胎盘。
石缝里的迷情
泰安楼坐落于大埔县城的龙冈村,是极为罕见的石方围楼,建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楼高三层,共有二百间房屋,一二层外墙为石墙,三层外墙壁及内墙为砖墙。因楼外墙为石墙,故俗称石楼。楼的一至三层四周向内设前走廊,一层走廊的柱子为上木下石,二三层为木柱,三楼前排中厅设有祭坛,为防外患,三层除前廊外,还在外墙与房间之间设有后走廊,也就是客家地区俗称的“走马棚”,遇到外敌进犯时,守楼者可以沿着走马棚游走,灵活机动地选择最佳的火力点。与传统的客家土楼与客家围龙屋相似,一二层不开窗,三层才开窗,并设有枪眼,整座大楼只有一个大门出入,门板镶上厚厚的铁皮,大门顶有蓄水池,供灭火之用。楼内主体建筑为平房,三层方形楼房把主体平房怀抱其中,形成楼中有屋,屋外有楼的格局。楼内格局的布置别具匠心,占据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为平房,分上下二堂,上堂中堂书“祖功宗德”,陈列先祖神主牌,并作为祭祀的祠堂,堂的两侧设有厢房,楼内平房四周为天井,楼内右侧天井有口水井,井水清澈而甘甜,至今仍为楼内住户的饮用水源。楼两侧还各有一座供楼内子弟读书求学的书斋,俨然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气派。
年久失修的泰安楼,难以掩抑其破败与苍凉的容颜。楼内鸡鸭成群,还可不时听到关在圈内的猪的哼叫。许多房间空空荡荡,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和密布的蜘蛛网,挂在木门上的锁五花八门,有古旧的铁锁,有大小不一的弹子锁,相同的是都已经锈迹斑斑。二楼前走廊上有一个燕巢,已经不再有燕子栖居,看那筑巢的泥土的颜色,似乎只有三五年的光景。在黝黑的楼板的反衬下,空寂的燕巢成了难得的亮点。三楼的前走廊上更是堆满了劈柴、稻草和农具,在后走廊厚厚的尘垢上,依稀地可以辨认出一些小动物的痕迹,通过周围的粪便,可以得知那些星星点点的脚印是老鼠的踪影。有一间房的门鼻上缠着铁丝,我碰了碰,铁丝居然也朽掉了,小心地推开门,猛地腾起一股烟尘。我捂着鼻子,定睛细看,只看见一团黑色的背影飞出了窗外,隐约是一只蝙蝠。
住在楼内的一位中年阿叔蓝进开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蓝姓三十一世裔孙,泰安楼由蓝姓十一世祖少元公建造,他在福建做烟叶生意发了大财。据说,这座楼是为他的宠妾修建的,他原来计划在楼的右侧,为其原配夫人再建一座同样的石楼,构成鸳鸯楼。遗憾的是,楼一侧的书斋还没修好,少元公就去世了,当时最小的儿子才出生不久,另一座楼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蓝进开还说,他们是从福建漳浦搬迁过来的畲族后代,几年前福建那边还有人过来拜认宗亲,并到这边的祖坟上祭祀。看来,这少元公倒真是个性情中人,能够无视当时礼教的束缚,不顾正偏之序,为宠妾送上这样的厚礼,而不是和当时士大夫中所流行的那样,把妾当成怡情悦性的一种工具,与花草无异,与牛马相类。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把63岁时在直隶静乐所买的妾,两年之后又转手卖给李又泉。两难的是,这雄伟的围楼的石缝里,又隐藏着那位失宠的正房的多少愁郁与愤懑?在少元公撒手人寰之后,妻妾之间又会上演什么样的戏剧?然而,岁月就是这样漠然,当年那些活生生的悲欢都已经模糊在蛛网和青苔之中,只有轻佻的风不时地吹拂起那个遥远年岁遗留在栏板和砖石间的积尘,让它们四处流散,旋转,坠落……
就建筑风格而言,泰安楼类似于以遗经楼为代表的永定方楼。大埔与永定相邻,交通便利,水陆两路畅通,民间交流频繁。当地不少居民都从闽西迁来,沿汀江下行进入大埔,李光耀的祖先就是从上杭迁居梅县,又辗转至大埔。大埔大东镇联丰村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花萼楼,是三环的客家圆楼,中间是鹅卵石铺成的晒谷场,还有一口古井,它从布局到细节都与永定的土圆楼同出一源。这些土木砂石构筑的城堡,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诉说着独特的文化记忆。当年那些南迁的客家先民披荆斩棘,就如艰难爬行的蜗牛,而这些移植过来的土楼,就像蜗牛背着的重壳一样。至于泰安楼为什么采用砖石结构,或许是少元公借鉴了漳浦一带的建筑元素,当地地处海滨,为了抵抗台风,民房多为低矮的石质建筑。随着散居于客家与福佬地区的畲民的汉化,畲族人群的民族认同也不断弱化。据我所知,客家地区族源为畲族的钟、雷、蓝姓居民,有不少自称为汉族后裔,其族谱也多有从北方南迁在石璧停留的记载,这显然有附会的痕迹。作为福佬文化主导地区的漳浦,畲族蓝鼎元家族在清初就以程朱理学传家,世代与汉族联姻,森严的家族礼教成了垂范一方的楷模。具体到泰安楼,只有其木质结构的楼廊还依稀地闪现着畲族风情,因为畲族先民的居住形式多为搭建在山中的简陋木棚或竹棚。看来,泰安楼正是畲族文化与客家、福佬文化多元互渗的历史见证。
一楼门厅的石板椅上坐着一位年过九十的老阿婆,她说自从嫁进这座楼,就再也不曾离开过,她脸上镂刻的皱纹,一如楼墙上细密的裂缝,一起见证泰安楼的风雨沧桑。在楼内碰见的多为妇女和小孩,难得遇到青壮年男子。问一个好奇地跟随我们的半大孩子,他说他父亲和叔叔都外出打工了,难得回家。楼内最为亮丽的风景也正是这些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在楼内追逐、游戏。在二楼一扇木门的后面,忽然伸出一张诡秘的小脸,把我吓了一跳,过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又大声地喊起了另一个孩子的名字。原来,他们是在捉迷藏啊,那个找不到同伴的小孩干脆跑到楼外玩耍了,这个躲藏的小孩因为受不了冷落,忍不住自我暴露了。他们烂漫的笑声使古老的泰安楼顿时变得年轻了许多,犹如自由的阳光照亮了灰暗的角落。一楼的一间房屋内,一户人家正在修筑新的灶台。客家地区对于“打灶头”非常看重,记得在我们老家,打了新灶的人家第一次生火,总要炒爆米花,散发给邻近的小孩,还要焚香鸣炮,祈祷生活过得红红火火。生息在楼内的一代代人们,就如楼外农地里的果树一样,在秋风中将成熟的种子和飘零的落叶,一块回馈给脚下的土地,一旦春天来临,又再一次爆出绿芽,新花怒放。
心上的城堡
齐安围在广东兴宁龙田的鸳塘村内,它以封闭的姿态背对世人,偏居于幽暗之中,显得隐秘、模糊而寂寞。我们驱车前往探寻,一路上反复地向路旁的村民和店家问路,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不知所云。在走了不少冤枉路之后,在几位老人热心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这座满脸沧桑的城堡式围楼。一位住在与齐安围紧挨着的小洋楼里的客家阿妹,非常纯朴地为我们做向导。还没进入围楼,一场雷阵雨就急切地为我们洗尘。围楼前零散地堆着一些煤炭,雨水冲击着地面,将黑色的煤点迸射在外墙上,但围楼的面孔经过岁月的点染,其灰色、漠然的表情再不会在乎这些雨点的挑逗,因为它那不修边幅的样子本来就是为迎击枪炮而准备的。
躲进严严实实的城堡,嘈杂的雨声顿时离得很远。沿着走廊穿行,发现除了墙壁倾颓之处,居然可以滴雨不淋地把里面转个遍。由于里面的建筑多为平房,远低于四周的围楼,内部的光线极为黯淡,显得沉闷而压抑。那位阿妹叫来了原来住在这座围楼中的阿伯,给我们介绍围楼的掌故。齐安围建成于清朝咸丰年间,由罗氏十二世祖汉光公的子孙集资而建。当时为了防备太平军祸乱,建筑突出了防卫功能。建筑外围是城楼,底层不设窗口,旨在抵御入侵者,但却留下了葫芦形的枪洞,下面架枪,上面作为瞭望孔,仓库中常年备有火药。围楼里建有完备的供水、储粮、排污系统,甚至还辟有菜地,在战乱时可以保障数月的日常供给。围楼的右角暗藏着一个小出口,平时用几根大铁棍锁住,一旦围楼被敌人攻破,这就是隐蔽的撤退通道。围楼的四角都有岗楼,左后角的更是有四、五层楼的高度,可兼作炮楼与瞭望塔。楼门用坚硬而厚实的原木制成,据说罗氏祖先原计划装铁门,但不了了之。大门框的用材是几尺厚的麻石,门框上还凿有方洞,可以安装栅栏。城楼二层修有四周相通的木廊,叫走马棚,可以调兵增援攻击压力最大的地方。土改复查后,政府把围楼分给众多住户,随着人口不断增多,各家把通道围堵起来,四通八达的走廊就被隔断了。围楼刚刚建好时,住户极少,随后逐渐增多,据说最多时住有上千人。而今,盖起了小洋楼的住户都搬了出去,剩下空荡荡的围楼,偶尔会碰上鸡狗在屋内溜达。大门后的一片废墟上长出了荒芜的杂草,还有几朵零星的野花被雨水击打得支离破碎。
走出齐安围,客家阿妹告诉我们旁边还有一座齐先围,建筑的历史比齐安围要悠久,是十二世祖汉光公的祖业。齐先围是一座两围的客家围龙屋,化胎两旁已经被拆旧建新,盖起了两座三层的小洋楼。一位领路的老者告诉我们,这座围龙屋最大的特色就是祖堂内的两副对联,其中简约地说明了建造齐先围的罗氏祖先的谱系。我追问他更加具体的情况,他也语焉不详。这两副对联为:
父创辛酉光祖德
母成甲子妥先灵
长乙酉次丁酉二酉趋庭愿效孔门家法
兄三子弟两子五子有志还期窦氏宗风
看对联的字面意思,好像是说建屋的祖先有两子五孙,更加详细的只有比照罗氏族谱才能得到正解。
为了拍摄齐安围的全景,客家阿妹领着我们爬到她家四层小洋楼的楼顶,还特意找来木梯,为我们打着雨伞。拍完照片后,她的母亲为我们泡了茶水,端出花生待客。闲谈之间,一位客家阿叔罗埔先告诉我们,鸳塘内部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语言,一个字读两个字的音,母音、子音各有24个。那位阿妹说“吃饭”的读音是“首席花散”,“发财”的读音是“发抵就达”,她说她就只知道这些。这种封闭性的语言和门户森严的齐安围,不正是异曲同工吗?我顿时来了兴趣。罗埔先大叔为我们提供了他自己搜集的文字资料,又主动地提出,要领我们去找一位还会讲鸳塘话的90岁老人。他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架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骑行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其间还走错了一条田间岔路。老人叫罗友先,又名罗硕民,1914年出生,他还特别强调其身份证上的出生时间是1913年。老人思维清晰,他说关于鸳塘话的起源,他听到的就有好几种,一说为罗姓祖先在京为官,因言惹祸,无奈出逃至江西九江,为避免重蹈覆辙,就自创了一种内部交流的语言;另一种说法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位前辈秀才所创;第三种说法是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位革命人士罗翼群,鸳塘当地的文人为了保护他,就发挥集体智慧,从江湖黑话中获得启发,创制了鸳塘话。据说罗翼群不仅借助鸳塘话的保密性来从事革命工作,传说他还在危急时帮孙中山脱离困境。鸳塘话的母音和子音分别组成了一首六言诗:
安手野行我快,短蓬孤就波遮。
问先宗身何处,桃花源李门家。
宽心东西磊私,亏跟砌粗他山。
漂身春秋淹呵,低声呼相讴歌。
前一首的二十四字为母音,后一首为子音,声调与古汉语一样,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为了方便我们记忆,老人形象地解释两则诗的文化蕴涵,并说他们当年学鸳塘话时,教授者也这样讲解:
安静地在野地里独行,我心快乐,
小小的草蓬孤零零地遮风挡雨。
要问祖先的根在何处?
桃花源里藏着那门人家。
宽心的只能是安顿自己的小家,
难过的是总要在他乡吃亏受累。
漂泊的岁月为什么淹留不止啊!
我低声哼唱,与梦中的她遥相呼应。
这些诠释性文字经过我的润色与锤炼。意味深长的是,这两首六言诗的字面含义,似乎以隐喻的形式表现着客家人千年流浪的漂泊体验。在我看来,鸳塘话正是近千年来缺乏安全感的客家人,在反复遭受外界排斥的过程中,以倔强的姿态背对世人的精神形式。这是作茧自缚的独立王国,是用语言的砖石修筑在心上的城堡。
罗埔先大叔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鸳塘也爆发了两派斗争,“旗派”和“联派”势不两立,常常派军宣队和社教队驻村工作,他们开大会,底下的群众就用鸳塘话开小会。那些革命干将一气之下,将“鸳塘话”定性为“反革命”语言,被禁止使用,相关的文字材料也被焚烧。随着那些会讲鸳塘话的老人们相继过世,中年人还知道一些皮毛,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鸳塘话注定无法抗拒行将消逝的命运。
从兴宁回到梅州,听当地的朋友说,梅城也有三种与鸳塘话类似的语言,那就是:上市(司)话、下市(司)话和江湖话。至于江湖话,顾名思义,是当地黑帮的行话。以前,因为江南一带还是荒无人烟,梅城城区分为上市和下市两部分。据说,很久以前,住在下市的人和上市的人相互不服气,于是,上市的人发明了上市话,下市人就发明了下市话。这样,各自的秘密就不容易被对方探听了。现在,上市话和下市话都已失传,只有个别高寿的老人还会讲几句。相对而言,掌握下市话的人还多一些,但原来下市有肖屋、丘屋、张屋、黄屋等,现在都已拆迁,因此会讲下市话的人住得很分散。通过辗转打听,了解到当地客家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溜水”一词就是下市话词汇,意思是不辞而别,“溪小”则是好不好的意思。“下市话”的发音采用客家话的切音法,就是以两个音切成一个字的方法。在1956年有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汉语发音也都是采用切音法。“下市话”只发出切音前的两个音,不讲出切音后的一个字,例如“食”读“索侧”,“饭”读“方建”,“茶”读“昌卡”,“烟”读“茶仙”,“酒”读“将九”,连起来读就是“索侧方建”(“食饭”),“索侧昌卡”(“食茶”),依此类推。关于“下市话”的发明者,民间有两种传说:一说发明者是下市人黄遵宪,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出任清朝驻日本参赞,鉴于大使馆内的机密老被日本情报机关窃听,黄遵宪发明了“下市话”,并在大使馆人员中推广,日本情报人员一直无法破译。此说可谓破绽百出,尽管首届驻日公使是大埔人何如璋,但使馆工作人员不可能都是客家人。二说“下市话”的发明者是下市人的上祖,黄遵宪在出任驻日本参赞时,利用“下市话”保住了大使馆内的机密。民间总喜欢将自己的身世、身旁的事物和前代名人尤其是乡贤扯上边,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关于“下市话”来历的传说同样不能免俗。
和齐安围的命运一样,不只是土石砖块修筑的城堡,就是这些语言的城堡,同样无法抵挡时间的洪流,在岁月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就像许多古建筑,即使留下模糊的外形,但在反复的修复和商业的开发之中,变得面目全非,将前人留下的草蛇灰线一样的生活遗迹,逐渐地磨蚀殆尽。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客家人的建筑和语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调封闭性和安全性,成为文明的活化石?不管如何牢固的城堡,终有一天会倒塌;不管如何保密的语言,也终有一天会被破译,或者莫名其妙地失传。但是,如果一种人群的心中总是矗立着无形的城堡,那么,在一种城堡和一种语言消失之后,他们必定会建造另一种形式的城堡和语言。我希望,随着这些城堡和语言退出历史的地平线,伴随了客家人上千年的不安也能随风飘散。只是,我心里也有一种模糊的担忧:如果这种不安消失了,客家人的文化认同是否就瓦解了?客家人是否也就被周围的人群淹没了?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