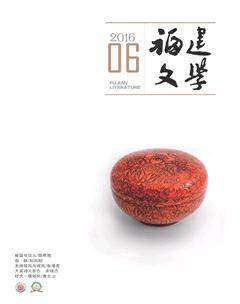脆弱之书
黄加芳
每个人都拥有最私人的隐秘体验,这体验是除开喜怒哀乐种种广义的情绪以外的感受,它是幽微的,不为外人觉察,同时也不足为外人道,有时它没来由地就来了,更多的时候,它乘着记忆的翅膀翩然而至,然后它作用到人的感官,使一个看上去无比平静的人心潮澎湃,感动不已——这时的感动无疑是最私人的感动,因而也是最真实的感动,最不自欺欺人的感动。一阵气息、一幕场景、一缕音乐,甚至仅是惊鸿一瞥的一个瞬间,都有可能让过去的时光,不期而至地被召回。当然,这时回来的记忆已经不复是它本来的面目了,记忆的美化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它是逝去的往事的回光返照。只因它遥远而美丽,感动才乘虚而入,填补了这中间漫长的距离。伯格森在他的名著《物质与记忆》中描述了这种记忆的伟力,他赋予了它一个形象的称呼:非意愿记忆。接着,是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这两个乖戾而诚实的人充分地利用了它,使这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的记忆真正像流星那样亮闪闪地划过精神的夜空。
在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之后,还有谁这样做呢?——巴乌斯托夫斯基。只是谁也不会将这三个名字放在同一句话中来提及,因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看起来实在是与前二者相去太远了。
事实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也是书写感动的圣手,只不过他的途径有些特别:他不是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被感动得有多深有多广,而是索性去细致描写那些给予了他原初感动的事物,涓滴不漏地描写,然后将这些事物放任自流,让它们自己说话,结果是凡阅读者都被深深感动了,心悦诚服,但秘而不宣。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巴乌斯托夫斯基大胆而细腻地写出了自我感动的根源,平常人写不出,只能领受。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写不出,而是羞于写。因为大凡纯粹的感动必得是私密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动的诱因总是“令人心碎”的——非如此不足以使人久久信服。这也就决定了这种写作是温柔的写作、阴性的写作、渗透着女性气质的写作。或者换句话说,它不是崇拜强力的写作,它是向弱的写作。这种写作,在多数人看来,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想,这或者就是《金蔷薇》在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黄色书籍”的原因吧。
向弱的写作,或曰脆弱的哲学,大约正是贯穿《金蔷薇》始终的题中之意。很少有一本书这样真切、艺术地撷取生活中那些柔弱但却至善至美的片段;同样,也很少有一本书这样真挚、诚恳地袒露人灵魂中那些脆弱但纤尘不染的角落了。说到底,向弱是一种美德,是自知苦弱但却始终隐忍,是承受,是热爱,是温情抚摸,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应该说,《金蔷薇》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与爱之书,这美与爱绝不庸俗,但它同时又切合每一颗凡俗的心灵。事实上,《金蔷薇》是通过美与爱来教导:生是脆弱的,恰如帕斯卡尔说过的,是芦苇,纵使他能思想,但终究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只得默默承受。
默默承受而不打算反抗的灵魂,是脆弱的灵魂;也只有自认脆弱的灵魂,才有望从根本上读取美与爱的真谛:因其脆弱,才爱得深,才绝对美。
在《金蔷薇》中,巴乌斯托夫斯基历数美与爱的具体征象,令人心碎的文字遍布全书:晚秋星光璀璨的夜空、拂晓时分如处子一般纯洁的霞光、洁净得好似泉水的空气、苍白的月亮、薄冰下的气泡、树林里忧郁的岑寂……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细节,是使人心由坚硬化为柔软的意象,面对这些,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本人所言:“……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人只好脆弱,一任脆弱,也只有脆弱才能够承载它的温厚和熨帖。必须承认,大自然中实在不乏这一些刺激人们恻隐之心的片段,只是要看人是否有幸遭逢它。一旦遭逢,人们有理由同情一场失控的哭泣,因为彼时泪水,万般珍贵。《金蔷薇》中有一篇《心灵的印痕》,其中写到风烛残年的孤老婆子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深秋果园里的哭泣:
“这时已暮色四合。果园里到处枯叶飘零。落叶在我们脚下颤动,发出很响的沙沙声,妨碍着我们走路。发青的晚霞中,闪烁着几颗寒星。在远处的树林上空,挂着一钩眉月。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在一棵被风吹得凋零不堪的菩提树旁停下来,用一只手扶着这棵树,失声痛哭起来。”
这是伤逝的泪水,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这样在遥远的俄罗斯大地上、在一位平凡孤独的老年妇女身上得到了印证。也正是面对暮秋的萧飒和凄美,人心才会不能自持,遥想身世,悲从中来。这时,就是再苍老坚硬的心灵也会禁不住变得柔软和易碎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际遇容易使人想起晚明张宗子《陶庵梦忆》中那位聪慧多愁的女戏子朱楚生,后者也是在绝美的自然面前深深地沉默了,并且黯然神伤:“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就这样,美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年龄,它正在两个素昧平生、不同世纪、不同命运的女性身上发生作用,人们不知道她们的生命中曾经历过多么刻骨铭心的故事,也不了解她们沉重的肉身曾承受过多少岁月的盘剥,只知道此刻的她们脆弱不堪,她们哭着,像无辜的白羊。
而《金蔷薇》中的爱,正如《金蔷薇》开篇的形容,是“珍贵的尘土”,它是凡夫俗子之爱,是普通生灵之爱,它甚至可以是引车卖浆者流之爱——《珍贵的尘土》中的主人公夏米不就是再卑微不过的清扫工吗?——但它却恰恰是最纯洁、最无私、最善良、最刚烈、最伟大的人类之爱。为了这高蹈的爱,人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而默默祝福着,任凭时光怎样难捱最终又怎样无情地夺走他的生命;为了这纯粹的爱,人甚至可以下决心抛掷自己年轻的生命而成就它的永恒:在《利夫内的雷雨》中,神情凄楚的姑娘安菲莎爱上了瘦弱的科利亚,这是同情之爱,是守护脆弱之爱,它一开始就与强力分道扬镳,而它对牺牲的崇尚又是那样坚决和令人惋惜。索洛维约夫说:“精神之为精神就在于它全然不具有任何强力,它原本天生无力。”看来,真正的爱意也是如此。
这样也就注定了真正的爱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因其脆弱,它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尽管保罗·蒂里希声称:“生命是现实性中的存在,而爱是生命的推动力量”,但这爱并不能施力于枯索的现世几何,只能在暗里以它特有的脆弱的温柔使想象中的人生变得丰盈起来。
读过《金蔷薇》的人,大概很少不被其中的名篇《夜行的驿车》打动。在这里,巴乌斯托夫斯基用小说之笔描绘了童话家安徒生的爱。固然,文章描写之细腻,情感之真挚,都使得它在作家的创作中堪称铭心绝品;但最为宝贵的是,它书写了人之为人一种真真切切的无奈,这种无奈是那样隐蔽,因而也只有敏感如安徒生者才体验得那样深刻:“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张闪闪发光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在现实的爱面前,昔日热情勇敢的童话诗人变得脆弱了,他的恐惧和追求纯粹的本质在现实面前探头探脑,而他求索真爱的勇气却被吓唬得七零八落,正如埃列娜·葛维乔里揭示的那样:“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是害怕童话的。您缺少爱的力量和勇气,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爱。”安徒生落荒而逃,很快地与一段可能相当美好的爱情失之交臂,以使它的美好得以在记忆中留存,并且保持原初的新鲜。
当文章写道“维罗纳全城响彻晚祷的钟声”,人们心里长久蛰伏的感动被唤醒了,所有读过这个篇章的人都会对悲哀和残缺的人生况味心领神会,但都不愿声张,尘世的喧嚣被驱散了,更加巨大的慈祥的安抚将人们激动的心魂笼罩,那是一种宿命的声音,同时也是圣洁和不置可否的声音,所有“终究意难平”的歉然在这大声音中都将归于静寂,因为一个恒久的记忆回来了,那是埋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对于前尘往事的美好记忆,它看似微弱实则强大,通过时光的炼金术作用到现下,人被自己的感动征服。
而脆弱之心永存。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