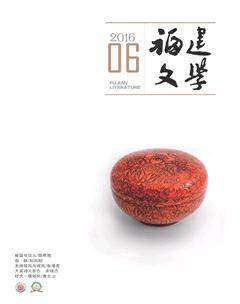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家鸿
说起丰子恺先生,关于他的身份,人们所能想到的是“漫画家”、“美术教育家”与“散文家”。这几个身份是对丰子恺先生文学艺术成就的公正评价,亦可以说它们是丰子恺先生的历史身份。除此之外,丰子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身份,那就是教师。我亦忝列教师队伍之中,品读此书,斗胆地说,我似在寻找一种精神标杆。虽不自量力,然心向往之。
这本《教师日记》的写作时间起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止于次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前后时间的跨度恰好八个月整,是丰子恺先生于抗战期间流寓广西桂林担任教职时的日常详细记录。我平素喜欢读传记、回忆录、书信集等散发出鲜活气息的书籍,其中最吸引我的当属日记。日记,是最接近本来面目的第一手材料,琐碎、生动、新鲜。品读此书,如亲见历史,可以触摸到它真实可感的温度。
此书名为“教师日记”,“教师”二字旨在于强调作者的职业或身份,然而日记中所记之人所论之事并不局限于学校之内课堂之上,而是拓展涉及广阔无边的人与事,以及硝烟弥漫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在好奇心的推动下,我一个字一个字,一行行一行行地仔细爬梳、揣摩、感悟着。
在1938年12月9日的日记中,丰子恺先生慷慨激昂地抒发着自己抗战必胜的信念,“今日吾民族正当生死存亡之关头,多些麻烦,诚不算苦。吾等要自励不屈不挠之精神,以为国民表式。此亦一种教育,此亦一种抗战。”在先生眼中,教育即为抗战,而且是最为特殊最为持久的抗战,对于抗战的全面胜利,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身肩如此重担的教师,定然是个勇敢的战士。
同是1938年的早些时候,先生即写过“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真是掷地有声,如雷贯耳,振奋人心。写下这一行字的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更可见其实为见识与信念兼具的可贵言论。在日记里,可见先生的痛心与怒气,亦可见先生的牢骚与担忧,但绝对见不到哪怕一点点的颓唐与消沉。即使面对一个陌生小女孩的新坟,先生亦可树起“不久当有凯歌迎尔归葬于西湖之旁也”之信念。这个战士以思想为武器,在教育的战线上,执笔胜过刀枪,在学生们的心灵里种下一株株参天大树,以抵挡乱世的狂风暴雨。
我很珍视1939年1月19日这一天的日记,这一天里,丰子恺先生慷慨激昂地写道:“我等侧身文化教育界者,正宜及时努力,驱除过去一切弊端,必使一切事业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乎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作为一个不上前线的战士,先生没有子弹,先生只有一颗努力实现“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之理想境界的心。一颗火热的心,在边陲之地悄悄地燃烧着。幸而有《教师日记》留传后世,否则抗战史中则埋没了一道鲜明的印记,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先生眼里,“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乃凡事成功之关键。这关键之道,看似宏伟,看似壮观,实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却显得格外繁琐、细碎,甚至在许多人眼中,可能显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我在这本书里竭力寻找的光芒,可以划破时代暗夜的光芒。
回忆起初来乍到时,先生写道:“我被邀请到桂林时,会见校长,即承告‘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之旨。此旨实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我甚钦佩,同时又甚胆怯——怕自己不胜教师之任。”“胆怯”二字恰恰体现了先生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真实心态,担心之余,还有憧憬,勉力为之可也。于是,作为读者的我才见到那个桂师的美术教员兼国文教员,那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丰子恺。
11月1日,先生自言自语道:“因为我未谙他们的性格,尚不能决定教学的方针。”这是懂得教育又忧心忡忡的老师。11月8日,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时,“标点不准乱用,字不许潦草。潦草者不给改。”这是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老师。11月26日,“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这是对教育之美好未来有巨大期盼的老师。12月1日,“昨天,昨天下午,你们那组人正在对着所画的无头婴儿哄堂大笑的时候,七十里外的桂林城中,正在实演这种惨剧,也许比我所画的更惨。”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老师。相对于“授业”“解惑”来讲,“传道”应是教师的第一天职,也是教育的第一要义。所传之道,并非是一味形而上学之道,而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热爱生命又是其中最为恳切与重要的。热爱生命,热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包括漠不相关的陌生人的。是的,在成长阶段里,促成学生形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养成悲悯之心,岂不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这些貌似朴实简单的话语,无不“本乎天理”,无不“合乎人情”,而在彰显着一个艺术家令人崇敬的教育思想。逢着战乱时代,先生不因学生基础水平的粗浅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亦不因校舍的简陋与环境的恶劣而有丝毫的随意应付,如此作为怎能不让如今的教育者汗颜?将心比心之后,我们能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思考与启发实在太多。
身为教育者,身为阅读者,身为一个且呼吸且行走的普通人,多年以后,我仍会记着丰子恺先生那颗可贵的反省向学之心。1938年12月2日,当先生以“桂林城里受难,你们乡下就很好”的言语来安慰目不识丁的邻人时,邻人摇摇头回答:“要大家好才好!”这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引起了先生的肃然起敬。先生写道:“我目送他。此是仁者之言,我用尊敬的眼光送他回家。”这于日常琐事中切实而郑重地向下看的艺术家,世间能有几个?不仅如此,在寻常的买卖中,先生亦会发现商人的“用心诚善”。
由此可见,先生在抗战岁月里,不仅高举着理想的旗帜与必胜的信念,更睁开着一双艺术的眼睛,发现并记录着普通百姓身上德行的美。这是一种志存高远的低头,埋首于平凡的人群里,撷取更多的地气,久而久之,正可以提升自己的艺术境界。《圣经》有言:“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在丰子恺先生拥有辉煌成就的一生里,这八个月的教书生涯并不惊天动地,并不精彩纷呈,甚至显得平凡普通。然而,我却觉得这段经历着实珍贵。真正的艺术家投身教育,总是毅然决然,高擎理想主义的旗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战争的出现固然是国家与百姓的大不幸,然而此不幸中亦有幸运。幸运之处在于大师们因环境的艰难、谋生的不易等诸多因素的存在,要么身不由己要么心甘情愿地身居中学教职。大师们进入中学,不仅是所在学校学生之福,亦为国家民族之福。自从民国以来的文化传播中,他们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走向觉醒,走向抗争,走向追赶理想的道路。我犹记得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亦记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大师们在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师们在中学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辛勤耕耘,最让我感动的并非高深的学问,亦非高明的思想,而是他们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以及倾注于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深情厚谊。
如果教育办不好,国家就不会有美好可期之未来。战争越是疯狂,教育越是需要坚持,越是需要这些投身教育的知识分子兢兢业业地贡献光和热。即使亡国了,教育也可以为国家保留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在这个功利化的社会里,阅读《教师日记》是一种别样的返璞归真,是品味一道思想盛宴,这其中既有关于教育的真知灼见,更有在艰难困境中迎难而上的卓绝勇毅,以及心忧天下的大师风范。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丰子恺先生的恩师,他们之间的往事所在不少,然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与《护生画集》有关的点点滴滴。晚年丰子恺在政治动乱的岁月里,不顾老迈之躯,依然信守对恩师的承诺,完成了最后的一幅幅作品,虽然笔力不及当年,笔墨里汩汩流出的风采却始终依然,一只鹅的“听课诵”,一只鳖的孤独,一条狗的失踪,一个个日常的画面,在丰子恺眼中,都是生命伟力的自然展示与完美呈现,都可以引起内心的深刻感触。这是作为学生的丰子恺,他的画笔流布人间的是对世间一切生命的敬意,以及深蕴其中的众生平等的博爱之心。不管是身为教师,还是扮演学生的角色,丰子恺始终是丰子恺,没有丝毫的褪色。大师与否,并不仅仅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拥有多大的影响力,更在于在低头俯视人间万物的时候,拥有一颗与生俱来的良善之心。这颗良善之心,时时刻刻地促成了他的作品与普罗大众的无缝对接,作品中的一字一句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愿意谛听的平凡人等。
在这个“大师”满天飞的时代里,真正的大师是严重稀缺的。呜呼,媒体话语如此强势,但凡在某个领域里出类拔萃、稍有成果的人,总是身不由己地被冠上“大师”的名号。面对此情此境,清醒者,不以为然;浑噩者满足者,享受之余还飘飘然。于是乎,久而久之,大师的内涵与外延也就渐渐显出穷山恶水的面貌了。
回顾往昔,大师的声音振聋发聩;环顾而今,大师的背影渐行渐远。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对严子陵的动人赞许:“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发自肺腑的赞许用在丰子恺先生身上,应当也是可以的吧!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