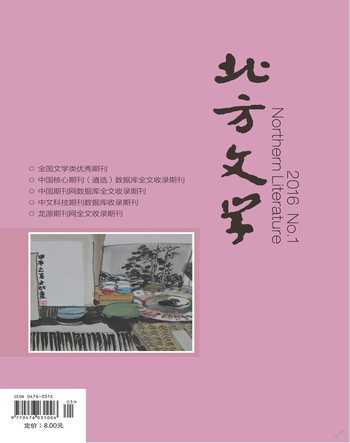云南插队经历对王小波创作心理的影响
杨开浪
摘 要:王小波曾被一些论者誉为“文坛外高手”, 引起了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关注。他曾经在德宏州陇川县插队数年之久,这段独特的经历在王小波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冲动。王小波的作品一再反复穿插大量的有关德宏插队时期的故事、经历,来反思历史的错位和时代的荒谬,成为其文学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构成。研究王小波的德宏插队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探讨王小波的文艺心理和深入分析其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关键词:王小波;德宏;插队经历;文化心理
一
王小波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曾被一些论者誉为“文坛外高手”,他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部曲,这些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技巧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自觉的拉开了距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和他生前几乎籍籍无名而异常落寞相比,1997去世之后,王小波的小说引起了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关注,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往往集中于其成名作《黄金时代》及以后的作品,从小说的叙事学分析,至王小波小说艺术的中西方资源均已有研究者涉足,随着不断阐释和研究使学术界呈“众声喧哗”之势。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王小波和地处边疆的云南省德宏州有着较深的渊源。1968-1970年,王小波曾经在德宏州陇川县插队数年之久。这段独特的经历在王小波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德宏的插队生涯和种种经历,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冲动。另一方面,王小波在德宏陇川插队的这段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素材。在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中,他一再反复穿插大量的有关德宏插队时期的故事、经历,来反思历史的错位和时代的荒谬,成为其文学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构成。研究王小波的德宏插队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探讨王小波的文艺心理和深入分析其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二
1968年,王小波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云南德宏插队时,年仅16岁。之前王小波曾看过一本当时风靡全国的书《美丽的西双版纳》,被版纳热带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少数民族吸引,毅然放弃了较为舒适的干校锻炼自愿远赴云南边疆,但阴差阳错到了和西双版纳颇为相似的德宏,从此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代的王小波像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受“文化大革命”时代宣传的感召,希望在艰苦的边疆地区奉献自己的青春,战天斗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然而在云南插队三年彻底颠覆了王小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崇高火热的理想和触目惊心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小波们一直信奉的人生理想和美好憧憬被残酷的现实世界击得粉碎。可以说,正是在德宏陇川插队的这段经历,在艰苦的生存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严酷拷问中,让王小波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有了最清醒和直观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中廉价的政治宣传和愚民政策有了切肤之痛,对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产生了新的质疑和思考。也正是是在德宏插队生涯中的种种经历,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热情,通过阅读和写作中重新构筑自身的生存方式,从而超越“文革”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
整个插队生涯给王小波留下的最恐怖的记忆恐怕就是无休止且异常繁重的民间劳作。当时王小波和其他21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弄巴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劳动由管理组织分配,王小波曾从事过割稻、扛包、挖沟、放牛等各种农事活动,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王小波而言构成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以致他有因病情发作而入医院治疗半个月的记录。王小波后来在杂文中愤怒地回忆说:“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人力能够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不仅王小波如此,这大概是所有插队知青的共同感受。知青们一边要日复一日承受强大的劳动强度,但是同时却缺衣少食,忍受着极端的贫困。严峻的生活体验使王小波真正走出了被长期灌输的浪漫化的革命想象,在不堪承受的苦难面前开始对生活的真谛展开痛苦的思索。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回顾自己的插队经历时曾说:“没有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我们偏爱从自己皮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对王小波来说亦是如此。显然,在插队过程中现实呈现的荒谬和连绵不绝的苦难,比任何廉价的政治宣传和狂热的鼓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王小波日后在小说和杂文中一再追溯德宏插队生涯、彻底反思文革历史的现实源泉。
比之物质贫乏,更令知青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禁锢和思想的贫乏。众所周知,文革期间是中国思想控制最为严密的时期,全国上下仅剩八个“样板戏”和浩然《金光大道》等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少量作品,对于“嗜书如命”的王小波等下乡知青而言,被剥夺阅读和思考的权力,让插队生涯简直像黑夜一样漫长。他后来回顾在云南插队生涯时曾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就不会被人看没了”。又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述著可以使我们免于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述著已经被隔绝了”。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王小波当时的痛苦和焦虑之情。思想的禁锢,精神的苍白成为王小波在劳动之余最不堪承受的重负。这种痛苦的体验一直缠绕着王小波,使得他在许多年之后仍不能释怀,在他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救世情结与白日梦》、《椰子树与平等》等文章中一次次“复活”,成为王小波反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的最佳参照物。
三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然,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正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缺乏中,王小波开始意识到个人在荒谬时代里的糟糕处境,开始从战天斗地、解放全人类等时代灌输的政治口号中逃离。知青的真诚被利用,勤劳变成了笑话,想改天换地、拯救世界却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王小波后来曾说:“刚当知青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话说,是“生活中到处充满了黑色幽默”。如果说对道德理想的执著与坚守曾是王小波的全部内心构成的话,那么插队之后回到北京的王小波至少在精神上已脱胎换骨,被全面的怀疑和排拒所取代。回顾在云南三年的插队经历,王小波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承志等作家不同,他们的作品也写到了知青插队时遭遇的种种苦难,但更多的是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情怀,蒙古草原、东北雪地等知青曾经插队的地方也成为可以不断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园。而在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和杂文中,他想表现的不是崇高与悲壮,激情与自豪,而是一种自始至终的荒谬与苦难,一种油然而生的被人任意摆弄和凌辱的“行货感”。正是插队生活的严酷拷问,使王小波对落后、愚昧和专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其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从容游历于主流意识的形态之外。
面对少年时期坚信不移的乌托邦理想的湮灭,王小波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失落,一种信念从根本上动摇产生的沉重的虚无感。而此时“文革“尚未结束,王小波深感厌恶和鄙夷的那一套空洞的思想理论和价值原则仍然大行其道,文攻武卫、阶级斗争、批判揭发如火如荼,这一切给作为“觉醒者”的王小波带来强烈的精神痛苦,同时不可避免产生了深深的焦灼之情。在其杂文中王小波写道:“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的黑下去,心里落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在王小波早期的生命意识里,一方面是日复一日的生产劳作带来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消解,另一方面却是感悟到时间的流逝,人生苦短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悖论中,王小波开始形成逆于常规的思维,主动选择了对主流生活状态的抗拒,在沉默中冷静的审视社会和人生,最终在各种因素的综合驱动下开始转向文学领域,在阅读和写作中重新构筑自身的生存方式。虽然王小波的小说处女作《地久天长》发表于1980年,但据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道:“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他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的作品我们已经无从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小波的文学活动始于云南插队时期,并成为王小波终身追求的事业。
四
法朗士曾说:“一切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分析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动机,我们应注意《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这篇小说对我们分析王小波早期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其创作动机提供了一把绝佳的“钥匙”。在这部具有浓郁的自我写真性质的小说里王小波写道:“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我开始去思索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些死前的游戏。”,“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永久存在”。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引述小说中的文字,除了王小波在小说中传达的“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令人动容以外,还在于他的思考远远超越了风雨如晦黑白颠倒的文革时代,甚至带有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最终选择了“以梦为马”的自由写作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因乃是把文学作为抗击世俗、战胜虚无的重要手段。结合在云南插队时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荒谬绝伦的现实,未来的人生到底应该何去何从?通过写作这种方式,他构筑了一个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超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可以在大海中自由遨游并建立高度发达的海底文明(《绿毛水怪》),凶残丑恶的公社书记变为了一头驴(《这是真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自由的交换性别(《变形记》)……艾布拉姆斯在总结诗歌的“表达说”理论时曾说:“艺术作品实质上是把内在的变为外在的,是在感情冲动之下发生的一种创造过程的结果。它同时体现诗人的知觉、思想和感情。产生诗歌的原因,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主要取决于模仿的人的行动和品质,即形成性原因,也不像新古典批评派所说的那样,取决于它想在听众之中引起的效果,即终结性原因,而是取决于人要求表达感情欲望的冲动,或者说是创造力想象力作用下的一种驱迫感,这种想象力像造物主那样自有它内在的动力”。这种“驱迫感”在王小波身上的体现除了前面论及的焦灼情绪的压迫,还由于王小波对自己的文学才能的一种期许与渴望。“写诗”是一个不堪的重负,但留给我的唯一的选择却是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在这里既显示了王小波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又显示了其生活道路上的奋发姿态,写作因而具有了事業和生活的双重意义。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回忆王小波时曾深情地说道:“16岁时他在云南,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在一面镜子上写啊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个画面中充满了动人的情致和意味深长的象征意味。在这里,写作与表达成为个人最隐私的事情,个性的自由也达到了最充盈的程度。这显然是王小波心目中最理想的写作状态,也使它实现自身生命意志的最佳途径。对王小波而言,对写作灵感的苦苦寻觅和追求实质上已外化为一种生活态度的获取,即如何战胜自己和虚无之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心的舒展和自我价值的升华。
确实,在王小波离开云南不久后创作了《绿毛水怪》、《战福》、《地久天长》等早期小说,经过《唐人故事》的探索再至“时代三部曲”,王小波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而当我们回顾王小波的文学道路时,他在云南德宏插队的知青生涯显得如此重要,尽管它曾经给王小波带来沉重的痛苦,但“诗人不幸诗家幸”,正是在对时代和现实的的逆反中使王小波最终选择了文学之路,也使这段独特的经历成为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和杂文取之不竭的源泉。
注释:
王小波:《人性的逆转》《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5页
李银河:《思想者说——王小波李银河双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239页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3页
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43页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4页
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123页
艾布拉姆斯:《批评理论的方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32页
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191页
参考文献:
[1]韦济木. 20世纪末的浪漫骑士——王小波杂文精神论[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 2004,(06) .
[2]张伯存.躯体 刑罚 权力 性——王小波小说一解[J].北京文学,1998, (9).
[3]许纪霖等.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4]王晓华. 王小波杂文的思想渊源,意义与局限——王小波杂文论[J].文艺理论研究 , 2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