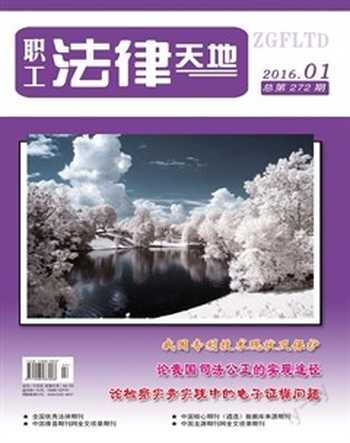夫妻间生育协议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摘 要:生育权纠纷与生育协议的效力问题目前仍有争议,各地法院对生育协议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局限在法律之债的范畴内探讨生育协议的效力,不论有效说还是无效说都将陷入于法无据或执行窘境。生育协议不能依据《合同法》产生合同之债,也不能依《婚姻法》产生与有名身份协议相同的法律之债,生育协议所生之债只能是自然之债。基于家事领域司法谦抑性的考虑,法院应当将因生育协议引发的纠纷排除在受案和审理范围之外。
关键词:生育权;生育协议;自然之债;无名身份协议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协议的方式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由此也给审判实践创造了越来越多的难题。所谓夫妻生育协议,是指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生育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后果进行的约定,涉及人身和情感方面两方面因素。关于生育协议的效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司法实务界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各地法院同案不同判现象显著。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生育问题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务之中,通常包括生育侵权损害赔偿和生育协议纠纷。生育协议包括夫妻间生育协议与非夫妻间生育协议、政府与公民签订的计划生育协议,在此我们只讨论第一种。实务中存在以下几种类型:①仅基于生育协议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生育协议效力或承担违约责任。②在离婚诉讼中附带提起生育协议诉讼。③生育协议履行后又反悔,请求返还。审判实践中,常用的有三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以于法无据,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诉讼请求。一种是以协议无效为由驳回诉讼请求。还有一种是无论当事人是否请求,均判令将已给付部分返还。要解决夫妻生育协议之债的问题,首先要对生育权进行定性。
二、生育权的基本内涵
生育协议是在当事人行使生育权的过程中签订的,因此讨论生育协议,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生育权。我国法律对生育权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与生育权的有关的争议有许多,与生育协议有关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均可单独享有的固有权利
生育权具有双向性。生育权的客体是“夫妻共同的生育行为”,与附着在其上的权利已经无法分割,所以法律只能用共有制度来处理夫妻间生育关系[1]。在这种权利形态中,权利主体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两人,客体是共同生育行为,内容是共有人通过共同生育行为实现自身的生育利益。所以共有是夫妻联合行使生育权的形式,但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所有形式。
生育权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夫妻双方除共同享有生育权以外,也可在法律范围内独立行使生育权。妇女的生育权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得到确定,随后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生育权主体扩大到全体公民。由此,男性的生育权也得到了肯定[2]。故将生育权定义为“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3]”能够更加完整地解释其内涵。
(二)生育权是一项可支配的私法权利
明确生育权的性质对确定生育协议的效力意义重大。如果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公民个人的私法权利,则个人有权通过订立协议的形式对其进行处分。如果生育权只是一项基本人权或仅得向国家主张的权利,那么就不具备私法上的可处分性,一方不具有针对相对方的诉权。就其性质,存在两种学说:
“私法权利说”又可具体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之争。通说认为生育权的本质是生育活动决定权,体现的是人可以自由决定生育与否的意志自由。而这种决定完全独立于夫妻身份关系。婚姻关系的确立对公民个人的生育权只是加以了一定的限制,但生育权的人格属性并未因婚姻而改变。生育权只是在夫妻关系领域具有了一定身份法上的意义。所以生育权是一项人格权而非身份权。
“公法权利说”又可分为“人权说”和“对抗国家权利说”,以朱晓喆、徐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一项国际基本人权[4]。以陈信勇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一项与用以对抗计划生育的公法权利[5],不得向他人主张。认为规定生育权的法律均属于公法,且从条文上来看也是与计划生育义务相对而言,故不可将其视为私法权利。
笔者认为,生育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私法上的人格权。《妇女权益保障法》条文规定的妇女“有不生育的自由”,足以用来对抗任何人对其提出的强令生育的要求。《人口與计划生育法》中“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的规定,也足以认定夫妻双方均享有独立的生育权。尽管民事法律对生育权只字未提,但这是立法的滞后性导致的,不能作为生育权不是私法权利的理由。由于生育权是一项私法权利,故可以通过当事人自己支配。由此签订的生育协议并非无效,而是一种有效的身份协议。
三、生育协议的定位及其效力
有关生育协议的司法案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生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一)生育协议的内容
所谓夫妻生育协议,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生育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后果进行的约定。内容包括:(一)双方权利义务,包括下面几种情况:1.不当出生或不当怀孕。2.擅自终止妊娠。3.禁止男方不让女方怀孕。其中第一、二种情形都是丈夫为维护其生育权而订立的,第三种情形是女方为维护自己生育权而订立的。实践中丈夫诉妻子侵犯其生育权的案例比例最高,诉讼理由通常是妻子擅自终止妊娠的情形。(二)违约后果:违反约定一方要履行生育行为或者进行金钱损害赔偿。这是以双方存在的夫妻身份关系为前提而存在的权利救济,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产生的不直接涉及财产内容的权利义务。实践中请求履行和请求赔偿的案例都有很多。
(二)生育协议的定位
1.不能产生与有名身份协议相同的法律之债
虽然生育协议规定了违约救济,会涉及财产利益。但要对一个法律行为定性,应当更关注法律行为本身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应从结果出发,将其定义为财产合同。夫妻生育协议属于有亲属身份的当事人订立的基于身份关系形成的财产关系的协议,与身份协议的定义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将其认定为身份协议是有充分理由的。
身份协议依照法律法规有无规定,可分为法有规定的身份协议和法无规定的身份协议。部分身份协议在《婚姻法》、《收养法》等实体法中已作出了规定,我们称之为有名身份合同。这种类型的协议直接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即可。还有一种身份协议依据的仅是宣示性的法条,不具有司法适用性,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协议的法律效力,我们称之为无名身份合同。
生育协议在《合同法》、《婚姻法》均未作出规定,属无名身份协议,其内容和效力没有任何条款予以规范。根据《合同法》第二条,《合同法》调整的是财产性合同,将人身合同排除在外。故生育协议作为身份合同不可类推适用相似的有名身份合同的规定。《民法通则》同时调整人身合同和财产合同,但《民法通则》没有类似《合同法》124条类推适用的规定,故也无法进行类推。
2.生育协议不能依据《合同法》产生合同之债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其第一款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合同,第二款却又单独把身份合同排除在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生育协议是身份协议的一种特殊类型,故不属于《合同法》所规范的合同。且《合同法》是直接反映、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而与身份有关的协议缺乏直接的经济内容,与市场经济活动存在本质的区别,其自身运作的特殊性注定了对其法律调整的特殊性。
3.生育协议只能是自然债务
自然之债源于罗马法,是指债权人不能依诉强制履行,但是债务人一旦为给付,则构成有效清偿,债务人不得基于非债清偿而请求返还[6]。自然之债不同于民事债,也不同于非债。我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自然之债的概念,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属于自然之债的情形。
生育协议虽然是无名身份协议,但不等于毫无法律效力,应将其认定为自然之债。生育协议作为一种协议,享有给付请求权和给付受领权能,故它与纯粹的道德义务还是有区别的,但也不可由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无法院强制力不等于没有给付请求权。法院不可能规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律强制力所及范围之外维护社会生活自然秩序的行为虽不为法律所规定,但也不为法律所禁止,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如果当事人愿意签署和自愿履行,应当构成有效清偿,已经自愿履行的又令法院判令返还的,应当不予支持。由此,将生育协议视为自然之债,只是欠缺了债权保护请求权和强制执行力,是一种不完全债权。
(三)夫妻生育协议的效力
有关生育协议的效力,有效说认为生育协议符合《民法通则》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要件的规定。无效说则认为生育协议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或者生育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7]。笔者认为两种学说均不周延,它们均是将无名身份协议作为无名合同来看待,将其视为法律之债。按照有效说,协议应当产生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但生育行为无法强制执行。按照无效说,又否认了生育权作为私法上的权利能够为当事人所处分和生育协议作为无名身份协议的一种具有债权请求力的事实。生育协议虽然是无名身份协议,但不等于无效身份合同。所以应当将夫妻生育协议放在自然债的视角下进行探讨,这样就可以既肯定其债权请求力和保有力,又否定其执行力,消除司法窘境。
四、司法困境的形成及解决措施
司法上之所以会对夫妻生育协议之诉产生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于法无据是所有司法困境出现的共同原因。生育协议根据现行法条,无论是《婚姻法》还是《民法通则》均没有任何明确依据,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第二,裁判后无法强制执行。法律对人身关系干预的广度和深度远低于财产关系,而生育协议作为一种无名身份协议,法院的可干涉程度更小,不适宜通过法院审判解决生育纠纷。第三,家事纠纷的非理性特点。我妻荣将家事纠纷的特征概括为“财产关系的合理性和身份关系的非理性。对待非理性的关系,适用理性的一般基准是不适当的[8]。”
因此笔者建议对仅基于生育协议提起的诉讼和在离婚诉讼中附带提起的生育协议诉讼不予受理。对生育协议履行后又反悔请求返还的予以受理但不予支持。原因如下:
第一,自然债与法定债特性不同。生育协议作为一种自然债和无名身份协议不适宜通过法院审判解决,诉讼外方式更有利于定分止争。当事人分歧较大时可通过离婚等途径寻求救济。对于这种司法不直接干预的自然之债,除了当事人协商处理外,基层自治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也可以在非司法领域发挥作用。
第二,家事司法谦抑性的要求。生育协议作为家庭内部的隐秘事由,常常“不得与外人道之”,且该纠纷证据收集和证明难度都极大。司法机关要避免将手伸到与公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家事领域,可以以一些特殊理由回避审查。对这类诉讼不予受理,则当事人双方可能会通过协商、共同亲属居中调解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解决,既防止夫妻双方在法庭上剑拔弩张,也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减轻法院讼累。
第三,生育协议与社会道德观念相悖。一般社会成员都会对生育协议嗤之以鼻,认为这种用金钱等外力维护生育权违背了情感的真谛与价值,如果受理甚至判令胜诉会给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生活带来负面效应,无法实现法律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五、结语
夫妻间生育协议是双方共同行使生育权的方式。生育权本质上是民事权利,其行使要遵循民事法律的基本理念,即意思自治原则。生育权作为私法上的权利,通过协议予以约定,在理论上不存在障碍。我国实践中夫妻之间其实不乏生育协议,但其效力很少得到承认。我们认为,生育协议作为一种无名身份协议,其效力以“全有或全无”的标准来判断,应当以自然债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对仅基于生育协议提起的诉讼,应当秉持司法谦抑性的原则,一般不予受理。法治社会的建立不等于法律可以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自然之债属于法律和道德兼顾的一个高明的中间领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采用。
参考文献:
[1]潘皞宇.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J].法学评论,2012(1):65.
[2]张作华,徐小娟.生育权的性别冲突与男性生育权的实现[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2):129.
[3]何勤华,戴永盛.民商法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59.
[4]朱晓喆,徐刚.民法上生育权的表象与本质——对我国司法实务案例的解构研究[J].法学研究,2010(5):66.
[5]陳信勇.自然债与无名身份协议视角下的生育纠纷[J].浙江社会科学,2013(6):87.
[6]李永军.自然之债源流考评[J],中国法学2011(6).78.
[7]林雅.夫妻间生育协议相关法律问题探讨——兼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9条[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3.
[8]我妻荣.家事调停序论[M].日本:有斐阁昭和27年(1).350.
作者简介:
朱堉茜(1993~),女,河北邢台人,华东政法大学2015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