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在语言当中
吴亮++黄德海++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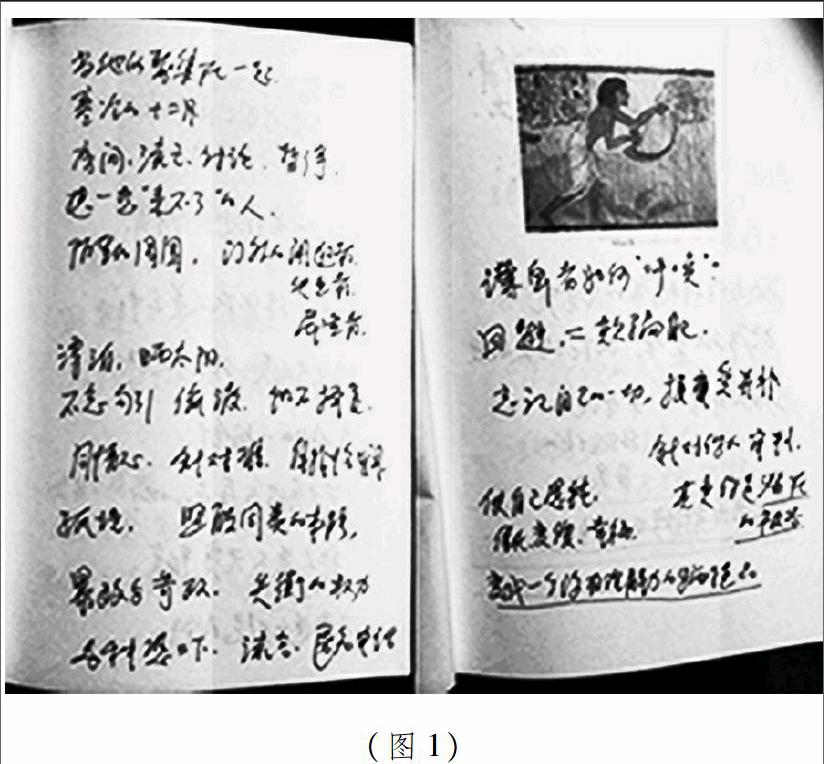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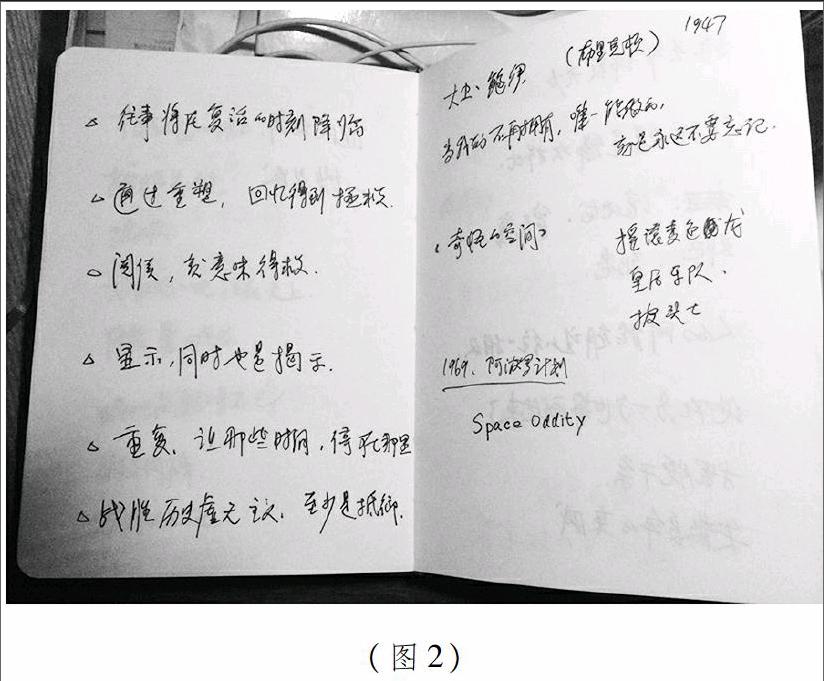
黄德海:《朝霞》这部长篇的构想,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了写出这样一部事先并未完全想好的小说?你曾经随口感慨过:“难以置信!这部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写就的长篇小说,但是作者为此已经准备了半个世纪……”为此准备的半个世纪,包括哪些方面?精神的?写作的?阅读的?对社会的观察?是不是正是目前的写作形式,把此前累积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了?
吴亮:写小说,就为了有点想象空间,不要那么落实,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原因。写作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小说。我1980年代、1990年代曾经写过几篇小说,写着玩的,一个故事,甚至是做了一个梦,我就给写成了短篇。很快,两小时就能写完。给《收获》写过一个短篇,一万多字,起因是我连续做了两个梦,第一天做了第一个梦之后第二天又接了一个梦,把前一天的梦接完,太奇怪了,就起念头写出来。那时候大量看影片,思维、想象完全在电影当中。在家里看影片的感觉跟在电影院不一样,电影院就是集体关进一个黑房子,在家里,房间开着,可以上厕所,可以停一停,它是在一个现实当中有另外一个非现实,同时出现,感觉特别迷幻。当时一天看四部电影,太厉害了,内容完全都混掉了。这种观看电影的经验就在梦里呈现出来,带有预言性质。当时我和西飏有来往,西飏那
会在写小说,我把这两个梦记下来之后稍微夸张了一下讲给他听,他说完全像电影一样。我就把它写出来给了程永新,后来就在《收获》发了一次,又在北岛的《今天》发了一次。(走走注:1991年《收获》第2期,《吉姆四号》)
这完全是偶然,我这前半生,虽然各种文体都写过,尤其评论,我总是要变换一些花样,语言游戏还是挺热衷的,但确实没有想过要写小说。1990年代以后写些随笔,就把自己带进去了,有些时候用第三人称,有些时候用第一人称,开始有了一些叙事,发现自己叙事还可以,但写不长,我平时对日常生活不是很注意。再往下写的时候就抓不住了,这是我很大的缺陷,只能在语言当中。所以你们看《朝霞》,就像是一个个镜头,有的是十五秒,也有的是五十秒,每一自然段,不是持续性很长的。
到了2000年以后,我出过一些散文集,有一点小小的叙事在里面,汪民安说,老吴你叙事能力很强。虽然那时候大家基本已经相互不看东西了,可是我还愿意为朋友写作,对我来说,朋友的评论很重要,我不知道读者在哪里。那时候我仍然没有什么叙事的欲望,就因为我写了一本《我的罗陀斯》,后来金宇澄也说,吴亮你叙事能力很好,很能讲故事。那本书一开始也没有想讲故事,就像我在后记中讲的,“2009年秋季,当李庆西和蔡翔差不多同一天嘱我为他们共同编辑的《书城》杂志撰写专栏的时候,不假思索的我欣然同意了”,我不是一个非常有主动性的人,没什么计划。当年我写了一篇《艺术家和友人对话》,周介人说你可以写一本书了,你有这个潜力,于是我就写了。我的潜力都是人家发现的,一直是别人推着我。
《书城》约我写书评,我说现在那些书,我已经看不过来了,太多了,而且那些书大家都在看,再说有什么好说的?我说不出更好的观点。要不然,我就写写1970年代所读过的那些旧书吧,那些书名你们一定也很熟悉。那时候我们没有书看,所以每一本书都很新鲜,我们在农场、乡下都看书。我这个专栏是从2010年开始第一篇一直到2011年,一共写了十八篇。写第一篇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写一个系列,后来他们说那篇文章简直就是一个序言,点出了很多线索,每个线索都可以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写出了一个当时读书的氛围,从我中学刚刚毕业进入工厂开始,每一篇题目,就成了我书里面的章节,当时的题目叫《我的阅读前史》,围绕着书带出了很多人,譬如这书是爸爸的、祖父的、邻居的、同学的,顺便就把那些朋友说一说,我是因为书认识那些人的。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真实。我当时做工人混病假,就是为了赢得读书时间。
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围绕着书,我没想过要写回忆录,写到中间发现,这个时代出现了。我开始有意识加强那些人物的命运,比如我的邻居有自杀的、被抄家的,诸如此类。这是我第一次以叙事为主要手段的写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前,我最后写后记,顺手写了一句:“《我的罗陀斯》,一本回忆录,说不定它将是我多卷回忆录的第一卷,或其中之一。”现在回头看,那本书就是阅读的回忆录而已,不是我的回忆录,因为我基本上没有谈自己。2012年我开始给《上海文学》写专栏,写了五六期,后来因故没有状态继续写了,这是外部原因。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想接着写下去,感觉语感已经接不上了,我的语感很难改变,写不下去的主要障碍是,我没有办法真实地回忆这段历史。
1970年代,从宏观来说是“文革”时代,后来讲发展,“文革”是被否定了,对“文革”中的一些事可以适当地、有节制地描述;还有一点,那时我在成长过程中,我被蒙蔽,我思考很浅,都是历史环境造成的;我写的人都是我爸爸妈妈邻居,都是我私人朋友,少年时代的朋友,都没什么问题,当然有的邻居名字改了改,但1980年代以后我怎么写?我完全成熟了,我是以写作为生的评论家,任何事情都应该有观点,中国意识形态特别和文艺和写作有关,我经历很多,我能写吗?我真正的态度,我和朋友大量的讨论,能写吗?我又怎么写1980年代末?我是直接写自己1990年代初精神状态?就是一下子,时间在那里,一切关系全部中断,不想出门,无聊、喝酒、听音乐,诸如此类,必须要回到这个现实,我写了1980年代初和1990年代初,1980年代末没办法触及。另外一点,我的成年时代,我认识那么多人,少说也有几十个,多则一两百个有名有姓的,我都还记得,我能够直呼其名吗?他讲的话我能说吗?也许他会赖账,或者他已完全忘记。
我本来想写三部曲,先写1980年代,然后再写新世纪,但就是上述这些原因想来想去,没能写下去。
至于写这个长篇,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是直接产生促成关系的。一是程德培的写作,他六十岁以后写的那些文章,大部分都发在我主编的《上海文化》上,他谈笑风生打麻将写文章,写得还比以前好很多。还有金宇澄,六十岁这一年拿出了《繁花》。我想,原来六十岁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也六十了,就一直想着,有空我要写一本书,但没有写过一个字。2015年8月26日,老金跑到我办公室来玩,“吴亮,你写小说啊”。他以前也讲过这话,但我到那时动心了,我说怎么写?他说你也在“弄堂网”上写嘛,我说这个我有兴趣,他说“弄堂网”那批人都是老上海,知道一点文学,不会给写作者构成很多干扰,他们喜欢怀旧。我说好,现在不要大家都看到。我决定试试看,有一个构思出现了。这天以前,我真是没有想过写小说,没有真正地起念。上“弄堂网”注册需要一个网名,我一看,别人起的都是什么“老爷叔”、“三娘舅”,就不想弄一个中国名字,干脆弄一个奇怪的名字吧。我有个朋友在北方,叫八爷,感觉挺牛的。“八爷”太张扬,于是改成谐音的巴耶,又似乎缺一个字,就加了兴隆的“隆”,注册好以后我就上网,再看“隆巴耶”这个名字,好像似曾相识,像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某个人物。
接下来就需要一个小说名字。当时随手取了一个,非常简单,“昨天不再来”,然后,8月27日这天,我写了第一段。假如你们有兴趣可以上去看看,看了之后就可以知道我的写作频率。每天写了多少,都是什么时候写的。下面有人跟帖发问:这个人什么时候睡觉?我每两个小时写一段,感觉中间没有间断。有时早上两点发一条,三点半一条,六点又一条,我马上进入非常亢奋的状态。
走走:最早出现的那个开始讲故事的人物,是谁?阿诺?少年的你?
吴亮:阿诺就是阿诺,一开始他没有名字,他只是我讲的故事中的另一个视角,同时又是剧中人,慢慢地,这个当年才十几岁的男孩与故事里的许多角色形成了对话关系,其他人必须称呼他的名,于是他就叫阿诺了。
《朝霞》的写作过程很难复述,为此思考的许多东西还记得不少,就是那个“写作中的状态”和“情绪与对话”以及“即时灵感”怎么出来的,我都无法解释。最焦虑的,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字都写不出……一家之言,灵感,就是一种瞬间的或短时段的人格分裂与鬼神附体。一般都在半小时左右,一种迷狂状态,手脑不分。
黄德海:过来了,那些焦虑的时间变得幸福。
吴亮:啊哈,德海见证了这些……
黄德海:见到了焦虑的惶惑,也见证了那些不可替代的萌生时的动人活力。
吴亮:写到一小半以后我自己对自己比较意外、比较欣喜的是,我写具体的东西很好,我以前觉得我可能写不好,我可能会用自己的晦涩和看不懂来吓唬人家,我想我很可能会这样。但是不是。2月5号下午,《朝霞》写下最后一个句点,疲惫而嗜睡,醒来则无聊,读书无法集中精力……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是否要考虑再写一个能够让我兴奋的东西?要积蓄能量……然后,等待契机,冲动不可抑制,《朝霞》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还会有第二次吗?
走走:德海你身为青年评论家,怎样看待《朝霞》这样一个文本?还记得自己当初读到《朝霞》时,是怎样的感受吗?
黄德海: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庞然大物来了,迟缓、沉重、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滞涩,处处是阻碍。这时,就像看到水面整块的平静涌起,慢、大,甚至是安静的,但你知道,大鱼来了!
吴亮:德海阅读《朝霞》,与我写《朝霞》有个根本不同:他读的时候,后面有个大东西等他;我写的时候,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每写一段或连续写几段,得意和惶恐交替出现……惶恐的不是刚才写得不好,而是根本不知道往下怎么写!我写评论从未惶恐。
走走:为什么?手熟?已知和未知的不同?
吴亮:写评论对自己要说什么很明确。写小说完全不同。
走走:小说更需要解决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
吴亮:每个人物都有自由意志,可能性太多了。
走走:德海你觉得《朝霞》是在你的情感体系、思想体系之中还是之外?
黄德海:对这本小说,我觉得最有意味的是,它渐渐地延伸出(或者确切地说,生长到)作者开始没想到的很多角落,包括思考的、情感的、身体的……这些角落原先就在,可是一个虚构文本把这些角落照亮,缓缓显露出来,这是虚构给予写作者的报偿,同时也是挑战。因此,以我对吴亮的认识,有些方面是在我情感和思想体系之内的,有些则远远超出了我的“前见”。
走走:能具体讲讲这内和外吗?比如你的“前见”是什么,你对文本的潜在判断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只有知道一个评论家所代表的普遍视野之后,我们才能更容易理解这一个文本的位置?
黄德海:其实不是。因为你问到我的情感和思想体系,我不得不先说此前的情形。除开这个,这个小说本身有自己的意义(不是每个人都是对作者非常了解了才去读一本书,不是吗?),这意义在于,尽管作品建立在虚构基础上,也并不是连贯性的故事,甚至有些跳跃和拼贴,但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却是完整而丰富的,有所写那个时段的总体感。更有意思的是,作品居然在这些之上有一种自带的反思功能,你在作品里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那种反思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性。
走走:你们觉得思想这个词适合用来形容《朝霞》吗?
吴亮:你用了“思想”概括这个小说的特征,问我对这样“形容”有什么意见,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让你提出这个看法:一是小说作者是个批评家,二是小说本身确实涉及了许多知识领域……当然,《朝霞》中有不少涉及思想的情节与段落,对话、读书札记、引用典籍、作者或叙述者的议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内容都是直接思想的,怀疑、来自正统体系的反诘、其他体系的接触、逻辑与常识、甚至接近于危险边缘的想法、不为人知的独立思考等等,这些思想活动在那个年代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除,要不然就无法解释1976年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不过同时,正如你不断提醒我的,这个必要部分的表达在技术上非常困难,这的确让我难以放手来写,现在的定稿对原稿做了许多无可奈何的删改,这样一来,思想的含量与直接性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减弱,但是反过来说,说不定所谓思想性的弱化对小说的艺术性和多义性以及模糊性是有好处的,把人物放到历史情境中,同时把作者放在历史情境中,让读者与作家同行自己去思想吧!
从宏观到微观,从古代到当下……它们都有具体的抓手,也有几次天马行空式的,好像从这座城市头上掠过的风……我难以还原写作时的思维过程,我更喜欢他们谈话中无意抖落出来的知识,而不是那几段邮票与热带鱼的,太像上课,劳尼舅舅的杂碎闲扯很好,很松弛,从容和无意义……
黄德海:我对这个作品的思想性段落——如果非要这么称呼的话,怀着非常浓烈的兴趣,一方面是刚才吴亮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或被同质化。同时,小说摈弃思想性似乎是一种“艺术正确”,但思想从没在小说里绝迹,只是很多所谓的思想不过是平庸的常识。这个小说中的思想,没有脱离人物,而这些思想,即使现在,也仍然是很多人的思维死角。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被吴亮自己认为回到了19世纪写法的小说,可以认为是回到了小说有更庞杂容量,也有更坚韧活力的传统。而在小说越来越孱弱的今天,这活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新的东西(因为现在的思想进入,已经不是小说的本能,而是思考的结果)。
走走:这部长篇某种角度上说是反小说、拒绝读者的,没有必然的开头,也没有必然的结尾。读者其实可以从99节的任意一节开始阅读,也可以随意中止、继续……小说目前的开头第一句是“邦斯舅舅回到溧阳路麦加里的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但其实,小说中叙述的主要时间远远早于这个开始,许多事早已发生。结尾是“阿诺睡着了,他梦见了马思聪”。其实在这句话之前,“文革”已然结束,许多事已经在无动于衷地继续前行……对于你来说,这个小说存在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吗?也许就像这个世界,没有必然的起点和终点?
吴亮:我现在可以用评论者的眼光看《朝霞》了。重读,发现了中间部分的复杂性,尤其在于叙事形式与信息的纷繁,有隐喻也有莫名之处。因为后半部分的过于吸引人,包括吸引我自己,中间部分的复杂性、隐喻、思想以及形式意味,会被忽略或搁置。中间部分,是浑沌……
小说采取了回述的形式展开,叙事中的顺序不是完整连贯从一个起点均匀地向此刻走来,而是根据叙事者的片断记忆、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呈现,它们招之即来,偶然、浮现、追述、联想、唤醒、回忆……它的视角与时间意识是主观的,同时又是尽可能忠实于客观时间与客观真实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起源于现代小说形式观念、却渐渐回到19世纪传统小说形式与19世纪文学精神的虚构作品。
整个小说从阿诺先后离开牛皮筋与殷老师回到纤纤身边后,戏剧性开始凝聚起来了,叙事形式渐渐简化了,好像一个主旋律诞生,邮票聚会、天津馆雪夜吃饺子、老鼠与猫系列事件、无名信、被掩盖的洪灾报信人、贺子蓝的出现……
19世纪在这个意义上归来了。
走走:那在你看来,19世纪的文学精神是什么?
吴亮:19世纪小说的要义:命运、性格、个性……我本来以为我会写出一个非驴非马的作品,结果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思考是19世纪的,让作者直接在小说中议论也是19世纪的,“回到19世纪”包括这一层意思。
黄德海:小说在18世纪就这样,19世纪已经整饬多了。如果把小说的源头追溯得更早,那么较早期的希腊长篇叙事,更是思想的。我觉得吴亮这里说的“回到”,更像是“复兴”的意思,把一个过去的东西,在现时代复活,重新有意义。
吴亮:我的个人自我启蒙,统统在1970年代完成的,思想来源即19世纪,个人经验啊。撇开个人经验不论,19世纪离我们最近,此其一;19世纪世界大变局开始,此其二。故19世纪非常非常重要。
黄德海:可是你对很多新艺术形式的确认和新的写作方式的尝试,也似乎让人觉得你的思想来源经过特殊的调整……
吴亮:1970年代末开始接触萨特、弗洛伊德,1980年代初起全面接触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刀枪入库了。
黄德海:现在,通过小说,又出来啦(微笑)。
走走:这部长篇形式上是会令期待强情节的读者生畏的,涉及的知识面即使不是深邃至少也是繁杂的,充满各种象征(模型、鼠灾、手绘地图……)与纵横恣肆的旁征博引(古诗、《圣经》段落、歌词……),像邦斯舅舅的信就很有趣,涉及医学、烟草等方方面面的小知识。
吴亮:如你指出的“繁杂”倒是我计划中的,这不仅来自我的部分经验,也来自我后来了解到的其他同代人的间接经验。真实生活中我有个舅舅,写的家信中经常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没有我写的那么专业。我其实是削掉了很多,很多枯燥的东西给削掉了,把一些想象出的经验放在这当中。我一直有一个看书的习惯,笔记一直有的,笔记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薄薄的,做得很漂亮。现在家里有二十来本,都没有写完,不同类型的我都记在里面,有抄的,有感想,也有一些关键词,还有我想写的东西,诸如此类,很乱。
每次看这一大堆笔记,看到一半就不看了,因为觉得太乱。另外加入微信以后,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我的微信?每天晚上我都要东拉西扯发五六条,都是我每天读书的印象或者是思考的问题。从工厂时代我就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每天都要看书。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很小的厂,我在那里学会了抽烟,只有抽烟的时候,不工作是合法的,连续抽烟就可以连续不上班。那时都不讲效率,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在偷懒,很松散,工厂里面有很多空子可以钻。躲在什么地方看书,都可以。甚至有的老师傅拿《解放日报》在厕所里面一坐就是半个小时。1970年代末那会儿,我还在厂里,开始管得严,我看书,我们厂长看到就扣工资,“看书就看书,还看‘马列?”这话很恶毒,好像我在装什么蒜,后来就没有办法拿书看了。那时我订了几份杂志,一份是《历史研究》,一份是《经济研究》,还有一份叫《哲学译丛》,另一份忘记了,总共四份杂志。花了我很多钱,应该很珍贵吧?我太渴望读书了,就一篇篇论文两页三页给撕下来,折成豆腐干拿在手里,没事就看,每天细读一篇文章,总不能再把我的纸头收走吧。就是到了这种程度。说我自学成才实际上是抬举我了,我就觉得看书的时候最充实,真正的充实,看文字比工作有意思,没有想过看了有什么用。
走走:你现在每天都看些什么书呢?
吴亮:非常杂。中国的作品也看,但中国文学还是看得少。只是不太说,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我说不看,不太礼貌。确实我年纪大了,眼睛要看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就看得少一点,写这个小说,我使用了大量读书笔记,有直接抄录,也有自己想象,还有许多有趣内容没有用上。
找到两页没有使用的“提示”:前一页,原计划写林林与几个人的秘密活动,后放弃;第二页,好像应该放在内心独白中,不确定的主体……(见图1)
另一本:左侧是核心观念,用来提醒;右侧关于大卫·鲍伊,没有撕掉……(见图2)
在我本来预想中,想捏造一些并不存在的知识,或扭曲一些知识,结果没有实行,其实应该有这个。曾经的常识,后被认为是谬误,不胜枚举:牛顿都相信过炼金术,拿破仑相信奎宁可以治百病。
我在翻我笔记的时候想再写一个小说,把我这些读书笔记放进去。里面会出现一个主要的人物,他和很多人交往,他回到家里每天一直写回忆录,把自己的思考也放进去。但是他最终一直没有办法写完。我就是想写一个写作的过程,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还没有着手。
走走:《朝霞》的叙述风格大大挑战了当前的快速消费文化,我觉得适合这个文本的理想的读者是愿意与作者共同创造的,创造的是经由你的经验捕捉到的自己的经验,还有意识的跳跃、变动。这部长篇令我着迷的还有,它瓦解了单一向度的大叙事,是一群微小的小叙事所组成,每段叙事各自拥有一个人物的一个面向的生活,有趣的就是,小说从少年阿诺开始写起,到结尾他长大成人,我们读者其实不知道那些琐碎的小事件,比如读书、讨论、弄堂暗巷的冒险、暗恋、与年长女子的生理体验……对他这个人的将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哪些会是决定性的影响……据说你曾经设想过每个人物的未来,那些曾经特别独立思考的脑袋,最终大部分是平庸化的,我觉得尊重这种未知就是在尊重这个世界,没有去轻易简化它。
吴亮:《朝霞》以为要写四十万字,边写边留下未来线索,随机会造一个角色出来,如姚宗藻、张守诚、董医生、郭小红、顾安邦、卡娜依姆(马立克在新疆的女朋友)等等,还有没有深入写的殷老师、陈子谟,最后又冒出几个重要角色,但是故事必须要落幕了……不必所有人名都要交代清楚,所谓“挂在墙上的猎枪一定要打响”。随着人物的一个一个出场,随着他们的成长,故事越来越紧凑,人物关系以及他们的欲望、命运、企盼、等待、迷茫一起涌向了结尾,似乎走向那个似乎有朝霞的柏拉图洞穴出口……为那些小说中的人物们设想各自的未来命运,乃至为其中的几个角色安排最后结局,是小说写到后半程产生的念头,似乎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应有的交待,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为之伤透了脑筋,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我可能因为老了,害怕为别人安排结局其实是不愿意看到结局,尤其是,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角色,他们一开始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身份、一个临时想象出来的扁平人物,渐渐地,这些男男女女一个个鲜活起来,活动变为人形,他们呼之欲出,在写作的后半阶段我与他们生活在一块儿难舍难分。
把《朝霞》所有的人物做了一次清点,有名有姓者有四十余,并初步对他(她)们进行社会学分类,颇为有趣。不是人物性格分析,是“文革”时期的社会学分析。
写作这样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怀旧,我无意识地展示这种指向过去的怀旧,我的读者仿佛不是当代的年轻人,而是半个世纪前的年轻人,我愿意将他们停格在我的小说尾声,停格在我这个文本当下,他们的面容、行止、姿态、期盼与忧伤统统凝固在其中,永远在场,不被遗忘,不被抹去……昨晚又回溯性地读《朝霞》,因模糊记得其中有若干对这个小说本身的阐释与解析,结果找到一段,殊为重要:第36节第一自然段,终于用明晰语言描述了这个小说的“生成”,它必须通过写作本身来达成,渐渐明朗,于是在第36节被揭示出来。由于这个作品内容过于丰繁,别人问起,我常会语塞。
(走走注,第36节第一自然段:“一个宏伟的小说构思,不会是某个夜晚降临的偶然意念所能推动得了的,这不一定是规模的宏伟,更是容量的宏伟,从一句话开始,作为开端,敲响了第一个音符,第二个,第三个,一句话的生成,然后向某个不清楚的方向缓慢流动,渐渐加速,分岔,两个或者三个分岔,水越蓄越多,能量随之集中,需要更多的出口,句子和句子前赴后继,句子已经不为注意,句子汇合成句丛,一个一个句丛的团块,块茎,有自己的生命,它们开始自作主张,它们有了内部的欲望,还有自己的意志,那个叫做人物的角色,他,他和她,更多的他和她,他们!杂乱无章的堆积,他们彼此相识,最初的几个星期,他们各行其是,分头行动,后来他们把拼图找到了,但是新的误解,困惑,未知,他们将要做什么,其实是,他们在过去了的那个最为怪异最为枯索最为难以命名的时代,究竟还做过些什么惊天动地和不值得一提的无意义的必须之事,每时每刻,滑稽,经济,哲理,上帝,野心勃勃,搔首弄姿,幻影与三棱镜,必须有一个光辉的结局,为了阿诺的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为了发生过的一切生活痕迹留下文字,在虚空里消逝。”)
走走:也是在阅读这个文本时,我再一次明确地意识到何为文学的语言,它们具备深度、节奏、层次感,语言终于不再只是讲述情节的工具。必须关注文字本身。所以,所有叙述都通过语言发生……
吴亮:这个“语言自觉”我一直是有的,不过写这部小说有了新体验:写人物对话似乎不是我想象的,是“他们”在说,我则在速记,速度很快。
走走:那你信任这样的语言吗?
吴亮:要听你们的感觉,听你们的意见了。
走走:你笔下的对话非常棒,它们全部都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没有故意为了所谓文学化而扭曲,但非常具有意义的弹性,也准确地反映出我们的真实生活经验,这是怎么做到的?
黄德海:我觉得吴亮这次的对话是一绝。这个速记的说法,很有意思。其实在写这小说之前,吴亮的对话才能已经展示过了,比如在那个著名的批评一个学者的长长的帖子里,就有很多戏拟的对话,活灵活现。程德培的文章里就专门讨论了吴亮的对话。所以这种高峰体验式的写作,归根结底也是这方面的才能和练习而来,这样笔才能跟得上。
吴亮:写多人对话,特别嗨,大部分是迅速完成的。
走走:我觉得诀窍是非常简洁,除了动词,其他能省则省,没有多余的情感累赘,特别写实主义风格,每个字词都透明地实在地说着事儿。
吴亮:眼前有场景幻觉,却并不考虑语言问题,但会记得人物的性格与文化特征。
黄德海:简洁,了解那些人的基本思路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在虚构里写出的是真实的人的想法。
吴亮:脱口而出,就这么简单。
走走:不过有意思的是,整个文本形式复杂,内容却是单纯的。这种单纯也许是因为几乎所有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即便是尚未刑满释放的姚宗藻托人想办法带给张守城的信,威胁也是赤裸裸表现在纸面上的。)没有复杂的潜文本。没有隐藏的另一种关系,没有在表面下面隐藏冲突、紧张、恶意等等,所以这其实是个特别单纯特别干净的小说。
吴亮:谢谢走走读得这样仔细。其实《朝霞》中有告密,有检举,邦斯舅舅为什么去劳改?兆熹为什么被判徒刑?林家兄弟为什么逃亡?我一开始就写了,只是不那么触目惊心,这已经常态化了。
我在《我的罗陀斯》里面有一章写到“死掉的父亲”。一个是我姨夫,就是我妈妈的妹妹的丈夫,扬州人,失踪了,就是跳江死了,找不到了。还有就是我邻居,和我玩得很好的小伙伴,其中一个父亲跳楼自杀了,在1970年左右。他自杀前我还看到他,这个男的是一个资本家,长期高血压。那时他还有一点闲钱,五块钱一把的象牙筷子去买回来,还买一些小小的红木凳子,两块一把,很有眼光吧?他太优哉游哉,有人就想到,这个人一直隐藏着嘛,给揪出来,斗了一次,就跳楼自杀了。我写过很多我邻居的死亡,死人不说话,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世界末日。死了这世界就没了,就是一片黑暗。活下来的人都不知道。对死有点感受的话你就知道,极限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已经写过了,这次是写小说,不能冷冰冰地写。
我这个小说倒不是想写那些深渊的东西,虽然可能中间会出现一些深渊的思考,我的主旋律就是一种生的韧性,怕与爱,尽管他们这么苟且地生活,编故事啊、不见人等等,但是还是要自己的生。
捷克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尔特晚年撰写了一本回忆录《世界美如斯》,这本书令我产生共鸣,这本书很厚,塞弗尔特都八十岁左右了,写的都是他以前认识的朋友,捷克文坛上的人等等,像写日记一样,写得非常好,能看出来里面的气息。他本身不是没有政治立场,但不那么尖锐,就是在夹缝当中,生活得还可以,看起来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在书里面歌颂自然、风光、友谊,当然这里面不完全那么美,也有很多的死亡,他去悼念。如果把他的书和哈维尔的放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是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种生活,他没有说谎,他很真实。他不是在赞美这个时代。即便这个时代有各种悲剧与黑暗,人们还是有快乐的,有伤感、离别、死亡,有亲情、友谊。当然我不会像他那么有诗情,容易发现美,在我的小说里面看不到太多美的描绘。
走走:对,背景仍然是肃杀的,但我想说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这些年轻人的关系特别美好,没有告密,没有权力的争斗,没有支配与操纵,甚至没有虚伪……
吴亮:因为他们的关系很单纯:同学、邻居、亲人……他们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脱落”下来,病假、逃避、赖在家中,这个状况在19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
走走:但是我看过一些关于“文革”告密的研究文章,正是上述的亲近关系,滋生出大量告密、汇报的材料。
黄德海:我觉得也是这些人没有那样,父子成仇、夫妻反目、以邻为壑,我们见得也听得多了。这个,就是一个小说纯净的地方,它来自作者,也让小说不再是习见的,只跟随运动起伏的某种作品。
走走:所以还是心怎样,看到的/写出的世界就是怎样。
黄德海:完全赞同。
(本访谈整理自聊天录音与微信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