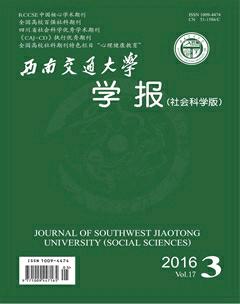论《战国策》策士谏言中的道家思想
张琰 施仲贞
关键词:《战国策》;策士;谏言;道家思想;顺应法;自然无为;“环”术;辩证法则
摘要:关于《战国策》中的策士及其谏言,学者大多关注到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纵横家思想。其实,在《战国策》的策士谏言中,亦有着道家的渊源影响及其思想内蕴:《战国策》策士谏言奉行的“顺应法”,即 “顺应”被谏言者的意愿,以其是非判断和好恶选择作为游说的原则和标准,就衍生自道家的“自然无为”;而策士谏言中的“环”术,即不设置明确的是非价值观,任何策略和主张都因势而变,则以道家的“辩证法则”为理论基础和思路方法。
中图分类号:B223; 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131-05
The Taoist Thoughts of the Counselors Advice in Zhan Guo Ce
ZHANG Yan1, SHI Zhongzhen2
(1.Teachers College, Wuxi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Wuxi 214153, China; 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Key words: Zhan Guo Ce; counselors; advice; Taoist Thoughts; the law of conformance; natural inaction; the circle method; the dialectical law of Taoism
Abstract: Most of the schola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thoughts of the strategist when thinking of the counselors and their advice in Zhan Guo Ce. In fact, the counselors advice in Zhan Guo Ce originated from and was influenced by Taoism and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law of conformance that counselors advice adopted in Zhan Guo Ce came from the Taoist natural inaction, i.e., the counselors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adaptation when giving advice to others and used the kings and emperors judgements, likes and dislikes as their standards of lobbying. And the circle method in counselors advice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 of thinking from the dialectical law of Taoism, without clear demarcation of rights and wrongs, and they insisted that any strategies and ideas had to change with the variation of conditions.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时代,《战国策》正是围绕这一时期策士谋臣的谏言谋议和论辩辞说展开,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诸侯国在军事、外交和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和斗争。可以说,《战国策》中刻画最精彩、最吸引人的核心灵魂人物不是君王贵族、将相诸侯,而是奔走于各国之间、巧言善辩于朝堂之上的策士们,他们以言语掌控时局、力挽狂澜甚至改变国家命数运势,“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1〕,“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这些曾经风云际会、长袖善舞的“高才秀士”,以崇尚智能和实用理性为轴心精神,高扬着个人主义,洋溢着主体热情,纵横捭阖,气势飞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3〕,凭一己之力,以非凡的口才和胆识,在战国这个严酷的乱世之中,在时代和生存的重压之下,脱颖而出,改变了自身乃至国家的命运,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于《战国策》中的策士谏言,学者大多关注的是其中所反映的纵横家思想,禇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就称《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4〕。其实,在《战国策》的策士谏言中,亦有着道家的渊源影响及其思想内蕴。本文拟从策士谏言的“顺应法”和“环”术来探讨《战国策》策士谏言中的道家思想。
一、道家的“自然无为”与策士谏言的“顺应法”“自然无为”是道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5〕,“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5〕,“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5〕。老子在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指事物自身的初始本真状态。道家认为世间任何事物都应该顺由其自身的情状去发展,“无为”而行,顺性而动,不要强制以外界意志和力量阻扰和干预。“自然无为”也即应对事物任由其发展,不施以强力人为。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张琰论《战国策》策士谏言中的道家思想道家这一“自然无为”的思想被纵横家所吸收和引用,甚至纳入纵横理论领域,用来作为应对游说劝谏对象的方式与准则。《鬼谷子》云:“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鬼谷子·捭阖》)〔6〕进谏言者所要面对的游说对象往往千差万别,各有不同:有的人有才德,亦有人无德不才;有的人有智慧,亦有人愚昧蠢顿;有的人勇敢,也有人懦弱胆怯。想要成功地达到游说目的,就要以“无为”之法以对,即根据谏言对象的秉性和特点,调整和实施游说策略。陶弘景注:“言贤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贤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阖而异之;智之与勇可进而贵之,愚之与怯可退而贱之。”〔6〕捭阖、进退、贵贱等游说方法和策略的选择,都应该针对被劝谏对象的虑怀和意向“度身打造”,进而推波助澜,水到渠成。
《捭阖》是《鬼谷子》的第一篇,也是后面另外五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和体系根本。如果说在纵横学的“旷世奇书”《鬼谷子》中,可以看到其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念纳入了整个纵横理论体系;那么,在同处于战国这个“轴心时代”的《战国策》中,则可以看到将这一“无为”理念付诸于游说实践,且运用得几乎炉火纯青的一个个纵横家们鲜活的身影。这些生存于战国这一“纵横之世”的策士们,为了扬名谋禄、显达于世,取悦获信于当世之君,或运筹帷幄于朝堂之上;或游说周旋于诸国之间,以所依附的统治者的需要和意愿为其权谋游说的根本出发点和行动标杆。
《齐策·齐王夫人死章》记载:齐王夫人死后,要从其宠爱的七位年轻美妾中重新再选一位为新夫人。齐王于是向孟尝君询问新夫人的人选问题。孟尝君为了揣度齐王的想法,便进献上七对女子的珠玉耳饰,其中有一对特别漂亮。第二天他观察哪位美妾戴上了最美的耳饰,就劝谏齐王将其立为新夫人。为了摸透谏言对象的真实心意,顺其内心想法,身为齐国贵族、宗室大臣、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尚且如此,其他没有如此显贵出身而又渴望高官厚禄、显达于世的普通策士们,为了不冒犯君王,取悦于上,就更可谓是乐行此道、无所不用其极了。
《战国策》中还有一个与《齐策·齐王夫人死章》非常类似的例子。《楚策·楚王后死章》记载:楚国的王后死后,还没有确立新后。有人就问楚国的大臣昭鱼为何还不请楚王立新后,昭鱼回答:“王不听,是知困而交绝于后也”〔2〕。昭鱼自己不提建议的原因,是担心所推荐王后并非楚王心中最佳人选,自己立后的主张不能被采纳,反而会交恶于未来的新王后,使自己陷于困境。那人就给昭鱼出了个主意:去买五双耳环,让其中一双最为精美;将这五双耳环进献给楚王,进而观察第二日是谁佩戴了这双耳环,就请求楚王立她为王后。进献耳环的方法虽非昭鱼自出,但他迟疑于如何猜度楚王心意,以被劝谏者楚王的虑怀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其原则策略正是出自“自然无为”之法。
《韩策·魏之围邯郸也章》则记载魏国兴兵伐赵,并且围困了赵国的邯郸,于是赵国分别派使臣到齐国和韩国请求救援。当时作为韩国谋臣的申不害,在被韩王问及应该与哪个国家联合时,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使用暂缓之计,推说“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2〕。随后,申不害便鼓动两位对是否出兵救赵持不同态度的大臣赵卓和韩晁,让他们分别向韩王进谏,自己则暗中观察韩王对两种主张的态度,以揣摩韩王的心意。在摸清了韩王的心思之后,申不害才向韩王进谏联齐伐魏以救赵,此建议当然正合韩王之心。韩王龙颜大悦,当即就接纳了他的谏言,后来与齐国一起围魏救赵,解了赵国的邯郸之围。申不害进谏韩王成功的原因,是其以“无为”之法应对君主的询问,度君而行,顺君之意,“顺龙鳞”,所言正是君王心中所愿所想,当然可以使其谏言很容易就被接受和采纳。
除了直接使用“无为”之法,有时,策士们也会用循循善诱、引君入彀的方式间接使用这种“自然无为”的顺应法,即在整个谏言过程中,策士并不直接去揣摩被游说对象的内心意愿,也不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将原本被问询的“总问题”分解、细化为若干由浅入深的“分问题”,层层深入,抽丝剥茧,帮助被谏言者认清局面和形势,从而自己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魏策·魏王问张旄章》记载:魏国大臣张旄在被君王问及是否可以与秦国一起攻打韩国时,先询问魏王如果联合秦国讨伐韩国,“韩国是会坐以待毙,还是会割让土地来顺从天下的诸侯?”魏王回答韩国会选择割地求和。于是,张旄又问魏王:“韩国会因此怨恨魏国还是秦国呢?”魏王回答韩国会怨恨魏国。张旄再问:“那在韩国看来,是秦国强大,还是魏国强大呢?”魏王答道:韩国定会认为是秦国更为强大。张旄趁势最终总结式地深入发问:“(您认为)韩国是将会愿意割让土地,以听从它认为强大的国家,联合它所不怨恨的国家呢;还是会甘心割让土地,来听从它认为不强大的国家,联合它所怨恨的国家呢?”魏王回答韩国会选择割地以顺从于它认为强大的国家,并与其所不怨恨的国家联合。张旄最后向魏王进言道:“攻韩之事王自知矣。”〔2〕张旄在整个被问政的过程中,都没有直接、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面对纠结于“是否要联秦攻韩”的魏王,他把原本概念化、抽象化的议题落实,使其具象化、简单化、缩小化,分解成三个分式问题和一个总发问的组合,帮助魏王自己衡量和辨清魏秦韩三国综合国力的强弱以及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认识到魏国的内外条件和真实处境,度权量能,从而自己得出处理魏秦韩三国之间关系策略的结论。
无论是直接使用,还是旁敲侧击地间接使用这种“无为之法”,策士们都是本着“顺应”被谏言者的原则,以君王的是非判断和好恶选择为其游说的原则和标准,帮助君主“说”出心中所感所愿所想,最终不仅巧妙且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谏言任务,而且往往通过进谏获得了君主的信任和亲近。
二、道家的“辩证法则”与策士谏言的“环”术除了“自然无为”,世间万物的辩证法则也是道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老子就有着朴素辨证法思想: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5〕,“曲则全,枉则直”(二十二章)〔5〕。庄子也认为:“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庄子·秋水》)〔7〕。道家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着正反对立的两个方面,并且都是在矛盾对立的关系中互相依存的。对立的正反两面在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极限的时候,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当这种转变足够强大及彻底的时候,甚至还会改变事物的状态和本质,转换成其对立面。老子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第三十六章)〔5〕这是老子在歙张、弱强、废兴、取与的矛盾对立与相互转化间,对于事物发展祸福盛衰依伏、盈虚相互消长、物极则必反的分析与看法。
道家的辩证法谈的是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与法则,本不涉及谋略。但其精髓被纵横家们袭用并引入到纵横领域后,就为其谏言游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指导和思路方法。纵横学的奠基之作《鬼谷子》就指出:“阳还终阴,阴极反阳”(《鬼谷子·捭阖》)〔6〕。阴阳之间不但相互依存,而且阴、阳发展到极致之后还能相互转换。《鬼谷子·内揵》:“环转因化。”〔6〕陶弘景注:“去就之际,反复量宜,如圆环之转,因彼变化。”〔6〕此为“环”术。因为“环”乃圆形,没有明确的取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纵横家没有明确的是非价值观,他们认为任何外交策略和政治主张都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都要因势而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改变。
《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中的苏秦,起初用“连横”的主张游说秦惠王,以秦国本国为主,联合东方个别国家,以攻打其他的诸侯国。无奈十次向秦王进献游说的奏章,都不被采纳,致使“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2〕。在巨大的仕途打击和人生挫折面前,苏秦发愤苦读,锥刺其股,他的目标很明确:“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2〕对于功名利禄、富贵权势的孜孜以求,正是以苏秦为代表的《战国策》中纵横策士的至高理想。在这样的人生追求下,任何观念和主张都是可以不用坚持的,都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在发奋研读一年后,苏秦再次整装出发,但他这次的游说目标是华屋之下的赵肃侯,游说主张则是为赵王度身定制的“约从散横”——在外交上,倡导诸侯国“合纵”抗秦,同时破坏秦国和别国的“连横”。这次苏秦成功了,“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2〕。合纵和连横是鲜明对立的两种外交策略,但苏秦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推连横,后主合纵,其政治主张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定论。在苏秦看来,合纵和连横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是否适合自己的游说需要,以及是否被所游说的君王所接纳。所以,形势变化了,其纵横主张自然也就会随之作出改变。
除了外交策略,策士对内的政治主张也是可以随时反复、作出改变的。《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记载,苏秦游说秦惠王要强兵,以武力和战争来征服诸侯:“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2〕“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2〕可此后,《赵策·秦攻赵章》中,秦国攻打赵国时,苏秦又劝谏秦王要息战、休养生息:“求得而反静,圣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2〕他甚至信誓旦旦地断言,自己向其他诸侯国所极力推行的合纵政策不可能实现,秦国将不会面临天下诸侯合纵的威胁:“不识从之一成恶存也。”〔2〕观点如此互相矛盾、随意更改,但他凭着巧舌如簧,终于说动秦王,“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2〕。
《战国策》中的策士不仅外交和内政主张可以左右摇摆、前后不一,在对待与国君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与儒家追求的“仁义忠孝”价值观不同,纵横策士以“环”术来处理君臣之交,主张不必执着坚守于对错忠义,不必强谏,合则跟随,不合则散。如门客士尉劝谏靖郭君远离齐貌辨,靖郭君不予理会,士尉就径自辞别而去,毫无留恋(《齐策·靖郭君善齐貌辨章》);公孙衍因与田需的个人私怨,竟然对魏襄王扬言“需亡,臣将侍;需侍,臣请亡。”〔2〕(《魏策·犀首见梁君章》)有的策士甚至可以为谋私利不顾国家君臣道义,《楚策·楚考烈王无子章》中的楚考烈王没有子嗣,春申君为此很是忧虑。赵国人李园设计把自己的妹妹献给了春申君,春申君对她很是宠爱,后来李园的妹妹怀上了身孕,她劝春申君道:“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2〕她建议春申君把自己进献给楚王,以腹中春申君之子鱼目混珠,假托是由楚王所出,欺蒙楚王,如若此后诞下男孩,就可立为新楚王,“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封尽可得”〔2〕。如此荒唐不忠的提议,春申君居然“大然之”,“而言之楚王”〔2〕。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相国之位、江东封地,春申君完全无视与楚考烈王的君臣情义,丧失了为人臣者的信仰和底线,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可叹的是,春申君最后被李园灭口于宫门之内,其全家亦受牵连尽灭。
《战国策》里的策士,因为习行“环”术,缺失自身的信仰和立场,其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往往一味只是钻营自身的利益,毫无顾忌地膨胀个体的私欲。他们蝇营狗苟,言行不一,前后矛盾,言不由衷。《秦策·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章》中,天下的策士聚集于赵国都城邯郸,共同商讨合纵攻秦之策,看似同心协力、一团和气,局势一触即发。但秦国的相国应侯一语道破:“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2〕于是,秦王派唐雎到赵国的武安城大宴群士,尽散五千金,并且扬言:“(只有武安的谋士可以得到丰厚的赏金),在邯郸聚集的策士们谁又能领取到这些金子呢?”不久,居住在武安、得到赏赐的策士们与秦臣唐雎的关系就迅速升温成“昆弟”之谊了。于是,秦相应侯又指派唐雎再次尽散五千金,并申言赏金散的越多,为秦国建立的功业就越大。唐雎又到武安,散发的金子还不到三千,这些策士们就再也按耐不住了,断然撕毁了先前戮力攻秦的誓约,顿失一心为六国谋利,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调言论,“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2〕。
《战国策》中的策士还善于将“环”术纳入到具体的谋略中,作为其“出尔反尔”的“小人”之计的理论支撑。《秦策·齐助楚攻秦章》中,张仪为了离间齐楚同盟,游说承诺楚怀王“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2〕。楚怀王禁不住六百里商于之地的诱惑,便派使者和齐国断绝交往。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楚王甚至还派出勇士去大骂齐王。齐王震怒,齐楚绝交。而张仪则一面私下结交齐国,一面在确认齐楚已然交恶之后,“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2〕当楚国使者质疑张仪先前答应的是六百里而不是区区六里时,张仪却振振有词地宣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2〕在奉行“环”术的张仪看来,先诓以六百里,再欺楚王以六里,不仅不是该遭谴责唾弃的失信行为,反而是让人颇可自傲的智慧和才能的表现。类似的还有《秦策·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章》,宜阳的战事正处于关键阶段,为了攻克韩国的宜阳,获取楚国的欢心,防止楚韩联盟,冯章谏言秦武王:“不如许楚汉中以欢之”〔2〕,楚怀王大悦,韩国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宜阳失守。宜阳之役后,楚怀王根据冯章的许诺向秦国索要汉中,冯章却奏请秦武王道:“王遂亡臣,因谓楚王曰:‘寡人固无地而许楚王。”〔2〕冯章以否认誓约、背信弃约之计,既赢得了宜阳之战的胜利,又保住了汉中之地。在策士的“环”术精神中,一场战役的胜利比起个人甚至国家的信义更为重要和实际。
由此可见,作为先秦时期的纵横家,《战国策》中的策士们在谏言中运用的无论是“顺应法”,还是所谓“环”术,都与先秦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其实,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原本就出自道、墨、儒、法等各家。“纵横家”之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8〕郭预衡在探寻纵横家之源流时,明确指出其“来于各家、自成一流”①。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则说道:“(战国时)儒、墨、道、阴阳及诸人著书立说,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见获政治上之重用……惟纵横一家,独获用于上层统治者。”〔9〕一些原习道学者,为了所学能用于世,改习纵横之术,而其原有的道学思想也就同时被纳入融合到其纵横之术中。
此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也使得纵横策士们能够对其他诸子学说广泛涉猎、兼收并蓄,汲取其中的思想精髓,为己所用,道家学说自然也包括在内。于是,从道家的“自然无为”中,衍生出了策士的“顺应法”;道学的“辩证法则”则启发了策士的“环”术。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策士谏言中的“顺应法”和“环”术虽源出道家,但其作为纵横之术,又拥有独特的内涵,那就是“实用主义”。道家学说的“自然无为”和“辩证法则”,根源都在追求“道”这一理想境界;而纵横策士汲取其精华,将这一形而上的“道”转变为形而下的“术”,其指导思想就是纵横学的实用理性。
注释:
①见郭预衡的《儒家流为纵横说》,刊于1947年7月30日的《经世日报》“读书周刊”。转引自熊宪光的《纵横家研究》第48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29.
〔2〕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356,570,965,930,75,75,75,74,75,665,666,666,852,593,593,593,192,192,117,118,118,133,134.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65.
〔4〕禇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13.
〔5〕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9,80,212,80,161,207.
〔6〕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7,7,21,58,60.
〔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577.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0.
〔9〕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5:189.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