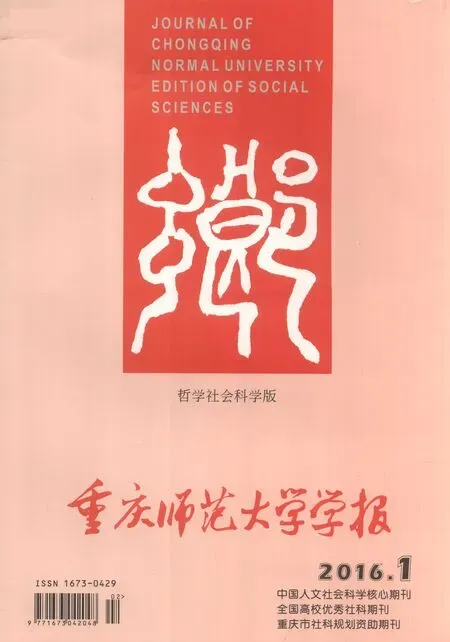建炎元年李纲的“国是”及其失败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047)
建炎元年李纲的“国是”及其失败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047)
建炎元年五月,康王赵构建立南宋政权,李纲就任宰相。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李纲以靖康之难为鉴戒,明确提出罢和议,务自守的“国是”之说。由于朝中重臣的意见不一,李纲在具体实施其专务守策的过程中,虽然能够得到高宗的支持,但却难免遇到来自于各方的阻力,终致其“国是”以失败而告终。
建炎元年;李纲;“国是”
北宋末年的金人南侵,带给赵宋政权前所未有的危机。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自东、西两路入犯,“北边诸郡皆陷,又陷忻、代等州,围太原府”。[1]卷22,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417十二月,宋徽宗禅位于钦宗。次年,改元靖康。十二月,宋钦宗向金人呈奉降表,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廷“诏降宋二帝为庶人。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2]卷3,本纪第三,太宗,56五月,赵宋的“兵马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3]卷5,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115历史进入南宋。南宋兴起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外有金人相逼,内有此起彼伏的兵乱、盗乱,如何布画新政,度过艰险危机就成了高宗即位之初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李纲正是在这个重要关口登上了南宋政治舞台。建炎元年(1127)五月甲午,“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3]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120六月庚申,“诏李纲立新班奏事。执政退,纲留身上十议”。[3]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1册,142李纲所上“十议”,包括“议国是”、“议巡幸”、“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政本”、“议责成”、“议修德”,其内容涉及到南宋政权建立之初急需确立的战、守、和等问题、如何处理参与张邦昌伪楚政权的人员问题、以及保证新政实施的久任责成等现实问题。对于李纲提出的新政,高宗朝廷由支持渐变而为放弃。在这个过程中,李纲与拥立高宗的黄潜善、汪伯彦等重臣论争激烈,并于八月罢相,其施政纲领也就随之而失败了。本文依据这段历史事实,探讨李纲提出的“国是”的依据、方向以及失败的内在原因。
一、李纲“国是”之依据:以靖康为鉴
李纲在其所上“议国是”中明确提出“不务战、守之计,惟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他又结合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国内外方方面面形势极为严峻的现实状况,在战与守的二策中,选择“自守”作为应对金人南犯的对策和当时的“国是”:“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俟于可为之时。”[4]卷58,《议国是》,636李纲所奏的这个“国是”,是以其自身亲历的靖康之际朝廷对金策略不定,战、守、和三者俱失之,最终导致二帝北迁,易姓建号的惨痛教训为依据的:
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和与战两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为然,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捍贼;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师。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款四方勤王之师,使虏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伎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号。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4]卷58,《议国是》,635-637
早在钦宗即位之初,金兵渡河之际,徽宗东幸,“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当金人步步紧逼,群臣多以为不可守,钦宗去留之意未决的最艰难时刻,李纲挺身坚持固守:“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黙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顾宰执曰:‘执政有何阙?’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時宇文粹中随道君皇帝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右丞。’面赐袍带并笏……宰执犹以去计劝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者……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勿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会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取纸御书‘可回’二字,用宝,俾中使追还中官、国公。因顾余曰:‘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不令稍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与李棁同出治事。”[4]卷171,《靖康传信录上》, 1577-1578李纲临危受命,先后任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职,率众坚守东京,“敌兵攻城,纲身督战,募壮士缒城而下,斩酋长十余人,杀其众数千人。”[1]卷358,《李纲上》,11243金人攻城不下,遂遣使议和。其议和条件则是“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4]卷171,《靖康传信录上》,1581李纲认为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固不可以不和”,但不可割地及过许金币,因为“金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
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4]卷171,《靖康传信录上》, 1580
然而,李纲的意见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朝夕,肝脑且涂地,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4]卷171,《靖康传信录上》,1581李纲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此事当徐议之。’纲退,则誓书已行,所求皆与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张邦昌为质。”[1]卷358,《李纲上》,11244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庚辰,皇弟康王、少宰张邦昌使于大金军前,给事中李邺为计议使,右武大夫高世则副之,赍和议誓书,送伴萧三宝奴等同行。”[5]卷30,219宋廷誓书坚称“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违此誓,神殛无赦,宗社倾覆,子孙不享。”[5]卷30,220至此,宋钦宗放弃了“守”的策略,转而以“和”为应对金人的第一要务。
但是,随着数万勤王之师的渐至京师,钦宗朝廷对金人的策略又发生了由和而战的变化。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之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条下记载,“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京师”,“京城人知勤王兵至欢踊,气增十倍”。“上再三慰劳,问计将安出?师道奏曰:‘臣以为讲和非计也。京城周围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十数丈,粟支数年,不可攻也。若于城上扎寨,而城外严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踰旬月,虏自困矣。然业已讲和,不可止。金银不足,请以见数与之。如其不退,乃与之战。且四镇之地内保州乃宣祖陵寝所在,不宜割与’……又请缓给金带,禁游骑不得远掠,俟其惰归,扼之于河,当使匹马不还。上皆是之。”[5]卷30,224~226钦宗由先前与金人“金石不渝”的议和之举,随之而转为对种师道反对讲和与割地之说的“是之”,其原因是基于勤王军队的陆续抵达以及对金人剽掠暴行的愤恨:“及勤王之师既集,西兵将帅日至,上意方壮。又闻金人虏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坟墓殡歹赞 发掘殆尽,始赫然有用兵之意。”[4]卷171,《靖康传信录上》,1583以此为背景,正月二十七日,李纲上殿奏陈宋金双方的兵力和形势,提出了“以计取之”的方略:
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己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4]卷172,《靖康传信录中》,1587
宋廷上对于李纲提出的对敌意见并无异议:“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举事。”但这个计划却又因为姚平仲提前举事而流产。据载,姚平仲“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谓斡离不者,取今上皇以归”。但姚平仲却不得所欲,劫寨失利,惧诛戮而遁去。李纲遂被指为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的主要责任人。“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议”,[4]卷172,《靖康传信录中》,1587~1588遂罢李纲与种师道,遣使交割三镇。其割三镇诏书曰:
敕太原府守臣,应中山、河间、太原府并属县镇及以北州军,已于誓书中议定,合交割与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纳叛亡,有渝信誓,因举大军,直至京畿。重以社稷为念,所系甚大,遂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其犬牙不齐去处,并两平兑易,合照誓书施行。如有州军未便听从,仰将此诏书遍行告谕,各务遵禀。毋或拒违,自取涂炭。
两朝封疆接畛,义同一家,各宁尔居,永保信睦。[6]《宋少主敕太原守臣诏》,162
钦宗朝廷既已满足了金人的索求,意欲“割三府以寻欢盟,庶销兵革之忧,以固两朝之好”,金人遂退师北还。宋廷也罢去诸道勤王之师,就此进入“和”的时期,二月十二日戊申大赦天下。至此,钦宗朝廷的对金的策略又由战转变为和。
但是,朝廷上下的反和之声并未因议和而停止,太学生杨诲上书论割地、晁其上书论三镇不可弃,其言辞皆激烈慷慨。御史中丞许翰更深入分析割让三镇的危害及姚平仲劫寨失利的原因,明确提出议和乃非策:
方今若失三镇二十州之地,则天下之势已断。西北无河东,则陕不可守;无河朔,则汴不可都。计不过谋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为东晋者,乃王导、谢安英贤相继,扶危救倾,仅能立国,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后世无王导、谢安之才,或有而不见施用,则东晋割据,犹恐未易为也。……今使虏不释憾,则渡河之师当战,战则必有漕运之役,有应援之兵,有屯据之要,皆当素治,不计小节,但责成功,而后将帅志一,士卒气奋,三镇之守,有死无二。若我将以疑遣,师以苟行,则精锐已亡,何以取胜?凡今为和议者,苟取目前之无事,则又未可必也。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为虏,则宁南向作贼,死且为中原鬼。”使三镇之众发愤怨怼,人为寇攘,非小变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况又方来之患,亦未知税驾欤?自古用兵,必有异议……《书》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陛下所以疑者,度众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败,自持其说。近者种师道为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当少扰之,使自蹂籍,而后可乘。又地势横入河中,渡兵隘桥,此利诱使出战,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师道有谋。故前日之攻,失在不用老将而用骁勇,不恃谋将而恃词说,非兵不可用也。[7]403-405
许翰以史为鉴,结合当时实际状况,基于“非兵不可用”的前提,尖锐指出“凡今为和议者,苟取目前之无事,则又未可必也。”在朝廷上下反议和、反割让的强大呼声下,钦宗于三月十六日发布诏书,罢黜主和大臣:
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师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纾祸。赖宗社之灵,守备勿缺,久乃退师。而金人要盟,终勿可保。今肃王渡河北去未还,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镇,先败元约,所过残破州县,杀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诏元主和议李邦彦、奉使许地李棁、李邺、郑望之悉行罢黜。
与此同时,钦宗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往援三镇”,声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且保塞陵寝所在,誓当固守。朕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以偷顷刻之安。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7]492
钦宗朝廷二月下诏割让三镇以退金师,三月则称“永保疆土”,“不忍陷三镇二十州之民”,这就违背了宋金双方先前的议和盟约,使先前的和议前景变得难以预测。加之宋廷又接连做出联合辽国旧将以抗金的举动,终使宋金之间脆弱的和议彻底崩溃。对此,《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的记载较为详细:
先是,朝廷以肃王为彼所质,亦留其使臣萧仲恭以相当,逾月不遣。其副赵伦惧不得归,乃绐馆伴邢倞曰:“金国有耶律余睹者,领契丹兵甚众,贰于金人,愿归大国,可结之以图斡离不及粘没喝。”执政以仲恭、余睹皆辽贵戚旧臣,而用事于金,当有亡国之戚,信之,乃以蜡书付伦,致之余睹,使为内应,仍赐伦银绢。伦还,见斡离不,即以蜡书献之,斡离不以闻于金主。又麟府帅折可求言辽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结宋以复怨于金。吴敏劝帝致书梁王,由河东之麟府,亦为粘没喝游兵所得,复以闻。于是金主甚怒,以粘没喝为左副元帅,斡离不为右副元帅,分道南侵。粘没喝发云中,斡离不发保州。[8]583-584
宋执政者误信金使赵伦之言,致书已为金国效命的辽国旧将耶律余睹,其书慷慨激昂,约其共举反金,承担起兴复大辽国的使命:“使人萧仲恭、赵伦之来,能道辽国与燕云之遗民不忘耶律氏之徳,冀假中国诏令,拥立耆哲……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继有辽国,克绍前休,以慰遗民之思。方今总兵于外,且有西南招讨太师同姓之助,云中留守尚书愿忠之佐,一徳同心,足以共成大事。”又称宋朝当全力相助,“以中国之势,竭力拥卫,何有不成?”[6]228此书约辽旧将背金以兴复故国,全然跳出了此前与金国议和的思维,这就把南宋再次引向了战争的边缘。而南宋朝廷根据大将折可求情报做出的联结西辽以抗金的决策,更触发金主之恨。靖康元年十月十八日庚戌,金人遣使持书责宋叛盟,质问宋廷“遗契丹王及余睹蜡书,并元割三镇”之罪。其言曰:
曾自为辞,管行割送,今则反假士民之固守,更张军势以解围。兹事难图,昔言安在?乃者差萧仲恭、赵伦等赍书报复,回日辄受间谍之语,阴传构结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5]卷58,靖康元年十月十八日庚戌,433
金人以强硬的态度斥宋廷背盟之罪,同时引兵南伐。靖康元年九月丙寅,金左副元帅宗维攻陷太原,十月丁酉,金右副元帅宗傑攻破真定。十一月丙戌,宗傑打到京师,丁酉,宗维也抵达京师。十二月,宋钦宗向金人奉呈降表。靖康二年二月丙寅,金主“诏降宋二帝为庶人,三月丁酉,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2]卷3《太宗纪》,56北宋灭亡。
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五月即皇帝位,改元建炎,任命李纲为宰相。六月庚申,李纲奏上十议,深入分析并总结了靖康之际,面对金人的入犯,宋廷固守、和议、应战三策变化不定,终于导致国家破亡的惨痛经历,指出其教训就在于“和与战两失之”,“并守策失之”。李纲为新政权提出的“国是”,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历史事实之上的。
二、李纲“国是”的方向:专务自守
高宗建立的南宋新政权一开始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谓“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3] 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乙未条引李纲所言, 122金人于灭亡北宋之后,坚决排斥赵氏,要求百司共议堪为新帝人选时,就明确规定“宜别择贤人,立为屏藩,以王兹土”。“赵氏宗人,不预此议”。[7]卷15,二月六日条,1611赵构的即皇帝位,被斥为“妄称兴复”,明言“赵构虽系亡宋之余,是亦匹夫,非众人共迷,无由自立”。对于赵构所建立的南宋新政权,金人坚决否认、势不两立的态度毫不含糊:
若赵构晓悉此意,亲诣辕门,悔罪听命,则使与父兄圆聚,复立大楚而已。如张氏(张邦昌)已遭鸩毒,则别择贤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无犯。若或仍敢恣狂,终无悛悟,即许所在士民、僧道齐心擒送,以靖国难。若亦不慎去就,稍拒官军,不即擒送,及不住扰乱新边,即是以迷固迷,与乱同道,自取涂炭,罪宜不宥,累年征讨,定无苏息。[6]《伐康王晓告诸路文字》,494—495
一方是强势凭陵、一意否决赵宋的金廷,另一方则是“以今日国势,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远甚”[4]卷58,《议国是》,635的南宋新政权。在双方根本没有可能并立的情况下,如何应对金人,就成了高宗赵构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李纲所奏十议中提出的“国是”也正是针对于此而发。
李纲分析了靖康年间谋略失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二个方面入手,否决了议和之说。
一是从宋廷内部入手,针对徽、钦二帝北迁的事实,从“孝友之德”入手,分析和议不可行之由:
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沉于虏廷,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而亏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窃以为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成皋间,太公为羽军所得,其危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力,羽不敢害,而卒归太公。然则不顾其亲而战者,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晋惠公为秦所执,吕郤谋立子圉以靖国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归惠公。然则不恤敌国而自治者,乃所以归惠公之术也。今有贼盗于此,劫质主人,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以卑辞求之,则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测之理。何则?彼为利谋,陵懦畏强,而初无恻隐之心故也。今二圣之在虏廷,莫知安否之审,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遗我,得金币若干则可,不然二圣之祸,且将不测。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与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命而已。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臣愚窃以为过矣。[4]卷58《议国是》,635-636
李纲把为“孝友之德”分为帝王之孝与匹夫之孝。匹夫之孝,“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帝王则为天下计,天下之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前日既信其诈谋以破国矣,今又欲陷覆车之辙以破天下,岂不重可痛哉!”[4]卷58,《议国是》,636从历史上看,汉高祖刘邦以不顾其亲而战,终归太公;吕郤不恤敌国而自治,终归晋惠公。所以,奉行和议,“割要害之地,奉金币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资盗粮也”。因此,只有“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才是帝王应有的“孝友之德”。[4]卷58,《议国是》,636
二是从金对宋必欲灭之的态度来看,指出卑身厚赂没有出路。
或谓强弱有常,势弱者不可不服于强。昔越王勾践卑身重赂以事吴,而后卒报其耻。今中国事势弱矣,盍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时之祸,而成将来之志乎?臣以谓不然。夫吴伐越,勾践以甲盾三百栖于会稽,遣使以行成,而吴许之。当是时,吴无灭越之志,故勾践得以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而卒报吴。今金人之于国家何如哉?上自二圣、东宫,下逮宗室之系于属籍者,悉驱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伪诏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岂复有恩于赵氏哉!虽卑身至于奉藩称臣,厚赂至于竭天下之财以予之,彼亦未足为德也,必至于混一区宇而后已。然则今日之事,法勾践尝胆枕戈之志则可,法勾践卑身厚赂之谋则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谓此也。[4]卷58,《议国是》,636-637
李纲把历史上勾践报吴之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的实际背景与宋金间相互关系作对比,认为勾践示弱以报辱,在于吴王无灭越之志,而金之于宋则必欲灭之而后已,故欲求和于金以纾祸的想法是有害无益的,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否决了议和之策后,李纲结合当时情势,提出了“国是”之说:“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姑候于可为之时”。[4]卷58,《议国是》,636李纲虽然也强调“欲措国于尊强者,非兵不可也”。[4]卷58,《议战》,642但是,以当时的国家实力来看,刚刚经历了靖康年间的大劫难,根本无力与金人大规模正面交战。所以李纲分析这种形势说:“方今当京邑残破,二圣播迁之后,国势益弱,士气益衰,而欲遽与之战,正犹病人气体未复,而欲与壮士斗,必不可也。”[4]卷58,《议战》,642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李纲提出了宜趋时之变,以武为先,益修军政,褒奖武功,振奋士气的自守之策:
俟其入寇,则多方以御之,所破城邑,徐议收复;建藩镇于河北、河东之地,置帅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军、习车战,凡捍御之术,种种具备,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时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凭陵。三数年间,生养休息,军政益修,士气渐振,将帅得人,车甲备具,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寿之休,亦将悔祸率从,而銮舆有可还之理。[4]卷58,《议国是》,636
对于自守,李纲的目标是使金人进无所掠,退不得归。为达到这个目的,李纲除了着眼于修城池、备器械、屯兵聚粮、坚壁清野、教车战以御其奔冲,习水战以击其济渡等常规的捍御之术外,更特别强调“为今日守备之策,当以河北、河东之地建藩镇,立豪杰,使自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以控扼。”[4]卷58,《议守》,643这些务守之策其实是李纲对金的一贯思想。靖康元年四月,在金人暂时退师之际,结合宋廷所割三镇军民不愿陷没金人,其势必将坚守的现状,为防秋以备金人,李纲向钦宗奏上“饬武备,修边防,勿恃其不来,当恃吾有以待之”的备边御敌八事,其中就对建藩镇、置帅府二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唐之藩镇,所以拱卫京师,故虽屡有变故,卒赖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监之,销藩镇之权,罢世袭之制。施于承平边境无事则可,在今日则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将士,习战阵相为唇齿,以捍金人,可无深入之患。又沧州与营、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势易以侵犯。宜分滨、棣、德、博,建横海军一道,如诸镇之制,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
自熙、丰以来,籍河北保甲凡五十余万,河东保甲凡二十余万。比年以来,不复阅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调发科率,逃亡流移,散为盗贼。今所存者,犹及其半。宜专遣使团结训练,令各置器甲,官为收掌,用印给之,蠲免租赋,以偿其直。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命之官,以激劝之。彼既自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逸。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4]卷46,《备边御敌八事》,536
李纲所奏是以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为议论的出发点,故所奏八事多涉及河东、河北养马监牧、开濬堤防、修治城池、优免租赋、积蓄粮草等事项,而其中又尤以建立藩镇以保家御敌为着眼点,强调其卫国守土的优势。因为从军民方面来看,河北、河东建为藩镇,择帅付之,许之世袭,且蠲免租赋,激励武艺,使之“自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逸”;从朝廷方面考虑,收租赋以养将士,习战阵相为唇齿,“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如此备御,则无金人深入之患。
然而,靖康之际,宋廷的实际状况却是敌寇当前,诸事可叹。李纲在《靖康传信录下》中悲愤地记录了朝廷面临的危局:“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皆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4]卷173《靖康传信录下》,1603但当时的宋廷上下并未对此措置防御,“大抵自贼马既退,道君还宫之后,朝廷恬然遂以为无事。方议建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台谏所论,不过指摘京、黼之党,行遣殆无虚日。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4]卷173《靖康传信录下》,1598在这种情况下,李纲奏疏所建议之事自然难以得到认同实施:
上俾宰执同议,而其间所论异同,虽建横海军一道,以安抚使总之,而藩镇之议寝;虽委提举官遵旧制教阅上户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尽行团结训练,置器甲之议不行;虽委沿边增修塘泺城池,而辅郡畿邑已降指挥,旋即罢止;虽委诸路相视监牧,而不复括马;虽放河北、河东租税,而止及一年;虽行加抬粮草钞,而贴以四分香药;虽复解盐,而地分不如旧制。[4]卷173《靖康传信录下》,1598
李纲之策既不得行,而出师援救太原,又因为节制不专、分路进兵等原因而失利,于是言者指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以及其他十罪,李纲最终落职,他的河东、河北的防御之策也就因此而搁置下来。
如前所述,靖康元年十二月宋钦宗降金,北宋灭亡。靖康二年五月宋高宗建立南宋。从时间上看,高宗即位,距离北宋的灭亡仅仅五个月;从金宋关系来看,靖康二年三月,金人扶立张邦昌大楚政权,坚决否决赵宋政权。时隔两月,高宗建立南宋政权,新朝廷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以及金人强力的威胁,其形势之严峻绝不亚于靖康之际。在这种情况下,李纲将其靖康时期未曾实施的藩镇方略再次提出,一方面可以说是对自金人入犯以来的对敌策略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为新兴政权稳步生存于艰难时世所做的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设计。
三、李纲“国是”之失败
李纲于高宗初即帝位、国家形势尚处于动乱之中出任宰相,既是时代大势使然,也是高宗全力支持倚重的结果。从新生的南宋政权所面对的时局来看,随时有金人再立北方伪政权,并强势南犯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所选任宰相的政治倾向其实也就成了南宋朝廷新的政治路线及对敌政策的方向标。在这种情况下,李纲的出任,可以说既是众望所归,也是高宗此期无主和之意的一个标志。诚如南宋吕中《中兴大事记》所说:“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宣和、靖康之祸,而开建炎、绍兴之业也与!当上即位之初,误国之臣不可用,伪命之臣不可用,张(浚)、赵(鼎)之徳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归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内用汪(伯颜)、黄(潜善),而自外召纲,则高宗之志主于恢复可见矣。观上未即位时,与公书云:‘王室多故,乘舆蒙尘。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叶济之功。’则高宗属意于公久矣。”[9]卷1,《宋高宗一》引《中兴大事记》,2然而,李纲的出任却纠结起朝廷重臣不同的对敌意见和个人的利益之争。在李纲尚未到任之前,反对之声已经兴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其时事云:
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由此与纲忤。[3] 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甲午条,120
御史中丞颜岐言:“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经筵官,置散地”……岐又请罢纲,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3] 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辛丑条,129
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乃言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报……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持劾副遗纲,封以御史台印。[3] 1册,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条,141
一方面,李纲的出任得到了高宗力排众议地强力主张与支持:“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尝欲言于渊圣,使远人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决,卿其勿辞。”[ 3] 1册,卷6,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条,141另一方面,政治倾向的相异也隐伏着李纲必然要承受的继之而来的朝廷各方势力的掣肘沮抑,以至于其施政纲领最终也因之而失败。
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李纲入相,立即以“靖康大臣主和误国”之由,谪贬了其时的主政者李邦彦、吴敏、蔡懋和使金请割地者李棁、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人。紧接着,在李纲的强力要求下,又处置了伪楚朝廷的张邦昌、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等人。高宗并手诏河东、北郡县,谕令坚守。其诏曰:
河东、河北,国之屏蔽也。朝廷岂忍轻弃?靖康间,特以金人凭陵,不得已割地赂之,将以保全宗社。而金人日横,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刼銮舆以北,则两河之地,又何割哉?方命帅遣师,以为声援,应州县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战破敌者,当授以节钺,应移用赋税,辟置将吏,并从便宜。其守臣皆迁官进职,次第录之。”[ 3] 1册,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卯,154

一日,同执政奏事内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
余奏上曰: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盛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而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阅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人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师,集于都城侧者三十余万人,其间多系召募民兵。倘择正兵之可用者,留十余万分屯要害州郡,运粮给之,以为后图,亦足以壮声势而备缓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东、河北之兵,在元帅府者,又皆援例以归,遂使行在禁旅单弱,虽旋搜裒,其势不多,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复追,而东南之人,其性轻剽,不可使之远战。耐劳苦,习战阵,惟西北之人可使。为今日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时,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乘此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戌,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夫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金人初犯阙,河北、京畿之马为之一空。其后破都城,首下令括马,而京师之马入于贼者万有余匹。今行在骑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马既无,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尺,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朝廷讨论监牧之制,修复马政,命四川茶马司益市马,责效在年岁之外,马不患乎不足,此今日不得已之务也。
国家新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县,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可横赋暴敛,科取于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劝诱,使斥其赢余,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衰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宜命州县委曲谕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务也。[4]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1625-1626

由于朝中重臣的意见不一,所以李纲在具体实施其专务守策的过程中,虽然能够得到高宗的支持,但却难免处处遇到来自于各方的阻力。黄潜善和汪伯彦是拥立高宗的重要成员,极受高宗信任。靖康元年十二月,时为康王的赵构开元帅府,靖康二年三月即以汪伯彦为元帅,黄潜善为副元帅。五月高宗即皇帝位,设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政令,就以中书侍郎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御营副使。汪、黄二人在对金策略上与李纲的务守不同,他们是主张议和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记载南宋刚刚成立之际的黄潜善、汪伯彦事迹曰:
潜善等复主议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始敌求割蒲、解,围城中许之。潜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誊赦文下河东、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其乙未丁酉所遣兵,且令屯大河之南,应机进止。[3]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条,127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给事中,充大金通问使,武功大夫赵哲领达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黄潜善、汪伯彦计,遣傅雱使金军,祈请二帝。未行,朝论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会尚书户部侍郎邵溥乞赴行在,潜善等因白用溥,溥辞,乃黜溥知单州,而更命望。[3]1册,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午条,138-139
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的方式处理新兴的南宋与金的关系,是为其后有可能的议和预设铺垫。以这种思维行事,拒绝出使者自然要受到贬黜。对于李纲的务守方略,黄潜善与汪伯颜通过高宗车驾行幸之地的确定,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左右高宗意志,最终消解了李纲的务守方略。
建炎元年七月初,有关边防军政的整治工作基本就绪,高宗车驾的去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此事,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纭,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京城,汪伯颜、黄潜善欲幸东南。李纲虑及中原之地,坚决反对巡幸东南:“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3]1册,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午,185李纲的考虑是“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委而弃之,岂惟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况治兵胜敌,以迎还二圣哉?夫江之险不如河,而南人轻脆,遇敌则溃,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他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车驾适襄、邓的主张:“为今之计,纵未能行上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愿为今冬驻跸之计,俟两河就绪,即还汴都。”[3]1册,卷7,建炎元年七月乙巳,184-185
高宗初亦有意独留中原,与金决战,故命李纲起草诏书,颁布于两京。其诏云:
朕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犯界。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已诏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国之势寖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橹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3]1册,卷7,建炎元年七月辛丑,179
然而,从当时的朝臣意向来看,黄潜善、汪伯颜皆欲奉上适东南,而群臣也多不以李纲之策为然:“时上虽用李纲议营南阳,而朝臣多以为不可。”“于是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议”。[3]1册,卷7,建炎元年七月癸丑,189高宗本来已经许李纲秋末幸南阳,但在黄潜善、汪伯颜力请之下,其意中变,遂取巡幸东南的避敌之策,而李纲以守备战的施政路线也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先是,纲为上谋,以秋末幸南阳,上许之矣。潜善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客或谓纲曰:“士论汹汹,谓东幸已决,南阳聊复耳尔,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纲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果然,吾当以去就争之。”[3]1册,卷8,建炎元年八月壬戌,198

先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才至京师,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附黄潜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当,且言所欲起北京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又言自置招抚司,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付帅司。同知枢密院事张慤素善益谦,每与之相表里。纲言:“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邪?时方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谦分析。是月甲子,命既下,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犹用其奏诘责招抚司。纲与伯彦、慤争于上前,言其不当沮抑之,以害大计。伯彦语塞而止。所方招来豪杰,以忠翊郎王彦为都统制,效用人岳飞为准备将……时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才十余日,伯彦等以为逗遛,复命东京留守宗泽节制,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属金人,而遽使亮以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恐误大事。”纲为之请,潜善等不以为然。上依违者累日。纲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职。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熟议而后行,不谓二人设心乃如此”……既而潜善有密启。翌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纲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岂难得?”纲曰:“亮谋略知勇,可以为大将,今未尝用而遽罢之,古人之用将,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语。纲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里。”纲退,闻亮竟罢,乃再章求去……遂罢纲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3]1册,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201-203
李纲在相位凡七十五日而罢,紧接着,黄潜善、汪伯彦共议罢李纲所施行之策。于是,诸路买马、劝民出财等策皆勿行。继之,傅亮以母病归同州,张所以罪贬,并于九月死于岭南,张换为乱军所杀,于是招抚、经制司皆废。九月,“黄潜善、汪伯彦共政,方决策奉上幸东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矣”[3]1册,卷9,建炎元年九月壬辰,213十月丁巳朔,高宗登舟幸淮甸。戊午,隆祐太后至扬州。癸未,高宗至扬州。金左副元帅宗维得闻高宗南幸,遂约诸军分道入犯。宗维自河阳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西京;金右副元帅宗辅与其弟宗弼自沧州渡河,攻山东,次年春攻陷青州、潍州;金陕西诸路选锋都统罗索与其副萨里罕自同州渡河攻陕西,明年正月戊子攻陷长安。从此北中国沦入旷日持久的战火涂炭之中。
[1] 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李纲.李纲全集[M].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
[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佚名,编;金少英,校补.大金吊伐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 汪藻.靖康要录笺注[M].王智勇,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8]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M]// 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9.
[10]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陈 忻]
Li Gang’s “National Affairs” and Its Failure in the First Year of Jian Yan
Chen Xin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In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Jian Yan, Zhao Gou established the regim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Li Gang became prime minister. Fac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Li Gang took the example of Jing Kang and explicitly proposed “national affairs”. Due to the different suggestions from other prime ministers, although Li Gang can get the support of the Gao Zong, in the process of his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he cannot avoid the resistance from all sides, so his “national affairs” ended in failure.
the first year of Jianyan; Li Gang; “national affairs”
2015-11-12
陈忻(1963—),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宋之交政治纷争下朝臣的创作研究》(2013YBWX091)。
K24
A
1673—0429(2016)01—0072—11
——靖康耻 血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