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伶毛世来
徐振泽
一代名伶毛世来
徐振泽

1月9日是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毛世来先生诞辰的日子,每到这样的“节令”,对京剧中那些惟妙惟肖的生旦净末丑,对那个年代戏院里金玉相击的紧锣密鼓,对当年氤氲于巷陌勾魂摄魄的皮黄之音,人们总觉得余音尚在、余温犹存。同时,对毛世来这一代的艺术大师也更加怀念。
毛世来祖籍山东,1921年生于北平,名家宝,字绍萱,父母共育有四男三女。其父毛德俊老先生虽有些文化,却始终无法改变贫寒家境。于是便陆续将长子毛庆来(家惠)、次子家乐、三子毛盛荣(家燕)送进“斌庆社”学艺,想籍此改变孩子们的人生。
三兄弟入科后,很快就表现出对京剧极高的悟性和天赋。除二哥毛家乐不幸于十二岁夭亡外,毛庆来和毛盛荣后来都成了我国京剧界名人。其中毛庆来师从俞华庭等,工武生,因其身手矫健,开打翻扑,干净利落,俊扮勾脸皆宜,曾同时为李万春、李少春这郎舅二人打下把,红极一时。毛盛荣先入“斌庆社”,后转至“富连成”四科,工武净,曾傍毛世来昆仲合演《十三妹》等。毛盛荣对京剧脸谱艺术造诣颇深,尤其对诸多前辈名家脸谱的不同笔法及不同剧目的人物勾法颇有研究。
摇篮、炼狱——“富连成”
1928年,刚满七岁的毛世来经三哥介绍进入“富连成”,这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京剧科班,由吉林富商牛子厚创办于北京,始称“喜连升”,后改为“喜连成”,其意似与牛子厚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为“喜贵”、“连贵”、“成贵”有关。1912年民清交替、市面不靖,加之牛子厚家务纷繁,无法兼顾,故将“喜连成”转让于沈氏兄弟,改称“富连成”。
从1904年开科到1948年停办,“富连成”共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近八百名京剧艺人(“庆”字科学员因停办转出),其中包括侯喜瑞(净)、马连良(生)、谭富英(生)、裘盛戎(净)、袁世海(净)、谭元寿(生)、冀韵兰(旦)等开山立派的表演艺术家。就连梅兰芳、周信芳、林树森等名家,也都曾在此带艺入科学习。
“富连成”为我国京剧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艺术家“摇篮”的美誉,然而对当年那些睡过这张“摇篮”的孩子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座炼狱。
“富连成”招收学生没有固定时间,但入学之初,不能算正式学生,而要考察一段时间,看看嗓音、相貌、身材、资质等方面是不是有“戏料”。倘若经过考核,认为无可造之处,就通知介绍人领回去。如认为可以造就,就由社方与其家长订立契约,此后,才正式取得“富连成”学生的资格,也就开始了学生们多年后都觉得不堪回首的学习生活。
旧中国有个说法,叫“棍棒出孝子,严师出高徒”,据此,在“富连成”施行体罚是很正常的事儿。毛世来生前回忆他坐科的日子时曾说:“入了科第一项是练基本功,早晨七点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都是练功时间。每天都由三位武功教师领着我们一百多人练武功。把子课、腿课和毯子功(拿顶、跑虎跳、毽子)天天必修。练功不但要吃苦遭罪,完不成功课还要挨打。挨打后当着大家的面又不能哭,可头下的小枕头却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一天的摸、爬、滚、打下来,早已筋疲力尽,半夜一上床就睡着了。因过于疲惫,不少同学经常尿床。”
为办好这个科班,从建班之初,“富连成”就订立了严格的《梨园规约》和《学规》。后来有人说在这些规约束缚下,“坐科七年就像蹲七年大狱”,这种比喻虽然难听,但也不算过分,因为学员一旦坐科就与父母脱离了关系,平时没有假期,只有每年旧历年底才放两三天假,但初一还得从家里赶回班里唱戏。学员平时不许出“富连成”社大门,外出演戏都要由管事的领着,散戏后还得整整齐齐地排好队,由管事的领回来。不管是谁,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在“富连成”出科的前一个晚上,与高盛麟翻墙出去看杨小楼、郝寿臣演出的《连环套》。第二天早晨,社长叶春善知道了此事,当即将二人带至祖师堂,不由分说便各打了二十大板。随后,叶春善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今天你们要满师出科了,按说应当对你们客气点。可是昨天晚上你们毕竟还没出科,就得守科里规矩。越墙外出犯了社规,所以刚才打你们。现在,我给你们烧香出科,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做人,永远不要做犯规的事。”
著名戏剧评论家黄裳(容鼎昌)在其所著的《旧戏新谈》中对“富连成”学员坐科的情况有过描述,虽寥寥数语,读来却令人潸然。文中写到:“十几年前,在天津念书时,曾经有一个时期每天下课后去赶看他们的戏,那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我十分喜欢李世芳、毛世来的《花田错》,当时的心目中,这真是一对璧人。散戏后,在后台看见下了装的他们,一个个委琐可怜,剃光了头,瘦削的面庞上有一对大大的含满了惊惧的眼睛,灵活地害怕地看着人。非常奇怪,在台上那么光耀的活泼的原来就是这么一批小可怜儿。”
黄裳先生这段文字补校于1948年,情景写得如此感人,足见这些“小可怜儿”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足见学员们坐科时的艰辛。
小脚一双 眼泪一缸
毛世来入科时只有七岁,但父母向人求借时那低三下四的话语,送他来学艺时的叮嘱,时刻都萦绕在他耳边,给了他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力量。在定行当时,他挺着小胸脯要学大武生,但根据其条件,科里给定了小生。后来,因那期科班缺少旦角,经萧长华总教习反复挑选,让他和李世芳、詹世辅等改学旦角。
毛世来学艺时,吃苦最多的是学“硬跷功”。刚开始练时,根本站不稳、立不直,脚趾就像针扎一般钻心的痛,脚背也火辣辣地发烧,浑身上下不住地颤抖,汗水、泪水、鼻涕一起往下流。经过半年多磨练,刚学会不扶墙行走,又开始练站方砖、站三条腿的凳子、站缸沿。窄窄的缸沿,用脚都站不稳,何况是木制的假脚呢?
毛世来在回忆录中说:“这双小小的假脚,从我学旦角开始直到出科,就像长在我脚上一样。为掌握这门技艺,我比别人多付出了几倍的艰辛,也比别人多挨了几倍的打。就连春节回家探望父母,我都得踩着跷,步行回去,到家后还要站在自家的水缸沿上听候父母训教。最后,经过师父的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努力,我终于把这门技艺学到了手。绑上跷以后,能像平常人一样,翻、扑、滚、打。在‘世字辈’中,就跷功来说,我称得上是佼佼者。”
“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之子叶盛长与毛世来原本是同科学员,在他的记忆中,毛世来不仅是“世”字班里头脑最聪明、接受能力最强的,而且还非常要强,练功的刻苦劲儿远远超过一般同学。他说毛是学花旦的,可每天都主动跟学刀马旦的同学比着练功。早晨耗顶,他总是最后一个下来,绝不肯比别人少耗。练“跷功”更是与众不同,往往是绑上跷一天也不解下来,连中午睡觉时都绑着。站三角凳耗跷时,他总好跟功底过硬的阎世善比,别人都下了凳子,他仍然咬牙坚持,站在凳子上,即便是大汗淋漓、两条腿直打哆嗦,汗水顺着裤腿往下淌,也一定要耗到世善下来他才下来。其它各项基本功他也是这么练,因此,他的功底非常扎实,一般刀马旦应工的戏,他照样能拿下来。
与毛世来同科的李世琦在回忆他们一起坐科的情况时说:我小时候入“富连成”学戏,在科里,我们无论学文还是学武的,都一块儿练功,世来师弟练得特别苦。他练功有股子狠劲,不仅练花旦应有的功,别人有的武功他都要练。比如说‘拨浪鼓子’吧,那是一种硬抢背,难度很大,一般是武生、武花脸才有,花旦并不需要练,可是他也练。世来是练什么有什么,我们都说他是天生来的灵,什么都难不住他,其实这正是他苦练的结果。他经常抓紧私下练功,所以在师兄弟中,他的功特别出色。

李世芳、尚小云、张君秋、毛世来合影
李世琦说:那时候花旦讲究踩跷,练跷功。不但在地上跑圆场、打把子,还要站在大板凳上练。板凳也就半尺来宽、三尺多长,脚上绑着跷板,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脚尖上,站在地上都吃不消,站在板凳上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当时与世来师弟一起练跷功的还有江世玉、贾世珍、王世祥等,几个人站在一条板凳上练,一站就是一个小时。每次在板凳上练跷功,世来总是超过规定的时间。后来江世玉他们改了小生,就不练跷功了,世来一直努力不懈,最后终于练到踩着跷跑圆场、打把子都很自如的程度。
在叶盛长、李世琦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跷功”,现在很多人在谈及毛世来时也都会联想起这项解放后一度被取缔的技艺,其原因是毛世来的艺术成就确实与“跷功”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全部,却有“毛因跷而红,跷由毛而承”之说。
京剧的“跷功”,又称“踩寸子”,乃我国戏曲艺术中的绝响之技,其中京剧“跷功”被认为是该剧种所有艺能中最难习练、最不易做好的功课,更是花旦表演中的特技。跷功的缘起是该剧种早年几乎都是男旦,在饰演女性角色时,即使演员对旦角的四功五法掌握和表现得再精妙,裙子下那双男人的大脚也着实大煞风景,这种情况对不能穿长裙、盖不住脚面的武旦尤为突出。为此,戏曲前辈发明了“踩寸子”,即蹬上一双木制“小脚”,将脚掌绑在上面,再套上跷鞋。脚下踩了寸子后,人的重心提高,身姿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尤显女性之柔媚。但观众们看到的只是这种东方芭蕾的精彩,却不知背后那“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滋味。为了塑造那纤纤“金莲”,演员几乎要把脚尖朝下插在跷内,然后用绑带把脚背同木芯牢牢扎紧,腿部和脚腕子都要绷直,脚跟不能落地,比跳芭蕾舞的难度还大。
到毛世来这代人学习踩跷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改进,不少花旦、武旦戏中,已揉入了为展示“跷功”而定制的情节,其间,演员常以一双木跷,踩在桌沿、椅背等“立锥之地”上表演。一次,毛世来在演出《辛安驿》时,带红扎手执单刀踩着硬跷走“矮子”,两只脚的跷尖轮流踢到平伸出去拿刀的双手,获得满堂彩,连同行也都叹为观止。
博采众长 少有所成
“师父”是毛世来坐科期间,甚至是他一生中感到最温暖的两个字。入科不久,“富连成”总教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肖长华就叮嘱萧莲芳说:“毛小五儿开窍得早,浑身是戏,将来可以大成,也能小就,你们要好好调教他。”此后,毛世来先后拜萧连芳、尚小云、荀慧生、梅兰芳、徐碧云、芙蓉草(赵桐珊)等为师,其中就包括我国京剧“四大名旦”中的三位,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毛世来如果不红,天都不红”。
旧社会师徒关系与现在不同,那时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拿手戏和绝技,如果他们把这些传给弟子,自己不仅不能再演,还要通过助演以及凭借自己的人脉,将弟子捧红。这就是“宁舍二亩地,不教一出戏”的缘由。但毛世来的几位师父却都能舍出自己的饭碗,把看家的本事传授给他。而且又都是在其门下学成后,将毛世来推荐给其他名师。
通过翻阅早年的报刊可以查得,尚小云就曾经与毛世来合演过《娟娟》,戏中,毛世来扮演娟娟,而尚小云则甘当配角。荀慧生也曾经与毛世来合演过《棋盘山》,由毛世来扮演薛金莲。关于尚小云带毛世来去赵桐珊家拜师的过程,更是一段梨园佳话。
一天,尚小云拉着毛世来的手来到赵家,尚与赵当年曾同在“正乐社”,与荀慧生并称“正乐三杰”,交情颇深。进门后,尚小云直截了当地说:“给你送来一个徒弟,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随后又“得寸进尺”地说:“《辛安驿》这出戏是你的拿手好戏,我不会,你必须得教给他。”
在几位师父的调教下,毛世来博取强记,择善而从,终将各家之长融入自己的表演艺术之中。
1929年,毛世来入科未满一年,就披挂上阵,开始在“盛”字班师哥面前唱帽儿戏。虽然起初只能当配角、跑龙套,却能把一个个小角色演得玲珑剔透、活泼可爱。不仅深受观众喜爱,还常常得到师父的赏钱。几年后,毛世来逐渐成了科里的小名角儿。此间,“富连成”的“盛”字科祸不单行,接连发生了许盛玉十四岁夭折、仲盛珍十九岁早亡的事儿。随后,李盛藻等人又离开了“富连成”,使得毛世来过早地挑起了重担,成了“富连成”的台柱子。好在他不负众望,不仅完成了承上启下的任务,也使自己的艺术水平和名气有了提升。
到1936年,毛世来已成为京城名角儿。那时毛世来给人的印象是娇小婀娜,明眸善睐,嗓音清亮,扮相俊俏,白口清丽干脆,做表入戏传神。他跷功极佳,以能唱擅做、文武兼备名盛一时。他尤擅演花旦戏,每个角色都楚楚动人,其眉目颇似尚小云,做工则近似荀慧生,又享有“小筱翠花”之誉。特别可贵的是,他在继承老师及前辈艺人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跷功、扑跌技艺,以及婀娜娴熟、玲珑娇巧的艺术风格。
伴随着毛世来的发展与成长,不仅观众中出现了“饽饽党”等捧毛集团,媒体也对其日益关注。著名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景孤血,当年在看过毛世来演出后写到:“毛世来《战宛城》邹氏下场的走,与《翠屏山》潘巧云的漫步,一个是孀居贵妇,愁眉蹙额,仍不失娴雅修嫣的走。一个是柳颤莺娇,春情冶荡,纵意所如的走。两者身份不同,心情有异,所以走法轻艳侧丽,自然有了差别。”通过景孤血的评论,人们领会到毛世来的表演确实是研精覃奥,仿佛用一双脚跟就能把心事传了。
在受到这些褒奖时,毛世来才十五六岁,真可谓少年有成。
“四小名旦” 一笑倾城
毛世来成功了,他与他们这批童伶的出现,不仅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京剧舞台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而且还使观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少年汇入了戏迷行列,他们经常夹着书包放学后去看戏,其中为数不少是来自北京大学等名校的学生。当时与毛世来齐名的童伶有李世芳、宋德珠等,他们各有自己的“粉丝”,数量不相上下。于是,有些戏迷就给报社写信,要求像当年《顺天时报》评选“四大名旦”一样,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四小名旦”。
1936年,北京《立言报》发起童伶选举,候选人只限于“富连成”和中华戏曲学校的学生。选举搞得很认真,由《立言报》社长金达志和主编吴宗佑接待选票,聘请北京几家报馆负责人监点票数。选举结果是李世芳以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四票夺魁,毛世来以一万两千五百六十一票获得“旦部冠军”,王金路、裘盛戎、詹世辅分别获得了生部、净部、丑部冠军。旦部的第二至第四名为侯玉兰、宋德珠、白玉薇。
1937年1月,北平各界名人、梨园名家与两校师生齐聚“富连成”,为当选者颁奖,毛世来所获奖杯上刻着“旦部冠军毛世来艺员”,中间还有四个大字——“娇媚天成”。
童伶选举尽管公开、透明,但也有微词。有人觉得“旦部冠军”应当由正工青衣膺选,起码也得是“花衫子”,现在由花旦鳌头独占,实难甘服。对此,吴宗佑不得不公开了一封信,以证明选举结果的真实性。此信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位要员写给《立言报》社长金达志的。称其打算购买十万份《立言报》,把报上的选票全数投给毛世来,让他荣登童伶主席宝座。吴接到此信,仓皇无计,求救于齐如山、徐汉生、吴菊痴等人,大家都以为不可,只好顶着压力,拖到最后,才使这次活动有了一个正常结果。
毛世来的同科师弟小武旦班世超对选举结果的评论则是:“毛师哥上跷之后,不但蹈蹈自如刚健婀娜,一曲《飞飞飞》宛若素蝶穿花,栩栩款款。他得了旦部冠军,是实至名归,要是有人还不服气,那简直是自不量力了。”
童伶选举结束后,北平戏迷余兴未减,其中一个动议就是单独推选“四小名旦”。此事酝酿了好长时间,直到1940年,在吴宗佑主编与新新大戏院经理万子和主持下,由毛世来等人联袂演出的《白蛇传》终于在长安大戏院登场。演出中,李世芳与宋德珠演《金山寺》、毛世来演《断桥》、李世芳演《产子》、张君秋演《祭塔》。由于在连贯的剧情中,几位“白蛇、青蛇”唱念做打皆别具一格,各有千秋,使台下的观众过足了瘾,掌声和报好声自始至终未间断。这次演出轰动了北京,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从此,“四小名旦”声名鹊起,个个红得发紫,这个称号也逐渐为国人接受,不过这次活动与童伶选举确实是两码事。
1947年,因李世芳在一场空难中不幸去世,北京《纪事报》又举办过一次“新四小名旦”选举,张君秋、毛世来、陈永玲、许翰英等四人当选,但由于活动影响不大,所以“新四小名旦”的反响似乎不如当初强烈。
1938年3月3日,毛世来在“富连成”正式出科。当时中国京剧界的规矩是北平出科的艺人,首先要去上海滩“闯关”。如果在上海唱红了,就可以回北平,否则就只能搭野台子跑江湖了。
毛世来去上海“闯关”获得了巨大成功,几天后黄金大戏院门前的海报和当地许多报纸上便出现了他的大名。继首演《英烈传》后,他相继演出了《十三妹》、《穆桂英》等大戏。毛世来的演出让挑剔的上海观众为之倾倒,唱了一个月,红了三十天,竟然与戏院签下了第二年再次赴沪的演出合同。此间,有媒体盛赞毛世来“红遍春申,一笑倾城”。
毛世来在上海的成功主要是自身确有实力,但与李万春鼎力相助也有直接关系。当时毛世来的大哥毛庆来正在李万春的“永春社”搭班,是李万春最合手的武打下串。为此,在毛世来“闯关”过程中,李万春不仅为其置办行头、大肆渲染,还在演出中为其配戏。有资料记载,在毛到上海首演《英烈传》时,毛世来前面踩跷,已使所扮之陈秀英绝妙可人,后又按剧情女扮男装,以大靠厚底,与李万春所饰王富刚对打,其中仅一个大刀在其左掌垂直旋转五百四十度的托月,就引出满堂彩,使得毛世来一炮走红。
在上海“闯关”成功后,年仅十八岁的毛世来返回北平,开始组建自己的“和平社”,由于有徐兰沅(谭鑫培、梅兰芳之琴师,时为广德楼戏院大股东)先生支持,又有袁世海、高盛麟、张连廷、裘盛戎、江世玉、艾世菊等诸多师兄弟助阵,和平社顺风顺水扯起了大旗。
5月初,和平社在吉祥园首演《大英烈传》,深受观众欢迎。从此,和平社不仅在北平站稳了脚,而且还经常去天津、沈阳、上海、青岛等地巡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此间,和平社打出“四小名旦之一 荀派文武花衫”的旗号,毛世来也挂上了头牌。
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毛世来又相继拜几位名家为师,且有百余出戏烂熟于心,使其每到一地或有新戏推出,皆好评如潮。更有人在看到电影对京剧的冲击后,一度将京剧“振兴”寄于毛世来等人身上。有文章曾言:“继四大名旦之后者,非世来莫属……仍望努力迈进,毋固步自封,俾江河日下之国剧,能有中兴之望也,万春世来勉乎哉。”

1936年,梅兰芳收徒李世芳、毛世来合影。
解放后,和平社改为“民营公助”的“北京市和平京剧团”,毛任团长。
1958年8月,毛世来率和平京剧团骨干调往吉林省,组建省京剧团,为吉林京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9年毛世来被调往吉林省戏曲学校任副校长。
“文革”时期,毛世来受到迫害,1969年携全家到吉林省永吉县插队落户。
1978年落实政策调回长春,翌年,在指导学生拍戏时,突患脑血栓。但在此后十多年里,一直带病传授京剧表演艺术,直到1994年12月19日病逝。

毛世来饰演《玉堂春》中的苏三
毛世来出身寒门,七岁入科,他朝乾夕惕,终以泪水与汗水,使自己成为妙龄驰誉的“四小名旦”之一,在菊坛大放异彩。他十八岁组建和平社,其胆识、其才干,以及所获得的成功,不能不令人仰视而观止。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继承、创造,并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艺术珍宝。他的后半生时运多舛,但虽处江湖之远却未寒报国之心,插队期间,他曾以靰鞡为跷、以羊鞭代矛,构想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以期将宝贵的文化遗产传于后人,振兴祖国的京剧事业。
先生走了,尽管其人生让我们看到了一颗燃尽能量之星划破天际的壮美,但总会让人黯然神伤。
1999年,黄宗江先生出版了《戏痴说戏》一书,其序言中讲诉毛世来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书中写道:“毛世来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可是在当年的中学生,如我辈心中,实在是光彩夺目的璧人,一提起他,依旧能唤醒儿时的温馨旧梦。”这种旧梦,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曾经”。
一种事物、一段人生,只要有过毛公这样的“曾经”:曾经让脸上的墨彩成为民族文化一笔;曾经让自己的辛酸给亿万人民带来思索与欢乐;曾经展现过令人仰慕的瑰丽与辉煌,就可谓足矣。因为一切事物,本来就只有“曾经”,哪里会有永远。京剧亦然、毛世来先生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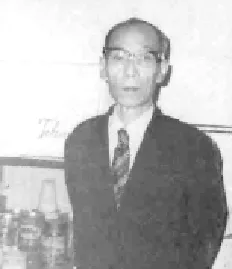
晚年的毛世来在女儿家
——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