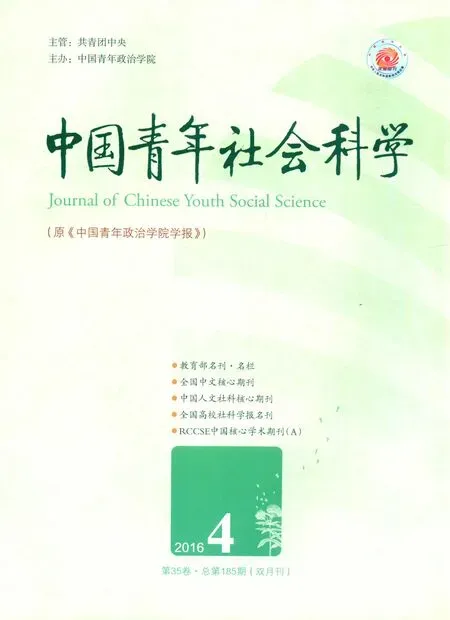青年人力资本积累与内生经济增长
■ 谭祖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9)
青年人力资本积累与内生经济增长
■ 谭祖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尽管主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知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内生路径,但是人力资本积累才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诸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重大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实施,归根到底都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质量和规模。政府应当加快调整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加大产业内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对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投资,改革现有的学校职业教育体制。
【关键词】青年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经济转型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度变迁和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完全走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增长轨道,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所谓“内生经济增长”,实质上就是“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是青年,因此,青年人力资本积累决定了内生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概念框架,研究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人力资本因素,探讨青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Thodore W. Schults(1961,1971, 1972)在其《人力资本投资》的著名演说及其随后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Schults认为,人力资本是技能的集合,是人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超过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并且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Gary S.Becker(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人格化的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及拥有的时间、健康和寿命,都是人力资本构成的基本要素[2]。在Becker的著作《人力资本》的微观经济分析中,接受教育、培训、医疗、维生素摄入,从经济系统中获取信息,都能够提高个体的生理和心理能力,进而提高预期真实收入。
Arrow(1962) 首次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并引入人力资本思想,建立了“干中学”经济增长模型[3]。模型假定凝结在资本品中的“技术”在资本品存续期内是不变的,其产出能力的上升是积累经验(学习)的结果,而经验的载体是人力资本。Paul M. Romer (1986)总结了传统的Ramsey-Cass-Koopmans增长模型和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有形资本的“知识”资本概念[4]。Romer的“知识”资本概念及其特性与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特征极为相似,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Robert E. Lucas(1988)在传统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1956)[5]中引入人力资本因素,以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式解释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6]。Lucas将个体人力资本简单定义为一般技能水平,将人力资本积累的两种不同模式分别定义为Schults强调的“教育”和Arrow强调的“干中学”。利用Romer的“知识”外部性假设,将人力资本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利用人力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假设,构造人力资本积累方程。
Christian Dustmann , Itzhak Fadlon, Yoram Weiss( 2011)建立了技能人力资本模型,证明不同的人力资本技能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价格和租金[7]。因此,人才外流效应(Brain drain effect)可能缓解甚至逆转,出现人才流入效应(brain gain effect)。这对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达成了若干共识:人力资本是最重要、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特性;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或路径存在多样性;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公共教育投资和私人教育投资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产权制度安排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的个性特征影响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及其价格构成;不同国家差异化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人力资本价格会导致人力资本流动。
二、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概念框架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一个经济范畴。如果以“人力资本”来代替“劳动力”要素,以“物质资本”代替其他要素,那么各种形式的生产函数都可以用一个更加一般化的二元生产函数来表示。其中,人力资本是最基本、最能动的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决定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具体而言,货币资本、机械设备等都是人力资本生产出来的,即使自然资源也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去开发才能利用,特别是生产技术,更是直接由人力资本发明、创造出来的,所以,人力资本积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进而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青年人力资本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力资本年龄阶段的概念。它是指已经进入法定劳动年龄,且具备了社会生产能力(体力、知识和技能),已经进入了生产过程,但是还必须通过学习和训练,进一步积累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才能提高其生产效率的群体。此处的“青年”是指学习能力处于上升时期,能够预见到通过学习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获取更高的期望收益的群体。青年人力资本具有四个特征:(1)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并已经进入生产过程;(2)学习能力处于上升时期;(3)必须进一步积累知识和提高专业技能;(4)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期望收益。
所谓“青年人力资本积累”,是指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性投资(主要通过增加教育、学习和培训的物质资本投入以及人力资本自身的机会成本投入),更新和增加青年人力资本的知识存量,并提高其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过程。
三、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人力资本因素
经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共同特征,是将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将技术进步归因于投资本身。换言之,正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推动了技术进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投资引致的“知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研究与开发(R&D)成果,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带来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资本的边际产品非递减。
学术界对上述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宏观模型尚未深入分析知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R&D的具体形式及作用机制。尽管在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 (2002)建立的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中,有技术性前沿知识、个性化内在知识和非个性化公共知识之分,还强调了技术应用的人力资本基础和二者之间的动态互补性[8]。但是,将“技术”与“人力资本”作为对等范畴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其合理性值得怀疑。虽然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分析了技术与劳动者技能的匹配程度不同带来的生产率差异[9],Stephen Kosempel (2004)也分析了技术的适应性问题[10],但仍然缺乏对于技术实现和技术匹配的人力资本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考察。Daron Acemoglu (2002,2003)[11]和Charles Jones (2005)[12]关于技术演进方向的研究,重点分析了技术进步是劳动扩张型的还是资本扩张型的,同时也试图证明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自主选择技术进步方向的基本原则。其研究结果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由投资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反过来会影响投资结构。然而,有些技术进步表现为投资过程或者投资结果,而新技术的应用又会引起劳动力扩张或资本扩张。
知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R&D,都是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路径。关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研究,以及关于技术演进方向的研究,的确也拓展了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领域。但是,知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R&D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值得深入考察,它们可能仅仅是内生技术进步同一机制的不同侧面,而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其共同基础。
如果将资本分为两大类,即物质资本(pphy)和人力资本(phr),那么产出(国民收入)(y)就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函数。物质资本积累是投资(i)的函数(假设投资等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是投资和人口(n)的函数。投资源于储蓄(s)(假设投资等于储蓄),储蓄又是国民收入的函数。同时,将人口增长看作消费(c)的函数,而消费也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于是,整个经济就成了一个内生的自我循环体系,它可以用下面的一组函数来表达:Y=f(kphy,khr) ;kphy=s;s=g(y);khr=Φ(kphy,n);n=Ψ(c);c=η(y)。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及其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是在经济的自我循环过程中实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技术进步?也就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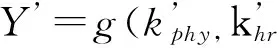
上述四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都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本质因素。换言之,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人力资本所内含的知识和技术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是存量又是流量。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干中学”特性。人力资本在其使用过程中具有自动学习功能、自主创新功能和自我增值功能。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是价值增值,而不是价值转移。人力资本的“干中学”特性不仅能够克服其作为资本的折旧问题,而且能够自我更新并不断提高其边际产出。物化于更新换代的资本设备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各种R&D 的研发成果,都是以物质资本为条件的人力资本的创新结果。资本设备或产品内含的技术是静态的,资本设备物质载体的消耗即为折旧,纯粹消费品的技术含量也不再具有生产性意义。只有再次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才能提高资本设备或产品的技术水平,从而加快资本设备的“精神折旧”或更新换代速度,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
一定的技术条件决定了要素配置方式,而技术是人力资本的创新成果。要素配置方式与制度因素有关,但制度变革也是人力资本的创新结果。所以,要素配置方式即生产过程中要素的结合方式,归根到底是由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决定的。随着人力资本专用性不断增强,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基于产品的产业量和价值链不断延展,人力资本向R&D和市场营销环节集聚。换言之,人力资本向产业链的动态创新环节集聚。因此,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反过来深刻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四、青年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是创新的结果,而创新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经济要实现成功转型,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中国制造2025”;也无论是“互联网+”战略,还是“智慧城市”目标,归根到底,必须转变为创新经济。转变为创新经济的首要条件是人力资本积累,特别是青年人力资本积累。
“供给侧改革”是供求结构调整,不但要减少过剩供给,而且要满足有效需求。因此,“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青年人力资本的结构调整问题。一方面要依赖青年人力资本从事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新流程,以及新管理方式和新营销模式的研究与开发;另一方面,要实现生产的集约化,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大幅度提高,这将会在行业内形成大量剩余人力资本。这部分剩余人力资本必须退出该行业而进入其他行业。然而,现代分工和专业化体系下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从一个行业退出并转入另外一个行业,其原有的经验和专业技能会遭受“精神贬值”,必须经过重新学习和培训实现“部分人力资本更新”。因此,留存于行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的研发活动和转移出本行业的剩余人力资本更新,都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而且主要是青年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从技术角度来看,“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主要目标。该战略包括四个关键环节:(1)制造业装备(资本设备)智能化;(2)产品更新;(3)人力资本与智能化资本设备的技术匹配;(4)人力资本转移。
制造业装备智能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改造。它是要运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装备工业革命。它与传统工业的标准化生产不同,必须实现个性化产品的社会化生产,所以,智能制造的装备必须是基于个性化需求和差异化产品的“柔性”智能生产线。智能化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首要条件,这主要依靠具有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力资本。
原生需求结构升级拉动引致需求结构升级,是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需求结构升级要求市场提供新的消费品满足新的消费需求,提供新的投资品(尤其是新的生产设备)满足生产需求。必须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进行新产品研发。产品研发也是个性化、差异化和柔性化的。
人力资本与智能化资本设备的匹配,主要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内含既定技术的资本设备(生产线)与其操作和控制人员的技术匹配。具体而言,要求处于生产环节的工人掌握智能设备的技术性能和产品的技术要求,能够熟练操控生产过程,及时处理各种技术故障,确保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尽管进入生产过程的智能设备内含既定的静态物化技术,但是与其匹配的人力资本仍然需要经历从“非熟练”到“半熟练”再到“熟练”的技术学习过程。这种“干中学”本身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由传统机械制造向现代智能制造转变,与智能装备匹配的人力资本,必须是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和很强学习能力的青年人力资本。
智能制造会带来人力资本的内外转移问题。在行业内部,人力资本会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首端研发(R&D)环节和末端营销环节转移、集聚。由于智能制造环节的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使与智能化生产线匹配的技术人员的需求大量减少,既不能与之匹配也不能向两端转移的人力资本将被迫退出该行业。行业内部的人力资本前后向集聚,并不是简单的人力资本转移。它不仅包括行业内原有人力资本的重新分布,还包括本不属于该行业的人力资本的进入。同时,退出该行业的人力资本中,一部分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青年人力资本在更新之后进入其他行业,另一部分未能实现“成功转型”的人力资本会处于失业状态。
“互联网+”战略的实质,是要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技术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要实现三大产业内部的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战略是基于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创新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创新必须依靠青年人力资本积累。“互联网+”集中表现为各次产业的信息化。当前中国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产业当属农业。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程度还很低。农业信息化依赖于农村青年对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所以,农村青年人力资本积累是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智慧城市”的核心内容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具有规模经济及自然垄断的特征。政府是其投资和供给主体。现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网络化水平,关键是如何实现智能化。现有“硬件”基础上的 “软件”智能化改造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本身的智能化,更是营运、使用和管理的智能化,所以,它包含设施和产品创新、营运模式创新、管理方式创新、使用方法创新等。无论投资主体是谁,所有这些创新都依赖于青年人力资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五、结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它将技术进步的原因内生化为经济体内对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R&D活动的投资。进一步考察技术进步的不同方式和路径,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基础,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的创新过程和结果。创新主要由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且预期获得更高收益的青年人力资本来实现,所以,青年人力资本积累是内生增长机制中的关键变量。
青年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的转型至关重要。“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各种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都依赖于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质量和规模。
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必须进行政策调整。(1)要加大产业内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特别是要提高研发和营销环节的人力资本投资比例。随着人力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效应增强,逐渐具备了“公共资本”性质,所以,行业内人力资本积累的投资主体,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以外,还应该包括追求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政府。(2)要增加对青年人力资本积累的投资。既要通过投资使其具备共同知识、学习能力、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也要采取合适的人口政策保持适当的人口增长率,还要具备适当的医疗卫生条件和福利保障措施保持其生理和心理健康。(3)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只局限于学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主要形成人力资本的共有知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主要是在进入生产领域之后才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其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技能对于创新更加重要。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或减税等方式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用于在岗人力资本的继续教育。(4)改革现有学校职业教育体制。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模式,无论是在初等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都鼓励企业和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实行分类分级职业技能训练。
[ 参 考 文 献 ]
[1]Thodore W. Schult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 March 1961, 1-17.
[2]Gary.s.Becker,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NBER,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3]Kenneth J.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29: 153-173
[4]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5 (Oct., 1986), pp.1002-1037
[5]Robert M.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56: 65-94
[6]Robert E. Lucas,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 ,3-42.
[7]Christian Dustmann , Itzhak Fadlon, Yoram Weiss,Return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rain Dra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5(2011) 58-67.
[8]Huw Lloyd-Ellis and Joanne Roberts,Twin Engines of Growth: Skills and Technology as Equal Partners in Balance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2,7(2):87-115.
[9]Daron Acemoglu and Zilibotti F.,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2):563-606.
[10]Stephen Kosempel, Theory of Development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5: 201-220.
[11]Daron Acemoglu,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4):781-810.
[12]Charles Jones, Growth and Ideas,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 2005,1B:1063-1111.
(责任编辑:任天成)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谭祖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重大项目“青年人力资本积累与内生经济增长”(课题编号:1890605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