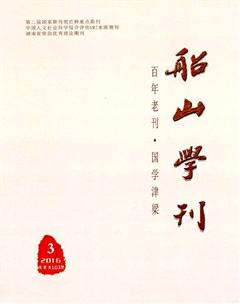王夫之与古代画学之道
谭媛元+郑林生
摘 要: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虽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但诗画一律,其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论析王夫之诗论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神理论”与“象外说”等艺术观点与古代画学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其诗学理论的意蕴,也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为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代画学;天人合一;神理论;象外说
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美学思想蕴含于他的诗学、文学、史学等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以儒学为宗,吸收孔孟儒家美学思想的精华,批判继承了道教与佛家美学的合理部分,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集大成者。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不仅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古代画学之道有着内在联系。
除了叶朗等少数美学研究学者外,许多学者对于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研究多限于史学、文学等领域,对他的美学理论却少有关注。尽管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诗论著作中,但“诗画本一律”①,诗画同理。诗与画两者虽表现形式相异,从深层次的本质上却具有共识性,精神有着共通性,诗学与画学也可以互参互见。正如苏东坡曾在《东坡题跋》中所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歌以“言志”、“缘情”为要义,情与景、形与神、意与象构成诗中意境。在中国传统画论中,也强调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天人合一②、象外之意等,并运用于人物品评、景物描写、艺术作品评论中,成为中国画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准则,因而王夫之美学思想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
一、 天人合一
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来探讨美学,并且比前人更深入具体,这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是具有独特性的。自古以来,中国古典哲学一直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与自然、社会的合一,心与物的亲和。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观,“太和,和之至也。” ③认为“和”是宇宙太和之气的本色,强调以“气”为本,以“气”解释“天”与“人”,认为天乃自然之天,“气”乃万物之始,人与自然万物皆同质于太和之气。“气”为“阴阳二气”④,阴阳二气形成气象万千的自然,而阴阳二气变化运作产生万物的过程称之为“气化”⑤,意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天之象,地之形,皆在其范围内。这如同中国传统画学论中所言的“气韵生动”“阴阳相生”“贯通一气”。中国画学认为艺术作品传达的是“生气”,是体现自然物象的精神与神动。例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提出“六法”⑥,把“气韵生动”放在首位,推崇生命运动之“气”的节奏与韵律。气韵就是画面的精神气质,即画面描绘世间万象具有动态的生命,达到形似神似,以空灵淡远的意境美感去体悟内在精神。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强调过于重视形似,则会失去画面的“气韵”⑦,五代荆浩列出绘画创作六大要素为“气”“韵”“思”“景”“笔”“墨”。⑧元代杨维桢在为夏文彦《图绘宝鉴》作序时提到艺术作品要达到传神,则需要“气韵生动”⑨。清代画家石涛用“贯通一气”⑩来描述绘画中的意境,认为绘画作品中的意境与“气”是一种本然性,画中景物,是“气”化的产物,笔墨则是“气”的传达。因此,古代画学强调“气韵”,认为“气”是构成画面“天人合一”意境的重要因素。
王夫之认为自然万物的合一,人与自然、心与物的和谐统一,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艺术而言,各种不同的审美要素和谐统一才构成了艺术之美,他以诗歌为例,提出诗歌是兴、观、群、怨四大审美要素和谐统一,而绘画则是各种不同颜色物象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源于人乃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的智慧情感和精神生命都依赖于自然,人的情感离不开身边万物,简而言之就是情与景的关系,“情”与“景”构成了“天人合一”之意境的存在。景是客观的,情是主观的,主观与客观的相统一,也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王夫之认为“在物者为景,在心者为情”,情与景有“在心”“在物”之分,情与景的关系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即景会心”?,曾言“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即情景互生?,艺术家在审美过程中触景生情,内心主观情感对客观景物进行感知,并伴随着作者的想象,对山川树木、烟云泉石、花鸟丛林等进行联想,从而抒发情感。因此,艺术作品中的景是饱含作者情感的,而情感是由景物触动而产生的,情中景,景中情,情景互生。关于情与景的关系,王夫之还强调情景交融的关系,曾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即在创作中“景”脱离“情”,则成了“虚景”,“情”脱离了“景”,“情”也成了“虚情”。只有情与景相互转化交融,情因景的融入而有了外观,景因情的渗透而有了生命,情与景结合得“妙和无垠”便是情景交融的最高境界,这是王夫之所欣赏与追求的审美取向,是他衡量艺术性的美学标准,也是意境生成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画学理论中同样如此,画家布颜图曾在《画学心法问答》有言:“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正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中国画透过描绘景物营造意境,以此表达情感,也要求笔与墨合,心与物合、情与景合,情景互生,情景交融。
此外,王夫之指出艺术创作达到“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重要方法是“阅物多”,亲身体验观察。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艺术创作对自然界的反映是“心目之所及”,即通过“心目相取”?,以瞬间的直接感知并带着作者的主观感情,不需要比较推理,来描绘客观真实的“物”,把自然界中固有存在的美感完整的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的审美意境。这也是王夫之“现量说”?的运用,即审美意象需要从直接的审美观照中产生,优秀的艺术作品出自艺术家对现实生活与自然景象的亲身经历,以及独特的个性感受,如润物细雨无声般自然真实,并且强调形式的独立性,即景会心的直观感知,反对形式主义,认为“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即在艺术领域中不应该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内,只有置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体会与感悟生活真谛,才能创造出优秀作品。诗歌与绘画,均为真实的直观感悟与情感流露之作,用以描绘事物与情感的方式,其审美意象需要直接从审美观照中产生。清代画家石涛就曾说过“搜尽奇峰打草稿”,宋代画院画家也强调写生为本,创作的前提就是王夫之所言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画者没有直接的产生对物象的审美观照,则不能构成审美意象,也无法达到情景统一。endprint
二、 神理论
“神”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是一个传统概念,许多美学言论中都有关于“神”的论点,中国哲学领域的“形神说”在战国末期至两汉较为成熟,并在魏晋时期进入美学领域,成为中国传统画学理论的审美概念。魏晋南北朝是古代画学论的奠基时期,并初步形成“形神兼备”的形神观。顾恺之曾在《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美学观点,即不在乎对外在形象的描绘,而是把传达内在的“神”作为描绘人物神态气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判断人物画优劣的标准。南朝宗炳将“神”融入山水画评论与创作的范畴中,在《画山水序》中强调“应会感神”,提出“山水以形媚道”、“澄怀观道”的山水“畅神”说。即山水乃自然造化的产物,山水之游是领悟天地之道的过程,画家在山水画创作时不仅描绘自然万物,而且参化生命玄机,抒发内心情感,具有内在神趣。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写意传神,赋予画面物象生命,正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画之六法,指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这强调绘画中要融会自己的精神意趣来达到形神兼备。宋元文人画更加注重神似,追求超乎对象“形似”之外的画之传神,强调内心情感的表达。苏轼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元代汤垕《画鉴》中把“传神”作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到了明清时期,对于形神关系更为注重,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指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胸中有丘壑,绘出山水“传神”之态。山水本身没有情感,但却能给予观者内心精神感受,因此山水画创作需要多游历,通过对山水物象的传神描绘,寄情山水,抒发情感。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一卷也专论传神。由此可见,古代传神论的发展历程,是从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到以神写形,形神结合,逐渐对“神”加以重视。
王夫之继承了顾恺之、苏轼等人的美学观点,常以“神”、“神化”来评论已达天然之妙的诗歌作品,把气的运动变化言为“神化”,认为“其妙万物而不主故常者,则谓之神。”如他在评唐寅《落花》一诗中写道:“传神写照。”?评李白诗《春日独酌》:“神化冥合,非以象取。”?评刘庭芝的《公子行》:“脉行肉里,神寄影中,巧参化工,非复有笔墨之气。”?可见他吸取了古代画学中关于神似的描述,认为诗歌创作也需要“神寄影中”,要“取神似于离合之间”,所以要“脱形写影”,这里的“脱形”“神寄影中”是指取形之外,即指“取境”,而“境”的产生是形与神统一的产物,这要求艺术创作是符合于形,又超越于形来达到神似,表现内在本质与生命气象,这也体现了古代画学中的形神兼备。可见,王夫之在评论诗歌中的神论所传达出的美学意义与传统画学理论是一脉相承密切相连的。不仅如此,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出发,对形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神似”需要从心出发,深入生活、观察对象特征,更提出“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21)的美学观点。即要求作者善于捕捉瞬间即逝的灵感,抓住事物本质后追求神似,即形神统一。正如他用绘画举例所言:“两间生物之妙,正以神形合一,得神于形而形无非神者,为人物而异鬼神。若独有恍惚,则聪明去其耳目矣。譬如画者固以笔锋墨气曲尽神理,乃有笔墨而无物体,则更无物矣。”(22)可见“形似”是“神似”的基础,即“得神于形”,只存在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而没有生命的灵动,则是有形无神;反之没有客观的审美主体,神韵则无所寄托,因此形神是辩证统一的,艺术创作不应该停留于“形似”或者单纯追求“神韵”,而是把握住客观形体后,对所感知的物象进行合理取舍,把似与不似相统一,即王夫之所言:“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从形似到神似,从有形到无形,形与神合一,超越有限,进入无限,超以象外,与生命相通,才能呈现无限生机,这也是画论中所言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古代画学重神,是对生命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视,强调超凡脱俗,神与天地万物相结合达到天人合一,因而形神关系也是天与人的关系,内心与物象的关系,也是王夫之“体物得神”的观念体现。
王夫之对神论观的创新性在于他提出的“神理”论,“神理”中的“理”,不是神秘莫测之理,而是把握物象客观规律,是形象思维内在的逻辑与道理,即“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此处“近”乃写景状物,如在眼前,“远”则是指代艺术作品中意境深远,形象鲜明生动引人深思。王夫之从绘画角度出发,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神理”的作用,画者所描绘的景物需要生动逼真,就需“以神理相取”,探求事物内在本质生命意态,如此才能传神写照。此观点与古代画学中强调的“穷理”“取真”相似,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23)便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观点,度是审度之意,取其真即图真,中国画不是单纯的对自然的描摹,而是描绘物象的内在精神气质,形似与神似的统一,着眼于整个自然,追求内在思想精神的天然流露。他从“真”的角度,讨论水墨存在的理由,认为“真”是追求自然的本真即物象内在的生命力,指出传统绘画观念中“画者,华也。”丹青妙色所表现的“华”或许只能表现外在形象的“苟似”;而“画者,画也”,是图真,表现的是大千世界的生命真实性。明代董其昌《画旨》中也谈论到:“朝起看云气变幻,可收入笔端。”(24)强调观物体察,探究物象内在生命气象。明末清初画家恽南田认为绘画需要注重“元真气象”,即归复生命的本真。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善于画竹,同样得益于他善于对物象的观察,对实景的真实描绘,曾言:“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此外,王夫之的神理论有更深层次的要求,即“势”。“势者,意中之神理也。”他曾强调“内极才情,外周物理”(25)的艺术创作原则,即经过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的事物本质与规律,其中“外周物理”则是侧重于取势。如果说审美意象是一个整体,那么连接这个整体的血脉,则需要“取势”,曾言:“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26)可见“势”与“理”相融合,要求画者发挥主动能力,经过艺术思维对物象进行精简提炼后绘出,以咫尺表现万里。如果反之,则缩万里于咫尺。这种以恰当的形式充分表现内容并取得最大的审美效果,称之为“取势”。王夫之所言的“势”是在艺术作品中超越于笔墨之外的力度与穿透力,是绵延伸展且“咫尺万里”的内在张力,他也借用古代画学论著中的常用语句来阐述“势”的艺术效果。例如他在评唐代马戴《楚江怀谷》一诗中,称其“笔外有墨气”(27)。在评论袁淑《效古》一诗中,称其“‘四面各千里,真得笔墨外画意。”(28)中国传统画论与画品中,一直强调“取势”“得势”,讲究画面构图“置陈布势”,展现画外之天地,这在山水画创作中最为明显,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道:“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此自然之势。”强调“咫尺万里之势”,后来宋代《宣和画谱》中评画:“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百千里趣。”郭熙在《林泉高致》言:“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以表现千里江山的气势与恢弘。董其昌也指出画山水要以取势为主,有言:“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可见这里“势”与“气”“理”相联系,贯穿于画外的气象与张力便是“势”,而“万里”与“咫尺”构成虚实,“咫尺万里”于山水画中是“远”的意境理想。不论王夫之是否借鉴古代画论观点来论“势”,但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处。endprint
三、 象外说
古人有“立象尽意”、“观象取意”之说,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意”与“象”(29)结合为一词,来阐述艺术创造的想象力。唐宋时期“意象”在艺术创作中已经成为追求的境界,要求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至明清时期,王夫之他把“意”摆在首位,讲究立意,同时需要营造艺术氛围,让观者如身临其境,从而产生情感共鸣。他认为审美意象表达分为“象之内”与“象之外”,“象之内”乃作品中直接表现出的审美主体,谓之实象。“象之外”是超越审美主体之外的景外升华,是虚实结合的意境之景。王夫之对于“象外说”发展在于强调化实为虚,寄有于无。认为意境在具象之外还存有一个虚象,正如王夫之所言:“‘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可见意境的生成是虚实结合的“象外之象”、“象外之意”,是“象外”与“圜中”(30)所构成的空中结构,即超脱于物象之外而得其精髓。王夫之所言的象外说是虚实相生,不即不离的“象外之境”,有近有远,有虚有实,一切虚无的东西也需要实的物象来支撑,强调“虚无”必须通过“有”来实现,那么“无”才更加可贵。同时他认为“无极可有,有不可无;朴可琢,琢不可朴。”即如果让一切都实而满,达到了极限,那么必然会失去意境的美感,如同质朴还能有雕琢余地,而雕琢过头了却难以还原质朴的境界。例如王夫之欣赏的诗句“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此中蕴含境之实与虚之灵,因而有着幽远无穷的意境。这也是他所认为的“象外”虚拟性,与作者的想象有关,是以外在“实”的形象显示“虚”的内心心境,蕴含了古代绘画艺术中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意味,留下了空间和余地,把虚景与实景结合,给予观者想象的空间,达到的“无画处均成妙境”的艺术境界。此外,王夫之提出艺术家应该从生活体验中养成艺术修养与审美概括能力,从中提炼出典型性的艺术语言与符号,描绘带有本质特征的局部形象,以小景写大景,以近景写远景,以此来涵盖整体,达到象外之象的美学效果。为了阐述此观点,他旁涉诸艺,以绘画艺术为例,指出画家描绘景物,如果没有亲身的感受,那他所画景物尽管笔墨俱佳,但只是“有笔墨而无物体,则更无物矣。”也无法生动的描绘出事物的特性。高明的画者在落笔时以胸有成竹,以小驭大,也是物象对心象的心灵转换,达到心灵映射万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十分强调心性的表达,正所谓“夫画者,从于心者也”(31),绘画艺术不是在于对自然景物的客观描述,而是心灵对物象的体悟活动。艺术创作以物象为准则,追求神似,强调与天地宇宙沟通往来的内在精神,是把具体的形象自外而内的转化,自物象向心象转化,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画特有的抽象笔墨语言构成了意象造型,在描绘物象时不应该为形象所拘束,那样是描绘不出富有神韵的“大象”,只有不拘泥于象,方能得其“真”。因此,王夫之的美学理论高度已经从哲学领域转化为艺术境界,“象外之象”的美是他所贯彻的美学原则,其关于象外说的阐述不仅存于诗歌等文学作品,也适用于绘画艺术领域。
王夫之在诗论著作中融汇古代画学之道,其“天人合一”“神理论”“象外说”等诗论思想与古代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也为现代艺术创作提供养分,为当下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 注 释 】
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出自宋代苏轼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的第一首,王韶华:《中国古代“诗画一律”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版,第10页。
②⑥⑧(23)(24)“天人合一”,儒家思想中认为“天”具有道德属性,即“人道”,而道家注重的“天道”是人与自然合一。总的来说就是个人与宇宙同一,个体的我与客观世界的物相互统一。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版,第1—22、816、821、257、261页。
③④⑤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开篇就解释了“太和所谓道”即是“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还谈到“此言阴阳者二气絪緼”“气化者,气之化也。阴阳具于太虚絪緼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11版,第15、57、32页。
⑦⑨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言:“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色彩,则失其笔法。”元代杨维桢在为夏文彦《图绘宝鉴》作序曰“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 郑笠:《庄子美学与中国古代画论》,商务印书馆2012版,第147、126页。
⑩(31)石涛在《画语录》中曾言:“为此三者,先要贯通一气,不可拘泥。”“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版,第41、3页。
??(21)(25)(26)王夫之:《姜斋文集:姜斋诗话》,《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版,第821、824、830、843、838页。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版,第457—458页。
???(22)(27)王夫之对张子容《泛永嘉江日暮回舟》一诗的评语:“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朝气,乃为神笔。景尽意止,意尽言息,必不强括狂搜,舍有而寻无。”王夫之:《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版,第999—1000、955、889、1023、1041页。
?(28)对谢庄《北宅秘园》的评语:“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王夫之评论南朝袁淑《效古》一诗:“‘四面各千里,真得笔墨外画意。”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版,第752、747页。
?王夫之把佛学提出的“现量”引入美学领域,在他的《相宗络索》一书中有言:“‘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这是现量对艺术构思方式与内涵进行思考。王兴国主编:《船山学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730—731页。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张彦远:《解读〈历代名画记〉》,田村解读,黄山书社2011版,第26页。
?王夫之评论唐寅《落花》一诗中写道:“三、四传神写照”,可见他运用了顾恺之的言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里的“阿堵”则是指目精。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版,第1494页。
(29)南北朝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言:“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胡海、杨青芝《〈文心雕龙〉与文艺学》,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89页。
(30)王夫之在对胡翰《拟古》的评语中有言“空中结构。言有象外,有圜中。当其赋‘凉风动万里四句时,何象外之非圜中,何圜中之非象外也。”这是对唐代司空图提出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言论的发展。崔海峰:《王夫之诗学范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