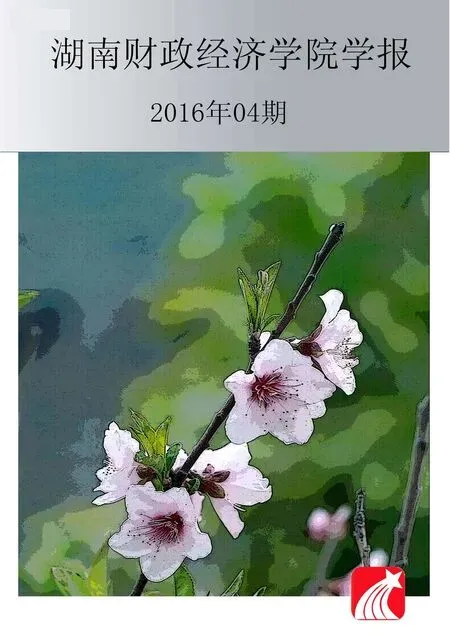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
——以中、印、日为例
刘培青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2.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
——以中、印、日为例
刘培青1,2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64;2.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421001)
通过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引入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运用SDA方法分解了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利用WIOD提供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印度和日本三国出口增加值的规模和影响因素的大小。结果发现:对三国出口增加值影响最大的是出口规模,其它因素影响不大,甚至是负作用。这表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口规模是出口收入的前提和保障,各国应加强在生产领域中的合作,避免贸易限制措施的采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增加值;投入产出;结构分解
一、引言
出口收入是各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各国出口规模与实际收入之间形成了偏差,普遍认为增加值标准更能准确衡量一国出口收入水平。这种新的贸易核算标准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1][2],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增加值明显低于出口规模。许多学者以出口增加值为标准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变化[3][4][5],这种方法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中美、中日双边贸易真实水平的测算[6][7]。随着方法的完善和研究的深入,对于一国出口真实获利水平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统一认识。明确了出口规模与获利之间的差异后,各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利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国家分别专业化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国内外的合作是出口产品生产的必要基础。同时每个参与国的要素基础和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决定了一国是以量还是以能力取胜。采取不同外贸政策的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存在明显不同,因此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获利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当前贸易规则和区域贸易协议对一国出口条件的改变,为我国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谈判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我们寻找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合理途径,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二、文献综述
对于出口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及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研究的文献较多,但以增加值为出口收入标准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并不多见。张杰、陈志远和刘元春(2013)[8]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增加值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FDI流入、研发投入、品牌营销、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持续扩大的出口规模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增加,而政府补贴确实能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企业获得更大的增加值收益。夏明、张红霞(2015)[9]以跨国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从理论上研究后认为,增加值率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中国行业增加值率由于进口中间产品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排挤。郑丹青、于津平(2014)[10]同样从微观角度运用回归计量方法探讨了FDI和出口目的地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驱动影响。江希、刘似臣(2014)[11]则通过协整检验和VEC模型研究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规模经济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祝坤福、陈锡康和杨翠红(2013)[12]以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从事实上阐述了加工贸易和国内增加值率低是影响出口增加值的主要因素。随着数据库的完善,卫瑞等(2015)[13]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为基础,采用SDA方法,从国际视域研究了不同因素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认为外需来源地结构变动、前向产业关联和外国最终需求规模是最主要的因素。
以上研究是对出口增加值研究的完善和补充。以回归计量方法进行的研究从宏观上探讨了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但其借鉴意义无法涉及到外贸领域的具体政策,也有可能遗漏某些重要因素。垂直专业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当然是中国获取出口增加值的因素,但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如何参与分工获取最多的收入更值得探究。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分析工具的不多见,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一国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工具,阐述了事实;另一种是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为分析工具,根据卫瑞等(2015)[13]的分解,将中国出口增加值分解为部门增加值率、前向国际产业关联(中间产品出口)、后向国际产业关联(中间产品进口)、不同国家最终需求产品结构、不同国家最终需求规模、最终需求来源地结构因素等,这种方法刻画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影响及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阐述了外国的生产和最终需求对本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
随着中国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出口规模与出口收入之间的差异越发凸现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从一国角度出发综合分析影响出口增加值水平的趋势和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反映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以上文献的基础之上,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一是以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在出口增加值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从一国角度出发提出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理解框架,分解出不同于以前学者分析的影响因素,补充现有对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二是运用SDA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印度和日本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考察出口规模、最终产品出口、中间产品出口、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地理方向、国内产业关联、国内与进口产业关联、进口产业关联、国内产业增加值率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三是在结构分解的基础之上比较三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口获利的影响因素。
三、方法和数据
1、出口增加值的测算
探讨出口规模和出口收入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普遍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和方法。随着数据的完善,方法也日趋完善。国内已有学者(卫瑞等,2015)[13]以世界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进行研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探讨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及其影响因素。这种分解方法展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国间的依赖和关联。但是从一国角度出发,这种分解方法得出的结果对于外贸政策的借鉴意义可能有限,因为国外最终需求总额、最终需求结构等外国的国内经济因素不是我国的政策可以控制的;另外这一分解结果也不能反映一国面对的贸易规则等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对一国出口获利的影响。从一国外贸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笔者以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出口增加值测算的基础。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对一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结果是一样的,只是立足点不同,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立足于全世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立足于一国。一国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简表如表1所示。

表1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简表
其中AD是指国内中间投入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M是进口中间投入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D是国内产出最终使用,YM是进口最终使用,X是国内产出,M是进口。
出口真实收入的测算实际上是只计算出口产品中所含的本国新增价值部分,根据投入产出核算框架和目前成熟的关于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一国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公式如下:
EVA=V(I-AD)-1(Ei)
(1)
EVA指一国的出口增加值规模,V是元素为Vi的1×n阶行向量,Vi是国内各产业的增加值率,它反映各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增值能力。AD的含义与上同,I是AD的同位阶单位矩阵,(I-AD)-1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反映国内产业关联程度。Ei是一国各产业出口值,(Ei)是n×1阶单位列向量。
在考察一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时,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是重要因素。Ei可以分解为各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与总量的乘积,因此(1)式可以写成:
EVA=V(I-AD)-1SE
(2)
出口目的地也是影响一国出口增加值的因素之一,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可进一步分解。
EVA=V(I-AD)-1SuNE
(3)
2、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
SDA(结构分解方法)是投入产出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一种技术,在经济、能源、环境等领域被广泛使用。它从基本的投入产出模型出发,把某个因变量(比如能源消费、污染排放、就业量)在某个选定时期的变化分解为某几个部分,以此考察各种技术、结构性因素变化对该因变量的影响。从t-1期到t期,出口增加值的增量变化根据公式(3)可分解为:
ΔEVA=f(Δv)+f[Δ(I-AD)-1]+f(ΔS)+f(ΔN)+f(Δ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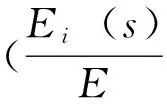
参考张友国(2010)[14]等学者的做法,笔者采用两级分解法来估计各因素的影响。令L=(I-AD)-1,下面是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分解过程。
从t期开始分解有:
ΔEVA=ΔV×Lt×St×u×Nt×Et+Vt-1×ΔL×St×u×NT×et+Vt-1×Lt-1×ΔS×u×Nt×Et+Vt-1×Lt-1×St-1×u×ΔN×Et+Vt-1×Lt-1×St-1×u×Nt-1×ΔE
(5)
从t-1期开始分解有:
ΔEVA=ΔV×Lt-1×St-1×u×Nt-1×Et-1+Vt×ΔL×St-1×u×Nt-1×Et-1+Vt×Lt×ΔS×u×Nt-1×Et-1+Vt×Lt×St×u×ΔN×Et-1+Vt×Lt×St×u×Nt×ΔE
(6)
根据两极分解方法,对公式(5)和公式(6)求算术平均值,得:
(7)
那么行业增加值率、国内产业关联、出口产品结构、出口目的地和出口规模水平五个变量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为:
(8)
(9)
(10)
(11)
(1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大特征是各国在生产领域的相互渗透,中间产品贸易快速增长。一国的出口规模可以分为中间产品出口和最终产品出口,所以规模效应可以分解为中间品(IE)出口和最终品(FE)出口,ΔE=ΔIE+ΔFE,f(ΔE)=f(ΔIE)+f(ΔFE),两者的效应分别为:
(13)
(14)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国内增加值的创造既有国内中间投入的作用,也有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两者的相互配套决定一国新增价值的形成。AD是国内中间投入直接消耗矩阵,AM是进口中间投入的直接消耗矩阵,A是包括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的中间投入直接消耗,A=AD+AM。AD的变化对国内产出的影响反映国内产业关联效应,体现一国国内各产业部门间的联系对国内增加值创造的效应。AD的作用越大说明本国产业结构较完善,在价值链中的控制能力较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对别国生产的依赖较小。A的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反映国内、进口产业关联效应,体现国内和进口产业的联系和配套对国内新增价值创造的影响。A变化的作用越大,表明国内生产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越大,没有进口中间产品产业,国内新增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AM的变化对产出的影响反映进口产业关联效应,也就是外国供给本国中间产品的产业间的联系对国内新增价值的影响。AM变化的作用越大则说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本国新增价值创造的影响越大。
AD可以写成AD=A-AM,借鉴彭水军等(2015)[19]的方法,采用里昂惕夫逆矩阵的乘法分解方法,由L=(I-AD)-1推导得出:
ΔL=LtΔADLt-1=Lt(ΔA-ΔAM)Lt-1=LtΔALt-1+Lt(-ΔAM)Lt-1
(15)
令LA=LtΔALt-1为国内、进口产业关联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L-AM=Lt=Lt(-ΔAM)Lt-1为进口产业关联对本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
两者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分解公式如下:
(16)
(17)
出口增加值结构分解方法的各种效应如表2所示。

表2 结构分解(SDA)效应
3、数据来源
计算过程中使用的中国、印度和日本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三个国家的出口数据、产业的增加值率、出口规模、各产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出口目的地结构等数据,均来自欧盟资助开发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为了消除汇率变化的因素,所有年份的结果均按2002的汇率水平计算。历年汇率水平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年度数据库。
四、实证分析结果
1、中、印、日出口增加值的总体趋势

图1 中国、印度和日本历年出口和出口增加值
图1报告了中国、印度和日本历年出口和出口增加值的总体趋势。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理论相一致,三个国家的出口增加值均小于出口规模。中国的出口和出口增加值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增加较快。日本的出口呈现平衡的态势,这也表现出日本近年来出口增长低迷,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下滑。日本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其出口和出口增加值增长缓慢。不过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出口和出口增加值之间的差距却不同:中国两者之间的偏差最大,这与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发展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日本其次,日本的国内生产中也存在生产外包,将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外包出去,两者之间也存在偏差;印度的出口和出口增加值之间的差距最小,反映印度经济相对较封闭。
2、中、印、日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
表3报告了中国、印度和日本出口增加值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以百分比表示,保留小数点后2位),显示了行业增加值率、国内产业关联、国内、进口产业关联、进口产业关联、出口商品结构、出口目的地构成和出口规模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其中出口规模可分为中间产品出口规模和最终产品出口规模。

表3 中、印、日三国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
(1)出口规模分析
从结构分解结果来看,对中国、印度和日本三国而言,出口规模的变化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基本上都达到了100%以上,这意味着出口规模翻一倍,出口增加值也增加一倍。报告期内出口规模对三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都超过了100%,对日本的影响更大一些。这项结果表明三国贸易收入的扩张都依赖出口规模的扩张。将出口规模进一步细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可以发现两者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在三国间呈现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对中、印两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差别不大。最终产品出口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上中国的影响要小于印度,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比印度更多的是嵌入其他国家的生产环节,而不是最终环节。但对日本而言,2000年之后中间产品出口的效应明显大于最终产品出口的效应,表明日本的出口增加值更多地依赖生产国际化的发展。这也可能是日本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出口中间产品在其她国家完成最后的组装就地生产、就地销售。
(2)行业增加值率分析
从行业增加值率来看,整个报告期内三国行业增加值率都导致了出口增加值的下降,其中日本行业增加值率对出口增加值率的拉低作用比中国更大,中国比印度的拉低作用大。分阶段来看,1995-200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这一效应都是正的,但日本的负效应特别明显,2000年之后,三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负效应。从这项结果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国家的行业增加值都是在下降的,2000年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三个国家中日本的行业增加值率下降最快,其次是中国,最后是印度。这可能是中国和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要高于印度,印度国内行业增加值率没有更多地受进口中间产品排挤的结果。行业增加值率效应为负这也可能是一国国内技术水平停滞不前的结果,行业技术和增值能力没有明显的提高。
(3)产业关联分析
产业关联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特征是国内生产中的中间投入有国内和进口之分,新增价值是不同国家合作的结果,因此在产业之间的关系上就存在国内产业、国内和进口产业、进口产业三个方面的关系。结构分解结果体现了这三者之间不同关系对国内新增价值的影响。
国内产业关联反映了国内各部门间的联系和技术水平,是一国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体现。从计算公式看,出口增加值是计算出口引起的国内各产业的完全消耗再乘以各产业的增加值率,而国内产业关联则反映在进口中间产品存在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国内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从分解结果看,三国国内产业关联对出口增加值的增长效应都不明显,在1995至2005年期间,三国都是负效应。整个报告期内国内产业关联但对中国的影响比日本要大,印度的效应最差。国内产业关联也是一国产业结构完善的表现,从分解结果来看,全球价值链中由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国内产业之间的关联被打破了,国内生产对国内产出的带动作用都不明显。
国内、进口产业关联反映国内中间产品和进口中间产品的合作和配套共同完成国内生产的关系,体现了分别处于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国内、进口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合作程度和互补性,也是一种价值链中上、下游的结合程度。实证结果看,三国国内、进口产业关联对出口增加值的增长效应也不明显,中国和日本为正,印度为负。这说明进口中间产品与国内产业之间的结合对产出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都不是特别理想。
进口产业关联反映进口中间产品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是处于国内生产上游环节的进口国外各产业中间产品之间的关联。它体现进口中间产品供给的相互配套对本国国内产出的影响。换言之,进口中间产品供给的相互联系会影响国内生产的多少和可能性,因此进口产业关联效应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外中间产品供给对国内生产的影响。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在中国和印度这一效应有反复,日本则一直呈现负效应。虽然生产外包能够在全球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但国外中间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对一国出口获取新增价值并没有太大作用。
(4)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对三国出口增加值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报告期内大部分年份是负作用。一种可能是不同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没明显变化,但就中国而言,这与海关统计中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的状况是相矛盾的;另一种可能是各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但不同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率没有明显差异,进口中间产品的使用导致不同国家出口商品的国内投入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没有明显不同,在不同产品的价值链上处于同一环节,对产品的增值能力有限,换句话说不论各国出口什么类型的商品,单位商品赚的钱都差不多。
(5)出口目的地分析
出口目的地变化对不同国家出口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中国和印度甚至有些年份是微小的负效应。这说明向谁出口对出口收入的增长作用有限,每个国家不必局限几个大的经济体,加快进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双边的贸易磨擦是维持和扩大出口收入的有效途径。不同国家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对出口增加值的拉动作用甚微也表明各国的出口国际市场或双边贸易关系没有明显变化,集中于固定的几个贸易伙伴国,出口的广义边际拓展有限。
总体而言,不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出口增加值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出口规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都是出口获利的重要来源,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影响了所有国家。部门增加值率的变化出口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大,而且是一种负作用,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有国家的增加值率都有所下降。国内产业关联对出口收入的影响也不明显,而且有明显的波动,国内、进口产业关联有利于出口增加值的扩大,进口产业关联则明显不利于三国出口增加值的增加。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对出口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大。
五、政策建议
由于加工贸易方式和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出口增加值比出口总额更能反映一国的真实获利水平,有必要从出口增加值的核算框架中探讨出口真实收入的变动趋势和影响机制,厘清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利的影响因素。
1、保持出口规模稳定增长
贸易限制措施对所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国是不利的。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贸易规模是各国获取贸易利益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贸易限制措施都会影响一国的出口规模的扩张,从而影响一国的贸易获利水平。区域性贸易协议对成员方而言如果只是产生贸易转移作用而无贸易创造效应,则对成员国出口获利水平并无太大作用。对我国而言,出口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贸易收入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TPP协议的生效和TIPP协议谈判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传统出口市场经济复苏乏力、贸易磨擦的影响都对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张产生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保持中国出口规模的稳定增长,这种量的增加是出口获利的前提保障。
2、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增加值能力
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国要想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必须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否则只能依靠低级要素投入量取胜。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由于各国只专注于一个最有优势的生产环节,各国的部门增加值率都有所下降。但各国在价值链中分配的利益是不均等的,从事不同环节获利能力不一样[16]。中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以扩大贸易规模的政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中国出口获利水平的持续增长[17]。以量取胜的贸易增长方式在国内外约束条件越来越严格的经济环境下必然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增加值能力以保证出口获利水平。
3、加快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扩大出口市场
对于不同出口商品和不同国家的外贸政策没有必要区别对待。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口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和用什么中间投入去做。高新技术产品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给一国带来的出口增加值并没有太大差别,对于中国而言过于优惠的扶持政策有可能助长这些行业不思进取,带来不公平问题。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对出口增加值的增长效应也不明显,市场多元化反而可以保持出口的稳定性,各国应加快市场多元化的步伐,而不是区域贸易限制。我国未来继续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途径在于进一步加快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目前所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等区域性贸易协议有利于我国应对TPP和保持出口收益的稳定。
4、加强在生产领域的合作
不同国家不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应加强在生产领域的合作才能保持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获利的稳定。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各国中间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都对本国出口增加值的增长产生较大影响,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相对复杂一些。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是不同国家完成产品的不同环节,每个国家的国内生产都需要进口中间产品的参与,如果国内产业和进口产业之间能够配合好,在价值链的上、下环节上合作好,国内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并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
[1]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9-55.
[2]李昕.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的增加值统计研究[J].统计研究,2012,(10):15-22.
[3]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J].世界经济,2014,(2):50-70.
[4]王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5):17-23.
[5]戴翔.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J].中国工业经济,2015,(1):3-20.
[6]王岚,盛斌.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J].财经研究,2014,(9):97-108.
[7]黎峰.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双边贸易收益核算:以中日贸易为例[J].现代日本经济,2015,(4):30-41.
[8]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124-137
[9]夏明,张红霞.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率的变化[J].管理世界,2015,(2):32-44.
[10]郑丹青,于津平.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微观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8):3-13.
[11]江希,刘似臣.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中美贸易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14,(11):89-98.
[12]祝坤福、陈锡康、杨翠红.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13(4):116-127.
[13]卫瑞,张文城,张少军.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增加值出口及其影响因素[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7):78-88.
[14]张友国.中国贸易含碳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0,(7):1287-1300.
[15]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5,(1):168-182.
[16]孔炯炯. 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15-118.
[17]刘爱东,张静. 国外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及启示[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2):48-56.
(编辑:周亮;校对:余华)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port Value- added Income in the GVC——Taking China, India and Japan for Example
LIU Pei-qing
(1.SchoolofEconomic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64; 2.SchoolofEconomics&Management,UniversityofSouthChina,HengyangHunan421001)
By introduc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added-value export in the non competitive input output model,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added-value export using SDA method. Provided by WIOD data,it estimates the Chinese, Indian, Japan scale of export added-value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countries export value added scale is the biggest impact; other factors have little effect, even negativ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ount of export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premise and guarantee of export profits. Countrie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to avoid the use of trade restrictions.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the export added-value;input and output;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10.16546/j.cnki.cn43-1510/f.2016.04.019
2016-04-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培育途径研究”(项目编号:2015B0307)
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对外贸易
F752.62
A
2095-1361(2016)04-0143-09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