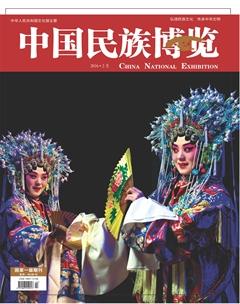顾况: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摘要】所谓“新乐府”,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它的特点,一是用新题,“即事名篇”,不受乐府古题的限制;二是写时事,专门“刺美见事”,反映现实生活;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作为标准。
【关键词】诗歌;乐府诗
【中图分类号】 I053 【文献标识码】A
一、理论先导
所谓“新乐府”,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它的特点,一是用新题,“即事名篇”,不受乐府古题的限制;二是写时事,专门“刺美见事”,反映现实生活;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作为标准。中唐元和(806-820年)年间,白居易、元稹力倡新乐府创作,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令狐楚等诗人积极响应,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乐府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新乐府诗歌创作的主帅,白居易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认为诗歌应当为政治服务,应当承担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使命。他还认为诗歌必须“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必须注意反映人民的疾苦,起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作用。他强烈反对当时文坛上“嘲风雪、弄花草”的空虚委靡的创作倾向,要求“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标榜《诗经》传统,提倡风雅比兴,强调诗歌的政治目的和教化作用是新乐府创作的理论纲领。
新乐府的诗歌理论,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带来的文艺思潮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早在初唐时期,王勃、陈子昂便针对当时“风气都尽,刚健不闻”,“彩丽竟繁,风雅不作”的文风,大声疾呼“天下之文,靡不坏矣”,“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用语虽有不同,但都批判了当时文坛上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提出了文学与政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到了盛唐,尽管文学创作已经呈现高度繁荣的局面,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安史之乱前夕,随着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具有经邦济世思想的士人,如萧颖士、元结、顾况等,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二、新乐府创作的典范
在新乐府的创作上,顾况也曾留下令人瞩目的诗篇,故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的诗派中,列顾况为“升堂”。
顾况继承《诗经》的讽谕精神和四言形式,创作了新乐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这种作法在中唐诗坛很盛行,萧颖士的《江有枫》、《凉雨有竹》,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奉平淮夷雅表》,元结的《二风诗》、《补乐歌》等等,无一不是《诗三百篇》的格式。顾况不仅有意运用《诗经》的体裁来做新乐府,而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反映人民疾苦。如《采蜡》一章讽刺统治者的享乐生活,同情采蜡者的悲惨遭遇;《十月之郊》一章批判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大造公室;《囝》一章则用闽地方言描写了一个被掠卖为奴,惨遭阉割的小儿与父生离死别的情景,沉痛地控诉了当地的阉奴制度。胡适称许“这一首可算是真正的新乐府,充满着尝试的精神,写实的意义”。诗人为被侮辱,被摧残的奴隶们大声疾呼,与后来白居易新乐府《道州民》反对贡倭奴的批判精神相映成辉。他效法《诗经》小序体例,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并标明主题,如“囝,哀闽也”、“采蜡,怨奢也”、“筑城,刺临戎也”,可直视为白居易新乐府“首章标其目”的先例。他以组诗的形式来讽谕现实,也为后世新乐府的典范作品——元稹的《和李校书题乐府十二首并序》、白居易的《新乐府并序》提供了范式和依据。
顾况还有现实意义很强的新题乐府《公子行》:
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镫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绿槐夹道阴初成,珊瑚几节敌流星。红肌拂拂酒光狞,当街背拉金吾行。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
《公子行》是刘希夷始创的新乐府辞名,顾况借而用之,描绘了贵族公子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他们“长衫刺雪生犀束”,“红肌拂拂酒光狞”,甚至“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诗人深刻地揭露了他们骄奢淫逸的无耻行径,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阶级。
另外,顾况的一些创作,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如:
《行路难》其二:
君不见少年头上如云发,少壮如云老如雪。岂知灌顶有醍醐,能使清凉头不热。吕梁之水挂飞流,鼋鼍蛟蜃不敢游。少年恃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行路难,行路难,昔少年,今已老。前朝竹帛事皆空,日暮牛羊占城草。
其三:
君不见古人烧水银,变作北邙山上尘。藕丝挂在虚空中,欲落不落愁杀人。睢水英雄多血刃,建章宫阙成煨烬。淮王身死桂树折,徐福一去音书绝。行路难,行路难,生死皆由天。秦皇汉武遭不脱,汝独何人学神仙。
《行路难》本是乐府旧题,总写世路艰难。而在这里,《行路难》其二,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了“昔少年,今已老”的惆怅。其三则借秦皇汉武求仙不得之事,讽刺了那些为长生汲汲以求的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两首诗,均突破了传统乐府就题写意的窠臼,扩大了乐府题材的表现范围。
后来,白居易的《海漫漫》与其三的主旨如出一辙: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
无疑,白居易的《海漫漫》正是对顾况《行路难》其三的展开,顾况新乐府创作的典范意义可见一斑。
三、对民间语言及形式的吸收和采用
顾诗的一部分语言通俗坦易,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民间语言及形式的吸收和采用上。
《赠别崔十三长官》首句即写到“真玉烧不热,宝剑拗不折”。这句诗显然是化用民间谚语而来。《行路难三首》中,“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平白如话,可直接作民谚使用。《囝》一章中,“囝”、“郎罢”的称呼也是闽地的民间方言。而《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活脱脱就是一首民歌:
昆仑奴,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江村小儿好夸骋,脚踏牛头上牛领。浅草平田攃过时,大虫着钝几落井。杜生知我恋沧洲,画作一障张床头。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
整首诗纯粹以白话写成,读来朗朗上口,与儿歌无异。
顾况的诗中还经常性地刻意摹仿民间风谣的形式,这几乎最终变成了他句式风格的一个典型模式。三三七句式是民歌常用的形式,在顾诗几乎俯拾皆是。上文提到的《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一开篇即是这样的句式:“昆仑奴,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梁司马画马歌》一出句也是“畫精神,画筋骨,一团旋风瞥灭没”;《李供奉弹箜篌歌》中,更是几次复用此句式“大弦长,小弦短,小弦紧快大弦缓”,“李供奉,仪容质,身才稍稍六尺一”,“驰凤阙,拜鸾殿,天子一日一回见”;《庐山瀑布歌送李顾》中也有“飘白霓,挂丹梯,应从织女机边落”……
后来,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也有与其类似的特点,如新乐府的代表作品《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鬚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鎚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塚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这首诗以一个老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在天宝年间为逃兵役而自戕的悲惨经历,意在规讽统治者戒边功,言浅意深。诗句平白如话,通俗易懂,多处使用民间的口语,如“八十八”、“爷娘”、“来来”、“老身”、“呦呦”、“老人言”等等,读来宛若翁在目前,如泣如诉。另外,像白居易的《杜陵叟》、《村居苦寒》,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民间的口语和俗语。
诚然,无论是在理论建树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顾况新乐府的成就都远不及杜甫和元结,但这丝毫不能影响顾况先驱者之一的地位。先驱的要义,不在于创造了伟业,而在于为通向新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指示了一个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况是当之无愧的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作者简介:唐甜甜(1982-),女,山东,抚顺市第十二中学,中级职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