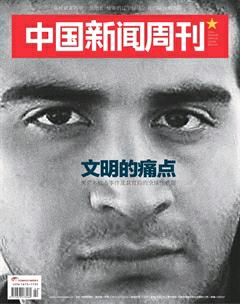最后的爱抚:被忽略的儿童临终关怀
陈薇
孩子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疼痛,但对于死亡的理解比较浅显,主要是害怕、孤独。他们的安全感,还来源于亲人的抚摸、喂食、嬉戏和微笑。在中国,针对儿童的临终关怀尚处于较大缺失状态

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山东男孩小安,是这样走到生命尽头的:他一连向爸爸妈妈说了三声:“谢谢”“谢谢爸爸妈妈给了我生命,让我接受治疗。”然后自己拔掉氧气管,三分钟后平静地离开了……
他是北京儿童医院周翾医生舒缓治疗团队的服务对象。从 2013年10月起,医院血液病中心副主任周翾尝试着为患者家长提供电话随访、疼痛管理等,帮助孩子们度过人生中最后的还能获得的快乐时光。
在湖南长沙的“蝴蝶之家”,各种颜色的蝴蝶折纸被精心装饰在玻璃大门上。位于长沙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中国儿童临终关怀中心”(China Kids Children Hospice),由66岁的英国女护士金林创办,希望让这些患有脑瘫、胆道闭锁、肝腹水等重症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们,最后一程走得不那么痛苦和孤独。
这里还有一面“蝴蝶墙”,一张张照片被嵌进纸蝴蝶的身体里。彩虹之上,是曾经来到世间又离开的孩子;蓝天白云中的孩子,是当下正在蝴蝶之家努力生长的小朋友。留在蘑菇上的,是那些从病危中收获奇迹、已经被收养的孩子们。
周翾团队、蝴蝶之家,是中国少有的为儿童提供舒缓治疗及临终关怀的组织。舒缓治疗(Palliative Care),是指从被诊断为可能不被治愈的疾病开始,向患者和家属提供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在内的一种全面性支持和照料,以帮助患者对抗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直至临终关怀。
在中国,临终关怀已有缓慢发展。北京有独立的临终关怀医院,如松堂关怀医院;有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社区卫生站;在天津、上海,一些综合医院内附设临终关怀病房。深圳上海等地还出现了老人临终关怀的社会公益组织……然而,针对儿童的临终关怀,仍是少之又少。
蝴蝶之家的价值观,贴在金林的办公桌前。或许,它可以解释儿童临终关怀的意义:“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不管生命是长是短或是否为社会做出贡献;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被爱、被关怀,以及在爱和尊严中离开。”
最后的关注
“大梅阿姨,我不舒服了,怎么办啊?”电话里,一个孩子这样问王旭梅。
“没关系,让妈妈给你吃点药就好啦。”她微笑着回答。
更多的孩子不愿意与她对话,有的则根本没有力气说话了。还有一个孩子,心里明镜似的,听见妈妈和她打电话,就在一旁哭。
王旭梅,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8年从业经验。从2013年起,她加入对重症离院病童的随访行动。避开早晚与吃饭时间,有时是下班后,或是上夜班时,她不时地给家长们打电话。
拨号前,她都会暗暗准备一下,预估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总是和想象的不一样”。
有的孩子,突然血象降低,全身都是出血点;还有的心跳很快,或者干脆不能吃饭了。让她耿耿于怀的是一些突然离世的孩子。当天还好好的,下午一点多说有点不舒服,家人正准备带孩子去医院时,孩子没有了。
有的孩子,回家后第一周状态不错。这让她暗自侥幸:“有时候想,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回家后就好了。后来发现不是,或早或晚,他们都会离开。”这时间,短则一天,长则五六个月,没有例外。
王旭梅做的工作,便是为这些进入临终期的孩子提供最后的指导和帮助。她的手机文档里,记录着每位随访孩子的病情发展。比如,一位6岁男孩,安徽人,去年6月起嗓子哑、咳嗽,确诊为横纹肌肉瘤,先后在上海、北京治疗,9月7日出院。
“9·12 患儿疼痛加重,耳朵处流脓、流血,耳垂痒感明显,咨询周主任,建议碘伏消毒,口服希刻劳。9·16 患儿食欲很差,昨天一直睡觉,今天睡眠少一点,头痛较昨天好转,吗啡一天两次,碘伏消毒耳朵患处,痒感好转,告知家长患儿病情,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喜欢钓鱼的孩子,坚持到10月8日离世。
“挺过来啊,挺过来啊!我们好好过年啦!”长沙蝴蝶之家的护理阿姨冯桂兰,抱着2岁多的男孩龙忠忠,一遍遍叫着他的名字,希望弥留之际的孩子能听见她的呼唤,回到这个世界上。
龙忠忠患有严重的脑瘫,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天门没有合上。感冒时会抽搐。那几天一直咳嗽,痰特别多。冯阿姨为他拍背,再用吸痰器为他处理。渐渐地,龙忠忠已经没什么意识了。脸和嘴唇都白白的,呼吸有些困难。
晚上十点,就像睡着一样,孩子在她的怀抱中平静离开。
之后,龙忠忠由护士洗澡擦身,换一身新衣服,加一个日常放在他枕头边的娃娃,最后用一块满是小蝴蝶的布把他轻轻包好,后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送走。
有人曾问过创始人金林,孩子临走的时候需要什么?金林回答,是爱抚。蝴蝶之家的孩子们,如果情况不佳,会得到护士或阿姨一对一的照顾,会在怀抱甚至安抚的呢喃中去世。
在她们看来,这些逝去的孩子就像一只只蝴蝶。中国有“化蝶”的故事,而蝴蝶象征着重生。蝴蝶之家成立至今,已经接纳了140多个孩子,有一半以上已去世。这并不让人意外:他们本来都是因各种病痛被父母遗弃、被医生宣判生命周期不超过6个月的孩子。
“对福利院来说,我们是一个中间的护理部门,是一个中点;有时候就变成终点。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奇迹发生。”蝴蝶之家中国区总监符晓莉说。有的孩子,刚来一两天就去世了;但现在时间住在这最长的,已住了5年。
2016年6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探访时,这里只剩下9个孩子,另有8个孩子被送往上海等地治病。当孩子生命体征基本稳定,蝴蝶之家会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医院。治愈后,他们可能被送回福利院或是直接被收养。到现在,已有十多个孩子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家庭收养,还有近十个在等待被收养。
精细护理
“尽可能与孩子有眼神上的接触;所有的玩具每周用1:10的水和消毒液的比例清洗;所有药物在被注射器吸入之前必须被充分摇匀;最好是面对孩子,坐的高度与孩子的眼睛对齐,用勺子从孩子嘴的下方喂食……”这些说明,来自一份厚厚的、中英文对照的护理阿姨培训材料。
在蝴蝶之家,一位护理阿姨最多只能照顾3个孩子。从洗澡水温、每天换尿布的次数,到药瓶上的标签说明、一次性手套的使用,这里的护理要求十分精细。工作安排以半小时为界,吃饭、活动、喂药都有严格的时间表。
这天中午,阿姨们正在给孩子们喂中饭。中饭是橘红色糊糊状的半流食,以骨汤作底,拌以大米、胡萝卜和青菜,发散着香味。几位阿姨,每人暂时对付一个,剩下的孩子在地垫上、在躺椅上玩着、轮候着。
一位脑瘫男孩Brandon正在吃饭。他嘻嘻笑着,有时故意将米糊反吐出来,等对面的阿姨迅速用勺子捞起,像在玩一个游戏。一顿饭下来,两人都出了不少汗。吃完后洗澡擦干,阿姨给他手臂上被蚊子咬出的红肿大包搽了药,还为他涂上润唇膏。
“来,叫一声‘阿姨好!”护理阿姨鼓励着刚洗完澡的Brandon,向记者打个招呼。Brandon望向记者的方向,眼神似乎无法聚焦,嘴张了好几次,勉强发出了一个“a”音。“真乖!真好!”阿姨大声称赞着。
“6月6日,小便两次,无大便。白天没睡。吃好。”孩子每天的基本情况,记录在“输入输出表”上,供接班阿姨和护士参考。每天量两次体温,用药每四小时、八小时一次。
蝴蝶之家采用的是西方儿童护理方法,有些与中国传统并不一样。45岁的护理阿姨陶晋芝,在蝴蝶之家工作快6年了。她原来自己在家带孩子,感冒时要多穿衣服捂汗。但在这里,“发烧时会让孩子只穿一层衣服,再用冰枕、泡澡、冰敷等办法给孩子物理降温”。自家孩子洗澡,哪怕皮肤红了都以为热一点好,而在这里,“每个澡盆旁都有水温表,水温在25-37摄氏度之间才行。”
这里的设计,一切以精细为目的。为防止大一些的孩子调皮,大门的门锁特意安在高位;药房里的抽屉,设置了需要用手从内打开的儿童锁。粉色、蓝色房间里,窗帘、靠垫乃至床单、被罩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色调。
儿童活动区的栅栏特意从木质换成了塑料材质,因为金林担心,木头的倒刺会刮伤孩子。所有人的棉质衣服每天清洗,以至于原来的家用洗衣机坏得过于频繁,最后不得不换成了工厂用的型号。
这里的孩子,中文名字都姓“龙”,是由福利院工作人员起的。他们的生日,有的依照被遗弃时父母留下的纸条,有的则是根据孩子生长情况估测的。进入蝴蝶之家后,每个孩子还会多一个英文名字。
这些孩子性情各不相同。有女孩是典型的“公主病”,什么都要先挑好的,别人先拿就不乐意。有女孩爱包包,还有的特别喜欢粉色。符晓莉笑着说,她上班的第一天是处理两个“妈妈”间的“纠纷”,一位“妈妈”投诉,“你家的把香蕉都吃了,害我儿都没的吃。”

有时候,刚来的小孩长得很“吓人”。有唇腭裂严重的孩子,一眼能看到鼻骨下。还有的,身体骨头凸出来、肉缩进去,瘦得像小萝卜一样。金林却抱起他,说“你看这眼睛,这么可爱、这么漂亮!”
起初,符晓莉心想,这不是明摆着撒谎吗?有一次,她忍不住问金林,“您真的觉得这孩子好看吗?”
“如果我们都不说她美,谁会说她美?如果我们都不爱她,阿姨们会爱她吗?”金林回答。
“这里会有悲剧发生,但是也有喜悦。这里的一切,都是爱的展现。”蝴蝶之家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我们不能忽视‘爱在临终关怀中的力量。我见过有孩子能得到最好的护理以及丰裕的食物,但如果没有人用心去爱他们,孩子很难从阴影中走出来。”金林说。
孩子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疼痛,但对于死亡的理解比较浅显,惧怕所有的陌生、恐惧、孤独及被抛弃后的惊厥。他们的安全感,还来源于亲人的抚摸、喂食、嬉戏和微笑。但是,对这些被遗弃、身患重病的孩子们来说,生命常常成为一种负担。
一位名叫Olivia的女孩,任何人的触碰都会让她一惊,吓得缩紧四肢。如果有人靠近到可以亲吻她的距离,她会被吓得发抖。还有一位肝腹水的女孩,不吃东西不睡觉,一天20个小时都在哭,身心破碎。直到几天后去世,没有人见过她的微笑。
“我第一次看到他,心都快碎了,好像全世界的愤怒都在他身上。”符晓莉如此描述另一位4岁男孩John。他哭闹时不断用力撞自己的头,拳头砸在地面,哭累了就直接躺在地垫上睡着。走路踉踉跄跄的,不和人沟通,也不互动,好像身体各个机能都在退化一样。
后来,他被诊断为倾向于自闭症。
慢慢地,阿姨们发现,John需要有一个规律的日程,他喜欢清晰的指令和界限。当熟悉了环境、明白自己被珍视之后,John开始学会自己吃饭、学骑三轮车,愿意去上学前班,在外面玩耍,四处跑动。
开辟离开医院环境的舒缓区
距离北京儿童医院1.5公里的金都假日酒店里,一处商务套间内“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活动中心。一进门,是三排矮矮的儿童桌椅,旁边是各种拼插玩具、儿童图书等。这是儿童活动室及茶水间。左手边是一个大活动室,有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还有电脑、音响、投影;右边则是小教室,可以举办小型讲座、会议。
这里是一个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及心理疏导中心,由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出资建设。在这儿,孩子们上过纸艺课、美术课、朗诵课,中秋节来做月饼,端午节包粽子。至于家长们,有的上瑜伽课,还有的接受免费心理辅导。
所有的电器,包括空气净化器、微波炉、烤箱,是由一位志愿者捐款2万元购买的。志愿者们也是管理员,每周轮班,保证中心常年免费开放。去年一年,这里只在大阅兵那天休息1天、春节假期休息了10天。
很早之前,周翾医生便感到,不论是孩子和家长,都需要一个离开医院环境、不考虑病情只供玩耍的地方。尤其是对众多外地家长们,他们在儿童医院旁租房居住,不化疗的日子里,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可去。
北京儿童医院旁,有月坛公园与南礼士路公园。非高峰时段,戴着口罩、没有头发的小病人们,常常去这两个公园玩。有一次,一个孩子摘掉了帽子,被公园里另一个正常孩子看见,后者大喊:“你有病!你有病!”接下来,这个孩子再也不愿意摘帽子了。
2014年8月6日,周翾与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建立了“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机缘巧合下,风能行业的多家企业个人、清华附小的爱心校友们捐赠资金,2015年3月28日,这个活动中心及心理疏导中心正式建成。
如果追根溯源,周翾想做儿童舒缓治疗,起源于一位特殊的病人。一位七八岁的女孩,淋巴瘤多次复发,几乎没有治愈希望。一天深夜,女孩进入弥留,完全没有力气,只是疼痛。医生开了一些退烧药和止疼贴剂,别无他法。
女孩去世后,妈妈给所有当值的医生护士们鞠了个躬,很感谢他们没有让女儿离开医院。“因为她知道她们一走,就再也没有人收留她们了,没有人管了,所以她们只要有钱就要治。一旦一只腿迈出了医院,说再回来,医院是不会收的。”周翾说。
一个残酷现实是,治愈率、好转率、病死率是评价国内医院临床服务的重要质量指标,加上三甲医院床位都很紧张,因此,有些医院不愿意收治危急重症患者,还说服毫无希望的患者离院回家。
周翾所在的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床位约120张,远远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赶来的病童们。由于医药费用低、效益不高,在热门医院里设置专门的临终关怀病床则更不现实。温家宝总理说过让人们有尊严地活着,那么,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有尊严地离去呢?自那时起,周翾有了一个梦想,将来开一家儿童临终关怀医院。
2013年,周翾去美国进修。她发现,美国大医院或治疗中心,都有单独的舒缓治疗团队,有专门的医生、护士、社工、心理治疗师等成员,每周开会,共同分析病例。21岁以下患有肿瘤的病人,可以免费住到临终关怀医院。有一家医院环境很好,还特别设立5间房专门留给孩子。
当年10月,从美国进修回来的周翾,开始带领护士和研究生们,在儿童医院血液科试行舒缓治疗。
今年66岁的金林,则是因8岁时看的一部电影改变命运。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栈》,讲了一位来到中国山西阳城县传教的英国女佣,在20世纪初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徒步转往西安的安全地带——“儿童之家”。
从那时起,金林立下志向,要去中国做同样的事情。上世纪末,金林夫妇俩陆续来中国做义工,发现福利院里有这么一群孩子需要特别的护理。2006年,退休后的金林在英国注册成立“中国孩子”(China Kids)的慈善基金会。2010年4月,长沙“蝴蝶之家”儿童临终关怀中心正式诞生。
6年来,得到越来越多支持的蝴蝶之家,缓慢而坚定地发展着。有人坚持收集马粪卖给园丁,来为蝴蝶之家筹措一些钱;一位外籍志愿者护士的姐姐,在家乡跑了一次马拉松,为长沙订购了一台保温箱。
这里还多了一个感官治疗室。有一个温暖的水床,可以让孩子感受水流的轻柔律动。泡泡水柱、五彩光纤和振动玩具为孩子提供了释放天性、舒缓心情的地方。这个感官活动室以一个男孩Daniel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被父母虐待、4岁就离开人世的波兰孩子,以此纪念像他一样被遗忘的孩子们。
如何跟10岁以上的孩子谈死亡?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感谢北京儿童医院护士王旭梅的付出,但她依然会坚持对重病离院病孩的随访。她曾给一位妈妈打电话,妈妈听上去很淡然,“我知道孩子不好了,可能没几天了”。
王旭梅以为这家长有了心理准备,稍稍放下心来。不料没过几天,她再打电话时,那位妈妈整整哭了二十多分钟,一句话也不说。当时她深刻感受到,这种舒缓随访还是挺重要的。没有接受专业的指导,有的家长好长时间里心态都缓解不过来。
出院之前,周翾都会和家长们长谈一次:“要让家长们知道病情确实不可治愈,那么,什么对孩子最重要?尊严。如果终点一定是在这儿,你宁愿选择曲曲折折走到这里,还是哪怕短暂一些却没有痛苦?”
孩子是最脆弱而敏感的,而对痛苦的管理,目前大多只存在于成人治疗,对孩童的关注少之又少。即使在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吗啡的口服药之前还没有引进。术后疼痛时,常说忍忍就过去了。
化疗引起的疼痛其实是很大的。周翾曾见过一个孩子,脊髓里长满了癌细胞,达到了最高级别的10级疼痛,甚至超越了分娩之痛。结果,这孩子只能无休止地、撕心裂肺地哭,让家长与医生几乎崩溃。
为此,周翾会为离院的孩子开一些延缓病情的激素类药物、减轻痛苦的止疼药物。做舒缓治疗之前,她不会这样做,觉得完全没意义,根本不会治好孩子。但是现在,她发现,这至少会给家长留多一些思想准备的时间,接受孩子的离去。
“让家长不后悔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走了,家长后悔了,可能一辈子生活在抑郁当中。”周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历了这么多离去,有些家长的反应超出预想。有一次,一个3岁女孩在病房剧烈咳嗽,随后陷入昏迷。这时,妈妈说,除了留着氧气瓶让姥姥再来看孩子一眼,其他的都拔了吧。这位妈妈不想孩子这么受罪,一边为女儿化妆,一边告诉她,“不是妈妈不救你,是真的救不了你。希望你不要痛苦。”
谈话时,还有家长直接问周翾:“你们有没有安乐死?”
从2013年10月至今,周翾的舒缓治疗团队已经为80多位病人提供了临终关怀服务。去年底统计,90%以上的病人都是在家中平静离去。
至今,让周翾还困惑的是,该怎么跟10岁以上的孩子谈死亡这件事?有的家长希望回家,但大孩子不同意。一个孩子告诉她,“我不想回去,我最怕的就是哪个阿姨过来跟我说你病没法治。”真离开了,不就没希望了吗,人不就垮了吗?
中国文化忌讳谈论死亡,因此,有的孩子还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病啊?我这是血小板减少”;有的孩子则特别抗拒,哪怕家长想与他谈谈,“不听,我不听!”“或许,等到我们不认为死亡很恐惧、很可怕,等到我们自己有了正确的死亡观,才可以接受舒缓治疗。”周翾说。
在长沙蝴蝶之家,工作人员接到过一些特别的电话。她们接收的孩子只能来自福利院,因此,一位外地爸爸哭着问:“我把孩子变成孤儿,你们收不收?”言下之意,为了让孩子临终得到陪伴,他甚至愿意先舍弃自己。
让中国父母“零抛弃”孩子,才是兴办蝴蝶之家的初衷。她们希望蝴蝶之家的孩子越少越好;但蝴蝶之家的儿童临终关怀模式则应该复制。她们希望,将来能够和医院合作、和社区合作,最终将儿童临终关怀理念散播开来。
事实上它已经开始繁衍。2013年11月,全国第二个蝴蝶之家、南京蝴蝶之家重症儿童安护中心(现更名为彩虹之家)开始接收孩子。2015年底,长沙蝴蝶之家联合了国内其他从事儿童临终关怀的组织,举办了第一次培训会议。今年,金林还被选为国际儿童舒缓护理组织理事会(ICPCN)理事。这是这个机构第一次有中国席位,尽管是由一位英国老太太作为代表。
周翾团队也有进展。2015年8月23日,“新阳光·儿童舒缓治疗专项基金合作中心”在河南省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挂牌成立。接下来,她希望在专业上更加发展,推进疼痛管理,随访系统化,并建设一个儿童临终关怀随访数据库,面向全国开放。
眼下,符晓莉正在与一些机构接洽,希望合作促成真正为家庭提供舒缓护理服务的项目。
周翾和符晓莉、金林,在去年的培训中正式相会。对于中国儿童临终关怀事业,她们走的是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但殊途同归。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小安、龙忠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