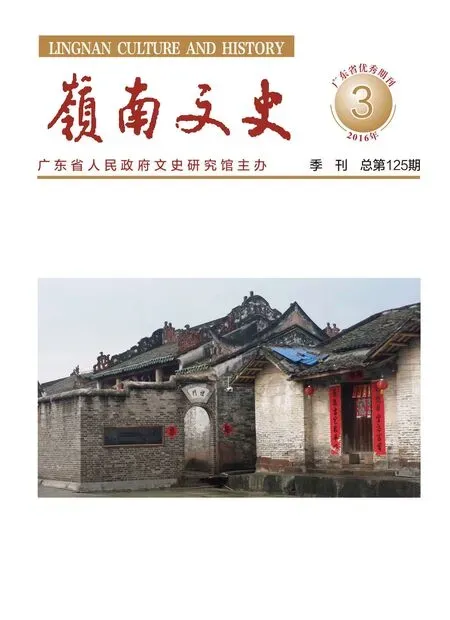追忆父亲古直二三事
古成业
追忆父亲古直二三事
古成业

1952年古直全家福
【编者按】古直(1885—1959),梅县梅南滂溪村人。青年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等一系列活动。古直在参与社会变革以及从事教育的过程中,创办或参与创办了梅县梅州中学、龙文公学、高要初级师范等学校。在任封川县、高要县县长期间,兴办教育、育苗造林、兴修水利,做过不少有益于社会民生的事。古直辞官后,隐居庐山,研究国学,专心著述,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文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转蓬草》、《新妙集》、《层冰诗存》、《隅楼集》、《层冰堂诗集》等。
别离
父亲的音容,只停留在我十一岁之前的记忆里。
1959年6月6日下午5时许,在广州东川路省人民医院二楼内科单人病房,当护士按惯例用棉签沾点温开水涂抹在父亲干裂的嘴唇上时,发现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就这样,父亲无声无息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次日,天保叔(即郑天保)来到我家,把一张几寸见方的纸片交给母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去世前十天写下的遗嘱。遗嘱只交带两件事:
一、火葬;二、将儿女抚养成人。
母亲接过纸片就眼泪涟涟,兄妹三人相顾无言,不知所措。我隐约听见天保叔向母亲解释:“之所以现在才交给你,一来因为老师交带过事后才给,二来当时老师精神很好,似正在康复,没想到真的要告别”。可能为了缓和气氛,点上一支烟后,天保叔又说:“看了之后我还笑老师:‘讲再见,还为时太早呢’”。天保叔这番话,不禁令我想起十多天前,几位来病房探访的友人道别时,父亲吃力扬手大声说“再见”的情形。
确实,父亲是不忍离去的。回过头看父亲1956年的自寿诗:“河清时节近中年,爱日长依共产天,喜得妻儿开口笑,良辰美景涌当前”。并注曰:“古人以百二十岁为上寿,七十正在中年。若以苏联学者百五十岁之说言之,则仅及中年矣”。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父亲对家国热爱之情。就在同一天,父亲还写下“酒颜红入少年林”诗句,表达了曾经沧桑的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太平盛世的憧憬,以及对摆脱年龄羁绊,还我青春年少的渴望。应该说,他是想多些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多些时间去完成未竟的研究的。无奈,病魔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离去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我拂去岁月的封尘,再打开记忆的橱柜,寻觅父亲的印记时,尽管都是些儿时影像,是些无序碎片,但这些已足使我回味,令我动容,因为都是些可以影响我一生的印记。

1956年在广州永汉路古籍书店从左到右:古直、张友仁、侯过
子约伯
晚年的父亲交游并不广,平时有来往的只限于居住广州,且是已经交往了几十年的朋友。
侯过我称他子约伯,是父亲负笈梅城师从谢吉我时认识的。解放后两人又同在省文史研究馆,兴致相投,时相过从,颇为密切。子约伯在正南路都府街置有房产,离我家相隔不过千米,故此往来甚多,也最无拘束。
子约伯家居二楼,楼前有个大院,一条水泥小道从大院大门直通到上楼的楼梯边。二楼的居室不大,但整齐有致,室内家俬挂饰陈设无一不显露主人的文化品味。在子约伯家我可随意走动,父亲在聊天时,我就从书房到厅堂,从厅堂到三楼天台逐处寻找值得流连的地方。与书房铺着狼皮毛的便床和铺着虎皮的躺椅、客厅角上各式树根、竹根、蛇骨做成的拐杖相比,我更喜欢与天台的花草为伴。因为子约伯是个农林专才,天台上的花草被打理得整整有条,充满活力。不说享用着一个凉棚,上面都铺着白花花蚬壳的十几盆墨兰,就是摆在围栏上最普通的风雨草,也显得生机勃勃,不时绽出火红的花朵。天台各种花草抽花展叶,婀娜多姿,实在令人不禁驻足。
记得一次昙花将开时,子约伯将一盆有几十个花蕾的昙花移至客厅,专门邀集父亲、张友仁、李菊生等友人晚上到他家赏花,父亲也带了我同去。在那里,和一帮兴致盎然的老人一起,我首次目睹了“昙花一现”的奇观。
父亲去世以后,我和子约伯也有过一次交往。那是我上初三的时候,一天从报张上得知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子约伯是主任委员,我就给他寄去一个扇面索字。十来天后的一次课间里,一位不认识的女同学喊我的名字,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扇面,秀丽的行草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扇面,内容是一首七律,落款“此侯子约先生贺层冰先生添丁诗,录与成业小朋友,一九六四年,萼生”。原来,我买的扇面是最小那号,子约伯不惯写小字,特找出十六年前我出生时他给父亲的贺诗,请当时的著名书法家秦萼生书写的。恰恰秦的女儿与我同读一所中学,所以有刚才的一幕。
三同
丘哲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人,从1955年起就任广东省副省长,是位一生充满传奇,为国家贡献良多的人。丘哲与父亲同年出生,也同时同地加入中国同盟会,交情甚笃,我称他丘伯。丘伯家居越秀北路一栋高墙围绕的四层楼房,进门是个花园,车库设在楼侧,一楼的客厅足百平方米大,转角处摆着一架乌黑的钢琴。来这里作客,茶水、点心样样有人照应。若到花园走走,也常见到在待命的司机和照料花木的园丁。过多人的关注反而令我觉得手足无措,不过身材高大的丘伯见状总是和蔼可亲地躬身摸摸我的头,往我口袋里塞几颗糖果,把我的局促不安驱散。丘伯的关心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因丘伯家有专人做菜,所以遇到他欣赏的菜色,常会同父亲分享。记得一天晚饭时分有人叫门,开门一看,原来是他的司机送来一大钵盅狗肉,揭开盅盖,深棕的肉汁里隐约见青黄的姜葱生菜等配料,香味扑鼻,让我惊喜一番。
但我上了三年级,父亲就再也没带我去过丘伯家,似乎听说病了。到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时他被错打成“右派”,一直到去世之后,才得以纠正。
1959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天晚饭时间过了父亲仍未回家,我们都很焦急,等到约七八点钟才见父亲行色匆匆提着一捆东西进门。父亲神情凝重,饭也顾不得吃就要我备笔研墨,交带妈妈把厅堂的地板擦干净。只见他将两卷刚买回的已装裱空白对联轴放在地上摊开,沉思片刻后提笔沾墨,疾书一联。原来,他刚获悉丘伯不幸病逝,准备次日送去吊唁的。
谁料到,仅仅过了五个月,父亲也随他而去。
在银河公墓向阳的坡上,丘伯的墓地和我父亲的墓地规格一样,相距仅10多米。不知是否暝暝注定,他们同年降生,也同年离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还是靠得那么近。
旧中大
同父亲到旧中大探访朋友,是我儿时一大乐事。
方孝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我父亲一同在中山大学执教时的朋友。他一直住在文明路国立广东大学和初期中山大学旧址的昔日教授屋舍,在我的记忆中是南轩3号。方教授专注于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汉语语音也颇有研究。父亲和他一起,多是探讨些学问上的事。方教授讲话稍带安徽口音,声音沙沙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两人侃侃而谈,时而翻书寻据,时而提笔作录,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方教授家里我有我的“天地”,一点也不寂寞。
其实,在所有父亲带过我去过的朋友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方教授家了。因为房子前面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院里的花草有种在地上,也有载在盆里,既有有人工栽培,也有随生随长,表面看乱乱的,但更显得自然和充满野趣,是个捉蟋蟀蝴蝶的好地方。加上方教授常常一人在家,无论怎样玩耍,也不用顾忌别人的目光。
至于院子之外,那更是一个自由广阔的天地,可玩之处就更多。若厌烦了在大树周围兜圈,不想再在长满杂草的土堆上跑,还可以走到东北角的一座山坡,拾级而上,坡顶有一座弃置的白色圆顶天文台。在那里,我总思量着怎么才能把门上那个满是铁锈的锁头弄开,能拥有一次真正有趣的探险经历。可惜,我从没打开过。
初春二月的旧中大是个红色的世界。方教授家东面有多棵高耸的木棉树,挂满了火红的花朵,在春风春雨的摇曳敲击和雀鸟的嘴啄嬉戏下,不时飘下木棉花。花朵总是旋转着急促下跌,像火球坠落,如果此时看准了冲上前去,伸手接住,那才是够刺激的事。所以,每到这时父亲说要到方教授家,我总力邀哥哥同去,比赛看谁检的木棉花多。
提起木棉花,不禁让我想起父亲写的几首咏木棉的诗,其中五言古诗《大学西堂望木棉花》应该就在这里任教时的即兴之作。诗中“巍巍百亩黉,终朝冒丹光,初意蜃气幻,旋疑烽火飏”句,正是我小时所见的景况。
父亲诗中的“大学西堂”,是指离方教授家不远的一栋三层的大楼,也是当年的教授公寓。父亲每次从方教授家告辞之后,几乎都要到西堂二楼一位李松生教授家坐一会。李教授看起来比方教授年轻很多,家里就夫妇俩,每次造访都非常热情,常执意挽留用膳。我一直弄不清他和父亲到底是不是师生关系,前不久专到中山大学探问,找到一位人文系同名的教授,他才七十出头,显然不是同一个人。据他说,以前已有搞外调的人来找过这位教授,但也一无所获,我只好作罢。
旧中大值得怀念,不仅因为它是父亲昔日执教故地,而且也是我童年的“伊甸园”。
至亲门生
一声叔(即胡一声)和天保叔都是父亲创办龙文公学时的学生。他们自幼家境贫寒,早年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父亲直接施教的时间不长,但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他们对父亲正直质朴、深明大义、言出行随、表里清澈的品格敬佩有加,一直十分尊重,父亲对他们为民伸张的义举也十分支持,所以彼此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
解放初期,一声叔是广州华侨补校的校长,住在石牌校区内。记得一次一声叔专门用小车接父亲和我到华侨补校观光,在他家吃了一顿南洋风味的午餐,一声婶下的厨。看着她用一块块淡红半个巴掌大的虾片放下油锅,瞬间成了大鞋垫似的脆片,觉得很神奇,后来带了一些回家大快朵颐,印象尤深。
天保叔住观禄路一座旧式洋房的三楼。他的小儿子比我小几岁,是淘气仔,每次去总见他骑着小三轮车在厅里跑来跑去。在两家的交往中,实际上天保叔到我家探候的次数更多。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解放北路的省政府交际处(即现广东迎宾馆),离我家很近,加上出入都自驾车代步,所以常来。来家后他总是让父亲坐沙发(省政府办公厅配发),自己搬一张椅子坐在对面。他脸庞瘦削,眼神炯炯,抽烟很多,多和父亲谈些近期国内外大事,十分健谈。
父亲去世后,家里陷入困境,天保叔及时按相关政策为母亲安排了工作,为我们兄妹申办了国家补贴,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让我终生难忘。而在1979年间,一声叔不顾年老体弱,数次在小女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搜集父亲的资料,了解相关的事迹,着手写《古直传略》,并在全国侨务会议上推介。这也令我十分感动。
两位情同至亲的叔叔本是为国家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却在20世纪那些特殊年代里先后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令人无奈又痛心。1970年我仍在农村插队务农时,闻讯天保叔病重,曾专程回穗探候。依旧在观禄路的屋子里,只见他面容肿胀,眼睛眯起,与以前大相径庭,可谓物是人非,不禁一阵阵心酸。
次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参加了天保叔的追悼会,在那里见到了臂带黑纱的一声叔和一些父亲的老朋友。彼此相见无言,默默哀思,只愿天保叔一路走好。
大书
父亲没有房产,住房是单位代租的,家里所有东西几乎都是政府配置(解放初期国家对干部实行供给制)或从朋友处借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办公桌、椅子、书柜、沙发、床都印有“省府办公厅”的白漆字样,而父亲必须用的笔墨砚台,甚至手杖帽子,则直接从子约伯家取。因为父亲从梅县到广州时只身而来,并无行李,名副其实的一无所有。
生活用品父亲可以不带,然而却带了并不轻巧的书:一套自己的著作《层冰堂五种》,一套装裱的信扎《李审言书简》。而后者十分笨重。因为它的页面有尺半长一尺宽,分成两册,每册的面与底都用整块杉木芯板做成,内页的制作大概是先将信笺裱在宣纸上,然后再裱在纸板上,既保存原信的风貌,又方便阅读。两册迭在一起足有半尺厚,重好几斤。父亲将这两册东西视为宝贝,平时把它放在柜子里,要看的时候才取出,而且小心护着,生怕我淘气起来把它弄脏了。对这部大书父亲不但自己常看,后来还拿回省文史研究馆的资料室存放,与同事们分享。
父亲没跟我说过这套《李审言书简》的来历,而我除觉得木纹均密的杉芯板最适合做弹射纸角的手枪之外,对其他毫无兴趣。我很想提出要那木板,但又觉得无疑“与虎谋皮”,后来还是知趣地打消了这种念头。
父亲去世后好多年,我才了解这部大书的奥妙。原来李审言就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家与国学大师、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详。李详是江苏兴化人,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的第八世孙,家贫而好学,当过农村塾师,后来至大学教授,博雅通识,尤精文选、骈文,一生于学术、教育、著述等方面成就斐然,作出了重大贡献。
辛亥革命前后,李详在文学批评及散文、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已为人所知,并得到学术界、文学界的推崇。当父亲获悉李详在安徽安庆存古学堂讲授史学与选学时,即修书向他请教。李详虽教务在身,但对于来自粤东这个20多岁年轻人言简意赅、辞题旨远的书信一点也没有小觑,有来必复。此后悠悠二十年,两人就汉魏六朝文学、清代骈文、史学文选、文学批评乃至新作序跋、时弊褒贬、生活情怀诸多方面不断有书信交流,相互赏识,相互激励,成为挚友。但二十年间两人始终未曾谋面,确为神交。因此,保留下来的近百封信极具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父亲十分珍惜,专门装裱造册保存。遗憾的是,这部大书在60年代的动乱中被视为“四旧”而付之一炬。虽然作为书皮的杉木芯板留了下来,然而我热衷于做木枪的儿童时代已一去不再了。
1982年,李详的儿子李稚甫教授夫妇费尽周折找到我的住址,特来家造访。李教授年逾七十,已退休,虽有腿疾,但思维敏捷,满腹学问。当时正应出版社要求着手编纂《李审言文集》。想不到没见过面的上一辈挚交,其后人竟有机会坐在一起嘘寒问暖,推心置腹。当我们谈起父辈的书信时,我说已荡然无存,而他却拿出我父亲写给他父亲的几份书信副本送给我,令我既感激,又不胜唏嘘。
自此之后,世交两家互有往来,我与李教授也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学习
父亲并不太注重我的学习,但对于自己的学习,却实实在在地看成头等大事。
刚解放时,新的政权正面临着经济建设和防止复辟诸多新问题。所以,自50年代开始,学习、尤其是政治学习,就进入到千家万户,渐为普罗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公职人员生活不可或缺的要求。毛泽东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番话,成了神州大地掀起各种学习热潮的理据。
当时作为统战系统的人,工作的任务只有一项,就是学习。幸而父亲本色就热衷学习,他总设法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尽管这种学习打着“思想改造”的旗号。
在中国古典文学范畴,父亲早就驾轻就熟,研习自如,著述源源不断。人们从《陶渊明年岁考证》推翻了梁启超的“五十六岁”之说,《钟记室诗品笺》问世八十年至今仍被公认为“最善”之注本二例,以点盖全,其学而不厌,探索不止的创新精神,已可窥知。但是,此学习非彼学习。对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等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的东西,要弄清与适应就非朝夕之功可以解决。幸好学问同源,父亲固有的思想方法本来就具备朴素唯物辩证法元素,加之他对新中国与执政党的满腔热诚,和求学若渴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所以仍难不倒他。他一度对《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经典手不释卷,孜孜不倦。此时,父亲曾写下:“前进!前进!风涌波骇,蛟横鳄厉,皆不足阻我的勇气”。道出了他思想改造的决心和志在必得的心境。
平时父亲去单位多穿长衫——那是他的便装,自清末青年时期就穿着的那种样式。如果是开会学习,他会换过一套四个衣袋的中山装以示庄重。另外,持一根藤手杖,天凉再戴顶同志帽,不用手袋提包,因为钢笔材料都揣在衣袋里。开会学习的事,父亲对家人从不提及。只是过了几十年,碰巧翻出了他的笔记本,才知道那时他被称为“主席”,常常主持各种学习讨论。从记录内容看,连侯过、杨干五这些几十年老友,也一本正经地向他汇报学习心得,以及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态度。原来竟然如此认真,确有点始料不及。
为了学习便利,父亲专设一个64开本200页的笔记本,这种不大不小的本子无论中山装还是长衫的衣袋都装得下,可随身携带,随时翻阅。打开笔记本,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秀丽的蝇头行草,均由右到左竖行排列。用蓝黑墨水写的,多为在机关学习、讨论、听报告的记录;用红墨水写的,大都是较重要的文章摘要;用黑黑的墨写的,主要是学习心得和读后感之类。若认为是重中之重的话,还用不同颜色的笔在旁打圈,提示重点注意。如此斑斓的记录,如此用心的标识,里面的所有星星点点,不就诏示了父亲追求真知的满腔热忱和严谨有序的治学风格吗?可能在我刚学会写字不久吧,这笔记本竟让我看上了,也在里面的空档写起字来。所以,父亲的这个本子,除满载新进思想的三彩秀字之外,又添了些东歪西斜的铅笔字,刻下了我的童稚与无知。
1957年反右风暴横扫知识界,不少老知识分子都惨遭打击,一蹶不振,连父亲的几位好友都未能幸免。以至那段时间父亲脸上多了点木纳,少了些笑容,不得不减少与友人来往,将内心的困惑与无奈带到中央公园,泻落在那土红色水磨石米的长靠椅上和风姿绰约百年菩提树徐徐而动的心形绿叶间。
然而,不知是不是上天的庇佑,父亲不但躲过了这一劫,而且还在这年当选为省政协委员。我想,正如他的感事诗所说“开泰乾坤臻四美,只应努力爱时光”。我想,这应归功于他的努力学习吧。
结语
若从我能记事时算起,和父亲一起的日子不过短短的八年。这八年,恰恰是我人生的起步节点,也是我认知世界最重要的阶段。
父亲没留下任何物质财富,然而他身上那种朴实无华、善良正直的秉性给了我纯真性情和无数幻想,赋予了我无形的力量。父亲没有直接教我游戏、认字、作文、画画,也没有要求我成就大业,然而他为我营造温馨快乐童年的同时,为我指出了寻求真知的路径。最重要的是,他教会我善待别人,也善待自己这一社会生存的重要法则,让我终生受用。正因如此,我才脚踏实地地学习、工作,拥有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父亲泉下有知,应得笑慰。
(作者单位:广州南方高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