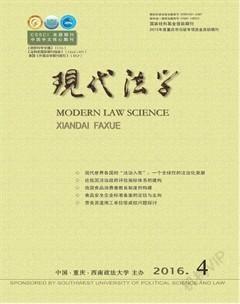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摘要:基于国际社会在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认定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在“即便是自我判断性质的条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与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范围(包括实体与程序方面)之外”问题上的大致共识,建议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国际仲裁庭应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事项上采纳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非排除措施;必要性;最少限制方式
中图分类号:DF 964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4.13
在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均纳入例外条款或曰“非排除措施”(nonprecluded measures)条款,允许缔约方基于保护特定价值与利益(包括缔约方的安全利益、公共秩序、卫生健康、环境保护、劳工标准、金融体系与机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之目的而采取特别的行政举措,其可免除承担相应的条约义务。的确,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各国一方面应信守其于条约内承诺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亦应被授权于特殊情形下出于保护特定国家利益之目的而采取背离条约义务的措施,可以说,投资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在要求各国承担其必要的国际义务与保留其行使相当的国家主权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链接与平衡作用。
但遗憾的是,缔约方在拟定非排除措施条款时,为了保留主动权,往往借助一些抽象性甚至模糊的语句对具体情形予以高度概括。另外,在对东道国行使非排除措施的条件限制方面规定得也较为宽泛与随意,表述方式不尽相同。正是这些不太确切或具体的规定,给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缔约方之间的争端。围绕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问题,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争端:其一,应否对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其二,东道国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是什么?
一、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断性质之争少数学者认为,在回答“应否对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一问题前,必须先弄清楚所适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self-judging)性质——如果条款具备自我判断的性质,意味着东道国在采取具体行政监管行动和措施方面拥有自我判断的权力,即便在争端发生后,投资仲裁庭对这一条款的适用(包括确定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方面)无权审查或者只拥有极少的司法管辖权[1-2]。因此,对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属性予以辨析可称得上是正确回答“应否对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
(一)非排除措施条款自我判断性质的判定
现代法学银红武: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关于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Stephan W. Schill与Robyn Briese认为,就目前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同的自我判断条款的定义。但是,自我判断条款具备两个特征:第一,此类条款赋予缔约方单方退出一项国际义务的自由裁量权(包括通过条约义务的免责以及证明违约的正当性等方式)。第二,对于是否符合免责条件的评估不能完全客观地建立在外部观点的基础上,而应主要依据当事方的意见而得出结论(尽管仍将保留对当事方援引条款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审查)[2]67-68。对于非排除措施条款来说,假若在“缔约方所采取的措施”前有“其认为必要的”(it considers necessary)之类的修饰语,则可认定此类非排除措施条款具有自我判断性质[3]67-68。如《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条约(2004)》与《美国—卢旺达双边投资条约(2008)》第18条第2款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均使用了标志其“自我判断”性质的典型用语,即“其认为必要的”这一表述“本条约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另一方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来履行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义务或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
正是基于这一认定标准,在美国投资者针对阿根廷政府于2001年至2003年经济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提起的一系列国际投资仲裁申请案中,仲裁庭针对阿根廷政府主张免责所依据的1991年《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的非排除措施条款“该条约不应排除任一缔约方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公共秩序,履行其关于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的义务,或者保护其自身的重大安全利益。”,基本认定其只具备非自我判断性质(如CMS v. Argentina案 参见:CMS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65-374.、LG&E v. Argentina案 参见:LG & E Energy Corp., LG & E Capital Corp. and LG & 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para. 214.、Enron v. Argentina案 参见:Enron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31-339.、Sempra v. Argentina案 参见:Sempra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73-388.与Continental v. Argentina案 参见: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 182-188.)。
仲裁庭关于美阿双边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非自我判断性质的认定,引起了较大争议,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如Diane A. Desierto认为,对于像美阿双边投资条约中未明文显示其自我判断性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应着重考虑相关缔约方的国家历史传统与缔约惯常实践,从而对其自我判断性质进行确定。在对美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以及政府在对外投资争端中所持的一贯立场进行了详细分析后,Diane A. Desierto进而认为,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均具有自我判断性质,即便是对于那些未包含“其认为必要的”用语的条款而言,亦属于具有“隐性自我判断”性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4]。BurkeWhite等人也认为,美阿双边投资条约的非排除措施条款之所以仅需受非常有限的司法审查,是由于其具有“隐性自我判断”的性质[1]381-386。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强调该国投资条约中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美国政府认为,即使对于自我判断属性尚未明确的非排除措施条款,也应当解释为具有自我判断性质。美国政府所持的观点得到了Kenneth Vandevelde的证实:“可以非常确凿地认为,自1984年以来,美国对基本安全利益例外的解释都具有自我判断性质,尽管直到1986年的美俄双边投资条约才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这一点。”[5]
(二)争议解决办法: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与非自我判断性质的区分
不难理解,各方为何如此看重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断性质问题——对东道国(或该国学者)而言,强调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即便是未含“自我判断性质”标志用语的条款也主张其为“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能为本国在判断重大国家利益或价值遭遇损害或损害威胁时自主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护此等利益方面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就国际投资仲裁庭或支持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相关方来说,坚持否定抑或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更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追求或保护。笔者以为,应坚持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与非自我判断性质的区分,因为即便是非排除措施条款具备所谓的自我判断性质,亦不应妨碍仲裁庭对措施行使条件的实质审查,理由如下 作者借助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访学的机会(2015年8月~2016年8月),与合作导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Diane A. Desierto教授就这些观点进行了交流并向其请教。:
第一,自我判断性质的语言标志认定标准不科学。虽然投资条约内的典型非排除措施条款大都符合“本条约不得解释为/不得排除……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来履行……义务或保护……根本安全利益”的条文范本,但是也有一些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表述较为宽泛和随意,如《中国—新西兰双边投资条约(1988)》第11条中“禁止与限制”条款条文内容为:“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约束缔约任何一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保障公共健康或为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而采取任何禁止或限制措施或作出任何其他行为的权利。”根本未使用“其认为必要的”用语,但不能仅凭此而对其非排除措施条款的本质予以否定。毕竟,判断条约条款是否为非排除措施条款,关键还得从其功能与本质上予以认定。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的确定也应如此,不应拘泥于条款条文(或译文)是否包含相当于“缔约方/其/他认为”之类的所谓“自我判断性质”标志语的表述。换言之,仅从条款的个别短语上判断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既不可靠,又不科学。
第二,对于投资条约中并未出现任何表明其自我判断性质的明文表达的非排除措施条款,有关缔约方更是应该将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确实为“必要的措施”的认定问题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予以裁判。事实上,对于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的认定,应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有关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从条约用语所具有的通常意义、条约上下文并结合条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综合考虑。若从条约上下文方面考察,以《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为例,该条约第7条规定,一旦产生关于条约“所授予或创设的任何权利”争端,应递交仲裁解决。若将该条约第11条的非排除措施条款认定为具有自我判断的性质,似乎很难解释,为何第11条要与该条约内的其他条款予以区别对待,认为其不应受中立第三方的裁判呢?投资条约的宗旨与目的是对不同主体的利益予以调整,因此中立第三方的裁判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立第三方相较于缔约方而言,能更好地避免对相关方所涉利益有所偏袒。
第三,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之争其实是东道国在适用非排除措施这一问题上应否接受中立第三方的实质审查之争,对过于强调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的当事方而言,其本意是想逃避仲裁庭的审查。如一些学者主张,非排除措施条款中的允许事项属非司法管辖事项,因此应排除在国际法院或仲裁庭的审查范围之外[6]。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在国际社会中,一些当事方尚且将涉及国家安全的争端递交国际法院裁判,并且国际司法机构(包括国际法院、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及其他仲裁机构)从未承认过争议的政治属性可以阻却司法管辖,这无疑就给有关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允许事项属非司法管辖问题的论点予以了有力的否定性回击。其次,该观点与当事方当初同意接受仲裁机构的全面管辖(这就意味着其已就投资争端放弃了司法管辖权)并于投资争端产生后又与投资者达成仲裁合意的举动是前后矛盾的。况且,在国际习惯法方面并未出现任何有关东道国基于非排除措施条款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可免受外部司法审查的规则,亦未渐进发展成一条关于缔约国在对明确具有自我判断属性的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方面拥有完全的自我判断能力的准则。再次,主张非排除措施条款应排除国际法院或仲裁庭审查的观点有悖于条约的统一性理论。因为,现代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条款通常规定将两者间所产生的直接与投资相关的法律争端递交仲裁解决。若将同一条约内的非排除措施条款排斥在国际仲裁的管辖范围之外,那么投资条约的整体统一性将受到严重破坏。最后,基于东道国的行为必须受制于一般国际义务的习惯法规则,上述观点也可被证明是错误的。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4条,缔约方必须善意地履行条约义务。对此,国际司法判例也予以了确认,如Schwebel法官在解释《美国—尼加拉瓜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基本安全条款时就曾指出,仍然应该由仲裁庭来决定成员援引条款的行为是否出于善意 参见:Case concerning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Merits, 27 June 1986, ICJ Reports 1986, 4, para. 220.。正是基于这点,在CMS v. Argentina案中,针对被申请国阿根廷所提出的美阿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应为“自我判断性的条款”的主张,仲裁庭予以了澄清,认为对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查应为仲裁庭的职责。仲裁庭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其所依据的是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 (Hungary v. Slovakia)案,因为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在关于“危急情况”抗辩之国际习惯法规则的适用条件问题上曾认为,“有关国家并非是判断这些条件是否满足的唯一裁判”。因此仲裁庭坚持认为,应当对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条件进行“实体性审查”,而不仅仅只是“善意原则”的审查 参见:CMS v. Argentina, Award, paras. 365-374.。事实上,美国在援引自我判断性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时,也往往会接受仲裁庭的实体审查。美国参议员Helms于2000年9月曾经讲到:“尽管美国认为这些条款是自我判断的,不过在美国政府看来,缔约各方都期望相对方善意地适用条款。”最近,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即使是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超脱仲裁庭的司法审查范围,援引方仍应该就其采取的行动接受仲裁庭的审查。
第四,过于强调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主张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实施条件可排除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之外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国家利益保护主义,极易导致国际投资领域不公平现象的产生,当然最终也会侵害东道国自身的利益,毕竟投资条约具有双边或多边的性质。但假若淡化两种所谓不同性质的条款的区别,对即便是具有自我判断性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仍然实行审查,将确保东道国行动自由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可对东道国以特殊情形为借口行损害投资者利益之实的行为予以防范与甄别。一旦发现东道国滥用非排除措施条款,则可进一步作出裁决,责成东道国就其恶意行为对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3]121。
第五,过于强调非排除措施的自我判断性质也很容易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无论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还是东道国与国际仲裁组织间,甚或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间)产生紧张局面,甚至滋生单边主义,因为援引者会在争端解决活动中极力强调其在采取相应措施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力甚至会超出缔约方在缔结条约时所能预见的范围。如此一来,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反而极有可能会对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破坏影响,这恐怕与缔约方纳入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并且,过于强调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极易导致逆世界潮流的极端观点产生与蔓延。如Stephan W. Schill与Robyn Briese就提出,自我判断条款甚至可以起到防御一国不受全球治理机制约束的作用,因其能使一国摆脱国际治理机制(尤其是像国际法院这样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对该国所享有的监管权。显然,此类极端观点与当今世界的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发展洪流以及强调全球治理、和谐世界等先进理念是格格不入的,理应予以抵制乃至摒弃[2]83。
综上,与其在有关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和与其关联的审查标准(部分学者主张,针对不同自我判断性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应实行不同的审查标准[3]118-122)的两次分歧上纠结不已与争论不休,还不如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将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直接纳入仲裁机构的审查程序。毕竟,各方在“即便是自我判断性质的条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与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范围(包括实体与程序方面)之外”问题上出人意料地已达成大致共识,淡化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也许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下一步的关键还是要找出甚至创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能为各方乐意接受且最好能实现各方共赢的统一审查标准。下文将具体结合非排除措施“必要性”审查标准的选择事例予以说明。
二、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唯一办法”标准、自由判断余地标准抑或善意原则标准针对东道国所主张的“必要的措施”,仲裁庭应如何判定措施的“必要性”呢?综合国际投资仲裁实务界与学界的观点,有几个可供选择的“必要性”要求审查标准:“唯一办法”(only means)标准、自由判断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标准、善意原则标准以及“最少限制方式”(least restrictive means,简称LRM)比例要求标准。这里先讨论前面三个标准的适用。
(一)《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唯一办法”标准
在CMS v. Argentina仲裁裁决的申请撤销案中,撤销委员会认为该案仲裁庭犯了“很明显的法律错误”,即误以为《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必要性”要求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 1. 一国不得援引危急情况作为理由解除不遵守该国某项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除非:(a) 该行为是该国保护基本利益,对抗某项严重迫切危险的唯一办法;而且 (b) 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2. 一国不得在以下情况下援引危急情况作为解除其行为不法性的理由: (a) 有关国际义务排除援引危急情况的可能性;或(b) 该国促成了该危急情况。的“危急情况” 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英语条文中,第25条的标题为“必要性”(necessity),但我国学者均将其译为“危急情况”。其实正是因为“必要性”(necessity)为非排除措施条款中的“必要的”(necessary)的名词形式,故在判断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问题上,自然就会联想到《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关于“必要性”的要求。要求相同,因此未对这两个条款的关系予以辨析。撤销委员会强调,《美国—阿根廷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并不享有《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的所有实体性要求,比如第11条并未包含一个类似于《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第1款(b)项的条件要求 参见: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s. 129-132.。
关于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必要性”要求是否就等同于“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唯一办法”要求问题,学者们则意见不一。其中,少数学者持赞同的态度。如Alvarez等人认为,通过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丙)项条文内容如下:“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甲)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丙)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规定,《美国—阿根廷阿双边投资条约》第11条内“必要的”一词应等同于《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中的“唯一办法”要求[7]。可是,大多数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否定意见。总的说来,多数派学者的主要反对理由如下:
第一,基于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与“危急情况”之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先后适用顺序,一般而言,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应优先于“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规则的适用。导致这一适用顺序的原因大致有两个:其一,根据“特殊法优先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generali)的基本法律原理,若作为投资者提起投资者—东道国间国际投资仲裁之诉基石的投资条约包含了非排除措施条款,将直接导致国际习惯法“危急情况”抗辩理由的不可适用性 这也是专门委员会在受理撤销CMS v. Argentina仲裁裁决案中所使用的第一个解释方法。(参见: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 133.)。其二,非排除措施条款与“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规则同时存在且彼此各自独立发挥作用:前者在审查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事项上属于基本国际法规则,而后者仅为辅助的国际法规则 该解释方法是专门委员会在受理撤销CMS v. Argentina仲裁裁决案中所采纳的第二个方法。(参见:CMS v. Argentina, Decision of the Annulment Committee, paras. 134.)另外,在Sempra v. Argentina仲裁裁决撤销案中,专门委员会也采用了这一解释方法。(参见:Sempra v. Argentina,Decision on the Argentine Republics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the Award, paras. 205-210.)。因此,仲裁庭应先适用投资条约内的非排除措施条款,以此弄清楚东道国所主张的非排除措施是否符合条约的规定。
第二,虽然投资条约内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类似于“危急情况”之国际习惯法规则 这一解释方法为Enron v. Argentina案与 Sempra v. Argentina案的仲裁庭明确采纳。(参见:Enron v. Argentina, Award, para. 334;Sempra v. Argentina, Award, para. 373-388.),但两者还是存在明显区别。在条款的设计方面,《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规定得更为详细,如提出了“该行为并不严重损害作为所负义务对象的一国或数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方面的要求。另外,在功能层面也存在差别,“危急情况”之国际习惯法规则是为了证明缔约方的行为并未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是缔约方出于免除其承担违反条约责任之目的。
第三,鉴于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的适用是确保在公共利益与外国投资者利益间实现一定程度的平衡,若将非排除措施条款中的“必要的”用语等同于《责任条款草案》第25条的“唯一方法”要求,其结果可能会直接导致这一条约目的无法实现,因为“唯一方法”的要求相当难以满足。试想,只要还存在足以应对当时特殊情况的其他任何方法(即便这些方法的成本更高或许更低效),那么“唯一方法”的要求就无法满足,从而也就无法主张“危急情况”的抗辩。也就是说,若将“唯一方法”的要求适用于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必要性”要求,定会导致投资条约中的此类条款对东道国而言毫无用处[8]251。
由此看来,似乎认为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必要性”要求不能完全等同于“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唯一办法”要求的主张更有说服力,本文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
(二)欧洲人权法院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
尽管Alvarez与Khamsi极力倡导用“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唯一办法”要求标准来解释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但Burke-White与von Staden却主张用另一个外部标准来对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必要的”一词进行解释,即仲裁庭可适用由欧洲人权法院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他们认为,自由判断余地原则是“一种恭顺的审查标准,仲裁庭在运用这一标准时,无须对具体情势下的事实以及内国有权机构就这些事实所做的评判进行严格审查,而只须查证被申请国是否已经以一种公正的方式对事实予以了考虑,而且已就此作出了通过合理性检测的结论”[9]。将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作为审查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要求的标准乍看起来确实具有吸引力,然而,在其具体适用中的确会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第一,即便是在欧洲人权法院内部,对于自由判断余地原则本身而言,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如de Meyer法官在Z v. Finland案所出具的不同意见的裁判书中曾较为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原则:“已经在该院的判决书中存在了太久一段时期的关于各国享有自由判断余地的空洞语句没必要说得如此委婉……(自由判断余地)这一概念,鉴于其原则上的错误性正如其于实践毫无用处一样,应该立即被摒弃。” 参见:Z v. Finland,EctHR, Reports 1997-I, Judgment (Merits and Just Satisfaction), 25 February 1997, p. 358.
第二,由于自由判断余地原则的基本原理与欧洲人权法院47个成员各自不同的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偏好息息相关,所以若成员间在某一事项上缺乏太多的共同之处,欧洲人权法院将会授予各成员较大的自由判断余地。比如,各成员基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出于“道德保护”目的而对言论表达自由予以规范时,各国就享有广泛的自由判断权[10]。但在通常只涉及双边投资条约的投资者—东道国间投资仲裁情形下,自由判断余地原则的适用范围(相较于人权领域)显然要小得多。
第三,将解释权授予一个中立第三方的做法已构成了国际关系法制化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对于一部条约而言,若其中一个缔约方放弃这样的授权,而其他缔约方也同样不履行相应的义务,那么对该条约的解释或适用就会完全成为缔约各方(民主)决策过程的结果。争端产生后,赋予任一缔约方自由判断余地,毫无疑问,只会使得各缔约方通过同意中立第三方裁判而使各自的国际义务变得更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四,从国际法院的审判法理来看,并未发现太多支持运用自由判断余地原则的证据。在Oil Platforms案中,当面对一个非常类似于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美国—伊朗友好、经济关系与领事权利条约》第20条第1款(d)项条文时(因为后者也规定,缔约双方可采取“保护其重大安全利益而必要的”措施),国际法院法官Higgins对“必要的”一词的比例要求予以推断,她顺便提到,这并非意味着援引条约第20条第1款(d)项的国家享有“自由判断余地”:“法院本应该接着审查‘必要的其意思是什么,而不需要提供任何所谓的‘自由判断余地。在当时事件所发生的情形下,本来就应该注意到,在一般国际法中,‘必要的一词应理解为也包含一种‘比例需要。” 参见: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6 November 2003, ICJ Reports 2003, 161, para. 48.事实上,在该案判决书中,法庭并未提及自由判断余地原则。
第五,从理论角度看,似乎很难解释为何一个单独由欧洲人权法院所发展起来的原则会与其他地区国家间(比如美洲国家间)的投资条约相联系,并用来解释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更何况,欧洲人权法院从未声称过,自由判断余地原则已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或一般法律原则。关于这一点已为Siemens v. Argentina案所证实,该案仲裁庭就曾明确表示,自由判断余地原则并不是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 参见: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Award, 6 February 2007, para. 354.。
(三)善意原则标准之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主张,仲裁庭在对具有自我判断性质的非排除措施条款进行审查时,应适用善意原则的审查标准[3]120-121。但作为国际法核心原则之一的善意原则,由于其可操作性尚待进一步发展,目前国际协定或各类法律文件均未对其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学术界也未达成一致共识,且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利用这一原则对东道国适用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行为进行审查的案例并不多见,故不认为该审查标准在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认定实践中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经过以上讨论,不难得出结论:无论是“危急情况”国际习惯法的“唯一办法”要求,还是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以及善意原则,似乎都并非为解释投资条约非排除措施条款中“必要的”一词的最理想选择。那么,对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较为适当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考虑到国际投资仲裁的普遍实践并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比例原则分析中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可谓不二选择。三、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审查尽管各内国法院抑或国际仲裁庭在适用比例原则时会存在些许差异,但裁判者在决定政府某一具体行为的比例问题时通常会考虑三个因素:第一,适当性因素。相关行为必须是为实现合法目的并通过适当方式而采取的行动。第二,必要性或最少限制方式因素。所选择的行政措施必须是为实现相关目的而采取的最少限制的行为,在实现相关目的时,不存在能将对投资者个人的不利影响降至更低程度的其他任何同等有效的手段。第三,严格意义比例因素。所采取的行政举措必须符合狭义上的比例(proportionality stricto sensu),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所涉各主体间的不同利益进行估量并试图加以平衡[8]2。
比例原则分析的方法能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与外国投资者的商业利益进行全面和尽量客观的协调与平衡。以非排除措施的比例审查为例,比例原则一方面尊重缔约方希冀通过非排除措施条款的拟定来达到其保护特殊利益与价值目的的做法,使缔约方正当合法的缔约意图能得到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又对东道国动机不纯的、打着非排除措施幌子的行为起到正确甄别与有效约束之作用,从而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现有与预期投资利益。因此,这一审查标准在有关东道国提出非排除措施抗辩的国际投资仲裁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一)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审查的法律依据
1.比例原则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活动的合法性依据
正如Aharon Barak法官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法律制度下,希望通过适用比例原则来对案件进行审理,都必须为该原则的适用提供一个法律依据。”[11]211就比例原则用于分析东道国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的审查而言,其所依据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第(寅)项的规定条文内容为:“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卯)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根据该项规定,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比例原则可成为国际法的正式渊源之一。对于ICSID公约框架下的投资争端,根据公约第42条“投资仲裁适用法”第1款条文内容为:“仲裁庭应依照双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规则对争端作出裁决。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一方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规定,作为国际法规则组成部分的比例原则自应在ICSID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被认定为可适用的准据法规则之一。另外,在其他的投资者—东道国非ICSID仲裁活动中,由于国际投资的实体争议解决可能无关国际法规则(比如东道国仅在受内国法调整的商事合同中作出受仲裁管辖的同意表示),那么再将比例原则作为适用法规则之一予以适用,可能会存在困难。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仲裁庭仍可将比例原则视为相关国内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对其进行适用。例如,即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关于“适用于争议实体的规则”条文内容为:“(1)仲裁庭应按照当事各方选择的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则对争议作出决定。除非另有表明,指定适用某一国家的法律或法律制度应认为是直接指该国的实体法而不是其法律冲突规范。(2)如当事各方没有任何选择,仲裁庭应适用其认为可适用的法律冲突规范所确定的法律。(3)仲裁庭只有在当事各方明示授权的情况下,才应按照公允及善良原则或作为友好仲裁员作出决定。(4)在任何情况下,仲裁庭均应按照合同条款并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作出决定。”并未明确规定可适用国际法规则,但比例原则依然可以内国法规则的身份适用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框架下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活动。
2.比例原则适用于非排除措施“必要性”审查的合法依据
正如Higgins法官所说的那样,基于“必要的”一词的解释而触发的比例原则分析,其是以“一般国际法”的身份介入的 参见:Case concerning Oil Platforms (Iran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6 November 2003, ICJ Reports 2003, 161, para. 48.。因此,鉴于比例原则广泛被认可的“一般国际法”地位,再加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丙)项关于“国际法规则亦可用作解释依据”的规定,从而将这一原则作为一条普遍的国际法规则来对东道国的有关行政措施予以“必要性”审查就具备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换句话讲,对于投资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而言,其解释程序理应将比例原则当作一个适当的工具来判断缔约方的行为是否为“非排除措施”条款所覆盖,也即东道国所主张的非排除措施是否为最终能通过“必要性”审查的真正“必要的措施”。
(二)“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问题上的具体审查运用
1.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比例要求审查的优势与不足
就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而言,“最少限制方式”测试选择从批判的角度对东道国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予以平衡或进行比例协调,在这一过程中,比例与平衡关系始终被仲裁员作为首要的与最终的考虑要素予以对待。在“最少限制方式”的具体测试中,仲裁员并不会对援引非排除措施条款的当事国所寻求实现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作出裁判,其分析只集中于两点:(1)对主张非排除措施条款免责的当事国而言,是否还存在可以如同所选择采取的措施一样能实现相同水平保护的另一替代措施;以及(2)替代措施是否可实现对外国投资只造成更低程度的限制性影响。如果这样的替代措施是存在的,那么当事国已选择采取的措施就谈不上是“必要的”,因此该国就不可主张适用非排除措施条款来为自己的违约行为开脱责任。
然而,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比例原则的“最少限制方式”检测标准过于严厉,并对此提出了种种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仲裁员应如何对替代措施之成本与已采取措施的成本进行比较的问题。如在CMS v. Argentina案中,针对阿根廷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仲裁庭找出了大量的可替代措施,包括“对受影响的人口给予直接补贴” 参见: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May 12, 2005, Award, para. 323.。在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检测中,裁判者会注意:替代措施(如对公用服务行业的消费者提供补贴)能否实现与所采取措施已实现的相同水平的保护,并且与已选择的措施(即对公共服务合同下投资者的权利予以废止)相比,可替代措施对外国投资所造成的限制可能更少。依照仲裁庭的此种分析逻辑,其结果会是东道国将永远被要求承担由采取更少限制的替代措施(即对公用服务行业的消费者提供补贴)而带来的各种成本。试想,若选择采取此种极为牵强的替代措施,补贴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必将对被申请国造成难以承受的政府预算开支压力。基于现实考虑,仲裁庭的分析显得过于理想化。
2.改进: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
(1)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Reasonable LRM)
基于人们对上述通常的“最少限制方式”检测标准所产生的质疑,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应运而生。该方法对可替代措施所带来的不同成本实行一种更为科学的权衡,主张在审查过程中不仅要确认是否还有另外的更少限制替代措施,而且还要对实施该替代措施所引发的不同成本予以考虑,从而才能最终得出该替代措施是否合理的评估结果。更确切地说,假设其他替代措施虽然在对外国投资造成最少限制影响的同时也能实现相同的利益保护,但却会产生不合理的管理与执行成本,那么政府选择采取的措施仍然为“必要的”。在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之下,仲裁庭还可对东道国在假设采取替代行动的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各种费用以及时间延误成本进行估算。事实上,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理念并非没有先例,在WTO的Korea Beef案裁判中就有所体现 Korea: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and Frozen Beef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December 11, 2000) WT/DS161/AB/R, WT/DS169/AB/R, para. 16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认为WTO上诉机构在该案审理中所采取的仅是比例审查标准。对此,DH Regan予以了批判,并有力地证明了该案所采用的审查标准为合理性的“最少限制方式”标准。(参见:DH Regan.Judicial Review of Member-State Regulation of Trade within a Federal or Quasi-Federal System: Protectionism and Balancing[J]. Michigan Law Review, 2001, 99(8):1853-1902.)。另外,包括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在内的众多法院以及仲裁机构(特别是在被申请国采取合法行为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案件中)都表示,比例相当结论的作出并不要求进行严格的“必要性”审查,只要东道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从大量的合理性可选措施中挑选出来的就足够了。这一方法也可被描述为一种“合理的必要性”审查标准,因此在“必要性”的裁判方面,应作出比德国有关比例分析的古典理论较为宽松的解读。
(2)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Deferential LRM)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在适用比例原则对仲裁案进行裁判时,应采取遵从的比例分析方法。如Caroline Henckels认为,裁判者在对是否存在合理的可替代措施予以评估时,可以通过降低举证标准,如针对东道国所得出的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排除措施的结论,只要求其提供一个合理的依据,以此对“比例原则”审查提供一种遵从(deference)[12]。Stephan W. Schill指出,投资条约仲裁庭经常提及“遵从”这一概念,其含义主要涵盖以下几点:首先,遵从指的是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尊重各主权国家的条约缔结权,包括缔约方的条约解释决定权以及仲裁庭即便持不同政见亦不应对条约义务进行“改写”。其次,遵从亦可指以一种国家友好型(或主权友好型)方式诠释国际条约(包含投资条约)的解释原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遵从意味着赋予东道国一定的自由裁量余地或自我操作空间,在此范围内,其主权行为通常不受国际司法仲裁机构的全方位审查。据此,仲裁庭在审查东道国行为时,其标准可从不可诉原则(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s,即不进行任何仲裁审查)下的完全遵从跨到对内国层面一开始所做的任何事实或法律决定进行重新考虑。在具体仲裁中,各仲裁庭需在上述量程内找到一个恰当点位,并依此审查标准对外国投资者保护与公共利益进行均衡,正是这点为投资条约仲裁注入了更多的合理性因素[13]。
截至目前,在ICSID所有的已审案件中,Continental案的仲裁庭可称得上对遵从理念下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的认识表现得比较成熟。就该案的裁决书而言,在两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第一,仲裁庭对是否存在这样的可替代措施予以关注,该替代措施不构成对双边投资条约的违反,而且在东道国采取其所主张的非排除措施时(从2001年11月开始),该替代措施又能够以较为合理的方式得到施行,并且还能实现相等的效果或救济。第二,在对这些替代措施事实上可否以合理的方式得到实施,以及可否避免采取该案所审查的措施予以评估时,仲裁庭应牢记,其既没有义务就阿根廷政府的经济政策(2001-2002年)作出裁判,亦无需对阿根廷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选择行为进行审查。仲裁庭的使命是较为遵从地仅对阿根廷所提出的“必要性”请求是否站得住脚进行评估,从而确定阿根廷政府出于保护其重大利益的目的,除了采取已实施的措施外,在当时再也没有其他合理的替代措施可供选择 参见:Continental Casualty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9), Award, paras. 198-199.。
另外,其他一些ICSID投资仲裁庭也在审查东道国非排除措施问题上表现出一种遵从的态度。以LG & E案的仲裁裁决书为例,仲裁庭注意到,阿根廷政府的应对行动不是通过对具体公共服务合同予以单个评估,而是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外国投资者的合同权利全部予以中止 参见:LG & E Energy Corp, LG & E Capital Corp, LG & 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1, Award, Oct 3, 2006. para. 241.。个案评估的方法大致会包括对具体公共服务承包合同下的投资者权利是否应予以解除进行评估,依据就是这些权利对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持续性与覆盖范围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譬如,授权外国投资者提高电力或天然气行业服务费率的合同权利就必须与电信服务合同下的权利有所区别。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东道国在维持投资者于前一合同下权利的同时,却对后一合同下的权利予以解除,也有可能是合乎情理的。假若这样的话,相较于“一刀切”的行动,个案评估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更少限制的替代措施,因为这一做法是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的,不排除某些公共服务合同有可能会逃过被解除的厄运。更何况,这一替代措施的执行成本明显少于CMS v. Argentina案仲裁庭所列举的“采取直接补贴”这种有点极端的可替代措施而产生的高昂开支[14]。但是即便针对阿根廷政府并未采取单个评估的做法,仲裁庭最终还是裁定阿根廷政府的行为符合非排除措施的构成要件。
当然,对于遵从的(或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一部分人也表现出担忧,认为这一审查标准对于主张非排除措施的东道国而言过于温和,因为被申请国的主张较为容易通过检测。面对这样的质疑,最终需考验的还是仲裁庭的智慧:如何在均衡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权益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取舍,毕竟东道国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享有经济主权。
四、结论在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方面,仲裁方式将变得越来越普遍,仲裁庭的权力也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基于各方在投资条约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以及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标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并为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创建一个可行的统一标准。鉴于“危急情况”之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唯一办法”要求标准、自由判断余地原则以及善意原则在作为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标准事项上的不合适性,建议国际投资仲裁庭继续采纳“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当然,仲裁活动的发展也对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本身必须变得越来越完善提出了要求。研究表明,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标准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标准在对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问题上,将能更有效地实现公正合理的仲裁结果:一方面,对于东道国正当合法的非排除措施,在通过客观并准确的审查后定会得到一个有利于东道国的裁决;另一方面,通过对被申请国打着采取非排除措施的幌子,却行侵害外国投资者利益之实的行径予以证伪,从而有效地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
近些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纳入了非排除措施条款,如2004年重新签订的《中国—芬兰双边投资条约》第3条第5款;2012年《中日韩投资协议》第18条“安全例外”条款、第19条“临时保障条款”与第20条“金融审慎措施”条款;2012年《中国—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第33条“一般例外”条款等。伴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者(如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案与Ping 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and Ping An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Limited v. Kingdom of Belgium案)甚至是我国政府(如Ekran Berha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卷入国际投资纠纷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国际投资仲裁庭在非排除措施审查事项上的动态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与研究价值亦将日益凸显。ML
参考文献:
[1] W.Burke-White, Andreas von Staden.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8(2): 381-386.
[2]Stephan W. Schill, Robyn Briese. “If the State Considers”: Self-Judging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J].Max Plan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9(13): 61-140.
[3]杨福学. 国际能源投资相关条约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4.
[4]Diane A. Desierto. Necessity and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for Non-precluded Measure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3): 827-934.
[5]Kenneth Vandevelde. Of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Shifting Ideology of the BITs[J].International Tax & Business Lawyer, 1993(11): 159-170.
[6]Thomas J. Bodi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Activist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M].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95:221.
[7]Jose E. Alvarez, Kathryn Khamsi. The Argentine Crisis and Foreign Investors: A Glimpse into the Heart of the Investment Regime[G]// Karl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