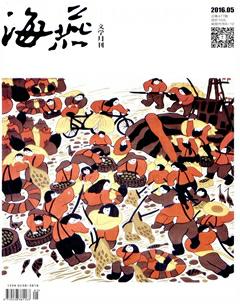老舅(散文)
刘仲丹
我第一次见到老舅,他已经快到五十了,老舅,是我妻子的舅舅。
那是八十年代后期,春天,妻子告诉我,老舅来了,我一怔,老舅?哪个老舅?想了一下儿才缓过神来,原来是年少离乡,在外面当盲流多年的老舅回来了。我买了点肉,骑上自行车去了四十里外农村的岳母家。
在土里土气的农家小院与老舅初次相见,“内容”和“形式”是和谐统一的,眼前的老舅,个子不高,木讷朴实,双手低垂,一脸风霜,罗中立的《父亲》如果年轻二十岁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炕上坐着衣着简陋的老舅妈和怯生生的三个女孩,老舅不是串门走亲戚,是携妻女还乡了。
唠嗑,我大体知道了老舅这些年的经历。岳母家解放前日子“好过”,有良田几百亩,有自家的大菜园子,甚至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几本书。这些东西放到现在,是令人羡慕的,在五六十年代却成了罪过,叫作“成分高”,划为富农。作为富农子弟,老舅的青少年时代不堪回首,处处受欺负,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搞上对象。熬到一九六〇年,低标准,饿个半死,老舅一咬牙,跑到了黑龙江,那年,他还不到二十岁。
一部中国移民史,何其丰富,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湖广填四川,人们多以为那都是老早年的事情,是古代的事情,最起码也是旧社会的事情。是流离失所的现象。新中国早已绝迹了吧?答案是移民行为一点也没有减少。择其大者,就有三五九旅的后身整建制地屯垦戍边,七千湘女上天山,大城市的工厂迁到山区搞“三线建设”,毛主席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之后全国的农业大学搬往农村,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不用说后来的出国热和民工潮了,如果哪位写部《新中国移民史》,一定很有看头。
在我们辽河平原,移民的方向是“上江北”,江北,就是黑龙江省,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松花江以北,目的只有一个——填饱肚子。我们这里,哪个村都有几家“上江北”的,八十年代,吃饭不成问题,人们又纷纷回流,我的同事里有好几个他们的后代,这是后话。
我岳父岳母的家族里,“上江北”的不少,我妻子的二姑,在齐齐哈尔扎根落户,她的表哥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黑龙江人,在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当着中层领导;我的大舅哥,一九七五年去黑龙江讷河当盲流,受尽辛苦,后来进入齐齐哈尔商业系统,儿子在鞍钢工作,他两头跑,习惯的还是黑龙江,爱喝哈尔滨啤酒,就秋林公司的红肠;老舅的哥哥大舅,残疾人,一九六〇年跑到江北,靠裁缝手艺谋生,过得不错,比老舅早几年回到老家,在县城中心买了三间破房,竟被动迁,小有资财。老舅的经历比他们还丰富,他从黑龙江又跑到了宁夏,在那里娶了媳妇,生下三个丫头。
晚上吃饭时,老舅不止一次地放下酒杯,非常严肃地强调:“姐姐姐夫,我这可是有家有口地回来的!”晚饭后,其他人都已入睡,我岳父、岳母、我和老舅聊天,老舅转身从行李里拿出一个黑黢黢的东西,细看去,是一个铝饭盒,大号的那种,很旧。他一脸严肃,说:“我不是空手回来的,我腰里有货!”打开,竟然是一饭盒的人民币,一百元的,五十元的,十元的,五元的,甚至还有两元、一元的,皱皱巴巴,十分肮脏,老舅一副扬眉吐气的样子,说,这是他多年的积蓄,有一万多元!我问这钱怎么这么乱,这么埋汰?老舅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饭盒平时藏在炕洞里,攒下钱就搁进去,所以这钱很不齐整。我问为什么不存在银行里,安全不说,还有利息啊。老舅很不解地端视我,说出一句令我目瞪口呆的话,“存银行里?要是国家黄了咋办?”
之后就是二十多年的交往,我们爷俩挺对脾气,见面爱唠嗑,他家有什么事我尽可能地帮帮忙,年年节节的尽点孝道。
可能是生活经历尤其是年轻时的经历比较特殊,老舅的想法和举动堪称特立独行,有些事令我特别难忘,这是个观察人生观察时代的极好标本。
老舅的节俭令人难以想象,他家不到万不得已几乎不买东西,一年里买的肉绝对不会超过三斤,老舅的头发是土黄色的,像一堆陈年麦秆,没有光泽,明显是营养不良所致。我问怎么不买点肉哪怕买点肥肉耗油也成啊,老舅说他家人都不爱吃肉,但我观察老舅在别人家随礼时筷子往肉碗里动的还是挺勤的。我岳父是退休教师,家境不错,自己养猪,过年杀了吃,每当杀猪,就唤六七里地外的老舅来帮忙,吃完杀猪菜,割上五斤八斤让老舅带回去,老舅赶个驴车,悠悠闲闲,慢慢腾腾,很有些诗意。每当这时,我岳母就说,他家过年啥也不会买了。
老舅好喝两盅解解乏,又怕花钱,恨不得有二分钱一斤的白酒。有一年春节,我送他两瓶酒,不是什么名酒,就是百八十块钱的货色。岳母说,这酒白买,你老舅要是知道一瓶一百,到死他也不会喝的。从那以后,过年我就给他买散白酒,当然是不错的散白酒,据说老舅喝得很舒服。
他家大丫头在果园打工,东家给了一筐落地果,参差不齐,孩子们眼睛里看出火来,老舅一言不发,很果断地搬到街上,卖了几块钱。
老舅的为人准则是万事不求人,不给人添乱,长年累月在大地里在猪圈旁在院子里劳作,几乎不接触其他任何东西,他劳动好像很有快感。有一次我看他割玉米秸,很大一片,看得我眼晕,老舅轻轻松松,说“爱干这活儿,割一根少一根,不像当院的活计,没影没形。”
老舅爱听评书,他是绝对不可能买收音机的,我有时去岳父家,赶上老舅在,他就猫腰站在汽车旁,跟着司机听里面的评书。司机请他上车,没有一次成功,显得不通人情。我岳母评价,你老舅可是有脸皮的人,他土霍霍的,怎么能上车讨人嫌。
老舅好像念过几年书,在他那个封闭的生活圈子里,尽可能地“关心政治”。某次,老舅问我,政治局常委都是谁啊,让我愣了好一会儿,有吃了怪味豆的感觉。他又是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的,他的很多生活经验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曾经跟我岳父说,在大虎山火车站认识一个采购员,答应他能低价买到木头,留了地址和电话,哪天联系联系。都什么年代了,还采购员,这明显是遇到了骗子。老舅的老闺女定亲,已经过了二〇〇〇年,老舅跟我说,人家儿不错,是下放户!下放户,作为文革的一个事物,比土里刨食的农民有些优越感,但那是啥时候的事了。
有件事让大伙百思而不得其解,老舅要盖房子。他回乡后花两千块钱买了一处破房,将就着住了不少年。手里有点积蓄后,张罗盖房子,是每个农民的梦想,老舅当然不例外,问题是他要大张旗鼓盖四间“北京平”。这比盖三间普通平房要多花不少钱,谁都知道老舅的钱是哪里来的,是生生从自个身上抠出来的。而且,他没有儿子,姑娘们都已出阁,他为什么要盖这样“超标”的房子呢?我岳母感到事情不小,专门找他讨个明白。老舅说我可不像××(同族的一个酒鬼),家不像个家外不像个外的,招人笑话。我岳母说你盖三间砖房也不错啊,老舅说,这屯子有几家“北京平”?有几家“北京平”??我让房子利利整整的戳在哪儿,让家族和街坊看看,我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家,行!就为了那句可能出现的“行”,老舅花去半生积蓄,盖了四间宽宽大大的平房。我专门看了一回,老舅洋洋自得,领我看这看那,我到厨房看看,还是老一套,感觉就像王府里住着个乞丐,太离谱了。
这个屯子紧挨森林公园,经常有人来旅游。有一次,我陪省城的一帮朋友去森林公园玩,大面包车里,有人指着一处民居,说太好了太好了,为景区增色不少,这儿的老百姓日子好过啊,我看过去,正是老舅家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