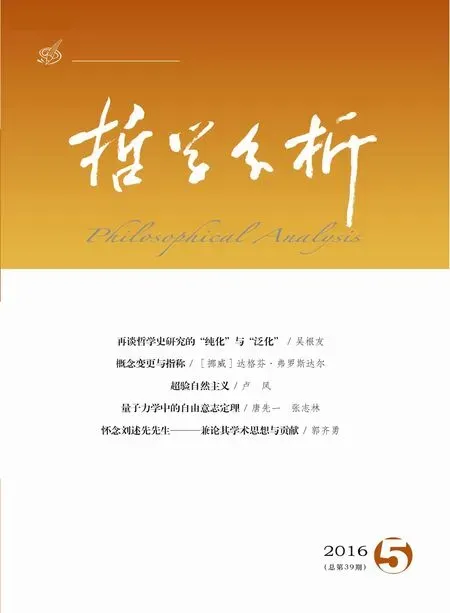普特南学术思想研讨会
《哲学分析》编辑部
·动态与书评·
普特南学术思想研讨会
《哲学分析》编辑部
当代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于2016年3月13日辞世。自《哲学分析》创刊以来,普特南教授一直担任本刊顾问,并有文章在本刊发表。为表达对希拉里·普特南先生的追思和哀悼,《哲学分析》编辑部于2016年3月29日召开“普特南学术思想研讨会”,共同缅怀这位当代世界杰出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亚军教授和黄翔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安维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李侠教授、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员以及波士顿学院哲学系David Rasmussen教授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会议。以下为各位学者的发言内容。
陈亚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听到普特南去世的消息,心情有些复杂,让我想起来2000年奎因的去世。我当时正在纽约参加美国东部哲学大会,大家似乎心理上都有准备了,因而显得比较平静。我在很早以前,2010年,以及更早些时候的2000年,都给普特南写过信,最后他告诉我,他身体当时已经很不好了,基本上跟家人在一起,对外所有学术交流、接待来访、包括培养学生的义务他已经完成了。我当时心情就很复杂,作为这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能再继续他的哲学事业了,当然有的时候他还会参加活动,但是已经不再做比较深入的思考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听了他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很出乎意料地吃惊。
回想自己的学术经历,普特南对我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学德国哲学出身,后来到了美国到了哈佛,课题也是做德国哲学。当时听了一些关于普特南的传说,就到了普特南的课堂看看到底这是什么样的高人,结果我没有想到,那一次整个改变了我后来的学术兴趣、学术走向,以至于后来我完全进入了实用主义的研究。这种改变不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受到普特南的影响,而是说就是由于普特南的引路。我当时修了普特南的“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哲学”以及“非科学知识”课程。正是从这些课堂上以及他要求我们阅读的那些文献当中,我逐渐对实用主义有了不同以往的了解。过去只有一些粗浅的印象,从那以后对这个实用主义非常感兴趣,几十年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也对普特南哲学有一些粗浅的研究。
其实研究普特南的思想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他的思想变化很快,所以很不容易把握,后来我还是用了历时法。我跟《哲学分析》杂志的关系最初也是因为普特南。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美国,童世骏寄了一篇普特南的文章,非常匆忙,要我把他翻译出来,说我们这个刊物创刊号要用。我说时间可能不够,他说不够我也要等,必须你来翻译,而且他已经跟普特南说了这个事情,我当时非常快就把文章翻译了,寄回来,后来我们创刊号也用上了。所以我说借普特南,不光进入实用主义,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刊物。普特南确确实实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重大影响的一个人物。
我在哈佛上课的时候,当时普特南的兴趣从大的方面说是实用主义。他专门开了实用主义的课,实际上他个人的兴趣点是在威廉·詹姆斯,特别是威廉·詹姆斯的知觉理论。当时我不是很理解普特南为什么对威廉·詹姆斯特别感兴趣。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普特南当时正处在思想转折的过程中,从他的内在实在论向后期自然实在论或直接实在论转变的过程中,他在寻找思想资源。他对“语言转向”的评价当时已经不那么高了,不像我们原来认为语言转向可以解决很多哲学重大问题。他现在回过头对知觉的话题重新进行思考,包括现象学的东西,包括威廉·詹姆斯,包括奥斯汀的东西,试图寻找突破内在实在论困境的途径,寻找一个出路。后来我们就知道,1994年他做了杜威讲座,在这个讲座中以及在这个讲座之前,他提出了新的实在论思想,而詹姆斯以及他的知觉理论,恰恰为普特南的这种实在论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源。
普特南的贡献是很多的,在他去世后,我们也读到一些谈论他的贡献的文章,知道他在很多领域贡献非凡。我最关注的是他的实在论,形而上的这一块。我们学界有一段时间,包括罗蒂认为普特南实在论有一个非常剧烈的转变,认为早期当然是科学实在论,后来内在实在论按照罗蒂的解读几乎就是反实在论,后来当然到了所谓自然实在论,或者直接实在论。按照我的理解,其实普特南实在论情节始终很深,只不过寻求不同的方式怎么解释这个实在论。即便在内在实在论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么一个信念,这是第一点,应该要明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变化中一脉相承的东西。虽然他的思想变化很大,但是在这样一个实在论的信念上面,他首先是始终如一的。他的科学实在论,今天看来,并不是他的独创,因为其他人也有,包括他的学生波义德(Boyd),他关于实在论的论述比普特南要细致得多。普特南的独创可能还是他的内在实在论。
非常有意思的是,“内在实在论”这个名字之所以流传开来,被拿来命名普特南中期思想,这里面有一个误解。这个名称,这个“内在实在论”是普特南自己提出来的名称,但是当时在1976年,他提出这个名称的时候,的的确确那个时候正在酝酿一个思想转变,怎么样在科学实在论到后来有人说的反实在论中间走出一条出路来。但是,当时用内在实在论这个概念提出来,还不是对这种出路的命名,而是谈论原来的科学实在论,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后来人们拿它来命名普特南转变后的实在论立场的名字,匆匆将“内在实在论”名称就冠到新学说头上。普特南发现自己无力改变这个状况之后,也就顺应时尚,从《理性、真理与历史》开始用“内在实在论”标记自己的哲学立场。
后期普特南意识到,虽然说内在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实在论立场看起来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们是出自同一个前提,那样一套话语实际上是一致的,核心关注是如何达到世界的勾连,形而上学实在论主张我们可以越过语言的界限达到与世界的符合,而内在实在论则主张我们不能越过语言的界限,只能在语言框架之内完成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谈论。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总的来说还是同一个前提出来,解决不了问题,中间面依然存在。在普特南后期对实在论阐释当中,我们会发现由于在知觉这个概念上面的突破,他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所用的那样一套语汇,而和威廉·詹姆斯,包括现象学的思路基本上相似了。这个思路你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思路。我觉得普特南真正要说他是实用主义,实际上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后期的自然实在论中。他的实用主义与罗蒂等人的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有把这个注意力集中放在实用主义真理论上,普特南实用主义实际上更关注彻底经验主义。我觉得实际上他晚期的思想是要回到那样一个立场上去,就是消解了那样一个中间面,在知觉这里面,通过一种改造重新找到一种方式,能够把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联不变成一种表象的关系,而变成一种实践的或者意向的关系。
在这个之后,他后来也谈关于伦理学的东西。普特南曾经说过,为什么在知识论里面已经摧毁了形而上学实在论,而在道德哲学领域却还坚守着形而上学实在论呢?没有道理的。
普特南这里有一个关于他自己立场多变的辩词,我来读一下:“我在不止一个场合批判自己早先所持的观点,奇怪的是,有些哲学家对于我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我改变自己哲学观点这一事实已被看作是种性格上的缺点。在我轻松愉快的时候,我回应他们说,我经常改变观点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而其他哲学家未改变他们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犯错误。但现在我想就此严肃地谈点看法。我一直记得我和鲁道夫·卡尔纳普在1953年到1955年间的谈话,特别是我记得卡尔纳普是如何地强调他曾在一些哲学问题上改变他的观点,而且这种改变还不止一次。……当然,还有罗素——他影响了卡尔纳普就像卡尔纳普影响了我一样——也因为改变观点而受到批评。尽管我现在不同意卡尔纳普在任何特殊时期所持的主张,但对于我来说,卡尔纳普仍然是那种将追求真理看得高于个人虚荣的人的杰出范例。哲学家的工作不是生产出某个观点X,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以‘X观点先生’或‘X观点女士’而广为人知。如果哲学研究(使这个词著名的正是另一个‘改变观点’的哲学家①普特南这里指的是维特根斯坦。)能对数千年古老的哲学对话有所贡献的话,如果哲学研究能使我们对于那些被称为‘哲学问题’的谜有更深的理解的话,那么从事这些研究的哲学家们就是在做着恰当的工作。哲学不是一个有终解的话题,最新的观点仍然不能清除其神秘性,揭示这一点正是哲学工作的特点。”
关于普特南对大问题的关注,我再念几句普特南的话:“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也包括一些不是我的学生的人)常常夸赞我,是因为这样的事实:我一直喜欢就‘大问题’而不是仅仅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但这是赖欣巴哈教给我的。赖欣巴哈教导我:……一个‘分析哲学家’并不意味着拒斥那些大问题。”
黄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研究者无不受惠于普特南教授。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请这些研究者们以某种方式暂时遮蔽他们所研读过的普特南教授的文献,然后再检查一下大脑中所剩下的哲学版图,碎片化程度的高低就反映了受惠于普特南教授的多少。我本人从接触科学哲学的第一个学期读到“The‘Corroboration’of Theories”一文开始,一直受惠于他。现在如果遮蔽掉缸中之脑、孪生地球、非奇迹论证等等概念,我脑中的哲学地图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尽管讣告把哲人与他的哲学分开,他的哲学已然被散播到上百个国家,继续编织着活人大脑中的哲学地图。
普特南教授在哲学家中是出类拔萃的。这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哲学领域中他极为博识(polymath),涉足的领域从早期的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心智哲学、知识论,到后期伦理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学哲学、犹太哲学等,覆盖英语哲学绝大部分。第二,在所涉足的领域中均能作出原创且持久的贡献。比如上面提到的缸中之脑、孪生地球、非奇迹论证等概念,都已成为讨论怀疑论、语义外在论和实在论问题时无法回避的概念。第三,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给人以善变的印象。他曾是科学实在论、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但在后期放弃了这些立场。而正是这种自我反思、自我修正使他的思想总是处于理论争论的最前沿而独领风骚。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无论这三个方面中的哪一个做到像普特南教授那样好已属难能可贵了。
普特南教授卓越的成就部分是因他的天分。他的高中同学,20世纪最为成功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说:“他拥有巨大的才能和创造力,和我所见过的最为丰富的心灵”(He had enormous talents and creativity,one of the finest mindsI've ever encountered)。然而除了我们只能赞赏和羡慕的天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这就是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即使在讨论极为技术化的论题中,普特南教授也从未失去对哲学最基本问题的关注与探求。他是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出身,师从赖欣巴哈、卡尔纳普、蒯因等大家,然而并未在研究过程中局限于科学哲学的技术性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的反思使他坚持可以用来支持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某种实在论立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支持。后期对新实用主义、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问题的探讨也都指向哲学根本性问题。对于分析哲学研究者来说,对技术性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许多技术性问题的难度与复杂程度相当高,学者们耗费全部或绝大多数的精力对付这些问题也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一个只关注技术性问题的学者完全可以被视为优秀的分析哲学家。然而,如果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都只关注技术性问题而忽视哲学根本性问题则是不健康的。目前一些对分析哲学忽视哲学根本性问题的微词并非空穴来风。而普特南教授的哲学为我们展示了最为健康的分析哲学。一方面,它展示了分析哲学家如何在关注哲学根本性问题的视野中展开其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分析哲学方法如何有效地应用于对各类哲学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正是分析哲学的方法保证了讨论过程中概念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格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普特南教授留给我们的哲学不仅是好的分析哲学,也是最好的分析哲学。
从这样一个视点出发,我认为我们仍然有可能在普特南教授多变的哲学发展中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以贯之的地方。以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层面为例。普特南教授的多变的实在论立场,无论是早期的科学实在论、中期的内在实在论,还是后期的杜威式的实在论,都在试图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切实可行的规范性原则。尽管由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这个一以贯之的追求表现出不同面目,也造成了普特南哲学更为深入的发展。早期的科学实在论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反实在论倾向的回应。中期的内在实在论是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转向以及建构主义所表现出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的回应。而后期的杜威式的实在论也可以被看成是在实用主义的(而不仅是康德式的)框架下内在实在论的更为精致的版本。它受到杜威的启发,试图保留亚里士多德对常识世界辩护的某些洞见,而不落入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以此反对当代形而上学和诡辩哲学的滥用。这一点在与罗蒂和塞拉斯的对比中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两位哲学家也同样以分析哲学的资源来探讨哲学根本性问题,也都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新实用主义的发展。罗蒂与普特南在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知识论的过程中共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但与普特南不同的是,罗蒂放弃了对知识客观性原则的追求,而试图在实用主义哲学资源中寻找和说明人与世界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普特南教授看,罗蒂的追求尽管值得尊重,但仍需避免某种形而上学和诡辩哲学的渗透与干扰。在这一点上,普特南更接近塞拉斯。也许由于同是科学哲学出身的原因,两人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知识论的同时,从未放弃过对科学知识客观性原则的追求,尽管两人进路有所不同。普特南从语言哲学入手,直到后期才把研究焦点转入到知觉,这个联结心灵、身体和世界这三股绳子的界面,而塞拉斯则直接从知觉的基本特征入手探求其自然化的科学实在论。我个人认为普特南和塞拉斯所指引的方式,是哲学的未来所在。
安维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由于承担国家社科重大课题“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文献编目及研究”,多次赴国外查阅文献,其中格外关注H.普特南的著述及其研究性文献。根据这些文献,对H.普特南的科学哲学思想有所思考。
普特南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数理哲学方面的,如他在1975年出版的两部哲学文集:《数学、事物与方法》(Mathematics,Matter and Method)和《心灵、语言与实在》(Mind,Language and Reality)等,加上他更早些时间编辑的《数学哲学》(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1967)和《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1971)。但其代表性著述无疑是广为流传的《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
对于此后的著述,学界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此后的著述都是对《理性、真理和历史》的扩充或延续,如2001年出版的《启蒙与实用主义》(Enlightenment and Pragmatism)和2002年出版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塌》(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另一种观点认为,普特南观点易变,后期著述已经放弃了“理性、真理和历史”的基本立场如2002年出版的《没有本体论的伦理学》(Ethics Without Ontology)和2008年出版的《作为生活导向的犹太哲学》(Jewish Philosophy as a Guide to Life:Rosenzweig,Buber,Levinas,Wittgenstein.)
H.普特南的哲学思想引起了学界的世界性反响,代表性的研究著述主要有:Y.Ben-Menahem在2005年编辑的《普特南作为当代哲学的核心人物》(Hilary Putnam,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Focus),P.Clark-B.Hale在1995年编辑的《普特南研究文集》(Reading Putnam)和C.S.Hill在1992年编辑的《普特南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Maximilian de Gaynesford在2006年撰写的《普特南其人其说》(Hilary Putnam)以及Randall E.Auxier等在2015年编辑的《普特南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lary Putnam)入选了著名的丛书《在世哲学家名人堂》(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在中国科学哲学界,H.普特南在科学哲学上的贡献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理解。我们通过分析其著述的科学底蕴和哲学范畴来重新解读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与传统观点相比,普特南所理解的科学哲学并不是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消解形而上学,而是用新的科学方法(包括逻辑分析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解答哲学上的难题如自我及其思想的确证、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分法等等。这对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启迪是,我们似乎应该摈弃流派跟踪、远离哲学基本问题的流俗,回到用科学方法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主流。
第一,我与陈亚军兄、黄翔兄略有不同的是,我并不看重普特南是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更关注他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对于中国学界特别是科学哲学界,如何正确或准确地理解普特南思想并非易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看重普特南的哲学观念还是更看重他的学术方法。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看重普特南是不是实用主义,要不要重视他在实在论和非实在论上的选择。以往的国内研究往往看他的观点,但很少去关注他的论证手段和论证的方式,我主张从文本解读的学术路径出发,把重点放在他在解决哲学问题所使用的那种学术方法、论证手段,例如他在思考“钵中之脑”问题时使用的思想实验方法,在思考“图灵测试”时使用的逻辑推演方法等等。一个思想家,最重要的不是他或她的观点,而是他或她得到这个观念所使用的学术方法。
第二点体会,我跟陈亚军和黄翔两位教授有点一致的地方。在普特南那里,他跟一般的分析哲学家,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区别在于,他不仅有分析哲学的精神气质,或者分析的能力,同时还有传统哲学或哲学自身的大智慧。与一般的分析哲学家不同的是,普特南所思考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语言及意义层面,而是高度关注哲学的最高问题如心灵与世界、语言与实在、知识与信念、自我与确证、理性与行动等等。对这些哲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使得普特南与其他现代哲学家区别开来。当然,普特南并没有倒退到传统哲学的本体问题中去不能自拔,而是采用现代的分析技术来处理上述哲学的基本问题,如用公理化方法解决意义问题的不同理解,用思想实验的方法处理“钵中之脑”等问题。这就使得普特南与传统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对于我国的科学哲学而言,黄翔教授及成素梅教授的观点及其取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对于我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拘泥于流派跟踪、赶时髦的研究方式,是值得反思的。借鉴普特南的思想方式,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何为科学哲学、如何做科学哲学等重大问题。这也是我在2012年主持国家重点课题“西方科学哲学史研究”和2014年主持国家重大课题“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文献编目及研究”时所进行的新思考:科学哲学不是哲学家对科学认识过程或实践过程的哲学反思,而是用科学方法特别是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来解答哲学问题。我们以为,“哲学或科学及其变革对双方的依赖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例如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对牛顿经典科学的依存);文化或许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相对的或‘地方性的’,可能是科学与哲学、事实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的共识与统一(例如欧洲中世纪在上帝证明中的‘双重真理’观)。科学哲学史研究是‘另一种科学哲学’(Thomas Mormann,2010),或另一种别样的哲学思考,一种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哲学、知识与智慧置于同一个思想平台上的考量。”①参见安维复:《科学哲学史作为另一种科学哲学》,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昨天晚上我翻到了普特南的一本旧作,就是《理性、真理与历史》,这本书当时15块钱,新版的现在已经98块钱了,看来思想是越来越昂贵了。找到这本书是想知道我在什么时候看的,结果在书上没有找到日期记录。昨天夜里,我在博客上匆匆写下一个题目:哲学也是可以很好玩的——纪念普特南。最初喜欢上普特南也就是因为他的两个著名思想实验:“钵中之脑”(brain in a vat)、“孪生地球”(Twin Earth),原来哲学也是可以这么好玩的。不像陈老师、成老师、安老师等都是哲学圈的老人,我是新兵,也无缘认识普特南。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真正的荣誉是来自莫名者的尊敬,对普特南而言,我就是那个莫名者,因而,来自我的尊敬是作为哲学家的普特南应该得到的荣誉,因为这份荣誉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意在内。
仅就我个人的粗浅认识:普特南对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让哲学变得有趣味。他做了很多研究,在哲学的很多领域都颇有建树。这是很值得惊奇的事情。我们的哲学研究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封闭的领域,在这个区间内展开工作,搞得哲学非常没有趣味,逐渐把潜在的热爱者赶走,从而导致哲学越来越没有趣味。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这个指定区域是哲学的富矿还是贫矿?然后就开始组织全国力量去挖掘,挖掘几十年以后,恍然发觉这些年所取得的所谓成果抵挡不住来自某一哲学家的思想冲击。普特南让我们知道:原来哲学不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枯燥无味,而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他提出的伟大思想试验,在幽暗的青春时光里,极大地震撼了我们的心灵,由此,我也就被吸引到这个行当来了。
别小瞧我手上的这一本旧书,只要它有好的内容,就会把人们的兴趣吸引过来。对我个人而言,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原来哲学的领域如此宽广,不像我们这边,用手术刀式剪裁技术把哲学肢解了:搞得我们的哲学如同鸡肋一般,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思想上与心灵上的慰藉。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按老的套路一边把大量的人力、经费投入到哲学的贫矿上,一边又严格限制人们对富矿的开采,如果若干年后,这些努力仍没能拿出任何像样的东西的话,那么,中国热爱哲学的人都被赶跑了,剩下的就是“平庸的罪恶”的泛滥,这是很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当下仍然没有一种觉醒的话,哲学在中国就成为一种名存实亡的存在,那么国人的思想就处于永远需要进口的状态。感谢普特南,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已有的哲学的贫乏。
第二,我们一直在讲,哲学在当下的中国还具有一种使命:那就是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点亮别人,去照亮世界。达成此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批判与反思精神。普特南的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其观点前后经常变来变去,我喜欢这样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理论自诩为绝对真理,敢于否定自己,这就是理智的诚实,也是中国式哲学最为缺乏的品质。中国当下的哲学理论容不下对自己的否定。如果有一天,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何必再去坚守那些错误的东西呢?如果一个时代,人们由于恐惧而信奉一些错误的东西,那么这类虚假繁荣过后,就一定是群体的思想废墟。这是与启蒙之路背道而驰的现象,也是作为理性的人所不能接受的。
第三,哲学人的使命。即便如我这般很普通的哲学工作者,在一个幽暗的时代也有一个需要坚持、甚至突破的责任。任何时候,我们的工作可以出现技术性错误,但不允许出现违背良知的错误。基于理性与常识去做一些工作,可能会显得有些稚嫩,但那代表了一代人在很低认知起点上的觉醒状态。假以时日,我们会看到一种力量:一种源于理性的力量在贫瘠的土地上萌生出来。中国文化骨子里是一种崇奉盲从的文化,当一个一个觉醒的个体不再盲从,而是大胆说出“不”的时候,文明开始作为一种力量与福祉呈现出来,这就是哲学人在当下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哲学人的一个首要工作就是先让哲学变得有趣味,以此召唤那些迷失或者隐退的爱好者,重新集聚与出发。在这方面,普特南是我们的榜样。让中国哲学在这一代人手中重新变得有趣、并丰满起来,如冰冻的大地在思想的春水流过之处,自然会重新绽放,这就是我们期待的哲学的春天。我们就是那些哲学的种子。
虽然普特南去世了,但是哲学仍然在路上!我就说这么多。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普特南是在不断拓展其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善于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超越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涉猎许多哲学分支,尤其是在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心灵哲学等领域内卓有建树,晚年则转向了犹太哲学、伦理学的研究。学术界对普特南的许多哲学思想并不陌生,但是,普特南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测量问题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他提出内在实在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却鲜为人知。为此,我在这里就这一问题发表管见,来追思这位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并感谢他作为《哲学分析》的名誉顾问,对杂志自创刊以来的学术支持。
普特南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于1948年到194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时,认为大的哲学问题都是伪问题,因此,考虑从哲学转向数学。然而,1949年秋天,当他到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聆听了赖欣巴哈开设的“时空哲学”课时,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完全打消了“哲学已经终结”的消极情绪。他说:“赖欣巴哈通过事例,而不是通过说教,使我懂得,成为一名‘分析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只是拒绝大问题。尽管赖欣巴哈像艾耶尔一样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但是,对于赖欣巴哈来说,经验主义只是挑战,而不是终点。这种挑战表明,大问题——时空的本性、因果性问题、对归纳的辩护、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问题——能够在经验框架内得到适当的澄清,而不是被完全抛弃。”①Hilary Putnam,“Rechenbach's Metaphysical Picture,Erkenntnis”,Vol.35,No.1/3,1991,p.62.这样,在赖欣巴哈的影响下,普特南从此把哲学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
赖欣巴哈不仅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代表人之一,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哲学家,他除了对时空哲学有深入的研究之外,还在1942年出版了《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一书。虽然我没有资料证实,普特南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测量问题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赖欣巴哈的影响,但是,至少从上面提供的普特南的回忆来看,普特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经接受了赖欣巴哈在经验框架内澄清哲学大问题的思维方式。从普特南发表的文章来看,他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测量问题的关注,竟然长达40年之久,这一点是明确的。而且,他的内在实在论思想的形成与提出,与他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测量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
在1965年,普特南发表了第一篇关注量子力学解释的文章,标题是“哲学家看量子力学”。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论证的观点是:量子力学的解释不是一个物理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基于这种认识,他进一步在1968年发表的《量子力学的逻辑》一文中,通过提出一种能够使共轭变量(比如,位置与速度、能量与时间)同时存在的非经典逻辑,来解决测量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量子测量问题不是通过提出新的技巧或者新的应用来解决,而是通过对量子态的重新定义和解释来解决。他把逻辑与量子力学的关系和几何与广义相对论的关系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可明确地表述为,②Michael Redhead,Incompleteness,Nonlocality,and Realism—A Prolegomenon to the Philosophy of Quantum Mechan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这种关系意味着,如果说,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导致了一种新的几何观念,即,非欧几何,那么,量子力学的产生,也应该被看成是导致了一种新的逻辑,即非经典的量子逻辑。其基本的观念是,如果L指经典逻辑,P′是用这种逻辑得出的含有“悖论的”物理学概念。现在,引入一种新的非经典逻辑L′来恢复实在论的“旧的”非悖论的物理学P,从而得出下列等式,即:

1975年,普特南在《量子力学与观察者》一文中,继续以双缝干涉实验为例,在详细地讨论了冯·诺意曼的量子测量理论和薛定谔的猫悖论的问题之后,进一步重申了他在1968年提出的量子力学的逻辑解释。冯·诺意曼的测量问题是指,根据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描述微观客体运动的薛定谔方程,只能给出概率解,而每一次量子测量结果,却必须得到一个确定的值,而这个确定的值,并不是通过方程计算得到的,而是测量得到的。那么,微体客体从测量之前的叠加态到测量之后的定态的转变,是在那个测量环节发生的呢?薛定谔的猫悖论用宏观的方式揭示量子测量的困难所在,是指在一个含有毒药瓶的密闭盒子内放入一只猫,这只猫是死是活,取决于观察者打开盒子的观看动作。运用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普特南认为,量子力学的“态的叠加”的惊人特征,是量子力学的所有解释都必须阐述的问题,但是,人们不应该以经典的方式进行思考,在物理学的思维方式中起作用的并不是从形式上证明不存在隐变量的量子理论,而是如果他们以经典方式思考问题,就会与可理解的物理学图像不相符。对物理学家来说,有用的思维方式是把叠加态也看成是一个新的态,即,一种新的条件(condition)。普特南认为,这只是物理学家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然而,每一位量子力学哲学家都会从某个方面对这种传统智慧提出挑战。他本人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在1994年,普特南在文章中公开承认,他在60年代提出的量子力学的逻辑解释,是不可行的。但是,他通过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与测量问题的讨论,揭示了经典实在论(即,他所说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并根据量子测量的相对性形成了以多元真理论为核心的内在实在论的观点,却是众所周知的。他认为,关于微观客体的讨论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框架内提出才有意义。就像我们对量子测量现象的认识是相对于测量设置一样,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也只能在我们的语言(文化)框架内现实,真理是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是信念的融贯,而不是与实在的相符。
为了阐述他的这种观点,普特南先是把实在论区分两大类,一类是大写实在论:“Realism”;另一类是小写的实在论:“realism”。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成为一名“实在论者”,那么,我们最好是小写r的实在论者。“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版本超出了小写r实在论的范围,带有典型的哲学幻想的特征。①Hilary 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edited by James Cona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6.这种大写R的“实在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哲学态度:只认为“科学客体”是真实存在的哲学家自称为是实在论者,但是,坚持桌子等宏观物体也是真实存在的哲学家,也是实在论者。根据现象学家胡塞尔的观点,第一种思路表达了“外在客体”的一种新方式——数学物理的方式。这是自伽利略革命以来出现的一种西方思维:运用数学公式来描述“外部世界”。这两种态度或关于世界的两种图像,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哲学纲领。①Hilary Putnam,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The Paul Carus Lectures,LaSalle: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many,1987,p.4.
普特南在1982年发表在《哲学季刊》第32期的另一篇文章中,又把当代科学实在论划分为下列三种基本类型,并通过对每一种类型的实在论态度的阐述,来表明他自己的实在论立场。②Hilary Putnam,“Three Kinds of Scientific Realism”,in Words and Life,edited by James Cona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492—498.
其一,作为唯物主义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as materialism)。普特南认为,这种实在论把所有的特性都看成是物理特性,或者说,我们能够把“意向性的”或语义学的特性还原为物理特性,例如,大家熟悉的语义学的物理主义的主要观点是,X指称Y,当且仅当,通过一种适当类型的“因果”链条把X与Y联系起来。这种观点面临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是,物理主义者如果不运用语义学的概念就无法阐述把什么算作是“适当类型”;另一个困难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因果性”概念:第一种是数学物理学运用的因果性概念:“因果关系”是一个系统的“态”之间的精确关系,其中包括在决定论的意义上存在着从较早的态转变到后来的态的转换函数;第二种存在的因果性概念是作为一个事件的“产生者”,例如,老师对学生的论文的批评可能是导致学生情绪低落的原因。这种因果关系不可能根据物理学的概念来定义。在这种情形中,“背景条件”和“诱因”的区分是兴趣相关和理论相关的。普特南指出,如果“科学实在论”是这种科学的扩张主义,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他申明自己就不是一位实在论者。因为在他看来,真理、指称和辩护是涌现出来的(emergent),不能被还原为特定语境中的陈述与术语。因此,物理特性与意向特性都是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称是一位二元论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多元论者。
其二,作为形而上学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as metaphysics)。普特南认为,这种实在论是指接受菲尔德(H.Field)所说的三种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一个确定的独立于心灵的客体集合组成的;二是认为,关于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是千真万确的和完备的;三是是认为,真理就是某种类型的符合。③Hilary Putnam,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The Paul Carus Lectures,p.30.普特南认为,这三者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观点除了华而不实之外,没有明确的内容,或者说,它是作为一种有力的超验图像呈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强实在论立场,也是一种“上帝之眼”的观点。普特南曾在多篇文章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很容易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对相对主义观点的一种辩护。然而,“逼真”论证或“科学的成功”论证都不可能证明这种真理概念是合理的。普特南试图使它的“内在实在论”成为介于这种经典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第三种方式。他指出,“我不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在我的观点中,就我们现有的概念而言,真理不会超越正确断言(在正当条件下)的范围……真理是多元的、不明确的、无限的。”①Hilary Putnam,“Three Kinds of Scientific Realism”,p.495.
其三,作为逼真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as convergence)。在普特南看来,当代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是以“意义”理论为出发点的,因此,批判实证主义观点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实在论都必须包括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的概述。“逼真实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既存在着电子之类的理论实体,也存在着像桌子之类的宏观客体,或者说,把关于“线圈中有电流”的陈述看成与“这间屋里有把椅子”的陈述一样客观。普特南称自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者”。这种实在论的核心假设是:在成熟的科学理论中,后面的理论比前面的理论更好地描述了前面理论所涉及的实体,或者说,后面的理论对前面理论所指称的实体的描述更接近于真理。普特南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够说明科学成果的可交流性。这意味着,理论假定的相互关系不是精确的,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误差,只是一种近似正确的理论。比如说,我们不会预期今天的物理学理论没有变化地幸存下来;而是希望,明天的物理学理论与今天的理论具有概念上和经验上的不同。关键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认为明天的物理学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电子给出了更好的描述呢?
普特南认为,拉卡托斯(I.Lakatos)在他的研究纲领中通过“硬核”假设,使后继理论中指称的实体等同于前面的理论中指称的实体。这种做法是无助的,除非“硬核”与“保护带”是站在后面理论的立场上得出的。如果是这样,“硬核”假设就不再可能得以维持。例如,狭义相对论中保持了牛顿物理学中的动量、动能、力、质量等概念。如果我们在“非相对论性”的低速和宏观的情况下,把“硬核”看成是近似正确的牛顿力学定律,那么,我们就能够把狭义相对论看成是保持了牛顿物理学的“硬核”。然而,这完全是根据牛顿的观点以任意的方式来定义“硬核”。当代的新实证主义者也没有放弃知识增长的观念。但是,他们基于观察语言来谈论知识增长的观点,其动机是不合理的。因此,这种观点很容易遭到反对。现在有一些科学哲学家(例如,劳丹)认为,使相互矛盾的理论中的术语指称相同的实体是毫无意义的。一百年前的物理学家指称的实体没有一个能说现在是存在的(因为这些理论的“经验陈述”是错误的——例如,理论的预言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后面的理论是关于前面理论所支持的实体,也是没有价值的。理论是产生成功预言的“黑箱”,后继理论不可能更接近于对微观实体的正确描述。
普特南提出“宽容原理”(the principle of charity)来反驳这种观点。宽容原理的意思是说,为了避免我们解释中的许多错误信念或不合理的信念,我们应该经常把不同理论中的相同术语的指称看成是同一的。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个原理。接受了这个原理,就等于是接受了一组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不管是以直接引进事件的方式,还是以间接向别人学习的方式,一旦把一个术语引进到某人的词汇当中,在这个人的用语中,这个词的指称就是固定的,一旦指称被固定下来,人们就能用这个词阐明关于这个指称的许多理论,甚至阐明这个指称的理论定义是否是正确的科学描述,这样就使一个科学术语成为跨越理论的术语。例如,如果“电子”这个术语跨越了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变化,仍然保持它的指称,那么,“线圈中有电流”就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做到把适合于一种语言的真理和指称的概念看成是跨越理论的概念。①Hilary 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202.
基于这种反驳,普特南从一个术语的“意义”出发来论证自己的实在论立场。首先,他认为,客体与存在概念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客体的概念不能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因为除了概念选择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逻辑概念的用法。或者说,如果没有阐明所使用的语言来谈论事实,只是一种空谈。因为在普特南看来,“意识到存在量词本身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形式逻辑的规则相一致的方式——来使用,是很重要的”②Hilary Putnam,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The Paul Carus Lectures,p.35.。其次,他认为,一个术语的“意义”比一个语句的“意义”更重要。指称不仅是一种“因果联系”,它也是一个解释的问题。解释在基本意义上是整体论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而不是彼此独立的。“意义”是一种“用法”,并不是对意义的定义。为此,普特南承认,他的“内在实在论”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实在论(pragmatic realism),它提供了使实践和世界中的现象具有意义的一个图像,而不是寻找“上帝之眼”的观点。对世界的这种图像只有通过科学的成功才能证明是正当的,或者说,关于实在论的肯定论证是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一种奇迹的唯一哲学。
有意思的是,当普特南运用所提出的量子思维,完成了他对内在实在论思想的论证,并于20世纪90年代又从内在实在论转向直接实在论之后,2005年,他却又在《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发表了《哲学家再次看量子力学》一文。③Hilary Putnam,“A Philosopher Looks at Quantum Mechanics(Again)”,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6,No.9,2005,pp.615—634.在这篇文章中,他不是为量子力学的某个特殊解释进行辩护,而是颠倒过来,反而又以内在实在论为前提,对量子力学的解释进行分类研究。他在这一篇文章的开头,首先重申了1965年的文章的部分观点。他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物理学家中间流行的操作主义是错误的,因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电荷、质量等概念时,他们是在讨论能够通过其形式特征、所遵守的定律系统及其效应区分出来的一个特定的量。从字面上把关于电荷、质量的陈述“翻译”为关于可观察量(比如,仪表的读数)的陈述是一种曲解。对于实在论者来说,与量子力学相关的所谓解释问题是,如何用与实在论相一致的立场,来理解量子力学的问题。
普特南之所以在事隔40年之后,再次撰写《哲学家再次看量子力学》一文,是由于他在1965年的文章中,没有把贝尔不等式和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考虑在内。所谓贝尔不等式是指贝尔在1964年证明基于定域性假设证明了一个能够通过实验证实量子力学与隐量变理论哪个正确的不等式。1982年以来的大量实验支持了量子力学,而不是隐变量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普特南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说明,物理学家对待量子力学态度所发生的变化。他说,他在1962年与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讨论量子力学问题时,这位物理学家一开始对他说“你们哲学家总是认为理解量子力学是有问题的,而我们物理学家自玻尔以来已经更好地理解了量子力学。”结果,他们坐在剑桥的长椅上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位物理学家对普特南说:“你是对的,你使我相信,这里确实是有问题的,不过,很抱歉,我不可能花几个月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普特南说,当在200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再次听到这位物理学家关于夸克理论的报告时,却发现,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说:“根本就没有关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玻尔是对一代物理学家进行了洗脑。”①Hilary Putnam,“A Philosopher Looks at Quantum Mechanics(Again)”,p.619.
普特南讲述的这个小故事表明,与20世纪的第一代物理学家相比,当代物理学家已经完全接受了量子力学的语言体系,并且,习惯于运用这一语言体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普特南认为,用与实在论相容的方式,来理解量子力学的问题,首要前提是先明确量子力学在说什么。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假设出发,来理解量子力学。他正是基于对量子力学的理解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抛弃了经典实在论,形成了他的内在实在论的观点。
戴维·拉斯姆森(David Rasmussen,波士顿学院哲学系教授):我是第一次来中国,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同行一起分享对希拉里的怀念。我自己是做科学哲学出身的,毕业后却做了政治哲学和欧陆哲学。哈佛大学正在编纂普特南的文集。我与主编马里奥·德卡罗(Mario de Caro)教授有着很友好的关系,因此从他手上得到了不少新材料,其中包括希拉里生前还未发表的一些文章。今天我想与大家共享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尤其是在该文集第三卷的序言里面,讲到对普特南哲学的贡献之处。
我自己在波士顿大学工作的时候,在学习小组上与希拉里和他夫人Ruth Anna开始接触。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人。60年代初左派思想在美国很流行的时候,他们夫妇也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影响。我有一个学生想让我指导他做关于普特南哲学的论文,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找普特南教授本人,他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于是我把这个学生推荐给了希拉里。我认为希拉里最为重要的转变是在后期转向实用主义道路,尤其是他在“三个杜威演讲”(three John Dewey lectures)中所表达的想法。这是我特别想与大家分享的地方。
我们先简单看看希拉里学术生涯的发展过程。他年轻时候把精力放在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上。60年代在心灵哲学领域里发明了计算功能主义,到了1988年又自己放弃了计算功能主义,尽管之后还有很多人继续在为这个功能主义进行辩护。同时他和克里普克在语言哲学领域里发展了语义外在论,提出了词语的意义并不在头脑中的著名的判断。塞拉斯区对外在对象的科学形象和日常形象作出了区分,桌子在科学形象中是由微小的分子组成的,而在日常形象中则是我们可以眼睛看到、手触摸到的具有特定性状、重量、硬度、温度等性质的物体。而在希拉里看来,科学形象和日常形象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看法与他对一系列哲学二元之分的批判相一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晚期的对事实和价值二元之分做出了系统批判。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个二元之分的批判,是在一次他与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朋友聚会时谈起的。哈贝马斯在其他的学术演讲中也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在希拉里的早期学术生涯中,他批判了一些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坚持的约定主义,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实在论。在80年代,他又发展了内在实在论。内在实在论试图在超越笛卡尔式的二元框架的前期下为科学实在论寻求辩护。正是因为他抛弃了笛卡尔式框架,使得他能够进入到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寻找他的理论的资源。他在学术生涯的最后10年中,把精力放在我们称之为对于世界的道德形象的问题上,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试图辩护一种在实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学。
我刚才提到的哈佛大学正在编纂的《普特南文集》第三卷的前言,仔细分析了普特南哲学的一个特点。我认为它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是他在进行实在论讨论中逐渐发展并最终成熟的。自然主义不再去预测超自然的原则。Mario De Caro把他的自然主义称作“自由化的自然主义”(Liberal Naturalism),并为之总结了一系列特征,比如多元论等等。其中第八个特征是说,人类常识性的世界观(commonsense worldview)并不需要科学来建立,在科学基础主义和常识性的世界观冲突的时候,科学基础主义只能改变自己而不是变动常识性的世界观。这个也是蒯因的看法。形而上学无法对世界进行完全的描述。希拉里的自由化的自然主义在后期转向了规范性问题。价值这个东西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具有先天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论规范和道德的规范都无法还原到某些先天的形而上原则中。因此,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的时候我们在具体的活动中根据不同种类的需要,可以区分某些规范是知识论的规范而另一些规则是道德规范。然而,这个区分一旦被哲学家上升到形而上学,则是希拉里所反对的。正是他这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固定区分的质疑,使得他很自然地进入到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进而批判整个西方哲学,反思西方哲学根本性的看法和根本性的态度。
这个有着45页篇幅的前言系统地梳理了普特南哲学的发展进程。大致上来说,前期的普特南哲学主要是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而后期的实在论发展导向了自然主义的发展方向。对自然主义目前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认为所有的哲学的命题最终都要由自然科学来判断其真伪,而哲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科学。第二种对自然主义的理解方式认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无法独立于科学,因为对世界描述是科学所给出的。它并不认同第一种对自然主义的理解方式,即认为任何哲学的问题都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第二种理解方式和第一种理解方式区别是,在第二个理解方式看来,对世界的描述总是建立在某种局部的视角之上的。这两种对自然主义的理解基本上主导着当代分析哲学的主要思想。希拉里则提供一种和这两种理解方式不太一样的理解方式。希拉里同意哲学依赖于科学对世界的描述这个看法,但在后期他坚持说,即使是物理学对世界的描述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尽管物理学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最好的科学,它依然是建立在自己的视角之上。
(责任编辑:肖志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