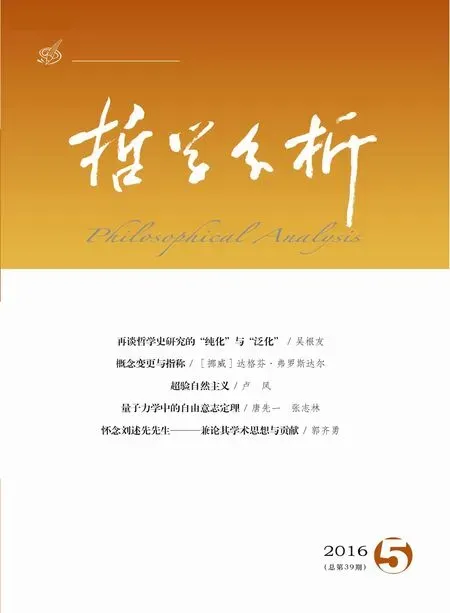个体:从类、性到关系和普遍相关性
王中江
个体:从类、性到关系和普遍相关性
王中江
一般所谓物和个体的性质和普遍性,一般所谓物和个体的特殊性和个性,真正讲来只是事物和个体内在关系的相似或不相似。同一类的个体,它们自身的关系是相似的,否则就是不相似的;同一类个体中的每一个体的不同,在于每一个体都存在着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唯一独有的关系。个体自身就是关系体,它自身的关系体又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浑然一体的关系之中。万物整体上是所有个体的关系体,世界整体上是一个关系的世界。
个体;类;关系;相关性
为哲学的探讨寻找一个出发点非同寻常,哲学上的一些主要不同往往也是从这里发生的。①古代中国的部分哲学家们以经验世界的物和有为根本的前提去解释世界;现代英美的新实在论者诉诸常识来支撑什么存在的大厦;在当代哲学家中,蒯因(W.V.O.Quine)从何物存在这一简单性的本体论问题入手走向本体论的承诺。有关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参阅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江天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我想从“物”(thing)和“个体”(individuals)的概念开始进入到现实事物的存在及其何以如此的探寻历程之中。进入世界的大门和观察世界的窗口有许多,在任一大门和窗口都可以看到和接触到事物和个体,它们不计其数,花样繁多,只要不是视而不见,谁都会很自然地肯定世界上存在着个体和事物。我想补充的是,这种肯定不能只是意味着蒯因(W.V.O.Quine)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世界而作出的一种本体论承诺,而没有说出任何意义上的本体论事实。②对物(everything)的本体论承诺当然不能等于同本体论事实,但不能说本体论承诺中没有任何本体论事实。中国哲人们相信,天地世界中存在的是万物:“有天地,然后天地生焉。盈天地之间者惟万物。”即使像小说中也包含有“真实性的”东西,虽然它的整体故事不是陈述具体的事实。参阅金岳霖的《真小说中的真实性》,参见《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7—386页。对于大量的现实个体和事物,哲学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如若有一种哲学,它深刻到连基本的事实都容纳不进去,我敢说这种哲学就失去了它的最低限度的真实性。我的这一立场可以叫做现实实有论。
一、从物和个体到类和个性
现实世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物”和“个体”,它们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实在性。对此我深信不疑。真正让人感到为难的是,一般所说的物和个体究竟是指什么。物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非常古老的术语,而个体则不是。但中国哲学中物的指称或外延实际上主要是指个体事物。①我倾向于斯特劳森的做法,将在近似的意义上去使用这两个词。参阅彼得·F.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江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此,我不涉及古代中国哲学家们对物的起源的解释,我关心的是古代中国哲学家们说到物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什么。照荀子的说法,在各种不同的名称中,物是一个最普遍的名称。根据中国哲学的名实论,名称是对实际事物的命名和概括,为事物命名的目的是为了辨别、说出它们。②有关名与实的关系,《公孙龙·名实论》说:“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物而不过焉,实也。”物作为一个最普遍的名称,它是对所有实际的事物作出的命名和概括,它指称和表达的是所有实际的、实有的事物。
至于这种实际的实有的事物具体又是指什么,中国哲学家们大都没有进一步涉及和明说。③这不是说他们对“物”没有描述。按照《庄子》和《列子》两书中的看法:一切具有“貌像声色的东西”都是“物”。据此,物是“貌像声色”的东西。我推测,他们使用物这一概念,基本上是指称和表达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所有事物的种类或类别;二是事物所有种类中的所有个体。这可以从中国哲学家们广泛使用的作为物的同义词的“万物”的名称中得到佐证。④按照中国哲学的看法,物与类是相伴而生、相伴而存的。《国语·晋语六》说:“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类。”《荀子·劝学》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列子·周穆王》说:“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就于物类。”《周易·易传》和《战国策》有“物以类聚”的观念。《庄子·秋水》篇中有“号物之数谓之万”的说法。这里的“万”同“万物”中的“万”一样,看上去它虽然是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显然它不是指世界上实际的事物只有“一万个”种类,更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万个”个体。⑤《庄子·则阳》对万物的“万”正好有一个说明:“今计物之数,不止于万,而期曰万物者,以数之多者号而读之也。”“万物”的“万”是用一个大的具体数字既表示宇宙中不计其数的无限众多的事物种类,又表示无限多的个体。它的量词是“种类”,也是“个”。⑥正如金岳霖指出的那样,现实化的物并不都是以个体而存在的,有些具体事物如水、空气、土壤等,就很难说它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但如果我们从它们存在的具体空间来看,譬如水是处于一个湖泊、一条河之中,湖泊和河流都可以说是个体。因此,如果将物的概念换成近似意义上的个体,物的种类和个体问题,就可替换为个体的种类和个体的数量问题。世界中大量存在着个体之间相比作用而产生的象,如同《周易·系辞传》所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和裴頠说的“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崇有论》)那样,物始终是同形和体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上的事物无限多样,事物的种类不计其数,个体的数量无穷无尽。事物的种类很可能像个体那样,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少。凭借一些专门领域的统计,我们知道了世界上部分生命种类及它们的个体数量,比如地球上人类个体的数量;再比如地球上部分动物的个体数量(有的很多,有的很少;有的已经灭绝了,有的快要灭绝了)。我们努力弄清和掌握某些种类及它们中的个体,同我们偏爱它们有关。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更关心事物的种类而不是它们的个体的数量,比如病毒和细菌。如果说用专名或私名指代的都是个体,原则上宇宙中所有事物种类的所有个体都可以有专名或私名。由于实际上我们无法知道宇宙中所有个体的数量,我们自然也无法使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专名,这也没有什么必要。世界上大量的个体都是默默无名的。已有的专名基本上满足了我们指称一些个体的需要。一个总的趋势是,相比于类名的不断增加,个体专名的增加更快更多,这是因为我们接触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扩大,我们认识到的不同种类的个体越来越多。
宇宙中具体的实际事物(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和个体是主要的实有和存在者,所谓的东西这个名称主要也是指代个体性的事物。有些东西像液体、气体不好区分它们的个体,但大海、河流仍可以说是一个个体;一个沙漠是一个个体,沙漠中的沙同样是个体,不管它是大些还是小些。沙子这个词形象地说明它是一个个的个体。个体的“个”当然是可数的一个个的“个”,个体的“体”都是某一个的“体”。每一个的个体是“唯一”的一个,又是唯一的某一个的“体”。这就决定了一个事实,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完全替代另一个个体,哪怕看上去它们极其相似以至于我们无法区别它们,但它们仍然是各自的个体。具体事物的“体”,直观上看都有形、有状、有象。它们的形状千姿百态,它们的“体”有大有小,有的非常巨大,有的非常细小。中国哲学中所说的“至大”(实际上是极大,并非“无外”)和“至小”(实际上是极小,并非“无内”)。“天”和“地”曾被中国哲学家们认为是两个巨大的个体(“有形之大者”),生物学中的微生物是比较细小的。巨大和微小一般都超出人的视力范围,我们需要借助工具去观察它们。望远镜满足了我们观察遥远巨大个体的愿望,显微镜适用于我们观察细小的东西。这两种工具的不断改进,使我们观察极大、极小尺寸的个体都在改观。彭加勒(H.Poincaré)说科学研究的事实有等级之分,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选择的事实是否简单。科学家们在两个极端下寻求它们,一个是无穷大,一个无穷小。天文学家面向无穷大的星体,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面向原子和细胞等,他们都发现了无限奇妙的世界。社会学家面对复杂的人,他们用了很多方法但结果最少。①参见昂利·彭加勒:《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11页。所谓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简单,就像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的编者说的那样,表面的单纯可以隐藏复杂;①参见罗素:《数理哲学导论·编者注》,晏成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看上去复杂的东西原本也可以是简单的。人类大多数学科的研究领域,不是无穷大或无穷小这两个极端中的事物和个体,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事物和个体。
一些哲学家一直说我们看到的个体的“体”,都是它外观上的形状和现象,我们看不到它们的内部特别是它们内在的东西。现在借助工具比如透视,已使我们能够看到某些个体内部的形状和形象了。就我的观点来看,不管我们看到看不到,当我们说到个体的“体”的时候,它指代的是这一个个体的全部或它的整个的东西──从它的外部到它的内部,从它的结构到它的机能、作用和它的整个过程等等。按照墨家后学“体”分于“兼”的说法,“体”是指组成个体的各个部分,“兼”是指一个个体或事物的整体。我所说的“体”就是一个个体的整体,它类似于荀子所称的“万物同宇而异体”的“体”。荀子这句话还向我们指明了一点,万物的个体都存在于宇宙中但它们又是不同的个体。为什么说它们是不同的个体呢?
说个体不同,一是指个体属于不同的“类”;二是指同一类的“个体”又有它们各自的个性差异。对任何具体事物和个体进行描述和界定,就要使用各种一般的名词、形容词和概念等。用专名或私名表示的具体事物和个体,虽然它们的名字中也有名词等,但这些名词一般不表示它们的类,也不表示它们的差异。此外,当说一切都是物、一切都是个体的时候,物或个体就是唯一的类,也是全部的个体之物;这是最普遍的类,也是外延最大的类。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大共名”,也是哲学家说到最高处的“道断”之言。但说个体有不同的类,个体又有差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和东西。
对于解释事物、辨别事物和运用事物来说,“类”这一概念既非常重要,又非常难以把握。②这里我们无法讨论类的各种问题。首先,如上所述,世界上的事物、个体的种类,非常非常之多。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事物的种类的数量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将所有的分类方法都使用上,事物的“种类”的数量可能会极大,但是否会多到一个绝对的“无数”这是一个疑问。事实上,它非常有可能是有限的众多,但究竟有多少,恐怕我们永远都难以说清。如地球上的生物,单是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或者单是海洋的鱼类,它们的种类就非常多,人类已知的,仍是其中的一部分。相比于事物的种类来说,事物的个体就更多。个体一方面可用名词来描述,一方面要用专名来表示。不管个体有专名还是没有专名,它们是空间上的有,实际上它们就是空间本身。
更重要的是,对个体进行分类主要依据什么。抽象地说,它依据的是个体的实质性的东西,类就是一个近似地表达个体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念。我不同意罗素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事物的“类”仅是或只是一个逻辑构造(甚至虚构)①如他说:“类事实上像摹状词一样是逻辑的虚构。”(罗素:《数理哲学导论》,第170页),是一个命题函项,是完备的符号语言中可定义的东西,它不是未定义的符号所表示的“世界上的最终内容”。一般的类的符号或者代表特殊的类的符号都不能列入到未定义的符号中。罗素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从外延上将类看成实体、个体或者是一堆聚集起来的东西。罗素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不会将“类”看成是由专名指称的个体或者是一堆具体的东西,不会认为类是指特殊的实体。承认这一点,不意味着类是逻辑构造甚至是虚构。追求“健全实在感”的罗素,对实在的感知和看法让人捉摸不定。在他一生哲学发展似乎是盖棺定论的最后阶段中,他说他的哲学发展过程始终保留着一些基本的信条,如相信真理有赖于对事实的某种关系,相信世界是由许多相关的事物构成的,相信句子的构造一定同事物的构造有些关系等等。②参见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2页。迈尔(Ernst Mayr)前后对类的看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纠正一下罗素,纠正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蒯因。起初,迈尔从唯名论立场出发,认为“类”就像“家具”那样的概念,它只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而没有存在论的意义。自从他到了新几内亚探险之后,他改变了这一立场。他在那里收集到了一百多种鸟,当地人称呼这些鸟也有一百多种名字。当地人意识中的“种”的概念同欧洲人的“种”概念具有高度的类似性。这促使迈尔改变之前对类的唯名论立场,开始相信“类”和“种”的概念具有存在论的意义,而不只是语言学上的意义。
蒯因对类的说法,有的可以接受和保留,有的不能接受而要抛弃。他说,类是抽象的东西,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具体的存在和有。比如,石头的类和一堆的石头不同。一堆石头是具体的对象和有,它跟成为它的分子的石头一样具体,但这一堆石头的类不能等同于这堆石头。“因此,类是抽象物;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把它们叫做汇集或聚集,但是它们是共相。这是指如果类的话。”③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江天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蒯因区分普遍词项或谓词与单独抽象的词项,认为类属于抽象的单独词项,它是为抽象的或具体的东西命名。普遍的词项或谓词,它或者适用于一个东西,或对许多东西的每一个都适用,或者对任何东西都不适用。“类”要用模式变元的值来约束④同上书,第92页。。类本质上是概念性的而且是人造的,“类”是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蒯因的这些说法只是说对了一部分,他没有说出的部分是他要否定的东西。
蒯因区分本体论承诺和本体论事实,反对将本体论承诺等同于本体论事实,认为存在不依赖于语言,谈论何物存在则依赖于语言,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蒯因承认有作为抽象物的类或属性的东西、共相(他说具体的东西再加上类,这就是一般言谈所需要的全部本体论,也是数学所需要的一切)①蒯因将类与共相和属性视为同义。我使用“类”的概念,将从共相和属性思维转到关系思维上。,但他根本上将“类”看成语言和逻辑构造,看成只是“本体论承诺”,而排除类在本体论事实方面的任何信息,这是不可接受的。承诺与事实、语言与存在有区别,不表明它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不表明用语言谈论不依赖于语言的存在就只有语言学上的意义。蒯因在本体论承诺与本体事实之间,在语言与存在之间作出区分不是问题,问题是他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让承诺和语言不透露存在和事实方面的任何信息。“类”不等同于存在物,但也不能由此说当我们使用类时我们只是纯粹使用一个语言符号而没有用它表示任何东西。蒯因走得太远了。在他那里,不只是类,也不只是哲学,各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探讨,最终都成了这一个领域的语言和逻辑选择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语言和选择再简单,不同领域彼此再包容,我们对这个世界依然是一无所知。他的这种实用主义是够彻底的,但非常不切实际。
我不否认“类”作为一个名称或词汇具有语言学方面的要素,它是音、形、义的统一体,它可以写出和读出,但当它被用来表示一类事物时,当它被作为一类事物的名称时,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语言符号,它指称着一些具体的事物和个体,这是它的外延;它还表示、表达着这类事物的一些重要的共同的东西,它是这一类名的含义。至于它表达了多少,表达到什么程度,这则取决于我们对这类事物的认知程度。比如物理学家用粒子表达一类物理事实,他们对它表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他们对粒子的认知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也承认,语言和词汇是人类的发明,但这种发明同事物和个体是有关系的,就像犁耙同土壤和耕种有关系一样。作为木质的犁耙,它本身没有土壤的东西,但它是适用于土壤的特性并能同土壤发生良好关系的工具,语言的起源也是如此。我们用类名表示一类事物的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属于语言的东西,而是属于事物的东西,至少我们认为它是属于事物的东西。退一步,即使我们弄错了具体事物的那些东西,“类”名仍然指称着具体事物和个体,只要还有一个个体,这个“类”的外延就不是空的,这个类名就不能只是一个语言符号和逻辑构造,更不是逻辑虚构。它是本体论承诺,但它也表达了本体(更准确地说是个体)的部分事实。在这一点上,罗素有一个说法是可取的。他说:“就像一个具体的人名意味着一系列细节一样,‘人’这个名词也意味着一大群不相同的人。这群人由于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或者共同的秉性,而形成一个整体。所有的人都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相似,因此我们只需要一个名称就能够通称他们。”②罗素:《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1页。将“类”同“个体”统一起来(个体的类和类的个体)看①“零类”或“空类”,从具体化和现实化角度来说,至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本有个体的类,由于它的所有个体都没有了,它就变成了空类(如恐龙);一种是原本就没有个体的类,如中国人所说的(“龙”)。,类就是表达具体事物和个体的某种共同的东西,不同的类则是表达不同种类的事物和个体的不同的东西。简单说,这就是“同类之同”和“异类之异”的问题。现在要问的是“同类之同”何在,“同类之异”又何在。
二、个体之异与同:相似和不似
事物和个体的异同有不同的情形,它有个体在同一种类上的同,又有在不同种类上的异和在同一种类中的异等。分类方式不同,个体的同异所在自然也不同,但它仍然是有同和有异,不管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一类个体相对于其他一类的个体的异,这是个体的类别之异,这是个体的大异;个体在同一类别之下的异这是它的“小异”。反过来说,属于同一类别的个体它们是相同的,它们的这种相同又是它们的大同,而它们之间的异则是小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绝对相同的个体,所谓同一类别的个体的同和同一类别个体的异,都有一定的伸缩性和相对性,因此,我更愿意用相似和不似去表示个体的异同。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类”是指种类相似(“惟犬最甚”)。孟子对类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②荀子的说法也可以借用:“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荀子·正名》)犹如维特根斯坦说的家族类似和概念图像,类或共名表示的是一类事物的相似性或某种相似特征。类不是具体的存在,但它是一类个体“共具”的东西。反过来说,不同的类的个体,它们的不同就是它们的不相似。据此,个体在类别上的大同就是它们的类似和近似;它们在不同类别上的大异和在同一类别中的小异,就是它们的不似;用近似性去描述个体在种类上的相同性,可以避免将类之间的界限绝对化,避免用一个过分强的标准去识别和要求个体,为同一类别个体之间的小异留下了更为方便的解释空间。
在类的视角下,事物和个体的相似和不似是指什么呢?换言之,“类”所表达的本体或实体方面的事实是什么呢?按哲学上的一般说法,类被认为是事物或个体的共相或属性。个体的类的共同和相似,就是它们具有相同的共相和共同的属性。对某些实在论者来说,事物和个体的共相或属性,就像个体和实物那样也是客观的实有。蒯因虽承认作为抽象物的类是共相或属性,但他不承认类是实在,更不承认它是存在。斯特劳森(PetetF.Strawson)认为类是一类事物的共相和特征性共相,它是由抽象名词、共名和形容词构成的。相比于殊相由事实构成,殊相的思想是完整的思想,共相则是对事实的抽象,它的思想是不完整的或不必是完整的。
从共相和属性去解释类的一般性的做法又如何呢?它是我们要放弃的本质主义或性质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广泛存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中国哲学传统也不能说没有。本质主义思维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常常用性质、形式、共相等来看待一类事物,认为每一种事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属性(其中包括将事物的性质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做法),认为同一类个体的差异在于它们的个别性、质料和殊相。本质主义思维在语言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主—谓”形式,其中的主词有专名,也有名词;谓词有类名、名词和形容词等。本质主义在中国哲学中的部分表现是以道、天、天理、气等为万物的最高本质,以此去说明事物的共同本性。中国哲学中不同形式上的本性论、良知论,或人性、佛性、道性等,也是不同形式的本质主义。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哲学更带有本质主义的特征。只是,相对于西方,中国的本质主义思维要弱些。
对本质主义思维已有各种各样的批评,这些批评首先来自西方哲学内部,也有一部分来自突出中国哲学独特性和长处的一些人士。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解构者,怀特海批评本质主义犯下了“自然之两分”(Bifurcation of nature)和“具体误置谬误”的错误,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等等。本质主义者常常抱着头头是道的二分法:以个体的共相或理为实、为体、为本、为真,以个体的特殊、个别为用、为现象、为幻。沿用存在与本质二分的方法,我们当然可以说存在即本质,本质即存在。熊十力建构的“体用不二”的哲学,要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在本质与存在、体与用的概念上纠缠了,我们要从中跳出来,立足于另外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和事物。
我们再看看哲学上一般是如何解释同一类个体的不同、差异和不似的。所谓凡物莫不相异,所谓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都表达了同类个体之间的差异。为什么说同类的个体是不同的呢?这是一个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十分复杂的一般所说的个体的“个性”问题。用个体性、个体实质(一种意义)、材料、殊相、特殊(特别性)、个别等概念来说明个体的纯粹的“自我性”、独一无二性,甚至用纯粹没有任何性质的“能”等去说明个体的个性,是本质主义思维的一部分。金岳霖说他的“能”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程朱理学的“气”,正是它给予了个体的统一性和个体性。它没有任何性质,它是不可表达的“X”。①参见金岳霖:《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第74页。
在我来看,只要是有和实,都可以知,也都可以表达。这同样适应于康德设想的不可知的“物自体”(它是“现象”的原本,现象是它的复本)。如果它确实是有的话,它就是可知的。我们所知的个体的一系列现象,就是个体自身的“体”。罗素批评康德的“物自身”说,如果物自身引起了现象间的许多差异,那么物自身之中必也有些差异对应于这些差异,不断地追究下去,真实界与现象界十分接近。①参见罗素:《数理哲学导论》,第60—61页。罗素指出,预设一个不可知的基体X,犹如“一个悬挂属性的看不见的木钉子,好像火腿挂在农家的屋梁上一样”②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第145页。。但罗素还是留下了一个他认为与科学无关的“难以名状的个体性的本质”。这个残留物同他保留的没有性质的“质料”具有一脉相承性。罗素对构成世界的没有性质的质料界说道:它“就是一些字所指的东西,那些字如果用得正确,就是谓语的主语,或关系的项。从这一种意义来说,我认为构成世界的质料是由像‘白’那一类的东西而成,而不是由有白的性质的物件而成”③同上书,第154页。。这一界说同罗素认为个体同它所有的属性之总和不同的观点相一致。受这一说法的影响,金岳霖认为把许多共相合起来合成不出一个个体,要成为一个体,还需要没有性质的质料或能作为它的底子(共相类似于它上面的花纹)。
将个体区分为质料与形式,或理与气等二分法确实很常见。用没有性质的质料、能去解释个体的这个性、那个性,同用形式、共相、普遍、属性、理等来说明个体的本质彼此对应。许多哲学家一直相信,前者是对个体的“具体”的说明,后者是对个体的“抽象”的说明。如果说共相、形式或性质只是个体的抽象物,那么只作为名字的质料X怎么能够同它结合到一起而成为具体的事物和个体呢?深究起来,它有着严重的困境。姑且用形式、共相与质料(或能)二分的做法,如果个体是一个合体,那它的形式的部分与它的质料的部分原本都有着对方,骨头里有材料,肉里也有形式,没有纯粹的自身中没有形式的材料,反之亦然。质料本身就有形式,它不是光秃秃的头,要等着形式给它生出头发和戴上帽子。形式本身也有材料。当金岳霖说“所有共相和殊相的总和将使我们达到不可表达的X”时,他已经接近了作为质料的X实际上同时就有着共相和殊相本身。
同一类个体的差异,不能用没有性质的质料去解释,用殊相和个性去解释也走不通。因为我们所说的一个个体的个性总可以用在同类的其他个体上。认为个体的差异是属性在事物和个体中的表现强度不一样,或者它是使得事物和个体彼此相似的特征在不同的个体中具有不同的强度,这种以理念论为基础的解释,就意味着现实的个体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和模型。我们不接受理念论,当然也不接受个体对理念表现的强度说。解释个体的差异,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个体不可分割,它保持自我同一,它不能为任何他物个例化,它不能成为任何他物的谓项,等等。这些说法都是类似于“X就是X”的自语重复,它没有说出个体差异的实质性的东西。从个体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来看,处在相同时间段的个体很多,它的时间不是唯一的;与此不同,一个个体占据的空间则具有唯一性,即便它移动了,它还是有一个空间。这算得上是区分个体差异的一个外在方式。
同一类别个体的个体性、个别性究竟何在呢?同类个体的同是它们的类似性,同类个体的差异的不似,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去描述它们,也可以用非常严格的方法去判断和识别它们。个体在这种意义上的不似必须是它的“唯一的”东西。从人来说,每个人的长相好像都有“唯一性”,他们的长相为什么不同呢?生物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帮助了我们。生物、生命都具有“基因”,这就造成了某类生物的“相似处”,但每一个生物个体和生命个体的基因又都有唯一的不同于其他个体的不似处。每个人都拥有人类的相似基因,这使人类成为一类,但每个个体又有自己独有的不似的地方,它是唯一的,这就造就了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个体的个体。人类的指纹相似和每个人指纹的不似与此同理。这好像又回到了万物种子说。在没有永恒不变或不一成不变的意义上,不妨说人的基因就是人的种子。正是它造就了个体的相似性,也造就了个体的差异。还有,从个体的过程来说,每一个个体的一切不是其他任何个体的一切,就像一个人的一切经历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那样。①从任何个体来说,它的唯一性要通过玻姆指出的众多的特性来确定。参见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秦克诚、洪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1—183页。除了生物和生命个体之外,大部分无生命、无机的同类个体,它们之间的个体差异也一定取决于能够使它与同类其他个体区别开的不似之处。对人来说,世界上的大部分个体不需要辨别和区分,只有那些重要的才有专名去区分它们。
三、关系:个体之内
个体的同类相似不在于它的共相和性质,同类个体的个体差异、不似也不在于它的殊相和特殊,那么个体的同类相似(异类不相似)和同类个体的差异及不似,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呢?我们要另起炉灶,若先作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那就是个体根本上是一个“关系体”,而不是什么属性和殊相、形式和质料的混合体。我希望进一步促成哲学上的转变——即从“本质”、“性质”、“属性”思维转向“关系”、“关联”思维,从共相哲学转向关系哲学和世界观。②同关系相近的联系、关联、关涉等概念都将出现在我们的用语中。在某种意义上,性质和作为词尾的性字仍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至少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指称事物的关系,如相关性、交互性等。
将目光转向关系概念和关系的世界,就是从本质主义或性质主义思维中走出来,从共—殊二元论中走出来。“关系”(relation)一词源远而流不长。要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就被作为存在论的十个基本范畴之一被而提出了。但之后它默默无闻,直到晚近它才又受到哲学家们的注意,逐渐成为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在需要的限度内接触到哲学上的这一新传统。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哲学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我赞成这样的判断,也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关系思想。①参见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但遗憾的是,汉语言的“关系”一词出现得很晚②中文“关系”一词被认为是一个外来词。这不准确,它已出现在中国明代的文献中。参见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概论·自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也不是一个哲学术语。作为哲学术语的关系一词整体上仍然是近代翻译和引入的产物。早期中国哲学中的“相与”、“相待”、“有待”等,还有后来佛教中的“因缘”、“缘起”等,扮演了类似于后来“关系”这个词的部分角色。建立关系哲学或关系世界观,势必要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不同寻常的哲学概念。③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关系”概念已受到哲学家的某种讨论,比如金岳霖(参见《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4—268、587—600页)、张东荪(《知识与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70—230页;《层创的进化论》,参见《新哲学论丛》,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16—349页)、张岱年(《真与善的探索》,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52—162页)等。在当代,深受怀特海有机思想影响的唐力权主张“场有哲学”(参见《脉络与实在》,宋继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93页),罗嘉昌提出了“关系实在论”的概念(参见马丁·布伯:《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为此,我们要广泛借助东西方新老传统的已有的“关系”概念思想资源及其相关资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画地为牢,反对将两者对立起来和人为设置的非此即彼的教条主义。主张有机哲学的怀特海说“就一般的立场来看”,他的“有机哲学似乎更接近于印度或中国的某些思想特征,而不是像西亚或欧洲的思想特征”④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页。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以“我与你”为主题深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性”思考,这是一种狭义的关系哲学。参见他的《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但意味深长的是,生命主义和有机主义哲学恰恰又诞生于现代欧洲。同样,又正是西方部分汉学家在中国哲学和思想中发现了有机主义、整体观、自然的连续性和关联性思维;⑤李约瑟引用张东荪的东西哲学的比较,按照这个比较:“欧洲哲学倾向于在实体中去寻求真实性,而中国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去寻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9页)“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关注着关系,所以就宁愿避免实体问题和实体假问题,从而就一贯地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西方人的头脑问的是:‘它本质上是什么?’而中国人的头脑则问:‘它在其开始、活动和终结的各阶段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它做出反应?”(同上书,第221─222页)张东荪认为,东西方哲学和思想一开始就受到了语言形态主谓不分明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注重实体还是注重关系的差异性。(参见张东荪:《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参见《知识与文化》,第189—198页)李约瑟引申说:“在所有的中国思想中,关系(‘连’)或许比实体更为基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21页)卡普拉(F.Capra)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的整体观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中看到了两者的一些契合。晚近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们正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反过来将这看成是中国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异,将东西方思想二元化、两极化,就像好长时间中盛行的西方物质主义、东方精神文明的错觉那样,不幸的是这种错觉至今还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解铃者与系铃者可以是一个人。机械主义、启蒙理性和技术文明诞生于西方,反思和批判这些东西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环境哲学等也兴起于西方,①用艺术和形象的方式表达生态理念,尚恩·莫森(Shaun Monson)导演了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地球公民》(Earthlings),另一部是《万物一体》(Unity)。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
关系无所不在,我深信这一点。金岳霖曾这样表达这一本体论事实:“关系比比皆是。没有联系的实体这种思想,尽管本身在逻辑上可能是没有矛盾的,但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有些事物,我们有时的确说,它们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但是,这样一个陈述中蕴涵的东西,仅仅是对某种特殊的关系或恰巧成为我们注意的问题的关系的否定。在任何特殊的方面是没有联系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没有事物是没有联系的。”②金岳霖:《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王路译,载《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整体上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性质的世界。从这里出发,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世界。
一般都将关系看成是事物或个体之间的事,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也不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多少种关系。比如罗素认为任何关系都有关系者,它们构成了任一关系的关系项。构成关系的关系项至少要有两个,它也可以是三个、四个或者更多。在序列概念之下,罗素讨论了“非对称性”、“传递性”和“连通性”等关系类型。罗素眼里的关系,有事物和个体之间的事,而没有事物和个体自身中的事。莱布尼茨和布拉德雷的哲学有许多引人注目之处,在关系概念方面同样如此。他们对关系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认为关系不真实、不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概念太狭隘。不过,他们的质疑反而刺激了关系概念的发展。
莱布尼茨受限于性质概念和传统的主谓命题形式(这是上面已批评的),又只是从个体之间看关系,这就束缚了他的关系概念。如果他认识到关系不限于个体之间,它同时(或者是逻辑上的首先)发生在个体之内,个体的关系首先可以用一般的“主谓形式命题”表达;如果他认识到个体之间的关系项没有什么占有空位的问题,它们的联系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非常多样的,个体之间的判断形式就像罗素所说的那样也不限于主谓③参见《罗素文集》(第1卷)《对莱布茨哲学的批判性解释》,段德智、张传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0—44页。,那么,他对关系的疑虑就可以消除了。跟莱布尼茨同样,布拉德雷谈论关系既限于个体之间,又受限于性质思维。他推论说,承认事物有关系就要承认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有性质。但关系无法同性质相联,因为关系不等于关系项,不等于任何一个关系项的性质,它是关系项之间的属性。如果关系同关系项没有联系,关系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有联系,它们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要有一个在A、B之外的第三个关系性的东西。假定它们之间存在着使之联系的东西,那就会陷入无穷的后退。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关系不可能。①有关布拉德雷的关系思想,参见金岳霖:《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载《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245—248页);新近的研究参见藏勇:《罗素与布拉德雷关于关系的争论》(博士论文,韩林合指导),2011年。
事实上,关系不限于个体之间,它同时也是个体之内的事;另外,谈论个体不能再安逸于性质上的主谓判断。有必要提到两位先驱人物。一位是怀特海,一位是摩根。怀特海将关系概念同他的有机体概念结合起来,主张哲学的探索要从一般的主谓、实体和性质判断转向事物的关系判断。②要求从性质思维转向关系思维的怀特海强调说:“‘关系’是支配着‘性质’的。一切关系的基础都在于各种现实的相关性。”(怀特海:《实在与过程》,前言)研究事物的随附性,也是基于事物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关系这一前提。金在权说:“我们认为,环绕我们的世界并非孤立的物体、事件和事实的简单集合,而是组成为一个系统,即显示出结构的某种东西,其组成要素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着。这种世界观对我们关于事物的图式来说似乎是极为重要的;它反映在下述常识性的假设之中: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物能够影响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们能够根据一个事物而说明另一个事物,通过关于一个事物的信息而推知关于另一事物的信息,或者通过影响一个事物来影响另一事物。”(金在权:《随附性的种种概念》,载高新民、储昭华主编:《心灵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3页)只是,怀特海的有机概念太泛了,关系并非都是有机关系。摩根(C.L.Morgan)将关系从事物和个体之间引入到事物和个体之内,认为事物和生命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进化和产生新颖性,是因为事物内具的关系改变了。③参见摩根:《突创进化论》,施友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26、69—79页。他说的个体的内具的关系是指事物的结构。只是,个体的关系体不就是个体的结构体。事物和个体的结构只是事物和个体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④摩根的突创进化论中的结构和关系概念,对张东荪的哲学产生了一些影响(参见张东荪:《层创的进化论》,第316—349页);受到摩根思想影响的当代日本哲学家广松涉也主张哲学的探讨要从“性质实体”转变到“关系实体”上。(参见广松涉:《存在と意味·序文》,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
个体本身是关系物、关系体,谈论关系首先要从个体之内开始,从个体之体入手。对我们来说,追问个体的实体,就是追问个体之内的关系。事物和个体没有康德想象的那种不可认知的“物自体”。如果真有什么“物自体”的话,那也只能是事物和个体中的“关系”,但它是可以认知的;事物和个体中也没有金岳霖所说的那种没有任何性质的“能”,如果有的话,它也可以用关系来描述。同样,一般所谓的个体的性质,实际上是个体之体的关系。对个体的所有描述都可以说是对个体关系的描述。现在我们要牢记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关系体。如果说个体和事物都是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就是个体的关系实体;如果说个体和事物都有性质或本性,那么它们的性质和本性就是它们的关系性和相关性。玻姆(David Bohm)说,他从量子力学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整个宇宙不可分割的量子相互关联才是基本的实在,而表现出相对独立性的部分,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特定而偶然的形式。”⑤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根据科学发现的事实,彭加勒(Henri Poincaré)认为科学是一种关系体系,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事物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对象和客体就是作为结合物的关系,只有从关系中才能找到科学的客观性。①参见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2—168页。杜威认为科学主要是研究事物的关系。他说:“人们越来越承认,科学对象纯粹是关系性的,与个别事物的内在品质无关……物理规律所陈述的是某些变化的相互关系,或者是变化的方式和样式。”(杜威:《杜威文集》,涂纪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金岳霖看到个体与关系的紧密关联,甚至从关系上看共相和性质,认为性质不同蕴涵着关系不同,认为对多数所与的联合地进行描述对象就是关系:“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总是靠关系,而一共相之下的个体也靠关系。”②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1页。只是,金岳霖主要以共相立论,认为个体都有共相,共相之间的关联是共相的关联。金岳霖所说的共相的关联,就是共相的关系。我们解构本质主义思维,首先就是解构共相思维,解构将个体的本质归结为性质和属性的思维;其次是解构将个体的实体归结为没有性质的纯粹的材料或能的思维。③如果说构成个体的要素、成分都是不同的材料和质料的话,那么这些材料和质料都是带着性质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带着关系的。在关系哲学中,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没有性质的质料和材料。同一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关系体,它们自身都有着基本的近似关系,不同类的个体它们的关系体当然不同。同一类之中的每一个体自身的关系的差异性,是任一个体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唯一的不相似的关系。④从一类个体对共相或性质的体现程度来解释个体的个性,这是本质主义思维的一个表现。个体在表现一类事物相似程度上有高低,这就需要确定判断一类事物相似性高低的标准。这种做法更适合于自然事物。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这种做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现在还有人想这样做,他会招致来自伦理等不同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每个人都有独自的指纹,都有独自的DNA(除了同卵双胞胎等例外)关系体,它造就了人们某些彼此不同的个性。
事物或个体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层次。从高一层次往低一层次来说,个体的一个又一个的层次,就是事物的关系层次。比如原子、分子、电子等都是事物和个体的不同层次关系。还原论包括生物还原的研究,是对事物和个体的层层关系进行追寻,特别是从高一层次往低一层次追寻。生命体的关系层次更复杂,对它的追寻也更为困难。对于解释个体之内的关系来说,结构是有用的词汇之一。一般所说的事物的结构和构造,多用于形式和架子的意义。据此而言,个体自身的结构或构造,可以说是个体整体关系的支撑部分。整体结构的每一部分又有它的结构,又有不同的层次。整体结构与它的每一部分的结构,又有着复杂的关系。层次和结构只能说明个体之内的部分关系,而不能说明它的全部。它无法描述个体的浑然一体性,无法描述它的动态关系,它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个体纯粹数量的关系中。摩根的突创进化论的一个缺陷,就是将个体的关系等同于个体的结构。
个体的结构和构造起着支撑个体关系体的作用,个体的其他关系则使这个结构充实起来并表现为各种机能和活动方式。个体的结构关系、层次关系,各个部分和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各个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是以紧密、密不透风的内在的统一体方式结合到一起的,就像是具有高度黏性的胶水那样,它们是各种天衣无缝的关系体。借用彭加勒的说法,关系个体是用“永恒的结合物黏结起来的群”,是“被某些天然的和隐秘的亲缘关系约束起来的”。①参见彭加勒:《科学的价值》,第164—167页。有生命的个体的结构和关系同它的血肉处于浑然一体的有机关系之中,处于时间的动态过程中。②单独用概念构造不出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必须用概念所代表的各种具体事物才行。概念与个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常常被不同的批评者混淆。弄清了事物的结构,弄清了构成它们的所有的层次、要素和成分,弄清了个体的整个关系,人工可以制造出一个个体,哪怕是有机体。但个体的历史性和历程性无法被制造出来。
个体作为一个关系体,它是高度自组织和自协同的,它以此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统一性和持续性。这可以叫做个体的关系状态和功能动态。有机的个体自不用说,就是无机的个体也有着保持自身关系体的顽强个性和势力,哪怕它是一块石头、一根木头。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最单纯方面的意义,也有繁多、关系和活动方面的意义,还有“隐德来希”、知觉和欲求方面的意义,这使他的单子自身具有一定的完满性和自足性,使他的单子成为它自身的活动源泉。撇开第一个意义,后两种意义同我们说的个体自身的关系体是契合的。农作物的种子是关系复杂的有机体,人类对种子的改良使它的内部关系达到一种更好的状态。人的自然有机关系体更复杂。人的基因作为人类有机体的密码,包含着人类有机体十分复杂的关系。医学对人体的复杂划分和对越来越多细节和微观的认识,使我们对人体复杂关系体的认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也使人类对各种疾病的治疗越来越具有针对性,效果更加显著。部分疑难病症的疑难之处,就是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认识到它们同人体的复杂关系(器质上的),特别是它的动态关系(功能上的)。
对于人类有机体,我们不仅要关注它的复杂关系整体,而且还要关注它的动态过程。身心的区分(人的关系体显然不是两者就可以涵盖的),特别是将身心看成是两个独立的实体的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两者的密切关系完全割裂了。③身心二元论或心物对立论都是不成立的。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怀特海的看法:“根据有机哲学,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594页)有人温和地修正了它,提出了一个叫做“身心交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m)的弥补性看法(如威斯顿认为某些物质事件和心灵事件彼此互相引用);④参见John Wisdom,Problems of Mind and Matter,London: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37—102。有的人激烈地要彻底地抛弃它(如柏格森等有机哲学家们);还有人在似是而非的意义上说明两者的关系,如将人的眼耳鼻口等看成是同心灵对立的身体的部分,说身体的这些部分不听心灵的使唤,像不懂事的小孩子那样经常哭闹着要这要那。其实它们都是心灵意识的结果,可一直被仅仅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受到抱怨和怪罪。人的身心、形神是最为协同的关系统一体,保持身心的平和或形神的协同是良好人生所不可缺少的。对任何一方的过度偏爱都会造成对另一方的伤害,这同时也是对身心协同关系的伤害。
四、关系:个体之间
从个体之内或个体之中入手讨论个体关系,同我们一般从个体与个体之间看关系的视角不同。但这两者是统一的。个体和事物自身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体,同样,个体的关系从来又都是处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以能量交换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展开,它使世界像无限的滚滚洪流奔腾不息。单从一个个的个体来看,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个体,个体自身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关系体。合起来看所有的个体,将个体之内的关系视角移到个体之间、移到事物之间,个体之内的关系就进入到了个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单从一个个体看,我们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独自性(没有关系),在不同的场合下,我们也会强调它们的独立性和独自性①佩里认为独立性就是非依存性,依存性只是一种特殊关系,这样的独立概念不能成立。参见R.B.佩里:《实在论的独立性理论》,载《新实在论》,伍仁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8—168页。,但要知道这往往都有特定的意义,决不是说它同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李延年的一首诗写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佳人”既“绝世”又“独立”,同人的审美意识分不开,正如庄子所说:“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庄子·则阳》)现实中的个体自身的关系,实际上始终都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始终都是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世界中展开的,始终都是个体之间相互参与和相互交换的过程,这是关系世界观的“合内外之道”。
莱布尼茨、布拉德雷、怀特海等发展了个体之间关系的内在的方面,罗素、穆尔、金岳霖等发展了它的外在的方面。前者把关系引向了后来被称为有机哲学的方向,后者把关系引向了逻辑学的、知识论的方向;前者强调了事物之间彼此关系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对事物特性的影响,后者注重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影响事物的性质。这两种关系学说之间也发生了关系,后者在很大程度是批判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的产物。罗素、穆尔、金岳霖批评内在关系论,但他们又有不同。罗素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这是强外在关系论),这同他坚持认为对整体的任何局部分析都可以获得真理的观点相统一。金岳霖肯定事物存在着内在关系,但它们并非都是内在关系,也有“外在关系”(这是一种弱外在关系论)。
从个体之间的内在方面发展关系概念,莱布尼茨、布拉德雷和柏格森的做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莱布尼茨的“单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被设想为没有部分、不可分割的最简单的实体,它是真正的原子(复合体则是单子的组合),它没有可出入的窗口,彼此之间也不发生关系,它突然产生,突然消亡。这样的看法使莱布尼茨的单子变成了死的东西。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可能意识到他的完全没有窗口的单子太孤单,他又通过单子的繁多性和上帝的作用将关系引入到单子之间,认为每一个单子都同别的单子不同,单子具有繁多、牵涉和关系的特性,每一个单子都有同其他单子发生关系的通道:“现在,一切生化之物和每一物的联系,或其适应,暨每一事物和其他一切事物的联系或适应,使每一单纯的实体有一些表现其他实体的关系,由是,他是宇宙一面永恒的生活的镜子。”①莱布尼茨:《单子论》,钱志纯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09页。
柏格森和怀特海都从有机和生命概念入手发展关系的概念,他们共同批判对个体和事物的机械主义和唯物主义立场。对柏格森和怀特海来说,宇宙万物和个体都是有机体的生命存在,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性。对我来说,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内在关系,机械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可以批评,但不必认为万物和个体都是有机的存在。事实上,万物并非都是有机体(虽然有机与无机的界限有相对性),并非都是生命性的存在。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生命的绵延和生命冲动,犹如机械论说万物只是数量关系一样不真实。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批评说:“当我们从总体上看他的哲学,看他是如何试图把生命的概念与自然的概念等同起来,把自然中的一切归为一个词‘生命’,这时候,我们发现他强调生命的做法正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们强调物质的做法。他们把物理学作为起点,论证说不论自然还会是什么,它至少是物理学家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物质。他们继而把整个自然还原为物质。柏格森把生物学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最终把整个自然界还原成生命。我们须问,这个还原是否比唯物主义类似的还原更成功。”②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55页。柯林伍德对柏格森的批评,也适应于怀特海,他也是整体上将自然视为有机体和生命的哲学家。现代中国的部分新儒家人物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思想的主要来源一个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一个是中国古典传统中的道德之“心”和“良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生命”的概念同“心”的概念结合起来,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生命和本心。为了促进人类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为了改变我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建立生态哲学,不能设立一个不可靠的宇宙生命和本心这一前提,虽然拟人化和拟心化的宇宙让人感到亲切和温馨。
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对内在关系说和有机关系说有更多的亲近感,对新实在论的外在关系论我们也不简单否定,因为他们也揭示了事物之间的某些关系形式,这些关系形式确实是存在的。只是,罗素等对内在关系说的批评过头了,他忽略了事物和个体之间的一些深层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他在论证事物存在着外在关系的同时,也为事物内在关系的存在留下了广大的空间。不管如何,个体之间关系上的内外说,有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承认个体之间都有关系。世界之所以是所有个体和事物组织起来的全体、复合体、统一体和整体,宇宙中所有的事物和个体之所以是连续的和贯通的,那是因为所有的个体和事物之间都具有彼此的关系性和相关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的整体性、连续性和贯通性,世界如何被组织起来、被贯通起来,那是基于它的关系性。无限个体整体关系的最简单说法,就是它们的普遍“相关性”(我在类似的意义上使用关联和关涉)和“交互性”。
“相互”和“交互”概念恰当地反映了事物和个体之间的双向和对流关系。相互和交互不仅发生在同类的个体之间,也发生在异类的个体之间。相互和交互使个体在它们作为自身存在的时候,又使它们同时被他者所规定。如市场交易的达成始终建立在买卖双方的相互和交互关系中。事物和个体的相互性和交互性基于它们深深的相互依存性和互为条件性。中国哲学的术语是“有待”和“相与”。《庄子·齐物论》中有一则罔两(影子外之微阴)同影子问答的寓言,它表现了事物广泛联系的意思。罔两随影子之遇而不安,它疑惑地问影子说,影子啊,你一会儿行走,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坐下,又一会儿又站起来,你为什么那么飘忽不定而没有独立的操守(“特操”)呢?你让我跟着你摇摆不定。影子回答说,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有所凭借和依靠(“有待”),是因为它所凭借和依靠的东西又有凭借和依靠。这个寓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本体论事实,即万物、个体和现象都是处在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关系世界中。形影不离不仅是一个关系事实,而且是一个关系紧密的事实,虽然我们不喜欢当影子而更喜欢充当形体的角色。《庄子·田子方》从万物、动物和人对太阳的依存关系进而推论出万物皆有所待的观点:“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苏轼的一首哲理诗——《琴诗》——写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首诗非常有力地表达了事物(具体为“琴声”)是相互关系的产物。
万物之间彼此相互的依存性和交互作用性,用庄子的用语说就是“有待”。万物都是有待的,没有不相待的事物。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幽闭起来的心灵的堡垒,想象一个独往独来的我,但这不是现实中的心灵,也不是现实中的“我”。现实中的心灵同身体是无法分离的,现实的我也脱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庄子不满社会的束缚和约束,渴望无限的自由和逍遥,以至于他设想了没有任何依赖的无待的自由和逍遥,想象出了一些看似是有空间而实际上是在虚拟世界中的极限之游和逍遥,如“而游于无有者也”、“游乎尘垢之外”、“游心乎无穷”、“游乎万物之所终始”、“游乎无何有之宫”、“游于大莫之国”、“游心于物之初”、“游于太虚”、“浮游乎万物之祖”、“游无端”、“游无朕”,等等。
飞翔被认为是自由,列子御风而行应该是很自由了,但庄子认为列子还是“有待”,还不够自由。他认为还有比列子的飞翔更高的无待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下,而御六气之变,彼且恶乎待哉?”“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至人无为”。这同样是庄子想象和幻想的自由,如果真有圣人、神人、至人,他们也不可能完脱离世界的相互依存而独存。一些境界高的人,是能够超越一些限制的人,特别是来自我和社会的一些人为的限制,减少对一些事物的依赖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依赖。庄子想象的无限逍遥和无待很美妙,但一旦回到现实的个体关系中去,庄子就发现人和万物都处于有待之中,这就像《庄子·田子方》篇所说的那样:“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事物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依赖,而且还存在着一种不可逃离的必然关系——“命”。庄子从无限的逍遥和无待想象急转直下一下子又回到了高度不自由的现实境况。《庄子·人间世》借孔子之口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冷静和理性的荀子,认为人是一个“相待”的存在,他们通过社会的分工和相互关系使生活得到相互资借,否则一个人的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荀子·富国》)。所谓孤独和离群索居的人,所谓隐士和出世的人,他们只是减少了一部分社会关系,真正讲来,任何人都无法做到彻底的“遗世而独立”。
《庄子·则阳》记载有季真的“莫为”和接子的“或使”概念,一般将它们理解为“无为”和“有为”,但这两个概念不限于人事方面。莫为是说宇宙和万物没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和东西的支配;“或使”则是说宇宙和万物受某种超自然绝对力量的支配。关系哲学不预设什么超自然的任何力量,它倾向于季真的立场而不赞成接子的说法。对关系哲学来说,“莫为”应该承认万物之间的“相为”①这里的相为不同于《吕氏春秋·圜道》中的用法:“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或使”应该承认具体事物之间的“互使”。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支配宇宙和万物,它们何以如此是基于它们自身的“自然而然”。这个“自然而然”是什么,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郭象接受并放大了庄子的“咸其自取的”的立场,从始终不变的个体和事物的“性分”出发,否定庄子根本之道的主宰性,否定个体之间的“有待性”,将事物的“自生自化”孤立为事物和个体各不相涉、各不相与的封闭性过程,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无待”的“独化”。郭象的“独化论”不只是说宇宙和万物没有创造者,它同时也是说它们彼此之间完全隔离和隔绝,它们是内不由于己、外不由于他物的一个个封闭的小堡垒。郭象的“独化”正像庄子幻想的“无待”那样,不是一个真实的观念。郭象为了缓和他的“独化”概念与个体的相关性事实的紧张,他为“独化”设置了一个“玄冥之境”,将事物和个体的变化原因引入到了神秘的世界中。“玄冥之境”恐怕是郭象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就难怪大家会迷惑不解了。郭象的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崇有论,但他尊崇的“有”是孤立性的有,是封闭性的有,一句话是没有关系的有。郭象的思想体系看上去冠冕堂皇,但除了他否定造物主这一点可以接受外,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独化论要加以否定。
裴頠的“相济”崇有立场比郭象的“独化”崇有论切实。在否定王弼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认为万有、万物存在的原因及变化都来自实有自身方面,裴頠同郭象有类似的地方。但他没有事物的自生就是事物完全独自活动的想法,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裴頠深刻地洞察到了世界的普遍相关性和相互依存性,认为真实的世界是现实事物互助互济(“济有者皆有也”)的世界。①对于事物之间的相济关系,曾子有一个很好的类比:“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吕氏春秋·明理》有一个适用更广泛的说法:“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济”是助益和促成。助益实有的东西仍然是实有的东西。裴頠还用了一个“资”(资借和借助)的概念,说“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崇有论》,见《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裴頠的说法同关系哲学的理念十分吻合,世界上没有完全自足的事物和个体。
人类梦想超级的力量,甚至干脆将自己看成超人,这不仅是希望我们有强大的能力,也是想获得一种优越于他者的特权。单是人的自然生命,它就很脆弱。人体就像许多生命体一样,必须时刻同自然保持交流关系。事物为什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资借的,照裴頠的解释,那是因为每一种事物的先天禀赋都有“所偏”。借用《列子》一书中的说法那就是“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因个体有一偏性的限制,它就不能完全靠自身来满足和保持它的同一性和持续性,它就需要凭借其他的事物。裴頠推论说:“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崇有论》,见《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我们接受裴頠的相济关系的观点而不接受他的解释。事物和个体正是因为有不同的禀赋和个性,恰恰使它们如此这般,如此那般;如果它们能够禀赋一切,它们就不再是具体的事物和个体了。按照关系世界观,事物和个体之间之所以要相互资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按照它们的各自禀赋,它们原本就处在彼此不能完全分开、分离的关系世界中。
在主张万物的普遍相关性和交互性上,没有比佛学的因缘说或缘起论更精致的理论了。万物都是关系,都是因缘,这是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真理,也是佛教义理中最诱人和迷人的地方之一。在佛教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派别中,这一理论被不断地传承和扩展。从它的最基本的方面说,这一理论认为事物和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各种原因、条件相互积聚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缘的“因”被认为是事物产生的主要的直接的条件,“缘”所起的作用则是次要和辅助性的。缘起说突出了事物因于缘而生生灭灭的方面,对仗而动听的“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常常被当作这一观念的最好注释。缘起有时又被作为因缘的同义语使用。对我们来说,因缘或缘起论所说的不同条件、因素和原因,就是事物和个体的不同关系和关联。很不幸(虽然它是佛教大厦的支柱),因缘或缘起观念在佛教中被用来论证事物和个体为什么说没有自性、是真空和虚幻的存在。为使我们个人摆脱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烦恼,竟然就说事物和现象都是不真实和虚幻的,这是对万物和个体的不尊重(虽然它有“真空妙有”的温和说法),虽然佛教的不杀生和反对贪恋的理念客观上起到了抑制人类的占有冲动。万物是因缘和关系的存在,这是真实的。为了将因缘或缘起说同我们的关系世界观念融合起来,为了肯定事物和个体的关系世界是一个实在和真实的世界,我们采用因缘或缘起说的直接意义而排除它的推论。人们在人际关系中乐道的缘份和机缘,事实上已经摆脱了这种推论。
儒家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说明事物的普遍相关性和交互性也是有用的。“体”在早期中国思想中被运用于部分,也被用于个体的形体,后来它又被用作形质、实体和本体(“气”、“理”、“良知”等)、本性等。宋明哲学家们津津乐道“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他们所说的“万物一体”的“体”,不是指个体的形体,更不是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形体,它主要是说万物具有共同的实体、本体或本性。对张载和王夫之来说,万物共同的本性是气;对程朱来说,万物的本性是天理;对陆王来说,万物的本性是良知和心。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本性,它们整体上是统一的、相通的和连贯的。在“仁者以万物为一体”这句话中,万物一体是“仁者”达到的一种精神自觉和境界。对儒家来说,“万物一体”不只是一个仁者的自觉和达到的境界,它首先是指万物原本就具有的本然和实然状态。如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①王阳明:《传习录》(下),载《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照王阳明的说法,不管一个人是否自觉到,不管他是否是一个仁者,万物实际上都是一体(“相通”)的。这样的思想同儒家的“天人合一”、人道即天道、应然即本然的信念是统一的。关系哲学使用的“一体”概念,首先是指万物具有统一性和相通性,它是无限的整体和统一体。②关系或关联性思维不接受方法论上的原子主义和个人主义,同样,它也抵制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思维和行为。政治权力独断论之下的整体和统一是强制性的,整体的宇宙没有这种强制性,因为其中的力量是相互制衡的,就像最通俗而又充满着真理的石头剪子布或老虎、杆子、虫和鸡那样。除了良好的法治和体制,任何强制和专制都建立不起健全和良好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万物共同体来说,贯通也是一个不错的词汇,它可以作为整体的同义语。万物是整体一体,也是贯通的或通贯的一体(“通体”)。①认为世界和万物具有一体性并不等于说世界和万物没有摩擦、矛盾和冲突。作为和谐的反作用力,摩擦和冲突可以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就像人体难免患者大大小小的疾病那样。一般不将生物世界中的食物链等同于人类世界的冲突和摩擦,事实上也不能这样等同。人类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控制、消除摩擦和冲突,但它们仍然存在着,只不过有时严重些,有时轻些。相对于个体的有限的局部的整体性,相对于个体的小宇宙形象,由无数个体组合起来的世界和宇宙是大世界和大宇宙,是无限的整体和无限的贯通。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同儒家的一体和合一(“统一体”)具有类似的地方。但关系哲学所说的一体又不同于宋明儒学家的用法,它不是以气或理或良知为本体、本性的统一体和整体。我们不预设本质主义的绝对本体,更没有将宇宙和万物道德化的愿望。对关系哲学来说,万物一体主要是指万物的相关性和相互性,主要是指万物是一个关系整体、统一体和贯通体。
万物和个体的关系和一体世界可以被想象为佛教《华严经》的因陀网或帝天网(比喻诸法相即相入、重重交织)②F.卡普拉评述佛教的因陀罗网说:“在佛教中,宇宙网络的图像甚至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它的精髓就是把世界描绘成完美的相互关系网。在其中,一切事物都以一种无限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着。”(《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第205页),更可以被想象为我们时代的无限网络世界。带着各种信息的巨大电子网络信息,它同万物和个体的关系世界具有一定的对应性。网络世界使我们更容易懂得一个本体论事实,即事物和个体自身之内是小关系体和小网络,事物和个体之间是大关系体和大网络。毫无疑问,人同样是处在关系的世界和关系的网络中,而不是处在性质之中;良好的关系和网络不会让我们失去自我性,实际上它就是人的自我性。持续的良好的关系和网络让我们感到真实、充实、充足。
只要有个体和事物,就有个体之间、事物之间的关系。个体本身是关系体,个体之间同样是关系体,而且是包含了所有个体自身关系的无限关系体。从局部的角度说,我们说个体本身是一个关系体;从完整的关系世界来说,个体的关系体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体是浑然一体的。当我们说到鱼类的个体时,它自身的关系体同河流、湖泊和海洋等的水是分不开的。在世界中,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关系的真空。莱布尼茨描述花园和池塘的关系时说:“物质的每一分子,你能设想他如长满花木的庭园,又如一养满鱼族的池塘。但此花木之每一枝条,此动物之每一肢体和他的每一滴体液,仍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一个这样的池塘。虽然庭园中花木间的土及空气,或池塘中鱼之间的水,不是花木和鱼,但是他们仍然含有花木和鱼,但是往往是如此精微细小,而非吾人所能觉察。”③莱布尼茨:《单子论》,第114页。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关系的个体,就像庄子想象的无待至人极限之逍遥和神游那样,但事实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同其他个体没有关系的个体。
(责任编辑:肖志珂)
B2
A
2095-0047(2016)05-0091-22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