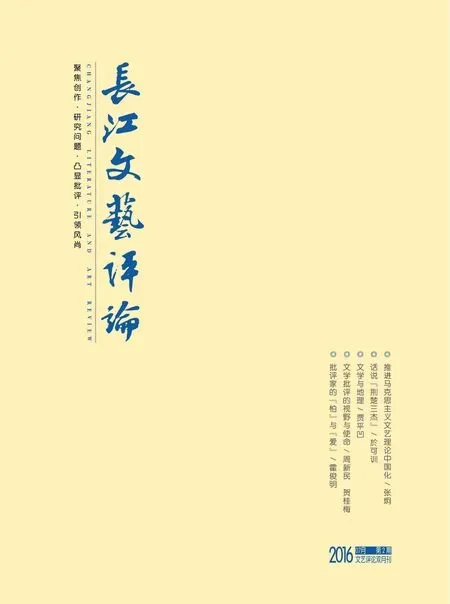智性写作与勘探存在
——吕志青“智性小说”论
◎ 昌 切 李雪梅
智性写作与勘探存在
——吕志青“智性小说”论
◎ 昌 切 李雪梅
几年前我们曾经就吕志青的小说写作做过一个对话。在那个对话中,我们把吕志青的小说写作称作“智性写作”。“智性”或“知性”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一个概念,意思大抵与理解力和想象力相当。按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的说法,这是一种使对立或不协调的事物平衡起来的能力。而按我们的理解,则是一种使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个别与一般在特殊的艺术形态中获得平衡的能力。凭借想象力构筑感性、具象和个别的艺术世界,凭借理解力赋予这个艺术世界以理性、抽象和普遍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这是吕志青经常采用的一种叙述策略。
吕志青写作已经有不少年头,他的小说当然不会只呈现一种面孔。一种面孔的小说是吕志青在上世纪80、90年代写的一些先锋小说,例如《最初回旋的地方》《我们的埃玛》《剧作家之死》和《经典疑案》等;另一种面孔的小说是他在新世纪写的若干与底层文学有些联系的小说,例如《老五》《消逝》《油壳鞋》《爹的婚姻》《证据》和《圆觉寺的经历》等。不客气地说,这两种面孔的小说缺少个性,不是吕志青可以独享的专利。真正能够使吕志青不泯然于众人的是他的智性写作。他新近发表的长篇《黑屋子》就沿袭了智性写作的路子。他在创作谈中说:“在写作前和写作中,我一直有这样几点简单的想法,其一是继续我2000年以来在中篇写作里的某些追求,其二是尽可能比较深入地去触及现实,触及人的心灵。其中包括由个体到群体,由个别到一般的途径。”[1]“其二”是对“其一”的说明,一个意思。触及现实或人的心灵,他所采用的便是原有中篇写作于个体中写出群体、寓一般于个别的艺术途径。
吕志青的这种艺术追求是相当自觉的。新世纪初,他有意识地改变了先前“不及物”(言不及义)的高蹈的先锋姿态,把目光转向现实,尤其是“当下主要的现实”,力图从“当下主要的现实”中去“发现存在”,去探询人心的奥秘。[2]不是也不可能是另起炉灶新开张,他并没有弃绝反而有效地利用了先前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仍然刻意在小说叙述的技艺上狠下功夫。他的智性小说,勘探存在或人的心灵,想象诡异,构思奇崛,叙述冷峻绵密,喻意隐晦而含哲理,多有反讽的意味,不乏思辨的张力。这样一种小说,不仅在湖北是稀有的,而且在整个中国似乎也并不多见。
一
吕志青勘探存在或人的心灵,擅长从知识人荒诞不经的生存状态入手,常把聚焦点投射到知识人畸形的两性关系之上。《黑影》里面的庄佑、《爱智者的晚年》里面的何为、《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里面的何磊、《失去楚国的人》里面的康小宁、《蛇踪》里面的小冯、《闯入者》里面的胡祥、《黑暗中的帽子》里面的臧医生、《穿银色旗袍的女人》里面的“我爸”和“我妈”、《黑屋子》里面的齐有生和臧小林,等等,他们不是期刊的编辑就是大学的教授,不是心理咨询师就是研究员,不是大学生就是记者……都是社会上体面的知识人。所有这些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在吕志青冷静到冷酷的叙述中,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悖谬性,全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种荒诞不经的生存状态,在《黑影》和《爱智者的晚年》中具体表现为知识人的自我分裂。庄佑是研究苏格拉底的专家,崇尚并向往苏格拉底的智慧人生。他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获得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在死后才能够获得的智慧。他几乎成功了,因为他拥有了某种灵视的能力,可以发现此前他无从察觉的一些事物。庄佑似乎“看到”一个黑影正试图对沈捷图谋不轨,为使沈捷免遭黑影魔爪的侵害,他义不容辞地担当了沈捷的保护人。然而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自己才是真正对沈捷伸出一双魔爪的那个黑影。庄佑的心身或灵肉是破裂的。破裂而不自知,渴望灵视而盲视自我,这在热衷于思考“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庄佑那里,不失为一种辛辣的讽喻。何为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以研究海德格尔见长。他崇尚并向往诗思共融的“诗意的栖居”。可是,何为爱慕的那个梦中情人梁可,偏偏是一个被刻板的国家机器打磨成光滑的标准件的毫无诗意的区政府的秘书科长。他们操着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谈情说爱,其结局可想可知。反倒是一向被何为所不齿的一个性工作者用她生动的身体语言为他营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神奇地治愈了困扰他多年的失眠症。何为与庄佑实质上是同一个人,一个有知无识、知理不知实以至于不知自己为何物的暧昧而愚昧的爱智者。他们都是感性和具象的个体,但从他们的身上,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是可以发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3]来的。
《穿银色旗袍的女人》和《失去楚国的人》触及到了“主要的现实”,其中呈现的知识人荒诞不经的生存状态更值得我们留意。这两个中篇写的是价值归属或信仰的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我爸”和“我妈”当年共有的一个信物、热恋的一根红绳。在崇奉这部“圣书”的宗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信仰看似牢不可破、坚定不移。然而几十年过去,中国突然来了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从重精神到重物质的方向性转换。原有的精神凝聚点涣散了,信念动摇,婚姻的纽带发生断裂,“我爸”和“我妈”一并改变了共有的信仰。信仰还是信仰,未失本义,看起来依然牢不可破、坚定不移,但是旧瓶子里面装的是新酒,更换了内容。“我爸”转而痴迷于传销,为追随传销大军宁可抛家弃子也在所不惜;“我妈”转而痴情于伊斯兰教,宁可为此死去也决不回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在中国,如同从极左转向极右,原是十分轻便容易的一件事情,相似的事例可以说史不绝书。与《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不同,《失去楚国的人》写的是丧失信仰支撑的知识人无聊的精神状态。无人生方向而无欲无求,无定则而无可无不可,一切都无所谓、都不在乎,这种状态不是无聊还能是什么呢?依叔本华说,无聊与痛苦相对,介于痛苦之间,出现在意志消歇的那个瞬间。而在向无坚实的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特别是在物欲横流、价值离散的当下,无聊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倒立是小康每日必做的功课,就像大妈跳广场舞一样坚持不懈,直到把倒立磨练成了一门精妙绝伦的艺术;老康的绝活则是蓄胡须,他居然能够把胡须蓄到三尺三。小康和老康的作为,适可与一千个儿童在荒漠上齐诵国学经典媲美。
帽子是贯通《黑暗中的帽子》全篇的一个喻体。喻体与本体的联结,我们觉得,吕志青可能只取了“隔”这一层语义。帽子“隔”的功能被转换成“中立”的立场,被用来划定医患之间的心理疆界。臧医生的心理疗所就号称“中立中心”。实际情形如何呢?臧医生口头或名义上的中立完全被他实际行动上的介入给否定了。臧医生为遭到家暴的何莉莉治疗竟然把她治上了床,哪怕治上了床还要重申他那个互不进入对方心灵的中立原则。他把这种关系称作“新型同居”。但是,在何莉莉的眼里,就算是“新型同居”,也应该是一种灵肉理当彼此进入的亲密关系。臧医生对另外两位女患者沈洁和范彬彬采用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其目的都在于使患者摆脱一种权力的控制,其结果却是使她们掉入另一种权力控制的陷阱。这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与中立毫无关系。隔而不隔,不隔而隔。不隔的是人对人控制,隔的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心灵。在当今的物化社会中,人心隔离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人心灵相通只是永远滞留在卢梭头脑中的一个梦想。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存在,我必依他人存在,所以我必无绝对的自由意志。纯粹的客观知识和中立立场何处可寻,从何谈起!事实上,福柯的话语/权力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否定这种常识(common sense)。控制与反控制,无休无止,这才是现代人无可逃避的真实处境。吕志青借代校长老吴的口说,现代社会的权力并非绝对控制的古典权力观所能解释,任何人都无从挣脱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网的束缚。
《黑屋子》是吕志青新近发表的一个长篇。这个长篇一如既往,继续以两性关系为书写对象,由此探究知识人荒诞不经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根由。与他以前写的中篇《闯入者》相比,《黑屋子》的探究要来得更为全面和深入。《闯入者》只是把着眼点放在知识人有理无欲的残缺的婚姻状态上面,而《黑屋子》则不仅写了知识人多样的两性观和婚姻形态,而且探究了形成这多样的两性观和婚姻形态的社会根源。《黑屋子》沿着主副两条线索展开,主线写的是齐有生与臧小林爱情婚姻关系的演变过程,副线写的是老汤、老冯、老费、老柴、老穆、小潘和沈慧等“精神破落户”对待性的各种看法和态度,处理两性关系或婚姻的各种方式。副线是辅助性的,被用来放大主线探究的主旨。这个主旨,或其抽象的意义,显然是在对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不断思辨、对真实与谎言的不懈追问中表达出来的。齐有生与臧小林的婚姻既坚实又脆弱。越坚实便越脆弱,皎皎者易污。他们曾经真诚相待,心心相印,所以坚实;一朝心生罅隙,两心转眼间判若云泥,所以脆弱。齐有生天生是一个主宰者、偏执狂或精神暴徒,他执意追究的并不是臧小林是不是在婚内出轨,而是臧小林是不是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追究事情的真相,其实是追究臧小林是不是还葆有当初的那份真诚。倘若失去了真诚,爱情便无所附丽,婚姻便不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与这种追究如影随形的是齐有生对于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思索和辨识。他想知道,为什么在当下,满世界都是人心隔离如山的破碎的男女关系。老费一婚再婚,无所顾忌地消费他的杯水主义的性爱观;老穆因婚姻的破裂而心生恐惧,不敢再走进婚姻的囚笼;小潘可以随意跟人上床,但从来不向与她交欢的人交心;比小潘在性事上来得更随意且更明白的是沈慧,她从十六岁开始就跟一些比她大得多的男人上床,“一个接一个,都快接近二十个了”。沈慧随性学专家老汤学过性社会学,读过波伏娃的名作《第二性》和各种有关萨特的传记,“可等她全部看完,她发现所谓自由情侣实际上只是一个神话”,波伏娃“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的形象刻印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坚信这个名闻遐迩的女权论者并没有摆脱女人角色的自我规定。老汤的主张是性爱分离,因为他认为自五四就流行开来的性爱合一的“理想爱情”,实际上只是一个蒙蔽欺骗世人的谎言。在他那里,性不等于爱,性爱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通过这个老汤,作者写到曾经喧闹一时的大学老师的换妻事件。换妻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不就意味着性爱可以分离吗?我注意到作者有意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当今世界,人们关注大地,土壤,河流和天空;关注食品安全,关注车祸,空难,和各种自杀;却看不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非死于矿难、尘肺病,和环境污染。”接下来作者转述了那个声称用唯美的艺术为丑恶的现实立法的作家王尔德的话:“罪孽是现代社会剩下的唯一的鲜明色调。”这大概也是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判断。作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不过是想借描写知识人种种畸形的两性关系来探明造成普遍性“心难”(精神灾难)这种现代病的病原。作者把探究的工夫全部用在了主线上。探究的过程似乎近似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与霍桑的《红字》似乎也有那么一点艺术联系。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作的重心在“罚”不在“罪”,他不吝笔墨、颇为刻毒书写的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拷问自我灵魂的忏悔和赎罪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证伪”而“正义”的过程。吕志青呢?他的写作重心不是也放在齐有生执拗地质询臧小林出轨的真相、臧小林不停地自审以至变态地自罚、齐臧无间歇地相互折磨的过程上了吗?吕志青写到了基督教,写到了超自然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从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引出了独断论和唯一性的绝对价值。透过齐有生,作者告诉人们:人的心灵隔绝、人际交往不真不诚,造成普遍性“心难”这种现代病的真正病原是绝对价值的丧失、相对价值的泛滥。相对价值是虚无主义的孪生兄弟。美丑齐一,长短不二,无可无不可,这种心理可谓源远流长。面对相对价值泛滥的现实,作者明显感到绝望,因此,他不惜痛下杀手,把齐臧一起推向了坟墓。当然,吕志青一向对一切标示绝对的东西保持警惕,这是一个需要另文讨论的问题。
二
吕志青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他相对固定的叙述方式。构造隐喻结构便是其经营小说惯用的一种手段。对此他有说明:“我希望在我的小说的内里,在其结构上,显示出一种隐喻性;而在其局部,在整个叙述的表面,则希望尽可能地靠近生活的外表,甚至是非虚构的外表。”[4]正因为如此,吕志青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才能既远离单纯模仿生活的小说,又避免了单纯的玄思和空想。
《闯入者》里牙科主任胡祥与妻子大学教师小孟每天都重复着那种单调无聊、规矩到近乎刻板的生活,但流浪儿小七子的突然闯入却破坏了这种平静,小孟与生俱来的母性大放光芒,而胡祥被压抑多年的性欲则以一种变态的方式得以发泄。胡祥与小孟这种靠理性玄思与单调程式维系的婚姻一旦遭遇闯入者,被遮蔽的种种情态便显露无遗,甚至会以超出常态的方式发生恶性膨胀。小七子莫名其妙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胡祥与小孟的生活秩序,人性中隐而不显的东西浮现了出来。事实上,小说的重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去思考,让人们发现事物的模糊性和多种可能性,吕志青用小七子搅动胡祥和小孟近乎刻板的生活,各种可能性才得以一一敞开,或许这才是他设置小七子这个不速之客的苦心所在。在《爱智者的晚年》这个中篇中,失眠症作为一种隐喻,它不再是一个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精神病症。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写失眠的何为行走在深夜的街头,流浪汉响亮的鼾声和香甜的睡态令何为瞬间明白,自己和那些失眠的朋友们不过都是被精神和心灵放逐的流浪汉,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像流浪汉的编织袋那样一个安睡和做梦的地方,是因为他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孤独和虚无之中,找不到精神的栖息地。
如果说《闯入者》《爱智者的晚年》是对现实的隐喻,那么《南京在哪里》《穿银色旗袍的女人》和《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则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隐喻。《南京在哪里》从一个代课老师的提问出发,在寻找“南京在哪里”的答案时,大量与南京相关的知识被挖掘了出来,直接颠覆了被提纯的教科书上的知识点。南京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看南京,聚集在南京这个地名上的知识可以无限地发酵、无止境地膨胀下去。客观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在这里显露无遗。《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中那个父亲口中“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与“小七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她是否真实存在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构成对父亲与母亲现实生活的解构。父亲和母亲曾经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文革”以后母亲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非公开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父亲则陷入狂热的传销中不能自拔。这是历史的荒诞,也是现代人内心分裂的形象写照,更是现代社会信仰崩塌后的精神乱象。《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几乎贯穿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其中1937年燕大青年奔赴延安、1966年红卫兵北上接受领袖检阅和当下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交错上演,历史时空和现实世界并置在一起,在三代人的不同面貌的青春岁月中隐喻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燕大青年的革命理想和红卫兵的迷狂叠映在当下青年的性爱游戏中,折射出作者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反省,更呈现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
与在整体结构上的隐喻追求相应,吕志青小说的精神内核常常通过反讽的方式呈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讽是揭示现代人生存悖论和存在困境最有效的工具,它以超越性叙事态度搁置叙事人的价值判断,在对事物的冷静观照中令其自动呈现出自身的荒谬性。具体说来,吕志青小说的反讽技巧融喜剧性、批判性和悲剧性于一体,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又加深了小说的思想性。
“喜剧性似乎是反讽的形式特点和固有因素”[5],《黑暗中的帽子》里的口罩风波、《失去楚国的人》中的倒立行走、《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中的当年“革大”和如今传销惊人相似的学习场景……无不都是极具反讽意味的狂欢化场景,这种借助反讽的沉思与冷峻的怀疑相交织,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幽默,从而传递出作家深沉的思考,让读者于哑然失笑之余陷入沉思。性爱场景也是吕志青将严肃题材喜剧化的重要途径。吕志青笔下现代人的性爱很难同幸福愉悦划上等号,反而常常是精神上虚无困顿的人们最真实的写照。《黑暗中的帽子》里臧医生和何莉莉在床上毫无意义的重复翻滚、《黑影》中视美人如毒蜘蛛的庄佑却“两只爪子放在前面,哇!猛地一下,就跳到你身上来了,跟一只老虎似的——”,《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中禹斌和朱晶晶在床上的“秋裤游戏”……这是如米兰·昆德拉所谓“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6]的智慧体现,诸多荒唐可笑的性爱场景,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的极度匮乏与灵肉的剧烈冲突。反讽艺术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其实是一体两面,反讽表面的喜剧性品格往往渗透着悲剧性内涵。吕志青的反讽和幽默更多的来自他对于处在悖谬境遇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的深思。他对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度是失望和怀疑,由此产生的虚无感与错位感是其反讽的现实基础,也是其小说的悲剧内核。在喜剧性和悲剧性之外,反讽艺术的批判性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反抗的意味,是借戏谑的反抗形式表达对现实和世界的批判性认识。《穿银色旗袍的女人》中母亲当年极其认真地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如今在家中极其虔诚地做礼拜和在镜头前极其严肃地表演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形象,透过这种极具反讽意味的角色转换,可以发现历史与个体在强权政治下的荒谬无比。《失去楚国的人》中康小宁听信一个游医的建议以倒立治疗颈椎病,先是在办公室带动了同事以集体倒立代替工间操,直至在广场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倒立表演队,最后以荒诞而富有喜剧性的倒立方式进入城门的场景,则是在机智的逻辑归谬后跳出规训逻辑的圈套设置。在这些颇具狂欢意味的场景中,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是对现实规训的反抗,而历史更是反讽性叙事戏谑的对象,像《一九三七年的情节剧》中拥挤的火车上女生以一个军用水壶解决问题的滑稽场景直接消解了接受领袖检阅的神圣性,《南京在哪里》陶校长提前退休后客厅里高悬的“南京在哪里”横幅透出历史的荒诞,以谐谑的反讽面对历史的悖谬,这无疑正是揭破蒙蔽历史真相的层层面纱和话语迷障的有效途径。
小说的思想表达与结构形式、艺术手法是密不可分的,小说要阐明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就必须具有能充分揭示存在的可能性的艺术形式。能否找到最好的小说形式将自己感受到的现实表达出来,最能体现一个小说家处理现实的能力。吕志青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实验新的形式,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地表现他所理解的碎片化现实,探索和表现由于失去信仰和价值而陷于混乱的现代世界,他的隐喻和反讽并非卖弄技巧,他仅仅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更加举重若轻地表现他对存在的严肃思考。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吕志青无疑已经找到属于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叙事方式。
三
从思想和艺术的渊源上讲,吕志青智性写作的叙述策略与先锋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吕志青的小说创作历经三十余年,始终受着先锋文学的滋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吕志青就很快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模仿”生活的路数转向先锋小说的“非模仿”创作,创作了一批颇具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小说,甚至到90年代前期,正如前文所说,吕志青仍然不舍旧情,写过若干先锋小说。直到90年代中期,吕志青小说写作的理想才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一点,他自己有交待:“我既不想与现实主义合流,也不想继续沿着此前的路数写下去。总的说,我仍希望在写作中保持一种实验性和探索性。但这实验和探索更多的是针对文本内部,而非针对文本的外部或语言的表面。具体说我想把隐喻化表达看作我在某个阶段上的主要目标之一。”[7]正是这一觉悟成就了今日的吕志青,2000年左右的《黑影》《南京在哪里》《穿银色旗袍的女人》等小说就已很好地实践了吕志青的这一小说理想(前文论述所及的小说主要都是在这一转型之后的创作)。此后,这一小说理想又不断得到强化,更加强调贴近现实,尤其是“当下主要现实”,希望从中“发现存在”。吕志青清楚地知道,他当年追随的先锋小说之所以退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面对和处理当下现实时的软弱无力。在进一步切近现实后,吕志青的写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并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提升了他的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在他的小说上打上了吕氏标记,使其拥有了别具资质的风采。
有位批评家曾经指出现在的某些小说存在“像木头一样的写实”[8]的缺憾。这种“呆萌”的小说既缺乏自己的见解又缺乏独特的表达方式。这里似乎包含这样的担忧,即担忧小说思想的贫乏,这种思想的贫乏既源于作家缺乏对于时代的复杂性的洞察,更源于在这个一切服从于经济杠杆的时代里作家对于思想的漠视,其后果就是作家失去了对于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不但提不出有价值的现实问题,也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施展艺术想象的才能。当下变幻莫测的现实提供了太多的小说素材,这是小说家们的幸运,同时也令小说家们陷入了表达的困境。怎样才能与置身其间的现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怎样才能在一个共时的语境中为读者提供一种源于并超越现实的非凡想象?怎样才能在深切地感悟和透彻地理解现实的基础上使之以独特艺术形式再现于小说之中?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期待作家们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对于作家们来说,则是严峻的考验。对很多作家而言,日新月异的当下生活已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甚至现实远比文学更精彩,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以文学的方式创造更深刻的真实是作家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吕志青敏锐地看到了大多数作家正身处的现实困境,他不断提醒自己:“好小说似乎应是这样:它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可又不大容易被生活拉下水。”[9]这正是吕志青对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清醒认识。在这种看似平白的表述中,吕志青的小说理想凸显出来。强大的现实生活好似一个无以伦比的巨大漩涡,不断吸引作家们靠近,在提醒作家们关注现实的同时也不断销蚀作家们的独立的思想和想象的翅膀,一不留神就身陷其中难以自拔,变成“像木头一样的写实”。对吕志青的小说而言,智性写作是其“不被生活拉下水”的制胜策略,也为当下文学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探索。从故事层面看,吕志青的小说常常关注现代人的两性关系、灵肉冲突,关注知识人的精神状况、爱恨生死,这是一种贴近现实的书写,那些建基于穿透现实的理解力的审美形象,使吕志青的小说血肉丰满。然而,反映现实并非吕志青小说的旨趣所在,他拒绝对现实进行机械的模仿,他的兴趣在于通过对现实和人性的沉思创造一个审美的世界;他也无意于提供一个解决现代人悖谬生存现状的答案,而是致力于提出问题,以怀疑的眼光质询人们生活其中的悖谬世界及其面临的种种精神危机,在对各种可能性的探讨中勘探人们的存在困境,这种小说家的哲学思考,为他的小说带来难得的思想深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吕志青的这种思考并非是要将小说变成哲学,而是像昆德拉那样“动用所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10];这种哲学思考使吕志青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从具象的书写中透出抽象的意义,在个别的书写中呈现出普遍的意义,而这些特质正是构成吕志青智性写作的核心所在。难得的是,吕志青对存在之真的执着追寻并未陷入形而上的自说自话,恰恰相反,他小说中的每个存在命题都透出深切的现实关怀。虽然吕志青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弯路,但他很快就在反省中从纯粹抽象而玄虚的写作回到现实,这种小说的“及物性”一方面表现在小说贴近现实的生活使他的形而上思考有血有肉,另一方面表现在吕志青关于存在的思考都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种种异化和悖谬现象的深入开掘,直面现实(包括外部现实和心理事实),切中时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就总体特征而言,吕志青的智性小说,在思想意蕴层面,受到存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将思辨的力量有机植入文学,使小说负载了丰富的思想信息,从整体上植根于对现代社会精神状态的忧思;在叙事层面,吕志青的小说又十分重视结构、文体等形式技巧的实验,在存在之光的照耀下,形式已不仅仅是形式,而且成了他探索意义的途径与工具。二者的有机融合共同构成吕志青“发现存在”的小说追求,借助小说内部形式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话,吕志青从多层面实现着对存在的探询。因此,吕志青的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思想主题上的存在质询和形式风格上的先锋格调;但在这些内容与技法的深层,都蕴藏着他关于小说价值的思考。或者说,吕志青不仅关注人性与存在的分析,小说结构与技巧的探索,而且还自觉进行着关于小说本体的探求与实践,此时的小说已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文学书写体裁,更是一种察看生活的方式和智慧,这也是一种小说的智慧。我们有理由相信,吕志青会为文坛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以勘探存在为旨归的吕氏智性写作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
昌 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1][4][9]吕志青:《关于〈黑屋子〉(创作谈)》http://www.zhongshanzazhi.com/zssd_detail.asp?articleID=2322&classId=63)
[2]吕志青说:“到2006年,我开始更加注重作品的及物性,即作品对现实的触及,尤其是对于当下主要现实的触及,并努力地去发现存在,或者说对于存在有所发现。”(吕志青:《我的写作(代跋)》,《南京在哪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65页。)
[3]【法】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5]【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6][10]【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4页,15页。
[7]吕志青:《我的写作(代跋)》,《南京在哪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365页。
[8]《李敬泽:有些小说像木头》,《信息时报》2009年4月19日,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