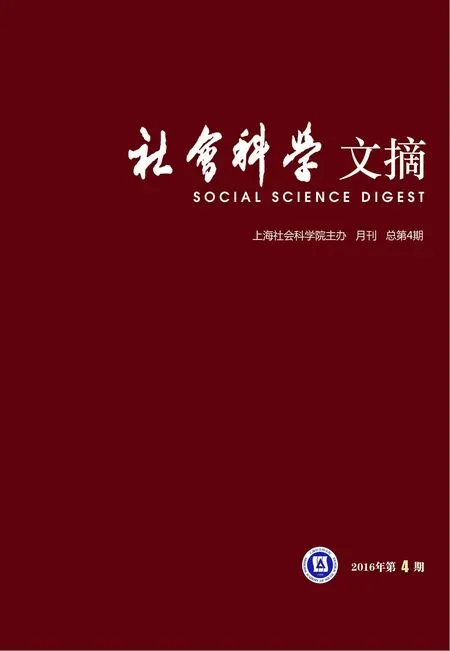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搭便车”行为的再认识
文/张丽琴 石静敏
“搭便车”行为的再认识
文/张丽琴 石静敏
学界对于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的探讨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文建立在既有成果以及持续性观察的基础上,以地处华中地区的一个城中村——八里墩接近6年的拆迁维权为例,考察“搭便车”行为的不同样态(类型)及成因,并就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进行分析。
国内研究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分析,无论是核心概念的界定,还是基本研究思路,大都源自曼瑟尔·奥尔森和奥斯特罗姆等学者的理论。奥尔森认为,在集体行动中,只要有产生集体利益的共同行动,个体都会计算他们不做贡献的好处;只要他们相信不参与行动也能得到利益和保障,就存在潜在的“搭便车”者。观察经验表明,在国内维权类民间组织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个别参与者意图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但应该看到的事实是,占取集体或者他人“便宜”的行为在客观上有各种形态,“占便宜”的尺度和原因也各有不同,由此,便形成了“搭便车”的类型差异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成原因不同问题。
八里墩维权小组是一个由城中村村民自发组建的反拆迁组织,该组织2010年初成立,2015年底解体。持续期间,梁民勇等行动精英代表村民通过到当地各大部门上访、邮寄材料、在村庄横挂标语、赴京上访,以及组织群众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表达利益,进而使补偿价格得到些许提升。但到最后,这个组织却由于内部管理困境以及外部压力而难以为继,走向解体。
“搭便车”的成因及类型
和其他同质维权组织的情况一样,“搭便车”行为在八里墩维权中普遍存在,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是诉求对象过于强大。拆迁维权的诉求对象是政府,村民对庞大的政府力量充满敬畏,为免被贴上“维权积极分子”“与政府作对”的标签,他们即使参加维权组织,也始终持有观望态度,只会有节制、有选择地参加抗争活动,断不会毫无保留全力以赴。另一方面是基于组织的自身特征。拆迁维权组织具有临时性、弱组织性及非政治性等特征,这些因素使它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去约束参与者的行为。第三方面是由于参加的村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利益表达能力不强,意志容易发生动摇,道德责任感较差,行为选择比较功利和随意。
出现在八里墩集体维权中的“搭便车”行为可分为两类,且各有不同的成因。
(一)经济型“搭便车”的成因与形态
经济型“搭便车”是参与者在经济上完全不付出或没有完全付出的行为。由于集体维权中的经济付出主要是承担维权费用的分摊,因此,经济型“搭便车”其实就是参与者对费用分摊责任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
经济型“搭便车”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种情形是不参加维权但分享维权成果的行为。这部分人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参加到维权组织中去,因此没有分担维权成本,但维权效果在村庄范围内具有公共性,于是他们也就有了不劳而获的机会。第二种情形是行动上参加了维权组织,但不愿意集资的行为。这部分参加者主要是经济困难的家庭或家中只有老人和幼儿的“空巢”家庭。第三种类型是途中退出组织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原因,部分原本自愿加入维权组织且承担了早期集资的村民,中途离开维权组织,没有支付后续集资,但只要维权组织存在,后续的抗争效果他们照样可以分享。
尽管经济型“搭便车”普遍存在,但其对维权组织的影响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常态下,大多数利益表达行为均由行动精英代为实施,无须村民参与,也不会产生相关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维权组织的常见支出是各种资料的印刷费、横幅标语的制作费,上访的交通费、维权资料的邮寄费等,总额不大,分摊之后属村民可承受的范围。因此,即使有人在经济上“搭便车”,但也不会对组织运作带来实质性困难。
(二)自保型“搭便车”的表现及影响
自保型“搭便车”是出资但不愿参加维权活动,或出资且愿意参加维权的人在需要进行高风险抗争行动时“临阵退缩”,坐等他人“冲锋陷阵”的行为。其前提是行动者有积极维权的主观愿望,但只“出钱”而惧怕“出面”,或敏感时刻不“出力”。自保型“搭便车”行为是随着维权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
自2010年维权组织成立以来,八里墩的拆迁形势随时间推移而变得越来越紧张。2013年以后,负责该村改造事宜的拆迁公司开始在村内实施各种严重程度不一的扰民行为,同年年底,六门桥片区开始进入拆迁状态。2014年10月起,养马口片区和六门桥片区出现频繁的强拆、误拆现象。但除行动精英和当事村民之外,却没有其他村民愿意出来与拆迁方对抗——当初商议好的正当防卫举措没有实施,群众会议中村民誓誓旦旦要捍卫家园的行动也未能兑现,而且即使维权领袖组织大家到街上堵马路或者集体“散步”抗议强拆,参加的人数也逐次减少,甚至到了后来基本上无法组织起来。
关键时期,自保型“搭便车”的大面积发生使维权组织迅速陷入运作困境。一方面,它表明了局势平和时期,一般人难以察觉的维权组织内部的合作难题,村民在拆迁中由“个体自救”到“抱团图强”是附条件的,“集体的团结”也是务实主义指导下的团结;另一方面,它加速了维权组织内部的分化,积极行动者和消极行动者之间相互推诿、指责,维权组织由平日的“人多势众”假象迅速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境当中;再者,它也向拆迁方展示了维权组织的重要弱点——关键时刻人心不齐,这为后续推进拆迁奠定了基础。
“搭便车”行为的消除困境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着力探讨维权组织应如何建立和实施“选择性激励机制”,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这些建议大都缺乏操作可能性。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由维权组织的自身状况决定的。维权组织大都历时较短,规模小,资金来不稳定,不但组织化程度低,而且缺乏严密的内部管理规则,奖励和惩罚机制也基本不存在。以八里墩为例,行动精英不可能通过与参加者签订协议的形式,确保村民必须参加维权活动或者履行集资义务。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不可能动用群众集资款给予积极者奖励;对于消极参与者,行动精英也缺乏强制性制裁手段。可见,“选择性激励机制”的建立存在客观不能。
另一方面是出于维权领袖的顾虑。在对个别参加者实施激励或科以惩罚时,维权领袖需要兼顾内外风险。对内,激励性做法可能使其他村民感到不满,引发内部争议;惩罚性做法会促使行动消极者及其他有类似心理的人离开组织,削弱士气。对外,实施严格的奖惩机制有可能被外界认为维权团体“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维权领袖在组织中拥有巨大的控制力——这种足以让政府深感不安的误解是维权领袖最不想看到的。因此,“选择性激励”的实施还存在主观不能。
另外,任何激励机制在高风险行动面前都存在失效的可能。在漫长的利益表达过程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相对理性的,即使他们愿意响应维权领袖的号召,出席群众大会以及承担维权成本分摊,但对于有可能受到政府打击或者法律制裁的高风险抗争行动都会三思而后不行。在危险性较高的行动面前,奖惩激励机制的效能显然存在边界,行动的风险越高,激励机制越容易失效,没有参与者会为了获得内部奖励或者惧怕自己人的惩罚甘愿使人身和财产安全遭受严重损害。
结论:对“搭便车”行为研究的几点补充
理论上,一个理想的集体行动参加者应对组织、领头人和其他同伴都怀有忠诚之心,积极响应号召,自愿分担维权成本,并时刻与其他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合作。越是这样,维权组织所能产生的施压效果就会越大,参与者的共同目标也就越有可能实现。但实际中,成员之间关系固若金汤、行动步调一致的维权组织是不存在的。通过对“搭便车”问题的研究,本文期望能为学界提供三点补充信息。
首先,经济型“搭便车”和自保型“搭便车”各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实质影响。对于维权成本不高,参与者的经济负担不大,但抗争效果对维权组织的规模和团结程度有严重依赖的场合而言,自保型“搭便车”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在维权成本高,但所需集体行动次数少,尤其是高风险抗争行动不多的维权场合,经济型“搭便车”则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次,“搭便车”行为难以消除。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及既有研究中,国内学者提出的各种具体方法,诸如建议参加者之间签订协议、提高参加者的认同感和道德水平等,都不能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奖惩机制不合理和不必要,而是奖惩机制在草根组织中难以建立以及付诸实施。
再次,“搭便车”行为增添了集体行动的理性色彩。在持续性抗争中,尤其是那些因政府发展行为所引致的、以政府为诉求对象的集体维权中,维权者出于对政府权力和法制权威的畏惧,对行动选择大都非常谨慎,从而使集体维权显得更为理性。诚然,促成理性行动的关键原因,是参加者的内心在彼此观望、权衡得失、相互计较的过程中所形成了对激烈抗争行为的自我抑制力量。
(张丽琴系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石静敏系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摘自《社会工作》2016年第2期;原题为《“搭便车”行为的再认识:类型、成因与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