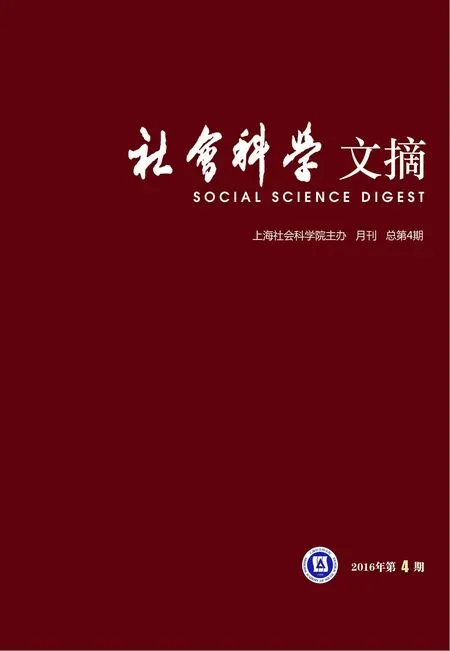当代外国文论新动态
——从四部著作看外国文论四个取向上的进展
文/周启超
当代外国文论新动态
——从四部著作看外国文论四个取向上的进展
文/周启超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与“文学学”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2007)深入浅出地介绍“文学学”(Literaturwissenschaft, 文学科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和各个理论方向,介绍文学的各类体裁,介绍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阐释20世纪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叙述的系统性与表述的精细性,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一个代表。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对于当代中国读者的价值,首先体现于认知层面:有助于充实我们对当代德语文论进程的认识。我们看到:当代德语文论中,与“接受美学”一同出场的还有其他学派;“接受美学”本身也还有后续发展。当代德语文论的多形态性提示我们:不应把当代德语文论“简化”为“接受美学”。即便是“接受美学”,我们对它的接受也还有不小的空间。在过去35年中,“文学学”的问题越来越多样化,“文学学”的方法和时尚变幻纷呈,“文学学”的范式更迭似乎越来越快——这一切只是“文学学”200年来的发展历史的最新阶段。《新德语文学学导论》归纳出当代“文学学”10大范式:阐释学;形式分析学派;接受美学;心理分析“文学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文学的社会史/文学社会学;话语分析;系统论;传播学;文化学。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对于我们中国读者的价值,更体现于本体层面,反思层面: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文学学”这门学科的反思。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其命名应当是“文艺学”还是“文学学”?它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是一门人文科学?这些问题,关乎文学研究的性质与宗旨、路径与方式、价值实现、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定位”。德语文论界对“文学学”有自己独特的建构:“文学学”(Literaturwissenschaft)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Literaturtheorie)和文学批评(Literaturkritik)。
《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将其对“世界文学”的考察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探。在2000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已被译为多种文字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1999)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首都”与“边疆”。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文学世界”犹如一个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在运作的“共和国”。
基于这样一种相当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娃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勘探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立意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作者看出,“直至今日,在不同的民族文学教材中,对世界文学的描述只是一个简单的并列”。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应该与所有幻想特殊性和岛国性的,与独一无二性的民族主义习惯相分离,尤其应该终结文学民族主义造成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在世界的范围比较。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
跨民族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有自己的运行模式,有自己的生成机制。对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文学空间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卡萨诺瓦走向了一种对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自主自律的机制的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的这种清理,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者的思维定势,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
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和简单的平行转换。翻译并不是中性的。所谓翻译的“中立性”是表面的。所谓美学标准的“普世性”其实是握有文学“祝圣”之话语权的“普世性”。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
应该指出,卡萨诺娃对“同化”与“分化”这两大策略的分析,对于我们习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原理”,显然是一种超越,至少也是一种补充。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我们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
《艺术话语·艺术分析》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那么,作为“职业读者”的文学学家,应该如何分析文学文本呢?《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则是这位著名文学教授的一种现身说法。在这里,多年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一线耕耘的秋帕教授力图建构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涵义。文学学领域的“科学性”有何特点?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容?作者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且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与《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既以新视界阐述“文学原理”,也以新维度展示文本分析,彼此有内在关联,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颇具开拓精神与创新锐气。
《20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学派与集群》与“理论学派或集群发育学”
“学派与集群对20世纪的学术氛围产生了何种影响?某一集群内部或集群与其学术环境之间交流的模式是什么?概念性知识如何转换为文化环境?学派或集群延续着一套什么样的解释性约定以及认识论上的偏好?学派或集群内部以及外部接受其运作方式会带来何种影响?学派与集群如何形成、怎样瓦解?缘由何在?”《20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学派与集群——文学理论、历史及哲学》(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manities——Literary Theory, History,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2015)便聚焦于这些问题,或者说,聚焦于“理论学派或集群发育学”。
该书强调文学理论的跨学科性,关注文学理论学派或集群之间的关联性;作者都是该学派或集群的资深研究者,甚至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阐述耶鲁学派的那一章名为《(耶鲁)学派的故事》,作者即为希利斯·米勒。《芝加哥学派:从新亚里士多德诗学到修辞叙事学》一章则由詹姆斯·费伦写就。这样的作者,能从专业角度出发,阐释学派或集群的核心概念、思想渊源、发展流变。这样的梳理不仅会促进文学理论观念史、思想史研究,还会推动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书中所论述的结构主义学派、符号学、现象学和阐释学派,对文学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该书还涉及一些多年来未得到深度开采的理论学派,譬如波兰结构主义、特拉维夫诗学与符号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该书定位于这些尚未得到透彻研究或系统梳理的学派或集群的理论建树,体现出当前国际文论界对理论学派或集群之最新的且有深度的开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摘自《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
——《艺术史导论》评介
——《戏剧学导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