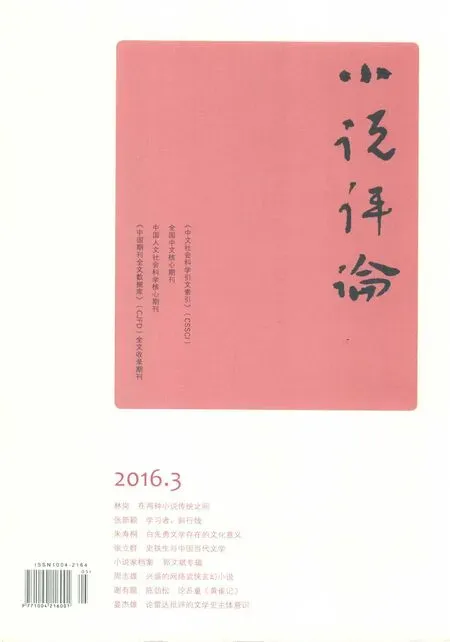形塑与分裂:政治理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
——以《蛙》中“姑姑”的形象为例
栗 丹
形塑与分裂:政治理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
——以《蛙》中“姑姑”的形象为例
栗 丹
在莫言早年的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内涵往往是建立在生命与伦理的意义基础之上:《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丰乳肥臀》中坚忍而顽强的母亲上官鲁氏,《檀香刑》中风流而妩媚的“狗肉西施”孙眉娘,等等,她们往往带有很强的传奇性与诗意,人物的内涵当然也很丰富,但与此同时,她们也常常是当代文化与政治的绝缘体,不太能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与历史进程产生瓜葛。而《蛙》中的“姑姑”则不同,她虽然也具有某些相似的个性,比如率真而强势,专断而干练,等等,但她身上的传奇意味与前几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已经明显淡化,而带有了很强的现实性。其直接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进程,在战争、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多重张力场中演绎的人生,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感。本文试图以“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为切入点,展示20世纪以来以革命为主旋律的政治理性的起伏对乡土社会和人性的塑形与分裂。
一、政治理性与自我认同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的文化帝国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女性在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有限。就前者而言,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强调原则性地界定了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就后者而论,受到激进革命涤荡的现代政治伦理体系虽然打破了男女不平等的藩篱,其性别身份(妻子、母亲、女儿)仍然制约着女性介入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蛙》中的“姑姑”却是一个特例,而之所以如此,与姑姑特殊的身世相关。“姑姑”(万心)的父亲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不幸牺牲。“母亲”和“姑姑”受到株连,被关押在日军的监狱里。后经组织营救转移到解放区。解放后,作为烈士的后代,“姑姑”自然受到组织的照顾,为继承父业,她被送到专区卫生学校深造,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不久,“姑姑”显示出了做妇科医生的超人禀赋——医术高明,又加上她黄金般璀璨的出身,使她超越了性别限制,和众多屈身庭院灶台间的普通妇女判然有别。她不仅走向了社会,而且成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宠儿,受主流意识形态庇护,被国家政治制度接纳,全身心地融入这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环。
就性别政治观之,千百年来,女性的边缘化身份制约了她们对政治的介入。但仅从“姑姑”这一形象及其映射的真实历史即可知,“政治对女性毫无吸引力”的结论推导相当草率。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无论何种性别,都一样不可能漠视政治的诱惑。一旦跨入以政治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人的身份就要受到规范和再定义:不仅要从中获得物质利益,而且还要从中获得精神满足。“人类在政治共同体中,要求政治生活赋予个体存在和行为意义。政治共同体为个体提供意义,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在政治生活中,赋予意义的途径主要是建立个体自我认同与政治生活的联系,政治认同使得政治个体获得意义。”①在小说《蛙》中,“姑姑”毫无悬念的将个人的自我认知与恢弘的革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自觉的将“革命的政治”变成了“我(个人)的政治”,个体通过对政治生活的身心融入找到了生命意义和集体归属感。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作为女性个体的“姑姑”在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使得“姑姑”把革命政治理性的价值和自我存在的价值置于同一水平线上,并将后者完全融入到前者的宏伟架构之中。正如罗洛·梅在《人的自我寻求》一书中指出:“一个个体内在力量和完整性的程度将取决于他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他所信仰的价值观。”②通过小说我们看到,职业生涯初期的“姑姑”从政治共同体中获得的内在力量充溢其本人的日常和社会生活之中。“姑姑”背着医药箱行走在高密东北乡的凸凹不平的乡间小道上,像革命的女侠健步如飞,像人间的仙女手到病除,像逢凶化吉的春风抚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是“姑姑”人生中最为耀眼的“青春之歌”,在这一生命旋律中,政治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达到了高度统一,因而相当程度上处于个体存在的完美境界。
然而,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任何平衡都难以永恒,某种统一而稳定的结构也随着社会和个人的变迁终归被打破。首先打破这种平衡的是“姑姑”的恋爱对象王小倜。王小倜是50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空军飞行员之一,英俊洒脱,众人仰慕,深得“姑姑”爱恋,谁知他竟驾机叛逃台湾。在“株连”的政治惯性思维之下,“姑姑”自然成了被质疑和惩罚的对象。在巨大的政治风险面前,个人情感的挫伤和被抛弃的耻辱简直微不足道,捍卫此前的人生意义并由此延伸出来的自我保护才是“姑姑”的心头重事。为了表明与王小倜彻底划清界限,“姑姑”用血书写下“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誓言来表明政治立场。“文革”大潮涌动,身背处分的“姑姑”需要用革命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她参与揭发了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老院长惨遭凌辱,最后愤然自杀;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同事黄秋雅,“阶级斗争”思维支配下的“姑姑”下意识地运用革命手段给予无情打击……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姑姑”不得不完全顺应着政治共同体发起的一切行动,政治权力的容纳、鼓励和支持成了她的终极寄托——爱情被埋葬,恩情被蔑视,友情被扼杀,良知昏昧,人性变异。在这一过程中,“姑姑”把个体伦理和革命伦理强制性地缝合在一起,把自我政治工具化的生活视为最有意义的生活,在组织和权力的规范中俨然实现了自我认同,自我纯化为一个“政治的动物”。她不能懂得象征着政治理性的政治共同体的内涵时刻处于动量状态,个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也处于不断分离和整合的过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随后的“文革”狂潮中,“姑姑”感受到了被“政治共同体”抛弃的滋味。肖上唇带领造反派把她作为“牛鬼蛇神”批斗,造谣污蔑,羞辱殴打,“姑姑”的“拒不认罪,动辄反抗,更使每一次批斗大会有声有色,成了我们东北乡的邪恶节目”。③然而,这种反抗并非“反对”,而是“辩诬”,一切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组织的无限忠诚。但是,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到,个体生命与政治浪潮的统一性,如同冬末的冰层,内部已经传出了塌裂之声。“姑姑”的自我认同形成于外力的笼罩和强力推动,一旦政治大潮消退,认同自然也会向个体本心摆动。而在此之前,个体往往迷失和融化于国家机器的转动中。
二、政治行为与个体迷失
计划生育政策关涉到民族兴衰、国家存亡,其历史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宏观意义上的政治正当性却不能保证执行过程中在微观层面中不出现失误、错误乃至罪恶。问题如此复杂与敏感,因此到目前为止鲜有文学作品对之加以反思。莫言以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人文勇气,闯进禁区,借此检点起这段历史的得失,反省民族文化的优劣。
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压力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姑姑”不仅要提供技术支持,还被赋予至关重要的政治使命——兼任了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事实上成为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充当高密东北乡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急先锋”。而这与乡土社会及其传统伦理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冲突: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对于劳动力需求巨大。与之相适应的儒家宗法文化由此衍生出传宗接代、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造就了官方和民间之间在节育和生育问题上的根本性矛盾,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伊始受到广大农民的顽强抵制。“姑姑”开始向基层宣讲计划生育政策后,群众威信就急转直下,连村中那些曾深得她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在执行过程中,躲避与抓捕联袂上演,反抗与镇压前后相继,甚至带有血腥气息。这种对抗在七十年代末的计划生育第二次高潮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为把张拳妻子弄去流产,“姑姑”率领秦河、小狮子、黄秋雅等乘坐计生专用船“进剿贼寇”,张拳用棍子打得“姑姑”鲜血淋漓,而跳河逃生的张拳媳妇在水中流产,失血过多,一尸两命;为抓到因袁腮取环而秘密怀孕的侄媳王仁美,“姑姑”带领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特别工作队进驻村中,以拔倒邻居肖上唇家大槐树的方式逼其现身,尽管王仁美在教育攻势下深明大义,但不幸在手术中丧生,而“姑姑”也被死者的母亲一剪刀捅在大腿上;为做掉侏儒王胆的胎儿,“姑姑”带人强闯民宅,用计生专用船追击她用以逃跑的木筏,致使王胆早产,“姑姑”伸出援助之手却只救活了婴儿……
理性观之,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既有合法性和必要性——人口数量适度是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控制人口是我们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艰难转型的无奈之举。但是,繁衍后代却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生生不息”在传统观念中更是人的创造力的原始表现。建国初生育人口曾一度被看成对国家的贡献,而在现代观念中生育又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生育和控制生育,遂在各个层面搅起冲突与悖反。不幸的是,“姑姑”作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被推到各种矛盾交锋的风口浪尖上。从“送子”到“限子”乃至不断发生“灭子”的悲剧,“姑姑”承担了国家政策的罪责与骂名。
对于一般人来说,只要政治指令符合公共善的要求就会感到问心无愧,至于是否符合道德人性的内涵则是崇尚政治理性的人不予考虑和思索的,大善之下的小恶不值一提。而莫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略过这一简单化思维背后蕴含的民族无意识。他深刻地反省到,群体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构不成真正的主体,它能构成实践主体却不能行使责任主体的功能,“没有个人的人格主体作为根基的那种群体责任感,哪怕它自以为是出自本真的内心(诚),也仍然是一种无个性的、甚至是奴化的责任感。”④然而,对群体的责任心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这一庞大的文化体系中从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责任心和罪感,却大量存在对政治指令的绝对服从和对公权力不计边界的滥用。“忠孝同构”导致的“舍小家为大家”、“家国同构”导致的“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模糊,而恰恰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最大区别。退休后的“姑姑”也许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她可以遵循惯常思路用千万个理由推卸掉个体的责任,自己不过是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所有的行为都是组织的决定,但是,这些在道德法庭却完全不然,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一切行为实际上都经过了自己的选择和决断,应该由自己负责,“不论何种理由我终究杀了人,我做了自己决不允许做的事。”“姑姑”无可逃脱的罪感和忏悔,实际上是建立在这种责任的彻底领悟之上的,亦可以说是建立在个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个体意识,把其他个体看成和自我一样的、具有平等生存权利的个体,就不会有真正的责任感。群体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对个体忽视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它在历史的进程可能迸发出惊人的进步力量,但是对个体价值、尊严和生命的某种漠视,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此,作家莫言的反省已经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深处,他在开始解构和祛魅政治宏大叙事的同时,试图促进个人理性的萌生与进步,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政治祛魅与价值复活
“姑姑”的人生轨迹和心灵轨迹是高峰和低谷并存的曲线,这两条曲线并不是平行的轨道,而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支配下,扭结穿梭,使其人生充满了张力。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划分,所谓“价值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所关注的是某些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行为的合理性。在《蛙》中,对生命无上价值的确认理应被界定为个体价值理性问题。而“工具理性”则是指人的行为由功利动机所驱使,借助“成本-收益”的计算选择行动方案,行动者纯粹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相对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在“姑姑”以计划生育政策“先锋执行者”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忠实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理性”,使生育伦理被当成是原始欲望和私人行为。在“公德”压倒“私德”的背景下,“工具理性”显著的行为也被笼罩在更大的“国家价值理性”之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成了被动执行系统命令的存在物,由此,人的价值和意义失落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更宽广的视野看,不独“资本主义”,在广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技术手段的发展往往使诸如国家权力、商业资本等元素以更加猛烈的方式渗透到个人的生活中,机械性的社会要素对个人的影响无远弗届。而工具理性扩张的则必然伴随着某种基本社会要素对人性的改造甚至侵蚀,这种不断地“形塑—分裂”造成的人性的异化恰恰构成了身份焦虑的原因和自我反思与救赎的起点。源出个人本心的价值理性的失语与某种群体价值背后工具理性的独裁,两者关系的扭曲与断裂,必然导致人性的工具化、贫乏化以及主体性的丧失,这也是真正实现救赎所不得不面临的困境所在。
我们看到,那个动辄就操持政治话语的“姑姑”,那个握持手术刀冷酷无情的“姑姑”,那个眼见家破人亡却无动于衷的“姑姑”,实际上就是被政治工具理性完全异化的“姑姑”。就理论形态而言,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是由于工业化、技术化高度发展造成的,他批判的对象是理性化社会对人身自由的控制;而中国现当代的工具理性则主要源于极左政治/大众运动的病变,莫言反思的则是这种泛政治化社会对人性的裂解与扭曲。二者表现样式不同,但在对人性异化方面则趋于一致——工具理性的扩张最终使人成为一种没有感性的僵化的木乃伊。深究起来,在“姑姑”身上,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倒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通览《蛙》之全篇,从“成群的蜜蜂跟着我飞”的“送子娘娘”,到远不止“对着虚空劈一掌”的“活阎王”,作为“革命红二代”并有着鲜明男子性格的“姑姑”始终将执行国家政策当做实现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方式,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纯洁信仰则是其价值构成的决定性维度。这种革命“典型”的背后,实则蕴藏着深刻的民族文化无意识。金观涛、刘青峰精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把个人道德投向社会制度,甚至和整个宇宙秩序联成一体以形成天道的传统,这是宇宙规律、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整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结构,其后果是革命斗争成为终极关怀和修身方式,即革命人生观之形成。所谓以革命为终极关怀,一方面就是以取消一切差别为理想道德境界……另一方面,道德最重要的特征是身体力行、言行合一;以这种革命道德付诸行动,就是参加革命,并用斗争作为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方式。”⑤据此则可以推论,当与道德修身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本属于工具理性层面的“斗争哲学”反而以“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组织归属感和精神依托拥有了不容侵犯的“价值理性”色彩——更何况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从社会学角度讲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有其相当充分的客观合理性。
既然如此,对上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深度纠缠的反思,就不得不只能在个人对公共政治的疏离中得到实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人通过公共关系网络完成自我社会身份的界定,当这种界定因与社会组织细胞的疏离而变成不确定的时候,身份焦虑的凸现客观要求个人通过省思而实现自我救赎和释放。于是我们看到,“姑姑”忏悔的节点以退休为标志,以身份的转换为契机。退休之夜,已经微醺的“姑姑”回家途中路过村边的池塘,于是发生了如梦似真一幕。蛙声一片,“蛙—哇—娃”的连带性联想,为“姑姑”对人生的反省提供了契机。“姑姑”退休,她不再是医院的院长,不再是计划生育领导机构的成员,她开始从政治体制中脱离开来,从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的身份中脱离开来,社会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权力不存在了,个人与社会网络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疏离。褪去种种社会关联,个人的良知在这一刻渐渐复苏,灵魂开始受到道德的拷问。然而,忏悔之路是如此泥泞艰辛,无数青蛙四面八方涌向“姑姑”,牢牢抓着她的肌肤——耳朵几近撕裂、裙子全部撕扯干净、“姑姑”几乎赤身裸体奔跑着——只有去掉了各种社会意识赋予的迷障,赤身裸体地面对自己,她才能领悟到自己的“罪恶”。
然而必须指出,触发“姑姑”进行“自我救赎”的关节点既非送子娘娘庙,亦非那些计划生育的“受害者”,而是被高度艺术化了的大自然的蛙鸣。这种安排反映了莫言深刻的洞见,也透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维模式:即人只有摆脱社会、隔绝政治,完成心灵“去蔽”,才能直抵本性,显露“赤子之心”和“恻隐之心”,焕发出自然母性,从而开始认同民间传统的生育伦理——这就是老子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的自然主义精神。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特有的“启蒙”方式,即在政治权力和社会组织不再牢固地绑架个人身份时,人的自我反思和恻隐之心才能得到恢复与成长。在小说中,这种反思的巅峰出现在“赤身裸体”的“姑姑”跑过小桥与郝大手相逢之后。喝完绿豆汤,“姑姑”感觉“脱皮换骨”,猛然要求嫁给郝大手——她试图通过与之携手制作有名有姓的泥娃娃,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充当“刽子手”的深切忏悔。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婚姻,它极力忽略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般配,虔心寻求的是灵魂上的救赎。郝大手是当地的泥塑工艺大师,能根据父母的外貌,捏出那些因流产而逝去的娃娃的形态。而“姑姑”则借助郝大手的技艺,为她毁掉的二千八百个孩子各塑泥身,摆在厢房,常年供奉香火,只等它们有了灵性,重到人间投胎。摆脱了政治捆绑的“姑姑”开始真正面对自己的灵魂,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与尊重恢复了她的善良内心与圣母情怀,从而能够实现精神救赎,获得人性升华。
通览小说,我们从“姑姑”这一形象的变迁中仿佛看到了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纠缠,个体人性、民间文化与国家理性的冲突,而小说本身则某种程度上以“姑姑”这样一个普遍却不普通的人生画卷折射了二十世纪跌宕起伏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不同侧面。而埋藏在更深处的话题则是,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和问题成为人们在实现现代性中的关键问题,并在不同层面对人性进行形塑与分裂,这充分表现在“姑姑”的思想中,万小跑以及杉谷义人的思想中,甚至应该说贯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中,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其“幽暗”的一面,需要我们鼓起理性的勇气去面对。正如小说最后一部分(第五部)的开篇万小跑所言:“先生,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负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王仁美和她腹中孩子——当然也是我的孩子——之死,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甚至推给王仁美自己——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⑥小说令人震撼的地方就在于此,作者勇于面对自身的懦弱与无力,由己及他,以深沉的笔力写出了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在协调上述两种理性时面临的困境,它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会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莫言抓到了这一点,也就抓到了当代文化反思的命脉。人类如何去面对被异化的命运,如何去协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掩卷沉思的永恒命题。
栗 丹 东北财经大学
注释:
①彭勃:《自我、集体与政权:“政治认同”的层次及其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 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③⑥莫言:《蛙》,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73页、289页。
④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⑤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