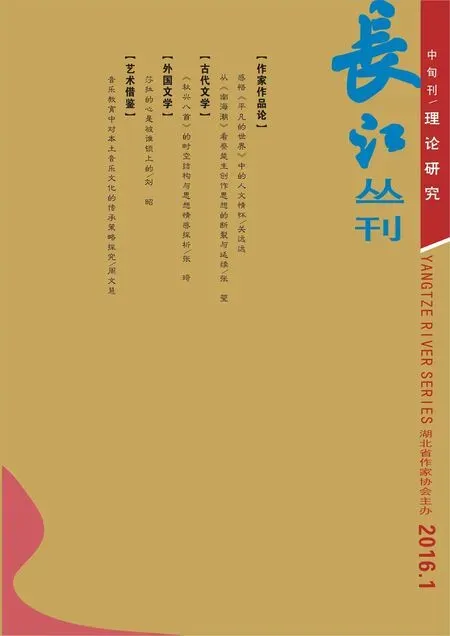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文学创作特质辨析
刘振生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文学创作特质辨析
刘振生
【摘 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莫言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位作家虽然国籍不同,但同属于东方文化圈,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韵味。这一点既反映了东方日本和中国在文化背景和文学叙事上的共通性,也揭示了这两位作家所代表民族的历史轨迹和将要面对的共同未来。他们除了在表现手法上受到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的影响外,在主题方面的趋同和相近也尤其值得关注。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莫言 文学
一、源于森林与大地的创作灵感
大江健三郎于1935年出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离开了人世,母亲独自养育了他们兄弟7人,家境曾一度贫困不堪。高中毕业后他从穷乡僻壤只身来到东京求学深造,考入东京大学的法语专业。此时的他受到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旺盛的精力。 1957年他在就学期间完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刊登在《东京大学新闻》上,荣获该报“五月节奖”,崭露头角,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翌年,延续此时的文学风格,又在当时重要的文学杂志——《文学界》上发表了以美军占领日本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饲育》,荣获第39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从此登上日本文坛。
大江健三郎故乡四国的森林和溪谷是其人生初期二十年的世界全部。这里让他充分享受到了大自然给予的恩惠——山、水、森林、田园,也让他在这段时间拥有了一个质朴而简单的生活情致。森林的静谧、神秘使他尽可以带着童趣去想象和探索,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着作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灵感。这些来自于童年生活的点滴累积,逐渐在后来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耶斯普马基在颁奖会上评价说:“大江的作品是对过去的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回答。譬如,我们祖先逃避现实而来到了大山里、一个世纪前所发生的农民起义以及兄弟间的失和、来自新生智障儿的精神打击。另外一个就是核爆炸、核武器的悲惨结果与智障儿的关系。”[1]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农村。尽管他出生于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但少年时代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并切身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变革与发展。故乡地域辽阔,广袤无垠,但生活上曾长期闭塞、拮据。这些来自自然的、社会的“羁绊”使一个农村少年对外部世界逐渐产生了幻想并曾想一度逃离家庭、逃离家乡。经过都市的来自于钢筋铁骨“森林”的洗礼,使他在内心中逐渐产生了回归故里、回归现实的念头,并最终通过创作实现了回归。他的回归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够将过去的记忆化作其创作的素材、作品的骨架,甚至是作品的灵魂。通过创作,他感受到家乡的创作舞台是多么的广阔,家乡的一草一木、名人趣事给了他莫大的创作灵感。莫言的文学也正式开始并定位于高密家乡的真实故事与美丽传说。
正如很多评论家所言,莫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用他那狂放不羁的语言表现与叙事方式来给这一时代和人类内心加上了属于自己的注释。山东有着无尽的传奇与神秘,高密大地也成为他创作上的可以无限想象的大舞台。他的作为红高粱家族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通过塑造爷爷、奶奶、母亲等形象来讲述民族的苦难和生命的坚韧、执着;《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和《蛙》都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这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素材触摸着作者的内心世界,激发着更多的创作灵感。《生死疲劳》则充满了莫言所惯用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风格,以生命的轮回为着眼点,书写着民族的历史悲歌。莫言通过自己源于故乡的独特创作灵感,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小小村落扩展为惟东方才有其特殊寓意的世界性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大地上,以“我爷爷”、“我奶奶”等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的百姓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且善于为生存奋斗,为生命讴歌。这恰似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又如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心的悲戚。
二、基于现实与想象的艺术表现
文学创作是一种从抽象到形象的思维演绎过程,期间离不开作者的无尽设计与想象。而设计与想象也不能是无源的任意的天马行空。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文学构成源于故乡曾经的春华秋实、曾经的喜怒哀乐、曾经的爱与恨、曾经的情与仇。从世界文学的大舞台来看,尤其是从他们文学创作的特色来看,除了源于家乡的艺术表现灵感外,也有很多方面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的写作风格接近。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创作对当代美国文学做出了强有力的和无与伦比的贡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一个庄园主家,自幼受到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他的作品体现了南方人的特性,富有幽默感。作品深刻地表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在地位等敏感问题上的不同。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充满神秘色彩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从而希望读者思考造成马贡多百年孤独的原因以及寻找摆脱命运捉弄的正确途径。
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创作上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大江健三郎六岁时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从而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十岁时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的祖父母、父亲都死于这个充满暴力、展示人性的恶时代,外界的刺激和影响使他在内心世界中表现出了很大的反感与反抗情绪。《万延元年的足球》表现了关于残疾儿的主题。主人公蜜三郎因家中生下了一个残疾儿而不知所措。他的精神陷入了痛苦及崩溃边缘,甚至连象征生命力的性功能也无法唤起。消沉、堕落,还是抗争、崛起,无奈之下他只好跟随弟弟鹰四离开东京,返回家乡四国。在那里他一方面从处于贫瘠生存环境中的村民身上感受到了生命力的不竭,另一方面也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根所家族的历史先辈以及弟弟鹰四的主动抗争中,感受到了可以面对现实努力改变的力量。通过努力,他终于从曾祖父、弟弟和鹰四等人身上悟出了抗争的意义,从而开始否定自己迄今为止的懦弱行为。最终蜜三郎勇敢地从地窖里走出来,做出了抚养残疾儿子的积极选择。
长篇小说《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完成于1977年。在这部作品里大江健三郎仍旧对核时代进行文学创作与想象,表达了强烈的人类核危机忧患意识。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来构架通篇,其主要情节就是主人公“我”的想象和基于想象的虚构,与此同时以“我”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遇为并行的另一条线索。作品的故事情节带有很高的科学幻想色彩,描述宇宙主宰为了拯救地球所面临的核危机,派来了两个人以帮助拯救这一世界的情景。但是,地球并没有因为有两个帮忙人而改变其发展轨迹,甚至走向了相反方向。这一作品完成发表后乃至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甚至有人怀疑这是杞人忧天。但是到了2011年福岛大地震爆发、核泄漏出现就深刻地印证了作者的想象力与创作上的预见性。
莫言出生于1955年的新中国和平发展时期,但与之前的东北民族斗争史在时间距离上并不遥远。正如他的系列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道神嫖》等,实际上就是对战争与暴力历史记忆的整理与想象。山东齐鲁大地的丰富的文化精神在高密也处处被浸染。莫言以家乡为原点进而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典故来描写这些活跃于高密东北地区的人物,同时运用了自己源于青年时代累积的想象力,天马行空地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了民族生命抗争与文化精神自立的文学世界,进而通过对祖父、祖母、母亲、姑姑等人物形象来进行艺术加工,试图获得对所属民族、族群精神史的唱诵。
《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8年,是一部体现中国作家良心、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文学力作。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农民因大量种植大蒜却无引导而导致滞销,最终无力挽回损失的真实事件,体现了作家勇于干预生活的艺术追求。这原本是一个被报纸报道的事件,但出于对社会的表达与批评,莫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这部长篇小说。小说采用了当地民间艺人演唱与作者正面叙述结合并行的方式,充满张力和激情。反映出作品除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的同时,也充满了深厚的魔幻现实主义韵味。
2005年莫言完成了新作《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作者对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推动。作品中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构筑了一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场景,勾画出了农民百姓对道德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无比执着的图像。作品似乎在架构上吸收了《聊斋志异》等经典之灵气,表现出对现实社会人们贪欲的讽刺与批判,也是一定意义上对人性根本的质问与清算。
三、自我突破与文学责任
大江健三郎一直是一位致力于探索日本人、日本文化与世界关系的作家。他个人的经历,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1958年小说《饲育》获芥川奖时他就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选择文学的责任所在。”[2]由此可以窥视出其对本人创作的客观认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因而,他既是一个作家、文人,也是一个有思想、有勇气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试图通过文学在一定层面上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所敬仰和推崇之关键所在。在他看来,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二十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一个总清算。他还认为自己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读者,只是在对日本读者说话。这也反映出作者对日本文化现状的不满与焦虑。
莫言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经济贫困和政治贫困相交织的时代。无书看、无饱饭,这些经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深刻记忆和更多的幻想。同时,由于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在精神上备受压抑,以至于不断地想寻找一个突破口,走出高密农村。这种心理特征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了他后来从事小说创作。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这里有他不可能进行选择接受的质朴的说唱、社戏等文化生活,所以他的创作自然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正是他创作的舞台。同时也通过他依赖故乡——背离故乡——回归故乡的一个肉体与精神的自然循环过程,使他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
如前所述,山东高密有很多神话及民俗传统,这些都成为莫言文学创作的底蕴与基石。《红高粱》系列中的很多民俗,令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民族、族群的灵魂与精神所在。正如他本人所言:“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然而,只有接触到这种内心冲突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3]他的表述反映出作者对源自家乡文学创作的一种自我突破的期许,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对社会与人生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更具有世界性并分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而成为为中日两国、两个民族及两代人可以相向而行结为忘年之交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大江健三郎著,于长敏译.万延元年的足球·序[M].北京:光明日版出版社,1995.
[2]大江健三郎著,于进江译.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2):61。
[3]叶开.莫言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振生,文学博士,大连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文学与文化比较。
——以大江健三郎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