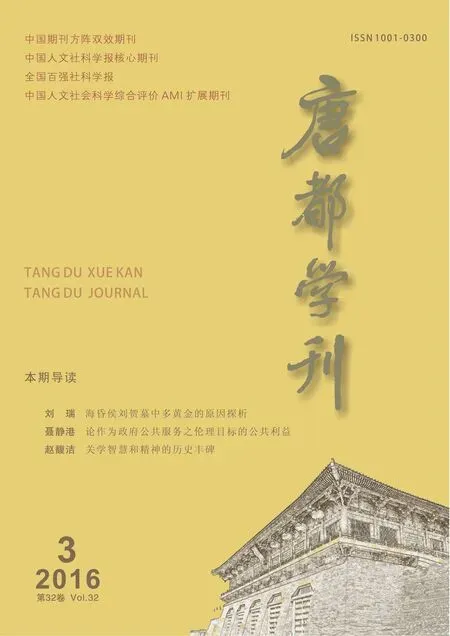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论略
师彬彬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论略
师彬彬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主要包括财产刑、贬夺官爵、迁徙刑、死刑与连坐五大类型,司法机关主要依据罪行轻重实施相应刑罚。东汉宦官犯罪轻则处以经济刑或贬夺官爵,重则施以迁徙刑、死刑或连坐,甚至多种刑罚并用。东汉政府虽以严酷刑罚惩治宦官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有效遏制宦官犯罪。东汉宦官因犯罪、连坐或被诬告而处以刑罚者比较普遍并沦为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对当时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映了汉律的严酷、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趋于激化。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呈现差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刑罚类型多样化与刑罚实施复杂化两个方面。
东汉;宦官;犯罪;刑罚;类型;特征
学术界虽已关注汉代刑罚制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参见陈乃华的《关于秦汉刑事连坐的若干问题》刊于《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第1~6页;宋杰的《论秦汉刑罚中的“迁”、“徙”》刊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87~94页;张仁玺的《秦汉家族成员连坐考略》刊于《思想战线》2003年第6期,第97~102页;高叶青的《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刊于《南都学坛》2004年第6期,第1~13页;[韩]任仲爀的《秦汉律的罚金刑》刊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6~31页;张仁玺的《汉朝贵族官僚的特权考略》刊于《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83~85页;李俊方的《汉晋财产刑的传承与变迁》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47~151页;程政举的《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刊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62~65页;连宏的《论汉代的迁徙刑》刊于《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2~25页;[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王子今等译的《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徐世虹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战国秦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511页;程树德的《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51页;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5页;邢义田:《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收入《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100页;本书编委会编著:《文官之管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45页;宋杰的《汉代死刑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如明确了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未与社会群体相结合。目前尚未出现深入探讨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的论著,因此这一问题仍有待加强。本文拟在梳理史料与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类型、效果及特征以深化对东汉法制与政局演变问题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类型
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类型比较模糊,如顺帝永建二年(127),“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市,梵、防、酺、芝、敦、凤、就、国皆抵罪。”[1]3243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主要包括财产刑、贬夺官爵、迁徙刑、死刑与连坐五大类型*余华青先生认为东汉宦官的黜免论罪主要包括免官职、除封国、贬爵位、遣就国、削实封、徙边、没入财产、论死与家属连坐等方式,参见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司法机关主要依据罪行轻重实施相应刑罚。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主要涉及中黄门、中常侍与长乐太仆等高级宦官,集中于东汉中后期。
(一)财产刑
财产刑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剥夺罪犯一定财产的一类刑罚,是汉代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宦官犯罪的财产刑涉及罚金、减租与没入财产三种形式,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
罚金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罪犯在一定期限内交纳一定钱财,“罚金乃刑之最轻者”[2]1533,主要适用于轻微的过失犯罪。东汉宦官因罪处以罚金可考者仅见于明帝时期,“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复召(郭)躬问之,躬对‘章应罚金’。……帝曰:‘善’。”[1]1544
减租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削减罪犯征收封国民户的租税,东汉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宦官实施减租可考者较多,但仅见于顺帝时期。例如,“(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1]2518
没入财产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没收罪犯的财产充公或由司法机关处分,是汉代财产刑的一种重要形式。东汉中后期,宦官因罪没入财产者比较普遍。和帝时期,“(清河孝王庆)中傅卫私为臧盗千余万,诏使案理之,并责庆不举之状。庆曰:‘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纠察。’帝嘉其对,悉以臧财赐庆。”[1]1802桓帝延熹八年(165),“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大司农刘)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1]2199“(灵帝)建宁二年,(中常侍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1]2523。光和二年(179)四月,“(司隶校尉阳球)奏收(中常侍王)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颍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颍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尽没入财产。”[1]12499灵帝时期,亦有宦官被诬告而没入财产。中平元年(184),“中常侍赵(忠)、(夏)恽复谮曰:‘(中常侍吕)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草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宗亲,没入财产焉。”[1]2533
(二)贬夺官爵
贬夺官爵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降低或剥夺罪犯官职或爵位的一类刑罚,东汉宦官因罪贬夺官爵者涉及贬爵、免官、削国与除国四种形式。
贬爵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降低罪犯的爵位,东汉宦官因罪贬爵可考者仅见于桓帝延熹八年(165)。例如,“(都乡侯赵忠)黜为关内侯,食本县租千斛。”[1]2534另如,“(司隶校尉韩演)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乡侯)刘普等贬为关内侯。”[1]2522
免官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免除罪犯的现有官职,东汉犯罪的宦官免官者比较普遍。例如,“(顺帝)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1]2517。另如,桓帝延熹八年(165)正月,“(太尉杨)秉奏(中常侍侯)览等佞谄便僻,窃国权柄,召树奸党,贼害忠良,请免官理罪。……上不得已,乃免览官。”[3]423再如,“(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1]1856又如灵帝熹平元年(172)五月,“有司奉奏(长乐太仆侯)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1]2524。
削国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削减犯罪王侯的封国土地,东汉宦官因罪削国者极少。如桓帝延熹八年(165)正月,“(太尉杨)秉奏(中常侍侯)览等佞谄便僻,窃国权柄,召树奸党,贼害忠良,请免官理罪。……上不得已,乃免览官,(中常侍具)瑗削国事。”[3]423
除国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取消犯罪王侯的封国。东汉中后期,犯罪的宦官除国者较多。例如,“(长乐太仆蔡)伦初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1]2514另“(桓帝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夺封邑。”[1]1856
(三)迁徙刑
迁徙刑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罪迁移居住地,是汉代惩治犯罪的一种常用刑罚。汉代迁徙刑*学术界关于汉代迁徙刑问题的系统研究,参见[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王子今等译和《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邢义田的《从安土重迁论秦汉时代的徙民与迁徙刑》收入《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2~100页;宋杰的《论秦汉刑罚中的“迁”、“徙”》,第87~94页;连宏的《论汉代的迁徙刑》刊于《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22~25页。大致分为免官遣就国或归本郡、徙封、徙边、谪戍、谪徙、迁虏六种类型,呈现阶段性和形式多元化的特征。东汉宦官因罪处以迁徙刑者较多,涉及遣就国、徙封与徙边三种形式。
遣就国亦称遣还国,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犯罪的王侯遣回封国,是汉代最轻的一种迁徙刑。顺帝时期,宦官因罪遣就国者比较普遍。例如,“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程既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士,赐车马衣物,遣还国。”[1]2517另如,“(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1]2518
徙封指司法机关依法强制犯罪的王侯从大或富的封国迁移到小而穷的封国。顺帝时期,犯罪的宦官徙封者较多。例如,“(永建元年)秋九月,有司奏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为司隶校尉虞诩诃叱左右,谤讪大臣,妄造不祥,干乱悖逆;(长乐太官丞)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师,益其骄溢。诏免程等,徙为都梁侯。”[3]345另如,“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1]2517
徙边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遣送罪犯到边远地区并不准擅自迁回原籍,是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一种刑罚。“汉魏晋之徒刑或徙边,均为减死罪减降处置,并非正刑”[4]93,东汉统治集团主要将徙边作为减死一等的重刑“以全人命,有益于边”[1]1545。例如,“(顺帝建康元年十一月)己酉,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1]276顺帝时期,宦官因罪徙边者较多。如永建元年(126),“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司隶校尉)虞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诩子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1]1870-1871另如,“(中常侍高)梵坐臧罪,减死一等。”[1]2518
(四)死刑
死刑指司法机关采用暴力手段强制剥夺罪犯生命的一类刑罚*宋杰先生认为汉代死刑分为显戮与隐诛两种形式,自杀和下狱死属于隐诛,参见宋杰的《汉代死刑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汉以死刑为重罪”[5]38。东汉中后期,宦官大多因重罪施以死刑。例如,“(顺帝永和)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有罪诛。”[1]268另如,桓帝延熹九年(166)十一月,“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郡吏王)允讨捕杀之。”[1]2172再如,灵帝建宁元年(168)五月,“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大将军窦)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1]2242又如,中平元年(184),“灵帝以(张角弟子唐)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1]2300
此外,东汉后期,部分宦官被诬犯罪而处以死刑。如灵帝熹平元年(172)十月,“(司隶校尉段)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1]2153-2154。另如《后汉书·皇后纪》载建宁四年(171),“中常侍曹节、王甫疾(黄门令董)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1]446另如中平元年(184)三月,“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搆(中常侍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遂自杀。”[1]2533
东汉宦官因罪实施死刑者比较普遍,主要涉及自杀和下狱死两种类型。自杀即罪犯自主结束生命,是汉代死刑的一种特殊形式。东汉司法机关强迫犯罪的高级宦官自杀,避免了下狱拷掠以“养臣下有节”[6]226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尊严。
由于严酷的刑罚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东汉宦官因罪或政治斗争失败而自杀者比较普遍。例如,“(长乐太仆蔡)伦初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1]2514另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司隶校尉韩演因奏(中常侍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1]2522再如,灵帝熹平元年(172)五月,“长乐太仆侯览有罪,自杀。”[1]333又如,中平六年(189)八月,“(中常侍张)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1]2537
东汉后期,宦官亦有被诬告而自杀者。如灵帝中平元年(184)三月,“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搆(中常侍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1]2533

(五)连坐
连坐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对与罪犯有一定身份联系的人(如亲属、邻居、同僚)连带实施的一类刑罚,大多适用于惩治重罪。两汉政府广泛实施连坐,“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8]580,从而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并增强了刑罚的威慑效果。东汉宦官犯罪的连坐集中于东汉后期,涉及亲属连坐和职务连坐两种形式。

东汉宦官因亲属犯罪而连坐者比较普遍,主要处以贬夺官爵。如桓帝延熹二年(159)十二月,“(州从事朱震)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1]2171另如,延熹八年(165),“(司隶校尉韩)演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1]2522再如,延熹八年,“(中常侍侯)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除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1]2523又如,“(灵帝)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京兆尹盖)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1]1882
职务连坐即司法机关依法强制对存在职务过失的官吏连带实施的一种刑罚,“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6]1101。东汉中后期,宦官被实施职务连坐者较多。如桓帝延熹六年(163)十二月,“(司空周)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侯)览、东武阳侯具瑗,皆坐黜。”[1]1538东汉中后期,相关官员因宦官犯罪而处以职务连坐者较多。例如,“(顺帝永和)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有罪诛,连及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晧,下狱死。”[1]268另如,“(桓帝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夺封邑,因黜(侍中尹)勋等爵。”[1]1858

二、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效果及特征
本部分拟在对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分类与名称厘定的基础上,归纳其效果和特征。
(一)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效果
东汉宦官因犯罪、连坐或被诬告而处以刑罚者比较普遍,对当时的政局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东汉司法机关虽以严酷刑罚惩治宦官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有效遏制宦官犯罪。
首先,东汉宦官享有有罪先请与免于刑戮的特权,不仅体现了皇帝对司法权控制的加强,而且反映了政府对特权阶层的法律优待。东汉平民犯罪后,司法机关一般可以直接依法逮捕和审判。有罪先请指一定范围内的官僚、贵族及其子孙犯罪后,普通司法机关不得擅自逮捕与审判而必须奏请皇帝裁决,一般可以享有减免刑罚的特权。例如,“(光武帝建武三年七月)庚辰,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1]35东汉中后期,部分宦官因有罪先请而减免刑罚。如安帝延光四年(125),“有司奏(中黄门王)康、(中黄门苗)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1]2517另如,“(桓帝)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中常侍曹)腾,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皓奏。”[1]2519再如,灵帝中平元年(184)十二月,“黄巾贼别党起于豫州,(豫州刺史王)允击,大破之。于是贼中得中常侍张让书,允具以闻灵帝。帝深切责让,让辞谢,仅而得免。”[3]519东汉宦官的死刑主要涉及自杀和下狱死两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死刑的威慑效果。

再次,由于东汉中后期监察制度的衰落与异化*参见李小树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7页。,司法机关对宦官犯罪的刑罚效果随之削弱。其一,东汉中后期,部分监察官员纵容宦官犯罪。如顺帝时期,“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1]2017另如,“(桓帝)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1]1107。再如,灵帝时期,“阉宦擅朝,英贤被害,(侍御史田)丰乃弃官归家。”[9]201其二,东汉中后期,一些监察官员沦为宦官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桓帝时期,“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佟、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1]3283另如,永康元年(167),“是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以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间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1]3283-3284再如,灵帝建宁二年(169),“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太常张)奂独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1]2141又如,中平元年(184)六月,“(司隶校尉)张忠怨(荆州刺史徐)璆,与诸阉官搆造无端,璆遂以罪征。”[1]1621
(二)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特征
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具有差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刑罚类型多元性和刑罚实施复杂化两个方面。
其一,东汉宦官犯罪呈现刑罚类型多样化的特征。东汉宦官犯罪者,司法机关主要依据罪行轻重实施相应刑罚。如《汉书·陈咸传》如淳注曰:“律,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6]2902另如,“依当时律条,臧直十金,则至重罪。”[6]3388东汉宦官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处以贬夺官爵。如顺帝时期,“(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1]2518《后汉书·刘瑜传》亦载:“(桓帝延熹)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夺封邑。”[1]1856东汉宦官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实施财产刑。如桓帝延熹八年(165),“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大司农刘)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1]2199《后汉书·侯览传》亦载:“(灵帝)建宁二年,(中常侍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而览伺候遮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1]2523东汉宦官犯罪者,司法机关或实施迁徙刑。例如,“(顺帝)永建元年,(中黄门孙)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1]2517东汉宦官犯重罪者,司法机关或处以死刑。如《后汉书·窦武传》载:灵帝建宁元年(168)五月,“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1]2242另如,光和二年(179)四月,“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京兆尹杨)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1]1768
其二,东汉宦官犯罪具有刑罚实施复杂化的特征。东汉皇帝、权臣对宦官犯罪的刑罚的执行影响甚大,宦官被诬受刑、有罪减免刑罚与刑罚执行滞后的案例比较常见。东汉后期,部分宦官被诬犯罪而处以死刑。如灵帝熹平元年(172)十月,“(司隶校尉段)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1]2153-2154另如,《后汉书·皇后纪》载:建宁四年(171),“中常侍曹节、王甫疾(黄门令董)萌附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1]446另如中平元年(184)三月,“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搆(中常侍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遂自杀。”[1]2533
东汉中后期,一些犯罪的宦官因皇帝庇护而免于刑罚。如《后汉书·孙程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载安帝延光四年(125),“有司奏(中黄门王)康、(中黄门苗)光欺诈主上,诏书勿问”[1]2517。另如,“(桓帝)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中常侍曹)腾,益州刺史种皓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皓奏。”[1]2519
东汉中后期,部分犯罪宦官的刑罚执行比较滞后。例如,“(长乐太仆蔡)伦初受窦后讽旨,诬告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1]2524《后汉书·孙程传》亦载:顺帝时期,“(中黄门)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1]2518
三、结语
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主要包括财产刑、贬夺官爵、迁徙刑、死刑与连坐五大类型,司法机关主要依据罪行轻重实施相应刑罚。东汉宦官犯罪轻则处以经济刑或贬夺官爵,重则施以迁徙刑、死刑或连坐,甚至多种刑罚并用。东汉政府虽以严酷刑罚惩治宦官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有效遏制宦官犯罪。
东汉宦官因犯罪、连坐或被诬告而处以刑罚者比较普遍并沦为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对当时的政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映了汉律的严酷、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趋于激化。东汉宦官犯罪的刑罚呈现差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刑罚类型多样化与刑罚实施复杂化两个方面。东汉宦官享有有罪先请与免于刑戮的特权,不仅体现了皇帝对司法权控制的加强,而且反映了政府对特权阶层的法律优待。东汉皇帝、权臣对宦官犯罪的刑罚的执行影响甚大,宦官被诬受刑、有罪减免刑罚与刑罚执行滞后的案例比较常见。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王雪静.两汉时期“下狱死”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S1):1-5.
[8]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朱伟东]
Brief Account of Penalty for Eunuchs’ Crim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HI Bin-bin
(CollegeofHistor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
Criminal penalties for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five major types: property-related penalty, penalty by degrading or stripping off the official ranking and titular honors, banishment punishment, death penalty and joint liability penalty. Corresponding penalties would be impo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verity of eunuchs’ crimes by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s. The eunuch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ere subjected to penalties ranging from fine penalty, degrading or stripping off the official ranking and titular honors, banishment punishment, death penalty and joint liability penalty. Though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with these harsh penalties, the eunuchs’ crimes were not effectively curb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t was common that eunuchs were punished because of crimes, joint reliabilities or false accusations, as a power struggle,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lso reflected an intensify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aw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severity of the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ruling groups. The eunuchs’ criminal penalties took on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istics, mainly featured b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riminal typ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penalty implementatio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unuchs; crimes; penalty; types; characteristics
K234.2
A
1001-0300(2016)03-0010-07
2016-01-21
师彬彬,男,河北邢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