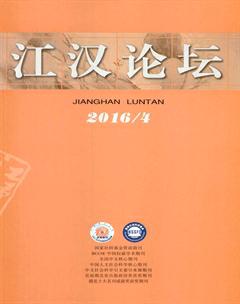出土文物与汉乐府《秋胡行》古辞考
柳卓娅 陈文华
摘要:汉乐府《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六曲中的第六曲,古辞已失。汉代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以及汉代画像石“秋胡戏妻”画像等一系列文物的出土使我们考察《秋胡行》古辞的本来面目成为可能。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编号为13号的木牍上记载的书目《列女傅》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其中“鲁秋洁妇”故事,应是《秋胡行》演唱的记录。古辞《秋胡行》的歌辞考察对汉乐府歌辞留存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出土文物;汉乐府;《秋胡行》古辞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94-05
《秋胡行》属汉乐府相和歌清调六曲中的第六曲。古辞早已流失,歌曲内容、唱词及如何演唱均不得而知。近些年学术界对此有所关注,但是没有实质的突破性进展。众所周知,《秋胡行》本事即秋胡戏妻故事以诗歌、小说、戏曲的形式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并传唱不衰,研究其本源,对于我们把握《秋胡行》古曲的源流和表演形式以及全面认识古代音乐和文学的本原状态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结合汉代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和汉代画像石“秋胡戏妻”画像等一系列出土文物对相和歌《秋胡行》的歌词和表演形式作一还原式的研究。
一、汉代画像石与《秋胡行》所涉内容
《秋胡行》之所以取名“秋胡行”,应该是与秋胡之事有关。汉代流传的秋胡故事,《乐府诗集》引《西京杂记》和《列女传》有关记述,尤其是《列女传》卷5《节义传》中的《鲁秋洁妇》对故事有详细记载。大意是鲁秋胡婚后五天就离家谋官,五年后回乡,在路上调戏一采桑女子被断然拒绝,回到家发现此女子竟是自己的妻子,其妻愤而自杀。故事结尾处的“君子曰”、“颂曰”对秋胡妻的评论可以代表时人的观念和评价,秋胡之事的流传也正是因为秋胡妻的贞烈行为,《秋胡行》歌曲的流传也是如此。《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日:“后人哀而赋之,为《秋胡行》。”
《秋胡行》歌曲演唱的内容与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画像石“秋胡戏妻”图像应该是一致的,对此汉代画像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
首先,汉乐府其他故事题材歌曲歌辞与当时流传的故事、画像石相关图像都是基本吻合的。如“季札挂剑”故事,口传、演唱和画像三者内容完全吻合。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刘向《新序》:“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已死……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这就是汉乐府《徐人歌》,歌辞为:“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而“季札挂剑”也是贤士类画像石的典型题材。画面一般会突出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并跪拜的情景。这正应和了歌曲对季札的歌唱。类似的还有“二桃杀三士”题材和“周公辅成王”题材,也是故事、歌曲、画像基本一致。近年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中,与《秋胡行》有关的“秋胡戏妻”图是常见题材,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秋胡戏妻》图,左侧站一男子,背着行囊,身体前倾,榜题为“鲁秋胡”,右侧桑树下站一位榜题为“秋胡妻”的女子。正在摘下桑叶放进树边的竹篮。身后的男子面相显露调戏之意,女子手把桑条,回头训斥,一副不可侵犯的姿态。图像人物姿态与流传的“秋胡戏妻”故事大致吻合。《秋胡行》的歌曲应该也是因为秋胡妻的悲壮故事而创作,从而流传更广更久远,汉代画像石也善于从这类故事中取材。也有学者研究故事画像时认为古代也有按画面讲诵故事,画面和故事内容是吻合的。由此,“秋胡戏妻”故事的讲唱和图画流传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口头讲唱传播和图像传播两种传播方式是互相照应并互相促进的。
其次。画像石所画往往是与传播内容密切相关的题材,而且往往是情节最高潮的部分。除山东省嘉祥县汉武梁祠堂画像石“秋胡妻”图外,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四川彭山县崖墓画像石棺、四川新津县汉代画像石棺等也发现了汉画“秋胡戏妻”图像,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了“秋胡妻桑园严辞拒绝秋胡”这一场景。这些图即使分布地区不同,但是同一故事的画面内容却如出一辙,都截取了关键性场景。画像石选取秋胡妻厉言拒绝一幕情节进行描绘,可见当时人对故事流传的重点取向,同时这应该也是《秋胡行》歌曲所要重点演唱的内容。这一点在后代拟作的《秋胡行》中得到了证明。后代拟作的《秋胡行》咏本事的诗作也是赞颂鲁秋胡妻的主题,最典型的是与汉代时间相隔不远的晋代傅玄的《秋胡行》,对鲁秋胡妻的美丽端庄、甘守寂寞、勤劳持家、高洁贞烈给予了高度赞扬。如果《秋胡行》的本辞不是以赞颂鲁秋胡妻为主,那么后世的拟作也不可能在主题上如此高度一致。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秋胡戏妻”画像石在整个墓葬中的位置。作为丧葬之用的画像石在应用时是分类刻画和放置,“秋胡戏妻”画像石往往是和古代贤士贞女画放在一起,这也突出了时人对于“秋胡戏妻”故事的价值取向,即“秋胡戏妻”画像石所画“秋胡妻”正是《鲁秋洁妇》中的“秋胡妻”。
二、《神乌傅(赋)》系列文物出土与《秋胡行》的渊源考察
关于《列女传》的编撰过程,在《汉书》卷36《楚元王传》所附《刘向传》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这段话提示我们刘向所编之书多属于收集、整理而成,所谓“序次为《列女传》”。对此也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书实际是刘向利用校书工作便于接触大量古籍条件进行编撰而成的。那么既然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那么在其编撰之前,应该有成型的列女故事包括“秋胡故事”的文本在流传了。
“秋胡戏妻”故事早在汉初,甚至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传,这一点已经被出土文物所证明。1993年出土了著名的《神乌傅(赋)》的江苏东海尹湾汉墓中,编号为13号的木牍上记载随葬物品清单,正面标题是《君兄缯方缇中物疏》,除记刀、笔、管等文具外,还记载了一些书目,有《记》、《六甲阴阳书》、《恩泽诏书》、《楚相内史对》、《乌傅》、《列女傅》、《弟子职》等,《乌傅》即《神乌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列女傅》,虽然只有书名没有原文出土,但是对照原件影印本,《列女傅》的“傅”字与“神乌傅”的“傅”写法是一样的。“傅”通“赋”,“列女傅”即“列女赋”。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能够确定《神乌赋》就是汉代专门用来讲故事的一类赋,也被称为俗赋。以此类推,《列女傅》也应该是汉代专门讲列女故事的一本赋集。据尹湾汉墓所出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等标有纪年的简牍大致判断,该墓下葬时间为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代。而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撰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也就是说《列女傅》的成书时间和刘向编辑《列女传》的时间大致相当,甚至要早于《列女传》的成书时间。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编辑《列女传》时不可能忽视《列女傅》的存在,《列女傅》(《列女赋》)应该是刘向编撰《列女传》的重要取材之一。有学者就曾进行过大胆推测,认为“尹湾简犊中的《列女傅》虽不是刘向《列女传》的全书,但应当是其中可以韵诵的部分故事”。
三、汉代说唱俑的出土与《秋胡行》文本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四川汉墓陆续出土一批说唱俑,其形貌、说唱时的动作、表情形象生动,而且还持有辅助表演的敲击乐器。随葬俑中会出现说书俑,说明说话、讲故事已经成为汉代百戏表演的重要项目。说唱者在叙事抒情时,为了更好地刻画形象,传达感情,自然而然地与歌唱或朗诵结合起来,发展成连说带唱的形式。这种形式,比纯粹的散说或通篇歌诵要自由灵活,更适合细腻的描写和抒情,更受到听众的欢迎。有学者研究赋的“不歌而诵”时指出所谓“歌”和“诵”实际本来只有一步之别,诵的抑扬顿挫、高低清浊与歌的洪细圆转、悠扬的旋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七略》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歌诗五类,其中前三类为书面语的文人赋,后两类一为口诵体(杂赋)、一为歌唱体(歌诗);而“口诵体”(杂赋)十二家的最后有“成相杂辞”,“成相杂辞”许多学者都认为是“唱”而非“诵”,那么它可以作为从“诵”到“歌”的过渡环节。各种娱乐方式中,“唱”“诵”交错,更是常见的现象。自西汉设立乐府以来,许多本是用于讲诵的谣谚也被合诸管弦,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说书俑常常自己持有乐器,如鼓和鼓棰,正是因为讲故事的过程中有说有唱。“这种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秦汉时代可能就叫做赋,也就是今天成为民间赋的作品。”同时这也提示我们。那就是汉代说书、讲故事的语言是讲究韵律节奏的,体现在故事底本的文体上,就应该是韵散结合的,而我们现在所见的故事赋,其文体特征恰好就是韵散结合的。由此,汉代故事赋(或者叫俗赋)的存在正是为说唱表演服务的,它就像一出由一人饰演所有角色的剧本,其戏剧性和表演性是非常显著的,尤其大量存在的戏剧性对白以及丰富的人物动作和表情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韵散结合的赋在口头传播时是讲唱结合的,《列女傅(赋)》在传播中也应该是有说有唱的,那么刘向将其选择编入《列女传》时,应该是既有说辞的记录。也有歌辞的记录。即使有所变动,也难免会保存着赋体讲诵的痕迹。其中具有韵文特点的人物对话。有可能就是当时用来演唱的唱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与《秋胡行》有关的《鲁秋洁妇》一文的确是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而且全篇在体制上虽以散文为主。但其中又夹杂了“力田,不如逢丰年”、“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等一些韵语和对偶句。这些应该就是当时的唱词或唱词的改编,而这些唱词的曲名,很可能就是《秋胡行》。
四、《秋胡行》演唱形式推断
一幅画像能在墓葬画像石中被广泛使用,可以推测出这些故事在当时的传播盛况和人们对其所承载思想的高度认可。在交通、通讯、媒体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一个故事如此广泛的传播和接受仅依靠大众口头讲述和有限的书面传播是如何做到的呢?《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由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成了历来对汉乐府歌曲的经典评价,即乐府歌曲的作者是有感于事而心生哀乐,因此作歌以抒情。如《秋胡行》歌曲就是为秋胡妻的悲壮故事所感动、感慨而创作,即《乐府诗集》所谓“后人哀而赋之,为《秋胡行》”。有学者曾研究指出乐府诗歌的接受和传播带有鲜明的“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传播学意义,本源性故事与乐府诗文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生发的关系,而且因为有故事,所以乐府作品得以广泛传播,反过来,也是因为被写进乐府作品,故事也得以更广泛地流传。这的确很有道理,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讲。基于汉乐府本身的演唱性,与其说汉乐府是“文事相依”,不如说是“曲事相依”。汉代的乐府作为歌曲艺术,因为有故事,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兴趣,从而使歌曲喜闻乐听,流传得更广、更久远;反过来,这些蕴含着人们哀乐感情的故事被付诸乐府歌曲之后,更是拥有了极为迅速的传播方式。在今天的山东、河南等地,还有很多“秋胡庙”、“秋胡墓”等一系列有关秋胡妻的古迹,可知这个故事的确深入人心。刘向的《列女传》共记述了一百多名妇女的事迹,也只有“秋胡戏妻”故事存在歌曲演唱并流传久远。而且这个故事在后世传播过程中“曲事相依”的特点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敦煌《秋胡变文》、元代石君宝的北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明清戏曲《秋胡戏妻》等故事的表演,直到今天这个故事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虽然书面和口头的讲述也在这个故事的传播和流传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得归于歌曲用于演唱的形式和功能。
汉代人是很喜欢看歌舞表演的。汉代傅毅《舞赋序》说:“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古代文献中很多记录表明汉代已存在歌舞小剧的表演。阴法鲁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的说唱文艺很可能是从汉乐府开始的。任半塘通过对汉代典籍所记载的歌舞活动进行分析后指出:“西汉已早有女伎之歌舞戏”,“汉晋间之运用歌舞,既已超出普通歌舞之程限,而人于化装作优之一步,则女娲、洪崖、嫦娥、东海黄公等,安知其不亦演故事,有情节?”杨公骥先生对汉代巾舞歌诗《公莫舞》进行破解,认为那是一出“母子离别舞”,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类简单的情景小戏在当时确实已经具备了表演的条件,存在表演的可能。
画像石资料显示,“伴唱”、“扦歌”、“稽戏”等艺术形式已经融入巾舞艺术表演之中,并在东汉时期的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域存在、流行,也就是说巾舞表演之中已经融入了歌唱和动作表演,表演者之间有了互动,这就为汉代乐府的角色表演提供了可能,“歌诗叙事”和“角色叙事”等情节化的艺术表现得到了加强。这种“新的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歌舞戏”主要的技术条件,“歌舞戏”乃至多场次的“歌舞剧”于东汉中晚期出现,应该是水到渠成。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中曾指出“乐府歌辞本多系歌舞剧”,《秋胡行》也应是一出“歌舞剧”。
首先,汉乐府相和歌演唱和伴奏特点暗示了表演结构的存在。《秋胡行》属于清调曲,《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记载“其器有笙、笛、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歌弦四弦。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晋、宋、齐,止四器也。”从这些规范的乐器使用和表演套路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歌曲表演程式性是很强的,也可见这种表演形式的成熟程度,《秋胡行》在演出时,也必然要遵循这种演出的程式化要求。赵敏俐认为汉代歌诗不再是简单的抒情艺术,而是表演艺术,比较复杂的相和曲调,已经适合于表演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同时,为了取悦观众,这一诉诸于表演的故事,就必须要有一定的情节,要适合表演,要有戏剧化的特征。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把这类诗篇称之为表演唱。是介于短篇叙事诗和折子戏脚本之类的歌唱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歌诗体裁。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综合了音乐、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成为有着独特韵味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而且汉乐府有几个相对独立的表演体系,所谓相和三调、大曲等。每种调式所用的乐器都有固定的要求,其中大曲在乐曲中还要再加上“艳”、“趋”、“乱”等名目。“解”在汉乐府歌辞中除了有章节的意义和音乐舞蹈的意义外,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近似于古代戏剧的“场”与“折”的提示作用。这些文本记录的乐曲和程式特点,也说明乐府表演不是一种简单的歌曲演唱,而是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的表演。从汉人的欣赏习惯来看,他们看重的并不是乐府歌诗中所表现的故事内容,而是对歌舞音乐的欣赏和情感的抒发,叙事在这里只占次要地位。
其次,《秋胡行》的故事、角色符合歌舞表演特点。从适合表演、戏剧化特征方面来看,《陌上桑》是最典型的,其中三解分别写了“罗敷之美”、“史君与罗敷对话”、“罗敷夸夫”,然后整个乐曲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秋胡行》的演唱与《陌上桑》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秋胡行》故事的发生地“桑林”,在中国古代乐曲文化中也具有特殊意义。“桑间濮上之行”代指男女幽会,简称“桑濮”。于是在桑林发生了很多男女故事并被编成戏剧上演,如汉乐府《陌上桑》,实际上《秋胡行》与《陌上桑》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骆玉明很早就曾撰文指出汉乐府《陌上桑》与“秋胡戏妻”故事关涉的问题不少,首先一点就是它们有非常相似的基本结构:场所(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美貌的采桑女)、主要情节(路过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秋胡妻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以悲剧结束;《陌上桑》中采桑女则有一个做官的好丈夫,并以自己的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陌上桑》故事实际是“秋胡戏妻”故事的变形,它把秋胡这个人物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这一种改变使故事的趣味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古辞《秋胡行》考察对汉乐府歌辞留存研究的启示
《秋胡行》歌辞的考察给我们研究汉乐府歌词的留存以很大的启示。如今文体分类比较具体甚至严格,但在汉代文体概念尚不甚明晰,很多今天划到文学范围的汉代作品,在汉代被流传和记录时。被不同的编著者和传播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取用,或记录,或改编,经、史、子、集各类作品中都可能会有保存。
无独有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河东蒲反歌诗》原诗很早就已亡佚,所以几乎从来没有人尝试对其歌辞的内容进行考察。但当代学者钱志熙在阅读王充《论衡·道虚篇》时却意外发现其中完整地记载着此诗的本事,甚至可以说就是歌辞的原始文本的记录,内容以河东人项曼都自述升天故事为主。《论衡》之外,东晋葛洪的《抱朴子·祛惑篇》也记载有项曼都故事,情节与王充所记基本上一样,只是文字稍有不同。相和歌曲的基本体制为说唱,文体常用杂言,并且时用对白,韵散结合,《论衡》及《抱朴子》所载的曼都自述正是杂言体,而且都是句式相对整齐。并有节奏与押韵。而王、葛两人的记载,表面看是一个杂文故事。实际是一首杂言歌诗。汉代方仙道流行,求仙风气浓厚,社会上流行着许多神仙传说。歌曲作者,也会采用此类神仙传说入歌。此歌虽经过王充、葛洪转述,但其歌辞的文本形式,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歌曲原状。但因为这首歌辞长期隐藏在《论衡·道虚篇》与《抱朴子·祛惑篇》中,“治子书与治集部者学问悬隔”,一直被作为一个纯粹的散文叙述作品来看待,一直没有学者发现《论衡》中所说“河东蒲坂项曼都事”,实际就是汉乐府的《河东蒲反歌诗》。
《秋胡行》歌辞与《河东蒲反歌诗》极其类似,虽然《乐府诗集》没有收集,但是《列女传》对“鲁秋洁妇”的记录明显带有“杂言”、“对白”、“韵散结合”的特点,而这恰是相和歌歌辞的基本形式。虽然乐府合乐演奏和歌曲流传的过程中对具体细节可能会有改动和变化,导致一首歌曲的歌辞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其基本内容不会有太大出入,即“鲁秋洁妇”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就是《秋胡行》的歌辞。
《秋胡行》采用一人主唱,其他人伴唱的演出形式,主唱的一人需要模仿秋胡及其妻子二人的角色和对话,取得戏剧性的表演效果,主要突出“夫妻新婚分离”、“秋胡戏妻”、“胡妻投水”等主要情节。这种表演是一种故事歌舞娱乐和贞烈行为赞颂的结合。学术界也有学者研究提出从傅玄的拟作《秋胡行》至敦煌出土的《秋胡变文》,数百年间秋胡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始终没有中断。从目前来看,这种秋胡故事说唱的传统早从汉代《秋胡行》古辞之时就已经开始,而且在内容和演唱形式方面对后世作品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