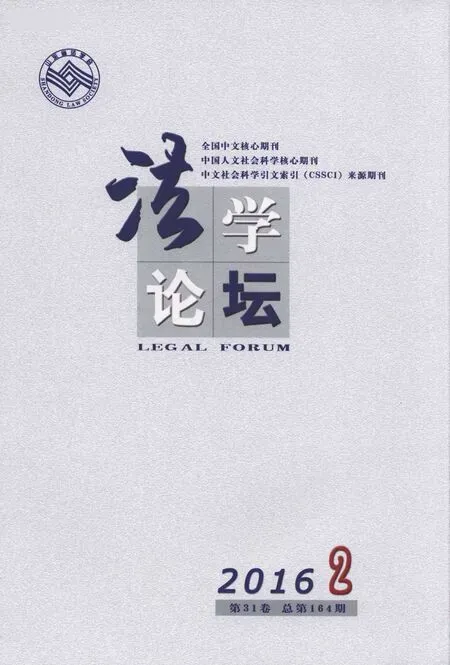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
上官丕亮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
上官丕亮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摘要:宪法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这种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我国现行体制并不相悖,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探索,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实施之门,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键词:宪法实施;法律适用;依宪释法;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
除了违宪审查之外,我国宪法还可以而且应当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即广大司法者和行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依据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来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的方式得以实施。*关于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方式、特点及意义,详见上官丕亮:《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在此,本文拟就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可行性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正当性论证: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在理论上能否证成?
在许多学者的眼里,“宪法实施就等于违宪审查”,而目前我国广大的法律实务工作者更没有形成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方式实施宪法的意识。显然,论述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的正当性并不是多余的。笔者认为,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实施宪法,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完全具有正当性。
(一)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首先应当解释法律。“如果法律要适用在具体的个案里,它就需要解释”。*[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从案例出发,法律工作者必须首先研究有关的法律规范。接着,他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确定该规范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德]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第三版),罗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正如一位法官所指出的:“法律不经解释即无法适用”,“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原则性和抽象性的规定,在审判中需要与具体案件进行对号入座的解释。因此,解释法律是法律适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孔祥俊:《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可以说,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必经环节。
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条款规定明确时就不需要进行解释,而只有在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或者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有歧义时,才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这似乎很有道理,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法律条款规定得很明确具体,但每个人对它的理解却往往是不同的,所以法律适用者不得不对它作出更具体更明确特别是能让当事人明白的解释。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卡尔·拉伦茨教授在其经典之作《法学方法论》中早就指出:“假使以为,只有在法律文字特别‘模糊’、‘不明确’或‘相互矛盾’时,才需要解释,那就是一种误解,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需要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最后应借助尽可能精确的措词来排除的——“缺陷”,只有法律、法院的判决、决议或契约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号语言来表达,解释就始终必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86页。
还有很多学者强调,普通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只有权“理解”,而无权“解释”。然而,实际上“理解”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8页。而马克思早在1842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强调:“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可以说,理解就是解释,对法律的理解就是对法律的解释,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近些年来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法律解释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比如,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强调:“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8月9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指出:“检察法律文书说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自身的执法行为和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事由进行分析论证、解释说明的活动”、“必要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对条文的含义、法条适用进行解释和说明。”在很大程度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具体办案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解释法律的过程。
另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律解释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比较解释、社会学解释、合宪解释等多种方法,合宪解释(笔者称之为“依宪解释”)只是一项冲突规则,它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中处于最后的序位,只是在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获得多种解释之后出现歧义时才被采用,即在多种解释中选择最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比如,有学者强调:“合宪性解释在各种狭义解释方法中应该处于最后的序位,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合宪性解释。”*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笔者以为,法律是根据宪法而制定的,为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法律适用者在适用法律而解释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时理应回到宪法,依照宪法来解释,至少要确保自己对所要适用的法律的解释不与宪法相抵触,显然“依宪解释”不仅应该是一项冲突规则,在法律解释产生歧义情形时,由法律适用者依据宪法来选择最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并且它应当是一项在法律解释的各个阶段交叉出现并始终都要考虑的“一以贯之的解释原则”、“普遍使用的法律认知原则”。*上官丕亮:《宪法实施的三大误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总之,只要有法律适用,就有法律解释,也就应有依宪解释,依宪解释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全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具体应用依宪解释方法的“依宪释法”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是法律适用的自然要求,完全具有正当性。
(二)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
源于英国的高级法观念,传播到美洲殖民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写入了美国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依照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及经合众国授权已经缔结或将来缔结之条约,均为本国之最高法;且不论任何州宪法或法律内容对之有何抵触,各州法官均受其约束。”正如美国著名宪法史学家爱德华·S·考文所指出的:“在美洲殖民地纷纷建立之时,与柯克和洛克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高级法学说在英国的影响已达到了高潮……传播到美洲殖民地。”“在美国的成文宪法中,高级法最终获得这样一种形式……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从而进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这是从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法学上最富有成果的时代。”*[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5、93页。自从美国以宪法文本确立宪法的高级法地位以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成文宪法,并纷纷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宪法至上的高级法地位,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一切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无效。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宪法明文规定了宪法的最高地位。*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5条第3款更是明确强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在位阶上宪法规范高于其他法规范,因此,抵触宪法原则之一般的法律规范将归于无效。”*[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7页。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撤销违宪的法律规范。无疑,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至上权威的重要保障。然而,保障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至上权威,仅依靠违宪审查制度还是不够的。
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规范难免出现违宪的情形,需要违宪审查机制来纠正。同样地,即使本身并不违宪的法律规范,也不等于在适用过程中不会走样、不会背离宪法,因为法律规范不能自动适用,在适用时首先需要法律适用者去解释它,在解释的过程中就难免出现忽视宪法甚至胡乱解释、歪曲解释并有违宪法的情形。可见,为保障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必须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解释法律时考量宪法,依照宪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精神来解释法律。“所有的法规所形成的法秩序应该有其一贯性,并服膺宪法之规定及理念,因此一个法律必须由宪法的基本理念来检讨及补充。”*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再说,宪法是法律制定的基础乃至直接的依据,法律依据宪法而制定,在制定法律时考虑了宪法的至上权威,相应地在适用法律时也理应考虑宪法的至上权威,依据宪法来解释法律。*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德国有学者将本文所主张的“依宪解释”称之为“基于宪法的解释”。所谓“基于宪法的解释”,是指在对能被做出解释的、拥有被解释空间的规范——如对民法典第26条——进行解释和适用的时候,要注意宪法中的基础性决定,“要注意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2句对于所适用的劳动法规定及其基本原则的影响”。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显然,依宪释法是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
二、合法性问题: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与现行体制是否相悖?
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依据宪法来解释法律,无疑这首先需要承认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均享有法律解释权。然而,众所周知,“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这是我国《宪法》在第67条中明确规定的。《立法法》更是作出了明文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条第1款) 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依宪释法要求广大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在办案适用法律时享有法律解释权,这是否与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
(一)依宪释法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
本来,只有适用法律才需要解释法律。然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我国的法律解释在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立法性的法律解释,一般简称为“立法解释”,是指立法者在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时对法律作出的解释;另一种是应用性的法律解释,通常又称“应用解释”或“具体应用解释”,是指法律适用者在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对具体应用的法律作出的解释。*参见上官丕亮:《论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法律解释”,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法律解释,它仅是指立法解释。*参见上官丕亮:《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2000年3月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等。立法解释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了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保证法律的正确执行,立法法草案规定,以下两种情况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一是,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可以说,《立法法》表面上主要是重复了宪法的规定,但在事实上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规定作了解读,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法律解释的性质和范围。“立法法所明确的法律解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定程序对法律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性质上属于立法解释,不包括对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关于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解释,不属于立法法调整的范畴,立法法对此没有规定。”*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然而,依宪释法所要求广大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进行的法律解释,仅仅是一种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解释。显然,这与宪法和《立法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的规定并不冲突。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广大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有权对法律进行应用解释。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关于“具体应用解释”是这样规定的:“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而且,《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只是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的确,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并没有明确规定广大普通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有权对法律进行应用性解释。但是,我国现有关于法律解释的各种规定也并没有明确排斥广大普通的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进行应用性法律解释。特别是,在长期以来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事实上就是在对法律进行应用性解释,本文指出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只不过是承认业已存在的事实而已。而且,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开始为官方所承认。除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强调“在裁判案件中解释法律规范,是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外,早在2003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就在一次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重要环节,对法律解释方法不能运用自如,就无法恰如其分地适用好法律规定。要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况,妥善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以准确实现立法的意图和法律规范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再说,承认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即“谁适用,谁解释”,这并不是否定司法系统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以及行政系统内国务院和主管部门的应用性法律解释权,*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在实践中我国大量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并不是在具体应用法律时所作的解释,而是在没有具体对象和具体案件时作出的一种抽象的解释。这种抽象的解释实际上同立法和立法解释很难区别。而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虽然可以对法律具体应用的问题进行解释,但实际上国务院及各部门较少作法律解释。国务院及各部门认为需要对法律条文的界限作进一步明确的,往往采用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办法,而不采用解释的办法,因为行政法规和规章比解释具有更强的权威和约束力。参见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5页。更不是要否定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高法律解释权。*参见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在适用法律时由自己对法律作出应用性解释,必要时也可分别报请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乃至国务院、上级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上级检察院乃至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如果上级部门发现下级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所作出的应用性法律解释违反有关规定,可以依法予以改变或撤销。而且,如果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时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发现所要作出的解释会超出应用性解释的范围,而属于《立法法》所规定的需要作出立法解释之情形,就不能直接作出解释,而应当依照《立法法》第45条和第46条之规定,逐级上报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性解释。同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中发现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时对法律所作的应用性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更是有权依照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2条和第33条之规定予以纠正,当然还包括作出立法性解释。由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执法者和司法者对应用性法律解释权的滥用。
(二)依宪释法与我国现行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冲突
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核心是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然而,“并不仅仅是该需要用宪法标准加以衡量的法律本身的含义是不确定的。事实上,该宪法标准本身的含义也是不确定的,是可以解释,也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也就是说,宪法规定本身也存在一个解释空间,允许对其作不同的解释和具体化。”*[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换言之,依宪释法不仅需要解释法律,而且需要解释宪法。
执法者和司法者只有在法律适用时在先对宪法相关条款进行解释并获得宪法相关条款的准确含义和精神之后,才能正式依照这些宪法条款的含义和精神对所要适用的法律条款进行解释。*参见上官丕亮:《宪法实施的三大误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依宪释法的法律解释性质,还应看到依宪释法与宪法解释的联系。*参见上官丕亮:《什么是合宪解释》,载《法律方法》2009年第9卷。法律适用中的依宪释法活动,本身属于法律解释的活动,但在解释中离不开宪法解释,甚至首先不得不解释宪法。正如德国公法教授Christian Starck先生所指出的:“所谓合宪解释(verfasungskonforme Auslegung)者,并非在解释宪法,而是解释法律。不过由于以宪法为取向的法律解释,其前提在于解释宪法,于此观点之下,合宪解释亦属宪法解释所要探讨问题的课题。”*[德]Christian Starck:《宪法解释》,李建良译,载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10页。为此,我们可以说,依宪释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宪法解释的过程,宪法解释是依宪释法的重要方面和步骤,由此“依宪释法”在实际上也成为开展宪法解释的一个重要领域。
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不得不予以回答,那就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等法律适用者在依宪释法时不得不先解释宪法,这需要承认行政执法者和司法者有权开展宪法解释,那么这是否与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相冲突?本文的回答同样是不冲突。
与前面所述的法律适用者享有应用性法律解释权的道理相同,我们同样可以这样理解:广大执法者和司法者对宪法进行的解释只能是具体的、事后的、面向个案的应用性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作出的解释是抽象的、事前的、面向一般的立宪解释*郑州大学苗连营教授曾撰文认为,宪法解释的核心功能在于宪法的适用,宪法解释只有与宪法适用联系在一起、只有与具体的个案联系在一起,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而我国宪法所明确列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只能理解为是一种与宪法的具体适用相分离的普遍性的、抽象性的解释,而不是具体的个案性解释,与宪法的适用无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远离于法的适用过程之外,它所创制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规范性文件,还是以解释名义出现的决定、决议,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而只能在适用过程中进一步成为法的适用者的解释对象。苗连营:《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同时也是最高解释*正如已故的蔡定剑先生所指出的:“不能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理解为其他机关都不能对宪法进行解释,它只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宪法文本中的‘解释’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解释有所不同;法院无权作出《宪法》第67条意义上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法院不能在通常意义上适用与解释法律。法院既然可以适用和解释法律,为何不能同样适用和解释宪法?”“《宪法》第67条并没有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只是赋予其宪法解释的最高效力,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国家机构的宪法解释”。*张千帆:《我国法院是否可以释宪》,载《法学》2009年第4期。显然,我们承认执法者和司法者等法律适用者有权解释宪法,并不会违反我国宪法的规定,反而可使执法者和司法者的应用性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宪性、最高性解释相互补充。可以说,依宪释法中的宪法解释是我国现行宪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更加完善,并且在当下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依宪释法有宪法依据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的最后一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依宪释法,即在适用法律时依据宪法来解释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由此可见,依宪释法在我国是有宪法依据的,可以说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理应包括作为国家机关的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它们的工作人员即具体办案的执法者和司法者个人“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适用法律时积极主动地开展依宪释法活动,依据宪法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来解释法律,进而间接地适用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三、可行性探究: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在当下中国行得通吗?
(一)国外有经验可借鉴
众所周知,德国有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和实践。在著名的1958年“吕特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强调:“基本法并无意成为价值中立的体系(秩序),也已在它的基本权利章中建立起一套客观的价值秩序,且对基本权利的效力做了原则性的强化。这种以人格及人性尊严能在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作中心点的价值体系必须视为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适用各法律领域,立法、行政、司法均由此获得了方针与动力。自然地,它也会影响民事法律,没有任何的民事法规可以抵触它,每一规定均须依照它的精神来解释。”*参见黄启祯译:《关于“吕特事件”之判决——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第七辑第一九八页以下》,载《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一),司法周刊杂志社1995年版,第106-108页。而后在其他案件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它多次强调基本权利作为一种客观的、在各个法律领域中都有效的价值判断的特性,并由此推导出一个结果,即任何民法规范都不允许同基本权的价值体系间发生冲突,它们都须按照这一价值体系的精神被解释。”*[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4页。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吕特案”确立的基本权利在私人关系中“间接适用”的理论在欧洲许多国家以及非洲的南非、亚洲的日本等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非和瑞士两国更是将基本权利在私人关系中的效力问题明确规定在宪法中。1996年《南非共和国宪法》第8条第1、2款规定:“基本权利在所有的法律中适用,对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机关都有约束力。”“根据基本权利的性质和附加在基本权利上的义务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适用时,基本权利条款对自然人和法人有约束力。”1999年《瑞士联邦宪法》第35条规定:“一、基本权利必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实现。二、所有国家机关受基本权利的约束,并有义务促进基本权利的实现。三、国家机关应当确保基本权利在适当的情况下适用于私人关系中。”
虽然德国等国承认宪法在私法领域内具有效力,但同时明确指出,宪法性权利在民事纠纷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像它在公民对国家行为的公法纠纷中那样直接援用宪法权利条款宣告公法原则无效。在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中,采取的是所谓“间接适用”(indirect effect)的观点,认为宪法性权利只限于对私法原则产生一定“影响”(influence)而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宪法“洋溢”(flows)的智慧或“放射”(radiates)出的那些思想光芒将照耀着私法体系并且影响着对私法规则的解释,由此私法规则应当在相应的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加以解释适用,但归根结蒂最终适用的还是私法规则。*参见[美]Peter E. Quint:《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德、美两国比较》,余履雪译,蔡定剑校,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这种主张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所谓基本权利第三人间接效力的方式间接适用宪法的做法,强调“私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宪法应当影响私法的解释”*Jeffrey Goldsworthy, Interpreting Co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85.,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依宪释法”活动。显然,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方式开展宪法实施,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等国的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其应用范围比较窄,它只应用于民事诉讼之中,仅仅主张依照宪法去解释私法,且只强调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作用。而本文所主张的“依宪释法”的应用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它应用于所有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之中,它强调依照宪法去解释所有的法律,且强调的是所有的宪法条款(不限于基本权利条款)对普通法律的解释作用。就拿其中所应用的司法领域来说,“依宪释法”不仅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诉讼领域。正如我国台湾地区一位学者所言:“人权第三人效力的操作则有赖于民事法官,至于法律的合宪解释又是所有法官在审判中都可以运用的解释方法。”*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二)在我国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已有相关探索
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实施宪法,在我国已有相关实践,法律适用者特别是法官们在我国的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审判实践中已经开展了积极的有益探索。这些实践,既表明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是法律适用的客观需要,也告诉我们:在当下中国的法律适用中,宪法实施是可行的。
例如,在1988年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中,针对沈涯夫、牟春霖要求保护新闻记者合法权益的上诉理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新闻记者和所有公民一样,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时候,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上诉人沈涯夫、牟春霖无视狄振智患有精神病的客观事实,拒不接受有关组织、群众、同事和上级领导机关的忠告和规劝,故意捏造和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了杜融的人格和名誉,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沈涯夫、牟春霖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参见《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8年第2期。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显然,在此刑事案件的审判中适用法律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援引了我国宪法第35条、第38条、第51条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禁止侮辱诽谤以及不得滥用权利的规定乃至原文来解释刑法上的“诽谤罪”规定,认定上诉人沈涯夫、牟春霖的行为不属于新闻报道自由,仍构成诽谤罪。
又如,在2007年肖传国诉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方是民(方舟子)名誉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人民中级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亦为法律所保护,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亦不受法律追究。对于公众人物公开进行否定性评价,属于正当的批评及争鸣范畴。无论批评或争鸣的观点是否成立,即是否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均不构成对批评或争鸣的相对人的名誉权的侵害。就批评或争鸣文章使用的言辞而言,过激的言辞,一般也是可以允许的。”据此,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肖传国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原告肖传国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言论自由为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利,公民行使该权利不得以侮辱、诽谤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方是民在访谈中对于肖传国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肖氏反射弧’理论的价值做出了负面评价”,“在发表评论时使用了诸如‘夸大’、‘冒充’、‘自吹自擂’等带有贬义性的词汇,但应当认为,质疑与否定本为评论自由的题中之义,肖传国虽因此感到自身名誉感降低,但上述评论尚未超出观点争鸣的范畴,并不构成对肖传国名誉权的侵害。”“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使其评论有所失当,只要其主观上不存在恶意,亦不应承担名誉侵权之法律责任。”“其评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虚构事实,侮辱、诽谤他人之恶意,即使其所依据的网络资料和据此发表的评论有不够准确之处,亦不应构成名誉侵权。”*参见“肖传国与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1146号民事判决书。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显然,在该民事诉讼案的审判中,一、二审法院均是依照《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及其精神,来解释《民法通则》第101条关于“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的规定,认定方是民(方舟子)对肖传国的负面评论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不构成“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再如,在1999年王红军不服阆中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案中,当时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马信云代表其家人参加乡人大代表选举未得到选票,马信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主持选举大会的人员要自己的选票是合法的。虽言辞过激,但并不是无理取闹,且没有影响选举工作的进行,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参见“王红军不服阆中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中法行终字第136号行政判决书。据此,改判撤销阆中市公安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的规定对马信云拘留10日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在该案中,法院事实上是依照《宪法》第34条关于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来解释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关于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规定,认定马信云的行为属于维护自己选举权的行为,而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有必要指出的是,2001年引发广泛讨论并颇有争议的山东“齐玉苓案”,因二审法院在这起普通的民事诉讼中不是通过本文所主张的“依宪释法”的方式在裁判说理部分间接适用宪法,而是直接依据《宪法》第46条进行判决,与我国现行体制不太相符,故受到质疑,后来在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以“已停止适用”为由废止了2001年专门为该案所发布的批复。*参见2008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齐玉苓案”的后续结局告诉我们: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间接适用宪法,才是当下中国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的切实可行之正道,才是当下中国的宪法适用之门、宪法实施的重要之门!
四、结语:积极主动走进“依宪释法”的宪法实施之门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它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是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对法律及宪法作出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性解释,但这与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和法律的抽象的、最高的立性性解释权并不冲突,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而且在法律适用中实施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明确要求。同时,德国基本权利第三人间接效力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而且在国内这些年来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的法律适用实践中我国各级法院的法官们已经开展了相关探索,产生了一些“依宪释法”的宪法实施案例,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开展宪法实施在当下中国完全具有可行性。现在需要努力做好的工作就是,广大司法者和行政执法者积极主动地走进“依宪释法”这扇宪法适用之门(亦即宪法实施之门),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在广泛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全面适用宪法,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责任编辑:王德福]
收稿日期:2016-02-24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研究》(10BFX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系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作者简介:上官丕亮(1967-),男,江西赣县人,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2-0014-08
Subject:Justifiability, Legitimacy and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uthor & unit:SHANGGUAN Piliang
(Kenneth Wang Law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Abstract: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by “interpret law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the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 It does not contradict to our current system, have legitimacy, and in practice has been related to exploration, complete with feasibility in present china. A pressing matter of the moment is to walk through the door, to apply constit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cross-the-board, and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pplication of law; Interpret law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justifiability; legitimacy; fea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