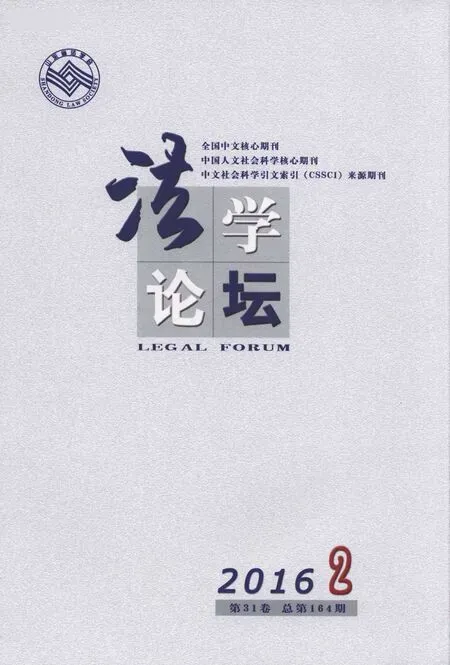环保法庭的困境与出路
——以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为视角
张式军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热点聚焦】
环保法庭的困境与出路
——以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为视角
张式军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近年来,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纠纷,各地法院纷纷成立专门环境资源审判组织,探索环境审判新机制。然而,环保法庭自设立以来,一直面临“无案可审”的尴尬境地,其中受案范围过窄且缺乏统一性规范是导致这一症结的重要原因,受案范围问题关系到专门环境审判机构的生命力,因此应当加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统一规范并合理拓宽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在界定我国环保法庭受案范围时可以考虑包含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因环境损害引起的私权诉讼案件、环境刑事诉讼案件、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关键词:环保法庭; 受案范围; 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公益诉讼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形势日趋严重,由此产生的环境纠纷和环境群体性事件也与日剧增,以“预期更好地启动司法力量解决现实中严峻环境问题”*刘超:《反思环保法庭的制度逻辑》,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为目的的环保法庭*本文所称的环境法庭是各种环境保护法庭、生态法庭与环境资源法庭的总称。应运而生。2007 年 11 月,我国第一个环保法庭——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成立。随后,各地环保法庭相继设立。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正式宣布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 年 7 月,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合计150个。*参见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7/id/1339942.shtml,2015年3月15日访问。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所说:“环境法庭的设立是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通过环境司法的专门化来提高环境司法能力建设的一大举措。”然而,被寄予厚望的环保法庭自成立以来,与预期中的理想效果相差甚远,多地法庭均遭遇了无案可审、“等米下锅”的尴尬,以 2013年的办案情况为例,有14 个省区市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的年度结案量为零。*参见丁国锋、马超:《多地环保法庭“无米下锅”》,载《工人日报》2014年10月25日。只有找到阻碍环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症结并“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案少”这一环保法庭面临的窘境,充分发挥环保法庭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明确并拓宽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对于环保法庭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意义重大。
一、问题——处于探索中的环保法庭
(一)受案标准各不相同
目前,各地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各不相同。以影响力较大的贵阳、无锡、昆明的环保法庭为例,贵阳、无锡环保法庭采用“四审合一”(民事、刑事、行政、执行)模式,昆明环保法庭则采用“三审合一”(民事、刑事、行政)模式。江苏的环保法庭受案范围全面覆盖环境与资源领域,将原来分散于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的案件集中于环保法庭,统一受理;环境行政诉讼方面,受案范围较为广泛,将环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强制措施、不作为、非诉执行案件以及环境信息公开案件一并纳入受案范围。云南法院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案件,但是,与江苏法院不同的是,云南法院将涉及资源类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排除在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之外。
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江苏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仅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云南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不仅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前两个法院相比,贵州环保法庭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更加细致也更具可操作性,其受案范围不仅包含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包含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甚至以司法审查的形式保障公民对政府涉及生态文明的重大决策的参与权与监督权。*参见丁国锋、马超:《环保法庭陷“少米下锅”尴尬》,载《法制日报》2014年9月24日。
同时,程序规则地方化趋势明显。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大多以各地的规范性文件确立,这些规范性文件多是地方政府规章或者上级法院的内部文件,效力层级不高。例如,无锡市环保法庭成立后,通过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涉环保类案件管辖若干意见》和与无锡市检察院会签的《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锡检会[2008]2号)等文件,明确地列举了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贵阳环保法庭通过《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的实施方案》和《贵阳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案件受理范围的规定》规定环保“两庭”负责审理涉及“两湖一库”水资源保护及因涉及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保护而产生的一、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相关执行案件。*参见黄莎:《我国环境法庭司法实践的困境及出路》,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6期。在国家制定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性规范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环境公害诉讼司法实践缺乏规范依据的困境,具有为国家立法提供参考的价值”*杨武松:《尝试抑或突破:我国环境公害诉讼司法实践实证分析》,载《河北法学》2013年第4期。,然而各地不同的立案标准带来了实践中的困境,即具有相同诉讼资格的主体,在不同的法院和不同的地区提起诉讼却面临不同的处理结果,这显然有损环境司法的公信力。
(二)受案范围过于狭窄
环保法庭受案范围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受案范围过窄。受传统环境侵权理论的影响,无论是“三审合一”还是“四审合一”模式, 在确定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时,仍然偏重于环境污染方面的刑事、行政案件以及环境侵权赔偿案件,生态破坏与自然资源纠纷类案件相对较少涉及;设置受案范围时具体思维仍然停留在传统三大部门的思维路径中,环境法思维和理论吸收较少;环保法庭设立与运作至今,受理的案件多为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和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诉讼案件,相比之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较少,部分法庭甚至出现“零公益诉讼”的尴尬境地。此外,对于是否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仍然存在分歧。*同①。受案范围狭窄且缺乏统一性规范,使得现实生活中一些新型的环境纠纷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予以解决,这显然有违环保法庭“构建一种长效机制以处理频繁涌现的多种多样的环境纠纷”*黄莎、李广兵:《环保法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的初衷。
二、质疑——环保法庭受案范围局限性的成因分析
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和单一性导致大量的环境资源纠纷不能被纳入诉讼机制予以解决,其背后既有环保法庭的“天生性”缺陷,也有外部的影响因素。
(一)内生性约束——环保法庭设立基础薄弱
各地环保法庭自成立以来,就因为“无法律的明确授权”而受到广泛质疑。实践中,多数地区环保法庭的设立都是借助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推波助澜”。2007年11月,作为贵阳市300余万人主要引用水源的“两湖一库”(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的水质恶化,引用水安全面临危机,这直接促成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的成立,从提上议事日程到正式设立环保法庭,仅仅历时68天。太湖被认为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三个湖泊之一,江苏的两个环保法庭都设在太湖附近,2007年5月太湖蓝藻事件引发的“水生态危机” 登上了世界各地新闻的头版头条,也直接催生了无锡的环保法庭。云南昆明和玉溪环保法庭则是在阳宗海重大砷污染事故的风口浪尖上成立的,后来拟推广建立环保法庭的重点区域9大高原湖泊中,就有6个是已经被污染的区域。*参见高洁:《环境公益诉讼与环保法庭的生命力——中国环保法庭的发展与未来》,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9日。可以说,大多数环保法庭的设置均带有明显的危机应对色彩,是在“穷尽其他救济路径依然效果不佳、苦思无计、难有出路的窘境下,呼应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的现实需求而进行的司法制度创新”,*刘超:《环境侵权救济诉求下的环保法庭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8页。被学者们称为“应景而生”的环保法庭也就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内生性困境”。*刘超:《反思环保法庭的制度逻辑——以贵阳市环保审判庭和清镇市环保法庭为考察对象》,载《法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近年来,许多学者基于“能动司法”理论对环保法庭设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做了诸多探讨,有学者认为“能动司法的本质是回应型法律,即法律应作为一种回应各种社会需求和愿望的便利工具;能动司法是架接环境法庭与法律正当性的桥梁”。*参见孟春阳: 《环境法庭的正当性分析——以能动司法为视角》,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在性质和设立原因上与环保法庭类似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税务法庭等早已突破了现有法律的规定;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作为否定环保法庭存在正当性的理由确实比较牵强”。*参见杨帆、李建国:《对我国设立环保法庭的几点法律思考》,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未来,随着相关法律的修改与司法解释的出台,环保法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终会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环保法庭设置之初均属于“回应性”的司法措施,既缺乏坚实的法理支持,也没有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及相应制度的支撑,多数环保法庭的设立难免沦为“应景之作”,甚至成为有些地方政府和法院变相宣扬政绩的工具。这种伴随着环保法庭发展起来的“天生性”缺陷正是造成多地环保法庭受案范围局限性和单一性的重要原因。*参见魏佳等:《环保法庭设立的困境与出路——以司法专门化设计为视角》,载《学术论坛》2014年第5期。
(二)制度性缺陷——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过少
作为环保法庭生命力的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近些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和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均对环境公益诉讼作了规定,然而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并未被立法所吸收,以上两法关于原告资格的确立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关键的适格原告、程序制度等问题依然付之阙如,很难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原告的主体资格等进一步作出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对与公益诉讼组织起诉资格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第二条: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社会组织。第三条: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第四条: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第条: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前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无违法记录”。使得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以及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抽象规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然而“解释”对于哪些“法律规定的机关”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并没有实质性的放开;公民个人的诉讼资格依然没有得到承认。*参见颜运秋、余彦:《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最高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征求意见稿〉评析》,载《法治研究》2015年第1期。现行法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限定范围依然过窄,从而导致了许多公益诉讼案件因“起诉人不具备原告资格”被阻挡在司法审查的大门之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无法得以充分发挥。
(三 )现实掣肘——环保法庭的无序增长
从2007年11月我国第一个地方环境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成立,到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近7年的时间里,全国已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300余个,其中福建省基层人民法院的环境审判庭达40个,江苏省基层人民法院的环境保护合议庭有29个,*参见张宝:《中国环境保护审判组织概览 》,http://ahlawyers.fyfz.cn/b/172083,2015年4月12日访问。环保法庭数量急剧增长之势下,环境案件的实际受案量却屈指可数,以 2013年的办案情况为例,河北 11 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一年环境案件结案总量为 24 件,江苏省 5 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一年共结案 5 件,浙江 2 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一年结案 3 件,有 14 个省区市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2013 年度结案量甚至为零。*参见卢越:《多地环保法庭“无米下锅”》,载《工人日报》2014年10月25日。由于案源不足,“许多环保法庭逐渐异化为非专业性的审判机构”,*宋宗宇、陈丹:《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机制障碍与路向转换》,载《重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部分环保法庭只得承办一些与环境纠纷无关联的民事、刑事类案件。
环境纠纷与日俱增,环保法庭却门庭冷落。环保法庭的出现充满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其“更大的功效不在于审理环境纠纷,更多地在于宣示有了专门的环境纠纷的审理机构,”*丁岩林:《超前抑或滞后:环保法庭的现实困境及应对》,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第 3期。成为地方法院提高自身权威的一种方式。然而,超出实际审判需要的跟风式设立带来的是长期无案可审的尴尬处境,进而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环保法庭的不合理设置不仅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有违司法的效率原则。
实践中还常常出现环保法庭与其他审判庭争夺案源的事例,多数法院的刑庭和行政庭不愿放权,民庭负责的资源、海洋等环境案件,也不愿意移交给环保法庭,这就使得新成立的环保法庭管辖的案件范围过窄,这也是环保法庭案源过少的原因之一。*参见孙佑海:《对当前环境资源审判若干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7日。
三、规划——我国环保法庭的未来之路
现实中环保法庭“遍地开花”与“门可罗雀”的落差告诉我们,仅仅设置专门的环保法庭并不能解决司法在处理环境侵权纠纷中所处的困境,关键是“环保法庭所适用的机制要有助于现实中的环境侵权纠纷能依法转换成环境侵权案件”。*刘超:《擎制与突围: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动力机制的缺陷与重塑》,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6期。
(一)统一并拓宽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过窄且缺乏统一性规范标准是造成多地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重要原因,因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大受案范围,让更多的环保纠纷通过司法的途径加以解决,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环保法庭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
1.统一受案标准。环保法庭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产物,“其设立不应是简单的组织机构的创设,而应是在环境司法法治化的进程中建立‘有名有实’的环保法庭,适用同样的程序和法律规则”。*鄢奥:《我国环保法庭存在的正当性及合法性研究——以清镇环保法庭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39页。目前,各地标准不一的受案范围既带来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也不利于环境司法公信力的维护。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明确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笔者建议,针对目前各地环保法庭受案范围的混乱状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尽快出台类似的规定对环保法庭的审级、管辖、受案范围等方面设立具体统一的标准。
2. 拓宽受案范围。“凡是违反了环境法律规范的( 行为) 都应纳入到环境审判制度体系内”,*杨帆、李建国:《对我国设立环保法庭的几点法律思考》,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这是改变当前环境司法困境的关键突破点。传统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将环境侵权行为定位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依据侵权责任的违法性构成要件,行为人只对损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四要件”说认为,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因素,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在我国侵权相关法律规定中,环境侵权行为即为“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此种思维模式下,包括生态破坏在内的诸多环境侵害行为均难以进入环保法庭的司法救济范围,结果也必然难以尽如人意。
法院是“维护环境法治、环境法律权威和环境公平正义的基本的、有效的、最终的保障”。*蔡守秋:《论加强环境法庭的建设》,载《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卷上),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环境案件本身又具有侵害对象不特定、因果关系复杂、科学技术性强等特征,只有将这些专业性的环境纠纷放在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里审判,才能最大程度地整合有限的司法资源,在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取得“案结事了”的效果。因此,未来在确定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时,应当突破传统环境侵权理论的局限性,不再拘泥于该行为是否符合行为违法性的要求,重点考察该行为是否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益,是否造成了现实的生态环境损害与破坏,将受案范围从环境污染拓宽至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从环境污染防治拓宽至生态保护防治。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建议,在确定环保法庭的具体受案范围时,可以考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以诉讼的内容与形式划分,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可以考虑包括以下案件:(1)因环境损害引起的各类民事诉讼与执行案件;(2)因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3)针对环保行政机关具体环境行政行为(包括环境行政许可、处罚、强制措施、不作为、信息公开等)提起的各类行政诉讼案件;(4)环境行政非诉执行案件;(5)对有关环境规划与环境保护等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6)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第二,以环境纠纷的类型划分,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1)环境污染案件,除了传统“四害”造成的“四污”案件*“四害”是指废水、废气、废渣、噪声;“四污”案件是指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和土壤污染。外,还应当纳入放射性、核辐射、电磁辐射、化学品等污染物所造成的各种污染案件;(2)自然资源保护案件,这类案件具体包括:水资源纠纷、土地资源纠纷、矿产资源纠纷、能源纠纷、森林纠纷、草原纠纷、海事纠纷、渔业资源纠纷 、大气资源(包括气象资源)纠纷 、旅游资源纠纷等;(3)生态破坏型环境侵害案件,具体包括:破坏森林生态、草原生态、土地生态 、河流湖泊生态、湿地生态的纠纷案件,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包括土地沙化 、荒漠化、沙漠化等)的案件,破坏生物多样性(包括野生动植物、水生动植物、珍贵稀有野生动植物等)的案件,破坏自然人文遗迹(包括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的案件。*参见蔡守秋:《论加强环境法庭的建设》,载《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卷上),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8页;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
(二)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拓宽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不断完善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的同时,积极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与发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环境行政行为违法,且有可能造成或已经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特定环境行政行为无效或相关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特定行政职责的诉讼形式”。*曹和平、尚永昕:《西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载《人民论坛》2010年第29期。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益诉讼并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新近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依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在西方国家,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逐步拓宽原告资格已成为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美国,如果环保行政机构举措不当,或对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及时采取制止或者制裁措施的,公民或民间团体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Steven Ferry, Environmental law: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 Inc, 2003, p105.2006年,德国通过《环境法律救济法》扩大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该法规定任何违反环境法律的行政决定或行政不作为均可成为诉讼对象,尤其是对于工业设施、垃圾焚烧设施,或者能源生产设施的建立等行为。*参见陶建国:《德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
我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市国土资源管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2009 年 7 月 8 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向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律师函,建议清镇市国土资源局在收到律师函10日内收回李万先在百花湖风景区内享有的 80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或其他附属物,并消除该建筑对百花湖风景区环境造成的潜在危害。同年7月27日,因该局仍未履行职责,中华环保联合会以清镇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收回土地使用权法定职责为由,向贵州省清镇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清镇市国土资源局收回与李万先签订的土地合同中出让的4号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附属建筑,庭审中,原告以被告已作出收回第三人土地使用权为由提出撤诉申请,法院经审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破冰之旅”,该案件督促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履行了拖延近 15 年的行政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初步显现。*参见高洁:《环境公益诉讼与环保法庭的生命力》,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29日。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负有监管和保障之责,公益诉讼的产生,与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密切相关。环境问题背后往往涉及作为环境监管机关的环保部门的行政失职。因此应当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为契机,积极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与发展,以实现不同领域环境公益的救济。
(三)扩大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资格
在当下的司法语境下,理想的环境法治图景是,“通过广泛设置环保法庭来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以加大诉讼途径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的范围和力度”。*刘超:《环保法庭在突破环境侵权诉讼困局中的挣扎与困境》,载《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因而环境公益诉讼是环保法庭的生命力所在,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是“环保法庭实现本旨意义的必然出路”。*鄢奥:《我国环保法庭存在的正当性及合法性研究——以清镇环保法庭为例》,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20页。实践中,各地为支持环保法庭的发展均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于2010 年10月25 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危害环境,给社会公共环境利益造成危害的,人民检察院、环保机构、环保社团组织有权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参见云南法院网: http://www.gy.yn.gov.cn/Article/xwgj/xwgc/201011/20926.html. 2015年4月28日访问。2015年颁布的《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也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有了适当放宽。
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适当扩大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主体资格。明确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同时将尽可能多的社会组织纳入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范围之中,充分发挥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积极作用;至于公民个人的诉讼资格,尽管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将公民个人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之内的成熟条件,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总比问题本身多”,*杨帆、李建国:《对我国设立环保法庭的几点法律思考——实践、质疑、反思与展望》,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1期。“滥用诉权”的现实担忧不能成为我们一味怀疑和否定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起诉权的理由,权利滥用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约束,不可因噎废食。随着环境权及环境诉权理论的不断完善,通过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制度,辅之必要的起诉条件和诉讼程序,在不远的将来,赋予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也未尝不可。只有建立多元化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体系,才能使环境公益诉讼成为“改进自身生存环境质量,保障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刘超:《擎制与突围:法院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动力机制的缺陷与重塑》,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6期。
(四)合理有序设置环保法庭
2010年6月最高院发布《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状况各不相一,因而环保法庭的设立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按需设立,没有必要在各个行政辖区内都设立环保法庭,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及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外,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院在设立环保法庭之前,应当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需求等进行充分的前期调研和专题论证,看其有无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见李新亮:《环保法庭设立应遵循什么原则?》,载《中国环境报》2014年10月8日。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应当对全国环保法庭的设立和运行状况进行充分把握,明确环保法庭的设立标准和审批程序,以实现资源与效率的合理配置。
(五)培育专业化的审判队伍
环境法庭的案件范围再多再宽,如果审理案件的法官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也可能会将告到门的环境案件拒之门外或束之高阁。环境案件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科学性强的特征,一旦法官面临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往往缺乏处理相关纠纷的动力。与此同时,环境案件的审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环境纠纷解决,而是通过环境案件的审理过程向公众宣传与倡导一种环境法治理念,正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等法院资深法官Paul L.Stein 所说:“法庭所做出的决定对环境和受该决定影响的社会来说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影响”。*Paul L. Stein, Major Issues Confronting the Judiciary in the Adjudication of Cases in the Areas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转引自王曦:《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为了应对此问题,应当加强对环境法庭法官的专业培训,通过专题培训、讲座、进修等方式对环保法庭的法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案件审理技能;同时,设立环境保护审判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吸收环境科学等专业人士参与环境诉讼的审判。国外的环保法庭也昭示了这一经验,比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环境法院就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 1名高级委员,8名专职委员和16名兼职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必须符合《土地和环境法院法案》(1979)第12条第2款所列举的资格要求,同时要参加法院每年定期举办的专业研讨会,委员的专业特长对于土地和环境法院案件的合理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Brian J Preston, Operating an Environment Court: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and 12 benefits of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2008) 25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Law Journal 385, pp.6-7.专家委员应是多领域的,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环境科学、环境评估、自然资源管理、城市规划、土地评估等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人员*参见刘超:《环境侵权救济诉求下的环保法庭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以及环境法方面的专业律师。只有建设一批具有先进环境法律理念、环境科学知识和良好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技能的复合型法官队伍,才能真正实现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化审判。
四、结语
环保法庭设立至今,一直毁誉并存。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产物,环保法庭在解决环境纠纷,加强环境执法,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受目前司法制度本身局限性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环保法庭的纠纷解决实效却并不如理想预期。加强环境法庭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明确和拓宽环境法庭的受案范围,只有明确和拓宽环境法庭的受案范围,让更多的环境纠纷得以通过司法程序有效解决,才能凸显环境法庭的功能。然而,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尴尬局面可能并不会单纯地因为受案范围的扩大就获得可喜的改观,其背后还需要一系列的内在法理更新和配套制度建设,这也在提醒我们,只要真正运用法治思维,环保法庭就不会无案可审。
[责任编辑:吴岩]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司法保障机制研究》(2014ZDA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式军(1966-),男,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2-0052-07
Subject:Ques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Courts——Based on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Author & unit:ZHANG Shijun
(Law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 problems and disputes, the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courts have sprouted up across the country. All these environmental courts are beneficial explorations of new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tribunal. However, since the environmental courts were established, they have been faced with the problem “lack of case sources”.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at are the narrow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and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s.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is great vitality of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courts. Therefor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should be issued to regulate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 specialized environmental courts s. 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should includ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s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s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Private Right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Non-litigation Cas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court;the scope of accepting cases;spec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tribunal;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