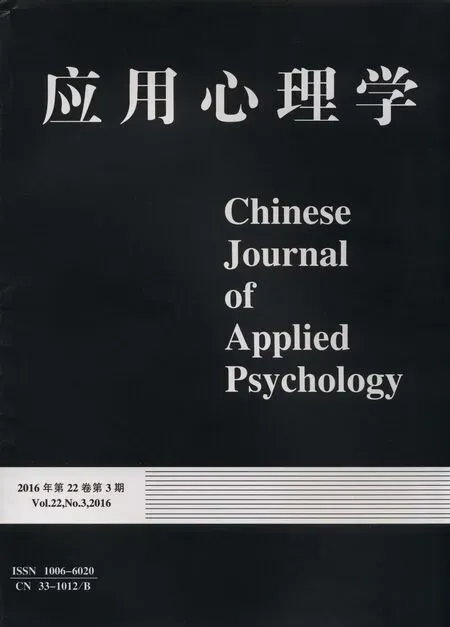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李梦迪 牛玉柏**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浙江 杭州 310018)
本研究探讨小学儿童亲社会想法和积极情绪在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影响中的作用。对杭州市两所小学二、四和六年级共270名学生进行实验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与暴力和中性游戏相比,亲社会电子游戏能显著降低小学儿童的攻击行为,且男生比女生更易受亲社会游戏影响,表现出更少攻击行为;亲社会想法在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积极情绪在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中不起作用。
亲社会游戏 攻击行为 一般学习模型 短时效应 小学儿童
1 前 言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电子产品已成为成年人,甚至是儿童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是指一切以电子化方式进行的娱乐行为(刘彪,陈卫东,2012),是电子产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分。
根据一般学习模型(General Learning Model,GLM)(Buckley,Anderson,2006),任何媒体刺激都会通过个体的学习机制对个体产生短时效应和长时效应。短时效应假设:个体的人格特征与游戏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内部状态(认知、情感和唤醒状态),而且三者可以互相影响。长时效应假设,如果个体不断接触游戏,那么游戏会对个体的认知、态度和情绪特点产生影响,随着玩游戏时间的增加,最终会改变个体的人格,而人格又成为短时模型中的个人变量。暴力性游戏增强玩家的攻击性相关认知、情绪和行为倾向,而亲社会视频游戏则可提高玩家的亲社会相关认知、情绪和行为倾向(Greitemeyer,Osswald,2009;陈朝阳,王晨雪,翟昶明,张锋,2012)。研究者通过故事脚本和词干补笔任务发现短时接触亲社会电子游戏能够降低大学生的攻击认知,研究还发现了攻击情感和攻击认知在接触的游戏类型与攻击行为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通过反应时任务和自陈问卷发现,短时接触亲社会电子游戏能够显著提高个体亲社会想法(Greitemeyer,Osswald,2011;Whitaker,Bushman,2012)。另外,对亲社会电子游戏与积极情绪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能够显著提高其积极情绪(Saleem,2012)。
研究者通过七巧板实验发现,相较于中性游戏和暴力游戏组的儿童,玩亲社会游戏的儿童攻击行为减少,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Saleem,Anderson,& Gentile,2012)。之后,研究者发现,在控制了个体变量后,相较于玩暴力游戏的被试,玩亲社会游戏的被试通过认知和情感的调节作用更少出现攻击行为(Greitemeyer,Agthe,&Turner,2012)。但是该实验没有把认知和情感分别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独立出来,因而存在情感和认知作用的混淆。无独有偶,研究发现玩亲社会游戏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攻击认知和攻击情感为中介减少攻击行为,换言之,亲社会游戏还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缓解攻击行为(Greitemeyer,Maria,& Robin,2012)。在暴力媒体和攻击行为之间,规范信念起到中介作用(段东园,张学民,魏柳青,周义斌,刘畅,2014)。已有研究虽然探讨情感和认知在亲社会电子游戏和攻击行为间的作用,但是针对的对象是成年早期的大学生而不能推论到小学儿童,而且研究没有探讨情感和认知各自对攻击行为的作用。
研究发现媒体中所包含的暴力内容会对玩家攻击性产生影响,观看暴力电视、电影和玩暴力游戏都会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暴力媒体对攻击性的这种影响是不分年龄段和性别的(Anderson et al.,2010)。另一方面,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早期玩暴力游戏所带来的攻击行为会影响个体之后的躯体行为,个体更有可能出现攻击行为(Craig,Akira,Douglas,& Nobuko et al.,2008)。7到11岁的儿童在长期接触视频游戏和电视节目后言语攻击增加(Oana,Moli,&Scott,2014)。视频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表现为青少年玩视频游戏的时间和斗殴次数成正比(杨依卓,2010)。上述研究存在不一致,研究侧重于揭示短时接触暴力游戏内容会降低亲社会行为,并且通过增加攻击认知、攻击情感进而增加玩家的攻击行为(Anderson et al.,2010)。而有关亲社会电子游戏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数量甚少。另外,相比年长儿童,年幼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Allana,Jean-Philippe,Allison,Rachel,David,& Stuart,2013)。故本研究拟探讨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对不同年龄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另外,在性别上,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亲社会电子游戏的影响,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因为相比女生,男孩往往更频繁地玩电子游戏,而玩电子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和所偏爱的内容上存在性别差异(Lucas,Sherry,2004)。已有研究发现,没有玩游戏习惯的在校大学生在玩暴力游戏后,后测任务中男性增长的攻击性显著高于女性(Anderson &Carnagey,2009);相较于女性,男性更经常使用暴力媒体,具有更高的攻击行为规范信念,且倾向于出现攻击行为(段东园等,2014)。而针对儿童,已有研究发现男孩相比女生更频繁地玩视频游戏,更倾向于暴力游戏(Allana et al.,2013)。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2 方 法
2.1 被试
选取杭州市两所小学二、四、六年级儿童各90名,其中女生129名(二、四、六年级分别是44、44和41名),男生141名(二、四、六年级分别是46、46和49名),年龄范围8~13岁(二年级8.99±0.66岁,四年级10.46±0.54岁,六年级12.31±0.47岁)。
2.2 实验材料与测量工具
2.2.1 电子游戏
采用三个评级为E(适合每个人)的电子游戏:Chicks(亲社会游戏)的主要任务是赋予一群可爱的小鸡技能,它们相互合作,保护同伴顺利到达出口;Pinball Deluxe(中性游戏)是经典的弹球游戏;Weapon Chicken(暴力游戏)的任务是操作一只小鸡不断移动,向冲到小鸡身边的怪物射击,消灭所有敌人过关(Greitemeyer,Osswald,& Brauer,2010)。上述游戏不含画面过于血腥和残酷的暴力游戏,以避免对被试造成更深的负面影响。
2.2.2 喜爱程度及难度、性质评价问卷
被试对所玩的游戏在愉快、丰富有趣、快乐、吸引、喜爱等维度上进行评分(7点量表),分数越高代表被试越喜欢该游戏,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α=0.874(Adachi,Paul,& Willoughby,2011)。此外,被试还需对游戏所表现出的难度、亲社会和暴力程度方面进行评分(7点量表),分数越高表示难度、亲社会或暴力的程度越高,共3个项目(Anderson & Dill,2000)。
2.2.3 亲社会想法问卷
以往研究在被试观看不同内容的视频后写出自己看视频时正在思考的想法,发现观看暴力视频的被试有更多的暴力想法(Bushman & Green,1990;Anderson et al.,2000, 2004)。本研究采用类似的方法,要求被试在完成游戏后尽可能多地写下当时的想法,再由两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编码;评分者一致性信度达0.9。如“应该学习小鸡这种奉献精神”等被标记为亲社会想法;“小鸡要去哪里”等被标记为中性想法;“我想炸死这些小鸡”等被标记为暴力想法。计算每位儿童亲社会想法的数量。
2.2.4 积极情绪问卷
被试在玩游戏后对自己的平静、同情心、愉快、高兴和满怀希望5个维度共5题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评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积极情绪越强烈,问卷信度为α=0.73,共5道题目(Elizabeth,Thomas,Connlly,& Thomas,2011;Saleem,Anderson,& Gentile,2012)。
2.2.5 七巧板拼图任务
采用Gentile,Anderson和Yukawa(2009)、Saleem等(2012)使用的七巧板拼图任务测量儿童的攻击行为。该任务要求被试从三组拼图(简单、中等和困难的各10个)中选择11个让“同伴”(虚拟的)完成,并告知若“同伴”能在5分钟内完成10个拼图的话,“同伴”将会得到金钱奖励,同时也需要完成“同伴”给他们选择的11个七巧板题目,但是无论拼图成绩如何,都不会得到奖励。为控制不公平处理带来的影响,告诉被试实验目的是研究奖励与否是否影响被试拼七巧板的表现。攻击行为分数是被试给同伴挑选的困难题目数量减1。为控制顺序效应,测验中将难、中、易三种难度的题目在试卷上、中、下位置进行了平衡设计,每位被试随机抽取一份。该范式具备测量人际行为的潜在功能(Gentile et al., 2009)。Saleem等(2012)亦运用该任务范式测查被试的攻击行为,验证了其有效性。
2.3 实验程序
告知被试完成两个任务。在第一个任务中,被试首先熟悉被指定玩的游戏(亲社会、暴力或中性游戏),随后让他(她)单独玩游戏15分钟,接着填写积极情绪问卷和亲社会想法问卷(顺序随机安排)。在第二个任务中,要求被试为“同伴”(虚设的)选取七巧板题目,再填写游戏喜爱程度及难度、性质评价问卷,最后询问被试对电子游戏和选七巧板两个任务的联系,确认其未猜出实验意图后,由主试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
3 结 果
3.1 控制变量的检验
为确保实验所选游戏符合实验目的,将小学儿童对三类电子游戏的亲社会程度、暴力程度、喜爱程度、游戏难度四项指标的评价进行了调查,结果见表1。

表1 小学儿童对三类电子游戏各项指标的评价结果(M±SD)
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儿童对三类电子游戏亲社会程度的评价得分差异显著F(2,267)=43.63,p<0.001,η2=0.248;Bonferroni检验发现,亲社会游戏组得分显著高于中性游戏(p<0.001)和暴力游戏组(p<0.001)。儿童对三类电子游戏暴力程度的评价差异显著,F(2,267)=54.40,p<0.001,η2=0.292;Bonferroni检验发现,暴力游戏组得分显著高于亲社会游戏(p<0.001)和中性游戏组(p<0.001)。儿童对三类电子游戏的喜爱程度和难度评价得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可见,选取的三款游戏在小学儿童看来的确属于三种不同内容性质的游戏类型,即亲社会游戏更具亲社会性,暴力游戏更具暴力性,而中性游戏的性质介于两者之间。
3.2 短时接触不同类型电子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
小学儿童在三类电子游戏组中的攻击行为得分见表2。以游戏类型、年级和性别为自变量,儿童攻击行为得分为因变量,进行3×3×2的三因素完全随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游戏类型主效应显著F(2,252)=14.856,p<0.001,η2=0.105;事后检验发现,亲社会游戏组的攻击行为得分显著低于中性和暴力游戏组的得分(p<0.001)。游戏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2,252)=2.901,p=0.057,η2=0.023。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亲社会游戏组的性别差异显著F(1,252)=4.89,p<0.05,η2=0.023,即女生攻击行为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在三类游戏组中的攻击行为差异显著F(2,252)=15.31,p<0.01;男生在亲社会游戏组的得分显著低于中性和暴力游戏组(p<0.01),即亲社会游戏能显著减少男生的攻击行为。年级主效应和其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0.05)。

表2 三类电子游戏组中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表现(M±SD)
3.3 亲社会想法和积极情绪的多重中介效应
将游戏类型、亲社会想法、积极情绪和攻击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将年级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见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两两相关显著(p<0.01),满足进行中介检验的前提条件(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

表3 各变量相关矩阵(n=18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再以游戏类型(2种)为自变量,小学儿童的攻击行为为因变量,中介变量是亲社会想法及积极情绪,建立假设模型。由于自变量“游戏类型”为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前应将该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以亲社会游戏组为1,中性游戏组为2。同时将亲社会想法、积极情绪和攻击行为变量进行中性化处理,各步骤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通过回归分析表建立路径分析图,见图1。游戏类型对攻击行为的路径及效应分解见表5所示。
由表4和图1可知,游戏类型对小学生的攻击行为的影响有部分是通过亲社会想法(M2)起作用,亲社会想法的中介效应显著(p<0.01),即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可以通过亲社会想法的部分中介作用减少了小学儿童的攻击行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0.49/(2×0.49+1.056)=48.88%。但是小学生的积极情绪(M1)在游戏类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中介作用不显著(p>0.05),因而亲社会电子游戏并不能通过增加小学生的积极情绪而减少其攻击行为。

表4 回归分析结果(n=180)

图1 模型路径系数图
注:*p<0.05,**p<0.01,***p<0.001。

表5 游戏类型对攻击行为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4 讨 论
4.1 亲社会电子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短时效应
以往电子游戏的研究大部分侧重在暴力游戏对暴力行为的影响且被试都是进入成年期的个体,而较少对儿童时期进行探讨。而已有研究表明,长期接触视频游戏,攻击行为会在童年期显著增加,且在青春期到达一个高峰,然后趋于稳定或在成年期出现下降(Geoffrey,Luther,& Eloise,2013)。之后研究者又发现,7到11岁的儿童在长期接触视频游戏和电视节目后言语攻击增加(Oana et al.,2014)。而国内研究也发现,视频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表现为青少年玩视频游戏的时间和斗殴次数成正比(杨依卓,2010)。因而可以看出儿童期是电子游戏对儿童行为影响的关键期,故本研究以儿童为被试,并且探讨的是电子游戏对儿童的有利影响。
结果发现,玩亲社会游戏的小学儿童相较于玩中性和暴力游戏组有更少的攻击行为(p<0.01)。一般学习模型(GLM)认为电子游戏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种影响的性质取决于游戏内容的性质。该模型不仅可以解释暴力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而且也可以解释亲社会电子游戏的非暴力或教育性影响(Anderson,Bushman,2002)。这与Anderson(2009)和Greitemeyer(2012)等人的实验结果一致。
本研究未发现短时接触游戏后攻击行为的年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儿童在年幼时就已接触电子游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图式(Gentile,Lynch,& Linder,2004)。根据一般学习模型,电子游戏对个体行为产生短时效应是通过对个体认知图式的不断强化实现的。且已有的研究也发现媒体中所包含的暴力内容会对玩家攻击性产生影响,观看暴力电视、电影和玩暴力游戏都会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暴力媒体对攻击性的这种影响是不分年龄段的(Anderson et al.,2010)。
本研究发现短时接触游戏后攻击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攻击行为显著地高于男性(p<0.05)。本实验显示女性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儿童时期的男性玩家相较于女性玩家更经常玩暴力游戏,已经对暴力性场面发生脱敏化(Bushman & Anderson,2009)。男生玩亲社会游戏、中性游戏和暴力游戏后的攻击行为存在差异(p<0.01),即男生玩亲社会游戏相较于玩中性和暴力游戏有更少的攻击行为,而女生不存在差异(p>0.05)。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亲社会电子游戏的影响,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的原因:第一,相比女生,男孩往往更频繁地玩视频游戏,而玩电子游戏上花费的时间和所偏爱的内容上存在性别差异(Lucas & Sherry,2004)。本研究中的亲社会电子游戏中具备明显的亲社会性动作,例如前面的小鸡为后面的小鸡挖洞、搭建楼梯、指路等,丰富的活动更吸引儿童。第二,根据一般学习模型,电子游戏对个体行为产生短时效应是通过对个体认知图式的不断强化实现的。男生在玩电子游戏时主要采用的策略是不断重复玩游戏,在这个过程中其相关的认知图式得到了强化;相反,女生在玩游戏时擅长用观察的策略,观察游戏界面、游戏机制和解决方案(Elizabeth,Thomas,Connolly,& Thomas,2011)。此外,男生比女生具备更强的视觉加工能力,并且更容易受到动作类电子游戏的视觉促进作用(Hamlen,2011)。
4.2 积极情绪和亲社会想法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不仅从亲社会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的直接作用进行验证,而且从认知和情感两种途径进行间接作用的研究,丰富了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发现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通过提高小学儿童的亲社会想法,减少了他们的攻击行为(p<0.01)。最近的一项采用脑电波指标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个结果(Liu,Teng,Lan,Zhang,& Yao,2015)。因此,可以引导儿童更多地选择玩亲社会游戏,降低儿童的攻击行为。同时可以在玩家发出助人动作后给予其明显的强化,包括游戏内的分数、愉悦的声音、画面等刺激物(王莉,陈炳发,2009)。但过度沉迷于电脑游戏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以及学业成就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沈彩霞,刘儒德,张俊,王丹,2011)。
本研究未发现小学儿童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即亲社会游戏对小学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仅仅是通过亲社会想法即认知方面,而情感在其中不起作用。Greitemeyer等(2012)也发现,攻击认知在游戏类型和攻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非常显著,而攻击情感的中介作用仅存在于游戏类型与大学生的间接攻击之间,与直接攻击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而Saleem等(2012)发现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通过提高玩家的积极情绪,降低玩家的攻击行为。一方面可能因为选取的被试年龄段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采用测量积极情绪的方法不同,其他方式的测量,比如PANAS问卷等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再有,移情可以部分抑制或者减少攻击行为(Maibom,2012);移情通过影响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可以降低攻击行为(Eisenberg & Eggum,2010)。因此,儿童的移情水平在亲社会电子游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有待进一步探讨。
5 结 论
与暴力和中性游戏相比,短时亲社会电子游戏提高了小学儿童的亲社会想法,进而降低了他们的攻击行为;小学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受到亲社会游戏的影响,表现出更少的攻击行为。
陈朝阳,王晨雪,翟昶明,张锋.(2012).亲社会视频游戏对玩家助人行为的影响——基于一般学习模型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6):103-108.
段东园,张学民,魏柳青,周义斌,刘畅.(2014).暴力媒体接触程度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规范信念和移情的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185-192.
刘彪,陈卫东.(2012).电子游戏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9(2):79-83.
刘桂芹,刘衍玲,张大均.(2010).暴力视频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措施.教育探索,227:126-128.
沈彩霞,刘儒德,张俊,王丹.(2011).电脑游戏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应用心理学,17(3):222-231.
王莉,陈炳发.(2009).儿童产品界面的设计因素研究.人类工效学,15(4):58-6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36(5):614-620.
杨依卓.(2010).暴力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干预措施.山东青年,12,18-20.
张学民,李茂,宋艳等.(2009).暴力游戏中射杀动作和血腥成分对玩家和观看者攻击倾向的影响.心理学报,41(12):1228-1236.
Adachi,P.& Willoughby,T.(2011).The effect of video game competition and violence on aggressive behavior:Which characteristic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PsychologyofViolence,1(4):259-274.
此外,考虑到将旧东盟4国和新东盟4国进行分组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因为毕竟各国之间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也有可能存在异质性,为消除这样的干扰,笔者对每个国家分别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呈现在表9。通过表9可以看到,分国别检验的结果与前文分组别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除了缅甸的Mono1和Mono2的系数并不显著以外,其它各国的回归系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缅甸近年来战乱频发,而国家的内战对人口流动造成了无法测算的影响,因此导致回归结果无法观测到人口集聚对缅甸城市发展的影响。
Liu,Y.,Teng,Z.,Lan,H.,Zhang,X.,& Yao,D.(2015).Short-term effects of prosocial video games on aggression: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FrontiersinBehavioralNeuroscience,9:193.
Anderson,C.A.,& Dill,K.E.(2000).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thoughts,feelings,and behaviorin the laboratory and in lif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78:772-790.
Anderson,C.A.,& Bushman,B.J.(2002).Human aggression.AnnualReviewofPsychology,53:27- 51.
Anderson,C.A.,& Carnagey,N.L.(2009).Causal effects of violent sports video games on aggression:Is it competitiveness or violent content?Journalof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45(4):731-739.
Anderson,C.A.,Shibuya,A.,Ihori,N.,Swing,E.L.,Bushman,B.J.,Sakamoto,A.,et al.(2010).Violent video game effects on aggression,empathy,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A meta-analytic review.PsychologicalBulletin,13(2):151-173.
Anderson et al.(2008).Longitudinal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on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Pediatrics,112(5):1067-1072.
Boyle,E.,Connolly,T.M.& Hainey,T.(2011).The role of psychology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omputer games.EntertainmentComputing,2(2):69-74.
Eisenberg,N.,& Eggum,D.N.(2010).Empathy-relatedresponding:Associations with prosocial behavior,aggression,and intergroup relations.SocialIssuesandPolicyReview,4(1):142-180.
Gentile,D.A,Anderson,C.A.,et al.(2009).The effects of prosocial video games on prosocial behaviors: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correlational,longitudinal,and experimental studies.Societyfor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35(6):752-763.
Dunlap,E.(2013).Trends in video game play through childhood,adolescence,and emerging adulthood.PsychiatryJournal,2013(6):301460.
Greitemeyer,T.,Agthe,M.,Turner,R.,& Gschwendtner,C.(2012).Acting prosocially reduces retaliation:Effects of prosocial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EuropeanJournalofSocialPsychology,42(2):235- 242.
Greitemeyer,T.,& Osswald,S.(2009).Prosocial video games reduce aggressive cognitions.Journalof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45:869-900.
Greitemeyer,T.,Osswald,S.,& Brauer,M.(2010).Playing prosocial video games increases empathy and decreases schadenfreude.Emotion,6:796-802.
Greitemeyer,T.,& Osswald,S.(2011).Playing prosocial video games increases the accessibility of prosocial thoughts.JournalofSocialPsychology,15(2):121-128.
Hamlen,K.R.(2011).Children’s choices and strategies in video games.ComputersinHumanBehavior,27(1):532-539.
LeBlanc,A.G.et al.(2013).Active video games and health indicators in children and youth:A systematic review.Plos One,8(6):e65351.
Maibom,H.L.(2012).The many faces of empathy and their relationto prosocial action and aggression inhibition.CongnitiveScience,3:253-263.
Mitrofan,O.,Paul,M.,Weich,S.& Spencer,N.(2014).Agg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behavioural/emotional difficulties:Seeing aggression on television and video games.BMCPsychiatry,14(1):287.
Saleem,M.,Anderson,C.A.,& Gentile,D.A.(2012).Effects of prosocial,neutral,and violent video games on children’s helpful and hurtful behaviors.AggresiveBehavior,38:281-287.
Whitaker,J.L.,Bushman.B.J.(2012).“Remain Calm.Be Kind.”Effects of relaxing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and prosocial behavior.SocialPsychologicalandPersonalityScience,3:88-92.
The Influence of Short-time Prosocial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LI Meng-di NIU Yu-bai WEN Guang-hu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Zhejiang Science-Technology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discuss whether positive feeling and prosocial thoughts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ort-time prosocial 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bebaviors.A total of 270 students from second-grade,fourth-grade and sixth-grade in Hangzhou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nd experiments.Results showed that,on the one hand,prosocial video games could decreas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significantly,compared with neutral and violent video games,and on the other hand,boy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prosocial games that show less aggressive behaviorthan girls.Moreover,prosocial thoughts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social 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but positive feeling is ineffective.Therefore,short-time prosocial video games could enhance prosocial thoughts,and then decreas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prosocial video games,aggressive behaviors,general learning model,short-term effects,primary school children
B849
A
1006-6020(2016)-03-0218-09
*通信作者:牛玉柏,女,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e-mail:1056926355@qq.com。 温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