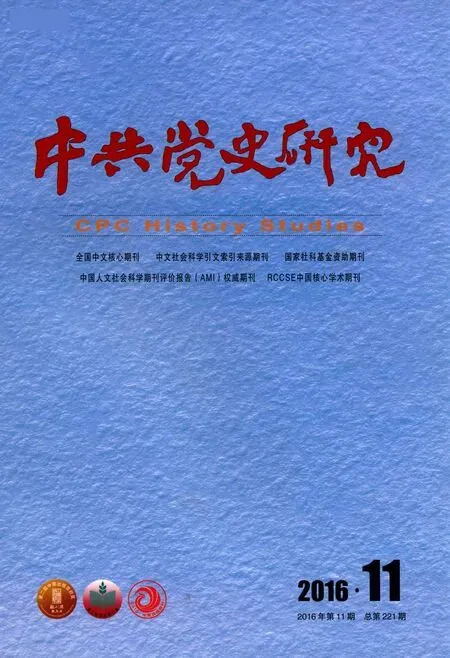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
葛 君
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
葛 君
新中国和民主德国遵循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共运的分工安排,在建交之后把加强贸易往来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在两国就1951年度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民主德国出于自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诉求,希望在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经贸活动中间充当唯一的代理人,中国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但由于西方的禁运政策,民主德国无法完成贸易协定中所应承担的义务,造成对华贸易欠账。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使得民主德国的供应形势更加困难,中国的特殊帮助再次加剧了对华贸易负债,直到1955年才最终实现贸易平衡。
中国;民主德国;贸易协定;德国问题;“东柏林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两个相继建立了新政权的国家,对于当时国际冷战格局之意义,堪比同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立以及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①Mark Kram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50 Years Later-A Review Article”, Europe-Asia Studies, Vol.51, No.6, 1999, p.1093.。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成立确实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力量对比。可是如果将观察的目光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具体探讨50年代的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外交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达成的具体合作和发展及其特点等问题,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都显得过于粗略笼统。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中国和民主德国的档案文献,更为细致地叙述两国在1950年至1955年间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在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一般特征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这是全世界和平的两个新的强大堡垒。”②《罗申大使演说词》,《人民日报》1949年11月8日。可在当时,这两个“堡垒”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足够紧密,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归因于斯大林对国际共运的内部分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领袖,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应该有某种分工,中国负责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工作,苏联则负责对西方的工作。在他看来,“欧洲的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欧洲……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言下之意显而易见:苏联的力量必须介入东欧各国,中国革命的经验将会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产生较大影响,而苏联发挥不了像中国那样的作用,就如同中国也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
斯大林的这个分工安排,直接影响了东欧各国与新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方式。东欧各国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反映在民主德国身上的一个实例是,当时民主德国政府决定任命柯尼希(König)出任首位驻华使团团长,这一任命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而在具体的外交操作过程中,民主德国外交部首先要将此决定告知苏联驻柏林的外交使团,由其向苏联外交部转递照会,由苏联代为向中国转告这个决定,随后需要再等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Roshchin)在北京向周恩来就此事进行交涉之后,才能最终获得来自中方的答复和同意*Übersetzung, 27.März 1950,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40, Bl.2;“Die ersten Jahre in Peking: Ein Gespräch mit Ingeborg König”, Joachim 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Erinner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Münster: Lit Verlag, 2002, S.19.即便柯尼希来到中国开始工作后,在一些对华关系的问题上,他还是会先去找罗申交换意见。参见Aktennotiz, 30.6.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35.。当时东欧各国都自觉遵守斯大林对国际共运所作的分工安排,同样新中国对于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间的绝对权威也给予了完全尊重,对于斯大林的分工建议也自觉遵令行事*一个十分明显的事例是,中共中央在组建对外联络部时,就明确其任务是“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但具体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东方各国兄弟党联络并帮助他们”,可见中共在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中是有偏向性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因此50年代初期,在新中国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初步交往过程中,大家首先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发展经贸关系这一方面。早在新中国尚未成立之时,东欧各国就已经开始筹划并安排自己的对华贸易工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2、216—217、253—254页。。当王稼祥被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同时还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负责与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时,那些急于同新中国开展贸易的东欧国家,就纷纷通过在莫斯科的代表找到他,以求取得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1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21页。。所以当1949年底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从王稼祥处了解到东欧国家的这些诉求之后,便立即要求国内作好与这些国家做生意的准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
民主德国自然也不甘人后,虽然建国时间相对较晚,但它也想尽快能与新中国发展贸易,并且在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上,民主德国政府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互通有无,从观察此后中德*本文凡提及“中德”这一概念时,皆指“中国与民主德国”,下同。两国就1951年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就可以发现,民主德国试图通过在对华贸易关系上可能占据的优势地位,以增加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一、1951年中德贸易协定的谈判、签订及其影响
当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有关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时,民主德国也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进行两国贸易协定的谈判。1950年1月2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求赴苏谈判的民主德国外贸部部长汉德克(Handke)要利用在苏联的机会同中国代表进行接触,为能够在6月初签订中德贸易协定进行事先协商,并同时向中方提出交换两国外交使团商务代表的要求,其中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外贸部要以能够代表中国与联邦德国企业签订合同作为谈判的目的*Protokoll Nr.68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am 24.Januar 1950, SAPMO-BArch, DY 30/IV 2/2/68, Bl.5.。
3月21日,汉德克便与李富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会谈伊始,他便向李富春开宗明义地强调,民主德国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中必须扮演重要角色,并向中方递交了一份为其后贸易谈判所准备的建议清单。李富春则表示,中方现在尚无法就两国贸易协定提出具体建议,所能提供的具体货物种类与数额也无法确定。对于德方所提出的建议清单,中方所感兴趣的东西主要集中在建立企业工厂所需的成套设备,各种机械制造设备,电子、化学、光学产品、冶金炼钢以及铁路轨道,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急需的。除了苏联的援助外,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希望能得到民主德国的援助,汉德克则再次强调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政治意义,并称北京、莫斯科、柏林之间的友谊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拥有决定性意义。*Gespräch mit der chinesischen Handelsdelegation in Moskau am 21.3.1950, PA AA, Bestand MfAA, A 15.341, Bl.1-3.
在发展对华贸易关系上,民主德国政府着重强调自己要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之间扮演重要的代理人角色,即作为新中国的唯一代表与联邦德国开展贸易活动。之所以向中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和当时统一社会党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密切相关的,而统一社会党在德国问题上持什么样的立场,又是由苏联和斯大林的德国政策所决定的。
学术界对于斯大林是否希望德国实现统一这个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未成定论。然而基本可以断定的是,在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之后,斯大林仍然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联邦德国能够有所作为。在1950年5月4日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就对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Grotewohl)所谈联邦德国的情况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斯大林看来,联邦德国的前景比格罗提渥所汇报的情况要来得更好,在联邦德国,“人民群众中对于帝国主义者憎恨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加剧”*《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皮克、奥·格罗提渥和瓦·乌布利希的谈话记录》(1950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4年第2期。。
6月2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关于在西柏林和西德加强斗争的决议》,认为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之前的一些政策和实际工作并没有完全以解决全德任务为导向,对在柏林的斗争所给予关注太少,对德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在联邦德国的和平民主力量的支持不够*Beschluß des PB, SAPMO-BArch, NY 4036/656, Bl.174.。在之后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三大上,决定继续把为争取统一而斗争确定为党的首要任务,认为只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欧洲的和平才有保障;要签订公正的和平条约,撤出所有的占领军队,重新恢复德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克服德国的分裂状态*Andereas Herbst, Gerd-Rüdiger Stephan, Jürgen Winkler (Hrsg.), Die SED.Geschichte-Organisation-Politik.Ein Handbuch, Berlin: Dietz Verlag, 1997, S.307.。
为实现这个目标,民主德国政府把同联邦德国企业发展贸易视为保持德国经济统一的一种方法。为争取联邦德国企业家的同情与支持,民主德国还在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之间所签订的贸易协定上想了一些办法。正如当时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Ulbricht)对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西德一部分大企业家对同东方发展贸易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向西德的工业家声明,在拟定我们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协议时,我们同意考虑尽可能地由西德向这些国家供货,其中包括向中国供货。”*《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皮克、奥·格罗提渥和瓦·乌布利希的谈话记录》(1950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4年第2期。通过这种方式,让联邦德国的企业家们在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中获益,从而让统一社会党在联邦德国能够更大限度地取得某种同情与舆论支持。
因此,民主德国在与新中国就发展贸易关系进行接洽的时候,便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中扮演代表中国的代理人角色,这无疑表明民主德国想要垄断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意味着统一社会党可以借此实现它的两个政治目标:其一,在中德关系中,民主德国将会是德国的唯一代表;其二,利用联邦德国在对华贸易上的需求,以求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上向整个德国社会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看来,一旦联邦德国的对华贸易只能通过民主德国进行,那么联邦德国的企业家们就会直接感受到统一的好处,联邦德国社会对于统一社会党的好感会大大增加。
当时民主德国已经开始有目的地接触一些联邦德国的贸易商,从一名汉堡出口商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个人对于通过民主德国与中国开展贸易是十分感兴趣的,甚至提出应该把这样的贸易活动以某种方式进行转化,变成以一个统一德国的形式来与中国进行贸易*Vermerk, 18.4.1950, PA AA, Bestand MfAA, A 15.341, Bl.4-5.。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开展中德贸易协定谈判的预先协商过程中,乃至在此后具体谈判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都反复向中国提出,自己必须成为中国与联邦德国贸易中间的唯一代理人,并且着重强调这其中的政治意义*An den Gen.Ackermann Staatssekretaer im Ministerium fuer Auswae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10.8.1950,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0.。而中国对通过民主德国开展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也寄予了很大期望,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在会见柯尼希时,就向他询问联邦德国是否能经民主德国进行出口。柯尼希表示,联邦德国的资本家很愿意跟中国做生意,民主德国也十分愿意帮忙进行运输。*《周恩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谈话记录》(1950年6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28-01。在两国就贸易协定谈判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到了第三方——联邦德国的身上。
中方也十分愿意满足民主德国的这一诉求。7月8日,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在拜访民主德国驻华使团时,便向柯尼希透露:在香港的英、华私商都想要促成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把中国的茶叶、大豆和小麦出口到联邦德国,从联邦德国进口机器到中国。对于此事,中国政府决定等到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抵京后再进行讨论。柯尼希对此马上坚决表态认为:出于经济和政治上考虑,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应当只通过民主德国进行,必须让联邦德国的每一件商品从民主德国出口,这样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叶季壮对此十分赞同,表示中央政府决定只通过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展贸易活动。*Aktennotiz, 8.7.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38-39.
因此民主德国需要尽快与新中国签订贸易协定。民主德国最初希望能够在1950年6月初就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根据这一设想,应该在4月初就派出贸易代表团赴京谈判*《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但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设想得那般顺利。民主德国的计划必须得到苏联首肯,乌布利希5月4日才在莫斯科将民主德国近期将派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情况通报给斯大林,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皮克、奥·格罗提渥和瓦·乌布利希的谈话记录》(1950年5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4年第2期。。随后,统一社会党在代表团团长的人选问题上延误了很长一段时间。在4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外贸部部长汉德克作了关于准备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报告,政治局责成其在两天内提出组成贸易代表团成员的名单,然而直至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才最终决定由萨克森地区的经济部长齐勒(Ziller)担任代表团团长*根据1950年4月18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记录,汉德克原先提名维特科夫斯基(Wittkowski)为代表团团长,但在记录附件中存在两份代表团成员名单,在第一份名单中维特科夫斯基的名字被划去,在第二份名单中代表团团长名字处留白。参见Protokoll Nr.84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am 18.April 1950, SAPMO-BArch, DY 30/IV 2/2/84, Bl.3; Protokoll Nr.94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am 13.Juni 1950, SAPMO-BArch, DY 30/IV 2/2/94, Bl.2.。导致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延期来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代表团成员都想要等到统一社会党三大通过发展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之后再赴京谈判,他们认为这样将会更有助于贸易协定的签订*Aktennotiz, 8.7.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38.。因此,民主德国的贸易代表团最终于7月底出发,途中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后,8月5日抵达北京*Bericht, 16.September 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65.,随即与中方的代表团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有关两国代表就贸易协定的具体谈判过程,正如柯伟林(Kirby)教授所发出的感叹那样:“极其冗长乏味的资料令历史学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外交与贸易代表们的广博知识与细心肃然起敬。”*William C.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8, 2006, pp.886-887.双方代表团成员各分成五个小组进行谈判:第一组负责起草协定中的法律和政治内容;第二组负责机器制造、电子、光学产品和精密仪器;第三组负责化工、医药、油漆、染料等;第四组负责食品、轻工业产品和纺织原料;第五组负责矿石原料。谈判的主要方式就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货单,询问对方哪些是他们所需要的仪器、设备或者原料产品,然后再确定价格以及交货日期。让德方代表团成员感到非常困难的地方在于,对实际谈判过程中所提出来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进行细致探讨,所有货单材料都要进行翻译、整理并作出概要简介。由于中方各个部门并没有作好事先的协调工作,于是就要向各个部的负责人频繁地重复递交材料。*Bericht, 16.September 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66-67.这明显反映出中方人员准备不够充分,工作经验不足的缺点。
在一些准备得较为充分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就能够较为迅速地达成协议。比如中国非常想从联邦德国订购到用于铺设铁路的钢轨,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见柯尼希时就已明显表达了这一想法*《周恩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谈话记录》(1950年6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28-01。。于是在双方第一次会谈中,就立刻谈妥了价值约500万美元的5万吨钢轨订单,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8月15日就致电柏林对此进行处理,开始从联邦德国进行订货,第一批钢轨预计于订单确认后的十周就能运抵青岛。*Bericht, 16.September 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67.可这批钢轨一开始似乎并未成功订购,但从11月底民主德国方面的来信来看,似乎最后还是为中国买到了一批钢轨,民主德国为此至少先行垫付了150万美元。参见《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1;《驻德使团关于商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而其他未作充分准备的货单,则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细致谈判。
在京谈判期间,齐勒为了把中国的订货需求制定入民主德国的五年计划,中途还曾回国一次*《章副部长接见柯尼希团长谈话记录》(1950年9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28-01。。双方的贸易谈判从8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初,此时两国的进出口货物分担表仍未最终敲定*到9月16日为止,民主德国向中国方面基本确定了1.359亿美元的出口额、8840万美元的进口额,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参见Bericht, 16.September 1950,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69.。但此时民主德国提出立即签字的希望,柯尼希为此向章汉夫说明: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在10月15日进行选举,如果双方能够在选举前公布中德贸易协定已获签订的话,会发挥很大的政治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中德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如果不能如期签字,民主德国政府则会感到失望。*《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1。中方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两国决定于10月10日下午先签订贸易协定,有效期至1951年12月31日,而具体的货物分担表则由两国代表继续进行谈判*协定的具体文本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货物交换及付款协定》(1950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第90—93页;《1950年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协定:章汉夫报告》(1950年10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1。。
中德1951年度贸易协定签字之后,统一社会党对它的政治意义给予极大重视,要求各报纸不断用各种方式扩大宣传,并且多次催促中国驻民主德国的外交使团也要写一篇关于中德贸易协定的文章以作宣传。而每当中国驻民主德国使团团长姬鹏飞拜会民主德国的相关人士时,他们都会谈及中德签订这份贸易协定的意义,最为称赞中国经过他们购买联邦德国货物,认为这是中国对他们的极大帮助,对德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向联邦德国购买的物资一旦指定必须经过民主德国的话,这就让想要与中国做生意的联邦德国资本家不得不同民主德国接近,这就有利于民主德国政府争取到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并引导联邦德国工业向和平方向发展。因此中德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德国统一、世界和平都有着直接关联。*《姬鹏飞大使致周总理:德政府对我经其购买联邦德国货物为之欢呼》(1950年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驻德使团关于商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
二、1951年中德贸易协定的执行结果和困难
既然要达成上述的政治效果,那么就需要双方努力把这个贸易协定执行好,为此民主德国方面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倾尽全力。1950年7月27日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决定准备尽全力帮助中共,并进一步提出准备与中国签订一个五年的长期贸易协定*Protokoll Nr.1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27.Juli 1950, SAPMO-BArch, DY 30/IV 2/2/101, Bl.22.。在贸易协定签字完毕之后,柯尼希再次在11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外贸部应当尽一切努力同中国扩大经济关系,中德贸易协定必须准确执行*Protokoll Nr.20 der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28.November 1950, SAPMO-BArch, DY 30/IV 2/2/120, Bl.1.。为了方便中国购买联邦德国物资,民主德国外贸部在柏林成立了一家表面上私营的中国出口公司(China-Export Corporation),以专门负责贸易协定内涉及联邦德国的出口工作。柯尼希告诉章汉夫,统一社会党认为自己有以一切代价来完成这个协定的责任。*《驻德使团关于商务工作的报告》(1950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
在为执行中德贸易协定竭尽全力的同时,民主德国也时刻注意中国与联邦德国的任何贸易接触,其中一个在汉堡的卡洛维茨(Carlowitz)贸易公司进入了民主德国政府的视野。这个公司在中国曾经拥有一些职员,1949年后他们开始在中国的国营或私营的贸易机构内工作,所以他们向联邦德国的供应商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德贸易谈判的情报,从而使得联邦德国的一个面向东亚的贸易公司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中国的订货,甚至连在民主德国境内的耶拿地方的蔡司厂也通过卡洛维茨公司与香港的某个贸易公司签订出口合同。类似情况是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柯尼希直接向章汉夫表达了不满,认为贸易协定规定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只能通过民主德国进行,双方应该多从政治意义去考虑贸易协定,并且动作要迅速,他认为中国的贸易部门过于从做生意的观点出发。*Betr.: Wichtige China-Information, PA AA, Bestand MfAA, G-A 75, Bl.131;《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1;《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3。在中德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执行的过程中,比起为各自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统一社会党显然更加看重它的政治影响和作用。
在1951年中德贸易协定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两国事先都无法预料的情况和困难,并最终导致民主德国在对华贸易上出现了很大数额的出口欠账。两国1951年贸易协定具体的执行情况,首先直观地反映在以下三个表格当中:

表1 1951年民主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协定额度(单位:千卢布)

表2 1951年民主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合同额度(单位:千卢布)

表3 1951年民主德国对中国的贸易供货额度(单位:千卢布)
首先需要对上述三表*Jahresanalyse des Warenverkehres mi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tand per 31.12.1951, 31.1.1952, BArch, DL 2/1451, Bl.17.内的“协定额度”“合同额度”“供货额度”作如下说明: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两个国家当年都会为下一年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以所达成的贸易协定来制定下一年的进出口计划*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特点分析参见〔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33—341页。。两国的贸易代表团会为了追求贸易上相互间的零平衡而先确定各自的进出口数额,这便是贸易协定额度。但是,协定所确定的数额只能代表两国代表团谈判和计划的结果,而要落实协定数额就必须与具体生产产品的企业单位签订合同,这便形成了贸易合同额度。可是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又会出现种种无法事先预料的困难,导致无法全部完成所签订的合同,最后以实际所交付的产品进行计算,便形成了实际的贸易供货额度。通过对这三个表格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一些认识。
在1951年的中德贸易协定中,所应该关注的重点并非是民主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状况,而是中国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所开展的贸易状况。从协定额度来看,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进出口贸易数额要比中国与民主德国进出口贸易数额高,其中进口额高出18.46%,出口额高出19.23%。这如实反映出民主德国政府力图通过这个贸易协定来实现它在德国问题上的政治诉求,把重点放在了实现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己去充当中国的贸易代理,当然也反映出中国确实有意愿和需要与联邦德国开展贸易活动。
事实上,在中国与民主德国签订贸易协定之前,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就比较活跃了,1949年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额为470万联邦德国马克,到195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310万联邦德国马克*《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Dok.4: Bericht des OAV, Mechthild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Politik-Wirtschaft-Wissen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S.51.。但是,民主德国为中国向联邦德国的订货任务执行得并不顺利。到1951年底,通过民主德国所签订的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合同额度只完成了协定额度的34.5%,更加严重的是,实际完成的出口供货额度连合同额度的一半都还没到,出现了59,011,600卢布的缺口。考虑到这种极为困难的形势,民主德国不得不与中方商量,请求取消一些未完成的供货合同,中方最终同意从联邦德国进口的合同中再取消3100多万卢布。*Jahresanalyse des Warenverkehres mi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Stand per 31.12.1951, 31.1.1952, BArch, DL 2/1451, Bl.18, 22.
民主德国原本以为,通过垄断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可以实现它在德国问题方面的一些政治目的,但从结果来看,未能如愿以偿。在联邦德国1950年7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讨论了关于扩大同东方集团国家和中国开展贸易提案,其中就曾明确表态,拒绝让民主德国扮演贸易中间人的角色。联邦德国政府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还考虑到了贸易时间会被延迟,中间环节的费用会变贵等因素。*88.Kabinettssitzung am 31.Juli 1950, Die Kabinettsprotokolle der Bundesregierung Online, http://www.bundesarchiv.de/cocoon/barch/0001/k/k1950k/kap1_2/kap2_49/para3_9.html此外更加残酷的原因在于,美国要求西欧各国对苏联、东欧各国执行贸易管制。8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促使西欧各国提高贸易管制水平,如果确认西欧各国向苏联、东欧输出禁运物资,不论何时,立即停止向西欧出口战略物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决定禁止向中国大陆出口钢轨。*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第245—246页。
所以像民主德国为中国向联邦德国订购钢轨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十分成功,其原因并不见得如柯尼希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有人在当中作了掮客,破坏了民主德国的贸易机构向联邦德国进行订货的可能性*《章副部长同柯尼希大使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030-01。。更具说服力的原因似乎在于,联邦德国执行了美国所要求的对中国贸易管制政策,禁止出口钢轨给中国。而由于西方的禁运,中国只好尽力抢运对联邦德国的订货,或改买其他现货立即装回,以争取时间。*《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159页。到了1951年5月底,联邦德国所有向中国的出口产品都须经批准,而美国占领当局要求汉堡港禁止让开往中国的货船装货起航*Dok.4: Bericht des OAV,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S.52; 149.Kabinettssitzung am 29.Mai 1951, Die Kabinettsprotokolle der Bundesregierung Online, http://www.bundesarchiv.de/cocoon/barch/0000/k/k1951k/kap1_2/kap2_39/para3_14.html。
这些状况直接对在柏林的中国出口公司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在西方各国加紧贸易管制以后,中国所需从联邦德国进口的货物,民主德国方面只能够买到三至四种。中国与民主德国是根据1950年10月世界市场的商品价格来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并签订合同的,这必然无法适应资本主义市场在贸易管制以后所引发的价格变动,这导致中国出口公司不得不以高于1950年10月的定价为中国购入联邦德国货物*例如,染料靛的世界市场的实际最高价格大约为每千克13卢布,而中国出口公司未经中方同意便以每千克38卢布的价格购入。参见An den Vorsitzenden Gen.Hans König, 21.März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47.,到1952年8月底已经额外支出1800万卢布。同时,中方用于作为货款的实物,根据1950年10月的定价为1.44亿卢布,但最终在西方市场卖出后,却比预计价格少了1600万卢布。这样就已经为中国出口公司造成了3400万卢布的缺口,对此,中方愿意承担其中2100万卢布的损失,其余则希望由民主德国方面负责解决。*Herrn Vize-Außenhandelsminister Hsu Ministerium für Außenhandel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5.12.1952,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31-132; An den Vorsitzenden Gen.Hans König, 21.März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46-148.
相比于恶劣的出口形势,民主德国与中国签订的进口合同额度则超出了贸易协定额度的2.1%,这无疑说明民主德国对中国的农产品的需求很大,中国的农产品处在“硬产品”的地位上*这里“硬产品”的概念援引自科尔奈。他提出判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出口中的产品是“硬”或“软”的两条标准:(1)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并获得硬通货收入;(2)根据买方国家当前的国内经济状况,急需此类产品,但无法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如果想要,只能用硬通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买(付出极高成本和作出极大牺牲)。这两个标准往往相互重合,但也并不总会一致。某项产品在谈判过程中是“软”还是“硬”主要取决于两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例如,大豆在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中就一直处于“硬产品”的地位。参见〔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333页。。截至1951年6月31日,中国已经向民主德国出口约7.5万吨大豆、2000吨大米、250吨桐油、200吨锑矿、400吨钨矿、160吨丝绸、500吨羊毛,而通过中国出口公司向联邦德国出口了15.1万吨大豆、1.425万吨花生(去皮和未去皮的)、4.05万吨大米、1.53万吨桐油、400吨麻*Analyse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Abkommens 01 mit China, per 30.6.51, 23.7.1951, BArch, DL 2/1448, Bl.81.。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向联邦德国的实际出口完成得好于向民主德国的实际出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方希望以此交换到更多联邦德国产品的心态。但当中国开始介入朝鲜战争后,便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对朝鲜的支援上,也开始与民主德国协商取消了向民主德国出口6.35万吨大豆、3000吨大米以及向联邦德国出口4.775万吨大豆的合同。*Jahresanalyse des Warenverkehres mit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Arch, DL 2/1451, Bl.18.
站在民主德国的角度来看,它与中国1951年贸易协定的实行结果,非但没能帮助它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反倒在对华贸易上造成许多欠账,为自己增添了一个经济包袱。客观上,西方的贸易管制政策直接影响到民主德国完成向中国的交货任务。比如本来需要从联邦德国订购并交付给中国的一台煤氢化设备就此搁浅,民主德国自身又缺少冶金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才而无法独立承担这一交货任务,格罗提渥只能建议,民主德国向中国提出取消这一项目的请求,并建议它向苏联求助*Protokoll Nr.82, 11.Dezember 1951, SAPMO-BArch, DY 30/IV 2/2/182, Bl.2.。可见,民主德国政府由于在主观上刻意追求它自身在德国问题上的政治目标,却对自身的工业和经济能力缺乏审慎估计,大量地接受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贸易订单,最终只能咽下自酿的苦果。
三、“东柏林事件”与中国对民主德国的特殊援助
由于对1951年中德贸易协定执行不力,民主德国在对华出口上出现了大量欠账,这直接影响了两国在之后若干年内的贸易关系,使得民主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华贸易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到了1953年“东柏林事件”爆发后,民主德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势变为更加危急,此时中国向民主德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农副食品援助,但这也继续增加了民主德国的对华出口负担。
“东柏林事件”爆发的重大背景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对德政策的变化和反复。1952年3月10日,苏联政府发出著名的“斯大林照会”,对于两德统一和对德和约提出了具体建议。当西方三国拒绝接受照会中的建议,斯大林就明显改变了自己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到4月7日斯大林会见民主德国领导人时,他明确提出,联邦德国正在成为独立国家,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应该被视为十分危险的国境线,而对于德国统一,斯大林则表示这应该成为统一社会党教育联邦德国人民的宣传武器。*《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皮克、奥·格罗提渥和瓦·乌布利希的谈话记录》(1952年4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4年第3期。
至此,斯大林已经决定把民主德国牢牢控制在苏联手中。1952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民主德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7月9日至12日,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二届代表会议,决定在社会的所有领域内有计划地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在经济计划、社会制度、国家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将以苏联模式来改造民主德国,正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编写组编,陆仁译:《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决议全文参见Beschluß der II.Parteikonferenz der SED vom 9.bis 12.Juli 1952,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und zu den Aufgaben im Kampf für Frieden, Einheit,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Herbst, Stephan, Winkler (Hrsg.), Die SED, S.588-592.这意味着将剥夺私营工业在民主德国经济上的地位,在农业上加速推进集体化,在政治文化领域则要同那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在党内和政府机关内部也开展清洗工作,弥漫着阶级斗争的气氛*Andreas Malycha, Peter Jochen Winters, Die SED: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Partei,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9, S.107-110; Dietrich Staritz, Geschichte der DDR 1949-199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6, S.94-100; Hermann Weber, Die DDR 1945-1990,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12, S.36-41.。这一系列的激进政策对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诸多困扰,在重工业上的大肆投资、忽视轻工农业的结果便是导致食物、生活用品的供应极其紧张,进而诱发了内部的社会危机,人民群众开始离开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国内形势岌岌可危*对于统一社会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诸多政策,特别是取消工人自1945年乃至更早时候所享有的诸多待遇,引起民主德国民众的不满,直接表现为大批人员逃往联邦德国。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出走联邦德国的人数共计约为44.7万人,1952年约23.21万人,仅1953年前4个月就出走约12万人,其中统一社会党党员或预备党员就有2718人,整个1953年的出走人数为40.81万左右。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8页。。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层又开始转变之前的对德政策。面对十分危险的民主德国局势,苏联部长会议6月2日通过决议,要求在民主德国不再执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1953年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形势的措施》的决定,承认1952年7月8日由统一社会党决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关于在民主德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当前形势下是错误的,建议民主德国立即取消对农业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取消对私营企业的压制政策,重新修改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放松政治、司法以及军事领域的管制。此决议文本参见Über die Maßnahmen zur Gesundung der politischen Lage in der Deutschen Demokartischen Republik, SAPMO-BArch, DY 30/J IV 2/2/286, Bl.4-9.。
但是苏联领导人当时的主要意图是要解决民主德国群众的出逃问题,却没有能及时注意到,民主德国5月所作出的关于提高工人劳动定额的决定,又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1953年5月1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通过《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厉行节约》的决议,决定在6月1日以前将劳动定额平均提高至少10%。5月2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所有国营企业在6月30日以前将劳动定额提高至少10%。提高劳动定额等于工人实际的工资收入相对降低了,然而有的企业领导不与工人商量,便通过行政命令强制予以执行,甚至使用不提高定额就降低工资的办法。参见Arnulf Baring,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June 17, 1953,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1-22;《柏林斯大林大街建筑工人罢工情况报告》(1953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303-01。。6月9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没有能触及已被提高了的劳动定额问题*统一社会党的“新方针”决定参见Kommuniqué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SED vom 9.Juni 1953, Wilfriede Otto (Hrsg.), Die SED im Juni 1953.Interne Dokumente,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2003, S.96-99; Protokoll Nr.34/53 der ausserordentlichen Sitzung des Politbüros des Zentralkomitees am 9.Juni 1953, SAPMO-BArch, DY 30/J IV 2/2/288, Bl.1-3; 6-22.。统一社会党的“新方针”确实减缓了之前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可工人的利益被无情地忽视了,这直接成为引发“东柏林事件”的导火线。从开始罢工、示威游行到最后演变为骚乱、暴动,直至苏联动用驻德部队介入镇压。为了缓和“东柏林事件”所造成的国内形势的紧张状态,缓解普通民众对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民主德国政府需要继续调整自己的社会经济政策,这就要求加大对民主德国人民在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上的供应力度,这单凭民主德国的一己之力实在难以为继,它首先自然是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同时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也成为民主德国主要的求援对象。
1953年7月21日,驻华大使柯尼希向周恩来转交格罗提渥的一封信,表示由于当前民主德国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统一社会党为此采取了新的方针,需要尽一切力量解决新方针中所提出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但是单靠民主德国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所有这些任务,因此对于目前国内急需大量粮食供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此外,柯尼希还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张货单,其中列有他们希望中国予以提供的物资种类及数量。但对于这些货物的偿付工作,柯尼希表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在1953年内完成,需要放到第二年才能偿付。柯尼希还告诉周恩来,民主德国无法完全履行之前已缔结的贸易协定中所担负的义务,只能完成1952年贸易协定中1.05亿卢布的欠账,1953年贸易协定只能先完成1.75亿卢布,还需要欠账5600万卢布。*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Premier-Minister Tschou En-lai, 21.Juli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98-200; 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S.28;《周总理与柯尼希团长谈话记录》(1953年7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86-01。
当周恩来向柯尼希询问是什么原因造成民主德国粮食及农产品供应形势的紧张时,柯尼希只是根据民主德国报纸所公开报道的观点作了一番解释,反倒是周恩来的评论显得一针见血,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指出:“我们建设中也有些冒进的毛病。虽然程度不同,亦有这种趋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贪图过渡得快些,而不是根据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自愿。听说东欧其它兄弟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化早一些,你们的教训也是我们的教训。”*An den Staatssekretär Anton Ackermann im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DDR,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88;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Premier-Minister Tschou En-lai, 21.Juli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201-202;《周总理与柯尼希团长谈话记录》(1953年7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86-01。
对于民主德国的援助请求,周恩来表示会告知毛泽东,并在研究了格罗提渥的来信以及民主德国所提出的货单之后,尽一切可能予以帮助。7月29日,周恩来批示,德方要求援助的物资约为5300万卢布,中国提出的援助物资的种类和数量与德方要求相同,粮食超过。希望财政部立即拨款,至于合同则以后再谈,对于何时还货问题,更不忙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
7月30日,叶季壮与柯尼希举行会谈,表示中国将会提供1.2万吨食用油(包括芝麻油、菜油、豆油),对于德方所提6000吨大米的供货要求,中方只能给2000吨,但是会另外提供1.5万吨小麦;关于鸡蛋供货,叶季壮认为新鲜鸡蛋在运输上存在困难,提出是否可以用冷冻鸡蛋来代替;民主德国所要求的新鲜鸡肉也无法供应,但可以提供2000吨的鸡肉罐头;此外,中国还将提供约4万张牛皮、1万桶猪肠。柯尼希对此表示感谢,认为中国基本上满足了德方的要求。*Aktenvermerk, 30.Juli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204-207.
8月8日,两国代表在北京签订1953年中德贸易补充协定。对于民主德国所提出的援助要求,中国予以积极响应,并表示全力配合完成。在周恩来给格罗提渥的复信中表示,他将帮助德国人民视为中国的责任,并以此为荣,而毛泽东更在之后加上“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这样的谦虚之辞*Dok.5: Schreiben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Zhou Enlai an Ministerpräsident Otto Grotewohl, Werner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Politik-Wirtschaft-Kultur; eine Quelle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S.71-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99页。。这一切都使得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由衷地对中国产生一种感激与钦佩之情。在民主德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中国自己的物质供应状况也十分紧张,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在民主德国之下,却仍然尽全力向他们提供援助;1953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由于气候原因,将不会提高与兄弟国家的贸易额度,但对民主德国则仍然施以特殊帮助。*Krü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S.28; Entwicklung des Handelsverkehrs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 27.November 1954, SAPMO-BArch, DY 30/J IV 2/2J/76, Bl.5.1953年9月15日,格罗提渥复信周恩来,对中国向民主德国给予的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九月十五日写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86-03。
除了签订贸易补充协定外,中国还打算通过增加出口的方式对民主德国进行帮助。在发生了“东柏林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判断比较严峻。他甚至认为,民主德国“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并且将它与朝鲜视为同类国家,其差别仅在于“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对民主德国的外贸工作中,不适用“中国1954年的对外贸易额不高于1953年”的命令,指示应当全力帮助民主德国,1954年可以答应向其出口3.2亿卢布,若当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则用一切努力满足民主德国的要求,并作好对方可能欠账的准备,而且中国还单方面承担用于中德贸易的租船费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62页;Information ü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29.August 1956, SAPMO-BArch, DY 30/IV 2/20/115, Bl.19; Entwicklung des Handelsverkehrs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 27.November 1954, SAPMO-BArch, DY 30/J IV 2/2J/76, Bl.3.
在民主德国发生“东柏林事件”之后,中国对其在农副产品的供应上提供了特殊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并不是直接无偿的赠送,而是需要民主德国通过今后的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进行偿付的。因此,与中国签订1953年贸易补充协定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民主德国自1951年以来的对华出口欠账又增加了5000万卢布。为了实现两国贸易平衡的目标,民主德国政府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四、尾声:实现平衡与民主德国放弃代理人角色
从1951年到1954年这四年间,民主德国的对华出口都存在着欠账情况。例如到了1952年底,民主德国对中国的实际出口才完成了两国1952年贸易协定总额的52.5%,中国则在此时已经完成了对民主德国出口计划总量的80%*Bericht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und a)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b) der Koreanischen Volksdemokratischen Republik c) der Demokratischen Repulibk Viet-Nam im Jahre 1952, PA AA, Bestand MfAA, A 6.696, Bl.85.需要注意的是,两国1952年贸易协定的正式签订日期是1952年5月2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于6月12日予以批准,中国政务院则于7月27日予以批准。参见An den Chef der Diplomatischen Missio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ußerordentlicher und Bevollmächtigter Botschafter Herr Tschi Peng Fei, PA AA, Bestand MfAA, A 15.341, Bl.22; 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5.8.1952, PA AA, Bestand MfAA, A 15.341, Bl.23.。因此民主德国需要在第二年对前一年的欠款进行偿付,这无疑又会产生新的欠账,直到1955年才第一次正式完成了当年的出口义务*Dok.114: Die Entwicklung des Außenhandels zwisch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und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51 bis 1956,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S.250.对于那些仍未能交付的联邦德国货物,中国外贸部于1953年3月决定中止这些合同,民主德国的中国出口公司不再承担出口的义务。参见An den Vorsitzenden Gen.Hans König, 21.März 1953, PA AA, Bestand MfAA, A 15.639, Bl.148.到了1954年4月8日,民主德国与中国则在柏林分别签订关于两国关于1951年贸易协定以及1952年贸易协定的债务清偿协议。参见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PA AA, Bestand MfAA, A 6.661, Bl.99.(具体数据见表4)。如果想要尽快弥补之前的欠账,达成两国在贸易上的均衡,只能通过加紧对华出口,想办法让对方加大进口数额,可事实上要尽快做到这些也绝非易事。

表4 1951—1955年民主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单位:百万卢布)*此表数据见于Dok.114,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S.250-251.
首先,民主德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存在一定的质量缺陷。当民主德国贸易副部长格雷戈尔(Gregor)在北京逗留时,柯尼希就曾向他指出包括机器出现生锈在内的各种不符规格的马虎情形,并且认为这将会影响到中国对民主德国产品的继续订货*“Die ersten Jahre in Peking”, Kürger (Hrsg.),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S.29; Dok.115: Information über den gegenwärtigen Stand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 Dok.116: Schreiben des stellvertreten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Lothar Bolz an den Ministerpräsident Otto Grotewhol, 17.September 1954,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S.254, 255.对于出口中国产品的质量和规格缺陷,连乌布利希都曾直接写信给相关企业党委,要求他们重视改进。参见Dok.119: Schreiben des Ersten Sekretärs des ZK der SED, Wahlter Ulbricht, an den VEB Elektrokohle Lichtenberg; Dok.120: Schreiben des Ersten Sekretärs des ZK der SED, Walter Ulbricht, an den VEB Feinstmaschinenbau Dresden, 18.11.1955,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S.258, 259.。其次,中国外贸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发展节奏。而在民主德国愿意向中国大量提供的机器设备中,有一些并不见得是中国所急需的,甚至连毛泽东也曾直接表示过,希望“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Entwicklung des Handelsverkehrs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 27.November 1954, SAPMO-BArch, DY 30/J IV 2/2J/76, Bl.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62页。。最后,由于中国自身的工业化发展,一些本来需要依靠进口的产品也开始逐渐依靠自己生产。在1951年和1952年这两年中,中国向民主德国进口了大量的小型机床,但是当自己也能生产这类机床后,对德进口就大量缩减*Dok.115, Meißner (Hrsg.), 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 S.253.。因此,从经济利益考虑,中国实际上并不见得急于扩大对民主德国的贸易额。
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出于政治考虑,最终还是将1955年对民主德国的进口贸易额从原来的2.7亿卢布提高到了3.2亿卢布。民主德国方面也开始思考自身在对华贸易上的缺陷不足,并在为1955年的贸易协定谈判中采取一定的改正措施,如要求相关各部门定期协商采取具体措施以弥补欠款;要求谈判代表有责任缩短价格谈判的时间,准备好所有出口产品的说明资料和定价,并事先准备好在不同经济领域内的比较价格,以这些具体的价格为基础,力求尽快签订贸易合同;采取措施保证有适合的运输船用于运输,确保运输速度;把相应的产品专家和买主派往中国,能够为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要求作好准备,同时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还计划派更多的代表团到中国去*Entwicklung des Handelsverkehrs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 27.November 1954, SAPMO-BArch, DY 30/J IV 2/2J/76, Bl.7-14.。总而言之,经过一番努力后,民主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从1955年开始实现平衡,之后逐年保持增长。
中国在“东柏林事件”后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援助,为自己在两国关系当中树立起了良好的政治形象。1954年4月19日,周恩来从北京出发参加日内瓦会议,飞机中途将在柏林停留一小时,民主德国为此派出庞大的欢迎团到机场迎接,包括总理格罗提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厄斯纳(Oelßner)、外交部部长博尔茨(Bolz)以及政府各部门首长等重要领导人*驻德使馆:《关于周总理经柏林情况的报告》(1954年5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397-01。。而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于7月23日至26日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与格罗提渥举行会谈,发表了《中德两国总理会谈公报》,并接受了柏林洪堡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04页。。在双方的会谈后所发表的公报中,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在谈话中,奥托·格罗提渥总理指出,西德广泛的经济界人士对于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关系非常关心;他们不赞成西德联邦与美国垄断利益片面经济联系。奥托·格罗提渥总理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照顾到德国人民的利益会支持这一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努力。
周恩来总理答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任何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无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奥托·格罗提渥总理有关西德经济界人士的愿望的建议当予以极大的注意。*《中德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7月27日。
这一声明意味着在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之间,民主德国放弃扮演中国贸易代理人的角色,而是以代表德国人民的利益的名义,建议中国加强与联邦德国的贸易联系。
形成这个声明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苏联和民主德国政府在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最终决定采取承认“两个德国”的政策。1954年3月25日,民主德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苏联政府表示自己已开始把民主德国当作一个主权国家来经营两国关系。此时苏联的对德政策已经从坚持德国统一的立场向着承认“两个德国”开始过渡,所以此时民主德国政府也就不再需要以中国对德贸易代理人的身份出现,鼓励中国既同民主德国又同联邦德国开展贸易,这可以在客观上给人造成存在“两个德国”的印象,而中国政府也愿意承认“两个德国”*有关中国对于“两个德国”的态度与立场参见葛君:《论1950年代中国对于承认“两个德国”的态度》,《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3期。。
为了帮助中国从联邦德国进口物资,民主德国外贸部曾专门设立了中国出口公司,但是由于西方的贸易管制政策,以及联邦德国政府拒绝民主德国作为贸易代理人的立场,导致1951年贸易协定的完成情况不容乐观。到1953年,中国出口公司基本无法再发挥作用,最后只能解散并结束工作。工作人员经过筛选后,进入中国政府在柏林新设立的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Aktenvermerk am Sonntag, dem 3.Mai 1953, SAPMO-BArch, DY 30/IV 2/20/119, Bl.4-5.于是,中国开始独自与联邦德国直接展开贸易工作上的接触,不再把民主德国当做中间环节看待。
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国就与联邦德国开始通过民间贸易机构进行了一些接触,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联邦德国驻日内瓦的代表同宦乡进行了会谈,宦乡向对方表达了加强两国贸易关系的愿望,并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Dok.9: Bericht des Gesandten Fischer, Genf, an das AA, 21.Juni 1954,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S.57.。而德国东方经济委员会(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的成员也多次拜访中国代表团的外贸代表,意图就发展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进行会谈。双方准备为一个各自完成2亿联邦德国马克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我国同意西德工商界派贸易访问团来我国》,《人民日报》1954年9月5日;Dok.10: Meldung der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agentur Xinhua, 3.9.1954, Leutner (Hrsg.),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 S.58.
对于中国开展与联邦德国的贸易活动,出于当时既定德国政策的考虑,民主德国采取积极配合的立场。在它看来,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求尽一切努力,扩大并加强东西方贸易,引导人民走向和平共处,并以此加强对战争贩子的斗争”。由于中国与联邦德国贸易代表的接触渠道很多,民主德国也想在这方面尽量采取主动。1954年底,民主德国决定组织一个小型的联邦德国贸易代表团前往北京,其中包括两名促进德国贸易的代表,四名联邦德国工业部门的代表,他们会根据在莱比锡展览会上的货单,与中国签订贸易合同,并讨论中国与联邦德国贸易协定的草案。但民主德国也注意向中方强调,双方只应讨论有关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问题。*Vormerk über zwei mit den chinesischen Freuden durchgeführte Besprechungen in der Zeit vom 15.bis 24.12.54 in Fragen des Ost-West-Handels, 25.1.1955, BArch, DL 2/1471, Bl.3.于是,民主德国原先设想在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扮演贸易代理人角色的强烈愿望如今已黯然褪去。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研究,一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适用,其关键的一点便在于市场对当时在经济上基本奉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在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中,各国家行为体间的政治考量单方面地决定了它的对外经济决策,而似乎基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
本文所叙述的新中国与民主德国1951年贸易协定的谈判、签订和执行过程中就反映出了上述问题。民主德国由于在德国问题上的政治诉求,希望利用自身在对华关系上的优势地位成为新中国对联邦德国贸易的代理人,从而导致自己承担大量从联邦德国购货并对华出口代理业务。而随着西方对华禁运和贸易管制政策的执行,这些代理业务都成为自己不堪承受的经济负担,在之后对华贸易中处于出口欠账的状态。到1953年又由于稳定国内社会的政治需要,民主德国再次不得不向中国提出农副产品上的援助请求,进而扩大了对华出口方面的经济负担。对于新中国而言,在50年代早期与民主德国的贸易交往中,面对民主德国两次在贸易问题上提出的重大要求,中国也都是从政治考量出发予以答应。特别是1953年,在中央已经决定1954年不再提高与各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统一社会党政权的稳定,毛泽东决定对民主德国实行例外的特殊待遇。而当苏联和民主德国确定调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决定采取承认“两个德国”的立场时,民主德国就主动放弃作为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贸易代理人的角色,反而鼓励中国要加强与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虽然这样的要求有利于中国外贸关系的发展,但其基本的出发点仍然没有摆脱对于政治问题的考量。
这些情况似乎都可说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的标准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国家物质利益或单纯的经济利益。对于什么才是符合自己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往往有着自己的特殊考量。就50年代初期的中国和民主德国而言,作为相互承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员,一种相互团结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观念建构了它们的最高利益,因而会出现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标而忽视甚至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现象,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那种“要多从政治意义看待贸易协定,而不要从做生意的角度出发”的观点便最能反映这样一种心态。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arly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GDR, 1950—1955
Ge Jun
After the PRC and the GDR were founded, both countries followed the Stalin’s arrang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postwar. When the PRC and the GDR had established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y wanted to strengthen their trade relations a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ng the trade agreement for 1951, the GDR asked the PRC to treat it as the sole agent of the tra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FRG for its own demands on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and China agreed to this request. However, due to the western embargo policy, the GDR could not complete obligations of its exports, resulting in outstanding loans on trade with China. East German Uprising in 1953 made the GDR’s domestic supply situation even more difficult, China’s special assistance once again exacerbated the GDR’s debts until 1955.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各国冷战时期档案收集和整理”(12&ZD188)的阶段性成果。
D829.517;F749
A
1003-3815(2016)-11-007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