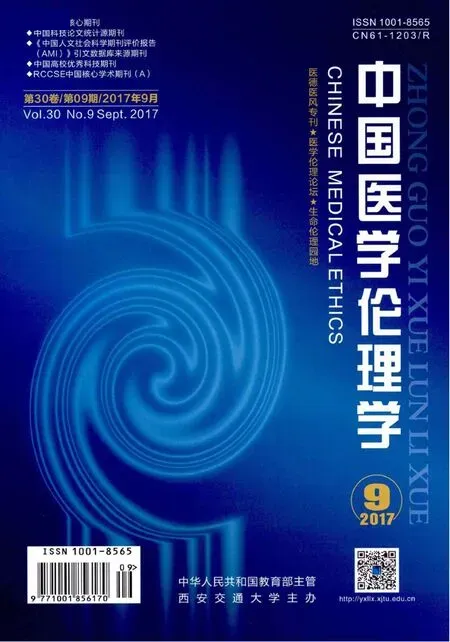临终患者的文化叙事分析
——基于哈尔滨市X社区医院临终关怀病房的田野调查*
张云龙,瞿 平,贺 苗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1309485807@qq.com)
临终患者的文化叙事分析
——基于哈尔滨市X社区医院临终关怀病房的田野调查*
张云龙,瞿 平,贺 苗**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1309485807@qq.com)
收集在哈尔滨市X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病房的病例和访谈资料,运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整理并分析临终患者的疾病叙事,心理体验及社会文化意义。通过3例田野个案的描述,分析和思考临终患者的忧郁与无奈、请求与愿望的疾痛体验,强调对临终患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文化叙事研究,进而为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临终患者;疾病叙事;文化叙事;临终关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性病和恶性肿瘤患者日益增多,他们不仅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和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内心的孤独、死亡来临的恐惧与不安。特别是对于一些临终患者,如何让他们安宁地、没有痛苦地、有尊严地死亡已经成为当代医学需要直面的新课题。本文主要利用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在哈尔滨市X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病房收集的病例和访谈资料,运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整理并分析临终患者的疾病叙事,心理体验及社会文化意义。
1 三例田野个案
1.1 肠癌晚期肝转移的工程师的病与痛
第一次见到53岁的患者A,他已经是直肠癌晚期,肝转移,全身黄染,眼睛凹陷,笔者进入病房时他正躺在床上,两个枕头把头垫得稍高一些,很专注地盯着手机吃力地看。他妻子开玩笑似地说“在炒股赚钱呢”。A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一个擅长三维动画制作的工程师,在江北一家私企工作,他在确认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就已经写好了遗嘱,申请了红十字会的公证,想在他死后捐献角膜和遗体。“我还能活多久?”是他经常问主治医师的话。
患者A的患病过程还是很波折的。2016年9月,他因为便血,去医院检查,最后通过直肠镜确诊为直肠癌晚期伴多发性肝转移。在此之前,就曾因便血去医院找专家看过,被确定为痔疮,当时也没太在意,又过了一段时间,身体越来越差,又去医院检查,再次以痔疮被劝回来,直到最后发展为直肠癌晚期。
据其配偶讲,刚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时,夫妻俩就坐在家里自言自语,“应该是在做梦吧,梦里再残酷再逼真,梦醒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像往常一样,那么好一个人,也没做什么亏心事,怎么能得癌症呢?谁得也不能是我们得呀!凭啥这样的事要落到我们头上,一定是搞错了。”直到现在,还仍然感觉像一场梦。
尽管这是直肠癌晚期,二人还是决定去医院,其配偶说,之前已经联系好了这家医院,但A想去肿瘤医院住院,但肿瘤医院的回复是,只能在走廊里加床,他病得很重且到了晚期,没有太大的治疗价值。在征得A的同意后,他们来到这家社区医院。其配偶说,他自己不让抢救,也不让放化疗,他不想太痛苦,他害怕全身插满管子。患者A去年12月4号凌晨死于肝肺转移瘤,从发病到死亡大概时间间隔50天。
1.2 想要安乐死而不得的“倔老头”
67岁的B生病前是个司机,患有顽固性心衰,一直在用硝普钠静点。据他讲,已经连着好多天没睡着觉了,半个月前嗜睡,和别人说着话,刚说完上半句,就睡着了。白天躺不下,躺下刚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憋醒了,躺着不行,就得坐着。因为长时间住院,两侧胯骨都长了褥疮。患者的女儿告诉笔者,“我母亲两年前就是在对面的病房去世的,也是心衰,比他严重,没住多久就去世了。所以我爸一直不愿意来这里住院。我爸说每当他睡着的时候就能梦见我妈在叫他。”因为睡不着觉,就服用安眠药,奇怪的是,吃完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反而更精神了。以前在大医院CCU的时候,经常自己骂自己,并拍着自己的脑门说:“怎么不听话呢,怎么睡不着觉?”有一次他突然有气无力地冒出来一句,“我想安乐死,太难受了”。我好奇地问他,“您怎么知道安乐死的?”他女儿说,患者B之前状态好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过。我说:“国家现在安乐死不合法,没人敢给你做呀!”他很气愤又有些无奈地说“这样反复睡不着觉,难受啊!”我问他的女儿,“安乐死,你能接受吗?”他的女儿摇头,“每一次发病去医院也能抢救过来,虽然痛苦、难受,但终归是活着的,活着怎么也比死了强啊!”
笔者告诉他,“你闺女舍不得你呀”,他有气无力地瞥了笔者一眼。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就这样被痛苦折磨着。他有两个孩子,在上海的儿子,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来陪护,在哈尔滨市的女儿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儿子每个月给妹妹打钱来,让妹妹照顾。虽然有医保,医保规定的两次住院必须至少间隔15天,也就意味着这间隔的15天得自费,即使是简单地对症营养支持治疗,家里也是捉襟见肘。B说:“用药也不咋管用,就是干耗时间,住不起啊!”一天夜里,患者B不停地按铃,值班医生说:“他一直按铃,我以为他发生了什么危险,着急忙慌地跑到病房,啥事也没有,隔一会儿又呼叫,叫了好几次,整宿没合眼。有时候觉得他以捉弄我们为乐。”值班医生有点激动地说:“我们对他已经很照顾了,他怎么还这样?”不过,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可能太孤独了吧,女儿晚上回家,没人陪护,他也痛苦,整宿的睡不着觉是什么感受?唉……”
1.3 患尿毒症而无钱救治的农民大叔
第一次见到64岁的C,他患尿毒症已经很重了,而且状态特别差。他的医生说现在比较有效的治疗就是换肾或者透析。然而,对于C来说,不仅肾源难觅就连基本的透析费用都支付不起。他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帮别人打工,小儿子在街上摆个小摊。听小儿子说:“我爸常年在外地干活,不在家,新农合的费用好几年都没交了,家境很不好,好几天没吃进一口饭”。
患者C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和处境,一直也不说话,眼神很忧郁、迷离。一天早上查房时,医生详细地向患者和家属交代了病情,当时C的姐姐、弟弟、妻子以及两个儿子都在。C的姐姐说,“大夫,得给用药啊!”医生说,“可以啊,交费,马上就用。”C的姐姐有些气愤地吼道:“多少钱啊?还不给用药了?”医生的情绪当时也有些失控了回应道:“你交啊?现在去交,交完我马上就用。”空气仿佛凝固了,此时,C的表情很复杂,难过、悔恨或是自责……他躺在病床上,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自始至终都是沉默,他浑浊的眼睛并没有埋怨谁,可能是因为呼吸不畅,一直在病床上喘着粗气。12月28日中午,C在痛苦中并没有太挣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 思考与发现
2.1 临终患者的忧郁与无奈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提出了人濒死前心理发展的五个阶段:否认和隔绝、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事实。[1]临终患者每个阶段所历经的时间长短会有差异,但无论是家属还是患者最终都不得不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纵观患者A最后的生命历程,他的病情大致也是经历了拒绝、愤怒、挣扎、沮丧和接受五个心理阶段。在刚开始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时,两口子坐在家里自言自语,感觉像是在做梦。之后是误诊的愤怒,以及对自己最初不当回事的懊悔。再接着是到各个大医院寻求治疗,做最后的挣扎,挣扎无果,心情沮丧,随之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接受了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并且写了遗嘱捐献遗体。患者自己有意识,知道自己的病情,自己选择了不放化疗,只要求对症姑息治疗。在哪里住院,家属也征求了患者的意愿。
在该患者刚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时,他和妻子两人无法接受事实真相,坐在家里自言自语,“也没做亏心事啊,人那么好,怎么能得癌症呢?”这反映出在老百姓的观念里,传统的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去研究问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模式。我国的临终关怀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西方的临终关怀模式。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决定在中国完全套用西方的临终关怀模式并不恰当。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中国人深受儒、道、释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故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因人地开展临终关怀,开展田野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C的情况并不鲜见,临终关怀虽然强调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但是临终关怀作为医院救治痊愈无望的后续阶段,仍有重要的人文价值。此时,给予这些饱受身心痛苦的临终患者基本的对症支持治疗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可以缓解他们身体上的疼痛,也可以给他们以时间和亲人们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然而,即使是缓和医疗,费用仍然是很大的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帮助让这些临终患者有尊严、舒适、安宁、快乐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王一方曾在一篇文章里论述过,当下高新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死亡定义,有尊严不是一个虚幻的口号,而必须从手术、用药、器官替代、护理延伸到陪伴、料理、抚摸、慰灵等过程。[2]他这里用的是“延伸”而非“替代”。在临终患者反复住院的过程中,经济的无能为力使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的治疗,较长时间的看护也让家属们身心疲惫,但在传统孝道的约束下,也不能弃之不顾,于是各种极其矛盾的思想斗争就产生了。
2.2 临终患者的请求与愿望
安乐死问题的争议一直都存在。国内外支持和反对安乐死的声音此起彼伏,至今仍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除荷兰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通过了安乐死立法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没有将安乐死合法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身患癌症,身心异常痛苦那也只能挺着。此时死亡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一种最大的解脱。
回顾患者B生命的最后阶段,彻底无眠的痛苦、安眠药效果的尴尬、医疗费用的压力、想要安乐死而不能的困境、小小的心愿以及折腾医生、医生的苦处,这都是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提高临终患者生命最后阶段的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很多重症的晚期弃疗的患者之所以会选择这家社区医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费用很低,一个单间的临终关怀病房一天的费用只需五十元,里面有两张床,患者一张,陪护的家属也有一张。廉价的费用自然就决定了无法提供更多的护理服务,大量的护理工作主要由家属来做。由患者身上长的褥疮可知,家属的护理差强人意,这可能是因为家属护理技能的匮乏,也可能是因为家属长期照顾导致身心疲惫、无暇顾及。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全社会对临终关怀的关注度并不高,医保在临终关怀上的投入远远不够,临终关怀机构没有固定的国家财政支持,社会支持较少,而临终关怀机构又多带有公益性质,长期下去难以为继。国家在临终关怀政策方面虽然有不少文件中提及,但已有学者指出,“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相关政策的缺位,使临终关怀事业发展陷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相关政策的呈现碎片化、操作性不强、缺乏财政支持、缺乏宣传力度。”[3]由此可见,从国家层面出发制定专门的、可操作的临终关怀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地方上再结合本地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临终关怀指南,同时自上而下地加大对临终关怀的宣传力度,鼓励、吸引地区社会资本和社会团体、志愿者以及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
3 临终患者对死亡认知与临终关怀的发展
3.1 临终患者的死亡态度和心理变化
在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态度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特别是随着现在自媒体移动终端的普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受各种有关死亡的知识。对安乐死的认知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减轻和消除临终患者的痛苦,旨在提高死亡的质量的、有尊严的死亡观正在临终患者及其家属之中普及。特别是在疾病的终末期,临终患者极端痛苦又治愈无望,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加之经济与家庭的双重压力,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已经成为多数临终患者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临终患者逐渐打破传统死亡观的禁忌,开始考虑姑息治疗、放弃治疗甚至是安乐死。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尊严死”“生前预嘱”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临终患者求生已不能时,在与死亡的交涉中他们的心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对死亡进行思考,如上文中提到的,有的患者会不时地问“我还能活多久?”,有的会以不同的方式如按铃、叫喊、摔东西来“折腾”医生和家属,有的会流露出忧郁、无奈甚至绝望的神情。此时家人、朋友、医生以及志愿者等社会工作者对临终患者的陪伴、照护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和人道主义关怀,能够使他们内心得以平静,坦然地面对死亡,接纳死亡,实现人生最后一站的平稳过渡。
3.2 临终关怀的发展
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44亿,占总人口的11.03%,2020年将达到2.43亿,2030年达到3.51亿,到2050年将达到4.5亿,届时老龄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30.00%,达至中国老龄人口的最高峰。[4]而老龄人口同时又是多种慢性病、肿瘤的发病聚集区,加之我国长时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日益增大。大型医院的医疗资源紧张,医疗费用高居不下,在社区开展临终关怀更显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发展社区医疗,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切实推进分级诊疗,将成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我国人口结构改变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风生水起之际,社区医疗在其中充当的分流作用愈发突出,而在社区医疗中推进临终关怀服务,充分发挥其治疗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属性,必将极大发挥出社区医疗机构在今后发展中的巨大潜能。
目前,国家正在实施“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的模式,后续还会进一步加入“养老、临终在社区”的服务模式。我们对临终患者这一群体进行田野调查,描述个体的疾病史、生命史,观察个体的疾痛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当数量积累起来,再逐步地扩展开来,就会形成一个区域的疾病生命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5]这也恰恰是我们做临终关怀田野调查的初衷和最终归宿。
[1]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论死亡与临终[M].邱谨,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12.
[2] 王一方.尊严死:重症医学的新课题[J].中国医院院长,2016 (12):89.
[3] 邓帅,李义庭.我国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相关政策的现状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3):402-404.
[4] 靳凤林.中国死亡哲学研究四十年[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3):273-280.
[5]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卷)[J].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4-45.
2017-06-15〕
〔修回日期2017-08-17〕
〔编 辑 李丹霞〕
CultureNarrativeAnalysisofTerminalStagePatients:BasedontheFieldInvestigationinXCommunityHealthServiceCenterinHarbin
ZHANGYunlong,QUPing,HEMiao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arbinMedicalUniversity,Harbin150081,China,E-mail: 1309485807@qq.com)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case and interview data in the hospice wards of X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in Harbin with the method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It sorted and analyzed the disease narrativ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nd social-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erminal stage patients. Through describing three field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pressed-helpless and request-desire pain experience in terminal stage patients.It emphasized the cultural narrative research in this special group,terminal stage patients, and further to provid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ospice care in China.
Terminal Stage Patients;Disease Narrative; Cultural Narrative; Hospice Care
黑龙江省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G201410);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项目“疾病、健康与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研究”(YF17-Y1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叙事医学视域下医学教育全新模式的研究”(15EDB04);哈尔滨医科大学创新科学研究资助项目“疾病与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2016RWZX13); 2017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身体、病痛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E-mail: hemiao767@163.com
R48
A
1001-8565(2017)09-1085-04
10.12026/j.issn.1001-8565.2017.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