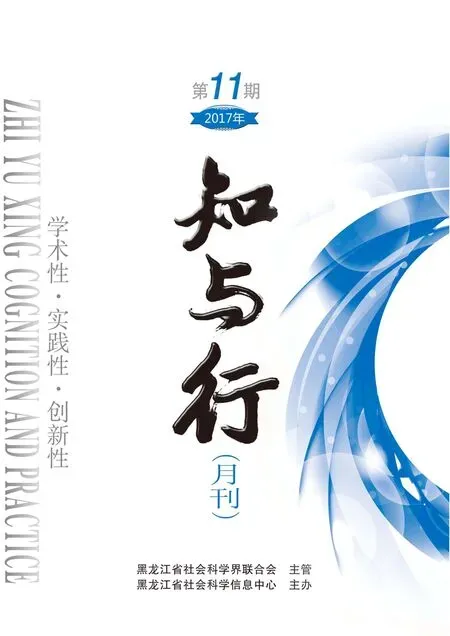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与启示
栾 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时事政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与启示
栾 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18)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第40周年,这几十年来,我国的监察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于2016年年底产生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于12月26日起,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开设监察委员会,正式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2017年11月,“十九大”后,又提出了要将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这就意味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此正式进入了崭新阶段。新时期,国家监察体制呈现出诸如监察资源整合、监察范围扩大、监察手段丰富、监察职权增强等新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现从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演进历程出发,并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最新要求,分析国家监察体制在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并在回顾与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对进一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启示,从而尝试提出了如加强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和制约、从制度层面确保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促进合署办公模式下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以及加强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合理内核的学习和借鉴等一系列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从而使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国家监察体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监察体制在探索与实践中稳步前行,国家监察体制演进的历程,是我们下一步继续向前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以史为鉴,方可知得失,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进程,才能总结出我们在探索前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并预测国家监察体制发展的新趋势,进而有所启发,尝试提出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推进,党的监察体制的恢复和重建也被最先提上日程,这也体现了党的监督在我国监察体制中的重要地位。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党章关于恢复并建立纪检监察机关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均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对党员加强教育,严格要求,坚决杜绝违纪行为[1]。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设办公厅、研究室、纪律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来信来访室五个部门,并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陈云任第一任书记*《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5日,第1版。。这对于党的纪检监察体制的重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79年3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局的纪律检查机构根据部门的总体人员构成情况做出了相关规定。到1980年1月为止,中央各部门已经建立的或者是正在筹建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数量大约已达应建总数的75%,至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监察体制开始日臻完善。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产生、任务、职权与领导体制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规定。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对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章中有关纪检工作的第43条做出了修改,取消了党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这一规定*《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日,第2版。。由于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党政分开等政治体制改革,党的监察体制也顺应这一趋势,1988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联合下发的暂行规定指出,党员违反党纪的案件需要根据党章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监督对象相关案件由行政监察机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处理。1988年7月,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中央纪委关于逐步撤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纪检组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关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88年8月1日,第1版。。其中规定,撤销党组纪检组以及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少数情况下可以保留纪委。与此同时,中央纪委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中规定“案件检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组织违犯党的纪律都必须受到追究”。同年,中央纪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报告制度的通知》,这标志着党内监督监察体制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改革开放后,1979年3月,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就国务院各部、委、局成立纪律检查机构问题做出规定之后,国务院各部、委、局相继成立纪律检查机构。但是,这种构建直接导致了党政、职能权限划分不清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以及工作全方位的展开。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相违背,因而,行政监察体制的恢复和重建势在必行。1983年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第91条的相关规定,成立的审计机关是改革开放后行政监察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革,使各级审计机关实现了从无到有。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做出了设立监察部的决定,由此,国家行政监察体制得到恢复和确立。1987年,监察部正式成立,尉健行任监察部部长。1988年,经国务院机构改革,监察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委之一。根据《设立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国家行政监察机关负有监督被监察对象是否贯彻实施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监督处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受理个人或单位对违反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受理监察对象不服纪律处分的申诉等职责。由于考虑到中央纪委和监察部两个机构的职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叠,1993年,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实行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监察部仍下属于国务院[2]。为了促进预防腐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00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随之各地方预防腐败局也相继成立。201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进行内设机构改革,将预防腐败局和外事局整合为国际合作局[2]。
改革开放后,司法监察体制的恢复和重建也很快被提上日程。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再一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司法监察体制内的权威地位以及其法律效力,使得司法监察机关的工作尽快步入了正轨,此外,在会议上同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起到了如虎添翼的效果——赋予了司法监察机构以立案侦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8条、第184条以及第二编第二章第十一节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有关规定。。有了法律所赋予的“尖锐武器”,司法监察机构更具权威。为推进司法监察体制的进一步完善,1995年11月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同年,全国地方各级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相继成立。2005年5月应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查机构统一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
二、国家监察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2016年12月26日起,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展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重构的开始,是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的一次重大革新,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对原有体制的一系列创新和突破,这预示着国家监察体制在未来的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一)国家监察资源整合
目前,就当前的国家监察体制来讲,我国的监察资源力量相对分散,正如第一部分中所论述的,目前的国家监察资源力量包括来自党内纪委系统的监察资源,政府的行政监察资源,所属司法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系统与反渎职侵权系统,以及政府系统的预防腐败局和司法系统检察机关内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这两大腐败预防系统,同时还包括政府系统的审计机关。在监察资源力量比较分散的情况下,监督的范围和对象也是无法达到完全覆盖的,纪委所能监督的对象只有中共党员,行政监察部门所能监督的只有行政机关及公务员,虽然反贪污贿赂部门及反渎职侵权部门可以监督所有的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但是也只能监督其职务犯罪行为而非一般性违法违纪行为[4]。而《方案》中“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及所辖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5]。这显然预示着国家监察体制在未来发展中实现资源整合的新趋势。王岐山在北京、山西、浙江就监察体制改革工作调研时曾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力度,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监察力量,从而实现监察委员会与纪委的合署办公,使监察工作覆盖全体公职人员[6]。通过整合国家监察资源,推进监察委员会体制,与纪委的合署办公,即可实现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一般违法违纪行为乃至职务犯罪行为的“全面覆盖”。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不同监察机关的资源浪费以及“重复工作”等障碍,实现监察工作上的协调,信息的共享,增强工作“有效性”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国家监察范围扩大
《方案》中提出,要扩大监察所覆盖的范围,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覆盖。我国监察机关当前的监察范围仅限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并没有覆盖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协机关等。也就是说,《方案》中要全面覆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仅仅只有公务员,如此说来,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范围将会扩大至履行公共职务、行使公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监察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部纳入监察范围,避免了国家监察工作领域的盲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监察权力的权威,对整个公权力机关起到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以求达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另外,更有学者提出,根据发达国家反腐败的经验来看,应把私营机构纳入国家监察体制的范围之中,加强对私营机构腐败的预防以及打击。
(三)国家监察手段的完善
当前我国行政监察体制的手段只有检察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而且行政监察的行使范围仅限于行政违法,但并未包含刑事违法,也并未被赋予刑事侦查权。因而可以说,现行的行政检察体制的监察手段的效力和种类相对来说十分的单一且有限。而设立监察委员会,将我国相对分散的监察资源力量进行了整合,将行政监察机关及预防腐败局,以及司法监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反失职渎职等部门整合在一起以后,也就意味着对这些部门的职权也进行了一次整合。相对于现行的行政检察体制来说,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手段更为丰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专门针对职务犯罪的刑事侦查权,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手段及措施,与此同时,同样丰富了来自所整合的其他部门相应的职权及手段,对于国家监察机关来说,相对现行监察手段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丰富。此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伴随着国家监察资源力量的整合,监察手段也实现了汇总,在未来也存在着进一步的派生和丰富的趋势。
(四)国家监察职权增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赋予了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和处置三项职责。而现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包括检察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与行政处分权相比,可以说处置权的效力更高,更具强制性,根据《决定》中的相关规定,我们也不难得出处置职权主要可以用在以下的两种情况:对于已构成职务违法但并未构成职务犯罪者,做出相应的处置决定;对于涉嫌构成职务犯罪者,则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一点,与现行行政检察体制中的行政处分权相比,无疑是国家监察职权增强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监察委员会有权监督监察公职人员能否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并考察其道德操守,显然比现行监察职权所涉及的范围要更广,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监察除了包含现行监督体制中的方面外,增加了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情况的监督,加强道德操守方面的监督,就等同于将腐败的思想和意图扼杀在摇篮里,以达到从根部防范和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反思与启示
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式进入试点的新阶段,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重构的开始,是对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全局的一次重大改革。通过回顾与反思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并进一步分析国家监察体制在现阶段所表现出的发展趋势,对于接下来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重任总结出以下四点启示。
(一)加强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和制约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呈现出监察范围扩大、监察手段丰富、监察职权增强的趋势,也就是说,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相对之前行政监察机关来说更强更大的监察权力。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7],对于拥有了更大的监察权的监察委员会来说也算是面临着一种来自权力诱惑的挑战,因此,正如《方案》中明确指出的“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在监察权力进一步强大的同时,对于监察权的行使加强监督和制约就显得刻不容缓。首先,《决定》中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受他们监督[5]4。因此,必须通过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巩固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其次,应加强专门的立法工作,对于改革后的监察体制配备相应的法律支撑,以在法律层面监督和制约权力。再次,其他国家机关也有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应进一步培养其他国家机关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意识,从而达到一定的威慑效果,以防止增强了的监察权的滥用。最后,监察权也应对外接受以人民群众监督为代表的外部监督,确立并实施监察权力的外部监督机制同样意义重大。
(二)从制度层面确保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不难得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是保障监察权力得以有效发挥的最基本前提这一结论。若监察权不具有独立性,则监察权力就无法独立发挥应有的效力。根据《决定》可知,监察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并对他们负责。与现行监察体制相比,监察机关将不再隶属于行政系统,监察权将独立于行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监察机关完全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关,监察权完全独立于所有的权力。而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讨论的,无法保证监察权的独立性,也就难以保障监察权力的有效发挥,因而,若国家能够制定出台相关的制度,来确保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性,使之不受多方因素的干扰和制约,那么,监察权力的行使也可以被保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说,如果能够从制度层面来确保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那么监察机关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效力。
(三)促进合署办公模式下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
《方案》中明确指出,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从当前合署办公模式的实际运行来看,在当前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模式下,处理好两个具有不同的编制及不同的职责,但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却十分相近的党政机构的工作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党政型合署办公[8]。在此种模式下,纪委和监察委员会二者在机构与职能上的合署办公,虽然使得之前相对分散的监察资源力量得以整合,但是,合署办公后的纪委和监察委员会所负责的工作之间还是存在着十分清楚的界限。总体说来,纪委主要负责的还是党内监督的工作,监察委员会主要还是负责在法律范围内的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监督监察工作。实质上也就是纪委与监督委员会二者执纪执法的衔接问题,纪委所执行的是党的纪律,而监督委员会所执行的是国家法律,所以说,在合署办公模式下,必然要使党内纪律与同一领域的国家法律相适应方有可能实现二者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
(四)加强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合理内核的学习和借鉴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可谓是源远流长,起源和萌芽于先秦时期,确立和健全于秦汉时期,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与变革,宋元时期得到完善和强化,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成熟、完备的中国古代监察体系。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直到今天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内核。首先,其垂直领导体制使其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从而相对独立地行使监督权。而监察权力行使的独立性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和追求的。其次,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监察机构专门化的特征,这就使得在行使监督权力时可以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强监督权力行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于提高我们监察工作的效率和成效,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再次,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手段丰富,既体现在监察主体上,又体现在监察的形式上,甚至在时间地点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从而很容易在监督范围、时间、地点上实现全覆盖,避免了监督的死角和盲区,这对于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在国家监察体制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丰富监察手段、增强监督效力等方面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重视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任用和监督。我国的纪检监察人员是行使国家监察权力的主体,是国家监察工作进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所以,我国古代监察体制中,对监察官员的“谨选慎用”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对纪检监察人员的任用和管理、打造一支有担当、有质量的纪检监察队伍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我们回顾这几十年来国家监察体制的演进历程,尝试分析并预测出国家监察体制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有监察资源力量整合的趋势、监察范围扩大的趋势、监察手段丰富的趋势、监察职权增强的趋势;我们反思这几十年来国家监察体制演进过程中的得与失,得到启发并尝试提出了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要加强对监察权行使的监督和制约,要从制度层面确保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要促进合署办公模式下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要加强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合理内核的学习和借鉴。
[1] 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1408.
[2] 洪宇,任建明.国家监察体制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方向[J].理论视野,2017,(7):61-66.
[3] 实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EB/OL].(2017-10-18)[2017-09-10].http://www.81.cn/dblj/2017-10/18/content_7793743.htm
[4] 宋小海,孙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初步研究[J].观察与思考,2017,(2):87-92.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J].中国人大,2017,(1).
[6] 王岐山在北京、山西、浙江调研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EB/OL].(2016-11-25)[2017-09-10].http://sx.people.com.cn/n2/2016/1126/c189130-29370929.html
[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4.
[8] 徐理响.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合署办公体制探析——以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例[J].求索,2015,(8):9-13.
栾超.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监察体制的嬗变与启示[J].知与行,2017,(11):15-19.
2017-09-15
栾超(1992-),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
D922.11
A
1000-8284(2017)11-0015-05
〔责任编辑:崔家善 陈奕诺〕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