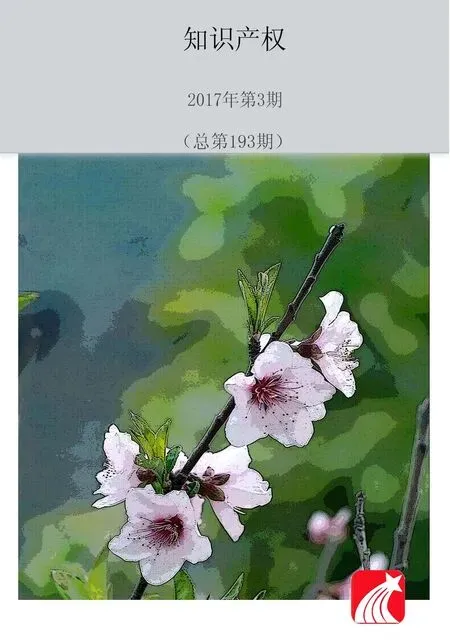网络著作权边界问题探析
孙昊亮
网络著作权边界问题探析
孙昊亮
著作权的边界问题是著作权制度最本质和基础性的问题。在传统自然权利理论的基础上,著作权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网络环境下,应将著作权置于权利能够和应该实现的范畴之内,把传统理论上认为属于创作者而被限制的权利划归回其应属的“公共领域”之中。基于功利主义和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石,将著作权界定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定商业利益分享权,是著作权的本质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制度的重新构建,有利于解决网络环境下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著作权以外的制度模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网络环境 著作权 边界
一、问题的提出
(一)网络环境下著作权边界问题的提出
网络作为新技术的代表,在各个领域对法律造成冲击。在网络时代,网络引发的各种新型法律问题不断涌现。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法律界依旧习惯性地用传统的制度和学说框架去应对新现象,不仅无法对社会现实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还可能阻碍互联网这一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害于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治理手段的创新。”①王利明:《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第110页。因此,讨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是法律制度适应网络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网络时代,或者说一个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著作权边界问题始终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从印刷机到数字点播机,每当著作权遭遇某种新技术时,都向立法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扩张著作权从而作者与出版商能够获得作品在市场上的全部价值;或者,抑制著作权,人们在此情况下就能免费使用作品的复制件。”②[美]保罗•戈斯汀著:《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这是一场社会公众与出版商、作者之间的博弈,双方的诉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权利人的利益应当得到尊重,而著作权像其他民事权利一样也不能没有边界。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完全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自由不能没有限制,权利也当如此。”③王轶、董文军:《论国家利益——兼论我国民法典中民事权利的边界》,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68页。因此,本文认为,著作权的边界问题理应是著作权制度最本质和基础性的问题。
三百多年以来著作权的边界始终像一场“拉锯战”,著作权扩张主义者认为,剥夺作者就其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以及允许后来者不劳而获,都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往往被披上“自然权利”的外衣,成为“天赋人权”的一部分,在“私权神圣”的观念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而另一些著作权低水平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为什么作者应当获得比他们伏案写作所必需之金额更多的金钱?超过这一必需金额的,就是一种意外所得(windfall),更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以低价方式让读者分享。任何作者无一例外地从早期作者以及传统中获取材料;既然前期作者都从他人那儿借用,就应当将其所得的一部分与后代作者共享。④[美]保罗•戈斯汀著:《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著作权低水平保护主义者往往以“激励理论”为基础,而且更加关注公共的利益。双方的“拉锯战”总是各有胜负,而“折衷主义”在立法和司法中更多地被派上了用场。然而,在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解决的时候,新信息技术的出现又使双方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在网络时代里,我们能够找到一条不受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影响的著作权边界吗?而这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边界呢?
(二)著作权的边界与著作权的限制
著作权的边界与著作权的限制有关,但并非同一内涵的问题。本文认为,著作权的限制是以作者对作品所享有的完全的“控制权”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著作权限制理论在于,首先承认作者对于作品享有全部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将一部分本属于作者的权利“限制”起来。所以,著作权限制理论的前提是自然权利理论,认为著作权是不受制定法约束的、不可废除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作者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是作者个人享有不与其他人分享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在著作权立法之初,所追求的是一种神圣的独占的绝对的新权利。
在近代著作权立法之初,并未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加以规定,作者对作品享有绝对的私权。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在实现其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作者及其他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等多重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各种可能相互冲突的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平衡精神的确立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被自然法权利的神圣光圈所笼罩的近代著作权法,在其初创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平衡各种主体利益的基本规范。⑤吴汉东著:《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0页。所以,从著作权法诞生的历史和理论基础的角度而言,著作权制度就是在绝对私权的基础上为平衡各方利益而加入了若干权利限制。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立法中都有著作权限制的规定⑥大陆法系国家多数在法律中专门规定对著作权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权利的限制”的方式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而与美国有显著差异。《美国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fair use),指的是根据四个因素灵活地在个案中认定未经许可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侵权。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不存在真正的“合理使用”,只存在“权利的限制”,但目前学术界和司法界均习惯于将我国的“权利限制”称为“合理使用”。参见王迁:《发达国家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2期,第62页。,以此可以反推出所谓著作权的限制是以绝对的私权为前提的。
然而,本文认为,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前提就存在问题。首先,著作权是否是自然权利,作者应否对作品享有绝对的垄断权是值得怀疑的,即使这种绝对的垄断权附加了众多的限制;其次,著作权是带有公共属性的私权,它的公共性导致了其作为一种私权不同于物权等绝对的私权,必须注意它的公共属性;第三,著作权不是以创作而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印刷术这种商业化传播方式的兴起是著作权诞生的前提,而无论作者在著作权体系中处于什么样重要的地位,“传播商”之间的博弈始终是著作权制度建立和变革的内在动力。
(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边界问题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著作权的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本文试图从另一种角度思考和认识著作权制度,将著作权置于其权利能够和应该实现的范畴之内,把传统理论上认为属于创作者而被限制的权利划归回其应属的“公共领域”之中,重新划定著作权的边界。虽然划定不属于著作权的范畴与对这部分权利进行限制,从实际效果而言没有区别,但是这样做具有相当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而言,使著作权回归到“商业传播利益分享权”的理性轨道上,否定著作权乃至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其期限性、公共文化性才能得到更好的确认和体现;其次,从实践角度而言,随着网络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品传播方式可能出现,确定著作权的边界就能够更加容易地判定新的作品传播方式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从而防止有关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律规定过于僵化而引发的法律真空。
著作权的权利范围并不是如自然权利者所鼓吹的那样,作者因为创作而享有了对作品的复制等权利,再从这样的“权利大厦”划出所谓的权利限制。而事实上著作权的权利范围被无限制地放大了,我们有必要让它回到应有的范围之内,寻找到它真正的边界。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改革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以使其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现实主义路径。”⑦王太平:《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88页。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不断地扩张,用于解释制定法的“宽授权、窄除外”规则在他人游说立法者通过新型的知识产权时也非常明显。与增加一种例外或者拓宽既有的例外制度相比,拓宽既有的权利、减少知识产权授权中的例外情况证明起来要容易得多。⑧David Vaver著,李雨峰译:《知识产权的危机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第95页。因此,著作权从最初的“复制权”,跟随着技术的发展变成了今天庞大而复杂的权利体系。这种权利体系不但无法从理论上自圆其说,而且抑制了公共文化权利等公共利益,著作权制度的过度扩张越来越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这一切都来源于对著作权边界的认识不清。因此,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明确著作权的边界,否则私权的扩张必然压缩公共领域的空间,损害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
二、网络技术对著作权边界的影响
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但使作品传播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使传统著作权的边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由“网络搜索”、“数字图书馆”、“技术措施”、“P2P技术”、“视频分享网站”等引发的著作权问题。这些问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虽然国内外学者纷纷从国际公约、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等多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论述,但是,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甚至网络著作权的无序状态愈演愈烈,盗版现象丛生。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新的传播方式不断涌现,网络著作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而尖锐。
针对知识产权制度所面临的新技术的冲击,学者观点不一。有学者主张继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有人主张改革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少数极端的学者主张废除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⑨参见[荷]约斯特·斯密尔斯、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著:《抛弃版权:文化产业的未来》,刘金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澳]彼得·达沃豪斯、约翰·布雷斯韦特著:《信息封建主义》,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David Vaver著,李雨峰译:《知识产权的危机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王太平:《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高富平:《寻求数字时代的版权法生存法则》,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2期;熊琦:《互联网产业驱动下的著作权规则变革》,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等等。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废以及强化或者弱化,都必须从社会发展进步的层次上去考虑,单纯以某些国家或群体的诉求为导向的权利正当性理由都是不恰当的。通过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从各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寻找著作权的边界是一条可行之路。
可以说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传统著作权边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时我们应当寻找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以及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传统的模拟复制环境下,为什么著作权边界制度可以维系,主要原因在于复制的高成本和低保真性,使大多数人乐于选择载体商品(如书籍、唱片)。传统的以控制传播为主要手段的著作权边界制度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然而在网络环境下,低成本的作品传播成为可能,作品得以非商业性的广泛传播,这种情况下仍然延用传统领域的著作权边界制度,显然不能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
在作品传播渠道被垄断的传统领域,作者的作品传播完全掌控在文化寡头企业手中。作者和表演者要想传播作品都要受到文化寡头企业的垄断,更何况获得著作权报酬了。这种所谓的报酬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比如,对绝大多数作者而言,要想出版一部自己的作品,不但要交纳书籍印刷费这样的正当费用,还要交所谓的“书号费”,更不要奢求获取著作权收益了。网络时代打破了这种传播垄断,但是文化寡头企业又欲利用所谓的著作权阻碍作品的自由传播。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作者和读者重新回到他们所设计的“作者—商业传播者—读者”的轨道上来。因为网络实现了“作者—读者”的作品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将抛弃商业传播者这个利益集团。他们要么高呼网络侵权损害他们的利益,要么想要在网络上也建立起一套以商业传播为主导的作品传播模式。这一切都要以著作权的强化保护为前提,所以在三百多年后,著作权再次成为商业传播者建立利益获取模式的工具。其他作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种模式中被忽略了,而他们却并没有为其利益诉求的代表者,这种情况下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遭到损害,著作权制度鼓励作品创作和促进文化繁荣的目标也无法实现。
著作权不同于以占有为基础的物权,在网络环境中权利难以实现。比如,一首歌曲的广泛传播,即使再强有力的著作权保护,在网络环境下也很难奏效。网络的发展使“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的范围大大改变,如QQ聊天、电子邮件、MSN等通讯工具都可以瞬间将作品传播给很多人。那么,是否因此而改变了这些行为“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的性质呢?本文认为,尽管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实质上通过网络而实现的仍然是“个人学习、研究、欣赏”的目的,所以这一传统领域内的合理使用条款也应当适用于网络环境中。网络技术使传统著作权边界制度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建构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边界。
传统意义上认为著作权属于文学产权,区别于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实际上,本文认为,著作权从本质上说是“市场”内的权利,脱离了“市场”,著作权即使存在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传统领域中,这一点并不突显的原因是作品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复制传播和单向的信息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都是商业经营者在“市场”中完成的。而人们不进入“市场”的日常作品传播,由于传播手段的局限性,只在个人、家庭等范围内进行,所以很容易通过对个人行为规定例外来进行区分。但在网络环境下,个人之间的作品传播也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这就使公共传播与个人传播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本文认为,以公共传播与个人传播来区分著作权的边界是不科学的,应该以“商业传播”与“非商业传播”来区分。
传统的著作权领域,由于一切作品传播都需要有作为载体的商品,所以作品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且,正因如此,自由表达如果不能得到出版商的青睐或公权力的支持,则必然难以广泛传播。因此,作者创作的三个动力似乎被商业利益这一种动力所吸纳。⑩这三个动力指的是“公权力支持”、“表达自由”和“商业利益”。导致了著作权制度作为作品创作激励而一统天下的局面。网络使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首先,自由表达的低成本传播成为可能;其次,商品媒介物的传播方式被电子信息的无形物传播方式所取代。三种作品创作动力在网络上展现出来,一方面,政府为主导的数字图书馆等官方信息库等建立起来,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使公众可以低成本地接受文化教育;另一方面,贴吧、博客等自由表达的平台大量涌现,大多数网民只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非为了著作权而创作作品。这是网络带给著作权制度的最大冲击。
三、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是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产权
虽然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但是始终被区别于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传统理论认为,著作权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文学产权,它是基于作者对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适用于所有作品使用的领域。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与文化产业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本文认为,作品具有文化本位性,作品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领域应该被分为两个范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范畴互相区别,而又相互融通,没有绝对的界限。文化事业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文化产业以商业利益为核心。文化事业又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科学文化和民间文化,所谓的政治文化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国家统治、教化人民而形成的文化;所谓科学文化是人类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所谓民间文化则是人在自由表达其思想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文化的不同性质和范畴,决定了作品的不同性质和范畴。例如,一部电影或者网络游戏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以商业利益为核心,要求其担负起维护政治稳定、国家统治、教化人民的重任是不可能的1当然,不排除电影和网络游戏可以寓教于乐,比如革命题材的电影和传统文化题材的网络游戏等,而且电影内容也会受到审查,不能危害到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但商业利益永远是文化产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反之,一部学术论文或者专著很难有财产性利益。2当然,少数畅销的学术论文或者专著可能也获益不菲,但是绝大多数学术著作由于受众有限,无法获得商业上的回报。
从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和形成等方面而言,实际上都是发达国家追逐自己利益的产物。专利如此,商标如此,著作权也一样。不同的是专利、商标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工业产权,是与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表现得更为明显。工商业发达的欧美国家是专利、商标保护制度的倡导者,自然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但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似乎更多地以保护作者的名义出现,似乎是作者创作所应获得的回报,不论经济发达与否,作为“自然权利”应当平等地属于每一个创作者。但事实是,著作权实际上是文化产业的产物,著作权制度的设计与文化商品的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为文化产业发达的欧美国家量身定做的。未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作品,即使赋予其著作权,其法律意义不大,毕竟财产权是著作权的核心权利,文化产业以外的文化传播显然产生不了财产利益,这样的权利除了阻碍作品传播之外没有任何用处。
不但如此,著作权的过度扩张对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文化市场的多元性正逐渐伴随着文化寡头的垄断而丧失,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大众意识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成千上万的艺术工作者在艺术创作和表演领域冲锋陷阵,日复一日地创作出多样的艺术作品。但由于文化企业巨头及其文化产品的市场支配地位,文化多样性——虽然我们难以觉察到它的存在——就要在大众视野和公众的共同意识中消失殆尽。3[荷]约斯特•斯密尔斯、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著:《抛弃版权:文化产业的未来》,刘金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3页。著作权在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著作权是适应文化产业发展而建构起来的制度,它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保护文化产业投资人的利益。但是,却挤占了非商业目的自由创作人的创作空间,形成了垄断的文化产品市场,左右着大众文化消费的取向。
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包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争鸣的公共领域,创建大众拥有制作发行资源的文化市场。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作品的著作权而破坏文化,正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树木的私权而破坏环境一样。木材商的权利固然应该受到保护,但当它影响到公共利益,比如生态环境的时候,就应当受到限制。作品与文化的关系,犹如树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树木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是私权,而文化涉及公共利益,属于公共领域。
现在的著作权制度其实是文化企业的著作权制度,广大的作者除了有极少数“幸运”地成为文化产品中的一环而享有极少一部分利益以外,绝大多数作者和绝大多数的利益都被文化企业所攫取。而社会公众的文化消费却被文化企业所控制,文化企业可以决定哪些作品能大量面世,哪些只能零散出现。而作品传播过程中,对作品的收听、阅读和观看使其内容渗透到我们的意识当中,改变着我们的思想。
思想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思想的表达是人性的一部分,抑制表达就意味着抑制了人性。我们不但可以原创式的表达,复制式的表达也是我们表达的形式之一。如果复制式的表达仅仅是为了表达,而不是为了追求任何商业利益,在不影响他人商业利益实现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归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著作权保护不仅仅是一种私权保护,同时也包括了内容审查。著作权起源于16世纪的出版印刷专营权,这种专营权是一种类似著作权的垄断所有权,它保护创作者和出版印刷者的同时,也可以借此阻止异教学说的传播并扼杀质疑其合法性的观点。国外的学者也认为:“企业把著作权当宝是为了保护投资。”1[荷]约斯特•斯密尔斯、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著:《抛弃版权:文化产业的未来》,刘金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4、10页。本文认为,投资是文化产业中的行为,在绝大多数作品创作过程中是不存在“投资”的,即使有创作的成本,那也是为了表达的需求,为了表达而创作的作者从来都不会想到收回“成本”,所以即使有所投入也不属于投资。由此可以看出,著作权是文化产业的要素,它与普通作者及文化产业以外的领域毫无关系。
著作权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而言,都是文化产业的产物。2尽管在三百多年前,著作权制度诞生的时候并没有“文化产业”这样的称谓,但出版商的大规模书籍印刷发行从现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而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产业”的出现。打着保护作者旗号横行三百多年的著作权制度,应当回归到它应在的位置上。如果没有著作权,那么出版商就无法阻止其他竞争者的进入,国家也无法在“出版专营权”结束之后,维持对出版物的审查,以控制言论、维护统治。著作权对作者而言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呕心沥血的作者无非是他人利益实现的工具而已。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1525年出版的小册子《对印刷商的警告》中揭露了某些印刷商盗用他的手稿,指责这些印刷商的行为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毫无二致。这被广泛认为是作者权利意识觉醒的最著名的标志。但是,本文认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丁•路德所指责的那些所谓“强盗”,就是盗印其手稿的出版商,也就是将作品商品化生产的商业利益追逐者。所以,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并非著作权之私权,而是作品商品化过程中的“商业利益分享权”。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说,人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为商品,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满足,精神需求日益增长。而现在的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庞大机器。因此,著作权制度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英国政府意识到的,将国家、地区或城市文化变成实业能够在日后得到不菲的收益。要想获得这些收益,就必须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制度。不论怎样,这将促使当地政府严格地执行涉及著作权类的政策。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根本看不到著作权保护文化产业有什么不好,即使著作权仅仅是为了保护文化产业的投资,那么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保护投资者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们忽视了作品除了可以成为文化产业中的生产要素之外,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社会价值。在整个著作权制度中,社会价值、公共利益被压缩到了不能再小的空间,我们谈论的著作权仅仅与好莱坞、四大唱片公司以及少数大型出版社相关。而著作权这种私权一定程度上却窒息了文化的自由创作和传播。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抛弃著作权制度,毕竟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社会需求的一种表现,我们是想将著作权回归到它本应有的范围中,寻找到它理应有的边界。
既然著作权制度是保护作品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分析作品创作的动机或者说动力。许多学者认为,著作权制度激励了作者的创作,论说著作权制度产出功能的文献不可胜数,并形成了专门的学说,即著作权激励理论。依此理论,作者为了获得著作权而创作了作品,更准确地说,作者因为著作之财产权而创作了作品。事实上,笔者认为,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大量作品的作者根本不是因为著作权而创作了作品。这根本无需赘述,人类的作品创作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优秀的作品不计其数,而著作权制度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作品作者也根本不是为了著作财产权而创作作品。本文认为,作者创作作品的动力无非有三:一是著作权激励,即财产权;二是公权力,即代表国家社会的利益;三是自由表达的需求,即人的表达本性。
本文认为,著作权与作品的性质密切关联,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畅销书等文化产业的“文化商品”是著作权保护的主要对象。从现实中的著作权案件就可以看出,网络著作权的保护要么针对流行歌曲,如百度搜索案;要么针对影视作品,如优酷、土豆网案;要么针对畅销书,如贾平凹《古炉》案,这些都是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商品”。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著作权制度既是文化产业的催生者,也是为文化产业保驾护航而诞生的制度,它不是也从来都不是为普通作者的利益而存在的。
著作权制度通过对作品赋予私权,使作品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一部分,便于其参与到市场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所以著作权制度的诞生就是伴随文化产业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市场的寡头在不断高呼着其作品的利益被侵犯的同时,花费着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资金拍摄一部影片,耗资数百万包装一位歌手。而一部影片的票房也在一片著作权侵权严重的惊呼中屡创新高,一位歌手的出场费也高达数十万,畅销书的收益也以千万计。这些现象都表明,著作权随着新技术的扩张除了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寡头们创造更多的利润之外,再无一用。而这种文化产业的过度繁华却往往导致了文化事业的衰微,因为著作权制度解决的只能是保护文化产业投资的问题,对于文化事业的促进并不能起到主要的作用。
四、网络环境下著作权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商业利益分享权
从以上关于著作权是文化产业领域的文化产权的结论可以推导出,一向被赋予激励作品创作重任的著作权制度,实际上只是与文化产业相关。在文化事业领域,除非有文化产业的介入1比如,出版产业可能介入到学术著作的出版中;网络服务商可能介入到公众的自由表达之中。,否则与著作权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著作权制度其实是一种作品传播商业利益的分享权,从著作权制度诞生一开始就是这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赋予作品作者著作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它的商业价值,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决定某一作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如果这个作品具有商业价值,那么,著作权的目的就是让该价值落入著作权所有人的腰包。而之所以这种商业利益通过赋予著作权这一私权来实现,主要原因是,只有这样商业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通过著作权这种私权,著作权人可以对自己作品的传播作出最为经济的或者说利益最大化的安排,比如:电影的权利人可以首先通过影院的放映吸引对影片最感兴趣、最乐意花大价钱先睹为快的观众,影院放映的票价往往是非常高昂的;然后通过发行DVD等数字放映产品,吸引对影片比较感兴趣的观众;最后,通过网络点播、电视台播放等方式实现影片的所谓“残值”。这种精巧地安排只有通过私权才能得到实现。所以,著作权被赋予私权的目的不是它应该被创作者所私有,而是一种为了实现其商业利益分享权而选择的最佳方式。
创作者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复制其作品,这与权利人拥有一个“羊腿”看上去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却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著作权并非对一只羊腿之类的有体财产给予保护。著作权所保护的是人的思想表达,思想表达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种捉摸不定的“财产”还真是难以确定其界线。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大法官就曾经评论过这一特征:“相比其他各类在法庭上争论的案件,著作权更加接近于所谓的法律的形而上学,其特性是,至少看起来可能是如此的微妙与精巧,并且有时几乎是转瞬即逝的。”2[美]保罗•戈斯汀著译:《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著作权的边界远比物权边界复杂和微妙,这一方面是其无形性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其本质认识不清,将著作权的范围划得过大,导致将公共领域的部分也包括其中,而遇到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时,不得不一一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但难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著作权这张权利之网上凿出无数个“限制与例外”的小洞,最终使著作权这张大网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事实上,著作权之网远没有那么大,它只是作品传播商业利益的分享权。没有传播就没有著作权,没有商业利益也就没有著作权,这就是所谓的“无传播则无利益,无利益则无权利”,传播与利益始终是著作权的核心价值。个人对作品的学习、研究和欣赏本来就与商业传播利益无关,所以根本谈不上权利,当然也更谈不上权利的限制。
此外,判定著作权侵权的规则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是一张由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错综交织的网。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本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其区分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如果把知识产权看成一种补贴——整个社会主动提供给某个部门的经济利益,以酬谢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更大利益——那么,几乎无人质疑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不断的检讨,以确保它能很好地发挥作用。”1David Vaver著,李雨峰译:《知识产权的危机与出路》,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第96页。
一个在非商业领域传播,或者并未导致作品商业使用利益减损的传播不构成著作权侵权。这不是因为著作权的所谓“权利限制”,而是它根本就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范畴,因为著作权实际上是一种作品传播商业利益的分享权,作品的非商业传播是一种纯公益的传播,是社会公共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涉及到侵权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应当恢复著作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出于非赢利目的的分享、传播或使用应属合法,因为这种合理使用有益于社会。而且,禁止倾销文化产品也是建立规范化市场的方案之一。不可否认,如果市场营销费用超过一部普通好莱坞影片制作费用的一半,那么这将不利于竞争。因为谁也敌不过这样的市场推广力度。2[荷]约斯特•斯密尔斯、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著:《抛弃版权:文化产业的未来》,刘金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9、51页。著作权所有人已经开始放弃著作权体制,逐渐转向契约形式,在产品赞助的基础上利用广告牟利。
《抛弃版权》一书中记述了这样的例子,作家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允许读者从他的个人网站免费下载小说,他不认为这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同时,可能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以及其他主流媒介销量很大。多克托罗甚至不在意发展中国家的读者盗印他的书卖钱。当然这也许只是个例,并不一定所有作家这样做都能获得相同的结果。但通过无偿提供作品的内容与忠实的读者建立纽带联系,是文化传播甚至文化产业的基本原则。在音乐领域,情况也一样,乐迷去听演唱会才是音乐人及其制作方赢利的模式之一。
本文并非反著作权主义者,所以并不认为没有著作权各方的利益也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但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在某些领域内,无须征得许可的作品自由流通,不但对作品的收益无害,甚至有益。比如,新的歌曲会免费由广播电台播放进行“打榜”等推广活动;而在电视台,特别是具有很强影响力的电视台或电视节目中推出自己的作品,则几乎成为每一个作者和表演者梦寐以求的事情。3比如,在中国,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已经成为了每一个作品创作者和表演者的梦想。除了极少数如陈佩斯这样的法律的执着守卫者以外,不会有人想到自己还享有著作权。这种状况不但是由于作者、表演者与强势媒体之间的力量悬殊,还因为在诸如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影响力强的媒体中传播自己的作品与表演可以更好地和公众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有利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然也包括精神利益。所以,本文认为,既然一个作者或表演者并不担心作品在广播或者电视中的广泛传播,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对网络中的非商业传播“斤斤计较”呢?毕竟事实是如果能够被社会公众非商业性传播的作品,往往是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同时已经获得一定收益的作品,这种非商业性的传播可以进一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并最终通过其他获利渠道获得更高的利润。
也许有人会问,这一点难道著作权人自己不知道吗?他们可以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里一样安排自己的权利,无须法律人多此一举。这也许是对的,在传统领域中。因为传统领域中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少数垄断性的文化传播团体,作者和表演者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约定权利的使用。即使是陈偑斯那样的案件也极少发生,因为中央电视台可以通过格式合同将作者和表演者的所谓著作权剥夺得“体无完肤”,当然这也是权利人所自愿的。但是在网络环境下情况却完全不同了,权利人无法通过契约的方式许可亿万网民使用他们的作品,而网民也被迫背上了“盗版”、“小偷”甚至“罪犯”的恶名。虽然他们事实上没有被“绳之以法”,但是造成的各种不利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律被亵渎,人们从此不再信仰法律,并形成了反版权的社会规范4参见孙昊亮:《网络反版权社会规范之反思》,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11期。;其次,社会公众会养成一种践踏法律的习惯,他们在其他场合也会以身试法;第三,使用应当付费的作品使用也因此而获得了“庇护”,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只是亿万侵权者之一,而本文认为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的作品传播是应该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的,这是“商业利益分享权”的一部分。
著作权在保护创作者利益的同时也保护公共利益,这在最早的著作权立法中就有体现,如《安娜法》中规定了公共领域。但是,如何实现这种公共利益才是问题的核心。长久以来,学者总是着力于论述通过著作权的限制增加公共领域的范围以保护公共利益,但是,本文认为,首先界定著作权的边界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促进作品创作与传播,繁荣文化的渠道有很多,通过著作权这种私权激励作者创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本文认为,作品所处的领域应当区分为“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事业领域”,通过这种区分界定著作权的边界。
把著作权限定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商业利益分享权,并不会影响文化事业领域作品的产出。事实证明,著作权制度体系以外所建立起来的学术作品共享体系,不但不会损害学术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相反还会更好地实现学术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统计调查表明,通过开放存取出版可以显著提高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通过对119, 924篇公开发表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会议论文的调查发现,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7.03,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2.74。在电子工程学科中,发表于同一期刊中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2.35,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1.56。在数学类论文中,发表于同一期刊中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1.60,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0.84。1刘畅:《开放存取期刊的影响力分析》,载《图书情报工作》2008年第12期。开放存取是指文献在互联网公共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该文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是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作品被准确地接受和引用。2王太平:《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90页。
除了开放存取以外,事实上在网络环境下,文件共享几乎占到互联网流量的一半。这一事实不断提醒我们,网络一代不再全盘接受著作权的老概念。他们把盗版和二次创作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会让老套的知识产权法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也开始明白,向消费者供应优质产品用不着通过著作权控制市场。作家在网络时代不必为了发表作品而接洽出版社,图书的编辑与装帧设计可以由作者亲力亲为。音乐人在最新技术的帮助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录制音乐。总而言之,作品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件事,在网络环境下都可以由作品创作者一人代劳,因为这是一个“万人出版者”的时代。那些从作品中渔利,甚至于压榨作者的商业传播者变得可有可无。其实这才是著作权扩张保护呼声的真正源头。
当然,著作权制度退出后政府应当在文化事业领域投入更多的财力。事实上,著作权制度也很难起到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很多情况下,作品的传播广度或者说盈利水平与其艺术水准并无必然联系,特别是文化日益产业化的今天,一个打工妹或者农民工比经过十几年专业训练的演唱家更受欢迎。受市场追捧的电影也多数是过眼烟云,很难既叫好又叫座。国家应该在“好作品”的产出上增加投入,所谓的“好作品”不但是受人欢迎的,而且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审美水平、弘扬普世的道德、宣传公序良俗。乐团或剧团没有足够资金支付作曲家合理的作曲费用,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政府对此应该慷慨解囊,给予补贴。毕竟作品的推陈出新对于推动艺术发展、教育公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参见[荷]约斯特•斯密尔斯、玛丽克•范•斯海恩德尔著:《抛弃版权:文化产业的未来》,刘金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75页。政府应该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这是政府的责任之一。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产品寓教于乐是公共需求的一部分,理应由政府来承担。
总而言之,学者认为,“无传播则无利益,无利益则无权利。”4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然,这里的权利指的是著作权。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应该是“无商业传播则无商业利益,无商业利益则无权利”。总而言之,著作权的本质属性是商业利益分享权,这在网络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基于功利主义和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石,将著作权界定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法定商业利益分享权,是著作权的本质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制度的重新构建,有利于解决网络环境下出现的各种棘手问题,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著作权以外的制度模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The boundary of copyright is the most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copyright syste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 the boundary of copyright has always been blurring.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we should place the copyright in a category, whereby the right can and should be materialized; returning the right, restricted by authors based on traditional theory, to the public domai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tilitarianism and legality,the copyright in the fi eld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hould be defi ned as the legal right to share commercial interests.Thi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nature of property arising from copyright.It is benefi cial to reconstruct the copyright system and to solve a variety of thorny issue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 by other modes beyond the copyright system.
network environment; copyright; boundary
孙昊亮,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是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著作权制度的应对和变革研究》(15BFX141)和2016年陕西省法学会项目《陕西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法制保障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产业法”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和“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