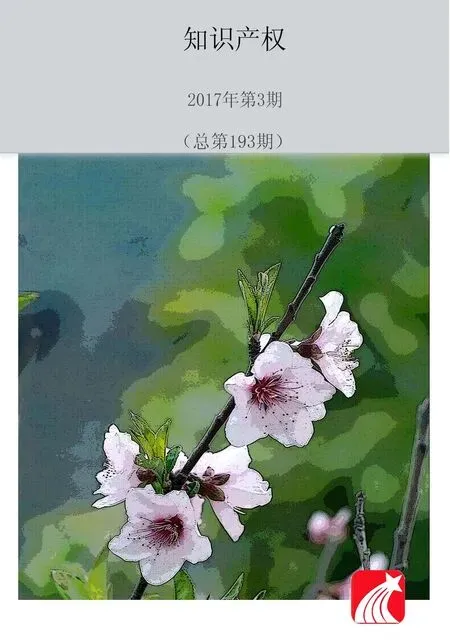角色商品化再论
李阁霞
角色商品化再论
李阁霞
角色商品化包括对知名虚构角色和真实人物人格特征的商品化。对于虚构动漫形象,通常是用版权法的保护模式,但版权法无法提供对角色姓名的单独保护。对于真人以及由真人扮演的虚构角色,无论是现行商标法、民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人格特征的保护都有不逮之处。只要能使相关公众将该特征与该知名角色相关联,对于可商品化的角色特征都应提供保护。从利益平衡角度,角色商品化的保护应当设立一定的期限。构建角色商品化的法律保护模式,应当在民法典中引入形象权来保护自然人以及由自然人扮演的知名角色的人格特征,还应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标法来对形象权所无法涵盖的知名角色特征提供保护。
知名角色 虚构角色 商品化 形象权
引 言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小鲜肉”宁泽涛比赛成绩并不理想,而关于他与国家游泳队因广告代言而产生的矛盾在网络上也传得沸沸扬扬。像知名运动员可以带来商业利益这一点,在现代商业环境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利益无疑是双向的:对于商家而言,利用知名人物的形象,可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从而为其带来普通营销方式难以企及的商业利益;对于知名人物而言,通过自己利用或许可他人利用自己的形象,可以使其个人价值最大化,从而为其带来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也正是因为名人形象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导致这个领域法律问题多多。
首先,对于商家而言,利用知名人物形象虽然可以为其带来不菲的商业利益,但请名人代言成本过高,所以不少商家会想方设法既利用名人的形象,又不支付高昂酬劳,比如将与名人姓名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注册为商标,利用与名人容貌相近的普通人来做代言,利用与名人声音相似度极高的配音演员来为产品做广告等。在这些情况下,所涉名人是否可以主张权利呢?如果可以,主张的权利是什么?又能否得到支持呢?
其次,对于知名人士而言,其因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的形象而获得的利益是否必然归属其个人呢?比如上面提到的宁泽涛等著名运动员,其是否有权支配自己的个人形象呢?另外,如果知名人士是因其扮演的形象而知名,比如六小龄童因其扮演的“孙悟空”而知名,那么,如果别人对其所扮演的“孙悟空”形象加以利用,六小龄童是否可以主张权利呢?
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对于搭名人形象便车的,在我国的商业领域中比比皆是,诉诸公堂的也为数不少,法院的判决却往往大相径庭,尤其是2016年年底的“乔丹”案判决,无论在学界还是商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本文“角色商品化”(character merchandising)一词系采用WIPO国际局于1994年发布的一份题为《角色商品化报告》的提法。①WIPO: “Character Merchandising”, WO/INF/108, 1994.12.实际上在这份文件发布之后,学界也曾掀起过探讨角色商品化的小高潮。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商标法》已经修订了两次,《广告法》修订了一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草案2016年在国务院通过,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而《民法总则(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三次,2017年全国人大将对该草案进行正式审议。但是,从这些法律文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涉及“角色商品化”的规定有多大进展,更不用说彻底解决了。所以商业活动中频频擦边、司法实践中各说各理的现象基本上一如既往。当今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名人形象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以本文认为,“角色商品化”这个“老问题”,还是非常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角色商品化的种类和性质
WIPO《角色商品化报告》将“角色”划分为虚构角色(fictional character)和真实人物(real persons)两类。前者既包括虚构人物,如人猿泰山、詹姆斯•邦德,也包括虚构非人物,如唐老鸭;后者则一般是指影视明星和体育名人等。根据WIPO的报告,所谓“角色商品化”,是指由虚构角色的创作者或真人,或者由其许可的第三方,对某一角色的重要的人格特征,比如姓名、形象或外观等,在商品或者服务上进行利用或者二次开发,使潜在的消费者出于对该角色的喜爱而愿意购买这些商品或接受这类服务。
WIPO的报告根据客体不同,将角色商品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虚构角色商品化”(Merchandising of Fictional Characters),这主要是指针对一些虚构的动漫形象而为的商品化运作;其二为“人格商品化”(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这是指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真实人物的姓名、形象、声音及其他人格特征。能够商品化的真人通常要求其在相关公众中知名,也就是说,商品化其实是知名人士的声誉,所以这种商品化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声誉商品化”(Reputation Merchandising);其三为“形象商品化”(Image Merchandising),这是指使用由真人扮演的虚构影视角色来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广告宣传或营销。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角色商品化时,国内有相当多的文章采用了“角色商品化权”这样一个概念。而实际上就WIPO报告所呈现的内容而言,起码在其报告发布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有“角色商品化权”这个概念;而WIPO的报告也自始至终只用“角色商品化”予以表述,并探讨了因角色商品化带来的利益可以依据什么样的方式予以保护,受益人因此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比如可以根据民法主张“姓名权”保护,根据版权法主张“版权”保护等。也就是说,实际上,WIPO只是将“角色商品化”作为能为角色的创作者或角色本人带来利益的一种现象,而非意在创设某种新的“权利”。况且“商品化”的表述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商品化的东西数不胜数,总不能都叫做“某某商品化权”;另外,商品化的角色或者说客体不同,其牵涉的法律关系也不同,这也很难用某种“权利”笼而统之,所以,“角色商品化权”这种表述是颇值得商榷的。
WIPO报告将角色商品化的第一种类型——“虚构角色商品化”,主要设定为虚构的动漫角色、图画形象,对于这类客体,通常都是通过版权法进行保护。对虚构的动漫形象的商业利用,都绕不开版权的限制,除非该角色(实际上是创作出该角色的作品)的版权保护期届满。当然对于诸如角色的独创性问题,对于由平面到立体或者由立体到平面的复制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在判断上也有争议之处,但也仍然可以在版权法的框架下解决。即便该角色及作品的保护期届满,创作者或继承人或其授权的第三人还可以通过将该角色申请商标注册的方式继续对其提供保护,阻止他人在某些商业领域的商品化运作。所以这种类型的角色商品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带来的问题都不大,本文也不准备对此进行探讨。
实际上虚构角色商品化的客体还涉及一种类型,那就是用文字表述创作出来的虚构角色,比如福尔摩斯、阿Q、令狐冲等。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是可以将角色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的,让读者读完之后立刻就会在脑海中形成该角色的形象和样貌。越是知名的文学作品形象,越是如此。但作者能否因此而阻止其他人未经许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该虚构角色的姓名,或者根据其描述而再现出角色形象呢?金庸先生起诉《此间的少年》作者侵犯版权,诉由就在于被告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原告作品中许多知名虚构角色的姓名。与动漫或者其他用线条、图画勾勒出的形象或角色不同,版权法对美术作品是单独提供保护的,所以在一部作品中呈现出的单独的美术角色,只要满足了独创性的要求,就可以独立保护。但由文字向二维图画或三维模型的复制,目前还很难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其原因大概在于再精确的文字描写,也很难做到在不同维度上的精准的复制,也就很难认定构成对文字版权的侵权;至于虚构角色的名称,更是很难满足版权法对最低程度创造性的要求。
但毫无疑问,文学作品中的虚构角色是确实具有商业价值的,不少商家对此都趋之若鹜。比如鲁迅的后人就曾调查过,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名、地点注册商标的,“阿Q商标共申请23件,祥林嫂商标共申请9件,孔乙己商标共申请31件,其中最多的是咸亨商标,前后提出申请的共有224件。”②《名人打响商标保卫战》,http://news.hexun.com/2014-11-28/170885860.html,2016年8月28日访问。并且,这些商标几乎都已获得核准。既然无法在版权法的框架下解决,而虚构角色的名称或姓名又确实能够带来商业价值,那么,是否应当对其提供保护,以及应当提供何种保护,就是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本文将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商品化的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人格商品化”及“形象商品化”,涉及到真人以及真人扮演的角色的商品化,本文在引言部分提到的一些问题主要就集中在这两种类型中,所以下面将重点探讨这两种类型的角色商品化问题。
二、现行法对角色商品化的保护模式
WIPO报告指出,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采用单独立法(sui generis legislation)的方式来保护角色商品化,我国也是如此。但角色商品化确实与知识产权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经营者对角色的商业利用大多是为了引起消费者注意,通常是作为广告宣传或者商标来使用,并有可能引起消费者对产品来源的混淆或者对产品与角色之间的关联产生误认,这无疑属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畴。除此之外,民法中同样也有涉及到角色商品化的法律规则。
(一)商标法
鉴于在角色商品化中,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他人未经许可,将知名人士或知名角色的相关特质,比如姓名、肖像、形象等注册为商标,所以有必要首先看看商标法对此是否有所禁止。
1.“不良影响”
我国《商标法》第10条列举了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其中第1款第8项是“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司法实践及商标审查实务中,在涉及到角色商品化时,法院或者商标行政管理机构经常引用的正是这一条款。但是,对该条款的运用,实践中非常混乱,由于人们对“有其他不良影响”在理解上并不一致,导致类似的案件往往得出迥异的裁判结果。
比如在“郭晶晶”商标案中,法院认为,郭晶晶是在相关公众中知名度很高的著名跳水运动员,该商标注册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申请商标系经跳水运动员“郭晶晶”授权或者与其存在其他的联系,从而产生误导公众的不良影响,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依法应当不予核准注册。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行初字第382号判决书。而在 “亚平YAPING及图”商标案中,二审法院则认为,争议商标的注册仅仅涉及是否损害邓亚萍本人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属于特定的民事权益,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故不应适用《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0)高行终字第168号行政判决书。
鉴于该款措辞过于模糊,而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又频繁引用这一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不良”影响标准应考虑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由于商标法已经另行规定了救济方式和相应程序,不宜认定其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知名人士或者说公众人物可以以“不良影响”为由主张权利。但在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中,除了坚持以“是否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作为判断“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准外,却又专门指出,“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即属于“其他不良影响”。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司法解释,理由何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一来,意味着一旦成了公众人物,其姓名就变成了攸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事物了,实在是有悖常识。实际上《商标法》第10条的规定,都是关涉“公序良俗”的,司法解释不应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随意对立法本意予以突破。对于使用公众人物姓名作为商标的情形,更宜通过权利冲突予以解决。
2.“在先权利”
《商标法》第32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这里的“在先权利”,在角色商品化领域,主要就是姓名权。
在“易建联Yi Jian Lian”商标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未经许可,在服装等商品上注册与第三人姓名完全相同的争议商标,侵害了第三人的姓名权,违反了《商标法》第31条的规定,该争议商标应予撤销。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708号行政判决书。但是,在沸沸扬扬的“乔丹”系列商标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与两审法院都不认可原告主张的“乔丹”商标侵犯了迈克尔•乔丹的姓名权,理由在于 “乔丹”只是英美普通姓氏,无法证明其确定性指向迈克尔•乔丹,所以原告主张争议商标损害姓名权证据不足。⑥商评字[2014]第052219号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行(知)初字第9171号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037号判决书。
但有意思的是,在“克林顿”商标案中,由“乔丹”案一审法院审结的判决书中则认定:“作为中国公众,其语言习惯呼叫的是外国人的姓氏部分,‘美国总统克林顿’已经为中国公众所熟知,故中国公众在看到‘克林顿’商标时,容易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产生联系。”因而,法院判决支持商评委作出的“容易产生不良影响”的裁决理由。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一中行初字第294号行政判决书。两起案件虽然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不同,但在对“姓名”的认定上,其不同的判断思路却能得出令人讶异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当然,2016年年底,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另外几起涉及“乔丹”商标纠纷案件中,法官的裁判还是回到了 “克林顿”案的思路上,认可迈克尔•乔丹就“乔丹”享有姓名权。⑧(2016)最高法行再27号判决书。
不过,上述分歧起码说明,在以民法上的“姓名权”作为在先权利对抗他人的商标注册方面,还是存在先天的缺陷。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只是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至于姓名指的是真名或者本名,还是也可以为笔名、艺名甚至是绰号,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就上述“乔丹”案和“克林顿”案的判决来看,起码司法实践中就此尚未形成共识,这就为以姓名权为基础对抗他人未经许可的商业使用带来不确定性。
其次,姓名权系人格权,如果姓名权可以作为在先权对抗商标注册的话,意味着任何叫做该姓名的人都可以提出异议,因为在人格权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权利范围因自然人声誉而有所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商标领域能够以姓名权对抗商标注册的,只能是名人。
再次,如果以姓名权作为对抗基础,那么当商标注册人与名人具有相同姓名时,后者就很难通过姓名权对抗商标注册了。因为从法理上很难解释,既然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格权,为什么名人的姓名权就可以排除普通人对姓名权的行使。
最后,对于将著名虚构角色的名称或姓名注册商标或作为商标使用的,显然就更没有办法以“姓名权”对抗了,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著名的虚构角色的姓名或名称,对于创作者或者扮演者而言,是确实能够带来商业价值的人格特征,也是角色商品化的重要内容。
其实无论是知名人物的姓名,还是著名虚构角色的姓名或名称,之所以需要对其提供保护,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并不是出于人格意义上的保护,而是因为这些人格特质具有商业上的价值。以人格权方式来保护这些商业上的财产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入歧途了。
(二)民法
在民法的范畴下,除了上面提到的姓名权之外,与角色商品化有关的还有肖像权、名誉权及隐私权。
1.肖像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100条是关于肖像权的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所以,以肖像权对抗他人对自己肖像的商业化利用是没有问题的。与姓名权一样,作为人格权的肖像权,在保护上并不因主体的知名度不同而有所差别。
但以肖像权保护角色商品化,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难以对不呈现面部特征的角色形象提供保护。如果有人以“刘老根”的形象注册商标或者进行广告宣传,但只显示侧影,面部特征难以分辨,不过穿着打扮可以让相关公众很容易认出这个角色形象,商家利用虚构角色进行商业运作的目的达到了,但权利人却难以主张肖像权的保护。
第二,当真人与扮演的角色形象之间差别太大,甚至难以从面部特征辨认出真人的模样,这时主张肖像权也存在现实的困难。比如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如果有人将这样的孙悟空形象加以商业利用,六小龄童就很难主张肖像权的保护,因为“孙悟空”面容上呈现出来的并非六小龄童本来的肖像。
第三,当有人聘请与知名人士面容非常相近的人做商业推广时,后者也没有办法以肖像权为基础进行对抗。因为模仿者呈现的是自己的面容,所以被模仿的知名人士也就无法以自己的肖像权为基础禁止这种行为。
可见,在角色商品化领域,肖像权能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2.名誉权
《民法通则》第101条关于名誉权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WIPO报告也指出,有国家允许当事人利用名誉权来保护自己的角色商品化权益。但这一主张只有在他人对其形象予以侮辱、诽谤的情形下才能适用。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商品化运作都不会去损害角色或形象的名誉,但是,定位不准确的广告确实会损害知名人士的社会形象。定位精准的社会形象代表的是可商品化的利益,所以他人未经许可的营销行为损害的是知名人士或著名角色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名誉权。
3.隐私权
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关于隐私权的规定,但隐私权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格利益之一,这已经成为共识。所以在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以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发布的《民法总则(草案)》中,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⑨《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第109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但对于公众人物而言,隐私权恰恰是受限的。虽然说普通人也可以用自己的名字、肖像、形象等进行商业经营和商业推广,但这并不是在角色商品化意义上的使用,角色商品化必须是利用角色本身的特质为经营者带来利益,普通人使用这些不为公众所知的人格特征,实际上不过是将其作为普通的商业标记使用而已。
另外,以民法上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传统人格权为角色商品化护航,除了上面提到的诸如适用范围狭窄等不便之外,还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以人格权被侵害为由提起的诉讼,其获得的救济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并不以侵害者的获益作为计算基础,而是一般以本地居民年度平均收入作为参照,实践中这一数额并不大,尤其是对于知名人士或著名角色而言,远远不能补偿其因他人未经许可使用自己角色的损失。
其次,人格权始于自然人出生、终于其死亡。但是,知名人士或者著名角色哪怕在本人死亡后,其原有的人格特征也仍然能为经营者带来商业利益,所以对于角色商品化能否延伸到自然人死亡之后,一直是存有争议的,认可这种利益可以延伸到自然人死后的国家也不在少数,这一点是传统人格权所难以突破的。
实际上,与上面探讨的结论一样,角色商品化的主体所关注的并不是人格权,而是包含商业价值的财产利益。但因其涉及的是人格特质的商品化,所以与一般的财产利益又有所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很难用传统的某一种权利来对其界定或者将其涵盖的原因。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
当商标法和民法在解决角色商品化问题上都有些捉襟见肘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1.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前面已经探讨过,作品的名称以及作品中塑造的著名角色的名称一般都无法获得版权法的保护,但著名的作品名称以及角色名称,因其在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又确实是能为使用者带来商业利益的,那么是否应当保护这种法益呢?司法实践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那么统一。
在“泰囧”案中,法院就指出,被告在宣传“泰囧”电影时,有意使用“人在囧途之泰囧”的说法,构成不正当竞争,原因是“人在囧途”已经构成“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被告的使用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初字第1236号民事判决书。但是,同样作为知名的电影名称,“五朵金花”案的原告就没有那么幸运。法院认为,原告不是市场经营主体,与被告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所以,被告将原告作品的名称用作香烟商标,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云高民三终字第16号判决书。
因而,如果以“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来保护角色商品化,就需要面对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角色商品化对于角色的创作者或角色本人而言,只需要是一种可能性,即便其并未也无意将角色商品化,他人未经许可也不得商业性使用该角色。也就是说,不需要角色或创作者有实际的经营行为。但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必须得“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这就将一大部分像“五朵金花”案原告那样的主体排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范围之外了。
第二,如果说电影、文学作品的名称还可以适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来保护,那么作品中的著名角色名称,如“孔乙己”、“阿Q”就很难通过这种方式来主张保护了。而在角色商品化的领域,恰恰是著名角色的名称,而不是作品的名称,才是某种“角色”。
第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谓“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实际上就是未注册商标,所以法院在裁判时也是以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可能作为判断标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泰囧”案适用这一规定没问题,但“五朵金花”案确实就难以适用这一规定,因为一个是电影作品,一个是卷烟制品,商品类别不同,消费者是不会产生混淆可能的。
所以,实际上在角色商品化领域,“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基本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2.虚假宣传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告法》也对虚假广告予以禁止。
WIPO的报告指出,涉及到真人的人格商品化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普通的知名人士,比如影视明星、皇室成员等,对顾客而言,产品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形象出现在相关产品上;另外一种就是知名的专业人士,比如运动员、药剂师等,这些人物形象出现在该领域的相关产品上,对顾客而言就具有“背书”作用,顾客通常会出于对这些专业人士的信任而选择产品。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中的“虚假宣传”通常都只能适用后一种情形。
3.一般规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1993年制定实施的,距今已经二十多年,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使得原来立法时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无法涵盖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的行为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些年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的一般规则裁判案件的判决越来越多。本文赞同这样的观点:“任何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都属于不正当竞争”,这只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原则或框架而已。在此原则之下,立法机构可以将其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具体行为纳入,作为司法部门,只能依据立法机构确立的具体行为类别,来判断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1李明德:《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点思考》,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简言之,这类一般条款是为立法机构准备的,不是让法官用来造法的。
实际上“诚实信用”原则一向被誉为民法的“帝王条款”,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果一般条款如此好用,往极端里说,整个民事法律规范都不用制定,只制定一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了。以一般规则来裁判案件,虽然法官的出发点是追求实质正义,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渠道,但难免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由于法官的业务水平不同,对该条款的理解也不一致,这就会导致裁判结果对当事人而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当事人难以根据法律规定来预判自己的诉讼行为的结果。
所以,本文反对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来解决角色商品化问题。
三、涉及角色商品化的几个典型问题
以上主要梳理了我国立法和司法上对角色商品化的保护方式及不足,下面本文试图探索对于角色商品化,应当构建什么样的法律保护模式。但在此之前,围绕角色商品化,还有几个典型问题需要探讨和澄清。
(一)角色特征
根据WIPO的报告,受到保护的角色特征或者说是人格特征的是那些被公众认为与角色相关的特征,比如姓名、肖像、外观形象或声音,或者能够以此辨认出该角色的其他特征。在这些角色特征中,理论上和实践中比较有争议的有这几种情形:
1.角色的姓名
对于虚构角色的肖像和外观,无论是虚构动漫形象还是由真人扮演的虚构形象,可以作为角色商品化的客体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虚构角色的姓名能否单独获得保护,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答。
(1)虚构角色的姓名
虚构角色的姓名既包括虚构动漫形象,比如唐老鸭,也包括真人扮演的虚构形象,比如林青霞的“东方不败”,还包括由文学作品创作出来的著名形象,比如阿Q,这些姓名能否单独作为商品化的客体受到保护呢?前面已经论述过,目前在版权法的框架下是难以对其提供保护的。同时,民法上对自然人姓名权的保护也不可能延及虚构角色。那么,对虚构角色的姓名或名称到底是否应当提供保护呢?
实际上当事人即便使用虚构角色的肖像或者外观来进行商业化运作,也不是看重其文学价值或者美学形象,而主要是为了利用知名虚构角色的知名度而已,所以在“三毛”案中,法院在审理结论中就指出,“被告将‘三毛’漫画形象作为商标和企业形象使用,严格地讲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作品”。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6)沪一中民初(知)字第94号民事判书。虚构角色的姓名或名称也同样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也同样能以其知名度为使用者带来商业利益,所以从理论上而言,没有理由不为这一人格要素提供保护。
(2)非典型姓名
在涉及到角色的姓名这种人格特征时,还有一种情形是有关角色的外号、绰号或艺名的,不妨称之为角色的“非典型姓名”。无论是真人还是虚构角色,有的角色并不以其本名为人所知,公众更熟悉的是其外号、绰号或艺名。在“Hirsch案”中,原告作为著名的运动员,以“Crazy legs”的绰号为公众所知。美国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形象权,原因是“在这个案子的关键点上,绰号毫无疑问地指示了原告赫斯克。”1Hirsh V. S. C. Johnson & Sons, Inc., 90 Wis. 2d 379, 205 USPQ 920 (1979),转引自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713–714页。在“乔丹”案中,虽然“乔丹”只是英美国家的普通姓氏,但是,在汉语的语境下,中国的相关公众是将乔丹指向NBA著名球星迈克尔•乔丹的。
(3)相同姓名
当普通人拥有与知名角色相同的姓名时,其在普通人格权意义上使用自己的姓名不应当有任何限制;但是,一旦其将该姓名用作商业活动,则该姓名就是作为商业标记使用了,会导致相关公众将该姓名与知名角色相关联,系对后者声誉或者商誉的不当利用,所以,此时对姓名权的行使,就必须要受到限制。当知名角色的姓名另有其他含义时,该知名角色就很难限制他人在商业活动中使用该文字。比如在“黎明”商标异议申请案中,商标局就驳回了著名演员黎明就该商标提出的异议,理由就在于“黎明”一词有其他含义,不会使消费者误认为该商标与某人有关联。2《关于对“黎明”商标异议的裁定》,国家商标局(1996)商标服异字第008号文件。当然,如果他人故意以造成消费者误认的方式使用该姓名,即便该姓名有其他含义,该知名人士也同样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
2.角色的声音
知名角色的声音可以获得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前提是这种声音具有可识别性,可以让相关公众将该声音与角色相关联。在这方面美国的司法判例比较多。比如在“Midler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雇佣另一位歌手演唱了原告曾经演唱过的知名歌曲作为自己产品广告的背景音乐,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形象权侵权。3Midler V. Ford Motor Co., 7 USPQ2d 1398 (9th Cir. 1988).在“Waits案”中,被告也是聘请歌手演唱了原告的名曲,并在产品广告中推广,法院指出,“当某一名人的声音足以指示其身份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形象权法律的保护,制止他人未经同意而为了商业性的目的加以模仿。”4Waits V. Frito Lay, Inc., 978 F. 2d 1093 (9th Cir. 1992).
不过,现实中有许多为人所知的知名角色,虽然其声音的识别度也很高,但却是配音演员所为。那么,这些角色颇具特色的声音应当属于谁的人格特征呢?本文认为,对于声音这种人格特征,不应轻易断定其归属。许多人声线相似,即便不相似,也有很多具有语言天赋的人可以成功模仿他人的声音,网络上那么多的“神配音”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加区分地因为某一知名角色的声音比较独特,就认定该声音属于该角色,对于配音演员而言是不公平的。配音演员应当仍然可以凭借其声音特色去配音,去商业运作,但前提是不得让消费者误以为是该知名角色在“献声”该商品或服务。这一点与利用跟知名人士相像而模仿后者出现在广告中比较类似。
实际上在前述美国两个关于侵犯知名人士形象权的涉及声音特征的案例中,虽然也都不是采用原告的原声,但其模仿者模仿演唱的歌曲都是原告曾经演唱过的在相关公众心目中知名度很高的歌曲,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原告亲自为广告献声演唱。法院所禁止的不是模仿者对自己声音或形象的正常使用,而是禁止其利用原告的知名度和声誉来牟利。
3.角色的其他特征
除了惯常的对角色的姓名、肖像、形象或者声音的使用外,还有一种商品化方式,其并不具体使用某一种角色特征,甚至严格来说也不算是人格特征,但社会公众看到这种特征后能够明显辨认出该角色。比如在 “Motschenbacher案”中,原告是著名的国际赛车手,被告在广告中的赛车采用了与原告赛车一样的装饰风格,只做了轻微的改变,而且广告中赛车手的面部模糊,无法辨认出具体是谁。美国联邦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形象权的侵害,因为“这些装饰性的标志不仅是原告的赛车所独有,而且使某些人想到这辆赛车是原告的,并且由此推断驾驶赛车的那个人就是原告。”5Motschenbacher v. R. J. Reynolds Tobacco Co., 498F. 2d 821 ((9th Cir.1974),转引自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722–723页。
真人扮演的角色有时在外观上与其本人差别很大,比如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虽然孙悟空的外在形象主要是靠美术师和化妆师勾勒出来,但其作为角色为公众所知却是靠六小龄童的生动表演。只要看到以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形象的外观,即便没有办法分辨出装扮者是谁,相关公众都立刻会将该形象与六小龄童相关联,未经许可将该角色商品化,无疑正是为了利用该知名角色的声誉,损害了角色创作者的利益。
(二)利益归属及保护期限
1.利益归属
本文在引言部分提到过宁泽涛因代言问题与国家游泳队之间产生龃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其在这届奥运会上比赛成绩不理想。那么,因角色商品化所带来的利益到底应当归属于谁呢?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是在央视拍摄的《西游记》电视剧中出现的形象,央视对该电视剧拥有版权,那么,到底是央视还是六小龄童可以主张角色商品化的权益呢?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审理的“Wendt案”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Wendt v. Host International, Inc., 125 F. 3d 806 (9th Cir. 1997),转引自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707–708页。
该案两原告在派拉蒙公司摄制的系列电视剧《欢乐谷》(Cheers)中扮演了其中两个角色。被告经过派拉蒙公司的许可,依据原告在电视剧中扮演的角色形象,制作了电子机器人在机场展示和销售。原告认为,自己作为自然人的形象,是独立于电视剧和其中的角色而存在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求,认为其对于在电视剧中扮演的角色享有形象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男女演员不会因为扮演了一个虚构的角色而丧失了权利,不能控制对于他或她的形象的商业性利用。”本文认可这一观点。所以,即便央视可以拥有《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版权,六小龄童也仍然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对其扮演的六小龄童形象的商品化利用。
2.保护期限
首先,对于真实人物,对其角色商品化的保护是否应当延及死后,这在理论上是存有不少争议的。如果以人格权作为基础对角色商品化提供保护,毫无疑问,这种“商品化”利益是不能延及自然人死后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美国关于形象权的法律由各州自行规定,据统计,“目前至少14个州的立法承认形象权可以在自然人死后获得保护。另有一些州通过判例法承认了死后的形象权。”3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739页。有些知名人士哪怕百年千年之后,其知名度也长久不衰。这种知名度无疑是可以在其死后也同样为使用者带来商业上的价值的。所以,角色商品化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不会随着自然人的死亡而自然消亡,并且可以继承、转让。
其次,对于角色商品化是否应当设定一个保护期限,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议。对于用版权来维护角色商品化利益的,无疑是有保护期限的,比如在我国,是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对于自然人扮演的角色的商品化问题,本文认为,在该自然人的有生之年,只要该角色一直保持着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就应当提供保护;在自然人死后,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时仍然保持知名度,则对于该角色的商品化利用,其继承人仍然可以保有这一权利。如果仅仅从知名角色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的角度,那么只要角色仍然保持知名度,按说相关权利主体就可以运用该角色为自己创造商业利益。但是,本文认为,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及公平角度,不为角色商品化设定一定的保护期限是不合适的。在知识产权领域,无论是版权还是专利权,期限的设定都是人为的,并不是保护期限一过,作品或者技术就不再有价值,相反,还有可能更有价值。但是,法律却为这类客体设定了一定的保护期,其主要原因是要在权利人与公共利益之间设法取得平衡。角色商品化也是一样的。至于保护期限设定多长时间为宜,既然虚构动漫形象在版权法的框架下是按照版权法的保护期限来设定的,那么,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角度,本文建议对于真人及真人扮演的角色的保护期限,也设定为自然人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比较合适。不过,具体能否获得这么长期限的保护,还要看该知名人士或其扮演的角色能否保持知名度。当然,为角色商品化保护设立一定期限,这只是在禁止权的意义上,如果知名角色的创作者或知名人士想就知名角色获得更长久的保护,不妨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这样哪怕角色商品化的保护期届满,其仍然可以凭借商标权继续对角色进行商业化利用。
四、角色商品化法律保护模式的构建
对于角色商品化而言,作为角色的创作者或者角色本人,其可以任何方式合法地商品化运作其形象,可以广告代言、商标注册、出售形象周边产品等,可以自己运作,也可以许可他人运作。所以角色商品化保护的意义主要是禁止权,需要设定一个法律框架,将未经许可对知名角色商品化的行为予以禁止。
本文认为,在角色商品化的法律保护模式构建上,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引入“形象权”保护。形象权对于真实人物以及由真人扮演的角色的保护,有其他法律保护模式所难以企及之处:首先,形象权的定位是经济权利,这就与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相比更符合角色商品化的本质;其次,引入形象权保护,可以将传统民法以人格权保护无法纳入的一些人格特征纳入角色商品化的客体,比如声音,比如无法辨认自然人面部特征但却能明确指向该自然人的一些综合形象特征;再次,形象权的引入,可以使商标法上“在先权利”条款发挥真正的作用,法官无需再频繁适用颇有争议的“不良影响”条款,当事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在先权利”对抗他人未经许可对其享有权利的知名角色的注册行为。
至于“形象权”应当放在什么法中,最合适的应当是《民法典》,因为形象权毕竟是民事权利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在《民法总则》的“民事权利”章加入“形象权”的规定:
“自然人享有形象权。禁止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商业目的,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形象、声音或其他人格特征。
前款所谓人格特征,是指相关公众可以从该特征辨认出该自然人身份的专属于该自然人的具有识别性的特征。
自然人形象权的保护期限是自然人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自然人形象权可以转让和继承。”
其次,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无法纳入形象权保护范围的其他知名角色商品化情形纳入。
《反不正当竞争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是禁止混淆。形象权的调整范围是自然人本身或由其扮演的角色的人格特征,但对于那些雇佣与知名人士面容相像或声音相像的人假扮成知名人士或其扮演的角色的,形象权就无法调整了。但这种假扮的目的都是为了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将假扮者认成知名角色,或认为其与知名角色有关联。实际上这已体现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5条,“经营者不得利用商业标识实施下列市场混淆行为:(一)擅自使用他人知名的商业标识,或者使用与他人知名商业标识近似的商业标识导致市场混淆的;(二)突出使用自己的商业标识,与他人知名的商业标识相同或者近似,误导公众,导致市场混淆的;……本法所称的商业标识,是指区分商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标志,包括但不限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商品形状、商标、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名称及其简称、字号、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姓名、笔名、艺名、频道节目栏目的名称、标识等。本法所称的市场混淆,是指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存在特定联系产生误认。”该草案对“商业标识”的解读,就涵盖了相当一部分可商品化的角色特征,如姓名、笔名、艺名等。而且草案将知名角色的人格特征界定为“商业标识”,实际上也准确指出了可商品化角色的本质。
但是,一则经营者对知名角色的商品化利用并不限于将角色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有时是在广告营销中使用知名角色;二则草案对“商业标识”的列举从立法技术上而言缺乏美感,这种试图做到无一遗漏的列举方式不仅会挂一漏万,而且看上去也颇为杂乱。所以,本文更倾向于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的基础上增加类似这样的条款:
“未经许可使用知名角色特有的人格特征,引人误以为该商品或服务与该知名角色或该知名角色的创作者有关。
知名角色包括在相关公众中具有知名度的虚构形象和真实人物。特有的人格特征是指相关公众可以从该特征辨认出该知名角色的专属于该角色的具有识别性的特征。
创作该知名角色的自然人死亡时间已超过50年的,或者作为该知名角色的自然人死亡时间已超过50年的除外。”这一规定也与设想中的民法典中对“形象权”的规定相一致。
再次,鉴于实践中将知名角色商品化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将该角色特征作为商标注册或使用,因而,在《商标法》中不妨也就角色商品化的保护设立禁止性规定。实际上如果《民法典》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已经有了完善的相关规定,《商标法》中不做规定也无妨。但是考虑到我国“部门修法”的现状,最好是在商标法中也加入类似《日本商标法》的禁止性规定。《日本商标法》第4条是关于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记,其第8项是“含有他人的肖像或者他人的姓名或名称或著名的别号、艺名或笔名或它们的著名简称的商标(取得本人的同意者除外)。”我国《商标法》第10条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商标不得注册的绝对事由,而角色商品化因为只是涉及权利冲突问题,所以只属于商标不得注册的相对事由,因而这种类似规定不适合放在《商标法》第10条。所以,对于角色商品化的保护,最好的立法方式是如同对代理人或代表人抢注商标的规定一样,单列一条:
“未经许可,将知名角色特有的人格特征进行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知名角色包括在相关公众中具有知名度的虚构形象和真实人物。特有的人格特征是指姓名、肖像、形象、声音或其他人格特征,相关公众可以从该特征辨认出该知名角色。
创作该知名角色的自然人死亡时间已超过50年的,或者作为该知名角色的自然人死亡时间已超过50年的除外。”
无论是在《民法》中,还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中,对于知名角色的人格特征,除了常见的几种外,都不宜做穷尽式列举,正如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法官在“White案”的判决中所指出的,“被告‘如何’使用原告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告‘是否’使用了原告的身份……将使用人们身份的具体方式列在一个清单中,将形象权视为仅仅保护这个清单中的具体方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规定,只有九种不同的使用他人身份的方法可以被用来侵犯形象权,那么这一规定不过是向聪明的广告战略家提出挑战,让他们创造出第十种方式来。”1White v. Samsung Electronics American, 23USPQ 2d 1583 (9th Cir.1992),转引自李明德著:《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723–724页。
结 语
角色商品化曾经在学界掀起过一阵探讨热情,后来又沉寂下去;现在除了个别学者偶尔关注外,好像已经没有太多人对此问题感兴趣了。但从角色商品化概念的提出到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实践中与此相关的问题却依旧层出不穷,而名人明星代言的商业价值也越发凸显。“乔丹”案的本质就是角色商品化,最终的审理结果却不能不令人遗憾。所以本文认为,对角色商品化重新深入探讨,促进立法的修改,改变法院的裁判思路,正当其时。
The types of character merchandising include merchandising of both fi ctional characters and human characters.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such as cartoon images are usually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which cannot provide independent protec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The real person characters and the fi ctional characters played by the real person can’t be perfectly protected whether by Trademark Law, Civil Law or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protected as long as the public can make the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well-known roles. For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there should be a certain time limit in the protection of character merchandising. In the Civil Code, publicity right should be regulated to prot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person and the fi ctional characters played by the real person. At the same time,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Trademark Law.
well-known characters; fi ctional characters; merchandising; publicity right
李阁霞,法学博士,烟台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