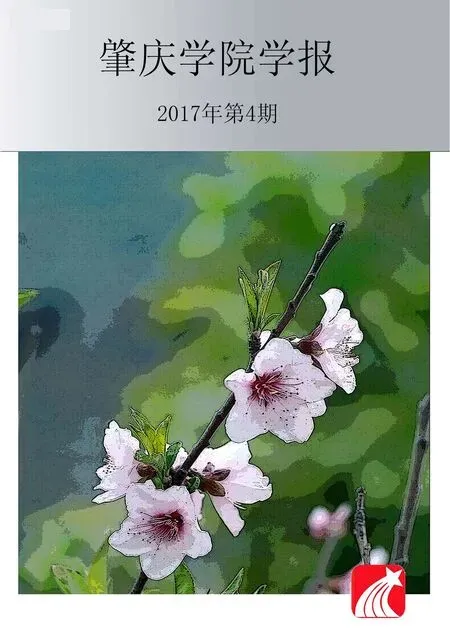二语习得中显隐性知识界面思考
曾玉萍
(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二语习得中显隐性知识界面思考
曾玉萍
(肇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语言界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界面研究属于微观研究。对其界面的关系,学者们提出强界面、弱界面和无界面三种。通过梳理显隐性知识的概念及其界面三分说、中介语和石化现象与显隐性知识间的关系以及显隐性知识的实验性研究,认为显隐性知识的区分因意识概念的模糊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任何一个中介语中均可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同的表象说明显隐性知识界面的存在。
二语习得;界面;显性知识;隐性知识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英国诺丁汉大学英文系教授Ronald Carter主编的一套“界面研究丛书(Interface Series)”引发了国际语言学界的界面研究的热潮,界面研究呈发展态势。语言界面非新词。语言有广义和狭义界面研究[1]2。语言界面研究可以是宏观的,如社会和语言、社会语用和心理语言界面研究等;也可以是微观的,如对语言学内部句法与语义的界面研究、语音与语法的界面研究等问题。
在中国,有学者从界面的形成、二语界面薄弱的原因及二语习得界面假说的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总体描述[2],也有学者对近十年来国内外语界面研究的思考[3]。但总体来看,语言界面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如概念不清、切入角度及切入方法等。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语言内部,即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界面问题,不介入界面的宏观研究,即语言学与各学科之间形成的界面的研究。通过梳理显性知识及隐性知识的概念及其界面三分说、中介语及石化现象和显隐性知识间关系及以及显隐性知识间关系实验性研究,认为显隐性知识的区分因意识概念的模糊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任何一个中介语中均可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同的表象说明显隐性知识界面的存在。
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界面的理论争议
(一)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 ichael Polanyi)在1958年从哲学领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显性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也包括数学公式、各类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对,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来自维基百科)。
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过程中是发展了一种或/和两种知识系统,即是发展了显性知识或/和隐性知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理解。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讨论肇始于Krashen。他认为成人二语学习者在发展二语能力时有两种独立途径,即无意识习得和有意识学习[4]。人们流利而能产的掌握其母语且能够在不能解释潜在的语法时立刻察觉语法的不规律性,这是隐性知识在起作用。隐性知识能够在没有意识到已获取的知识下影响语言处理,即不知道自己知道;而显性知识是我们知道自己知道的知识,并且我们意识到它的使用。显性知识指导有目的的行为,而隐性知识自动被使用。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涉及不同的心理过程和存储。潜意识过程习得的知识能潜意识地启动自发的语言表达,而有意识学得中学会的知识存储于意识状态中,仅在语言运用中起监控作用[4]。在显性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如果显性知识和输出有较多的实践运用机会,就会逐渐转化为隐性知识,最后到实现程序性知识的自动化这一固定轨迹。但有学者认为学习主要是隐性的[5],在这一过程由于受到一语(母语)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不完美的或不理性的。然而这种不完美可以通过显性指导得以改善。显性知识是描述的语法规则的知识,只有通过控制处理得以获取,尤其是学习者在计划时间内获取;而隐性知识是规则的程序性知识,通过自动化处理获取,尤其是当学习者流利而自然地表现时获取。记忆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系统就是通过意识连接并相互作用的,意识就是这两种知识的接口。有学者认为语言学习与认知技能相似,技能获取的基本原则是有意识的过程[6]。二语习得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差异的核心是学习者对相关知识或知识规则的意识程度,以及用语言表达相关知识和规则的程度[7]。
学者们在讨论显性知识及隐性知识时,把它们和意识、学习、习得、技能等联系在一起。但就认知系统而言,意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说意识是指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认知对象上。意识是显性/隐性之分的依据,有意识的参与则为显性,没有意识的参与则为隐性。但在二语习得中输入是多级现象,输入的知识到底是语言形式的意识、语言实例的意识,信息的意识,还是刺激事件的意识?意识、学习、及记忆之间的关系怎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商榷。
在二语习得中,意识是如何适合于认知系统。在何种情况下什么东西变成有意识的?它有何不同?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区分因意识概念的模糊性也不可能截然分开。
(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三种界面之争
对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的界面关系,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强界面说,弱界面说和无界面说。
强界面说的代表人物是RobertDekeyser[6]。强界面说是基于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所提出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8],认为语言学习与认知技能相似。通过一系列发展过程,先是积累陈述性知识(what),然后是程序性知识(how),最后通过训练达到自动化程度,即程序化的知识变的流利、自发且不需努力。技能获取的基本原则是有意识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二语学习的过程遵循从技能行为的that类知识(陈述性知识)到how类知识(程序性知识)的过程。
弱界面说的代表人物是Rod Ellis。他认为显性知识主要是在获取隐性知识中作为加工的辅助者起作用,显性知识可以转化为隐性知识[9]。其观点强调意识的作用。而另一位持弱界面观点的学者则更少强调意识的作用[10]。认为学习主要是隐性的,是联想的和理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直觉地根据交际中遇到的可能的相关实例认知和组织语言结构或语言形式-功能映射。任何新知识或者新技能的获得都会受到已经具有的知识或者技能的影响。牢固建立起来的母语系统对第二语言学习产生影响。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显性知识有助于帮助隐性知识的获取。
无界面说的代表人物是Stephen Krashen。他认为有意识的语法指导无助于潜意识的语言学习,因为它不能发展学习者的语法能力[4]。换而言之,所教的与所学的和流利交际所需的隐性知识之间无界面。其理论的核心是理解性输入假设,认为真正的语言习得是无意识发生的并无意识存储在大脑中,学习过的知识不能转化为习得知识。
学者们对显隐性知识界面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我们以下通过显隐性知识界面的实验性结果探讨这样问题。
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界面的实验性研究
(一)中介语及石化现象实验
中介语(Interlanguage)是指从母语(L1)始至习得第二语言(L2)止,其间经历的一系列的语言过渡“阶段”里所产生之“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既不同于学习者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会随着学习的进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的语言系统。石化现象是指许多外语学习者在其外语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止步不前的情况。二语习得研究中,中介语和石化一直是理解二语发展的基本概念,也是理解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重要概念。
Selinker提出的中介语假设及石化现象是40多年来指导二语习得研究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他把二语习得中石化这一特征和被称为潜在的心理结构(Latent Psychological Structure)联系在一起[11]。潜在的心理结构是一种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排列,会阻止学习者以一种永久的方式获得目标语形式。他认为石化的语言单位应该涉及三种系统的资料,即母语,中介语和目标语。在潜在心理结构中的中介语单位是隐藏的,只有在学习者试图用目标语表达他们自己的意义时才能被激活。
石化现象是二语学习者面临的窘境。无论学习条件多么有利,比如给予丰富的输入,有足够的学习动机及有交际训练的大量机会,学习者仍有某种行为错误。早期的对石化现象的理解趋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一旦石化发生,就会影响整个中介语系统。后续的理论和研究发现,石化现象是部分而非整体的,仅影响中介语的次系统且有不同的选择性影响个体学习者和他们的中介语次系统。Han就石化现象做了一系列纵向研究[12]。她的实验对象是昵称为G和F的两个成年男性中国人。他们有丰富的被指导的学习经验,也有在目标语环境下学习的经验且都有强烈的提高英语水平的动机。其实验显示出石化的三种情况,即中介语结构退化、中介语结构保持不变和中介语结构有所变化。这三种情况展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不同关系。她认为中介语结构退化和中介语保持不变表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界面的缺乏,而中介语结构的变化表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有强界面。在任何中介语中,有可能共存显性和隐性界面的呈现和缺失,在石化中隐性和显性知识间有不同的关系。二语习得中中介语及石化现象似乎涉及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裂。Krashen&Pon[13]对一名英语已达高水平的中国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跟踪记录发现,如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她描述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及违反语法规则的句子时,她能够改正95%的错误;在写作及有准备的发言中,她能够有意识地使用语言知识。而在随意谈话时,也许由于过程太快或过于关注信息而疏于调整输出,她会偶然犯错误,且在她已经有意识学得的20多年的简单语法规则上犯错。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即使是学得很好、实践中很熟练的规则也不能转为习得。
认知机制在任何一个中介语中均可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同的表象。中介语中的次系统有的会表现出强衔接/界面,有的会表现弱衔接/界面,还有的会表现出无衔接/界面。中介语的理解可以说明在二语习得者头脑中存在接口/界面,只是存在的强弱问题,尽管目前大部分都赞同弱接口/界面之说,但仍然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如石化现象、学习者之间的不同习得和学习者内部的不同习得。这些问题在讨论显性和隐性知识或学习时都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彻底厘清,想要确定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界面问题还为时过早。
(二)人工语法测试实验
隐性知识总是和人们流利的使用语言联系在一起,正是隐性知识使语言处理由控制处理(controlled process)向自动处理(automatic process)转变,以便在输出任务中实现无负荷运算[14]。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语习得过程就是隐性知识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知识表征的变化过程。知识表征的变化意味着学习者形成新的知识结构,或者重构与确认已有的知识结构。
Reber引用人工语法(Artificial Grammar)学习测试受试者的隐性知识[15]。他通过给受试者展示包括字母顺序的学习资料如VXXVS和TPPPTS并告知他们,字母顺序遵从一定的语法规则。然后对他们进行语法判断测试,内容包括新的合乎语法和不合乎语法的字母串。结果显示出非随机性,但受试者完全不能用语言表述潜在的语法。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有可能学习者隐性获得抽象的语法结构表征。Green and Hecht的实验显示出在自然的二语习得中,口头报告和句子纠错间存在明显的分裂[16]。他们发现受试者改正语法错误的能力落后于提供纠错的能力,正确的纠错和不正确的解释连在一起。认为改正句子的能力是由隐性知识所驱动,而通过指导,给受试者提供显性语法知识,可能有助于学习者隐性知识的发展,在纠错中学习者依赖的是显性知识。对此实验的结果,Shanksand John认为不具有强制性[17]。人工语法本身就很难用言语表达,另外在训练和任务报告及缺乏详细的询问之间有时间上的延期。Dienesand Scott所做的人工语法实验中,要求受试者在做判断时说出他们的心理状态,即他们判断的依据是猜测、直觉还是记忆[18]。当受试者说他们是猜测的,如果他们判断的精确性不是偶然的,就能断定他们使用了隐性知识。但同时也发现,受试者纠错的平均正确水平比错误的高,意味着人们做判断是依靠有意识的知识。Rebuschat也用了语法判断测试研究在不同训练条件下学习者学习德语动词位置规则的情况[19]。在涉及意义训练条件下,在可信度和精确度之间有关联。依赖于记忆和规则的反应是非随机的,显示显性知识的贡献;而依赖于直觉的可信反应是随机的,显示无意识结构知识的贡献。有趣的是,在需要受试者有意识寻找规则的训练条件下,显示出相当强烈的无意识知识。在猜测的回答中甚至也发现了非随机的回答,说明刻意诱导可以导致隐性知识。
从以上实验可以发现,语法判断测试考察的是识别语法错误、改正错误及说出语法规则的违反,但我们不能通过他们的语法测试判断他们提取的是外显知识还是内隐知识,抑或是两类知识兼而有之。另外,语法判断测试所测量的知识类型,取决于判断是定时的还是非定时的。如果学习者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某个句子的合乎语法性,其依赖的就很可能是内隐知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则依靠控制性的外显知识。测量标准一成不变地总是涉及合乎语法判断、填空测验等,很少考察自然话语的特征及其所体现的语言知识的运用。
四、结语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界面研究与意识及石化、中介语联系紧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涉及意识的心理过程,而对意识是这两种知识的接口问题,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二者间有动态联系且显、隐性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石化及中介语现象及记忆缺失症的存在似乎印证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离,但认知机制在任何一个中介语中均可发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不同的表象。而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实验研究可以看到,任何知识的测试不可能是纯粹的处理过程,语法判断既反映隐性知识也反映显性知识。高度受控的实验室的实验远离实际的学习及语言的运用,其发现应该说对二语习得无多大意义。实验室所研究的是控制隐性学习研究,创造适合非特殊性知识的理想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一种更有可能反映那种知识的方式测试学习者。可以说,涉及到语言符号和类似语言规则的任何任务的实施是一种语言学习的有效测量,问题是这种学习是否隐性或显性及它是否能产生隐性或显性的知识。另外,知识完全被无意识使用的情况是不现实的。
[1] Ramchand,G.&C.Reiss.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Interfaces[M].Oxford:OUP,2007.
[2] 盛云岚.二语习得界面假说剖析[J].现代外语,2015,38 (5):678-686.
[3] 朱跃、伍菡.对近十年来国内外语界面研究的思考[J].外国语文,2013(5):18-21.
[4] Krashen,S.D.—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2.
[5] Ellis,N.At the Interface:Dynamic Interactions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Language Know ledg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5(2):305-352.
[6] DeKeyser,R.Beyond Focus on Form: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Second Language Grammar[M]//C.Doughty&Williams(Eds.).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42-63.
[7] Hulstijn,J.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mplicitand Explici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Introduction[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2005 (2):129-140.
[8] Anderson,J.Acquisition of cognitive skill[J].PsychologicalReview,1982,89(4):369-406.
[9] Ellis,R.A Theory of 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N.Ellis(Ed.).Implicit and Explicit Learning of Languages.London:Academic Press,1994:79-114.
[10] Ellis,N.At the Interface:Dynam ic Interactions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Language Know ledg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Acquisition,2005(2):305-352.
[11] Selinker,L.Interlanguag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72(2):209-41.
[12] Han,Z.-H.Interlanguage and Fossilization:Towards an Analytic Model[M]//V.Cook and L.Wei(Eds.),Contemporary Applied Linguistics.New York:Continuum, 2009:137-62.
[13] Krashen,S.D.&P.Pon.An Error Analysis of an Advanced Learner of ESL:the Importance of the Monitor. Working Papers in Bilingualism,1975(1):125-129.
[14] Segalow itz,N.Automaticity and Second Languages [M]//C.J.Doughty&M.H.Long(Eds.).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alden,MA: Blackwell,2003:382-408.
[15] Reber,A.Implicit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Grammars[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67 (6):855-863.
[16] Green,P.&Hecht,K.Implicit and Explicit Grammar: An Empirical Study[J].Applied Linguistics,1992(2): 168-184.
[17] Shank,D.&John,M.Characteristics of Dissociable Human Learning Systems[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94(17):367-447.
[18] Dienes,Z.&Perner J.A theory of Implicitand Explicit Know ledge[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1999(5): 735-808.
[19] Rebuschat,P.Implicit Learning of Natural Language Syntax.Ph.D.thesis,University of Cambridge,Cambridge,2008.
On Interface between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acit Knowledg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ZENGYu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526061China)
Language interface can be studied from both amacro perspective and am icro perspective.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udy of explicit know ledge and tacit know ledge belongs tom icro one.About their relationship,researchers put forward three kindsof interface,i.e.the strong interface,theweak interface and noninterface view.By com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icitand tacitknow ledge,between interlanguage,fossilization and explicitand tacitknow ledge aswellas giving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explicit know ledge and tacit know ledge can’t be separated because of the ambiguous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y can be found in any of interlanguage.
second languageacquisition;interface;explicitknow ledge;tacitknow ledge
姚 英)
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445(2017)04-0038-05
2016-09-1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3XWW16);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项目(2013JK181)
曾玉萍(1968-),女,四川金堂人,肇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