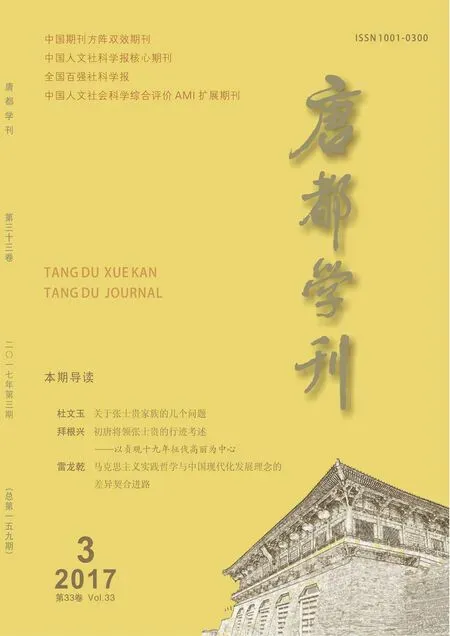“逍遥”的秩序之维
张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博士论坛】
“逍遥”的秩序之维
张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在庄子的思想中,作为理想生命形态的“逍遥”内在关乎人的实践,具有实践智慧的内涵。与“任意”不同,“逍遥”以“道”为根据,以“本真之性”的解放为内容;在超越现实既成规范或制度束缚背后,以“道”的整体性为视域,强调超越分与杂而对统一与有序的期待。这种“逍遥”以承认现实世界的此岸性为依据,在突出心性论的意义上“本真之性”的前提下,描绘了理想的人伦社会形态,并在指导人们获得理想的“在”世实践形态中,展示了其实践智慧的品格。
庄子;逍遥;秩序;本真之性
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逍遥”首先指向对界限或限定的超越,而这一超越既建立在“道”的实践智慧之下,又表现为对现实既成规范的突破。在庄子看来,“逍遥”总体上应该呈现一种向“道”回归的姿态。就“回归”而言,庄子首先突出事物的统一性,强调对存在意义上“通”的把握,并以“通”为本体论根据,提出对现实既成规范或具体社会秩序的突破和超越,将形上思考进一步引向对现实的批判。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逍遥”之自由内涵的某种弱化,使其区别于一般的“任意”,具有了“界限”,同时指向其秩序之维。
一、“道不欲杂”:秩序的本体论根据
“逍遥”以“道”为根据,而“道”作为庄子思想的第一原理,在成为存在根据的同时,也展现为存在之序,内含着统一性、条理性和有序性等内涵[1]84。在“逍遥”中则具体表现在应对现实的“困待”时,基于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二分,自觉地超越现实世界的“分”与“杂”,并向体现“道”的统一性和有序性的本然世界回归;同时,庄子进一步赋予这种有序性以审美内涵。
显然,在具有“自觉”的意义上,“逍遥”首先有别于“任意”,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实现了视域由“以人观之”到“以道观之”的转变。此外,与种种“有待”的存在形态相对,“无待”作为逍遥的实现形态,同时蕴含着“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2]17的内涵。这里“无待”表现出顺乎事物内在本性或法则的要求。不难见出,不论是主观条件抑或客观要求,都凸显出“逍遥”的现实之维,换言之,“逍遥”并非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而是基于现实之在的存在形态。学者将这一实现特质概括为“逍遥的此岸性”[1]250。不难见出,无论就本体论言,还是就现实的主体基本条件言,“逍遥”在区别于“任意”的同时,具有根本意义上的界限,即“道”。
而庄子思想的复杂性在于,“逍遥”作为理想的“在”世形态,同时表现出了超越性的一面。《庄子·齐物论》中庄子借对“古人知有所至”问题的讨论,指出了观念把握世界的三种不同结果,亦即世界通过观念展现的三种不同形态,分别即“未始有物”“未始有封”和“未始有是非”。进而庄子认为,观念上的“是非之彰”实际上成为“道之所以亏”的根由。这里,“道”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对存在(大全)的整体把握,展示了对一般经验世界的超越之维。而就“亏”言,庄子的思路同时又与主体的认识之境相联系,暗示了达至“道”的超越之境的现实之径,也展示了“逍遥”的此岸性或现实之维。
庄子将世界判分为两种存在图景,即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在《齐物论》中的表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2]79不禁使人产生了一种带有时空进化的理解。但是,庄子的思想方法,似乎更具有本体论或形上学的色彩[1]58。他进一步赋予本然世界以理想性、本原性和超越性,而现实世界则相应地表现出既成性、现实性和有限性。不难发现,两重世界图景的判分下,“逍遥”所蕴含的超越、复归等内涵,虽皆以理想之境或本然世界为指向,却都落实在了现实世界之维,因后者而具有现实必要性。以现实世界为视域,“逍遥”的超越性指向超越现实有限性的杂或分,同时体现着“通”的理论追思和现实追求。这又在理论上表现为对世界整全性或统一性的把握,即对“道”的体证和把握。而“道”本身在体现统一的同时,表现为对现实世界杂或分的扬弃,进而指向了理想的有序或秩序之维。
在庄子看来,“道不欲杂”。就现实世界言,因为有物与物(“物”取广义,包括“人”)之间的“封”,使得“分”成为其常态和存在的客观样态。而“分”同时兼涉多样性和无序性(“杂”)两重内涵。而“道”以“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道通为一”),根本上起到对多样性的统摄和对无序性的扬弃,彰显出存在的条理性和有序性。《庄子·田子方》中指出:“两者(按:阴阳,笔者注)交通成和而物生焉”[2]712,这一“和”就内在地蕴含了秩序性,并指示出这种秩序的内在性,使得现实世界的运行呈现出自身的法则,即规律性。此外,这种现实世界的有序性还取得了本体论的根据,所谓“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2]735“本根”与“天”皆指向万物的本原及根据,即“道”;在此,它们不仅是本原,同时也内在地规定了万物的运行方式。
庄子进一步赋予这一秩序性以审美内涵,指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735“明法”“成理”均可视为对秩序的揭示,而“大美”的评价,则在审美的意义上肯定了这种秩序的价值。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对“天籁”的肯定上。在庄子看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2]50尽管因风而有了不同的声音,但彼此间并非杂乱相斥,而呈现出自然的和谐;正如同“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2]716,都呈现出条理性和有序性,即本然的“和”的境界,而“咸其自取”更加指明了这种和谐的本然性和内在性。
二、“至德之世”:秩序的理想世界
一般而言,学界惯于将“逍遥”与自由相联系,以取得对其思想内涵的现代理解;而精神自由的界定,则成为这一研究路向上的贴切表述。与一般政治领域侧重个人权利意义的自由不同,“逍遥”内涵的自由意蕴指向了人性解放和精神境界。细察之下不难发现,庄子所注重的是对既成有限社会制度的突破,其思想以哲学上的心性论为进路,以人性之真的理想为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具体实现则表现为“逍遥”的理想境界,其中所蕴含的自由内涵同时以大全(“道”)的整体性和有序性为依归。
上文已经提到,“逍遥”兼涉超越与此岸两重面向,以超越言,其重在本真人性对现实“困待”的超越、解脱;就此岸言,则又同时关涉广义的人伦之维。有学者注意到,与“游”的观念相贯通,逍遥的思想实质展现为“游心”与“游身”两个面向[3]53。其中,“游心”侧重于对于现实既成秩序的内在心灵超越,而“游身”则指向对现实既成规范、秩序(“仁义”、名利)的妥协或对存在的本然秩序(“命”)的某种顺应。不难见出,“游心”侧重于理想的建构和人性之真的心灵维护,而“游身”则指示出,不论是待超越者,还是待顺应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指向“逍遥”的秩序之维。“逍遥”往往以超越现实之分、杂的姿态表现出自身的实质内涵,即对秩序或统一(“通”)的追寻。基于这种存在论的视域,秩序更多具有了价值内涵,蕴含了某种实践理性,而区别于单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实质上,所谓的本然世界更多的是逻辑的推论或理想的预设,二重世界划分本身就具有理想性的思维特征;而人的现实实践,则仍于现实世界之中获得其具体展开。现实世界进一步呈现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因而具体世界又在大的方面可以分判为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在庄子看来,自然领域所呈现的秩序性及其本然性、自然性的特质,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人类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参照对象。在庄子思想中,自然领域的秩序往往就是本然秩序的象征。与之相对,社会领域中,则可以区分出社会意义上的“治世”与“乱世”(《让王》)[2]988,个体意义上精神世界的“失位”[2]365与“和”[2]165。其分判的根据就在于“有为”(妄为)是对本然秩序的破坏。与之相应,“逍遥”以及其对本然秩序的回归则指向“无为”(不妄为)。
就“游身”言,“身”现实地关涉到广义上“人与人”共在的社会之维。庄子以“至德之世”为理想的“治世”社会形态,同时认为其现实的社会秩序也应当体现其形上根据。
首先,在社会政治领域,“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2]403天地之序或自然领域的秩序,在象征本然秩序的同时,成为社会秩序的直接参照。因而,“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2]469而与之相联系,“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2]465所以,社会秩序以本然秩序为形上根据并不仅限于本原和原则意义,而且指向了理想之境的实现方式。因为庄子生活年代的限制,他未能质疑政治制度上君臣关系存在的合理性。但他透过对君主施政原则的探讨,又同时放眼人与世界的关系,指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2]612以此作为施政的原则,“无为”成为社会有序的保障。
而社会之维的有序并不仅涉及政治领域的权力、社会地位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原则,它同时指向更广义的人与人关系的处理。而在这一问题上,庄子有别于儒家的现实人文主义路向,采取了形而上的超越进路。儒家重视现实的人伦之维,突出“孝悌”(家庭伦理)实践的本体意义,并主张以此为基础,建构社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整个思想呈现出某种规范伦理学的特点。而庄子则变换了视域,在“以道观之”的视域下,探讨人的本真之性究竟为何,并试图进一步以此确立人类实践的根本原则,以便超脱现实既成社会秩序及其规范,实现生存的理想之境;因此更多地表现出了形上学进路的特征。在庄子思想中,儒家的“仁义”成了有限性社会规范的体现,往往束缚人的本真之性,其自身也常常流于形式和名义上的道德,是待超越的对象。
据此,庄子又将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引入了心性论的范畴,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形态首先与个体的精神世界(即“心”)相关联。庄子认为“亲”是“命”:“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2]155尽管这有关广义的“身”,然而庄子却主张“虚以委蛇”,可见重心还是落向精神超越一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突出了对精神世界的平和的重视。
在此意义上,上述“无为”的施政原则,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收获具体的治世政绩或暂时缓和具体的社会矛盾),同时也是君主个人安顿性命的所在。“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2]369在这里,庄子不但把社会秩序与自然领域的秩序相沟通,观照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把社会秩序与个人的内在精神生命相贯通。庄子指出,乱世之中的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2]51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个体难以取得上述“性命之情”的安顿。而这种混乱同时也表现为在观念领域中是非之争的纷乱无序,“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2]63在这样的精神世界里,个体的精神世界往往呈现出“小恐惴惴,大恐缦缦”[2]51的状态,其情感好恶也因此发生的偏离,丧失了稳定,又反过来对社会造成二次危害,“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2]365精神领域的杂乱失序,不但加剧了社会领域人与人关系因争斗而形成的杂乱,更在实践意义上指向了对“道”和实践智慧的遮蔽和遗弃。换言之,与“身”游于社会在特定情境下所表现的无奈相对,庄子更注重“心”的内在平和以及内在超越的审美之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寓言中对日常劳作的审美升华。
实际上,就现实的个体言,“身”、“心”本不能绝对的分判,二者统一于“游世”实践或活动之中。“身”、“心”皆就主体而言,而“游世”则指向人的理想“在”世形态。在这一意义上,“游世”就是“逍遥”体现;不但“游”于世俗生活(人与人、人与物),更要“游”于“无何有之乡”(人与天、人与“道”)。无疑,“游于……之外”使得“逍遥”指向了超越之维;而“游心”起于对现实沉痛反思和精神提炼,内在地关涉着“身”与“世”,后者保证了“逍遥”在此岸实现的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游心”侧重于对“道”的呈现,在现实的生存中,这种呈现又体现为一种实践智慧对现实行动的引导,为“游身”和“游世”提供了形上和心性的保障。
三、“循道而趋”:秩序的“方法”(实践智慧)之维
凡人以“行”而“在”。就“行”而言,又在广义上涉及“做”。以此,人之“在”总是关乎实践意义上的“做什么”与“如何做”的问题;而对于理性的实践而言,在两个问题之间,前者往往因对后者的指导意义而应当先于并重于后者。而事实上,“做什么”往往并不都是理性的抉择,而同时也蕴含了非理性的面向。而非理性并不一定指向盲目或妄为,它同时包含了实践智慧的向度。但由于缺乏理性的认识和确证,往往表现出神秘性,难以获得,并在现实中往往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操控。
在以“劳动”为核心内涵的狭义实践中,秩序或规范往往以知识论意义的规律为根据,使前者成为方法论意义上调节具体行动的标尺或工具。而在庄子的思想世界中,秩序更多的是以价值和理想的姿态出现。与之相联系,实践也就与广义的“行”相关涉,而“逍遥”也作为“人”的理想的生存形态取得了实践智慧的内涵。本然的秩序性指向存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相应地具有了隐含性。而人类总是通过现实世界的具体秩序取得对前者的把握,虽然这种秩序呈现出明确性,但总是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即“辩之以相示”,“辩也者有不见也”[2]83。“逍遥”所内涵的秩序性之所以具有实践智慧内涵,正是由于它呈现了存在或“道”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表现出对有限性既成规范的超越。
庄子思想中,相对于“游身”所表现的某些妥协,“游心”的超越似乎突出表现了“与道为一”的绝对性。按照近现代哲学的表述,“与道为一”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目的”指向对现实既定社会及其规范制度的突破,从而实现人性或心性的解放,即精神的自由;而“规律”则指示了这种自由的本体根据,即“道”。
同时,“精神”也使得达至理想之境的方法或智慧之维得以凸显。一般而言,秩序除了本体意义的存在之序、社会之维的社会秩序等内涵外,同时还包括转化为行动指导的方法或智慧之维。在这一意义上,秩序与规律往往可以取得贯通。
方法首先与认识论相关,指向具体的行动步骤;而就实践的视角而言,方法首先关涉行动的原则。“方法”处在主客之间,是客观见之于主观,主观又还治客观时,用以指导人类实践。而通过方法,人的行动往往以实践的形态与本体的存在取得联系,已存在的本然秩序为根据,人的行动或实践同时获得了实践智慧的导引。区别于一般理论理性对规律的自觉,这种实践智慧范导下的行动或实践,更多地体现了实践理性的自觉,即对人的本真之性的解放。庄子理想化了客观或本然世界,赋予其绝对性的价值,成为理想目标和实践智慧的绝对来源。以此弱化了主观还治客观或参与世界创生中蕴含的能动性。因此单纯地做精神提纯,以便获得客观在主观的如实显现,以及主体对客观的自然顺应,呈现出精神合乎“道”之必然的特征。在庄子看来,这种“与道为一”正是人类使本性重获解放的本体根据和方法论原则,故而合乎“道”(必然)本身就蕴含着自由的向度,是实现“逍遥”的前提,在宽泛的意义上成为后者的界限。
作为“人”的理想生存形态或“在”世方式,“逍遥”现实地关涉人的具体实践或行动,具有实践智慧的内涵。“虚室生白”[2]150,即体现了智慧的生成。在于克除一般意义的片面、僵化的知识,达至对大全或道的直接体认。不难见出,实践智慧的获得除了日常实践的理性分析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整体性体认下获得智慧;就心性论的维度来看,“心斋”“坐忘”等心性护养工夫,也成为维护内在本性、获得实践智慧自觉的现实操作,即为道之方。在这一问题上,以心性论为视角,儒道两家似乎具有某种一致性。
可见,对“道”的体认,并非依赖于人类知识性或工具性的理性,而实质上指向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表现出对世界、大全的整体呈现和把握,同时以这样的智慧指导现实世界的具体实践,避免人的工具化、机械化。人是目的,尤其是人的本真之性*不同于康德的现实人伦道德视域,庄子的“真人”在成为“真知”的前提的同时,以区别于现实的片面和有限为特征,而以整体性为原则,以“以道观之”的视域来确立对世界的观念及对人自身本性的确定。。
“逍遥”根本上指向对人的本真之性的维护,即对现实既成限定的突破。就人之在而言,社会及其秩序形态是必然要求实现的对象,而在庄子看来,其根本在于个体“放德而行,循道而趋”[2]479保障在于“心”能游于世外,即超越现实世界,变换视域,达至对本然世界的观照。作为理想的生命形态,“逍遥”表现出某种“待道”或“顺待”[4]364的特征。
这里,与儒家公私之辨不同,庄子选择了知识论意义上的真伪之辨的进路。但这种知识论内在蕴含了伦理之维。这归根于庄子现实世界的理论兴趣在于寻找人性之真以及基于这一真的人伦之美和善。换言之,在庄子思想的价值系统中,表现出以本体之真统领美、善;由于庄子对本真的理解往往具有理想化的特征,故而,真与美之间又相互贯通,真统美、善,往往可以置换为美统真、善。在此意义上,真与美取得了根本价值的地位,而善则相应成为了从属。验之于庄子思想本身不难发现,“逍遥”虽然也关注到社会的理想形态和其内在的秩序之维,然而,这种关注始终是有限的,他对人伦的关注在与儒家思想的比较中,凸显出更多的形上色彩,区别于原始经验主义规范伦理学的“实”,呈现出“虚”的特点。然而,以同情的理解为前提来看,庄子思想整体上并不深入社会的维系,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体如何护养真性,从而不受外在刻意僵化规范的束缚。
四、余论
事实上,庄子并未明确探讨行为或实践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甚至对人的存在本身也并未提出确切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价,没有儒家“人最为天下贵”的论断。但在庄子看来,“乱世”起自“有为”,而“有为”所借以落实的是现实的既成社会秩序和规范。与之相联系,“逍遥”的秩序之维则体现为对既成秩序的突破、超越和本然秩序的回归。形式上来看,它呈现出一定的“返祖”和抽离的特性,但其实质在于以理想批判现实。其思想在哲学的支持上取得了通向具体现实的通道。其效能具有历史性、局限性,但其提示的反思维度和问题本身,仍不乏启示意义。
有必要指出,本然世界本身应当有别于已经被理想化并用以引导现实世界的理想之境。逻辑上看,本然世界本身一般被视为已经存在的本来如是的世界图景,同时具有“已然性”;如果不经过人类的认识和价值赋值(价值评价和理性化确认),仅是非人化世界的逻辑描述。庄子经过对现实世界的负面评价,进而将其形而上思考的成果理想化,即以一种本体论的世界图景的判分为前提,进一步在价值上判定本然世界的理想性和完善性,使其成为理想之境的理论表述。其中不免存在理想性和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未能对人类的现实实践做出考察。
此外,我们似乎也不能借“理想性”断定本然世界及其内涵的秩序同时具有“应然性”甚至“当然性”的内涵。因为对于人的日常行为或实践而言,本然世界的理想性,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方向的引导和审美的抒发,并不打算对具体的行为或实践产生实质性的控制和规范。与此相联系,“逍遥”更多地是以审美性的精神境界和实践智慧的形态显现并发挥作用。换言之,“逍遥”消解并超越着现实的既成规范,但同时自己却并不提供或很少提供某种现实的具体规范,表现出某种“虚”的特质。然而,区别于“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庄子悬设了人的“本真之性”。同时,以现实社会的既成性规范和制度作为对立面,“游”的此岸性保证了庄子思想不至直接滑向虚无。但不公开倡导虚无,实质却存在“走钢丝”的嫌疑。
庄子的思想内在地以“道”作为“逍遥”的界限,但对于“界限”本身的了解,庄子仅将其归入“道”的实践智慧,未能展开清晰的分析。也许这足以指导庄子及相应时代人的生活实践,但毕竟没有获得理性意义上更加深刻的把握,这就同时造成其思想本身的界限或局限。
[1] 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邓联合.“逍遥游”释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黄圣平.庄子论“待”及其意义[J].社科纵横,2011(6):363-365.
[责任编辑 王银娥]
Orderliness in Freedom and Ease
ZHANG Lei
(DepartmentofPhilosophy,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As an ideal form of life, freedom and ease, in relation to human practice, has the connotation of practical wisdom in Chuang-Tzu’s thought. Different from arbitrariness, on the basis of Tao a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Tao, with the liberation of authenticity of human nature as its content; behind the surmounting of reality to established specifications or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freedom and ease emphasizes the surmounting of splitting or cluttering, and the anticipation of unification and orderliness. Besides, it also recognizes the sidedness of the real world, highlights the premise of authenticity of human nature, describes the ideal of human society, and guides people to obtain the desired practical form, displaying the character of their practical wisdom.
Chuang-Tzu; freedom and ease; orderliness; authenticity of human nature
B223.5
A
1001-0300(2017)03-0104-06
2016-10-18
张磊,男,陕西富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以及道家哲学研究。